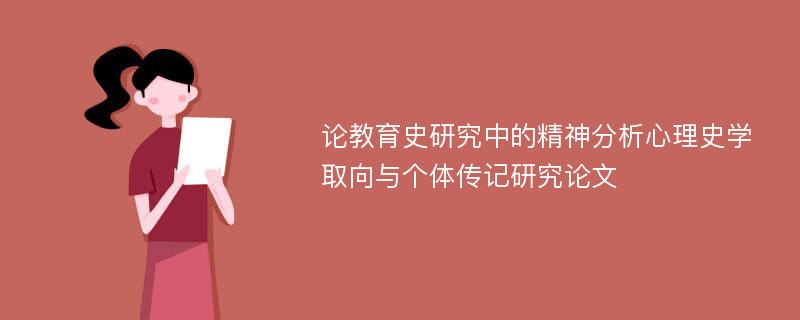
论教育史研究中的精神分析心理史学取向与个体传记研究
柯文涛
摘 要: 精神分析心理史学在研究方法上对教育史研究起着指导作用。随着这种“新史学”的不断深入发展,教育史学家逐渐将其引介至教育史领域,用于解决教育史上的“为什么”这一难题,深入分析教育人物的内心世界,从而形成教育史研究的精神分析心理史学取向。这一取向的典型代表是个体传记研究,在分析策略上它主张“研究你自己”(自传研究)和“研究他人”(他传研究),强调个体生命历程中发生的“重大事件”的影响,注重对童年史和家庭史的考察;在具体研究过程中则形成了“选择传主-暂定研究假设-搜集与整理史料-撰写传记”这一与传统史学大相径庭的四大研究步骤。
关键词: 精神分析心理史学;教育史研究;个体传记研究
史学方法论是从理论层面上对研究方法的研究,包括阐明研究方法的客观基础、本体基础、特点、功能、运用原则、局限等内容,在宏观上对教育史研究起着指导作用。在以往的教育史研究中,教育史学家主要解答“发生了什么”与“怎么发生的”两大问题;如今则更加关注“为什么”,即寻求历史事实背后的原因。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影响而诞生的心理史学在方法上为教育史研究提供了启示,能够有效地解释“为什么”这类问题,由此形成了教育史研究中的精神分析心理史学取向。而这种取向最为典型的代表就是个体传记研究。它主张采用心理学中的精神分析等方法对教育历史人物的心理特征和内在动机进行分析,以此弥补传统教育史研究的不足,从而深度解释教育史上的一些现象,汲取历史“事实”。
一、心理史学与精神分析的渊源
1900年,弗洛伊德的代表作《梦的解析》一书问世,其所创立的精神分析理论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轩然大波。该理论不仅对心理学、医学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对哲学、社会学、文学、人类学、电影学、政治学、教育学、历史学等人文社会科学也产生了深远影响。正如弗氏本人在《弗洛伊德自传》中写道:“自《梦的解析》一书发表后,精神分析学说再也不是纯属医学的东西了。当精神分析在法国和德国出现的时候,它已应用于文学、美学,以及宗教史、史前史、民俗学,甚至教育学领域。”[1 ]
虽说弗氏本人并非是历史学家,但他曾基于精神分析理论研究过历史,在史学界引起了一定的轰动。比如,在兴趣使然的作用下,他对达·芬奇这一历史人物进行了研究,并于1912年出版了德文版的《达·芬奇的童年回忆》(Leonardo da Vinci and A Memory of His Childhood )。一般认为,该书的出版标志着心理史学的诞生①,弗氏本人也被视为心理史学的创始人。在该书中,弗氏“以俄国作家梅莱兹考夫斯基所写的达·芬奇传记小说为依据”[2 ] ,尝试运用精神分析理论对达·芬奇的生平经历进行心理分析,从而探究达氏这个谜一般的全才式的杰出人物。在弗氏看来,达氏笔下画出的圣母之所以如此优美,与其童年的诸多经历不无关系。据考察,达氏本人是一位私生子,在5岁之前——一生关键的头几年里,他都与贫穷的、被抛弃的亲生母亲生活在一起,从小缺乏父亲的关爱,因此,他有时间感受到父亲的不在,自然格外依赖母亲。[3 ] 41正因为童年的种种经历,所以才使得他在以后的绘画中将圣母描绘得如此优美、庄重。在弗氏看来,达氏的经典画作《蒙娜丽莎的微笑》的原型就是其母亲的微笑。童年时期母亲的微笑深深地印刻在他的脑中,该画作也表达出他对母亲的怀念。通过对达·芬奇的分析,弗氏更加坚定地认为,“抽象的精神分析理论适用于史学文献,它是能够打开过去无意识心理的一种详尽而又聪明的分析方法”[4 ] 。虽说弗氏在分析达·芬奇时犯下了一些常识性的史实和理论错误,也由此受到史学界的批判和质疑,但弗氏主张使用精神分析理论研究历史却为史学研究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从这个意义上说,弗氏运用精神分析理论的方法策略进行历史研究的主动尝试远比该著作本身更为重要,“它标志着心理学与历史学相结合的方向和道路,预示了精神分析学说对史学研究的影响”[5 ] 31。
作为弗洛伊德继承者,新精神分析理论学派的艾里克森批判地接受了弗氏的精神分析理论,对弗氏的理论进行了修正和发展,即重视自我的关键作用,提出基于人格的“精神分析自我心理学”。艾氏认为,弗氏的精神分析理论过于强调本我和超我的作用,尚未充分地认识到自我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此外,在分析历史人物时,不能仅仅以性本能和性冲动来孤立地、片面地解释人物所有的行为,还须将社会、历史文化因素对历史发展的影响纳入考虑的范畴。因此,不论是唯性论、泛性论还是心理因素决定论,对于历史研究来说都是片面的。继弗洛伊德分析达·芬奇之后,艾里克森也试图运用改造后的精神分析理论分析马丁·路德、甘地等历史人物,并分别于1958年、1969年出版了《青年路德:对精神分析学与历史学的研究》(下文简称《青年路德》)和《甘地真谛:富有战斗性的非暴力主义起源》(下文简称《甘地真谛》)两本著作。在《青年路德》一书中,艾氏通过阐述路德的出生环境、童年经历、家庭、受到社会的影响,从而将其生命分为八个阶段。在艾氏看来,路德面临的自我同一性危机与当时的教会腐败和人们的宗教信仰危机不无关系。当路德于1515年成为一名牧师后,在修道院的静心沉思使得他摆脱了之前的自我同一性危机,并得到“第二次重生”,即产生新的自我同一性(新信仰、新思想)。正是在这种新信仰、新思想的指引下,路德才得以成为宗教改革的领袖。一般认为,“艾里克森的《青年路德》拉开了心理史学研究进入全新阶段的序幕”[6 ] 。与《青年路德》一样,在《甘地真谛》一书中,艾氏从甘地的童年生活与经历、与父母之间的亲子关系中寻找甘地的非暴力思想的来源,进而阐述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的主张并解释他的行为。艾氏认为,甘地在1918年领导工人罢工时产生了自我同一性危机,但在印度宗教的影响下,他克服了自我同一性危机,并产生了新的自我同一性,即行动的真谛——富有战斗性的非暴力主义。
除弗洛伊德、艾里克森等精神分析家尝试运用精神分析理论研究历史以外,同时期的历史学家也主张使用精神分析的方法研究历史,尤其是在美国。比如,美国历史学家巴恩斯(Harry Barnes)早在1919年就在《美国心理学杂志》上发表论文《心理学与历史》,以此来呼吁历史学家要关注心理学与历史的结合。[7 ] 美国史学家威廉·兰格(William Langer)也曾采用精神分析的研究策略对19世纪末英国的扩张进行分析,并于1935年著成《帝国主义的外交》一书。1957年,兰格当选为美国历史协会主席并发表了名为“下一个任务”(The Next Assignment)的演说,呼吁史学家采用新理论、新方法、新技术研究历史,即强调新的历史学。[8 ] 他所呼吁的新史学,不是信奉一般的、正统的心理学方法研究历史,而是采用弗氏的精神分析理论研究历史人物、历史现象,这就是其所认为的“下一个任务”。为此,他还主张史学界选派部分年轻的史学家去系统性地学习精神分析理论,以便使用该理论进行历史研究,从而深度阐释历史。
4.2 加强工程辅助措施技术的研究 由于消落带驳岸基质的不稳定性,工程辅助护岸措施尤为重要,虽然已有大量学者和专家们提出各种工程辅助措施,但均对驳岸有一定的坡度限制以及仅停留在辅助草本植物和低矮灌木扎根生存,能够不受坡度限制,与乔木相结合的创新型工程辅助措施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一些学术敏感意识较强的教育史学学者看到历史研究的心理史学动向,于是也开始将心理史学引介至教育史研究领域,并尝试使用精神分析等方法研究教育人物的心理特征和内在动机,从而形成了教育史研究的精神分析心理史学取向。比如,史学家章开沅和唐文权在研究教育家陶行知教育思想的过程中,就曾意识到心理史学对于分析教育家的人生经历具有重要价值。虽说心理史学存在种种不足之处,但对其视而不见抑或不予采用亦不可取。又如,胡志坚在其博士论文中探析了蔡元培、陶行知、黄炎培三位教育家的社会心理、行为特点。[14 ] 1虽然目前已有部分应用心理史学方法研究教育史的作品问世,但是这种方法仍被教育史学家鲜为提及。在精神分析心理史学取向中,个体传记研究又是其一大典型代表(精神分析心理史学研究一般可以分为个体心理传记研究与群体心理研究两大分支),它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身独特的分析策略与研究步骤。
二、教育史研究中的精神分析心理史学取向
第二步,暂定研究假设。所谓暂定研究假设,是指对所要研究的传主做出一个初步性的并且有待验证的判断,这个判断是一个未经证实的理论假说。如艾氏在研究青年时期的路德时就曾做过如下假设:“每个人在生命周期的青春时期,都用残存不忘的童年记忆和未来成年期的希望,为自己构造某种重要的观点和方向。”[20 ]
弗氏所著的《达·芬奇的童年记忆》被称为心理史学中的第一本个体传记研究著作,它与艾氏的《青年路德》一并成为“以后所有心理传记研究的典范”[15 ] 。此后的心理史学研究“热衷于传记研究的倾向,显然与弗洛伊德对达·芬奇的传记研究有关”[16 ] 。可以说,个体传记研究因弗氏而诞生,并在此后主导了整个心理史学领域。就教育史而言,个体传记研究旨在通过心理学理论(主要是精神分析理论)来分析、理解具有历史意义的个体,如教师、教育家、教育学者等,从而对其所作所为进行深度的、合理的解释。这不仅为教育史研究开辟了新视角,而且对教育史研究的深化发展来说具有积极的意义和价值。
由上可知,精神分析与历史学之间存在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弗氏所创建的精神分析理论能够弥补传统史学的不足,在解释“为什么”这一问题上有着独到的见解和强有力的解释,从而使得作为历史学与心理学相结合的产物——心理史学得以诞生与快速发展。而精神分析理论自然也贯穿于整个心理史学的发展历程。
语文学科具有较长的发展历史,而语文教学是我国教育中的一门重要的语言学科,学生通过对语文的学习,可以更加了解自己的语文知识,还可以提高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提升自身的语文应用能力。随着国家的现代化发展,在新课程改革的推进下,中学语文教学面临着巨大的挑战,需要加强对中学教学创新实践的重视和研究,不仅可以提高中学语文教学的质量和效率,还可以促进中学语文教学的良性发展。在义务教育阶段,语文是重要的学习科目。因此,提高教学创新实践能力对中学语文教学的意义不言而喻。
三、个体传记研究的精神分析策略及研究步骤
教育史作为历史学与教育学的交叉学科,具有双重学科属性,常常借鉴和吸收史学方法,自然会受到这种“新史学”的影响。此外,教育史研究与精神分析之间存在的若干相似之处也使得二者相互契合。其一,精神分析理论最初是弗氏用于临床精神治疗的一种医学策略,需要患者回溯过去的童年生活经历、家庭情况、突发性的重大事件等。这种在认识论上强调连续性和发展性的分析策略与教育史研究极为接近。其二,在精神分析理论中,家庭作为一个文化传递的组织而被精神分析学家所重视;而在教育中,家庭与社会、学校一样,同属于影响个体发展的环境因素,因此在研究教育人物时,也必须要考察其原生家庭,从而挖掘出家庭对人物的心理、人格、行为等方面的影响。其三,精神分析师在治疗患者时需要详细了解有关患者的一切资料,然后才能够对患者进行综合判断、原因阐释及后续治疗,这与教育史研究中的史料搜集、多原因分析问题相类似。由此可见,虽然精神分析学与教育史学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学科,但二者却因存在的诸多相似之处以及精神分析学能够弥补教育史研究的不足而走到了一起。
(一)个体传记研究的精神分析策略
第一,研究自己或他人。按照研究对象的不同,可以将传记研究分为自传研究与他传研究两种。自传研究主张从自身出发,使用精神分析理论“研究你自己”。没有人能比“自己”更加熟悉生命历程的种种,但这对同时拥有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双重身份的“自己”提出了挑战:一方面要熟知精神分析理论和历史学,并且知道如何使用;另一方面还要排除自身的主观刻板印象,将“自己”客体化为被研究的对象——他者。从目前仅有的几部教育史传记研究作品来看,大都属于他传研究,鲜有研究者进行自传研究。但是,这样的现状也不意味着他传就能够代替自传,自传有其自身存在的价值,正如胡适先生在《四十自述》的自序中提及的那样:自传能够帮助史学家寻找出历史事件的“心理的动机,幕后的线索和站在特殊地位的观察”[17 ] 自序2,还能够“给史学家做材料”[17 ] 自序3。可以说,自传研究与他传研究之间能够相互弥补不足,全面阐述有关传主的历史事实,从而推动教育史研究的深化发展。
第三,考察个体的童年史与家庭史。在精神分析理论看来,个体的童年经历和家庭生活会影响其一生,直至生命的终结。心理史学家也确信,童年时代的经历和家庭环境对人的个性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所以他们一般都十分重视对“养育方式、家庭模式、童年和青年的社会化的研究”[18 ] 。这与强调个体生命历程中的“重大事件”存在重合之处,有些“重大事件”正是发生在个体的童年阶段和日常家庭生活中。因此,心理史学家或精神分析学家常把童年史和家庭史的研究内容融入传记研究之中。
4.实现经营管理决策的信息化。建设生产经营一体化平台,实现各个层面、各项生产经营指标数据从采集到数据审核入库、数据处理、综合分析、文件归档等整个生产经营管理过程的网络化、集成化和智能化,做到 “同一平台、信息共享、多级监视、分散控制”,提高信息资源的综合利用率,使发生的费用都能在第一时间在信息平台显现,确保对投资项目运行情况、财务资产运行情况、物资材料运行情况等生产经营情况的实时监控。同时,完善综合信息查询、预警功能,实现生产经营指标数据的同比、环比、横向对比、纵向对比功能,做到自动预警、自动跟踪,使问题透明化,解决公开化,实现经营管理的数字化、生产经营趋势把握及决策的科学化。
第二,强调生命历程中的“重大事件”。在精神分析理论看来,父母的离异、父爱或母爱的缺失、地震、惊吓、车祸、火灾、某次考试不及格、体罚、触电、溺水、校园欺凌等生命历程中发生的“重大事件”都会对个体的人格、性格等心理方面产生不可预估的潜伏性影响。需要说明的是,这些“重大事件”并不一定是社会意义上的具有广泛影响的重大事件,也许仅是他人眼中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但却是对传主本人产生深远影响的、使其刻骨铭心和难以释怀的,并将其隐藏于潜意识下试图掩盖或不愿为外人所知的事情,具有个体独特性和差异性。因此,挖掘个体生命历程中的某些“重大事件”是个体传记研究的重要分析策略之一。这为寻求个体某些行为背后的原因提供了解释依据,即解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行为,从而更好地理解传主本人。
(二)个体传记研究的步骤
作为精神分析心理史学的典型代表,个体传记研究与传统教育史学研究存在明显的差异。从研究过程来看,传统的教育史学研究一般倾向于先搜集大量的史料,然后进行分类、整理,梳理出历史的脉络从而进行有关研究。但是,个体传记研究却是先确定研究的传主,然后确定与传主有关的问题并进行大胆的研究假设,最后用史料来验证假设正确与否。按照传记研究的特点,可以将其研究步骤分为“选择传主-暂定研究假设-搜集与整理史料-撰写传记”四步。
第一步,选择传主。任何研究都始于好奇,但好奇心终究是短暂的,只有研究兴趣才能够帮助研究者持续深入研究。因此,在进行个体传记研究前,一定要选择好研究的传主,即自己感兴趣的人物。另外,不要选择那些特别喜欢、崇拜或厌恶的传主进行研究,因为这会在研究中增添个人价值情感,难以做到价值中立,从而影响研究的结论。换言之,在探讨传主的主观世界时,一定要正视自己的研究动机。比如,弗洛伊德之所以选择研究达·芬奇,是因为对他感兴趣。在弗氏看来,达·芬奇被其同时代者誉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最伟大的人物之一”[3 ] 2,但他本人一直以来都是谜一般的存在,无人知晓这位全面的天才在其神秘面纱的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真实面貌。弗洛伊德曾在1898年10月9日致弗里斯的一封信中提到过他对达·芬奇的兴趣由来已久,“或许最著名的‘左利手’就是达·芬奇,没人知道他有过任何的风流韵事”[19 ] 。而直接促使弗氏研究达·芬奇的原因则是在一次偶然的接诊过程中,他发现了一位与达·芬奇拥有同样身体结构但并无达氏天分的病人,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撰写出了《达·芬奇的童年记忆》这部个体传记研究的著作。
此外,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钢琴四手联弹作品集》也是一套不错的四手联弹曲集,这是依据时代风格进行分册的一套作品,也已由国内引进出版。现有《巴洛克时期作曲家钢琴四手联弹作品集》《古典主义时期作曲家钢琴四手联弹作品集》《浪漫主义时期作曲家钢琴四手联弹作品集》《英国作曲家钢琴四手联弹作品集》。
心理史学最先应用于历史研究中,而后才被教育史学家引介至教育史研究领域。在兰格等人的号召下,以及艾里克森的《青年路德》一书发表带来的影响下,心理史学得以迅速发展,有关心理史学的作品也逐渐增加。据统计,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80年代,“整个西方主要用英语出版的各种心理史学著作至少有1723种,其中包括书457部,文章1131篇,博士论文135篇。”[5 ] 70西方历史学家运用心理史学研究的对象也是五花八门,不仅包括凯撒、林肯、拿破仑等政治人物,而且像达尔文、卢梭、尼采、托尔斯泰、梵高等文学家、艺术家、哲学家也在被研究之列,甚至连心理史学创始人弗洛伊德本人以及代表人物艾里克森等也都成为被研究对象。“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我国大陆学者开始接受并使用心理史学这一新的研究方法”[9 ] ,他们研究的对象也十分庞杂。比如,马良怀基于新精神分析学派代表人物、个体心理学创始人阿德勒所创的自卑与超越理论,探析了曹操[10 ] 以及其他皇帝[11 ] 的自卑心理及其超越;陈雪良基于精神分析心理史学对司马迁的人格及其创作《史记》的行为动机进行了探究[12 ] ;赵良采用精神分析心理史学策略对中国历史上七位皇帝的行为进行了传记研究[13 ] ;等等。
第三步,搜集与整理史料。确定研究的传主以后,史料的选择就成为研究的关键,拥有足够的史料尤其是一手史料往往是保证研究深度的重要前提。这些史料包括:日记、自传、回忆录、传主所写的文章与书籍、草稿、口述等一手史料;他传、他评、他述等二手史料。此外,传主的档案、手稿等也是重要的史料。若所要研究的传主仍活着,对其进行访谈无疑会有很大的收获;若传主已逝,对其亲朋好友进行访谈也将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胡志坚在其博士论文中使用心理史学对蔡元培、黄炎培、陶行知三位教育家进行心理分析时,就“以日记、自传和传记、论著为主,其他史料加以佐证”[14 ] 13。胡志坚认为,“历史人物心理特点的研究,首选的史料应该是人物的日记、书信,因为日记和书信最为及时和真实地反映了研究对象那时、那地、那刻的心理活动,较少出现因‘社会赞许’而产生的偏差;其次是自传和传记,因为自传能比较系统、全面地反映研究对象成长和发展的历程;再次是论著”[14 ] 14。
第四步,撰写传记。开始撰写传记就表示已经能够对研究假设进行评估,并能够就个体生命历程中发生的那些非比寻常的事件做出解释。在组织材料并解释的过程中,并非是像弗氏那样抛弃文化、社会等其他因素,夸大心理因素的作用,而是要综合考量。在撰写个体心理传记的过程中,需要对个体生命历程中的某些重要事件做出解释。解释的类型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属于因果解释类型,主张通过挖掘个体童年时期发生过的重大事件来解释个体日后的行为。弗氏对达·芬奇的研究解释就属于这种。第二种属于格式塔类型,即强调整体性的分析与解释,从纷繁复杂的文献资料中寻找出“格式塔”。近年来,我国郑剑虹等学者提出了第三种解释模式,即质量结合的解释模式。该模式强调对传主人格的精神分析和对重要问题或行为的阐释[21 ] ,从而将其生命历程叙述为一个完整的故事。
注释:
应该怎样与这样的老头儿相处?阿尔诺总结出来的经验是:因为疾病,父亲再也不能从桥那头走到我这里来,因此,我必须走到他那里去。他给父亲起了个绰号叫“流放的老国王”,他据此来解释父亲没完没了的回家欲望,他的不安全感,他认识上的混乱,以及他的茫然无措与孤苦无依。阿尔诺说:但是,作为亲人,我们别忘了被流放的国王,也是国王。
①实际上,在弗洛伊德创建精神分析理论之前,狄尔泰等研究者就已经开始尝试运用心理学的研究方法研究历史人物与历史现象,但这种非精神分析理论的正统心理学的研究成效不大,也未引起学界注意。因此,学界一般将基于精神分析理论的历史研究视为心理史学的开端。
1.5.3 导管固定敷料选择不当 敷料的黏性、抗菌性、经济性通常都是考虑的范围,相对来说,自黏性较好、透气性较强、不易产生皮肤过敏的无菌敷料是首选。
参考文献:
[1 ] [奥 ] 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自传[M ] .顾闻,译. 辽宁: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87.
[2 ] 朱立元.美学大辞典[M ]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0:696.
[3 ] [奥 ] 弗洛伊德.达·芬奇及其童年的回忆[M ] .张杰,张明权,张璘,译.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
[4 ] [美 ] 大卫·斯坦纳德.退缩的历史——论弗洛伊德及心理史学的破产[M ] .冯钢,关颖,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9:14.
[5 ] 罗凤礼.历史与心灵:西方心理史学的理论与实践[M ]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
[6 ] [美 ] 查尔斯·B·斯特罗齐尔.领袖——一项心理史学研究[M ]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3:67.
[7 ] Barnes H E. Psychology and History:Some Reasons for Predicting Their More Active Cooperation in the Future[J ] .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1919, 30(2):337-376.
[8 ] Langer W L. The Next Assignment[J ]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1958, 63(2):283-304.
[9 ] 陈曼娜.二十世纪中外心理史学概述[J ] .史学史研究,2003(1):61-69.
[10 ] 马良怀.曹操的自卑与超越[J ]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3):85-89.
[11 ] 马良怀.皇帝的自卑心理透视[J ] .河北学刊,1993(1):95-100.
[12 ] 陈雪良.司马迁人格论[M ]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13-20.
[13 ] 赵良.天子的隐秘:七位中国帝王的心理传记[M ]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4:1-7.
[14 ] 胡志坚.自我统摄下的心理与行为:蔡元培、黄炎培和陶行知的社会心理与行为特点研究[D ] .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5.
[15 ] Lichtenberg J D. Freud's Leonardo: psychobiography and autobiography of genius[J ] .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analytic Association, 1978, 26(4):863.
[16 ] 赵良.帝王的隐秘:七位中国皇帝的心理分析[M ] . 北京:群言出版社,2001:序言1.
[17 ] 胡适.四十自述[M ] .长沙:岳麓书社, 1998.
[18 ] 王岩,尹英杰,孙华. 西方史学之路[M ]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9:223.
[19 ] [奥 ] 弗洛伊德.达·芬奇的童年回忆[M ] .刘平,译. 北京:九州出版社, 2014:英文版导言97.
[20 ] Erikson,Erik Homburger. Young man Luther:A study in psychoanalysis and history[J ] . Psychosomatic Medicine, 1959,21(3):261-262.
[21 ] 郑剑虹,李文玫,丁兴祥.生命叙事与心理传记学(2013)[M ]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4:49.
On the Psychoanalytic Psychological History Orientation and Individual Biography in the Study of Educational History
KE Wentao
Abstract: Psychoanalytic psychology plays a guiding role in the study of educational history in research methods.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this “new history”, educational historians gradually introduced it to the field of education history, used to solve the “why” problem in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and deeply analyzed the inner world of educational figures,thus forming a history of education.The psychoanalytic orientation of psychology is studied. A typical representative of this orientation is the study of individual biographies. In the analysis strategy, it advocates “researching yourself”(autobiographical research) and “researching others” (biographical research),emphasizing the influence of “major events” occurring in the life course of individuals,and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investigation of childhood history and family history.In the specific research process,it has formed the four major research steps that are 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 historiography,“Selecting the Master - Tentative Research Hypothesis -Collecting and Organizing Historical Materials - Writing Biography”.
Key Words: psychoanalytic psychology;educational history research;individual biograph research
中图分类号: G5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6762(2019)03-0064-06
收稿日期: 2019-03-19
作者简介: 柯文涛(1995-),男,宁波大学教师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浙江宁波,315211)
*本文系宁波大学2018年度SRIP项目“王阳明的教育生活史研究”(项目编号:2018SRIP0327)阶段性研究成果。
(责任编辑 于小艳)
标签:精神分析心理史学论文; 教育史研究论文; 个体传记研究论文; 宁波大学教师教育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