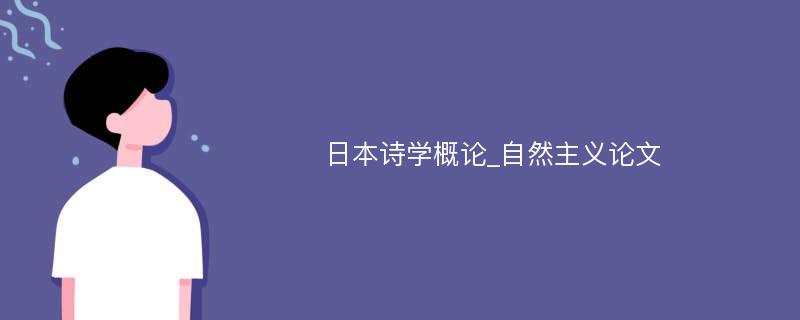
日本诗学概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学论文,日本论文,概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任何国家文学的发展都是个动态的过程。域外文化与本土文化的交融、碰撞,产生多种不同力的矛盾。文学融合本身就是矛盾的运动。研究日本诗学既离不开中日文学关系,同样也必须抓住“日本近代文学乃至近代思想的最大问题之一是东西两洋如何调和,或者说交融的问题。”[1](P15)同时,在日本文学史上,“歌学”“诗学”并用。一般说来,把写作和歌者称作“歌人”,研究其理论称作“歌学”;对写汉诗和自由诗者称作“诗人”。在这里,日本诗学既包含日本原初的诗学理论,也涵括吸收中、西诗学之后的诗学,因为在任何国家的文学发展历程中寻找所谓“纯粹”的东西只能是一厢情愿,从广义上讲,任何民族文化都是“杂种文化”。
1、古代和歌及歌论中的日本诗学 “和歌是日本文学的主流。”[2](P23)日本最早的典籍《古事记》(成书于712年)、《日本书记》(成书于720年)的歌谣和《万叶集》(最后成书于753-759)、《古今和歌集》(成书于905年)的和歌里体现了日本的古代诗学。在《万叶集》中的端词(词书)、左注、小注中阐发了歌学的具体内容,特别是在左注里频频显示出它也是口承文学的渊薮。《古今和歌集》的两篇序,即纪淑望(?-919)的真名序、纪贯之(?-945)的假名序,是日本诗学的开篇作,它对后来日本诗学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它的意义在于:
(1)在吸收汉诗学基础上确立本民族诗学自觉。在《古今和歌集》问世前,称作“国风暗黑时代”,即汉诗繁盛,和歌缺乏生气的时代。为了对这“暗黑”的反拨和摆脱,“复兴新的和歌时代而出现了《古今和歌集》”。[3](P113)从宇多天皇6年(864)正式废止遣唐使以后,是汉文学本土化的重要阶段,即深入消化中国文学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产生的日本诗学带有融合中国文学之后的本民族文学的自觉意识。在《古今集》真假名序中均强调和歌是“动天地,感神祗,厚人伦,成孝教,上以风化下,下以讽刺上”[4](P679)的精神。这与我国古代《诗大序》的内含是相通的。在不少歌人的创作中儒道释与日本本土宗教思想交汇在一起,如山上忆良既崇尚佛教的“无常”,也力倡儒家的“周孔之垂训,前张三纲五教”的伦理。在不少和歌中表现神灵不灭,超越生死,与后来的佛教的轮回思想浑融在一起。同时,在文学形式上《万叶集》亦受《文选》、《文心雕龙》的影响,建立了最初的日本诗学中的文体学体系。创立了以奇数为中心的短歌形式为根本的日本和歌形态。久松潜一指出:“短歌形成并成为日本诗歌中心歌体的过程就是文学意识发生和形成的过程。即短歌的确定,显示了统一的美意识的产生。”[5](P39-40)
(2)古代诗学理念“真”(まこと)、“ぁかし”、“きょし”、“さゃけし”(“清明”、“清净”)。“真”是“置于万叶中心的上古的理念,在近世则有贺茂真渊非常鲜明地指出了这一点。”[2](P206)所谓“真”是不加矫饰地非理性地自然流露和表白。显然,对“真”的理念的界定并非产生于口承文学时代,它是近世以后的发现。在《万叶集》中,保存着一批口承文学时代的口头作品,它明显地体现了上古日本尚未步入文明、理性阶段的初民纯朴的思乡的回归情结。在步入文明大道之后,面对尘世的纷扰,不免留恋集体无意识中的心灵故乡,这“真”乃是对初民真实、朴素的认可与憧憬,也是对现时的理想。“真”以日本本土固有的神道精神为根柢,因为神道以诚(まこご)为本。日本歌学的最早理念体现了人类返朴归真的思乡情结,这也是其文学理念的核心。
在上古时代,日本歌学的理念还有“ぁかし”、“きょし”、“さゃけし”用汉字标记写作“清明”“清净”,它们不仅是远古对神、皇室之情,也是对天地自然万物的心态。人们通过视觉、听觉通感于心,形成“清澄”感,这也是从《万叶集》中反映出的日本诗学内含之一。
(3)同时,在论述日本古代诗学理念时,应把《古事记》至《古今和歌集》中体现的理念联系起来作为一个整体把握。由于日本文学受中国文学影响之早之深,其本土化过程的复杂,不应机械地剔抉内与外。为此有的文学史家(如著名和歌研究家阿部正路)把《万叶集》与《古今集》的诗学(甚至联系《古事记》)统一考虑是很有见地的。[3](P123-124)
(4)奈良时代日本诗学成就辉煌。藤原滨成(724-790)的《歌经标式》(772)是日本第一部和歌评论著作,这是一部借鉴中国诗学的集大成之作。该书结合日语发音特点,旨在音(韵)、形(态)、意三者辩证统一,对和歌作出规范。他指出“和歌七病”,针对和歌盲目套用汉诗的艺术形式作了匡正。
空海(774-835)于810-820年间写成的《文镜秘府论》使作者享有日本诗学宗师的盛誉。该书在日本是与刘勰《文心雕龙》相媲美的空前巨著。《文镜秘府论》“距日本现存的首部汉诗集《怀风藻》问世仅相差70年,《怀风藻》时代只不过是日本人模拟、探索汉诗创作的初级阶段,而在半个多世纪之后空海借助中国人的研究成果,就开始系统地评论诗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质的飞跃。”[6](P293)他所援引、研究的中国诗学著作之多叹为观止,因有另文论及,这里不再重复。这部巨著在日本诗学上的贡献是巨大的。如在本书关于“言”、“意”关系的论述,对深入理解语言、文字之间的关系作了深刻阐发。他强调“意须出万人之境,望古人于格下,攒天海于方式。”(《文镜秘府论》)这里论述的不仅仅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显然他吸收了陆机《文赋》中的“罄澄心以凝思,眇众虑而为言,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7](P147)和《文心雕龙》中“神用象通,情意所孕。物以貌求,心以理应。刻镂声律,萌芽作兴。结虑司契,垂帷制胜。”[8](P253-254)而作出了创作要依靠语言又要超越语言的思考。
2、《源氏物语》体现的日本诗学 紫式部(978-1015)创作的《源氏物语》(1001-1008之间)作为日本古代物语代表作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杰出的,从诗学上来说也是崇高的。它不仅强调了文学的“虚构性”,而且在这部作品中的“物哀”(もののぁゎれ)和关于“物语”的议论,被后来的著名国学家本居宣长(1730-1801)看作是《源氏物语》的本质,也是日本文艺的本质。对于“物哀”至今无论在中文对译或理解上皆见仁见智,有必要通过对原典的重新考察来探究其内含。我们可集中从作品里紫式部借源氏对玉曼等在梅雨天耽于写配画故事而引发的一番话而阐述重要的诗学论(见“萤”卷)。
“啊,真讨厌啊!你们这些女人,真不怕心烦,都是专为别人欺骗而生的。明知这许多绘图故事中真的很少,还一个劲地当作真的为之心动,在这闷热的梅雨天,头发乱了也不顾,只管一个劲地写。”
但是,源氏说罢笑起来,又改口说:“但是,这也不怪你们,不看这些过去的故事,恐也没有他法排遣郁闷,清除寂寞。而且这些瞎编的故事里,也颇像真的似的,看了让你心伤(ぁゎれ),明知是些无稽之谈,却颇为合情合理,使你不得不心动。看过可怜的住吉姬的忧愁故事,不禁情同身受。又有一种故事,读时就觉得无聊,小题大做让人心惊目眩,但是,过后冷静一想,虽然生气,可是却出奇地引人入胜。”[9](三册,P48-50)
对于“ぁゎれ”和“もののぁゎれ”,本居宣长精辟地概括说:“‘这些瞎编的故事,也颇像真的似的,看了让你心伤(もののぁゎれ)’是源氏物语的眼”。“这一物语是以向读者揭示物哀(もののぁゎれ)为宗旨而写作的。”他在《石上私淑言》中论述道:“我国则万事自在,不受羁绊,不自明贤明,故不烦道人善恶,唯将发生之事原样写出,其中歌物语等,乃特以物哀为主旨,将好色之人之诸情诸意,如实从容写出者也。”[4](P781)
这里的“もの”是“ぁゎれ”的对象,“ぁゎれ”本意是叹息之声,简洁地说“物哀”乃是“触物显情”。物哀是由对象引发的感动,这里客主融合为一体,这种感情不是激情,是沁人心田的抒情,“总之,那种沁人心脾的悲哀感占据主要地位。”[2](P217)本居宣长所揭示的“物哀论”,“把中世以《源氏物语》为代表的诗学从佛教、儒教的观点,即宗教、道德立场中解放出来,把人的自然的感情、感动作为支点。”[2](P218)把文学作品与宗教区别开来,以表现人的自然感情、感动,是文学本身的回归。在这里有必要把日本歌学中文学与宗教的关系稍加详细论述。人与宗教的关系是反映在日本诗学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钦明天皇13年(552)佛教传入日本[10](P17),在古代日本社会产生巨大影响。在相当长时间里佛教思想曾覆盖文学及生活的各个层面。日本歌论经过长期的探索,使文艺摆脱附庸于佛教的地位,这是文学自觉的体现,是向文学本质的回归。有的研究者通过“歌道”的形成过程论述了这一问题。文学与宗教既有相通之处,又存在矛盾。日本人成功地借鉴了白居易的“狂言绮语观”“发展成歌道佛道一如的理论”。[11](P97)借鉴白居易的“愿以今生世俗文字之业,狂言绮语之过,转为将来世世赞佛乘之因,转法轮之缘。”古代日本人把和歌与佛道统一起来,“和歌佛道全无二”(《正彻物语》)这就是把它转化为“道”,一种精神修养,之后再使它既不违背佛法又有独立性,起净化心灵的作用。稍稍熟悉日本文学的人都会感到强烈的“四季感”,这就是“飞花落叶”,乃是从自然触发的对人的终极关怀。同时和歌诗学中非常强调抒情性,心灵的净化,沁人心脾,这在《源氏物语》中得到了突出体现。
3、中世至近世的日本诗学 从12世纪末至17世纪初约四百年间,日本经历了镰仓幕府至日本南北朝、战国时代,一直到安土、桃山时代。这是个动乱的岁月,不安的年代。不仅贵族、武士、僧侣感觉到荣枯衰盛的无常,连庶民百姓也直面世间的无常。求得宗教救济成为时代风尚。净土宗、净土真宗、时宗、日莲宗、禅宗,这些新兴佛教从贵族到庶民其影响无孔不入。逃避动乱,一心追求构筑美的艺术世界,成为文学的时尚。“幽玄”、“余情”成为诗学的重要理念。
(1)“幽玄”最早见于《古今和歌集》真名序“或事关神异,或兴入幽玄。”但是它成为和歌的最高理念,使之确立为歌风者是藤原俊成。藤原俊成(1114-1204)的《古来风体抄》(1201)至正彻(1381-1459)在《正彻物语》里说:“如此行云白雪之体,如风吹雪花飘然去,雾霭蒙蒙尤见花。情趣无限,飘白无瑕难以言状,此为无上之歌也。”对于“幽玄”众说不一。从广义上说是含有“优”、“艳”、“哀”、“不安”、“高迈”等含义,是种余情象征。狭义说是与“优”、“艳”、“高迈”并列而且与之有区别,是“闲寂”“哀”的静淡出寂的姿态。有的文学史家(如久松潜一)认为“幽玄”综合了“优”、“高迈”、“哀”等要素,这是很有见地的,后来时代的诗学的含义往往对以前的歌论重新整合,同时它体现了日本歌论力图超越语言、文字的局限,更深入表现人情感,指向象征的世界。“幽玄”后来在世阿弥(1363-1443)的《风姿花传》(1400)中进一步弘扬,现代作家川端康成得其神髓。
(2)从镰仓时代后期至整个室町时代,以五山禅林为中心而创作的汉诗文(包括诗学)被称作“五山文学”,它是日本中世文学的主流,是研究日本文学的重要方面。因为五山文学在中国禅宗影响下,经历宋、元、明的持续影响,是吸收中国文学的烂熟期,五山文学(包括诗学理论)具有不可忽视的多重价值。从诗学方面来看,我们需要提及的是虎关师炼(1278-1346),他师承一宁(字一山)的《济北集》中的诗话。弘扬朱子学,强调“诗赋以格律高大为上,诗贵熟语贱生语。”五山文学废骈俪体,主散体,以“复古”为旗帜,振兴日本汉文学适应时代发展。
(3)国学复兴与向近代迈进。文学史家把日本16世纪起始的“国学复兴”称作日本的文艺复兴。它与我国明代中期的拟古运动、17世纪欧洲古典主义产生时间相近,有着共通的规律。所谓“复古”并非简单地袭旧,实则是适应时代发展,解决继承与创新这一重大课题,其中很重要的是发掘出本民族文学传统中的核心理念,使古代文学作品和论述“经典化”。研究日本诗学(特别是比较诗学)理应把它作为重点。日本进入町人社会以后,已具有资本主义的萌芽,对于“人性”的关注,“以町人文化为代表的近世文化与中世文化的最大区别之一是人性的恢复。”[12](P117-118)以契冲(1604-1701)、荷田春满(1669-1738)、贺茂真渊(1679-1769)、本居宣长、平田笃胤(1776-1843)为代表的理论家们高举“复古”旗帜,通过对日本古典的发掘,使一些能适应时代的诗学理论经典化,扫除儒教、佛教对文学的束缚。主要表现为:弘扬以“真”为核心的文学本体论,反对以教戒为目的的儒佛观。契冲在《源注拾遗》中明确反对将《源氏物语》与《春秋》等同视之,同时主张人情的真实是文学的最高意义。如本居宣长对《源氏物语》的论述。他在《〈源氏物语〉玉小栉》中说:“物语中人情与行为的善恶是什么?一般说来,是知物哀。以有人情、顺乎世态人情者为善,以不知物哀、寡情,不顺乎世态人情为恶。”这与儒教、佛教的劝善惩恶是根本不同的。而且,复兴国学也确立了文献学研究方法,这与后来的民俗学研究密切相关,是从文化背景上探讨日本文学传统的必然。同时,我们也应注意这一时期的复兴国学也与后来的带有鲜明政治色彩的日本国家主义不无联系。
(4)传统并非是一成不变的东西,这一时代的日本国学复兴为日本民族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进入近代作了必要的准备。近年日本文学研究家在探讨明治时代文学理论时,已重新对日本文学的“近代性”进行探讨,用最简单的一句话来概括:在西方文化洪水般涌入之前,社会正孕育着巨变,一个理念已在生成,它首先是以“复古”的面貌出现的,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课题。
进入近世,町人社会的发展,随着江户时代儒教道德的普遍化,也必须在文学世界体现出来。为此“义理”和“人情”成为町人文学的两个主要方面。在市民文学占主流的江户时代,一方面要表现“义理”,同时面临儒教的衰落,出现了表现“人情”(个人情感世界)的倾向。尤其是在表现女性为主的“人情本”中体现得最充分。“义理、人情乃是近世町人文学的中心理念之一。”[2](P233)义理被抑制,人情取得胜利,越来越向反映人的本能方面的“情感”倾斜。诗学(歌学)的理念其实也是时代的感觉,如“ゎび”、“さび”(恬静、闲寂)是贯穿于西行的和歌、宗祗的连歌、雪舟的画、利休的茶道之中的理念,它贯穿人生无常感,华丽的外表中的艰涩,有种以纯艺术超脱的孤高感。
4、明治以来百年的日本 诗学早在明治维新(1868)之前,日本已开始与西方文化接触交流,作为标志性事件当然是明治维新。从此,作为东方岛国的日本始终处于与西方文化碰撞的前沿,其中是非曲直对我国特别具有参考价值。
(1)以森鸥外、夏目漱石为代表的“两条腿走路”(森鸥外语)既立足民族文化传统,又积极吸收西方文化的态度,成为主流。至大正年间的芥川龙之介亦在《僻见》中说:“近代日本文艺横的是模仿西方,纵的则是植根于日本土壤,志在表现自己的独立性”。坪内逍遥(1859-1935)的《小说神髓》(1883-1885)破天荒地提出“小说是艺术”的观点,主张小说模写“人情”为主,在日本文学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这部开山作一方面反映在西方科学为中心、进化论影响下日本诗学对西方文化的接受,同时也可以看到坪内执著江户文学,植根日本传统文化的一面,他是“处在日本近世与近代境界上的人物。”[13](P252)
明治时代日本诗学一个最大问题是在什么语境下发展自己的理论。吉田精一说:“说起日本的近代化,在江户时代、明治以后甚至到今日乃是西欧化的同义语。”但是他同时提醒人们:“因明治维新而与传统断裂这一看法是不正确的。”[14](p6)在西方上百年形成的文学思潮不问时序地纷至沓来,在日本也产生了所谓启蒙主义、自然主义、浪漫主义、唯美主义、普罗文学、新感觉派等等。我们可以自然主义、私小说为例看日本诗学的一些规律性问题。
从19世纪末至1912年,日本文坛占据霸主地位的是“自然主义”文学。中江兆民和森鸥外是最早介绍法国自然主义的理论家。小杉天外在《流行曲·序》中说:“自然就是自然,无所谓善,也无所谓恶,无所谓美,也无所谓丑,只不过是某一时代,某一国家或某一个人捕捉自然之一隅,给自然强加了善恶美丑之名而已。小说也可以说是思想上的自然,其善恶美丑均可描写,不可设下不可描写之羁绊。”[15](P45-46)他的《初姿》可以说是左拉《娜娜》的模仿物。永井荷风则在《地狱之花·跋》中说:“人确实有摆脱不了的动物性的一面,”“作家有向黑暗的一面特别研究之必要。由于祖先的遗传和境遇所产生的情欲、暴力、暴行等事实应毫无顾忌地写出来。”[15](P47)上述观点显然取之于左拉的自然主义理论。但是,日本自然主义的形成与发展不可能完全等同域外文化,它的本土化过程显示了一个民族在接受外来文化时的过滤、选择。日本经过甲午战争(1894-1895)使它跻身于资本主义列强之列,赶超西方形成新的热浪,此时恰值日本文坛浪漫主义活跃时期。但是在这种狂热中至少有些优秀作家能从时代的盲目中挣脱出来,起着时代批判的作用,它的显现是自我意识的突现。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批判,可以说日本自然主义(特别是后来的私小说)是“日本作家自我意识受挫后向另一极端发展的产物。”“是主观主义和感伤主义的刻印,逐渐开始以私小说这种形式形成与之相应,社会批判要素——或类似东西的存在开始消灭。”[16](P626)概括起来说,日本自然主义诗学产生的基础是科学主义、进化论,“不科学即不真实,为此,不真实的东西就应该被否定,这一点与法国自然主义十分相似。”[17](P78)但是,正如中村光夫所说“《棉被》的创作动机如果以跳跃式的话来表述,乃是作者个性的直接表现,这是日本文学主流和歌的形式在小说上的强用。”自然主义(私小说)作家多为诗人出身,日本的自然主义带有明显的浪漫主义色彩,是区别于西方的,所以他又说:“表面合体的衣裳在今天看来是超过想象的接近西方的现代化,而传统只是在背后支持了它。”[17](P81)
为此日本的自然主义(私小说)作品在西方人看来是反小说(因为它反对虚构),接近“随笔”(essay)以自我“告白”形式写出的作品,是自叙传(Icb-Roman)。这与日本自然主义文学时代的作品、作家、读者关系密切相连。那时自然主义作家在文坛建构的“文学者天国”,即在狭窄的精英文学圈内保证它的地位,不是在量上,而是在质上,只有在圈内承认才有地位,而且圈里的价值观与社会不同。为此,当时自然主义作家具有独领风骚的地位。
同时,从明治后期至日本战败以后,日本文坛经过数次向日本传统的回归,在一些作家(也是理论家)身上反映了这一轨迹,尤以谷崎润一郎(1886-1965)最为典型。被称作唯美主义作家的谷崎,在明治、大正年代,在东西文化激烈碰撞的历史时期曾醉心于西洋文化,并深受影响。但是,随着时代发展,对西方文化的消化、反思,日本文化传统和已成为精神底蕴的中国文化的乡愁使他产生向传统的回归。他在《谈中国趣味》(1922)中说:“说起中国趣味,单是说趣味这话似乎无足轻重,但是它意外地与我的生活有着不解之缘。当下我们日本人几乎对全部的西欧文化兼收并蓄,看起来像是被其同化了。但是,我们的血管的深处被称作中国趣味的东西,仍然是意想不到使人吃惊的根深蒂固。”[18](P81)
另外,在日本近代诗学中也反映出由于历史的原因,与中国文化的断裂引起的误读,这也反映在日本近代诗学观上,在一些诗学中存在着日本的“东方学”。这更提醒中日两国学者应该在全球化文化背景下全面研究中日比较诗学。
5、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日本诗学 从20世纪80年代在全球化语境中,在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影响下,日本诗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呈现多元化态势。其实早在60年代随着新批评理论、接受美学、读者反应批评理论传入,长谷川泉的《近代文学批评法》就以作家、作品、读者三契机建构了新的文学批评模式。[19]在70年代后期前田爱的《都市空间的文学》开拓了新的文本批评,成为“日本近代文学研究上一件划时代的事情。”[20](P240)用前田爱本人的话来说:“是追随符号学、现象学成果,按自己的想法对日本近代的历程,对都市的来龙去脉进行了回顾。”是对以往文学理论中“拘于作家主体和自我中心化的死胡同的突破。”[21](P580)
随着利奥塔、福柯、德里达、德勒兹、哈桑、拉康、西方女性主义文学、赛义德后殖民主义等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的译介、研究,日本诗学发生了更为突出的变化。用日本文学界的话来概括称之为“‘跨学科跨文化的’文学批评”成为当代日本比较诗学的突出特征之一。近年涌现的一批理论家具有代表性,如柄谷行人(1941-)、龟井秀雄(1937-)、小森阳一(1953-)等。
纵观当今日本诗学最主要特点似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1)对明治维新以来在西方话语影响下“自明”成见的反思与再认识,克服形而上的思维模式,特别是对“近代”、“近代性”、“近代史”的再认识令人耳目一新。柄谷行人在《日本近代文学的起源》一书中强调要把“日本”、“近代”、“文学”的起源都加上括号,从“起源”上对日本近代文学的自明性提出质疑,在被颠倒的事物现象中观察深深隐藏起来的“起源”。小森阳一亦指出“在新闻界概念随意流行的背景下,称作‘近代’的概念就会有了极为流通的方法,在文学研究领域里,‘近代’这一概念是一种花言巧语,是起着给某作品、某作家以特别好的权威贴标签的机能即是所谓‘近代’”。[22](P64-65)龟井秀雄的《明治文学史》(2000年,岩波书店出版)亦具有异曲同工。
(2)密切联系日本文化实际把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本土化是当今日本诗学界关注的焦点。对任何域外文化都不能生吞活剥,许多日本文学理论家们清醒地意识到不同话语的差异,对接受中的复杂性、存在的问题有清醒意识。柄谷行人援引福田恒存在《反近代的思想》中的一段话后指出:“从明治至大正的比较长的启蒙时代里,甚至连鸥外、漱石、荷风等人,也并非是自觉地把握近代的局限这一主题,并予以深究。日本的近代化,用当时的话语来表述叫‘文明开化’,他们最早感觉到了它的膺品性。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又起着最积极的推进作用。在明治时代里,连最优秀的知识人都只能具有双重姿态。与此相对,大多数知识人,对于西欧人早就看透了为近代文明的本质而深感不安的诸多现象,反而不加理睬的予以接受,仅以赞叹之心情全盘欢迎。”[23](P22-23)他认为当今对后现代的理解许多人似是而非。“我们说的是后现代实乃现代,我们在说现代实乃是后现代”。[23](P68)一些研究者对20世纪以来的一些术语的译介从本源上探讨这一问题,如柄谷行人、浅田彰、野口武彦、莲实重彦、三浦雅士等人在《近代日本的批评·明治大正篇》(福武书店,1992)指出:“观念”“自由”等等词语都是从西洋传入的”“从西洋传入的东西是用东洋哲学的概念翻译过来,作为它的结果反而是东洋哲学也依据西洋哲学来阐释了……为了要把西洋的东西用汉文译出,东洋哲学亦被带入两洋的体系了。”“由于翻译,东洋与西洋结合,正因如此,‘东洋’被‘发明’出来了。”[24](P70)这段论述对于理解东西诗学交融有启发。
(3)当今日本诗学的跨学科、跨文化的“文化批评”特点突出。进入21世纪的新的诗学,如果只就文学研究文学是很有局限的,新的诗学并非是对以往文学理论的扬弃,如对于曾有很大影响的“文本论”,一些日本理论家力图给它注入新的活力。他们设想以文本为切入点,在动态中综合把握,以小见大,用微观与宏现结合的批评方法建立以文本为中心的“跨文化研究”。
标签:自然主义论文; 日本作家论文; 日本和歌论文; 文学论文; 古今和歌集论文; 文镜秘府论论文; 源氏物语论文; 万叶集论文; 古事记论文; 文心雕龙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