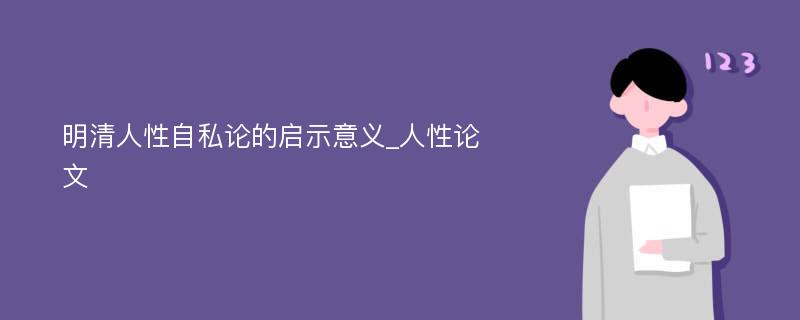
明清之际人性自私说的启蒙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明清论文,自私论文,人性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B2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8—1763 (1999)01—0045—05
明清之际,天崩地解,风雷激荡。社会的急剧动荡变化引起了人们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的巨大改变。当时的进步思想家从各个方面对封建专制主义、蒙昧主义和禁欲主义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批判,提出了许多富于启蒙色彩的命题。一时各种新说并起,蔚为大观,形成了中国早期启蒙思潮。人性论是中国早期启蒙思潮的重要内容。当时的进步思想家在人性问题上新见迭出,其中的人性自私说更是中国思想史上的石破天惊之论,体现出鲜明的启蒙的时代精神。本文试就明清之际人性自私说的启蒙意义作一简要的论述。
一 先秦诸子及宋明理学人性论对私的否定
人性问题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热点。自孔子以“性相近,习相远”(《论语·阳货》)的论断肇其端,历代思想家在人性问题上众说纷纭,聚讼不已。战国时孟子提出性善论,认为人心中先天具有仁义礼智之四端,有天赋的良知良能,坚决否认人具有自私自为之心。孟子性善论在历代均影响深远,成为汉唐宋明时期人性论的主流。但与孟子同时的前期法家人物慎到则提出了“人莫不自为也”(《慎子·因循》)的观点,认为人人都在追求自己的利益,为自己打算。尔后,荀子又提出性恶论,认为人的本性必然好利恶害,“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生而有疾恶焉”(《韩非子·性恶》)。韩非则进一步提出,自私、利已,为一切人所共有,人总是从考虑个人利害的角度出发处理与他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所有人“皆挟自为之心”(《韩非子·外储上》),人和人之间都为自己的利益而互相算计。慎到、荀子、韩非的这些论断实际上已经涉及到人性自私的问题。但是,尽管他们都间接地提及人性的自利自为,却都没有直接提出人性自私说,更没有对人性的自利自为在价值判断上予以肯定。相反,在他们看来,人性是自利自为的,同时也是恶的。他们之所以提出人性自利自为,只是为了论证他们推行法治或制订礼仪规范的必要性、合理性,利用或改造人的恶劣的本性。荀子从修养论角度出发,以此强调人们去恶趋善,进行道德修养的必要性;韩非子则从加强君主专制独裁这一目的出发,认为正因为人有好利恶害、自利自为的性情,统治者就必须认识、利用这种倾向,信赏必罚,有效地治理百姓,巩固统治。在价值判断上,他们对于人的自私自为之性是持明显的否定态度的,最终仍主张要“化性起伪”(《韩非子·性恶》),“去私心,行公义”(《韩非子·饰邪》)。
自汉至宋,人的本性自利自为的观点没有得到突破性发展。宋明理学的二元人性论提出了天命之性、气质之性的区分及其对立,认为天命之性纯粹至善,气质之性有善有恶。而这种区分产生的原因则在于有无“气禀物欲之私”。来源于“性命之正”,出于“义理”的是天命之性:来源于“形气之私”,出于私欲的是气质之性。这种人性理论,虽然所强调的是“气质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张载《正蒙·诚明篇》),不以之作为人的根本属性,但是,它实际上还是隐含了对于人性之私存在的承认。只不过这种私是完全以负面价值形式出现的,它与人的形体气质、欲望相联系,被称为人欲之私而与天理之公处于对立状态。它是罪恶的渊薮,邪恶的代名词,是被除、改变的对象,一有私心,便要求红炉点雪般将它驱除干净,达到一种人欲净尽、天理流行的“廓然大公”的境界。基于这种认识,在宋明理学中,与理欲之辨相表里的公私之辨被特别强调,人们修心养性,超凡入圣的方法,就是去除耳目形气之私,不为外物所诱,一切以遵循天理为准则。宋明理学公私之辨的命题,其具体含义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视人的欲望为私,认为私是与天理之公相对立的。对此,张栻曾作出清楚的阐发:“静者,性之本然也。然性不能不动,感动于物则动矣。此亦未见其不善。故曰‘性之欲’,是性之不能不动者然也。然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流为不善矣。此岂性之理哉,一己之私而已。于是而有‘人欲’之称,对天理而己,则可见公私之分矣。”(《宋元学案》卷50)在这种意义上,公私之辨就在于强调以封建道德原则来压抑个人的欲望;另一方面,公私之辨是将个体的独立性视为私,主张个体对群体的绝对服从,否定、轻视个体的价值、地位。程颐所谓“公则一,私则万殊,……人心不同如面,正是私心”(《宋元学案》卷15)就阐明了这种观点。可以看出,在公私之辨的重压下,个人利益、欲望被否定,个人仅被视为封建宗法关系之网上的一个小结,仅仅是维护某种虚幻的公共利益的手段和工具,没有独立的价值和地位。衡量个人存在价值的标准就在于个人对于某种虚幻的集体所尽的道德义务。实质上,公私之辨就是要求人们一切思想、言论、行为都符合封建纲常伦理,通过压抑个体的欲望,贬低个体的价值,以维护封建君主专制的统治秩序。宋明理学的这种说教,在封建社会中后期的数百年中,成为人们精神上的沉重枷锁。
明清之际,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人们的“个人感”逐渐提高,自我意识不断增强。他们不甘于仅仅作为手段、作为附属物而存在,产生了挣脱封建宗法关系之网,挣脱一切封建束缚而追求自由私产、寻求个人价值的要求。同时,在从事工商业、发展商品经济的过程中,他们又强烈地感受到封建专制制度对个体的压抑与束缚,意识到他们的自由私产要求与封建君主专制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感受到封建君主在“公”的名义下对个人私利的剥夺。这一切,给维护封建纲常秩序、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宋明理学人性论以巨大冲击。明清之际的人性自私说,正是在这一社会历史背景中,作为新兴市民阶层的思想意识被明确提出来的。
二 明清之际人性自私说对个体存在与价值的肯定
明清之际,李贽、黄宗羲、顾炎武、陈确、傅山等思想家都提出了其人性自私说。因各自的社会背景、个人遭际及探讨角度的不同,其理论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是其基本价值取向却是相当一致的。他们提出人性自私说,并且对于人性之私的道德价值予以充分的肯定,认为这是自然之理,是人所共具的常情,更是人类一切行为、制度、规范的出发点和衡量其正当性的标准。他们对于人性自私的合理性的肯定,与前代思想家视自私自为为人性的弱点、或者视私为邪恶的观点有着本质的区别,与宋明理学的公私之辨更是根本对立的。针对宋明理学公私之辨的命题,明清之际人性说主要阐述了两方面的内容:
一方面,肯定个人物质利益、欲望的合理性。李贽以极大的理论勇气,最早明确提出了“私心说”,指出私心是一切人所共有的本质,是人的本性,“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若无私,则无心矣。”(李贽《焚书·德业儒臣后论》)不仅如此,私心和物欲还是人性一切活动的原动力。耕田者奋力治田,是因为可以私有秋收之获;居家者努力治家,是因为可以私有积仓之获。读书者、为官者的行为也无不是为欲望、利益所驱动。这种自私本性,任何人都概莫能外。孔子居鲁摄相之事,无非也是为了私利,“谓圣人之不欲富贵,未之有也”。(李贽《明灯道古录》)至于“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超功利主义,是不存在的,“夫欲正义,是利之也,若不谋利,不正可也;吾道苟明,则吾之功毕矣,若不计功,道又何以可明也。”(李贽《焚书·德业儒臣后论》)在这里,李贽从人必有私出发,肯定了人们追求个人私产、追求财富的欲望的合理性。
黄宗羲则认为,“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自私自利是人类的自然本性。这种本性的充分满足,是人类早期的本然状态,也是人类社会的应然状态。国家机构的建立,制度、法律的产生,理想社会图景的设计,都必须以这种自私自利的本性的满足作为考虑的基点,使天下人各得自私,各得自利。如果国家君主认识不到这一点,“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则必然违逆人们追求利欲的本性,丧失其存在的合理性。
顾炎武肯定了对私利的追求是人的本性,认为“天下之人各怀其家,各私其子,其常情也”,(顾炎武《郡县论》)“人之有私,固情之所不能免”。(顾炎武《日知录》)他还指出,人性之私是客观存在,不容否认的,“有公而无私,此后代之美言,非先王之至训矣。”(顾炎武《日知录》)在他看来,人性离不开人们私利与欲望的满足,道德就存在于人们的物质利益之中。圣人对于私只能因而用之,顺从满足人的私利才能使天下大治。正因为如此,上古先王对于人性之私“非惟弗禁,且从而恤之,建国亲侯,胙土命氏,画井分田”,充分顺从满足人的私心欲望。
陈确、傅山等思想家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有私所以为君子”(《陈确集·文集·私说》),“私者,天也”(傅山《霜红龛集》)。尽管这些人性自私说着眼点不同,理论表述各异,但它们都在肯定人性之私的道德价值的基础上,肯定了人们追求感性物质欲望的合理性,反对了宋明理学的禁欲主义,为新兴市民阶层追求自由私产的要求作出了理论上的说明。
在另一方面,人性自私说还强调了个体的价值与地位。宋明理学的公私之辨,突出了群体价值取向,人的价值取决于他是否能成功地扮演在宗法关系之网中被赋予的特性角色,维护既有的等级秩序。独立的人格与个性是被漠视、否定的,即所谓的“公则一,私则万殊”。明清之际的进步思想家则从人性自私说出发,大胆肯定了个体的地位与价值,提出了个性解放的要求。李贽以私心作为人的本性,同时又在基本相同的意义上使用“童心”、“真心”的概念,认为“童心”、“真心”是“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李贽《焚书·童心说》),它排除了一切社会价值因素的影响。丧失了童心、真心,便不成其为真人。因此童心、真心是人成其为人的本质特征。李贽以童心、真心来谈私心,所要强调的乃是人的本性同强调公私之辨、理欲之分的封建礼教、义理的对立。童心是未经义理熏染的赤子之心,它是与封建礼教不相容的。“有道理从闻见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封建义理的灌输、礼教的束缚,会使人丧失本性,成为假人。因此,李贽要求复真心、做真人,呼唤本心的觉醒,实质上是躁动于封建礼教重压之下的一种个性自觉。他大胆地提出了对于个性的肯定与尊崇:
就其力之所能为,与心之所欲为,势之所必为者以听之,则千万其人者,各得其千万人之心;千万其心者,各遂其千万人之欲。是谓物各付物。……若肯听其并育,则大成大,小成小,天下无更有一物不得其所哉!(《明灯道古录》)
夫道者路也,不止一途;性者心所生也,亦非止一种已也。(《焚书·论政篇》)
封建礼教束缚人的私心,因此必须解除条教禁约,各得千万人之心,各遂千万人之欲,使天下万物并育,个性得到自由发展。这种观点反映了新兴市民阶层要求摆脱封建礼教束缚、肯定个体价值、追求个性自由的愿望。
陈确在其《私说》一文中,对个体存在及其价值作了充分肯定。与传统儒家的价值取向相反,陈确明确地将个体之“身”置于最重要的地位,认为个体之身相对于国家天下而言应绝对优先予以考虑,“故君子之爱天下也,必不如其爱国也,爱国必不如其爱家与身也”,这是人类自私本性的正当表现。陈确认为,成就治国平天下的经世之业,完成个人担负的社会责任和义务,都必须以肯定个体的存在及其价值为前提和基础。故此,“彼古之所谓圣贤者,皆从自私之一念,而能推而致之以造乎其极也”。圣贤们都是私爱其身,重视个体存在的价值的,他们完成治平之业,正是私爱其身观念的延伸,“有私所以为君子”。陈确的这些观点,与理学家克已去私之论相对立,体现了从社会群体本位向个人本位转化的时代精神。列宁指出,“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意味着个人感的提高”,明清之际的人性自私说正是在不同程度上表现了随着资本主义萌芽而产生的新兴市民阶层对个人地位与价值的追求。
三 明清之际人性自私说对封建专制政体的批判
值得注意的是,明清之际的进步思想家不仅以人性自私说肯定了人们的权利及个体的地位与价值。而且以此为出发点,对封建君主专制及中国封建社会家国同构的统治模式进行了批判,显示出人性自私说这一启蒙理论的现实冲击力。
基于“人各自私,人各自利”的人性原则,黄宗羲认为,国家机构和法律之所以产生,在其本来意义上就是要保障个人私利,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而使人们自私自利的本性得到充分满足和发展。但是,专制君主为了一己利益和享乐,不惜侵夺天下人的利益,使天下人自私自利的本性受到摧残和压抑,实质上是“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明夷待访录》)。黄宗羲对君主专制的这一揭露可谓入木三分。封建君主压抑、否定人的私心,要求人们存天理,灭私欲,而其所谓的“公”,实际上只不过是个人私利的一个幌子。他们为了满足自己的私利,剥夺了天下人自私自利的权力,“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敲剥天下之骨髓”(《明夷待访录》),犯下了种种罪恶。因此,黄宗羲指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这就从人性论的角度打破了君主为公的神话,视君主为压制摧残人们自私本性的大害。这种批判,视君主专制为反人性的制度,尖锐而深刻,其力度远远超过了历代的异端思想家。黄宗羲还进一步推论,“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明夷待访录》),从满足人们自私自利的人性的角度出发提出发废除、改变君主专制的必要性。实际上,黄宗羲的人性自私说已经成为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市民阶层反对封建君主专制的理论基础。
黄宗羲还从同一角度出发对封建法律进行了批判。他认为,法律的本质在于保障人们自私自利的要求,增进人们公利。三代之法就是如此。而后世的法律,则异化为压抑、否定天下人私利而保障封建君主一家之利的工具,“利不欲其遗于下,祸必欲其敛于上”,“何曾有一毫为天下之心哉!”因此,他认为,后代“所谓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明夷待访录》)。在黄宗羲看来,区分一家之法和天下之法的标准就在于能否使天下万民各得自私,各得自利,而封建法律正是违背人性的一家之法。由此他设想有能够满足天下私利的“公法”,即所谓的“天下之法”。这种设想,反映了新兴市民阶层对于财产的要求和对政治权力、地位进行重新分配的愿望。
黄宗羲从肯定人的自私自利的本性出发,批判了封建君主专制践踏人性的罪恶,揭露了封建法律一家之法违背人性的本质,并提出了其理想的政治、法律图景。其矛头所向,直指封建君主专制和封建法律这些根本性问题,具有鲜明的近代启蒙色彩。而作为黄宗羲理论出发点的人性自私说,其启蒙意义也在此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顾炎武则以其人性自私说为出发点,提出了“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此所以为王政也”的观点,认为理想的政治制度应该是在充分满足个人私利的基础之上形成社会公利,在肯定人们对私利的追求的基础上提出其制度理想。他甚至还提出了一种“使县令得私其百里之地”的具体运作方法,希望通过对个人私利的承认,有效地促进社会公利的形成。顾炎武一反宋明理学视公与私为互相对立、互为消长的观念,提出了在制度层面上公与私的统一性。这是对宋明理学公私之辨的否定。其所谓“公”,是以肯定天下人私利为前提的,是天下私利的综合与统一。以这种制度理想反观现实,顾炎武意识到,在现实中被标榜为“公”,宣称代表天下人利益的“国”,实际上并没有体现天下之私。相反,它是对天下之私的一种压抑和剥夺。中国宗法制的传统形成了家国同构的政治模式,“国”是“家”的延伸和放大,实质上就是统治者的一己之家。但是作为国家统治者的君主往声称“国”代表全体国民的整体利益,并强调压抑个体私利以维护“国”的所谓整体利益。宋明理学的公私之辨就是为此而作出的理论说明。而顾炎武认识到“国”只是一种虚幻的集体,是统治者的“家”,它并非真正的建立在天下私利基础之上的“公”,而只是一家一姓之私。这种“私”又是与天下人的私利相对立的。因此,顾炎武从这一角度出发,对“国”与“天下”的概念作了区分。他认为“亡国”是指易姓改号,朝代更替,而“亡天下”则是指道德论丧、仁义充塞,二者的内容是不同的。“国”和“天下”是不同利益的代表者与体现者。这一区分,揭示出以家国同构为其表现形式的封建君主专制一家之天下的本质以及封建国家与个人之间利益的矛盾,表现出一种批判并力图摆脱传统宗法利益至上观念的努力。从肯定被封建统治者以“国”这一虚幻的集体所冒充、排斥的个人私利出发,引申出对封建君主及家国同构的封建专制政体的批判,这是顾炎武对人性探讨的逻辑归宿。
综上所述,明清之际的人性自私说,以“私”作为人的本性,并且肯定了私的道德价值,这在中国思想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虽然从理论上说,人性自私说把在一定历史阶段中产生的自私观念视为普遍的人类法则,在本质上仍然是一种抽象的人性理论。但人性自私说的价值并不在于它如何正确地揭示了人性的本质,而在于它透过层层宗法关系的密网,提出了对个人私利、个体的存在及其价值的肯定。明清之际启蒙学者还力图从人性自和说出发,批判封建专制主义,提出对于建立在保障自私和自爱之心基础之上的理想社会、法律制度的向往。在宋明理学鼓吹禁欲主义,视私为邪恶,贬低、否定个体存在价值及物质生活欲求的时代,人性自私说无疑是具有启蒙意义的。它反映了新兴市民阶层冲破封建君主专制束缚、发展自由私产,争取个性自由的愿望和要求,是中国古代人性论走向近代的先声。
收稿日期 1997-06-06
标签:人性论文; 黄宗羲论文; 儒家论文; 明清论文; 明夷待访录论文; 人性本质论文; 启蒙思想论文; 顾炎武论文; 理学论文; 李贽论文; 经世致用论文; 君主专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