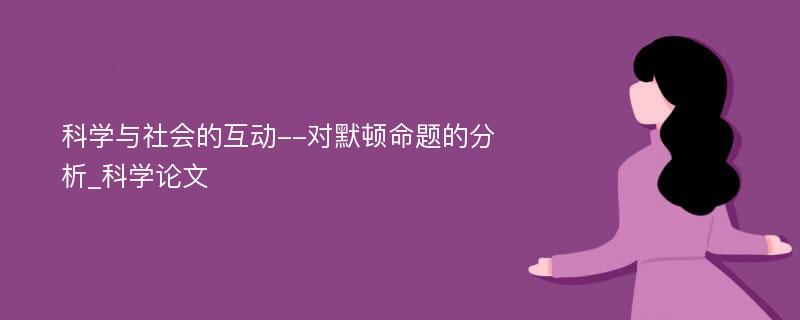
科学与社会的互动——“默顿命题”评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互动论文,命题论文,科学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罗伯特·默顿(Robert King Merton)是美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结构功能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博士论文《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中详细论述了17世纪英国的文化背景和价值观念对科学技术的巨大推动,同时也阐述了经济、军事需要对科学技术的促进作用,从而使该文成为科学社会学的奠基之作。默顿在文中的论述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持久争论,他论述的观点被称为“默顿命题”。
所谓“默顿命题”,按库恩(Thomas S·Kuhn)的说法,“它实际上是两个来源不同的命题的重合”〔1〕。第一个命题是17 世纪的工匠传统和培根所提倡的实验科学有力地推动了近代科学的实质性变革并使科学更具实用价值;第二个命题是清教主义促进了英国近代科学的制度化。本文试图就“默顿命题”的合理性作几点评析。
一、培根纲领:科学发展新思维
对于第一命题,学术界有人认为,17世纪的许多学科的实质性变革应归功于理性主义潮流的推动,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等人的思想是这股潮流的中坚力量;并强调科学的变革是科学领域内部的进化和理性演绎的结果,与工匠传统和经验主义毫无关系,而且断言“培根的朴素的野心勃勃的纲领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没有结果的幻想”〔2〕。 确实,17世纪天文学的伟大成就、开普勒的天体三定律、牛顿和莱布尼茨的数学体系以及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对世界体系的解释无一不闪耀着理性主义的光辉。但如果说上述科学领域的变革完全排斥经验主义参与,却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并且对这些领域取得成就的圆满解释不得不求助于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实际上,“天文学在17世纪尤其具有巨大的经济重要性。环球航行、世界贸易、建立殖民地的事业都是方兴未艾。在这方面,天文学家的图表、物理学家的钟摆和平衡轮钟都意味着可以及时拯救船只和货物,可以征服远处海外的帝国。”〔3 〕所以对第一个命题,笔者认为:首先,默顿所论述的科学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即17世纪英国的科学,而英国有着悠久的实验科学的传统。早在13世纪,在反对经院哲学的斗争中,英国的罗吉尔·培根就提出要面向自然,注重实验,反对盲目崇拜权威的思想,主张证明前人说法的唯一方法是观察和实验。英国皇家学会的章程也体现了这种经验科学的传统,并洋溢着功利主义气息。这份章程写道:“……我们明白,再没有什么比提倡有用的技术和科学更能促进这样圆满的政治的实现了。通过周密的考察,我们发现有用的技术和科学是文明社会和自由政体的基础。……因此,我们的理智告诉我们,我们自己在国外旅行的见闻也充分证明:我们只有增加可以促进我国臣民的舒适、利润和健康的有用发明,才能有效的发展自然实验哲学,特别是其中同增进贸易有关的部分。”〔4〕皇家学会的章程是这样写的,其会员也是这样做的。波义耳、 牛顿、胡克、哈雷、哈维等科学史上的一代宗师既受实验科学的熏陶,也对实验科学传统的发扬光大作出了重大贡献。牛顿曾自己动手磨制反射镜,制成了一架长约6英寸、口径1英寸的小型望远镜,并用它观察了木星的卫星和金星的周相。后来他又制造了较大的望远镜,并把它献给了皇家学会。胡克在皇家学会做了不计其数的实验,其中复显微镜的制作是较为出色的一个。他的《显微术》(Micrographia)(1665年)是最早论述显微观察的专著,详尽地说明了有效使用显微镜的方法。〔5〕波义耳也是在实验基础上定义了元素的概念,结束元素一词在使用上的混乱状况,为化学学科的建立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其次,在17世纪的英国,经验主义和功利主义渐成教育的主调,实验科学如物理、化学等逐渐进入大学课堂甚至中学课堂,这主要得益于职业兴趣的转移和教育体制的改革。职业兴趣的转移是全方位的,如军人、艺术、医学、宗教、科学等方面。据统计, 诗人和教士的人数在17世纪的前70年减少了1.8倍, 而医生和科学家的人数在同期都增长了1.4倍。〔6〕职业兴趣转移的这种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倾向使科学成为时尚,以致科学著作甚至出现在贵族夫人的梳妆台上。一时间功利主义成为人们的行为准则,以致有人对自己儿子的忠告是“不要学习任何东西,除非它能帮你谋利”。〔7 〕处于象牙之塔中的英国教育体制也受到功利主义的冲击。培根纲领的积极支持者、清教徒约翰·韦伯斯特(John Webster)建议按彻底的功利原则改造英国大学教育体制,鼓吹在大学用实验科学取代经院式的古典研究,连教士们也要求教徒要充分利用今世和来世两个世界,在学习深刻而玄妙的真理之前学习那些最明白最有用的东西。当时,科学活动只是有闲阶级的业余爱好,难以登上大学讲台,“人们所熟悉的科学活动(如光学、化学、电磁学的研究)的主要根基不在于学识渊博的大学传统,而往往在于已有的技艺之中,它们全部严格依赖于往往由工匠们帮助引进新的科学实验程序和新的仪器”。〔8〕实行教育体制改革后,大学传统和工匠传统逐渐结合,尽管这种结合是曲折而漫长的,但它毕竟使科学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可见,“培根纲领最初尽管缺少思想方面的成果,但仍然是许多重要的现代科学的开端。”〔9〕
最后,默顿在他的博士论文中论述了科学与经济、文化、军事等社会因素的关系即科学与其外部因素的关系,忽略了科学发展的内部因素,显然他的着眼点不在科学的内部。因此,如果把默顿的命题放在整个科学史的大背景中去考察难免失之全面,但对科学的实质性变革的解释却“可以通过对默顿命题的修正而得出说明,而不必抛弃这个命题”〔10〕。
二、清教主义:科学制度化的温床
默顿的第二个命题即清教主义促进了科学的制度化更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长期以来,人们有一种印象即科学与宗教是天生的敌对力量,科学代表真理,宗教代表谬误。人们不会忘记17世纪“日心说”受到天主教宗教法庭的指斥,19世纪地质科学的成就使新旧教的宗教人士大为震惊,直到今天进化论仍然是宗教的眼中钉。科学的发展使宗教的地盘越来越小,也验证了宗教和科学的对立。伽利略的被囚受审、布鲁诺和塞尔维特的惨死等科学史上的不幸例子更强化了人们的这种印象。哥白尼的“日心说”首先向上帝“创世说”提出了挑战;开普勒是哥白尼学说的热情支持者,并宣称“如果至高无上的上帝高兴要一个物质居所并4选择一个地方和他那些有福的天使们住在一起的话,在我看来只有太阳才配得上上帝居住”;牛顿则认为上帝在太阳系中只起第一推动作用。这样上帝从创世到退居太阳、再到第一推动,其功能逐步萎缩。宗教在科学咄咄逼人的气势面前节节败退,在此背景下论述宗教对科学的积极作用势必受到人们的质疑。
但是,如果我们认为在宗教和科学的关系中,宗教历来是错的,科学历来是对的,那未免过于武断。伽利略说地球是动的,太阳是固定的;宗教法庭说,地球是固定的,太阳是动的;而牛顿学派的天文学家根据绝对空间的理论认为,地球和太阳都是动的;今天我们根据相对运动的理论可以说这3种说法都是对的。实际上,宗教和科学的旨趣不同,双方的对立不是两者关系的全部内容,在17世纪尤其如此。如前所述,默顿是把科学与宗教的关系放在英国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来考察的。17世纪的科学尚未摆脱宗教的羁绊,仍处于“婢女”的地位。它既受宗教的控制,又受宗教的保护。科学与宗教具有某种相容性,这种相容性体现在清教的精神气质中。清教的精神气质首先是世俗活动,是颂扬上帝的手段。清教给世俗活动应有的位置,认为修道士的生活不仅毫无价值,而且放弃现世的义务是自私的,是逃避世俗责任;相反,世俗活动(如劳动)是人们的天职,是人们从“自然状态”进入“受宠状态”的最佳途径。个人是否受到上帝的恩宠,自己是不知道的,只有世俗活动,如市场上的成功、农田里的果实、实验室里的实验,才能驱散人们心中的疑虑,给人带来恩宠的确定性。自然科学活动是世俗活动的内容之一,这一点清教与中世纪的宗教不同,后者把研究自然、探索自然的奥秘看作是对上帝的亵渎,是对教会权威的挑战。中世纪的教皇格里高里一世就公开宣称,不学无术是真正虔诚的母亲,而清教则认为,自然界是上帝的杰作,研究自然、揭开自然的奥秘是颂扬上帝的大智大慧。因此,为了颂扬上帝、为了成为上帝的造民,许多人选择了科学。这样,“在大名鼎鼎的人物之外,科学又获得了大众性,探索自然奥秘成为时尚”〔11〕。其次是功利主义。功利主义是世俗活动的逻辑发展,在精神上寻求天国的孤独的朝圣者在世俗活动中没有立足之地。纯粹的宗教热情过后,在通往受宠状态的漫漫征程中,人们不得不以功利作拐杖。正如韦伯所说:“宗教的根慢慢枯死,让位于世俗的功利主义。”〔12〕作为清教精神气质的功利主义通过宗教、教育等活动逐渐融入英国的文化氛围。从皇室成员到平民百姓,从皇家学会到学校教育,从科学大师到无名之辈,都以功利主义为价值标准和行为准则,都以事业的成就和对公众有利的行为来证明自己是上帝的造民。他们“实践意义上的明显有用的活动日益被看作为最有效的赞颂上帝的方式”〔13〕。于是,在培根纲领指导下的科学的最终后果就与功利主义要求不谋而合。第三是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在清教看来,理性和信仰并不矛盾,信仰并非无理性之行为,上帝在灌输信仰时,以理性为前提。“那些信仰而不知为何要信仰,或不知道保证其信仰的充分理由的人,才真正对信仰具有一种幻觉、或印象、或梦幻。”〔14〕可见,这里的理性是指有理由性,即与经验主义相结合的理性。清教提倡在世俗活动中运用理性,如理性地使用资本和组织劳动,反对非理性地使用财富,“任何无节制的人生享乐,无论它表现为贵族的体育活动,还是平民百姓在舞场上或酒店里的纵情狂欢,都会驱使人舍弃职守、背离宗教,因此理应成为理性禁欲主义的仇敌”〔15〕。理性不但控制和约束人们的各种欲望,抑制人们的盲目崇拜,而且也是人们灵魂得救的标志之一,所以理性成为教徒们追求的目标。另一方面,科学就是理性的事业,它注重对经验材料的理性思考,强调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结合,这样科学发展的内在要求又无意中迎合了清教的精神气质。综上所述,科学与清教在17世纪的英国具有“选择性亲和”的关系,当然这只是两者相容的一面,实际上还有对立的一面。但正如其相容性不能否认对立性一样,其对立性也不能消除相容性对科学的赞许。
总之,科学的内在属性和外在后果都较好地适应了清教的精神气质,以致“被当作一种社会力量的宗教伦理是如此地把科学奉为神圣,使它成为一个受到高度尊重和推崇的注意力的汇聚中心”〔16〕。需要指出的是,近代科学的制度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其发展动因有科学内部的发展规律的作用,也有科学外部的诸社会因素的共同影响。显然,清教主义并不能直接导致科学制度化,只是因为与科学的内在要求和外在后果有某种相容性,从而为科学制度化提供了适宜的文化土壤。
三、多元分析:社会学的广角镜
默顿分析问题的范式受到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强烈影响,这种范式具有多元性、灵活性、突出文化因素的特点,它的影响是深远的,对后人的启发也是多方面的。
第一,多元分析范式对社会学影响深远。
它一方面给社会学提供分析问题的有效方式,另一方面在社会学领域与马克思主义辩证分析方法分庭抗礼。默顿的多元分析承认科学受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他说:“科学的重大顽强的发展只能发生在一定类型的社会里,该社会为这种发展提供文化和物质两个方面的条件。”〔17〕但是默顿在其博士论文中的论述如同荡秋千,让人难以把握其左右,其目的是想建立一个不分主次的多元模型,以调和科学外部史中精神史和社会史的对立,否认社会需要和生产方式对科学的决定作用。尽管默顿在其博士论文1970年再版序言中多处解释,说清教伦理只是间接的无意的对科学发挥着潜功能,但他论述的重点则是,作为文化价值的新教伦理是新科学的兴起及其组织化的巨大动力。默顿用1/3的篇幅多侧面反复论述了文化价值(清教主义或其他功能等价物)对科学发展的积极作用。他认为科学“是长时期文化孵化生成的一个娇儿。我们倘若要发现科学的这种新表现出来的生命力,这种新赢得的声望的独特源泉,那就应该到那些文化价值中去寻找”〔18〕。他在论述经济因素对科学的影响时说,社会需要本身并不能导致发明,许多最需要发明的国家,如亚马逊河流域诸国和印度实际上没有什么发明,所以社会需要对科学发明的促进还要一定的文化背景。其目的是试图证明“17 世纪英国的文化土壤对科学的成长与传播是特别肥沃的”〔19〕。
默顿把清教伦理看作是17世纪英国的文化价值,是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这是他的独到之处,也是可贵之处。实际上,清教是宗教改革的产物,宗教改革的实质是资产阶级文化领域的革命,它所倡导的既是资产主义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也是科学发展所需要的,它推动了整个一个时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为近代科学的崛起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柱。精教作为一种社会力量,它对科学的影响是自然的;作为一种价值观念,它已经成为众人的信仰。正如马克思在评马丁·路德时说:“他破除了对权威的信仰,却恢复了信仰的权威;他把僧侣变成了俗人,又把俗人变成了僧侣。”爱因斯坦也说:“没有科学的宗教是盲目的,没有宗教的科学是跛足的。”这里说的宗教应理解为信仰。也许这个信仰正是英国成为17世纪世界科学中心的原因之一,它使英国科学稳步发展而不至于“跛足”。
第二,引发了对宗教与科学的关系的思考。
“默顿命题”的核心内容,是清教伦理推动了科学制度化的进程。宗教与科学的这种“选择性亲和”的关系引起了学术界的研究兴趣。毋庸置疑,宗教与科学之间的对立是两者关系的主要内容,宗教与科学正是在这种对立关系中表现各自的特质。但如果就此把宗教看成科学的天敌,认为两者是绝对对立的,那就会陷入片面性之中。实际上,在一种条件下宗教与科学表现为对立,在另一种条件下则表现为广泛的联系。
宗教与科学的相互联系首先表现为它们在社会历史过程中的长期共存,相互补充。在人类文明的历史上,它们总是形影不离,哪里有宗教,那里就有科学。宗教与科学的共存现象还普遍体现在个体社会成员身上。从古到今,许多人在实际生活中既表现出对科学的强烈追求,又有虔诚的宗教信仰。近代自然科学的奠基人之一牛顿笃信创世主的存在,晚年一心想计算出上帝创世所用的第一推动力有多大。现代物理学巨匠爱因斯坦也认为,宇宙秩序的和谐完美体现出一种神圣的目的。
宗教与科学的相互补充是它们彼此联系的另一面。宗教与科学的旨趣不同,以日常经验为基础的科学是人们指向外部对象的活动,其目的是用精确的量化概念和严密的判断推理描述外在于人的各种客观过程,它回答什么是“真”的问题。但人类社会生活不仅需要真,而且需要善,更需要统一真和善的美。以想象中的超自然的精神实在为基础的宗教是人们指向自我的认识活动。宗教认为,整个宇宙(包括人类社会)体现了某种神圣的秩序,并要求人们从这个秩序中寻找自己的位置,承担自己的义务,树立并实现自己的生活理想。因此,宗教的前提固然荒谬,但它体现了人们要求在现实生活中达到真、善、美统一境界的愿望。
宗教与科学的相互联系还表现在相互包容、相互作用方面。远古时代,科学仅处于萌芽阶段,不可能从宗教意识中独立出来,至多表现为一些经验常识,远远不足以向人们提供关于客观世界的合理说明。在这种情况下,客观现象甚至科学自身的现象不得不依靠宗教来解释。经过长期的发展,经过近代史上激烈的搏斗,科学终于摆脱了受宗教支配的地位,发展出独立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体系。尽管如此,宗教与科学仍有一定的包容关系。一方面,科学的迅速发展有力地批判了传统宗教观念;另一方面,科学在赢得独立生存的权利后,与宗教的矛盾较前略有缓和。这是因为,科学与宗教在社会生活各自的领域内活动,科学无需以取消宗教作为自身发展的唯一前提,而且科学到目前为止还不能彻底否定宗教的一切命题。
宗教与科学的相互作用实际上就是相互对立,这客观上有利于宗教与科学各自的发展。科学以确凿的事实为依据,批判传统宗教观念,迫使宗教按照时代的要求改变自身的形态;同时,宗教对科学的挑战刺激了科学的发展,宗教教育对近代自然科学和人类科学的萌生和发展也起了积极的作用。
宗教与科学的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可以预言,在未来科学高度发达的时代,宗教仍会有自己的地盘,即科学的高度发达并非是宗教消亡的充分条件。
第三,启发了对科学与社会的互动关系的再认识。
“默顿命题”表现的是17世纪英国的科学与社会的互动关系,这种关系是非对称的,即科学与其他社会因素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对称的、不平衡的。17世纪的科学是社会文化环境中的“娇儿”,而今天科学和技术以压倒一切的方式支配着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各个方面。这种关系仍然是非对称的。几个世纪以来,科学不仅创造了巨大的社会生产力,使人类步入前所未有的发达阶段,而且为人类的自由和解放,为人类的全面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以致被人们认为是“阿拉丁的洞穴”。但是,当核武器、人口爆炸、环境恶化、生态失衡等威胁人类自身时,人们在惊慌失措中发现这个洞穴里还有一只“潘多拉盒子”。科学的这两难处境是技术理性发展的必然结果。所谓技术理性,是决定人们生活方式的基本文化旨趣,它包括如下基本文化观念:(1)人类征服自然;(2)自然的定量化。它导致用数学结构来阐释自然, 使科学知识的产生成为可能,为人类征服自然提供理论工具;(3)有效性思维。 它指的是行动中对各种行动方案的正确抉择和对工具效率的追求;(4 )社会组织生活的理性化。它包括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工,生产的科层制等;(5)人类物质需求的先决性。〔20 〕技术理性的这些文化观念已经被现代社会所普遍接受,正在执行着一种意识形态的功能。由于技术理性的意识形态化,在科学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中,科学技术以外的其它因素统统处于被动适应的地位。技术理性的这种特点历来受到人文主义者的激烈批判。他们认为技术理性本身是有意义的,它体现了一系列人类的基本旨趣,然而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不可能由它来决定,因为它并不体现对人类价值的终极关怀。哈贝马斯的社会交往学说,弗洛姆的技术人道化,萨顿的科学人性化都试图通过对技术理性的批判来遏制它向社会各个领域的渗透。作为技术文明的解毒剂,人文主义对技术理性的批判,为科学的未来发展,为探索科学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注释:
〔1〕〔2〕〔8〕〔9〕〔10〕(美)库恩:《必要的张力》,纪树立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13、115、116、116、115页。
〔3〕〔4〕(英)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陈体芳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61、60页。
〔5〕(英)亚·沃尔夫:《十六、 十七世纪科学技术的哲学史》,周昌忠等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86~87页。
〔6〕〔7〕〔11〕〔13〕〔14〕〔16〕〔17〕〔18〕〔19〕(美)默顿:《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范岱年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6、31、61、99、93、151、20、79、357页。
〔12〕〔15〕(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等译,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138、131页。
〔20〕高亮华:《人文主义视野中的技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59页。
标签:科学论文; 功利主义论文; 理性选择理论论文; 命题的否定论文; 社会互动论文; 命题逻辑论文; 政治论文; 宗教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