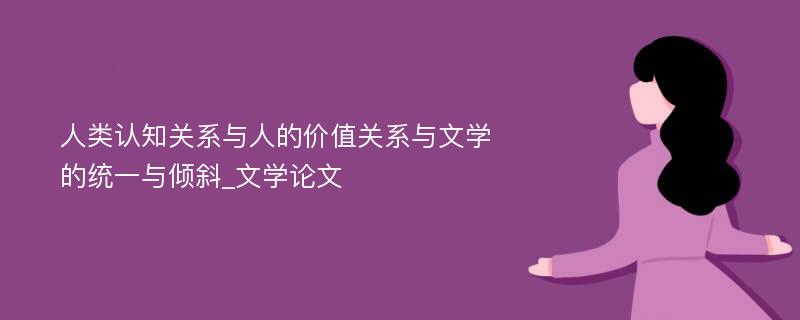
人的认知关系和人的价值关系的统一和倾斜与文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关系论文,认知论文,价值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人的认知关系与文学
人同外部世界以及人同人之间发生着各种关系,均以认知关系为基础为源头。没有人同客观对象的认知关系,人的一切活动都会失去可靠的依托,不可能达到有效的预期的目的。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们往往把人的认知关系和人的反映关系当作含意相近或相似的同一系列的概念来使用。因此,我们可以将认识论和反映论不进行原则性的区分,事实上也很难把两者分解和隔裂开来。必须指明的是,艺术的认识和反映不同于科学的认识和反映,艺术的认识和反映往往是通过体验和领悟来实现的。
一般意义上的认识规律和思维规律也在艺术创作活动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既不能用文学体验的特殊规律拒斥认识和反映的普遍规律,也不应用认识和反映的普遍规律来取代文学体验的特殊规律。文学的体验、感受和领悟总是这样那样地把艺术反映的特殊规律和一般意义上的认识的普遍规律融合为一个复杂的集合体,凝聚为活生生的艺术形象或艺术形象体系。通过文艺表现出来的人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关系是凭借艺术形象或艺术形象体系所呈现出来的图景观察历史、社会和人生。
通过文学认识历史,要求作家艺术家具有敏感的神经和开掘时代意蕴的才能,善于捕捉、吸取能预示社会发展趋向的“历史潮流”,通过“被意识到了的历史内容”,揭示出“较大的思想深度”。“被意识到了的历史内容”是从一定时代的“历史潮流”中提炼、概括出来的,“较大的思想深度”又是从“被意识到了的历史内容”中开掘、升华出来的。艺术反映决定、制约着艺术表现。艺术表现的广度和深度是同艺术认识的广度和深度紧密相关的。这两者之间从概率的意义上来说是相应的、同步的。我们从恩格斯对巴尔扎克的创作和作品的论述中十分明显地看到了这一点。巴尔扎克虽然是政治上的保皇党徒,但由于“看到了”他所属那个时代的新兴市民阶级必然代替腐朽的贵族阶级的“历史潮流”,使他世界观中的膺服真理的唯物主义思想因素占了上风,抑制了他的“阶级同情”和“政治偏见”,取得了“现实主义的最伟大胜利”也使他自己成为“比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切左拉都要伟大得多的现实主义大师”。“他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因为“他看到了他心爱的贵族们灭亡的必然性”,“从而把他们描写成不配有更好命运的人”,用编年史的方式,揭示出“上升的资产阶级在1816年至1848年这一时期对贵族的社会日甚一日的冲击”[①]。大手笔的作家艺术家几乎都程度不同地扮演着“历史的书记官”的光荣角色。
通过文学认识社会,要求作家艺术家努力反映出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并尽可能地开掘和拓展表现社会生活的深度和广度。正如列宁所指出的,托尔斯泰的创作和作品通过勾勒“无与伦比的俄国生活的图画”,从俄国的农奴制度的诸多层面,包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宗教制度以及伦理道德、家庭、婚姻、爱情状况,都进行了全方位的俯视和审判,表现出沙俄帝国的颓败和它的腐朽的历史结构的崩溃和瓦解。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巴尔扎克的创作和作品通过描绘“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的“中心图画”反映出法国社会转型时期各阶级的历史命运,社会生活的动荡和嬗变,新兴阶级取代腐朽贵族的历史变革。法国社会物质生活方式的更新所带来的经济状况的变化使恩格斯感受到,即便是“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②]。可见,不应当低估文学对社会生活的认识功能。
通过文学认识人生、要求作家艺术家从静态和动态的双重视角展现不同阶级、阶层、群体和个人的生存状态。从静态的视角看,在巴尔扎克的笔下,我们看到了农民的形象,我们看到了腐朽的贵族典型,我们也看到了资产阶级野心家的赌徒般的冒险行动;在托尔斯泰的笔下,我们看到了沙俄官僚地主的丑恶、秽行和骄奢淫逸的生活方式,看到了先进的探索者对农业改革的苦心构想和实验,看到了农奴“被搓成绳子”那样的困境,也看到了明智的地主老爷的精神复活,看到了资产者的贪婪和狠毒,看到了被流放的处于苦刑的革命者的坚韧刚强的性格……从动态的视角看,我们在巴尔扎克、托尔斯泰、歌德的文学描写中,十分清晰地体察到各式各样的人物的命运,伴随着社会转型和历史变动时期的作为各阶级和各阶层的代表性人物的升沉、兴衰、荣枯几乎成为观看时代前进的生动景观的窗口。历史转折的关口,给不同的人物安排不同的归宿,提供了不同的机遇。腐朽的贵族阶级的代表人物鲍赛昂夫人带着无可奈何的辛酸和悲怆走下了历史舞台,新兴阶级的代表人物浮士德为创造理想和爱的王国焕发出不畏艰险的追求的热情和献身的精神,在机遇和利益的诱惑和驱使下,也使拉斯蒂涅一些青年的野心家们鼓起了冒险的胆量和勇气,被变革浪潮冲击下的农民濒临破产,流离失所,或少数人转向市民,或陷于更加悲惨的命运……。不管是甚么样的作家和作品都在有意识无意识地表现历史、社会和人生,不包含或不渗透着历史、社会和人生内容和意向的文学是不存在的。
马克思主义的艺术反映论具有自身的特性和优点。它注重文学同审美客体或对象世界的密切联系,以现实生活作为创作的源泉,认为作品是对历史、人生状态和趋势的能动的反映。这种特殊的精神创造活动,非但应不排斥创作主体的作用,而且十分强调作家艺术家的能动性。马克思在评论密尔顿的《失乐园》时指出,创作主体之所以从事这种特殊的精神活动是“出于同春蚕吐丝一样的必要”、“是他的天性的能动表现”[③]。列宁认为,将“反映”和“被反映者”机械地刻板地僵死地“等同”起来,必然流于“荒谬”[④]。他明确指出:“反映不是简单的、直接的、照镜子那样死板的动作,而是复杂的、二重化的、曲折的、有可能使幻想脱离生活的活动”,甚至有可能“使抽象的概念、观念和幻想”发生“不知不觉的、人们意识不到的转变”[⑤]。马克思主义的艺术反映论坚持生活是创作的基础和源泉,并不忽视艺术的假定性幻想、想象、乃至夸张、变形这些由于创作主体所加工和改变对象的原来面貌呈现出来的极其复杂的艺术形象样式。因此,判定马克思主义反映论是直观的、机械的、庸俗的反映论是一种误解。其次,马克思主义的艺术反映论本质上是一种创造性的实践活动。这种艺术实践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密不可分,两者之间存在着生态的良性循环。艺术实践活动又往往通过作家艺术家的艺术体验来运作和实现的,换言之,艺术体验是艺术家的精神实践活动的特殊方式。我们还应该指明的是,马克思主义的艺术反映论包含着满足主体需要的价值因素。马克思主义的人论和文学观念中的认知因素和价值因素是不可分割的融为一体的。从一般的意义上讲,完全脱离价值因素的人们的认知活动是没有意义的。对作家艺术家们的创造性的精神活动来说尤其如此。他们从事艺术实践和艺术实践活动时不能不考察和设计预期的目的,达到实现自己需要的途径和手段。自身由外界引发的内在意欲促使他们去寻找满足自己价值需要的价值承担者,这势必将对象世界的“自在之物”变成“为我之物”,认识到表现对象的价值属性,自觉地进行价值选择,实现自己的价值需求。因此,用反映论排斥价值论,或用价值论抵制、消解反映论的观点都是违反两者内在的深层联系的。
二、人的价值关系与文学
马克思主义的人论与文学十分注重在主体客体化和客体主体化的双向互动的辩证运动过程中深刻体认和揭示人和文学的价值属性和认知属性的相辅相成的内在的深层联系。从主体到客体,萌发人们对外部对象世界的需要和价值选择的序列或范畴;从客体到主体,形成人们对审美客体的认知和真理的系统或模式。尽管人的价值关系是以人的认知关系为根基的,但主体对客体的意欲使人永不停歇地向对象索取,满足自己的利益,引发人对主体自身的作用、功能、效益、实惠、功利、愿望、目的和理想的积极乃至顽强的追求。马克思曾指出:“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⑥]。这是从价值论视角对人的本性或本质所作出的精辟的科学概括。马克思从价值论的意义上揭示了人与物之间的血缘般的深刻关联:“只有当物按人的方式同人发生关系时,我才能在实践上按人的方式同物发生关系”[⑦]。恩格斯认为,人们首先历史地“产生对个别实际效益的条件的意识”而随后才“由此产生了对制约着这些效益的自然规律的理解”[⑧]。出于生存、发展的多方面的需要,人总是根据对象方面所提供的条件和现实可能性积极、主动地向外部索取。因此,“人只须了解本身,使自己成为衡量一切生活关系的尺度,按照自己的本质去评价这些关系,真正依照人的方式,根据自己本性的需要,来安排世界。”[⑨]文学艺术的创作实践作为作家艺术家的一种复杂的高级的精神活动,具有更加强烈的主体意识,必然引发出适合于自己需要的价值选择的冲动。审美主体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对形成作品的内容、性质、结构和功能将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因此,注重人与文学的价值论研究是完全必要的。
为了强化和深化对人与文学的价值论研究,应当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开掘和拓展。
(一)人的需求与文学
表现人的需求是文学价值因素中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是创作主体进行价值选择、实现和达到预期的价值目标的构成部分,也是引起读者对作品的价值关怀的最富有吸引力的因素。文学的价值选择、价值构成和价值效果都必须尽可能自觉地指向和满足人的价值需要,首先是满足人的精神生活的需要,其次是为了调整人与人之间的价值关系和人与社会之间的价值关系的需要。然而,文学表现人的价值属性和价值关系,以满足人的主体需要,也不能不遵循必要的规范,使之变得更加合理和有效、正确和适度。首先,必须处理好需要和条件的关系。产生和实现人的某种需要都是以一定的条件为基础的。只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将人的需要摆到一定的时代、历史、社会和现实生活的人的生态环境中进行审视,才能恰切地“根据效用原则来评价人的一切行为、运动和关系”[⑩]。因为,需要、价值观念和效用原则都具有“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特定环境。创作主体通过文艺创作表现人的价值需求,只有不断深化和强化对产生“个别实际效益的条件”的“自觉意识”,才能正确地有效地合理地反映和表现出人的切实的价值需要。忽视乃至消解条件的依托来主观随意性地追求人的价值需求,可能导致真价值需要的失落、伪价值需要的滋生,或者将对价值需要的表现庸常化、低级化,或者使之脱离现实条件的载负陷于审美乌托邦的虚妄的空想。其次,必须处理好需要和奉献的关系。现实的人生活在社会关系中。自我需要和他人需要、群体需要、社会需要构成一个相互制约着的价值圆圈和价值网络。彼此之间的需要的满足往往是以相互之间的奉献为后盾的。因此,文学应当自觉地表现需要和奉献的关系,宣扬排他性的利己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意欲是无益于人类的共同利益和社会的全面发展的。“当一个人专为自己打算的时候,他追求幸福的欲望只有在非常罕见的情况下才能得到满足,而且决不是对己对人都有利”[(11)]。文学表现人的奉献,并不意味着压抑乃至牺牲个体的自身利益,企图把每个社会成员变成禁欲主义的苦行僧;文学表现人的需要,也决非推行和倡导人欲横流,尔虞我诈,相互倾轧,从而使整个社会和人的生态环境陷于迷乱,只不过是主张通过文学正确、积极、合理、有效地表现人的需要和人的奉献的关系,有利于实现对现实生活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良性的价值协调。再次,人的需要本身也存在着一个结构、等级和档次问题。处于不同社会地位,拥有不同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以及拥有不同的财产和权利的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必将是大异其趣的。文学艺术作为创作主体一种复杂的高级的审美活动,通过作品主要表现和满足人们精神需要。这中间一定存在着多样性、多面性和多层次性,具有文野雅俗之别。高雅文学和通俗文学都是需要的。正确地把握和调整艺术生产的合理布局是十分必要的。只要是健康的、积极的、有益的精神产品都是应当得到支持和肯定的。我们努力倡导能弘扬新时代主旋律的艺术精品,是以发展多样化的文学创作为基础的。当然也要克服和防止有时可能出现的两个极端:或用高雅文学拒斥通俗文学,把“雅”提升到“纯审美”的程度,变成一种贵族化的文学小圈子里的自我玩耍,得不到广大读者的审美认同;或用通俗文学抵制高雅文学,以至把“俗”降低为“庸俗”、“粗俗”、“鄙俗”和“媚俗”,使文学创作的格调和品位滑落,同样不利于通过培养广大读者的正确的审美趣味提高人们的文化素质。
(二)人的目的与文学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12)]。人作为历史的主体承担着历史的职责,历史的目的完全可以还原和转换为人的目的。历史的运作和发展过程只不过是实现人的目的、利益、理想的载体而已。以历史的人为核心探寻历史的人的需要方能洞察人的历史的意义,历史的人虽然不能摆脱人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的制约和影响,但人终归是历史的主人,通过历史的发展,实现自身的利益、意志、目的和理想。世界上根本不存在着不包含着人和没有人参与的历史目的性,也不存在着康德所构想的那种先验的神秘的“善良意志”,这种带有虚幻性的思想企图只说明思想家的软弱,是对外部世界无能为力的表现。将重大的冷峻的社会历史问题转移到精神领域,通过思辨的玄想,给予虚假的解决,这无疑于自我嘲弄和自我麻痹。实现历史的人的目的和理想,必须通过变革社会生活的实践活动。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13)]。只有这样,才能使达到人的目即和理想提供现实的可能性。历史的人主宰人的历史的过程中,利益的杠杆始终起着魔力般的作用,“这种利益是如此强大有力,以至顺利地征服了马拉的笔、恐怖党的断头台、拿破仑的剑,以及教会的十字架和波旁王朝的纯血统”[(14)]。不注意利益原则或将利益原则狭隘化都是不妥当的,坚持和实践利益原则的合理性和正义性是人从事有目的自觉行动的规范。文学如何表现人的目的性,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有这样一种文学舆论认为,人是目的,表现人的目的即是文学的目的。对这种目的论的人论和文学观念应当进行梳理和分析。持有这种论点的学者多半受到人本主义思潮的影响,他们把人提升到“本体论”和“目的论”的意义上,无非是想弘扬人的主体地位,但他们所论及的人带有虚幻和抽象的性质,好像是一种虚假的共同体,而非现实生活中特殊的活生生的人。这里,存在着几个必须辨明的具有相关性的理论问题。(1)从目的性和工具性的关系看,这种目的论的人论和文学观念是排斥和贬抑工具论的,主张“人是目的,不是工具”。据称此判断源于康德。依我们所察,即使是康德的目的论中也在他自身的意向内肯定了工具对实现目的的作用。对目的论和工具论的关系问题,思想理论界包括文艺理论界的观点诸多歧异,十分有趣。有的主张“人的本体论”,有的主张“工具本体论”,有的用“人的本体论”反对“工具本体论”,有的用“工具本体论”反对“人的本体论”,有的忽而主张“人的本体论”,忽而主张“工具本体论”,有的由于各执一端,造成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两大思潮的激烈冲撞。其实,目的论和工具论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如果把它们放在合理的位置上和适度的范围内,两者是彼此相融,互为一体的。没有目的论的工具论是盲目的,没有工具论的目的论是空泛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既是目的,又是工具,如果人只是目的,不是工具,又怎样达到自身的目的呢?如果人只是工具,不是目的,那么这种不是为了实现人的目的的工具,则是毫无意义的。诚然,从总体和一般意义上来说,人是目的是问题的主导方面。唯“工具论”是错误的。我们通常讲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四个现代化服务、为建设精神文明服务,不仅在目的论的意义上,同时也说明文艺有作为工具使用的职能。(2)从目的性和条件性的关系看,实现人的目的是以一定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为前提的。客观方面的社会历史条件和主观方面的思想文化素质对达到人的预期目的是十分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具备足够的乃至充分的主客观条件,经过人自身的努力,才能使人的追求变成现实。因此,实现人的目的,要求拥有相应的条件。这是常识范围内不言自明的道理。作家艺术家们应当确立掌握人的目的性和条件性的辩证关系的自觉意识,克服和防止或过分拘泥于条件缺乏表现人的目的的胆识和勇气,或不顾条件所提供的现实可能性一味提升和拔高人的目的,使之陷入虚假和空幻的乌托邦境地,以求得文学创作的良好的生态。(3)从目的性和规律性的关系看,属于价值论范畴的目的性和属于认识论范畴的规律性必须取得一致的情况下,才能实现人的意志和愿望。没有对客观条件、客观环境和社会历史的状态及其发展的真理性体察和确认,提出和实现人的预期目的是不可能的,甚至会陷入十分盲目、困惑和尴尬的境地,受到客观规律的残酷的惩罚和无情的报复。不尊重客观规律性的人的目的性或不追求人的目的性的客观规律性都是无效果、无意义的。树立正确的科学的人论和文学观念必须辩证地理解客观规律性和人的目的性既统一又倾斜的表现形态。在尊重客观规律性的基础上,侧重揭示人的目的性,或在着意追求人的目的性的同时,展现人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社会历史的客观规律性,都是允许的,也是值得提倡的。这对拓宽文艺创作的领域,促使作品样式,内容和思想内涵的丰富化、多样化也是十分必要的。综合上面的有关论述,我们认为,只有正确认识和处理目的性和工具性、目的性和条件性、目的性和规律性的辩证关系,才有利于确立科学的价值论和目的论相统一的人论和文学观念。
(三)人的自由性和文学
人应当是自由的。作为从事个体文学创作的作家艺术家也应当是自由的。处于非自由状态的人和文学是必须加以改变的。人和文学的自由度,是标示和衡量社会解放水平的重要尺度。任何专制主义的制度、体制、机制和思想意识都是在压抑人的自由,都是限制解放和发展艺术的生产力的。然而,对自由本身也存在着一个怎样理解和运用的问题。自由这个概念所包括的内涵是非常丰盈而又深厚的。不能限于常识的范围内把自由和自由状态解释为无约无束,为所欲为。这是极其肤浅的、表面的。自由这个概念具有三种相互关联的含义。(1)本体论意义上的自由,指人本身存在的自由状态,或以自由状态存在着的人本身;(2)价值论意义上的自由,指人同外部世界的价值关系中的自由,或价值领域和范围中人的自由状态;(3)认识论意义上的自由,指人作为认识主体,通过实践活动,感受、体察客观对象的秘密所获得的真知使自身的思想和行为处于自由状态。只有人取得和拥有这三种意义上的自由,才能真正成为自由的人。自由因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必然是相对的,需要经过深刻、漫长的历史过程才能达到人的自由的高水平和高境界。也可以说,自由,不管是人的自由还是由作为创作主体的人所创造出来的文学的自由大体上都是同所属时代的社会历史的发展程度相适应的。因此,自由属于人的历史的范畴。为了正确阐释这个问题,有必要进行多方面的剖析。
首先,正确理解人的自由和自觉的关系。马克思曾把“人的类特性”界定为“自由的自觉的活动”,“人的生命活动是有意识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人能“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证明了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即“社会存在物”[(15)]。人的自由和自觉作为区别于动物的基本标志,使人的生命活动不是低级的盲目的,而带有自觉意识的特征。马克思是把人的自由和人的自觉当作具有内在相关性的同一序列的概念来论述的。换言之,马克思所强调的人的自由是一种自觉的有意识的人的存在和活动的自由状态。这种自觉的有意识的自由才使人获得了自主、自立和自为。这种自觉的有意识的自由才使人通过创造他的产品和作品“理智地复现自己”。我们经常从生命美学或以人的生命为本体的文学观念中看到对人的自由的一种不恰切的解释,即为了论证和支撑自身的论点,将马克思的观点曲成己意,脱离“自觉”来片面孤立地强调“自由”,使这种“自由”变成不包含“意识”、理智的“感性的生命存在和生命活动”,于是把本来是自觉的有意识的自由沦为本能意义上的生命本体,从而将人的自由和文学低级化和低能化。其次,正确理解人的自由和必然的关系。自由和必然的关系同样是人论和文学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马克思主义认为,“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恩格斯指出:“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这无论对外部自然界的规律,或对支配人本身的肉体存在和精神存在的规律来说,都是一样的”[(16)]。审美的或艺术的自由和必然的关系也是如此。尽管审美的或艺术的领域和范畴内的自由和必然的关系带有自身的特征,但特殊规律不能孤立地存在于普遍规律之外,它只能并势必表现为一般的普遍规律的特殊形式,或显示为特殊形式的一般规律或普遍规律。特殊规律应是对普遍规律的印证和补充。任何脱离普遍规律去孤立追寻特殊规律的企图都是徒劳的,所得到的结果终究会流于悖谬和迷误,变成一种非现实、非合理的虚假理念。“支配人本身的肉体存在和精神存在的规律”也无法“在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获得真正的有价值的合理的自由。任何脱离规律去探讨自由的努力都是一种天真的或懦怯的幻想,都会使现实的真正的合理的自由变成一种被扭曲、被夸张了令人哂笑的漫画。那种随心所欲、为所欲为的自由多半是头脑中的幻象,对现实生活中的人们包括从事精神劳动的人们的行为的合理性和有效性不发生任何积极的影响,只能导致盲目和蒙昧的麻痹。尊重必然,则自由存,蔑视必然,则自由亡。人和文学的自由也是如此。诚然,人作为创作的主体具有主宰和控制自己实践的能力,但人的创造活动不是随心所欲的,同样是有条件的,只有在认识和掌握规律,驾驭规律的情况下才能获得行动的自由。即便是最富有自由度的文学的想象和幻想也要受到时代和历史条件的局限。远古时代的人幻想飞天,只能想象出人身肉翅和脚踏风火轮,不可能设计出航天飞机和洲际导弹。因此,将自由描绘成“天马行空”般的创作主体的精神辐射和精神遨游,均属苍白而虚妄的幻想和奇妙而荒诞的审美乌托邦。用头脑中想象出来的自由作为摆脱和净化现实生活中各种束缚的替代物,以此求得化装的或变相的满足,这必然导致真自由的失落,虚假的伪自由的滋生和蔓延。再次,正确理解人的自由和自律的关系。如果说,人的自由和必然的关系属于人的自由和“外律”、“他律”的关系,那么人的自由和自律的关系则要求自身内部的调节和控制。人的自由不是无限的、广阔无边的,也不能理解为一种自我放逐和纵欲主义的精神扩张。作家艺术家应当是有教养的人。他们应当清楚利他和利己的关系,他们应当知道奉献和需要的关系,他们也应当明白自己的文学创作活动必须在正常的法律和道德的轨道上进行,通过有效的适度的自我调节和自我控制,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和自由度。
三、人的认知关系和人的价值关系的统一和倾斜与文学
注重研究人的认知关系的同时,深化和强化对人的价值关系的探讨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问题。文艺作为审美关系的高级形态。作为审美把握现实的特殊方式,不仅从对象的客观属性出发,而且要注重外部世界对主体的主观需要,实现主体的价值取向,满足主体的价值要求,给主体带来效益和惠赠。价值范畴作为中介使审美主体和审美客体发生审美关系。审美作为关系范畴。它的思想内涵不只限于客体,也不只限于主体,而在于主体与客体相对应、相交融、相渗透所形成的一种价值属性。这种价值属性本质上是一种关系属性。从关系属性即从价值观念着眼,观察和驾驭人与现实的审美关系,必然会优化和强化文艺把握对象的特性,提高和增强审美反映和审美创造的功能,对建构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美学文艺学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马克思主义十分重视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范畴,马克思恩格斯从主体客体化和客体主体化,即主客体“互化”的辩证运动中发现并深刻阐明了认知范畴和价值范畴的相辅相成的内在联系,既注重从客体到主体的认知系统;又强调从主体到客体的价值序列。主体为了满足自己的意欲、需求、效益、功利,必然向客体去索取,具有顽强的执拗的征服精神。马克思说:“只有当物按人的方式同人发生关系时,我才能在实践上按人的方式同物发生关系。”[(17)]马克思的话表明,价值属性既不单纯地表现为物的属性。也不单纯地显示为人的属性,而生成于客体和主体、“物”和“我”、对象和人的关系之中。这种价值关系的实质与核心昭示着主体对客体的需求,是主体对客体的意欲,是主体从客体能否满足自己的利益、效用、功能方面对它所进行的选择和索取。因此,价值属性是客体即价值承担者和主体即价值索取者的双方的属性和特性的辩证统一。客观对象一旦成为人的对象,人则总会以自己的需求和索取的眼光、态度来对待它们,并努力以一种强有力的实践手段,对其进行加工和改造,为自身所利用,以创造出造福于人的价值实体,满足主体生存和发展的需求。从这种意义上说,凡是人与客观世界发生对象性关系的领域,都存在着各种形态的价值关系。人与现实的审美关系是一种特殊的重要的价值关系。文学艺术作为一种复杂的高级的精神活动,具有强烈的主体性和主观性。作家艺术家的意欲、愿望和理想必然产生强烈的价值选择的冲动,激发出艺术创造的活力。审美主体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对作品的内容、性质、结构和功能发生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因此,注重艺术价值的研究,对深化和强化文学特性是完全必要的。艺术价值论应当成为艺术认识论的深化和补充。从严格的意义上说,认识或反映活动是有意识、有生命、有情感意志倾向的人的活动,因而不可能是纯然客观、全然冷漠的,必然包含着一定的价值需求因素和成分。艺术反映论往往蕴含着艺术价值论,艺术价值论总是以艺术反映论为基础。体现主体需要、利益、效用、功能的客体的价值属性不是凭空产生的,对象的客观属性是引发主体的价值取向的契机,它作为价值的负载体和承担者始终是主体的价值效益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人对现实的价值关系不能也无法脱离人对现实的认知关系。客体的体现人的需求和意欲的价值属性不是主体随心所欲赋予的,而是人根据自身的需求和意欲同对象的属性、特征构成的潜价值彼此对应、交互作用、通过实践历史地形成的。
因此,人的认知关系始终是以人的价值关系作为推动力的,人的价值关系又始终是以人的认知关系作为根基和导因的。如果人缺乏对外部对象世界的状况、条件、内部联系和发展趋势的深刻体认,便无法从主客体的关系范畴中把握和驾驭人的价值选择、这必然使人的价值关系陷于盲目和虚妄。如果说,脱离艺术价值论的艺术反映论是空洞的,是缺乏目的性和目标感的,那么排斥艺术反映论的艺术价值论是蒙昧的,是没有依据和基础的。我们认为,只有在两者的辩证联系中提倡某一方面,才能使其得到合理强调,才能使其得到有效的甚至最大限度的发挥。从这个意义上说,两者互补则生,相克则亡。不能将提倡艺术价值论同坚持和发展艺术反映论割裂并对立起来,以反对、否认、歪曲、丑化艺术反映论作为抬高和弘扬艺术价值论的前提条件,因为这种思路带有明显的主观随意性的痕迹。它的基本脉络是排斥客体因素对主体因素的决定、制约和影响,特别是将价值的主观性浓郁强烈的特性加以膨胀,随意发挥,作出主观唯心主义的界定和解释。
人的认知关系和人的价值关系既然是辩证统一的,那么一定会包含着差别和对立,存在着偏衡和倾斜。认识论或反映论同价值论之间所配成的不同形态或称为“这种关系的规定性”[(18)]对诱发和产生不同的人论和文学观念具有相应的甚至直接的影响。侧重强调人的认知关系,形成反映论的文学观念,侧重强调人的价值关系,形成价值论的文学观念。正常情况下,这两种文学观念是互补的,存在着相互包含的内在联系。事实上也是如此。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的反映论文学观念和价值论文学观念的内容和指向必然是相通的,两者所各自载负的意义是互生的。侧重不是偏废。只有在极端的情况下,即人为地将人的认知关系和人的价值关系绝然隔裂和对立起来,使两者之间的倾斜和偏重变成不合理不适度的失衡和失重,才酿成文艺反映论和文艺价值论的激烈的对峙和冲突。脱离文艺价值论单纯孤立地强调文艺反映论或排斥文艺反映论一味夸大、膨胀文艺价值论,都必然使两者流于荒谬。这无异于用过头肯定的方式否定自身,导致文艺反映论和文艺价值论的相互贬抑和双重失落。
文学艺术作为人与现实的审美关系的高级形态,同人与现实的认知关系、价值关系实际上可以简括地表述为美与真、美与善的关系。西方古代的一位哲人曾说美是真和善焕发出来的光辉。此话是很有道理的。不应当也没有理由将美和真、善,或将真和善、美,或将善和真、美完全割裂并对立起来。这样做,势必造成对美、真、善的疏离和畸变,导致对三者相生相济、融为一体的生态环境的损害和破坏。这并不意味着不重视乃至从根本上否定文艺表现假恶丑的特殊意义。文艺表现假恶丑作为文艺表现真善美的补充或反叛,都具有一定的价值。只要以特定的历史条件为依据,从生活和人生的实际出发,文艺创作的天地是极其广阔的,作家艺术家通过作品表现出来的精神意向也是非常复杂多样的。不管怎样说,真、善、美是人们的创造性活动中带有本体论意义的重要方面,按照传统的说法,人对客观世界的认知关系、伦理关系、审美关系是不可分割的关系网络。凡是关系范畴,都存在着价值属性,都存在着由价值的客观因素和价值的主观因素构成的价值系统。认知关系和审美关系也是价值关系。美不能脱离真和善,善也不能脱离美和真,三者互生互存而生辉,相分相离则失色。从真、善、美的整体关联中,探讨其中的某一方面,必然丰富和拓展真、善、美的理论空间,为正确的、健全的理论建树开辟新路。从人们的认知关系、伦理关系和审美关系的总体框架中集中研究其中的某一环节,往往可以通过辩证的把握方式,取得新鲜的巨大的思想成果。
注释:
① ②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62—463、463、234页。
③ 《剩余价值论》第1册,第432页。
④ 《列宁全集》第2卷,第330页。
⑤ 《列宁全集》第38卷,第421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69页。
⑦ (15) (17) (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4、96、124、125页。
⑧ ⑩ (1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57、457、153页。
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51页。
(12) (13)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8—119、152、103页。
标签:文学论文; 本体论论文; 目的论论文; 艺术价值论文; 社会属性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艺术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文化论文; 历史规律论文; 社会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