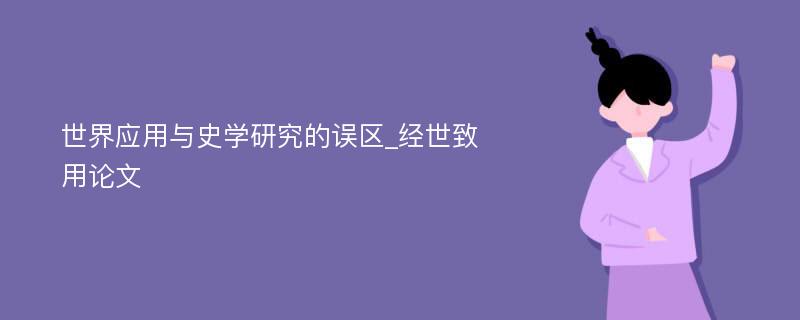
经世致用与史学研究的误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世致用论文,史学论文,误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世致用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之一,而中国史学和社会现实——尤其是现实政治之间的那种如胶似漆、难解难分的关系,是史学经世传统的重要表征。在这种传统的浸染下,“以史为鉴”成了圣君贤相们自我儆戒的规条,“史学所以经世”则被有为史家奉为治史修史的基本原则。正因如此,史学的命运紧随着政治的沉浮而沉浮。今天,我们通过对中国史学经世传统的寻踪探幽,审视、反思,或可找到历史研究与社会现实的最佳结合点以及走出史学困境的新路径。
一、史学经世与史学研究
史学经世的前提应该是秉笔直书,追求历史之真实。作为一名严肃而有责任感的历史学家,必须双肩担道义,超然物外,客观公正,不存偏私,实事求是。然而,通观中国史学史,史家群体之中,为了以前朝真史儆策世人,备受冷遇者有之;为了将当朝史事告于后世,罹难被祸者有之;为了所谓道德教化,为尊者隐,为显者讳的有之;而为了全身避祸或求荣求显,唯上是从,趋炎附势,曲笔作史的亦有之。从某种意义上讲,经世致用易,秉笔直书难,在两者不可两全时,坚持前者易,坚持后者难。曲笔有时是为了保命、求名、求显,有时则是为了实现其经世致用的宏愿。
在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下,君王的意志就是全社会的意志,因此,史家难以把握自我,实现自我。在很大程度上,他们的治史原则——实事求是、秉笔直书只能是一个虚悬的、可望而不可及的理想。每一朝代都有史家矢志铁笔写史,充当社会的良知,而代代都有史家因无法挣脱强权政治的桎梏而良知泯灭。在这种情势下,一些史家试图另辟蹊径。作为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殊文化现象,乾嘉学派对史学经世与史学研究之间关系的思考与处理,值得我们认真考察和探讨。
随着中央集权制的高度完善,清政府对于思想文化的高压和垄断,可谓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清代雍、乾两朝的文字狱之苛酷,在中国历史上实属罕见。显然,在布满政治神经的极为敏感的史学领域,如果史学与政治之间依然保持那种固有的、难以割舍的关系,则史家就随时都有因触犯莫名忌讳而罹遭惨祸的危险。为此,史家陷入了无以自拔的两难境地:一如既往地执著于史学经世的传统,坚持以警世为己任,为王者求资鉴的原则,凭着正义感和使命感,善恶必书,美丑俱录,执意求真,直抒胸臆,那将触犯规条,招来横祸;如果为保性命,阿谀逢迎,唯上是从,任情褒贬,曲笔作史,又将于心不安。经过小心翼翼的试探和战战兢兢的求索,在磨去了棱角,隐藏了斗志,压抑了参与社会政治的欲望之后,乾嘉史家们终于找到了一条可使性命无虞,可使良知不泯,可使理想附丽,可使精力投注的归宿——历史文献考据。
考据是对既有文献和史籍的考索与校订,是对历史真实的刻意追求,是对中国史家秉笔直书传统的一种曲折反映。对于乾嘉时期的历史考据学派来说,考据可以远离现实社会的是是非非,用不着终日惶惶然、惴惴然,只要不去刺激当朝统治阶级,任何内容都可以作为考证的对象,至于这些内容是否关乎世道人心,则不必过分在意。他们之所以选择以所谓“厚古薄今”为特色的历史考据,是因为研究“今”则必先满足政治的需求,而研究“古”却可远离现实,政治干扰较少,人身自由较多。可以于世无患,与人无争,于己有益。
在恶劣的社会环境的挤压下,乾嘉史家抛弃了史家史学经世的优良传统,淡忘了史家肩负的神圣职责,疏远现实,醉心古史。应该说,这是中国史学的莫大悲哀。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以乾嘉历史考据学为转机,在摆脱了历史和现实政治之间的那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纠缠后,通过超脱于现实,沉湎于学问的治史实践,中国史家开始尝试以学者式的(而非政治顾问式的)思维反观中国史学,他们开始朦胧地思考史学是什么?史学与政治,史学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应如何处理等专业化问题,从而使史学露出了成为一门独立于政治之外的专门学科的端倪。
在西方,追求纯然学术,标榜为学问而学问的学风一直受到社会的肯定和鼓励,而在中国,为致用而治学的功利主义学风却起着学术导向作用。史家德行的高下,成就的大小,往往以其著作的经世致用程度来论定。史家力倡将匡时救世之深意寓于叙事论史之中。王夫之认为:“为史者记载徒繁,而经世之大略不著,后人欲得其得失之枢机以效法之无由也,则恶用史为?”①这种文以载道,史以经世的思想为顾炎武表现得淋漓尽致:“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曰名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②在对史学得失进行综括的基础上,清代史家章学诚鲜明地提出了“史学所以经世”的著名论断:“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且如六经同出于孔子,先儒以为其功莫大于《春秋》,正以切合当时人事耳。后之言著述者,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则吾不得而知之矣。”③就是说,只重考据或空发议论的史学研究,是不明史学之真义。只有把经世致用之宏旨寓于其中,才可算得真史学。从以上史家对史学的有关论述中,我们发现了乾嘉史学的症结所在。
然而,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辩证的、复杂的。环境的挤压,使中国史学在乾嘉时期游离出了正常的发展轨道,而在这同时,也给史学创造出了一个转轨的机遇。
梁启超说:“清代学派之运动,乃研究法的运动,非主义的运动也。”④这种论断,可谓切中肯綮。所谓“非主义的运动”,在这里可以理解为:不高标史学经世的目的性,不讲求史学研究的效用性,不侈谈史学为谁服务的原则性,不讲世界观,只讲方法论。这里所说的方法,实际上是从顾炎武、阎若璩到惠栋、戴震渐次总结归纳出的一套系统的考据方法。正因为不措意“主义”,乾嘉学者才可以做到“……不以人蔽己,亦不得以己自蔽。不为一时之名,亦不期后世之名。”⑤摒除主观成见,追求学问真谛。对于乾嘉学派的积极影响,梁启超作了这样的归纳:“一、读诸大师之传记及著述,见其‘为学问而学问’,治一业终身以之,铢积累寸,先难后获,无形中受一种人格的观感,使吾辈奋发向学;二、因此种方法以治学,能使吾辈心细,读书得间;能使吾辈忠实,不欺饰;能使吾辈独立,不雷同;能使吾辈虚受,不敢执一自是。”⑥逃避现实之风气万不可长,沉溺古学之研究绝不可倡,但为求真理,终身许之,忠实不欺,讲求创意,虚心向学的精神还是足可称道的。这种学风的形成,固然与文化高压政策有关,但更多的是得益于对中国史学经世传统的合理扬弃。
纵观中国史学史,真正使史学游离出现实社会和政治的大概只有清代乾嘉时期。或许,正因为无视现实,不问政治,才使他们敢于以求真为名怀疑一切学术领域的成说,不以所谓“圣哲父师”之言为是,凡事寻根问底,必求是非,如梁启超所说的那样:“清学派时代精神,盖无论何人之言,决不肯漫然置信,必求其所以然之故;常从人所不注意处觅得间隙,既得间,则层层逼拶,直到尽头处;苟无足以起其信者,虽圣哲父师之言不信也。”⑦
应当指出,不受“主义”支配的所谓纯客观的、超阶级的史学研究是不存在的;无视现实需求,为历史而历史的史学研究也是没有生命力的。史学一旦失去现实社会尤其是现实政治这块沃土,就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如果把史学看作史家寄托思古幽情的工具或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那将是史学的严重堕落。现实性是历史学的根本属性,离开现实性,史学必将失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史学的研究范围、研究次序以及研究重点的确定,应以现实的需求程度为尺度。从本质上讲,现实需求是推动史学研究向前发展的根本动力。反过来说,历史学是对现实的一种特殊认知活动,对历史过程的每一认识,都是对社会现实的一种特殊审视,因此,作为历史学家,不但应该具有强烈的致用意识,而且还应该具有政治家的洞烛其奸的能力和敏锐判断,善于将思维的触角伸入各种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内部,以史家特有的思维方式、研究手段和方法参与社会,服务现实,指导人生。
不过,我们必须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对现实——尤其对政治的过分亲和,有时会混淆政治和历史之间的界限,丧失史学应持的理性原则,从而使史学沦为政治的婢女。在中国史学史上,这种先例不胜枚举,而文革时期的史学悲剧,更不应从我们的记忆中轻易地抹去。我们一向强调史学服务于无产阶级利益的功能,而当这种功能和某些历史真实发生抵牾时,史家一般因服从阶级利益而难顾历史之真实。从本质上讲,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所得的科学结论,应与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相一致,然而,无庸讳言,由于一些主观或客观的原因,史家很难避免研究成果与现实功利间的非一致性。
二、史学经世与史学误区
本世纪三十年代以来,我国学术领域逐渐发展壮大起来了一支马克思主义史家队伍。在现实政治需求的推动下,他们推出了一批和政治斗争密切相关的史学论著,如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等。这些史著,在注重战斗性和效用性的同时,力求内容和观点的客观性和科学性。但是,强烈的使命感以及斗争需要的紧迫性,使他们在革命性与科学性二者不可兼得时,不假思索地选择了前者。在研读了这些著作之后,我们很容易发现,其政治价值似乎更大于其学术价值。以郭沫若为例,他自己也承认,早年的某些史论,在对史料还没有充分接触之前,已让感情跑到了前面。这里所讲的“感情”,大概就是我们常讲的无产阶级感情。郭老的史学研究,有着十分明确的目的性,那就是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他的很多史著,都对革命事业和学术研究,起过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很显然,其某些论著,往往以革命的义愤代替了科学的分析。四十年代,当他看到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御用文人吹捧秦始皇时,他便对秦始皇极力地贬抑,因为秦始皇采用的是韩非的思想主张,他便“恨乌及屋”,对韩非的思想也大加挞伐。只因为吕不韦和秦始皇有过斗争,他便不惜笔墨对吕不韦尽情歌赞,甚至武断地论定:“吕不韦是封建思想的代表,秦始皇则依然站在奴隶主立场上。”⑧这些结论,显然有悖于历史事实。遗憾的是,作为一种较为普遍的文化现象,这种偏颇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于其它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身上。
建国后的史学,在论证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人民政权的合理性,以及党的政策路线的正确性方面,的确发挥了任何其它学科都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然而,长久以来,由于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并未能对史学领域存在着的问题进行全面而深刻的反思。对史学为无产阶级利益服务的片面理解和对史学自身发展规律的漠视,严重地阻滞着史学的正常发展,某种程度上也为文革时期影射史学的恶性泛滥提供了机缘。
我们不妨以半个多世纪以来,关于洋务运动评价的几次反复为例,来考察一下史学领域在经世致用问题上存在着的一些偏颇。
早在三十年代,陈恭禄、蒋廷黻、钱穆等就指出,洋务运动是一次“近代化运动”⑨。四十年代初,马克思主义史家李达、何干之等也一再肯定了洋务运动在抵御外侮、挽回利权方面所起的作用及其对促进近代化进程的首创意义,称洋务运动“具有爱国主义性质并使中国社会开始向近代社会迈步”⑩。这些结论,迄今仍闪耀着真理的光芒。但遗憾的是,有关这一问题的讨论和当时的政治问题纠缠在了一起。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的御用文人为了证明其对外妥协,对内镇压人民革命的合理性,别有用心地把洋务官僚说成是“中国近代化的先驱领袖”;把洋务运动说成是“以夷器和夷法来对付夷人”的爱国御侮运动;把洋务运动的失败和中国近代化的断层归结为时人不理解洋务派“对外避战以图自强的方针,而对洋务派的自强事业多方掣肘”(11)。表面上看,这些结论,似乎与李达等并无多大分歧,但其真实用意是昭然若揭的,即美化国民党的最高领袖蒋介石,美化国民党的妥协路线,把抗战胜利后中国近代化的希望寄托于处处依赖和仰仗美国的国民党政府。对此,范文澜、胡绳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健将,以笔作枪,分别在其论著中作出了与国民党御用文人针锋相对的结论,断言蒋家王朝与洋务派之间是一脉相承的关系,洋务运动是“重在防内,并无对外意图的卖国运动”,“加深了中国的殖民地化”(12),“为帝国主义开辟了道路”(13)。这些论断,虽然接触到了洋务运动的一些实质,但出于满足特殊政治需要的考虑,对洋务运动采取了极端的、全盘否定的态度,从而将洋务运动打入冷宫。严格说来,当时两个阵营关于洋务运动的笔战,并不能算是真正的历史研究。他们都把史学当成了政治的附庸、喉舌以及论证某种政治见解的工具。
六十年代初期。姜铎对范文澜、胡绳等人的观点提出质疑,重申三十年代李达等史家关于洋务运动的正确论断,肯定“洋务运动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历史的潮流”(14)。此外,对洋务运动与资本主义以及中国近代化之间的关系,也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与评述。然而,当时不少人把姜铎对洋务运动的肯定与当时的所谓翻案风硬加比附,肆意批判,从而扼杀了其正确思想的萌芽。十年动乱期间,“四人帮”的御用文人们竟把洋务派比做走资派,这就把洋务运动的研究推进了死角。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李时岳、胡滨等才率先打破沉寂,系统论述了洋务运动的性质和作用,明确地提出:“……洋务运动虽然不属于反帝反封建的反抗运动,但它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缓慢地逐步地朝资本主义方向运动,在暗地里或客观上为中国的独立和进步积累着物质力量”,“表现了中国社会不可逆转的方向”(15)。毫无疑问,这是得当之论。然而,近年来有些史家追逐时尚,强将洋务运动中的一些政策措施,暗比我国现今的改革开放政策,这就难免有重蹈旧辙之嫌了。从对洋务运动评价的循环反复过程中不难发现,我们在对史学经世的认识上还存在着许多问题,在对历史和现实,尤其是历史和政治之间关系的认识上还存在着误区。
误区之一:把历史为社会现实服务,狭隘地理解为为政治服务,从而使史学只能在政治的狭窄通道上蹒跚而行。现实社会对史学的需求是多方面的:既有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也有文化的、伦理的和其它各层面的。历史学家应该从各个不同的角度,通过对更为广博的领域进行研究和探索,从中挖掘和提炼出富于哲理性和启示性的内容,以更为理性的方式,从更为完整的意义上为包括政治在内的现实社会服务。然而,自近代以来,由于内忧外患的强烈刺激,史学的功能出现了单一的政治化倾向,史家一直在服务于政治的非学术轨道上运行。严重的功利主义价值取向,使史家笼罩在一片浮躁的学术气氛之中。
误区之二:与上述问题相联系,过分地突出了政治对历史的需求,过分夸大了历史对政治的借鉴作用。尊重传统是中华民族的一个较为突出的心理特征,而重视历史则是这种心理特征的具体体现。当出现了纷繁复杂的社会问题时,统治阶级不是直面现实去寻求对策,而是反求史籍以期得到资治的启示。中国浩瀚的史籍犹如一座“社会医库”似乎一切医世良方都寓于这个无所不备的医库之中。明君们可以从中得到治国安邦的宝鉴,而昏君们又总能由此得到为恶心安的佐证。中国古代社会又以超稳定和少变化为特征,某些问题重复再现或相近相似,如土地集中问题,灾荒、流民问题,阶级矛盾和统治危机问题等总是周而复始地出现。这种社会特征,使统治阶级养成了从历史中直接索求问题答案的惯性。而史家似乎也总能以历史研究为手段,最大限度地满足统治阶级的这种需求,所以在传统的中国,历史对政治的指导或资鉴作用便显得异乎寻常地重要。而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却以剧变和多变为其基本特征,至于当代社会,新情况、新问题更是迭次出现,各种事物(尤其是政治事件)的发展千变万化,并无固定模式,靠经验、仿传统必将一筹莫展。所以,如果我们仍以向后看的方式,企图简单地、直接地从古人那里寻求解决现实问题的现成答案,就未免显得过于迂腐了。传统社会的高层决策,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历史的经验,而在现代社会,更多地可能要参考现代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心理学以及运筹学等多方面的最新理论。因此,从表面上看,历史学的地位似乎每况愈下,我们所讲的史学危机,大概与史学的这种政治功能的相对削弱不无关系。当今史家的心理失落,从本质上讲是对传统史学的辉煌备加怀念的一种反映,于是,个别史家急切地以强化史学的经世致用功能为借口,试图通过加大史学影响政治的力度的途径,靠更为急功近利的方式来更为直接地为现实政治服务,以求摆脱目前面临的困境,结果是物极必反,欲速则不达。每一时代的史学,都有自己的特殊地位和功用,只是目前我们尚未找到当今史学的确切位置。不过,有一点清楚的,那就是:传统的、过分而单一地强调史学政治功能的经世致用观,并不能引导史学走出低谷,迈向蓬勃发展的康庄大道。
误区之三:存在着对历史服务于现实的方式、方法的错误观念。为了达到服务于现实的目的,有些史家以牺牲史学的客观性和科学性为代价,牵强附会,影射类比;为了满足某种特殊的社会需求,甚至可以随时随意地调整自己的某些史学观点,以致给人造成一种错觉:史学似乎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女孩,史家可以对其随心所欲,任情涂抹。任何一项重大的政治举措,都可以从历史中找到有力佐证。这就使普通民众产生了一种厌倦心理,认为与其费心劳神地去看那些信度不高的专业化史著,倒不如轻松怡然地去读一些野史稗乘,这种流弊,是造成史学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于古代并不存在学术自由的环境,致使学者不敢直截了当地议论现行政策或直陈政治见解。为了避祸保身,不忤当道,只好采取引经据典,委婉含蓄的表达方式。于是史学便成了满足这种需求的最理想工具。梁启超对此曾有过精辟的论述:“中国思想之痼疾,确在‘好依傍’与‘名实混淆’。……以清儒论,颜元几于墨矣,而必自谓出孔子,……康有为之大同,空前创获,而必自谓出孔子;……则亦依傍混淆也已。此病根不除,则思想终无独立自由之望。”(16)中国人固有的重传统、崇权威的文化心理,是这种“好依傍”和“名实混淆”学风的成因。本是自己的创获,但为了避免因惊世骇俗而被指为大逆不道,必须依傍于古代的权威以证明自己的思想“古已有之”。毫无疑问,史学是满足这种需求的最理想工具,它为此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这种学风的长期泛滥,曾严重地阻碍了中国史学的独立发展,成为牵强附会和影射史学的温床。列宁指出:“在社会现象方面,没有比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而站不住脚的方法了……。”“如果不是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不是从事实的联系去掌握事实,而是片面地和随意地挑选出来的,那么事实只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都不如。”(17)任何为了某种主观意图,不顾事实的内部联系,随意拚凑和罗列材料的行为,都是不科学的、不严肃的,都是对历史科学的摧残和践踏。明乎此,我们才能寻回完整而独立的富于理性精神的历史科学。
关于史学如何服务于现实,1980年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史学会代表大会提出了如下见解:“历史科学满足政治需要的正确理解应该是:历史向社会也向政治提供新的科学研究成果,而社会和政治则利用这种成果作为自己的活动向导。这样,不但丝毫没有伤害历史作为一门科学应有的尊严,相反,它既增加了科学的荣誉,也增加了社会主义政治的荣誉。”“历史学家为人民服务,可以是与迫切的现实问题直接有关的见解或建议,也可以写出高水平的著作,开拓人们的历史视野,提高人们的科学态度,推动学术进步,争得祖国的荣誉。”(18)实践证明,这些见解是比较科学和严肃的。
现实需求是历史学发展的根本动力,但作为历史学家,首先必须坚持历史科学的理性原则,他应该具有“入世”和“出世”的双重品格。入世可以紧切时代的脉膊,既可充当社会实践的积极参与者,又可永葆史学经久不衰的发展活力,从而将我国史学经世致用传统的精华部分发扬光大;出世则可以一种客观超然的平和态度,以局外旁观者的清醒姿态,保持理智,不逐时流,以事实为根据,以科学为准绳,纵论古今,斟酌得失,永远充当社会的良知,以史学独有的方式服务于社会,服务于政治。只有如此,史学才能焕发青春,永具魅力,发挥其鉴往知来的巨大作用。
注释:
①②《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八》;《日知录》卷十九《文须有益于天下》。
③《文史通义》卷五内篇五《浙东学术》
④⑥⑦(16)《清代学术概论》第十、十三、十一、二十六。
⑤《东原集》卷九《答郑丈用牧书》。
⑧《沫若文集》卷十五,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65页。
⑨陈恭禄《中国近代史》,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176页。
⑩何干之《中国早期启蒙运动史》。
(11)转引自《群众》,重庆,1945。
(12)范文澜《中国近代史》,延安1940年版第78页。
(13)胡绳《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33页。
(14)参见《人民日报》1962年9月13日。
(15)李时岳《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
(17)列宁《论民族问题和民族殖民地问题》,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19页。
(18)《中国史研究动态》1980年第5期。
标签:经世致用论文; 政治论文; 洋务运动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历史论文; 文化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读书论文; 清朝历史论文; 历史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