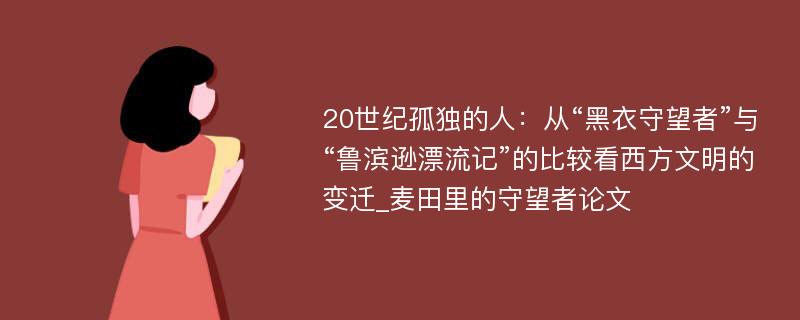
孤独的20世纪人——从《麦田里的守望者》与《鲁宾孙漂流记》的对比中看西方文明的变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看论文,孤独论文,世纪论文,漂流记论文,麦田里的守望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摘要】《鲁宾孙漂流记》与《麦田里的守望者》塑造了两个在本质上完全不同的孤独者形象。鲁宾孙的孤独是一种客观状态,是由自然环境的隔绝造成的,他心灵上并不孤独,他有信仰,有追求,有创造,一只航船就结束了他的孤独;而霍尔顿的孤独则是一种永远无法排遣的心灵上的孤独,是一种心理感受,面对异己的文化环境,他感到压抑、厌恶、失望、悲哀、仇恨,这是20世纪西方文明病,无药可治。这是由于传统价值观的崩溃而导致的交流障碍必然产生的恶果。从这两个孤独者形象的对比中,反映出了从18世纪到20世纪西方文明的变迁。
【关键词】《麦田里的守望者》 《鲁宾孙漂流记》 西方文明 孤独 20世纪人
这是两本几乎毫不相关的小说,一是英国作家笛福在18世纪初所写的《鲁宾孙漂流记》,一是美国作家赛林格本世纪中期的著作《麦田里的守望者》。他们之所以能被放在一起讨论,是因为这两部小说产生于西方文明发展的不同阶段,在处理相似的人的境遇问题上,其差异正揭示了西方文明的变迁。
18世纪是西方文明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与启蒙运动脱胎换骨的改造而迈入现代化的开端。这是一个朝气蓬勃、充满活力的时代。征服、创造、发展是时代的主旋律。这个上升时代的气概与魄力反映到了鲁宾孙身上。20世纪是西方文明高度发达的时代,但也是产生精神危机的时代。鲁宾孙的自信与乐观已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麦田里的守望者》中的主角霍尔顿的悲观与消沉。这是18世纪西方文明与20世纪西方文明的本质差异。这个差异在两部小说的对比中得到了充分的印证。
一、孤独者
霍尔顿与鲁宾孙的共同点在于,他们都是孤独者。鲁宾孙一人在孤岛上生活了20多年,其孤独是不言而喻的。而霍尔顿在自己熟悉的繁华都市中漫游,出入人群,本不应是孤独的,可他一再声称自己孤独得要命,贯穿小说始终的主题就是他的孤独。其实,此孤独非彼孤独。鲁宾孙的孤独是一种客观状态,而霍尔顿的孤独则是一种心理感受。如要在语言上恰当区分,前者应称为“独处”;后者才是真正的孤独。说到底,孤独本该是一种心理感受,独处之时往往并非是孤独之时,有时甚至是最积极、最充实的时刻。因而哲人先知都讲究独处。鲁宾孙虽处于一种与世隔绝的状态,但他的生活基调是蓬勃向上、生机盎然的,充满创造的激情、征服的鼓舞、成功的欢乐与宗教的慰藉。虽独处荒岛,实无孤独空虚对心灵的咬啮。这正是18世纪西方文明充满信心、前途光明的体现。
作为20世纪大都市人的霍尔顿体会到的则是一种性质完全不同的孤独,一种无法排遣、令人绝望的孤独。他是一个敏感的少年,对成人社会的虚伪极度反感,同正统的行为规范和流行的价值观格格不入,他对现代教育不感兴趣,对学校生活十分厌倦。故事发生在他离校出走的那一天。那天,与教师和同学的交往使他情绪低落,倍感孤独,于是连夜离校,来到自己家所在地纽约市。但他过家门而不入,而是漫无目的地游荡,希望摆脱压在心头强烈的孤独感。他乘车,住饭店,进酒吧,去公园、影剧院、展览馆、娱乐场、车站等任何有人群的地方,找一切机会同人接触。其中不仅有过去的同学、尊敬的师长、亲密的女友、喜爱的妹妹,也有出租车司机、电梯工人、乘车旅伴、酒店邻座等任何场合偶然碰到的人,甚至还有妓女、恶棍等。一有机会,他就要与人“交谈”,但最后他也未能摆脱孤独,反而使这种感觉一步步加深,变得更致命了。
这种在20世纪大都市人群中感受到的孤独,在霍尔顿身上还表现为他对环境的不适应上。他看什么都不顺眼,他讨厌电影,讨厌广告,讨厌明星、作家、社会名流,讨厌学校、教师、同学、学业,讨厌周围的人,讨厌一切。他整天沉浸在对过去的怀念以及逃离社会的不切实际的幻想中。他经常的感觉就是恶心、压抑、无聊、厌烦、悲哀、失望、仇恨等。他同鲁宾孙一样都被置入一个自己所不能认同的环境中:一个是原始的自然环境,一个是异己的文化环境。他们都在“寻求自己所处的环境无法提供的东西”〔1〕,因而两人都是孤立的。 但两人的心理感受则大不一样,一个是战天斗地、改造世界的充实,另一个则是无能为力、痛苦绝望的空虚。
霍尔顿的这种孤立才真正地是人的困境,比身陷孤岛还要严峻。这样的孤独鲁宾孙是体会不到的,它是20世纪的时代病,源于工业文明的高度发展。现代化大生产使人变成流水线上的机器人,无法体会主动性与创造性的乐趣;过度城市化使人变得冷漠,互不相通;全面商品化使人的关系变成交易,全无温情;大众宣传媒介使人的趣味标准化、庸俗化;高度的物质享受使人麻木而缺少能动性与革命性;而对更高物质享受的追求又使人疲于奔命,无暇顾及自己的精神生活。这一切都极大地破坏了人与人的交往基础,使现代人身居闹市,在熙熙攘攘中从早忙到晚,疲惫不堪却仍感到孤独寂寞。
二、交流障碍
20世纪人的孤独产生于一种可称为交流障碍的文化现象。人与人交流不仅限于居住在一起,相互碰面,相互交谈,更重要的是精神沟通。而现代社会却使这种沟通变得越来越困难了。现代人可以在办公室里同成千上万的人打交道,出入拥挤的公共场所,住在塞满人的高楼大厦里,乘车船飞机到地球任何一个角落,通过各种传媒可以同任何人交谈,了解世界各地发生的事情,但他却没有也不可能同任何人发生真正的交流。现代化无疑给人与人的交流提供了最大方便,但现代社会却是一个交流匮乏的社会。鲁宾孙漂流的目的是“寻财”,即使在荒岛上,他也是以对自然的改造与物质资料的丰富为目的,那是18世纪西方文明的主题。而霍尔顿漂流的目的是“寻交流”,这是20世纪人的精神危机。霍尔顿在短短的几天里,东奔西走,昼夜不停,寻求的就是同人的“交谈”。但是,无论是熟人还是生人,亲人还是外人,上等人还是下等人,聪颖智慧的人还是愚蠢麻木的人,他都无法与他们实现真正的交流。在无可奈何之中,他甚至在旅店里找了个妓女,并不是想解决性问题,而是要找人交谈。但他很快就发现那不过是赤裸裸的金钱交易,对方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根本不愿同他多说几句话,使他大失所望。经过多次失败,他终于认识到无法同任何人进行一次“理智的交谈”。他不断得出结论:“人们对什么都不注意”,“别人从来不相信你”,“别人总是坏你的事”,“他们从来不想理智地讨论任何问题”,“你说话时他根本不听”。交流如此之难,不得已而求其次,就用废话、空话、瞎话、言不由衷的话、文不对题的话、莫名其妙的话来维持一种贬值的交流。在霍尔顿同人的交谈中,充斥着这类话,因而他说自己是一个“最大的说谎者”,高兴起来可以一口气说几小时的瞎话。但这样的交流并不能给他多少安慰,反而加深了他的孤独感,以致对交谈者产生反感与仇恨。几乎每次同别人交往后,他都有恨对方的感觉。这正是存在主义“他人即地狱”的写照。这也反映在霍尔顿所在学校的同学关系上。几乎每一个人都在恨另一个人,相互讨厌却又因忍受不了孤独而相互交往。相互交谈有时简直就是相互虐待。霍尔顿说他无法忍受看着别人的脸,甚至在排队时看前面人的脖子都受不了。如果发生战争,他不得不同这样一群人并肩作战,那还不如把他拉出去枪毙算了。小说自始至终都是霍尔顿寻求交流的艰难历程,在他面前,一座座偶像倒塌,一次次努力落空,一个个希望变成失望。他为孤独所压倒,痛不欲生,“我想自杀,我真想从窗子里跳出去”(第104页)。 他有时甚至觉得自己已经死了,消失了。他也想到逃离社会,到一个没有人认识他、他也不认识任何人的地方,从此装聋作哑,一辈子再也不说话,“那样就再也没有必要同任何人进行愚蠢而无用的交谈了”(第198页)。
20世纪人的这种困境,18世纪身陷孤岛的鲁宾孙是体会不到的,虽然他也说“现在我要开始过一种世界上闻所未闻的忧郁而寂寞的生活了”〔2〕,但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个精神饱满、乐观充实、 奋进向上的人,完全没有孤独者的心态。“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3〕。笛福的时代是资本主义的少年时代, 无论他让鲁宾孙怎样呼天抢地地诉说自己的孤独与无望,也全无感染力;而霍尔顿即使不说,我们也能在书中体会到这种心境。鲁宾孙是被迫处于无法同其他人交流的境地,他从来没有放弃回到文明世界的希望。同霍尔顿的弃绝相反,他的人生观是参与,对他来说,交流障碍不存在,甚至在不同种族、不同文化的人之间也不存在。18世纪西方人相信,西方基督教文明是“世界语”,通过它可达到全人类的充分交流。他一旦获得“星期五”,就着手把他改造成有共同语言的文明人。这在小说中并不难,甚至无需用语言,凭手势即可。而对霍尔顿来说,无论多么现代化的交通通讯工具都无法把他与其他人拉近一步。鲁宾孙最后同吃人生番、异教徒、异端分子、叛逆者都达成了共识,在小岛上几乎重建文明社会。而霍尔顿身处文明世界却孤苦伶仃,走投无路。鲁宾孙还有一种更为深刻的交流,即同上帝的精神交流。这种交流使他达到“身心泰然,无忧无虑”的境地,“因为他时时在我身边,跟我灵魂交通,支撑我,安慰我,鼓励我,使我信托他的精力,并且唯愿今后永远在我身边,充分弥补我寂寞生活中的种种缺陷,使我不再感到远离人群的痛苦”(《鲁宾孙漂流记》第99页)。“这样,我的生活比有交往的生活还要好;因为……通过祷告同上帝谈话,不是比世界上人类社会最广泛的交游更好吗?”(《鲁宾孙漂流记》第120页)上帝远在彼岸,虚无缥缈, 鲁宾孙却同他达到了“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的神交程度。这是“杀死上帝”后的20世纪人绝难有的享受。
三、价值观念的崩溃
现代社会交流障碍产生的根源在于价值观念的崩溃。传统道德导向的价值观让位于功利导向的价值观。而功利导向的价值观因其自身固有的缺陷造成价值相对化与多元化,形成混乱局面,使人丧失交流的共同语言。有学者指出:启蒙后形成的现代文明所能建立的唯一道德系统是功利主义,而有用与否是因时间、因环境、因人而异的。于是,超越个人的绝对标准丧失了,“由此可见,启蒙运动不但改变了欧洲的世界观,由于其本身即包含了‘道德真空’的基因,遂为日后‘价值失落’,没有目的与无意义的世界播下了种子”〔4〕。在18世纪, 这种子尚未结出恶果,这种新价值观因而具有很强的生命力与吸引力,反映在鲁宾孙身上,就是“世上一切好东西对于我们,除了拿来使用之外,没有别的好处。”(《鲁宾孙漂流记》第114页)一棵大树在他眼中只是木板, 可以造船架屋置物;飞禽走兽只是食物,可以充饥果腹;“星期五”只是仆人,以充劳役,以解寂寞。至于世界上是否存在着绝对的真善美、不计功利的纯粹道德目的,则无关紧要。这种功利主义既是西方取得惊人成就的动力,也是西方产生精神危机的根源。到了20世纪,它潜伏的恶果开始充分显示,并引起强烈的逆反心理。霍尔顿就是这种心理的体现。他无法忍受功利社会的虚伪和冷漠无情。他寻求交流的历程,也就是他对爱、理解、人情味、道德情感生活的追求,是现代人在情感沙漠和功利汪洋中的挣扎呼救。
价值观念的崩溃还表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在鲁宾孙时代,西方人认为世界是上帝创造的一部机器,有着确定合理的构造与效用,按一定的规律运行。人只要认识了这些规律,就可开动这部机器向幸福的目的前进。随着人对规律越来越完善的掌握,必然导致对自然越来越有力的控制,人也就可达到越来越完善的境界。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征服自然”成了时代最强音。这也反映在鲁宾孙身上。他从一无所有的境地一步步通过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为自己创造了一个丰衣足食、无忧无虑的乐园,充分显示了理性的人以科学技术为武器所具有的改天换地的力量。到了20世纪,人对自然的认识与控制确实大大增强了,可这种乐观情绪却逐渐消失了,因为人也受到了无情的报复。现代人开始察觉到:人的幸福原来不仅在于物质财富的增长,进步也不一定意味着对自然奴役的强化,科学理性也并非必然地是人争取解放的可靠武器。在霍尔顿的漫游中,无论是先进的技术工具、丰富的物质享受,还是繁华的闹市街区,都不能解决他的空虚寂寞;而鲁宾孙在制成一个泥罐、一块木板中得到的乐趣,却是难以言传的。20世纪人已不能在物质财富的创造与享受中获得精神充实感了。那种“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良好感觉消失了。
价值观念的崩溃还带来了目的丧失。在鲁宾孙时代,占主导地位的历史观是一种进步观。此观点认为人类历史是一个不断完善的上升曲线,人对自然和人类社会本身的认识和控制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因而,明天一定会比今天好,光明总在前面,总有一个目的让人为之奋斗。鲁宾孙的实践就是这种观点的体现。他在荒岛上的全部创造活动都有一个既定的目的,即改善自己的物质生活条件,而他的每一努力基本上都获得成功,因而他的生活是一个天天向上的进步过程。而20世纪则是一个目的迷失的时代。历史是否有一个清晰而统一的既定走向,是否是一个理性的、有规律的进步过程,历史是前进的还是倒退的,这些在18世纪不成为问题的问题开始困惑现代人了。大同世界、乌托邦、天国乐园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科学技术、理性主义、进步、理想、人生的意义和目的都受到怀疑,人成了无家可归的流浪者。霍尔顿就是这个时代的产物。他是一个不愿意长大的人(他16岁,个子高,有灰色头发,像个成年人,但他说自己的行为常像个12岁的孩子)。他是一个“不考虑将来”(第14页)、“生活没有目的”(第59页)的人。他总是怀念过去,怀念死去的弟弟,怀念失去的童真,怀念幼小的妹妹。对他来说,美好的东西不在前面,而在后面。同鲁宾孙相反,他的漫游是一个无目的的、每况愈下的过程。每去一处往往是因为无处可去;每做一事往往是因为无事可做;每一次努力都是以希望始,以失望终;失望积累成绝望,最后心力衰竭,精神崩溃。对他来说,这个物质文明飞速发展的时代绝不是人类进步的标志,也不是人类追求的目的。他倒宁愿这一切都停下来。在自然历史博物馆里,他表达了这样的感受,“大厅里弥漫着一种气息,使人感觉好像外面下着大雨,这里是世界上唯一干燥,温暖,宜人的地方”,这是因为“每一样东西都一直停留在原地,什么都不会动”,“而有些东西应该让它们保持原状,人们应该把它们固定在这玻璃柜里,不再去动他们”(第122页)。
价值观念崩溃的最突出表现是在宗教方面。西方传统价值观是属于基督教取向的,经过宗教改革,基督教更成为个人面对世界的直接精神指导。鲁宾孙在困境中的精神支柱与行动指南都来自于上帝。而20世纪是科学理性取得绝对权威的时代,一切无法计算、度量或感知,不能验证的、超验的事物都成为不合法。于是信仰的基础坍塌了,宗教在被抽去实质内容后,剩下的只是空壳,已无法承担起精神指导的重任。宗教“对现代人已不再是发自内心的,不再是他精神生活的表现,在他看来,那只能被归纳入外在世界的东西,他已无法从中获得超俗的精神启示”〔5〕。这种宗教衰落状况从两部小说的对比中看得更清楚。 霍尔顿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当一个已成为名人的老校友作为赞助人来校作报告时,“告诉我们说:当他遇到任何困难时,都毫不羞涩地跪下来祈求上帝。他劝导我们应该随时随地地向上帝祷告,同他交谈。他叫我们把耶稣当作朋友,他说他总是在同耶稣交谈,甚至在开车的时候”(第17页)。这其实正是鲁宾孙在荒岛上所做的。在那个时代,这一切显得那么真诚可信,行之有效;而在霍尔顿时代,却显得那么虚伪做作,空洞乏味,只能使他恶心。他在看圣诞节表演时的感想是:“如果耶稣看到这玩意儿,可能会呕吐出来”(第137页)。因为在节日里、舞台上, 在庸俗的商业气氛中,宗教活动显得像闹剧,根本不能给人以启示和精神力量。在现代社会,“上帝死了”。这个杀死上帝的过程虽开始于鲁宾孙时代,恶果却结在霍尔顿时代。他因而在苦难的漂流中,找不到一点精神支柱。他也曾企图向上帝祷告,但他发现毫无用处。有一次,他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好像自己在大白天、在热闹的街上下沉、消失;此时他所能求助的只是他死去的弟弟,反复祈祷:“艾里,不要让我消失”(第198页)。
宗教固然是枷锁,但也是避难所。鲁宾孙在荒岛上不能说没有痛苦,但宗教给苦难以解释,使它变得易于忍受。他坚信,在上帝创造的天地范围内,没有一件事的发生不是他安排的。而上帝是公正的,其安排必有道理,“既然公正而万能的上帝以为应该这样处罚我,他当然也有力量拯救我;如果他认为不应该拯救我,我的责任就是绝对地、毫无保留地服从他的意旨”(《鲁宾孙漂流记》第139页)。在这样的信念下, 他“对天意的安排,感到心悦诚服,并且开始承认这是尽善尽美的安排”(《鲁宾孙漂流记》第96页)。这固然是哲学意义上的“不自由”,但也意味着“有依靠,无忧虑”。人杀死上帝后,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了。他自由了,但他也得对自己负责了,命运的好坏全在于自己的所为,在于自己的抉择。而抉择的标准全在于自己,没有一个绝对统一的“最高指示”,一失足成千古恨,这种自由反而成为可怕的负担。对鲁宾孙时代的人来说,一切有上帝安排,人不必自寻烦恼;“圣喻”、“圣裁”解脱了多少“自由选择”的苦境。而霍尔顿则无所依傍,孤苦无助,自由而无目的地在都市中徘徊、彷徨。费洛姆说:“只要个人没有觉察到个人行为的可能性与责任,那么他便不必害怕这个世界。当他自由时,他便觉得孑然孤立面对一个充满危险的世界。”〔6〕亚当在伊甸园偷吃智慧之果是人类第一次自由行为,而这次行为导致受苦,自由像是天罚。现代人赶走上帝,赢得了更大的自由,但从此人不得不负起过去由上帝承担的重担,于是“天堂永远失去了,个人孤立面对着这个世界像一个陌生人投入一个无边无际而危险的世界。新的自由带来不安,无权力,怀疑,孤独及焦虑的感觉”〔7〕。 这就形成了鲁宾孙的困境同霍尔顿的困境的本质不同。
综上所述,传统价值观念的崩溃导致了统一的价值观的丧失,目的的丧失,信仰的丧失,人与人共同语言的丧失。“道不同不相为谋”,现代人注定是精神上孤独的、无家可归的“流浪者”。鲁宾孙的困境以一艘船的到来而结束,而解救霍尔顿的船又在何方?作者也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只好不了了之地结束霍尔顿的漂流。
注释:
〔1〕Salinger:"THE CATCHER IN THE RYE".Bantam Books,Inc. NEW YORK,1981,P.187.引文均为自译, 以下引用处只注明阿拉伯数字页码。
〔2〕笛福《鲁宾孙漂流记》,方原译,第55页,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3〕辛弃疾词《丑奴儿·书博山道中壁》。
〔4〕〔美〕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第9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5〕〔瑞士〕荣格《探索心灵奥秘的现代人》,黄奇铭译, 第196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
〔6〕〔7〕费洛姆《逃避自由》第6、36页,北方文艺出版社 1987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