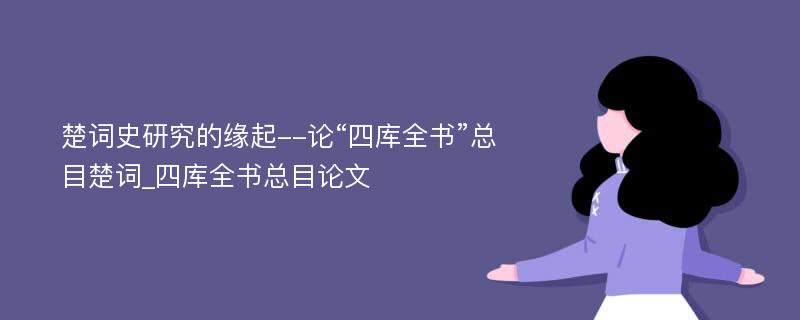
楚辞学史的滥觞——《四库全书总目》之楚辞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楚辞论文,滥觞论文,总目论文,四库全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下简称《四库》)沿用《隋书·经籍志》的分类方法,将楚辞单立一门,为集部之首。理由是“汉魏以下,赋体既变,无全集皆作此体者,他集不与楚辞类,楚辞亦不与他集类,体例既异,理不得不分著也”。(注:清·永瑢《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第1版。以下引文凡不出注者均引自此书。 )《四库》将楚辞与汉赋区别开,作为一个单独的类别,应该说是比较妥当的。《四库》收录楚辞类书目共计26种,144卷(有 2部无卷数)。其中著录6部65卷、存目17部75卷(内一部无卷数)、经部小学类1部3卷、子部类书类1部(无卷数),《四库》附录有未收书目1部1卷。 为便于观览,下面将《四库》所收书目按时代先后予以排列。
汉代1种
①王逸《楚辞章句》十七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宋代5种
①洪兴祖《楚辞补注》十七卷,内府藏本。
②杨万里《天问天对解》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③朱熹《楚辞集注》八卷《辨证》二卷《后语》六卷,内府藏本。
④吴仁杰《离骚草木疏》四卷,安微巡抚采进本。
⑤钱杲之《离骚集传》一卷。
明代7种
①汪瑗《楚辞集解》八卷《蒙引》二卷《考异》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②屠本畯《离骚草木疏补》四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③屠本畯《楚骚协韵》十卷附《读骚大旨》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④黄文焕《楚辞听直》八卷《合论》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⑤沈云翔《楚辞评林》八卷,内府藏本。
⑥张之象《楚骚绮语》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⑦陈第《屈宋古音义》三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清代13种
①萧云从原图、乾隆四十七年奉敕补绘《钦定补绘离骚全图》二卷。
②蒋骥《山带阁注楚辞》六卷《余论》二卷《说韵》一卷,通行本。
③毛奇龄《天问补注》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④林云铭《楚辞灯》四卷,内府藏本。
⑤李光地《离骚经注》一卷《九歌注》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⑥方楘如,《离骚经解》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⑦顾成天《离骚解》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⑧顾成天《楚辞九歌解》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⑨顾成天《读骚别论》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⑩林仲懿《离骚中正》,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11)夏大霖《屈骚心印》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12)屈复《楚辞新注》八卷,陕西巡抚采进本。
(13)刘梦鹏《楚辞章句》七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四库》于“旧书去取,宽于元以前,严于明以后”。(注:于文襄《论四库全书手札》,郭伯恭《四库全书纂修考》引,上海书店1992年12月第1版226页引。)这是《四库》选书的通则,楚辞自然不能例外。对汉、宋著作几乎见者辄收,而于明清选择很严、删汰较多。汉、宋楚辞注本自《四库》收录,几无漏遗,而明代楚辞注本今存的30种中仅录了7 种。清代自开国至乾隆四十七年基本成书的一百多年间的楚辞注本收录了13种,也很不全。
《四库》论述各书大旨及著作源流、列作者之爵里以知人论世,考本书之得失、权众说之异同,辨订文字增删、篇帙分合,“自有典籍以来,无如斯之博且精矣”。(注:郭伯恭《四库全书纂修考》88页。)知人论世、考镜源流的评价方式使《四库》在楚辞类书目提要中呈现出学术史的特点,虽然《四库》对于明清的著作并没选全,但所选篇目也基本上代表了所属各代的学术特点,当然这些特点带有《四库》馆臣的某些主观色彩。
《四库》在《楚辞类》序中对自汉至清初的楚辞学史予以提纲式的概括:“注家由东汉至宋,递相补苴,无大异词,迨于近世,始多别解,割裂补缀,言人人殊,错简说经之术,蔓延及于词赋矣”。寥寥数语勾画出一条楚辞研究发展演变的线索,显然这也就是《四库》馆臣对楚辞学史的总体看法。在对各代楚辞著作的介绍之中也基本上体现了这种观点。《四库》对东汉王逸《楚辞章句》予以褒奖:“逸注虽不甚详赅,而去古未远,多传先儒之训诂,故李善注《文选》,全用其文”。从总体上说是给予肯定的。当然《四库》馆臣对于汉人注书的简单也不满意,嫌“汉人注书大抵简质,又往往举其训诂而不备列其考据”。所评中肯,比较客观。
《四库》收录宋代楚辞著作5种,可以说这5种著作都是“补王逸训诂之所未及”,只是角度不同罢了,这是宋代楚辞学的根本特点。洪兴祖的《楚辞补注》“列逸注于前,而一一疏通证明补注于后,于逸注多所阐发,又皆以‘补曰’二字别之,使与原文不乱”。洪兴祖的“补注”正好补足了王逸的缺憾,符合《四库》馆臣“主于考订异同、别白得失”,试图恢复汉学,倡导考据的学术规范,因此,对《楚辞补注》最为推崇,认为“于楚辞诸注之中,特为善本”。即使如此,《四库》对《楚辞补注》的评价仍不失为客观。因为《补注》驳正旧解,重新阐发楚辞文义;校勘版本、订正异文。征引宏富,援据赅博,确实取得了很大成绩,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对于钱杲之的《离骚集传》,《四库》的概括是“其注旁采《尔雅》、《本草》、《淮南子》、《山海经》等书,其旨一禀于叔师”。补王逸之注的宗旨也比较明显。吴仁杰的《离骚草木疏》“征引宏富,考辨典核,实能补王逸训诂之所未及”。可与三国·吴·陆玑《毛诗草木鱼虫疏》、宋·罗愿《尔雅翼》“方轨并驾,争骛后先”,“迹其赅洽,固亦考证之林也”。但《四库》认为吴仁杰在考证这条路上走得太远了,因此不免于“好奇之过”。原因在于吴仁杰认定《离骚》之作多本《山海经》,在注解屈原作品时,全以《山海经》为根据,驳斥王逸旧注之说。如在“夕揽洲之宿莽”句下注引《山海经》中“朝歌之山有莽草焉”为证。本来引用《山海经》作为参证,认知草木之名是可以的,但一定以为屈原用了《山海经》,就不免牵强附会了。《四库》批评说:“骚人寄兴,义不一端,琼枝若木之属,固有寓言,澧兰沅芷之类亦多即目,必举其随时抒望,触物兴怀,悉引之于大荒之外,使灵均所赋,悉出伯益所书,是泽畔所吟,主于侈其博赡,非以写其哀怨,是亦好奇之过矣”。《四库》把握住了屈原作品借物抒情的特点来批评《离骚草木疏》,是恰切而中肯的。《四库》已经看出在楚辞学发展史上自吴仁杰始已从汉学的阵营中露出“好奇”的端倪。
朱熹《楚辞集注》是王逸《章句》、洪兴祖的《补注》后极为重要的楚辞注本。作为宋代学术风气的带头人之一,朱熹对汉学的训诂已不满足,嫌王逸《章句》“详于训诂,未得意旨”,因而作《集注》,总述屈原意旨而借以抒发一己之忧愤。《四库》引周密《齐东野语》记绍熙内禅事曰“赵汝愚永州安置,至衡州而卒,朱熹为之注《离骚》以寄意焉”。这种说法,古之信之者寥寥,但《四库》却没有否定,认为“是书大旨在以灵均放逐寓宗臣之贬,以宋玉《招魂》抒故旧之悲耳”。是借此抒写对赵汝愚遭贬的不平之意的。这样看来,《楚辞集注》已改变了洪兴祖《补注》的做法,而呈现出宋人好议论的特点。虽然朱熹治楚辞还没有像“明代诸人恣情损益”,但也并没有走汉学的老路,在很大程度上已离开汉学旧轨,而成为明代注书风气的先声。
《四库》对明代楚辞著作很不满意,不予收存,只在存目类中保留7种。在《四库》馆臣看来,“明代诸人妄改古书”、 “恣情损益”,大都不出佻薄之习。汪瑗的《楚辞集解》首当其中,“《楚辞》一书,文重义隐,寄托遥深,自汉以来,训诂或有异同,而大旨不相违舛。瑗乃以臆测之见,务为新说以排诋诸家……亦可谓疑所不当疑、信所不当信矣”。其后屠本畯的《离骚草木疏补》自谓补吴仁杰《离骚草木疏》之未备,又于吴仁杰疏多所删汰,“自谓简明过之,而实反失之疏略”,“又每类冠以《离骚》本文及王逸注,拟于《诗》之小序,亦无关宏旨,徒事更张”。在注解草木时又“不免自相刺谬,尤失于考证”。而其《楚骚协韵》补朱熹《集注》,“然所增实未尽当”,“本畯又好取《说文》字体改今楷法,是亦好奇之过也”。而黄文焕在崇祯中坐黄道周党下狱,“因在狱中著此书(指《楚辞听直》),盖借屈原以寓感焉……大抵借抒牢骚,不必尽屈原之本意,其词气傲睨恣肆,亦不出明末佻薄之习也”。《四库》对《楚辞评林》(沈云翔编)和收入子部类书类的《楚骚绮语》(张之象编)就更不满意,斥前者为“杂采诸家之说,标识简端,冗碎殊甚,盖坊贾射利之本也”。而贬后者“摘楚辞之句以供挦撦,已为剽剟之学”。反感的态度更表露于字里行间。明代楚辞著作中唯一不被贬抑的是陈第的《屈宋古音义》,《四库》叙其内容体例,较为客观。大概是因为陈第此书考据翔实,与清代倡导的征实之风相近的缘故。因与《毛诗古音考》“卷帙相连,非别为一书,故不析置集部,仍与《毛诗古音考》同入小学类焉”。
凭心而论,明代楚辞研究并非如此糟糕,不说《四库》未选入的20余种著作中尚有不少精心结撰之作,如李陈玉的《楚辞笺注》、周拱辰《离骚草本史》、陆时雍《楚辞疏》等,即使仅就选入《四库》目录的7种而言,也多有可取之处。 如黄文焕《楚辞听直》认为《九章》并非如王逸所说作于流放江南之时,而是作于怀王、襄王两朝,这样解释既与《史记》记载历史事件相符,也与作品相印合。此说法被清代林云铭采用,《四库》对此也并非不知,在叙林云铭《楚辞灯》时说“此说本黄文焕《楚辞听直》,亦非其创解也”。将黄文焕的创解挪至《楚辞灯》里叙述,虽并非故意掠人之美,但借此可看出《四库》馆臣对明代文献的避讳态度。
汪瑗的《楚辞集解》确实有不少谬误之处,应该辨别。但《四库》不问曲直,全盘否定,未免不公。清代学者焦竑对该书的评价值得注意:“余窃观其书,殆有意错综诸家而折衷之,非苟然者。今读之,有同于昔谈者,非强同也,理自不得异也;有异乎前论者,非好异也,理自不可同也”。(注:清·焦竑《楚辞集解序》,见董洪利点校《楚辞集解》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1月第1版3页。)当然, 汪瑗的创说并非都是正确的,但确有不少见解被清代及今之学者所采纳。对此金开诚先生有专文(《文史》十九辑《汪瑗和他的楚辞集解》)论及。例举很多被误解为别人观点的汪瑗创说,如湘君、湘夫人是一对配偶神的说法被误解为闵齐华《文选瀹注》的观点,《哀郢》创作于顷襄王二十一年白起破郢之时被误解为王夫之的创解,王夫之的《礼魂》为前10篇的送神曲之说也是变用汪瑗的说法等。
《四库》对明代著述的贬抑是有其多方面的原因的,从政治上讲,乾隆皇帝组织大量人力编纂图书,论其私意是“寓禁于征”,在征收、编纂图书的过程中借机销毁于自己不利的文献。郭伯恭《四库全书纂修考》说“然就事际言,则固高宗一人之私欲,为其子孙万世之业计,锢蔽文化,统制思想,防范汉人之一种政治作用而已”。(注:郭伯恭《四库全书纂修考》2页。)因此对于明代之书特加查禁:
乾隆四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谕:
明季诸人书集,词意抵触本朝者,自当在销毁之列。(注:《乾隆四十一年谕》,见清·永瑢《四库全书总目》。)
乾隆四十一年十一月四日谕:
如有收藏明末国初悖谬之书,急宜及早交出。(注:《东华续录·乾隆八十》,转引自郭伯恭《四库全书纂修考》第26页。)
皇帝对明代文献忌讳如此之多,馆臣自然不敢违谬,因此编选明代著作缺略甚多,而且多持贬抑。另一个原因是明代承袭宋代,好议论、发挥义理的风气较浓,而清代初年,由于多种原因,使士人们偏好考据,钻故纸堆,极力提倡汉学,对宋儒贬斥汉学的态度是很不满意的。纪昀曾说:“夫汉儒以训诂专门,宋儒以义理相尚。似汉学粗而宋学精。然不明训诂,义理何自而知?概用诋诽,视犹土苴。未免既成大辂,追斥椎轮;得济迷川,遽焚宝筏。”(注:纪昀《阅微草堂笔记·滦阳消夏录一》,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6年1月版10页。 )崇汉斥宋的立场十分鲜明,自然指斥与宋代学风一脉相承的明代,说明代楚辞著作“空疏”“臆测”“好奇”。由于这些原因,使《四库》在对明代楚辞的评价上,存在了不少的偏颇。
《四库》对清代的楚辞著作也颇多微词。由于《四库》在乾隆四十七年(1782)基本成书,乾隆十五年(1789)最后写定,受时间限制,《四库》所收仅限于清代建制到乾隆时代的一百三十年间,共计13种,占整个清代文献(70多种)的五分之一。乾隆以前的本子,《四库》也没有全收,与林云铭同时的朱冀的著作《离骚辨》,《四库》提到过但没收入。
《四库》认为清初的楚辞研究方法仍沿续着明代的路子,穿凿附会,多臆测之词,不免于武断。如对毛奇龄《天问补注》的评价是“先列《天问》原文,次列集注,而后以补注继之,亦间有所疏证。然语本恍惚,事尤奇诡,终属臆测之词,不能一一确证也”。又如对顾成天《读骚别论》“举《九章》以下诸篇未及作解者,一一评其大意,谓《离骚》之作在顷襄之世,屈原之死乃身殉怀王,力辟《史记》记事之谬。谓《九章》之《惜诵》《惜往日》二篇为伪托,定为河洛间人所作,谓《卜居》《渔父》亦为伪托,定为战国人所作。谓渔父即庄周,谓《招魂》《大招》皆招怀王,其说皆不免武断”。《四库》对屈复的《楚辞新注》从文学角度评解比较欣赏,说其书“采合楚辞旧注而自以新意疏解之。复颇工诗,故能求骚人言外之意,与拘言诠、涉理路者有殊”。但又“果于师心,往往臆为变乱”。理由是屈复指《离骚》“曰黄昏以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二句为衍文;又说《天问》一篇有错简;《九歌》末篇《礼魂》是《九歌》的乱辞。“大抵皆以意为之,无所依据也”。研究楚辞而“以意为之”到刘梦鹏《楚辞章句》已到极点,“《九歌》内《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各自标题,而删除《湘夫人》《少司命》之名,称《湘君》前后篇、《司命》前后篇”。“《九章》内删《抽思》、《橘颂》之目,统为《哀郢》,又移置其先后,均不知何据?”随意窜乱篇第,已不是治学的路数。《四库》对清初楚辞著作评价最高的是蒋骥的《山带阁注楚辞》,“所注即据事迹之年月、道里之远近,以定所作之时地,虽穿凿附会所不能无,而征实之谈终胜悬断”。“《余论》二卷,驳正注释之得失,考证典故之同异,其间诋诃旧说,颇涉轻薄……而汰其冗芜,简其精要,亦自瑕不掩瑜”。从总体上讲是肯定的,但指出了蒋骥无法避免明末清初“以意为之”的学术风气影响而形成的通病,即“穿凿附会”、“颇涉轻薄”等。当然这只是无妨大体的小毛病。
清初的楚辞研究除多以臆测之见而为之以外,还有一种不良的风气,即以时文之法研究楚辞,时文即八股文。八股文在明代已出现,并在科举中广泛使用,流行于明清两朝五百年,但用时文研究楚辞在清初才大量出现。大抵因为时文对士人影响已深入骨髓,某些文人便将时文之法用于整理古书。林云铭《楚辞灯》同朱冀《离骚辨》一样,“均以时文之法解古书”,虽然朱冀“攻云铭之说甚力”,但“亦同浴而讥课裎”。李光地《离骚经注》“所注皆推寻文义,以疏通其旨,亦颇简要,然楚辞实诗赋之流,未可说以诂经之法”。林仲懿《离骚中正》可谓以时文之法注解楚辞的代表。其书“谓屈原之赋以执中为宗派,主敬为根柢。自叙学问本领,陈述帝王心法,与四子书相表里。其说甚迂。故所释类多穿凿。如释‘名余曰正则字余曰灵均’,谓屈子窃取子思之道,所言正则、灵均与《中庸》天命之性、率性之道相合,是果骚人之本意乎?”
清代楚辞著作中例外的一部是《钦定补绘离骚全图》,萧云从原图,乾隆四十七年奉敕补绘。因为萧氏原图只存三闾大夫、郑詹尹、渔父一图、《九歌》九图、《天问》五十四图。“核之楚辞篇什,挂漏良多,皇上几余披览,以其用意虽勤而脱略不免,特命内廷诸臣参考釐订,各为补绘”。共补《离骚》三十二图,《九章》九图、《远游》五图、《九辩》九图、《招魂》十三图、《大招》七图、香草十六图。合萧氏原图,共一百五十五图。“于是体物摹神,粲然大备”。因为是“钦定”,馆臣们自然不便批评,但在评价上仍露弦外之音,“云从以绘事之微,荷蒙宸鉴,得为大辂之椎轮,实永被荣施于不朽矣”。对萧氏此书得受皇帝青睐并因此而不朽是不太以为然的。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四库》是以汉学考据的学问方法来衡量历代楚辞注本的,以此作为褒贬的标准。但同时《四库》又反对以研究经学的方法研究楚辞,而应以辞赋待之,还其文学的本来面目。这都是正确的,应该充分肯定。《四库》通过各代楚辞著作的评价给我们大致勾勒了简明的楚辞学史,也是对楚辞研究的重要贡献。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四库》于明清楚辞研究著作缺略甚多,而且贬抑过分,则可说是一个不小的缺憾。从这个角度讲,说《四库》薄今厚古,大概不算过分。
标签:四库全书总目论文; 楚辞论文; 四库论文; 楚辞集解论文; 山海经论文; 读书论文; 天问论文; 九章论文; 招魂论文; 乾隆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