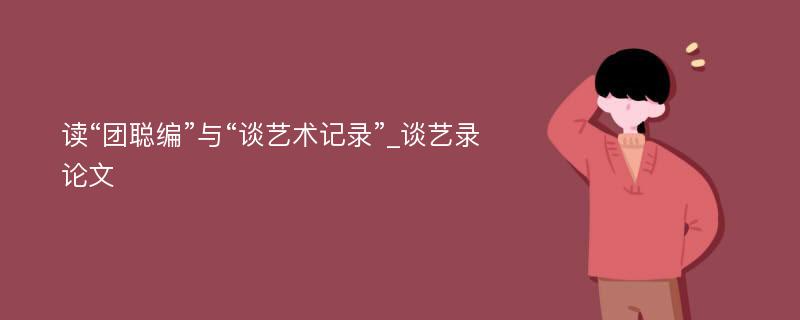
读《管锥编》《谈艺录》札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札记论文,管锥编论文,谈艺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其实是关于《管锥编》《谈艺录》的两条札记,即钱钟书先生对沈德潜、朱熹的诗学的评论。
(一)
钱钟书对沈德潜的“理趣”说给予高度评价,却对其《说诗晬语》颇为冷漠。
对“理趣”说的高度评价,是从诗学理论和文学史这两个角度来论定的。《管锥编》第三册“全晋文卷六一”条云:
沈德潜始以“理趣”、“理语”连类辨似。虞山释律然《息影斋诗抄》有沈序,作于乾隆三年,未收入《归愚文钞》,略云:“诗贵有禅理、禅趣,不贵有禅语”。后六年沈撰《说诗晬语》卷下论“诗入理趣”,异于“以理语成诗”;又后十六年《国朝诗别裁·凡例》有云:“诗不能离理,然贵有理趣,不贵下理语。”余观《国朝诗别裁》卷三二僧宗渭诗,沈氏记其尝谓门下弟子曰:“诗贵有禅理,勿入禅语,《弘秀集》虽唐人诗,实诗中野狐禅也”;岂沈氏闻此僧语而大悟与?这段话说明了沈氏这一诗学观的形成过程,以及可能存在的来自别人的启发,可见钱钟书对沈氏这一观点十分重视,否则不会如此细心地追究。对此,我们可以在《谈艺录》第六九条的“补订二”中,找到旁证:
余尝细按沈氏著述,乃知“理趣”之说,始发于乾隆三年为虞山释律然《息影斋诗钞》所撰序。
紧接着重又引证《说诗晬语》、《国朝诗别裁·凡例》诸材料加以说明,不仅称道沈氏的这一理论的发明之功,而且认为沈氏的说法“分剖明白,语意周匝”。
恐怕不仅仅是因为沈氏这一理论的诗学价值及其历史价值,导致钱钟书的高度评论与细心推究、考论,我想恐怕也与钱钟书的诗学理论有直接的关系。钱钟书的创作明显受到晚清以降诗坛的“宋诗”风气的侵染,并且他论诗也常常以“宋诗”为尺度。虽然他似乎对此颇为自警,但《管锥编》、《谈艺录》中,还是可以明显看出来。《谈艺录》是他早年的论著,其中论“宋诗”的篇幅、分量很大,似乎很说明问题。我甚至认为,既然《宋诗选注》中对宋诗批评甚严,近乎苛评,但恰恰说明他对宋诗研究很深,亦颇为好之,正如柳宗元对《国语》的批评,恰恰是因为受《国语》影响很大,并且研究很有心得一样。这里不妨举两个论著之外的例子,作为旁证。第一个例子是,据说钱钟书很欣赏吴宓“未甘术取任缘差”一语:“题雨僧师《空轩》诗后,余最爱‘未甘术取任缘差’一语,未经人道。”其实这一句诗,正是因为颇有“理趣”而未必是“未经人道”,才受到钱钟书的称道。第二个例子是,钱钟书《壬申年秋杂诗》,其中“除蛇深草钩难着,御寇垣守不牢”两句,出典宋明理学家语录,钱钟书颇为自负:“用理学家语作情诗,自来无第二人。”这两句不仅有“理趣”,而且恰恰是典型的“宋诗”的风格。
当然,沈德潜写诗、论诗均以唐诗为宗,但他的“理趣”说,正是针对宋诗“以理语成诗”的流弊而发的。因此,除了沈德潜这一诗学观点的理论价值之外,他对宋诗流弊的分析而站在唐诗的立场得出“理趣”说的观点,当然容易引起钱钟书的注意。《谈艺录》开篇所讨论的第一问题,就是批评“诗分唐宋”的观点。晚清以降,“宋诗”风气正炽,唐诗与宋诗的区别,当然也是钱钟书关心的一个重要诗学问题。这样说来,钱钟书关注并推崇沈德潜“理趣”说,就不是没有原因的了。
但是,我更注意的则是另外一个问题。除了“理趣”说,《说诗晬语》中许多很有价值的观点,似乎没有引起钱钟书的注意。其实,沈德潜的这些很有价值的观点,与钱钟书的诗学观十分相近,甚至相同,按照钱钟书论著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旁征博引而不厌其烦的一惯风格来说,似乎不应略过的。原因何在,不得而知,这里且引数例如下。
《管锥编》第一册“毛诗正义”第五则论比兴之义,列举历代各家之说时,首引胡寅《斐然集》所载李仲蒙之说:
蒙物以托情,谓之“比”;触物以起情,谓之“赋”。
认为此说“颇具胜义”,但“惜着语太简,兹取他家所说申之”。其中没有引《说诗晬语》的说法,其实,沈德潜的说法是值得注意的。《说诗晬语》卷上开篇第二则云:
事难显陈,理难言罄,每托物连类以形之。郁情欲舒,天机随触,每借物引怀抒之。比兴互陈,反复唱叹,而中藏之欢愉惨戚,隐跃欲传,其言浅,其情深也。
这个说法较低钱钟书征引各家之说,颇具胜义,并且与钱钟书自己所谓的“‘触物’似无心凑合”,“非同‘索物’着意经营”之说,庶几同旨。
又,钱钟书在同一则中,对项安世的说法,颇为欣赏,并且连引项氏对“经生解诗”的批评:“大抵解诗者皆经生,作诗者乃词人,彼初未尝作诗,帮多不能得作诗者之意也。”之所以连引这几句“题外话”,就在于《管锥编》第一册的“毛诗正义”这一卷中,我们一再看到钱钟书对清儒的严厉批语认为戴震“盖经生之不通艺事也”(第60页);批语钱大昕“意在尊经卫道,助汉儒张目,而拘于单文互训,未为得也”(第121页);批语阮元“经生不晓事, 不近情而几为不通文理也”(第135页);如此等等,不胜枚举。其实,沈氏《说诗晬语》卷上第三则,亦有此论:
读前人诗而但求训诂,猎得词章记向之富而已,虽多奚为?
钱钟书为何放过这一条有力的材料而不征引呢?沈氏处乾嘉学术盛世,此论是有感而发,有针对性的,批评对象很明确,正是用来批语清儒“经生解诗”的有力武器啊!
第三个例子。《管锥编》第一册“毛诗正义”卷第三七则论《陟岵》,钱钟书认为《正义》“说自可通”,但更作胜解云:
然窃意面语当曰:“嗟予行役”,词气不类临歧分手之嘱,而似远役者思亲,因想亲亦方思己之口吻尔。
此解确实较《正义》更上一层楼。然而,《说诗晬语》卷上第二三则云:
《陟岵》,孝子之思亲也,三段中但念父母兄之思己,而不言己之思父母与兄,盖一说出,情便浅也。
钱钟书以“窃意”自矜,不意沈氏早已发明在前。
第四个例子。《谈艺录》中论陆游,胜义纷陈,但对照《说诗晬语》,两者不乏为同调者。如《谈艺录》第三五则云:
放翁多文为富,而意境实是少变化。古来大家,心思句法,复出重见,无如渠之多者。《曝书亭集》卷四十二《书剑南集后》讥其“句法稠叠,令人生憎”,举例颇繁。《瓯北诗话》卷六复摘其复句数联。
《说诗晬语》也有同样的看法,其卷下第五则云:
放翁七言律,对仗工整,使事熨贴,当时无与比埒。然朱竹(垞)摘其雷同之句,多至四十余联。缘放翁年八十余,“六十年间万首诗”后,又十添四千余首,诗篇太多,不暇择也,初不以此遂轻放翁,然亦足为贪多者镜矣。
值得注意的是,钱钟书后来补订此说,在“补订一”中更进一步说:
似先组织对仗,然后拆补完篇,遂失检点。虽以其才大思巧,善于泯迹藏拙,而凑填之痕,每不可掩,往往八句之中,啼笑杂车遝,两联之内,典实丛叠,于首击尾应,尺接寸附之旨,相去甚远。文气不接,字面相犯。
道出陆游诗此病的“病源”与“病症”,一语中的而锋芒毕露,是典型的钱钟书口吻。但是,《说诗晬语》亦有此说,并且措词亦十分相近,或者说相同:
八句中上下时不承接,应是先得佳句,续成首尾,故神完气厚之作,十不得二三。
只是再后来重又“补订”此说,才顾及沈氏之说,但奇怪的是,不引上述《说诗晬语》中的话,而引沈氏诗集云:
沈確士《归愚诗钞·余集》七《书剑南诗稿后》:“剑南诗草多复多,中间岂无复与讹。后人嗤点太容易,以枚数阖伤繁苛”,自注谓朱竹(垞)瓯北及余“太容易”而“伤繁苛”者乎。
似乎钱钟书忘了读过的《说诗晬语》,这对于记忆力过人,以旁征博引著称的钱先生来说,太让人感到意外了。
此外,尚有数例,限于篇幅,不复一一列举了。
(二)
《管锥编》第一册《〈毛诗正义〉》中,关于《诗经》的阐释,对宋儒、清儒的批评,讥之为“以经解经”、“经生不解诗”,而对朱熹独有称赏。这一点引人注意。
第四七则关于《七月》的解释,钱钟书批驳旧说之后有长长的一段引申发挥:
毛、郑于《诗》之言怀春、伤春者,依文作解,质直无隐。宋儒张皇其词,疾厉其色,目为“淫诗”,虽令人笑来,然固“晓得伤个春”而知“人欲”之“险”者,故伤严过正。清儒申汉绌宋,力驳“淫诗”之说,或谓并非伤春,或谓即是伤春而大异于六朝,唐人《春闺》、《春怨》之伤春;则实亦深恶“伤春”之非美名,乃曲说遁词,遂若不晓得伤春为底情事者,更令人笔来耳……故戟手怒目,动辄指曰“淫诗”,宋儒也;摇手闭目,不敢言有“淫诗”,清儒为汉学者也;同归于腐而已(第一册,第 132—133页)。
宋儒、清儒云云,盖着眼于主流而已,于“大儒”批评尤严,倒是对诸家“小儒”网开一面。例如第一五则关于《燕燕》,对《彦周诗话》、《读〈风〉臆补》、《项氏家说》、《〈诗〉触》、《读〈风〉臆评》诸作者,偶有称赏,以为“诸家虽囿于学识,利钝杂陈,而足破迂儒解经窠臼”。虽犹不轻许,亦是持论甚严之一贯口吻,但毕竟有所肯定,态度大有不同。
对于宋儒清儒的批评,以及钱氏解《诗》之诗学原则,大抵尽在于此:“清儒好誇 ‘以经解经’,实无妨以诗解《诗》耳。”(同上,第70页)所谓“以诗解《诗》”,就是将《诗》当作文学作品来解读,不必本着见道卫教之“经学”眼光,于音韵训诂也不必拘于“小学”的原则范式。
对朱熹的称道,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第一五则释《燕燕》之余,意犹未尽,引《朱子语类》卷八○之“读《诗》且只做今人做底诗看”一说,(同上,第79页),以申其义,朱子此说,正好和钱钟书所谓的“以诗解《诗》”同义。又,第三四则关于《狡童》的释意,无取乎《传》《笺》寓意君臣之说,而同意朱熹《集传》“淫女见绝”之说,且下一断语:“窃以朱说尊本文而不外鹜,谨严似胜汉人旧解。”(同上,第108 页)所谓“尊本文而不外鹜”,即现代西方诗学所谓文学的“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相区别的原则,对于作品的释义,当以“本文的解读”为唯一原则,以“本文”为唯一孤立无援的解读对象,而无需援引作者、社会诸方面材料(参阅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第三、四章)。钱氏对朱熹这种诗学观的欣赏,正是有这种西方现代诗学的理论背景,如《谈艺录·自序》云:“凡所议论,颇采‘二西’之书。”钱氏此处对朱子称道有加,且引他书证曰:“朱鉴《〈诗传〉遗说》卷一载朱熹论陈传良“解《诗》凡说男女事皆是说君臣”,谓“未可为如此一律’;盖明通之论也。”(同上,第108页)“明通”二字,正是针对宋儒清儒“经生不解诗”而言。
总之,钱氏称道朱子,以致再三致意,原因就在于朱子“以诗解《诗》”的诗学观。反之,钱氏对朱子的批评,亦因为朱子偶尔“未能免俗”(“以经解经”),不能完全尽去道学家的固有眼光,于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如第二二则论《桑中》云:
朱熹《语类》卷八解道:“读《诗》且只将今人做底诗看”,而于《桑中》坚执为“淫者自状其丑”,何哉?岂所谓“上阵厮杀,忘了枪法”乎!
以谐语出之,而不同于对其他宋儒清儒的酷评,可以说是区别对待。
问题似乎尚不止于此。
钱氏解《诗》,旁征博引,大体有三端:一是以后世诗作为例;二是旁及对戏剧、小说等其他文体作品为例;三是以西方作品为例。此即钱氏所谓“打通”诸义,意在发明艺理,或艺术惯例,如《谈艺录·自序》云“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而不全在于解释某一具体作品本身。钱氏的这个原则,和西方现代“阐释学”的理论,有十分相通之处(《管锥编·〈左传正义〉》第三则即发挥“阐释学”的“阐释之循环”之说,以申己说),却与中国固有的“正统”之学术原则大异其趣,与“汉学”、清代“朴学”之学术规范相悖。比如上文提到的对《燕燕》一诗的解释,对于“瞻望勿及,立以泣”一句,钱氏先引《彦周诗话》论此二句所谓“张子野长短句云‘眼力不如人,远上溪桥去’,东坡与子由诗云‘登高回首坡垅隔,唯见鸟帽出复没’,皆远绍其意”,然后发挥此意,连引后世张先、辛弃疾等数十例,以及莎士比亚剧本中的例子,以为均与“瞻望勿及,立以泣”两句“异曲而同工焉”(同上,第78—79页),不仅说明艺术技巧,而且解释了这两句的语意。这种解释的方式,显然违反了“汉学”及清代“朴学”的学术规则:不是同一时代的文本,不可以作为“旁证”。
钱氏批评“以经解经”的道学思想,视清儒与宋儒为同类而一概否定,是一回事;而在方法论上,对于宋儒的“六经注我”较清儒的“我注六经”,似乎有所取焉。这似乎可以说是钱氏对朱子的态度较为亲切的一种学术背景。
也就是说,朱子“读《诗》且只将今人做底诗看”之说,不仅在“以诗解《诗》”的意义上为钱氏所欣赏,而且在上文所分析的钱氏所谓“打通”——以后世诗作为例而证《诗》——这个意义上受到钱氏的注意。《管锥编〈毛诗正义〉》第五则关于“兴”的解释,钱氏引朱子的话为据。《朱子语类》卷八○云:“《诗》之‘兴’全无巴鼻,后人诗犹有此体。如:‘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人生天地间,忽为远行客。’又如:‘高山有涯,林木有枝;忧来无端,人莫之知’;‘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钱氏对朱子这段话深以为然,只是认为“所举例未当耳”(同上,第63页)。然后,钱氏正是如朱子所说,连引“后人诗”以为例证。以我们在上文的说法,认为“后人诗犹有此体”,固然不错,但以“后人诗”作为例证,来阐释“兴”之意义,殊有不当,亦非汉儒清儒的做法,而只能证之以《诗》,从《诗》中寻找内证,或者在同时代的典籍中寻找“旁证”,“后人诗”不足为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