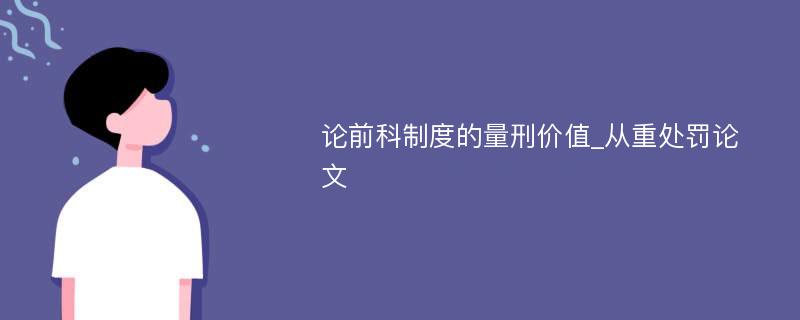
论前科制度的量刑价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前科论文,价值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具有前科而实施犯罪,是世界各国刑法典所规定的法定从重处罚情节之一。尽管前科的存 在导致犯罪人的一系列合法权益受到影响,但是,根据前科制度存在的立法初衷来分析,前 科制度所引发的主要后果,在于对于具有前科者所实施的后罪提高刑罚责难程度,换言之, 前科制度的首要价值在于其量刑价值,即直接导致对后罪的量刑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
一、前科量刑价值的实现形式
前科制度对于量刑的影响,是其刑事法律后果的主要体现。这不仅是前科制度存在的根本 刑事意义所在,也是世界上多数国家的通行作法。
以俄罗斯为例,该国刑法理论认为,把多次犯罪、累犯作为加重刑罚的情节,是因为在重 复实施行为并且具有前科的情况下,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明显增大,犯罪人的犯罪习惯和反社 会观点会进一步增强。[1]就是说,多次犯罪和累犯是以两次以上实施犯罪行为为前提的, 并且每次实施的犯罪行为都具有法律意义。如果该人的前科已被撤销或者消灭,那就不认为 是加重刑罚的情节。[2]基于以上理论,为了体现对具有前科者再次犯罪的打击力度,俄联 邦最高法院全体会议指出,对于过去犯有故意罪并有前科的人,不得无根据地适用轻微的刑 罚方法。换言之,如果对于具有前科者适用刑罚低于普通刑罚时,应当出示有关根据。前科 对量刑的影响,虽然总体上表现为从严的倾向,但是在具体的立法规定上仍然有所不同。具 体而言,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1.特别处罚。特别处罚,是指对于具有前科而构成的累犯处以特别的严厉之刑,分为两种 形式,一是无期放逐于殖民地;二是长期苦役刑。前者由法国首先采用,法国1885年累犯法 规定:对于危险性较大的多次累犯,除判处主刑外,附加判处无期殖民地流刑。后经意大利 学者在1890年国际法学会议上提出,为葡萄牙等其他国家所采用;而后者由比利时首先采用 ,比利时1891年刑法规定,对乞丐和流浪之累犯要判处长期苦役刑。此后英国1908年的刑法 和埃及1908年刑法,都有类似的规定。尤其是由菲利于1894年在里昂召开的国际刑法学会会 议上提出后,更为许多国家所采用。
2.从重或者加重处罚。从重或者加重处罚,是指对于具有前科而构成的累犯应当在量刑时 从重或者加重处罚。此种立法处理模式又可以分为以下类型:(1)确定加重,即刑法明确规 定对具有前科再次犯罪而构成累犯的,处罚某一确定的刑罚,例如美国纽约州、加利福尼亚 州的《惯犯法》规定:“犯重罪四次以上累犯,处无期徒刑。”(2)从重处罚。指在后罪法 定刑的范围内处以相对较重的刑罚或者较长的刑期,我国现行刑法典即采此例。(3)提高后 罪 法定刑的下限而上限不改变。例如1976年德国刑法典第48条规定:“如果认为以前判处的刑 罚对其未起警戒作用,最低自由刑为六个月。”挪威刑法也存在类似的规定:对于需要专门 技能的盗窃犯罪的最低刑为二年徒刑,但是其前提条件是被告人必须因犯同样的罪行有过三 次前科。[3](4)以后罪应判处的刑罚为基础,将本刑加重一定比例。例如《意大利刑法典》 第99条规定:犯罪被科刑后,再犯他罪者,加重其刑六分之一。具有法定的某些情节者(再 犯同等之罪者),加重其刑二分之一。(5)以后罪应判处的刑罚为基础,加重相应法定刑幅度 最高刑和最低刑差的几分之几。例如澳门地区原刑法典第100条规定,对第一次累犯(即第二 次犯同罪)的处罚,以后罪应判处的刑罚为基础,加上所适用的相应法定量刑幅度中最高刑 和最低刑差的二分之一。对于第二次累犯(即第三次犯同罪)的处罚要重于第一次累犯的处罚 。因此,适用于第二次累犯的加重因素是决定量刑幅度中最高刑和最低刑之差的四分之三, 高于第一次累犯的加重因素。[4]对此应当注意,澳门地区1995年7月25日制定通过的新刑法 典对累犯的处罚制度已经作了修改,改为另外一种同时限制最低刑和最高刑的双重限制原则 :“如属累犯之情况,须将对犯罪可科处之刑罚之最低限度提高三分之一,而其最高限度则 维持不变,但上述之加重不得超逾以往各判刑中所科处之最重刑罚。”(6)加倍处罚,是指 对于累犯的处罚应当加重本刑的立法例,换言之,应当在后罪法定最高刑的基础上加倍处罚 。例如韩国刑法典第35条第2项规定:“对于累犯之处罚,得加重至本刑的二倍。”
3.变更刑种。变更刑种,是指将具有前科的累犯之后罪的法定刑变更提高为更重的刑种, 即在刑种上加以变更,而不是仅改变刑度而不改变刑种。例如1871年德国刑法典规定,初犯 之罪被判处有期重惩役,经执行完毕,再犯应处有期重惩役之罪时,得科处以无期重惩役。 又如土耳其刑法第88条规定:“从一种刑变为另一种刑是对累犯规定适用的主刑;”第82条 第3款规定:“对以前同样惩罚的,则对该犯执行死刑。”
4.保安处分与刑罚并科。刑罚与保安处分并科,是指某些国家的刑事立法机关认为,由于 具有前科而构成的累犯存在过大的人身危险性,导致仅加重后罪之刑罚已经不足以消除其人 身危险性,因而并科刑罚与保安处分:以刑罚对其后罪进行否定性评价,以保安处分预防未 然之罪。例如英国1908年的《犯罪预防法》规定:累犯在刑罚执行完毕后,还要受五年以上 十年以下的保安拘禁。
5.采用刑罚替代措施。采用刑罚替代措施,是指对于具有前科而构成的累犯适用保安处分 ,以代替自由刑的适用。其中,有的国家对于累犯科以定期的保安处分,有的国家则科以不 定期保安处分。前者如英国1948年《刑事审判法》第30条规定:对累犯可以按年龄不同处以 不 同期限的“矫治训练”或者“预防拘禁”,以代替刑罚的执行;后者如1945年瑞典刑法、19 30年丹麦刑法等,都规定对累犯可以处以不定期的保安处分,以代替刑罚执行。
6.不定期刑。不定期刑,是指对于具有前科而构成的累犯进行判决时,只宣布判处刑罚而 不确定其具体刑期,或者仅确定刑期的上限或下限,至于最终所执行的刑期,则依犯人在行 刑中的具体表现而定。具有前科再次犯罪而构成的累犯适用不定期刑的规定,目前见于若干 立法文献之中。较具代表性的有两个:其一,1921年由菲利起草的意大利刑法草案第29条规 定:“犯三次轻惩役之罪或二次重惩役之罪的罪犯,应用不定期刑。”其二,1974年9月29 日 《日本刑法改正草案》第59条规定:“对于常习累犯,可以宣告不定期刑。……第一项的不 定期刑,在处断刑的范围内确定最高刑与最低刑予以宣告,但是处断刑的最低刑期不满一年 的,定为一年。”
7.不同处罚标准的评价。对以上几种前科量刑效应的现实立法例,笔者认为,首先,特别 处罚主义的立法原则最为不可取,此种处罚原则是对犯罪人人权的最大侵害,使得犯罪人因 一时之过错而被推至社会的绝对对立面,再无悔过自新的机会,并终身为一时过错而承担极 重的刑罚负担,并且此种刑罚并不是能从报应刑或者预防刑的任何角度加以合理解释,仅仅 属于重刑主义思想的极端体现。其次,应当摒弃的是“不定期主义”和“并科主义”,这两 种处罚原则不仅过于损害犯罪人的应有合法权益,使其被迫长期脱离正常的社会生活而生活 于交叉感染的不良监管环境中,难以期望其人身危险性能够得以早日减少,因而很难取得 令人满意的司法效果。再者,完全取代刑罚适用的代替主义,尽管从剥夺犯罪人自由的期限 上讲可能更为漫长,但是一来刑罚与保安处分在质上的区别和理论基础上的差异是根本不同 的,代替主义的理论根据不足,二来以相对较为轻缓的保安处分来代替严格的刑罚制裁,能 否真正取得更佳的改造效果,尤其是对于人身危险性已经极大的累犯之犯罪人而言,令人忧 虑。基于此,笔者认为,对于具有前科而构成的累犯,采取“加重”处罚的立法模式相对最 为可取,当然,这里所称的“加重处罚”,是就对于后罪的刑罚在量上的加重处罚而言的 ,而并非指实际在刑罚幅度上的升格处罚,因为笔者在同为“加重处罚”的两种立法例之中 ,更倾向于“从重处罚原则”而不赞同“加重处罚原则”,对于这一点,笔者后面将加以研 讨。
二、前科在中国刑事司法中对量刑的实际效应
前科的实际量刑效应在我国历代均现实存在,沿革至今而变化不大。
1.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前科量刑效应。中国古代史料关于前科量刑效应的最早记载,见于《 尚书·舜典》,其中有“怙终贼刑”的明确记载。何谓“怙终贼刑”呢,朱熹认为:“怙谓 有所恃,终谓再犯,若有人如此而入于刑,则虽可当宥当赎者,亦不听其宥,不听其赎,必 处以刑。”(《朱子大全·舜典象刑说》)而所谓“宥”,是指宽恕、原谅;所谓“赎”, 则是指通过“使入财而免其罪”,就是缴纳一定数量的金(铜)或丝即可赎罪免刑,此种赎刑 只有贵族特权者才能享有[5]。换言之,此时对于具有前科再次实施而构成的累犯,虽然尚 未如当代这样从重或者加重处罚,但是仍然存在相对较重的立法惩治措施,即不能宽恕原谅 ,不能赎罪免刑,必须实际追究刑事责任。
秦律不存在成文的立法文献,因而难以考证是否在立法上存在对于具有前科而构成累犯的 特别处罚制度。但是,从目前所可能查阅到的其他文献来看,秦朝的司法实践中对于一次犯 罪和多次犯罪是加以区别对待的。从睡虎地出土的秦墓竹简来看,作为司法文书的《爰书》 中,一般都要注明犯罪人有无前科,是初次犯罪还是再次犯罪。对于以前曾犯过罪的犯罪人 ,一般都要加重处罚。如《法律问答》中载:“司冠盗百一十钱,先自告,何论?耐为隶臣 ,或曰赀二甲。”[6]而根据秦律的规定,一般人盗得百一十钱,当处以赎黥,但是上例中 是服司冠刑的罪犯,又犯了盗百一十钱的罪,因此,适用加重处罚的原则,处以“耐为隶臣 ”。因而可以说,在秦朝的司法实践中,具有前科而构成的再犯(或者说累犯)已经受到加重 处罚的司法惯例所限制。
前科的量刑效应公开见之于历史文献,是出于北朝时期的魏律。根据《魏书·世宗纪》记 载,延昌二年八月诏:“其杀人、掠卖人、群强盗首、对虽非首而杀伤财主、曾经再犯、公 断道路、劫夺行人者,依法行决,自余恕死。”根据以上记载,至少在后魏时,“曾经再犯 ”是当时量刑加重处罚的因素之一。
中国古代刑法史上前科量刑效应制度化的标志,起于唐律。唐律分别规定了“再犯”和“ 三犯”制度:(1)所谓再犯,是指犯罪已被告发或已被决配而又再犯新罪。根据《名例律》 的规定:“诸犯罪已发及已配而更为罪者,各重其事。”对此《疏议》解释到:“已发者, 谓已被告发言;其依令应三审者,初告亦是发讫。及已配者,谓犯徒已配。而更为笞刑以上 者,各重其后犯之事而累科之。”[7](2)所谓三犯,是指经常性的犯罪,起码三次以上。 根据《盗贼律》规定:“诸盗经断后,仍更行盗,前后三犯徒者,流二千里;三犯流者,绞 。 ”但是应当注意的是,唐律所指的三犯,仅限于三犯同种罪行。
国民党政府的刑事立法源于《暂行新刑律》,虽然在其后于1928年颁行了独立的《中华民 国刑法》,并在1935年修订后在我国台湾地区沿用至今。台湾地区刑法典第六章规定了较为 完 整的累犯制度,其所体现的前科的量刑效应为:“加重本刑至二分之一。”
2.新中国刑法中的前科量刑效应。新中国刑事立法对于存在前科再次实施犯罪而构成累犯 的处罚,经历了一个由“加重处罚”到“从重处罚”之由严到宽过程。这一变化是与中国现 实的国情与罪情相适应的,经过几十年的司法实践检验,证明也是可行的和合理的。
加重处罚时期。民主革命时期的人民民主政权所颁行的单行刑事法律以及建国之初的有关 单行刑事法律中,有关规范均对具有前科者再次犯罪而构成的累犯采用加重处罚原则:(1)1 934年4月8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31条规定:“凡犯本条例第3条至30条 所列各罪之一项或者一项以上,经法庭判处监禁,又再犯本条例所列举各罪之一项或者一项 以上者,加重处罚。”(2)1942年《晋冀鲁豫边区妨害公务违抗法令治罪暂行条例》第5条规 定:“第一条、第三条之累犯,加重处罚。”(3)1952年东北人民政府《关于根绝烟毒处理 贩毒分子的决定》第5条规定:“凡排斥包庇毒贩运毒……,如系一贯累犯,情节严重恶劣 , 顽固抗拒坦白者,则应加重一级处分。”
从重处罚时期。1979年刑法典作为新中国第一部生效刑法典,确立了具有前科者再次实施 犯罪而构成累犯应当“从重处罚”的基本原则,1997年修订通过的现行刑法典再次确认了这 一 原则。
3.明确承认前科量刑效应的司法举措。我国刑事立法未正面承认前科及其刑事法律后果, 但是,作为前科制度范畴之内的累犯制度,在我国刑事立法上居于重要地位,它所起到的主 要作用,也是导致行为人的后罪被从重处罚。对于累犯制度与前科制度的关系,笔者将在后 面详说。
我国的刑事司法中虽然也未正面承认前科制度及其量刑效应,但是却长期处于用而不宣的 状态。最高人民法院所颁行的司法解释中,涉及前科量刑效应的文件为数不少。其对于前科 的态度,可以分为以下几类:(1)明确承认前科的从重量刑效应。换言之,具有前科者,应 当从重处罚。例如,最高人民法院1957年4月30日颁布实施的《1955年以来奸淫幼女案件检 查 总结》第二部分规定:“二、对利用教养关系奸淫幼女的,或者有奸淫幼女罪前科的,在 认定上述犯罪情节的基础上,从重处刑。”(2)明确承认前科的加重量刑效应。换言之,如 果犯罪人存在前科,则对其确定的刑罚应当提高一个量刑幅度。例如,1994年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办理伪造国家货币、贩运伪造的国家货币、走私伪造的国家货币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 律 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就规定:“因伪造或者贩运伪造的国家货币受过刑事处罚后,又 实施伪造或者贩运伪造的国家货币的行为,……”加重处罚。再如,1995年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适用〈关于惩治侵犯著作权的犯罪的决定〉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因侵犯著 作权罪曾被追究刑事责任,又犯侵犯著作权罪的”,加重处罚。
当然,也有的司法解释虽然没有回避前科这一提法,但是却回避了其量刑效应。例如最高 人民法院1963年12月6日《关于被假释或提前释放的罪犯又犯新罪如何处理问题的批复》认 为 ,“假释考验期满后,原判刑即作为前科,再犯新罪者,犯什么罪处什么刑。”换句话说, 是承认前科制度但是却不承认前科的量刑效应,不从重处罚。
笔者认为,前科制度存在的现实意义和法律意义,在于其所导致的一系列法律后果,包括 刑事法律后果和民事、行政法律后果,当然,其核心是刑事法律后果。而前科的量刑效应, 是其刑事法律后果的基础和落脚点。如果不承认前科的量刑效应即其对后罪起到的从重处罚 作用,那么其他法律后果存在的意义也就不大。因此,上述司法解释在承认前科的基础上回 避其量刑效应,导致其对前科的承认毫无意义。
4.前科量刑效应的评判。笔者认为,鉴于具有前科者再次犯罪的客观事实和由此所反映出 的犯罪人所固有的相对较大的人身危险性,因而对犯罪人再次实施之后罪给予相对较重的否 定性评价和较重的刑罚裁量,是可取的,也是合理的。因而采用从重处罚的原则或者加重处 罚的原则,虽然从严处罚的程度不同,但是在总体从严幅度上是可以接受的。
相比较而言,笔者认为“从重处罚”的原则较为合理,不至于过于机械而强行抬高犯罪人 实际所承担的刑罚之最低度。理由是,即使是具有前科者再次犯罪而构成累犯,犯罪人也并 不一定是人身危险性均极为严重,而是相对同等情况下犯罪的其他犯罪人而言具有较重的人 身危险性,并且因此而反映出对犯罪人前次犯罪所评定的刑罚在量上略不足,未能阻止犯罪 人的再次犯罪,因而有必要对于后罪的刑罚在量上略有增加,以突出特殊预防之刑罚目的。 基于此,在同一量刑幅度内对(具有前科而再次犯罪的)犯罪人相比较于初犯者“从重处罚” ,已经足以起到惩治其过大的人身危险性和补足前次犯罪刑罚量不足之缺憾。如果采用加重 处罚的原则,则过于机械和生硬,一次性将犯罪人的再次犯罪的刑罚抬高至另一量刑幅度甚 至是实质上变更为另一种刑种,则过于漠视犯罪人的合法权益,尤其是在上一量刑幅度是绝 对死刑等极端情况下,无端将罪不至死的犯罪人因前罪(可能是极为轻微之罪)的存在而硬性 判处死刑,因而此种前科量刑效应较不可取。但是,承认前科的量刑效应应当限于“从重处 罚” ,并不是绝对排斥“加重处罚”的适用。笔者认为,如果在刑法典将前科的量刑效应固定化 为单一的“应当从重处罚”,并将这一标准适用于所有前科事实,则导致前科的量刑效应显 得过于苍白无力。笔者认为,对于前后罪均属于严重犯罪,以及多次再犯罪的犯罪人,将其 前科的量刑效应升格为“应当加重处罚”,不仅符合现实需要,也具有司法可行性。
其一,基于“犯罪次数”的等级划分。笔者认为,将多次犯罪的犯罪人的“犯罪次数”加 以限制,从而将一定次数之后的犯罪人视为危险犯罪人,进而将其处罚原则由“应当从重处 罚”升格为“应当加重处罚”,是可取的,值得肯定。换言之,既使在已经对二次犯罪基于 前科存在而加以从重处罚的情况下,仍然难以遏制行为人再次犯罪的,表明犯罪人的人身危 险性确实非常之大,前科导致的“从重处罚”仍然不足以实现刑罚特殊预防作用,仍然不足 以防止犯罪人再次犯罪。此时,如果对于犯罪人的第三次以上的犯罪,还是只能再次套用前 科固有的“从重处罚”之量刑标准,则依然起不到应有的预防作用。
其二,基于“犯罪严重程度”的等级划分。笔者认为,如果犯罪人所实施的前后罪均为“ 严重”的犯罪,则此时基于前一重罪而存在的前科,对于后一重罪所起到的从重量刑效应, 就不应当属于单纯的“应当从重处罚”,而是“应当加重处罚”。至于严重犯罪的范围,笔 者认为,可以圈定为我国刑法典总则重点予以关注的某些严重犯罪类型,具体而言,包 括三种类型:一是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应当负刑事责任的严重犯罪类型,包括 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二是可以 实施无限防卫权的“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包括杀人、抢劫、强奸、绑架等犯罪 ;三是不适用假释的暴力性犯罪,包括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杀人、爆炸 、抢劫、强奸、绑架等暴力性犯罪”。笔者认为,上述犯罪受到刑法典总则的格外关注,足 以说明其社会危害性的严重程度。因此,笔者认为,将前后罪均为上述犯罪类型之一的严重 犯罪,将前科的量刑效应由“应当从重处罚”升格为“应当加重处罚”,不仅符合刑法的整 体立法精神,也有利于严厉打击此类严重犯罪,保护社会既有之稳定秩序。
5.现行刑法典上前科量刑效应的含义。中国现行刑法典规定,对于具有前科者再次犯罪而 构成累犯的,“应当从重处罚。”关于这一处罚原则的理解与适用,在司法实践中应当注意 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其一,关于“应当从重处罚”的应有之义。笔者认为,应当从重处罚,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的要求:(1)所谓“应当”从重处罚,是指只要犯罪人具有前科,并且前科尚未达到五年而 没 有归于消灭,均必须进行从重处罚,没有灵活的余地,不存在可以进行从重处罚也可以进行 不从重处罚的选择权。(2)何谓应当“从重”处罚?有一种观点认为,这里所称的“从重”, 是比照初犯从重进行处罚,也就是说,对具有前科者再次犯罪的从重处罚不是无原则的从重 ,而是以初犯为参照系的从重。换言之,当具有前科者所实施的犯罪行为与某一初犯实施的 犯罪行为相似时,比照该初犯应判的刑罚,在此基础上再从重一些。应当特别注意的是,对 于具有前科者再次犯罪的从重处罚,绝对不是一律按某一法定刑幅度的最高刑来判处刑罚, 当然此种判处方式也是符合累犯“从重处罚”的原则,但是一律判处最高刑,显然违背立法 原意,也是一种不负责任的量刑方式,应当尽量避免。正确的作法是,要根据全案的综合情 况加以考虑如何从重。
其二,具有前科者再犯数罪,如何从重处罚?对于此种复杂情况,究竟应当如何适用累犯的 从重处罚原则,法律无明文规定。对于此种情况,刑法理论界存在截然不同的两种观点:一 种观点主张,对数罪采取从重并罚的方法,应当是先对数个后罪分别处以正常刑罚,而后根 据刑法典所确立的数罪并罚制度进行从重处罚。另一种观点认为,对数罪采取分别从重处罚 的方法应当是,在数罪中只对发生在前科消灭期间之前的犯罪从重处罚,对于其他犯罪仍处 正常刑罚,然后按数罪并罚原则决定执行的刑罚。[8]相比较而言,笔者赞同后一种观点, 主要理由如下:其一,后罪发生在法定的前科存续期间之内的,当然存在对于前罪的量刑效 应,此时后罪应当被从重处罚;如果后罪发生在法定的前科存续期间以外,则不存在对于前 罪的量刑效应,因而就不能对后罪“从重处罚”。但是,行为人在前罪的刑罚执行完毕或者 赦免之后,再犯数罪的,可能存在某些犯罪处于前科的存续期间以内,而另外一些犯罪则发 生在前科消灭之后。因此,对于前者应当从重处罚,而对于后者不能从重处罚。其二,数罪 并罚制度,其本身已经具有相对独立的从重刑罚适用制度,即“限制加重”原则。这种刑罚 适用原则是就已经存在独立宣告刑的各个独立犯罪适用的,因而从逻辑顺序上讲,是各自独 立的数罪先行存在彼此无关的宣告刑,然后才依靠数罪并罚制度将各个宣告刑加以限制加重 ,决定最终实际执行的刑罚。因此,如果前述第一种观点,则是依据数罪并罚制度量定数罪 综合刑之后,再从重处罚。那么,此时所称的“从重”之刑罚在上下限上就无从确定,缺乏 依据。
其三,判决宣告之后发现存在前科之情况的处置。作为前科的前罪,只要是本国刑法典存 在管辖权或者是由本国司法机关所裁决,全部可以对后罪产生法定的从重量刑效应。但是, 以中国现实司法实践为例,由于地域广大,因而某一犯罪人在甲地犯罪并被执行刑罚的,通 常难以为乙地所知,这对于通信与信息不发达的地区,更是如此。就发达地区而言,也可能 因为工作人员的失误而导致漏查。同时,各级审判机关的管辖区域与层次的不同,导致彼此 信息的不通。基于以上情况,对某一犯罪人实施的犯罪行为实施追究刑事责任时,是否曾经 存在前科而应当从重处罚,失察的情况较多。因此而导致的司法困惑是,如果对某一犯罪人 的判决宣告之后,又发现犯罪人存在前科而尚未消灭的,应当如何处理?是置之不理而轻纵 犯罪人,还是停止刑罚之执行而再行确定新的刑期?如果刑罚已经执行完毕或者已经被赦免 的,是否还再加其刑呢?
可资借鉴的是域外立法例包括韩国刑法典和中国台湾地区刑法典。例如,韩国刑法典第36 条规定:“判决宣告后发现为累犯的,可以将宣告的刑罚期总算,重新确定刑期。但宣告的 刑期执行完毕或者被免除的除外。”[9]再如,我国台湾地区刑法典第48条规定:“裁判确 定后,发觉为累犯者,依前条之规定更定其刑。但刑之执行完毕或赦免后发觉者,不在此限 。”对上述法条加以分析可以发现,两者的处理方式基本上是一致的,即在后罪已经宣告的 刑罚被执行完毕或者被免除之后的,就不再追究;而在此之前的,则应当根据前科的量刑效 应而重新评价和确定后罪应当承担的刑罚。笔者认为,我国台湾地区刑法典的立法处置措施 是得当的和可以借鉴的。
三、前科的量刑效应不及于未成年人
未成年人犯罪,不管是否存在前科,均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这属于世界各国所通认的 法定从宽情节。因此,未成年人具有前科而再次犯罪的,是否也存在前科量刑效应呢?笔者 认为,在此种情况下,如果认定未成年人的前科具有法定“应当从重处罚”的量刑效应,则 显然与未成年人犯罪必须遵守的整体法定从宽情节,形成了实际的逆向情节冲突,显然在立 法逻辑上出现冲突,与刑法典所体现出的保护未成年人的整体精神相违背。
笔者认为,由于未成年人辨别是非能力和自我控制能力具有一定的限制,思想不稳定,容 易出现反复,因而再次犯罪的未成年犯罪人,未必就属于主观恶性较大和人身危险性较大, 未必就一定要适用前科固有的量刑效应即“应当从重处罚”的原则。基于此,与其在立法上 出现与刑法典从宽处罚未成年人之整体精神相冲突之不妥当的情况,不如干脆规定未成年人 的前科不具有导致后罪之刑罚“应当从重处罚”的量刑效应。实际上,域外有关于此的立法 例表明,未成年人的前科不具有导致后罪从重处罚的效力作为一项原则,实际上已经为许多 国家所采纳,已经经过多年的实践检验。例如《俄罗斯刑法典》第18条第4款规定:“一个 人在年满18岁之前实施犯罪的前科,以及其前科依照本法典第86条规定的程序被撤销时,在 认定累犯时不得计算在内。”
四、关于前科量刑效应的不同意见
从实体的角度来看,各国均将前科看成刑罚加重事由。但是德国刑法理论界有观点对此持 反对态度:[10]事实上,只是在很狭窄的前提条件下,以前实施的犯罪行为才可能作为提高 刑罚的理由(在罪责适当性范围内)。只有行为人在自己以前实施同种犯罪或者类似犯罪而被 判处刑罚后对社会规范的效力很清楚的情况下,自然反抗社会规范,因此刑罚被提高的,才 属于这种情况。因此固有的法律成语认为“以前的有罪判决,不得对行为人作为警告之用” 。 同时,顽固的反法律性这一要素(当然,它确实可以构成提高刑罚需要的事由),不能简单地 从重新犯罪的事实中推论出来,因为实施犯罪还可能是因为单纯的意志薄弱,或者因为受对 犯罪起促进作用的第三人的影响,但是,法院宁可对犯罪行为中表现出来的行为人的思想作 出认定。基于此,应有的选择是,只有当行为人事实上表露出来对相关法益的不受过去刑罚 影响的蔑视时,刑罚才可以因为重新犯罪而加重。尽管从特殊预防的角度来分析,对于重新 犯罪的犯罪人提高刑罚力度可能有意义:只要此种情况表明,过去科处的制裁并没有能够促 使行为人有一个符合规范的社会生活。但是,即使从这一认定中也不得直接得出结论——认 为 现在就可以对行为人处于较为严厉的刑罚,因为此种选择可能产生重大的反社会效果。
笔者不完全赞同上述观点,虽然在犯罪人再犯同类犯罪或者近似犯罪的情况下,可以更为 清晰地判别犯罪人对于社会规范的严重对抗性,更为明显地反映出犯罪人对于过去刑罚影响 的蔑视,因而应当提高刑罚力度。但是,并不能以此为据认为犯罪人实施其他类型的犯罪, 就完全等同于初犯而忽视前科的存在,从而绝对地、武断地割断前后两次犯罪之间的潜在性 联系。
笔者认为,初犯是在未受刑罚处罚情况下的第一次犯罪,其人身危险性往往因其是不知犯 罪与刑罚之因果关系,或者未经刑罚改造而误入歧途显得较为轻微。而具有前科者则是在受 过 刑罚处罚之后再次选择犯罪,无论再次犯罪的原因是什么,都足以表明犯罪人对于前次刑罚 惩罚与改造的忽视态度,或者说根本就是持否定的蔑视态度,最低限度也反映出犯罪人再次 实施犯罪时对于相关法益被损害的放任、认可态度。因此,结合前科制度的立法设置加 以考虑,笔者认为,对于具有前科者在后罪量刑时予以从重处罚,是可取的,德国刑法学者 的上述观点并不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