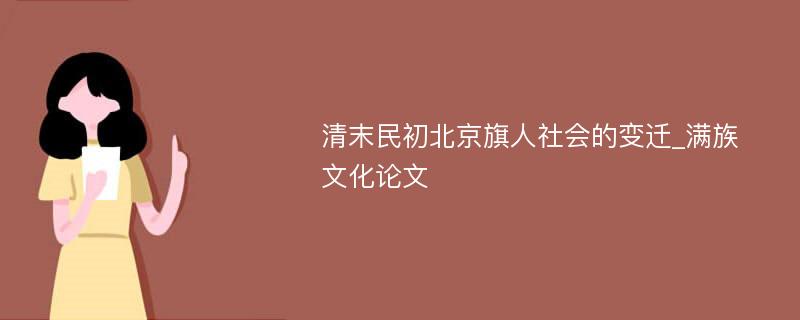
清末民初北京旗人社会的变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旗人论文,民初论文,清末论文,北京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中国少数民族之一的满族,以其勇猛剽悍建立了大清王朝,从而转变为一度拥有各种特权的统治民族。然而,随着时代变异,尤其是在风雷激荡的清末民初时期,晚清王朝江河日下,寄生其上的旗人,满族人的优越地位自然也不可避免地随着清政权的日益崩溃而发生巨大的变化。本文拟通过对清末民初居于京师的满族旗人社会生活的考察,展示这一痛苦的变迁历程。
旗人主要包括满洲八旗、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三部分,除一部分留在东北地区外,其余皆分布于关内一些重要的大城市,这里重点考察的是居于满清统治中心北京的满洲旗人群体,他们构成了旗人的主体,以下旗人一词皆指满族旗人。清末民初,北京的旗人社会发生了多方面多层次的变迁,主要表现为旗人生活的贫困化,社会地位的平民化,从事职业的多元化以及八旗兵的近代化变革等几个方面。
一
北京旗人生活贫困化的日益加剧。清初,北京旗人以军事为业,其生活所需全部由国家供给,清政府为此相继建立了份地制度和粮饷制度。从1644年12月起至1666年,清政府先后三次大规模圈占田地,将所圈之田分配给迁京的诸王勋臣和各等兵丁。一部分为皇帝和八旗王公贵族占有,形成大大小小的皇庄王庄,一部分按丁口分给八旗兵丁,作为负担兵役的“份地”;清政府还按八旗兵丁的不同级别发放不同数量的饷银,从而为八旗制度的巩固奠定了物质基础。另外清政府为了提高旗人的社会地位和减轻他们的经济负担,规定各旗壮丁差徭、粮草、布匹永停输纳,只负担朝廷的兵役。这种全部由国家包下来的制度,在一定时期内,使旗人生活无忧,全身心投入于军事作战,保证了大清王朝的一统天下和初期政权的稳固。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旗人家庭生计从康熙年间开始至清末变得日益困难。
早在康熙年间,京师部分旗人家庭生计就出现了问题。旗人家庭贫困的直接原因在于沉重的兵役及人口的增加。当时有不少规模较大的战争,参战的旗人要自备马匹、服装和武器,许多旗民家庭不堪重负而借债,战后,器毁马亡,难以还债,以致家庭陷入生活困境。不过,这种贫困家庭数量最初较少,贫困的程度也较轻,政府多采取恩赏银两、免去债务、修建房屋、增设兵额等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或缓和了旗人生计的窘境,从而未对旗人社会和满清政权构成多大威胁。但是乾隆中期以后,旗人生计问题日益严重,尤其是鸦片战争爆发后,“内忧外患”接踵而至,大清王朝出现全面的危机,伴随而来的是京旗子弟生活的空前恶化。政府所发的粮饷日益不够维持生活之用,寅吃卯粮对一般旗人家庭来说是极为普遍之事。不少家庭为了生计,将有限的家产变卖,更多的家庭则靠借贷度日,到月所领的粮饷被迫拿去还债,只得再借,陷入高利贷的泥沼;不少旗人以旗地作抵借债,到期不能还债则只有出卖份地。旗人的份地按清朝的法律是不准出售的,尤其是不准卖给汉人,但是不少旗人家庭为了维持生活,除了典当自家的衣服、器具外,就是以地作抵。在这一出售份地的队伍中,上有宗室,下有一般旗民。面对旗人不断出卖旗地的现实,清政府在一度严禁无效且又无良策解决旗人生活贫困的情势下,不得不承认既成事实,于咸丰二年(1852年)颁布了《旗民交产章程》。章程宣布,除奉天一省盗典盗卖仍照旧例严行禁止外,顺天直隶等处的旗地“无论老圈自置,亦无论京旗屯居及何项民人,俱准互相买卖”,同时宣布“从前已卖之田,业主售主,均免治罪”。[①]正式承认旗地可以卖与汉人。虽以后清政府对旗地买卖问题又出现过反复,但旗人典卖土地则愈演愈烈,至二十世纪初年,北京地区的旗地已经典卖者占十之七八,“现在旗人手内交租者,大抵十无二三。”[②]旗地的典卖是旗人生计困难的结果和表现,但旗地的典卖,无异于饮鸩止渴,对一般旗人家庭的生计来说,则失去了一个维持生计的基本物质来源。由于贫困状况的不断恶化,使得一些旗人铤而走险,闯入衙署闹事的事件屡有发生,有的贫困旗人则入伙为盗,抢劫钱局和粮仓,这些事例在《清实录》中多有记载。光宣之际,甚至一些有四品宗室、格格、额附名位的人“求其一饱而不可得”,只有那些当朝权贵仍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
旗人生活贫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原因应归于清政府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
从鸦片战争前后始,清政府的财政就出现了相当程度的危机。一是大量鸦片输华,使中国有限的白银大量外流。[③]再加上鸦片战争的消耗和对外国人的赔款,清政府库存白银减少,以致出现了财政危机。随之出现的银贵钱贱也影响了广大人民包括普通旗人家庭的生活。再加上国内持续十几年、横跨十八省的太平天国农民大起义,使清政府军费大增,而赋税收入减少。用来铸钱的铜也因交通阻隔而难以运进京城,清廷财政极为紧张。1853年太平军控制了长江通道,清政府的江南财源被切断,各省忙于就地筹饷和相互协拨,没有多少款项起运北京,但支出军费三年来累计已达3000万两。同年6月户部库存白银仅有22万7千两,国库可支用的白银不足七月的兵饷。[④]清政府为了解决财政困难,采取铸造和发行大面额值的大钱、钞票等措施,以应军饷之急需,而且连广储司存有的三口大小约重二千余斤、计可值银数十万两的金钟,也获准熔化充作军需。[⑤]由于所发银票“无从取银”,钱钞“不能取钱”,而大钱则“有整无散”,因此“民间怀疑而不用”,市肆采取各种方式加以抵制,“故有终日持钱竟至不能买得一物者”。从而银票、铜钱大钱贬值,其结果加剧了北京地区的通货膨胀。[⑥]1858年食米“从前每石只卖十余吊文,今则每石二十余吊不止;猪肉每斤只卖二三百文,今则每斤六七百文不止。至于杂粮、杂货、零星食物以及一切日用之类无不腾贵异常,计自去秋至今,增长几至一倍”。[⑦]在物价上涨的形势下,旗丁的粮饷却不能照额发放。1853年,八旗官兵的饷银,折发制钱,并搭放铁制钱二成,其实际收入已相对降低。从1860年起,清政府规定减成发饷,“骁骑校等项官兵,按四成实银、二成钱折开放;技勇养育兵等,按五成实银、二成钱折开放。”[⑧]这样,一般兵丁只能领到原饷的六、七成,有时还欠饷不发。咸丰时期,对京师旗人的所有优恤几乎全部中缀。正如上述,所发制钱与铁钱等贬值,八旗官兵“现因铁钱不能畅行,诸物昂贵,奸商把持”,“一切用度无不拮据”,不少旗人家庭的生活陷于绝境,以致有贫困旗人冒险叩阍(叩阍即直接找皇帝)的事。咸丰八年叩阍者正黄旗内务府差役吉庆称:“实因家寒,难以糊口。钱粮领出,铁钱不能使用,百物昂贵,起意叩阍”。[⑨]清政府经太平天国运动的致命打击已元气大伤,但其后并未有喘息的机会。“求富求强”的洋务运动耗资甚巨,甲午战争、庚子事变、巨额赔款、光绪大婚、慈禧寿辰耗费大量白银,清政府财政极度拮据,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只有靠大借外债、卖官鬻爵、加重广大人民的赋税来缓和财政危机,但这决不能解决其财政困难。在清政府财政危机和大大小小的官僚贪污腐化的形势下,那些完全依赖清政府饷银为生的旗人,生计自然日益艰难。光绪末年,京城诸旗营兵丁每月按规定可领饷银二两八钱,觉罗前锋护军每月可领饷银三两五钱,但每次发饷,经过层层克扣,实际领到的只有七八成;另根据时人的回忆,光宣之际,实际发放给旗丁的饷银数目不过是规定的五分之一。[⑩]按当时的粮价,旗丁连自身一月的生计也难以维持,养全家就更困难了。不少旗丁“面有菜色,衣皆蔽徙”,或“全家待饷而活,而饷为官吏所扣,不得已而质其子女以为奴婢”,常有“逃无所归,则相率为盗”,更有“穷到尽头,相对自缢”者。至清亡前夕,已有数十万旗民沦为饥民。
广大旗人贫困化的根源则在于满清政府所固守的八旗制度。满洲先人努尔哈赤,为了更有效地将本部落组织成一支强大有力的团体,以便在部落和民族的厮杀中求生存求发展,创立了八旗制度。这是一个军政合一、兵农合一的组织,旗人“出则为兵,入则为农,耕战二事,未偿偏废”。这一制度在当时确实显示出其巨大的威力,凭借它,努尔哈赤统一了东北各部,建立了政权,最终在皇太极的领导下于1644年大败农民军,迁都北京,建立了大清王朝。满族人完全是以马上功夫夺得政权的,作为文化落后、人数微少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面临着种种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为了巩固其政权,皇太极对八旗制度进行了改革,八旗兵丁完全以军事为业,成为职业兵,企图以全族的武力来维护大清王朝的统治。为此还在政治、经济等各方面采取措施,树立和维护旗人的优越社会地位,造成族天下的统治形式,以增强满族及整个旗人社会的凝聚力。在官员任命上,首崇满洲,满员居上。“我朝封爵之制,亲亲之外,次及勋臣,……此所记载首满洲,次蒙古,又次汉军。”[(11)]同一机关,满人居首,满员权重,印归满官,即他们多担任正职。同时在封官加爵方面,满人优先。从清初至清亡,政府官员的任用上基本上维持了这一格局。旗人在法律上也享有特权。“凡旗人犯罪,笞杖多照鞭责,军徒免发遣,分别枷号”,而不象汉人犯罪后,该笞杖的笞杖,该充军的充军。另外为了维护旗人的优越地位,不准旗民交产、旗民通婚、旗民杂居,同时清政府也下令禁止旗人远距离外出,从事诸如工商、演戏等其它行业,禁止向他人借钱等,以巩固八旗制度和维护旗人的“颜面”。清政府为维护旗人的高贵地位所制订的一系列条例制度,在一定时期确实在助于旗人自尊、自信的确立,有助于狭隘的民族意识的增强。如果说在天下未靖、政权不稳、仍需强大的武力来巩固新建政权之时有一定积极作用的话,那么伴随着战争的渐息和时代的进步,旗人所享有的种种特权和束缚,则日益构成旗人尤其是满族旗人进一步向前发展和进步的巨大障碍。后来的历史则证明了这一点。
政治法律上拥有特权,生活全由国家包起来,且不准从事其他行业,在此制度下的个人,没有了人生的一点风险,其后果往往是那些拥有特权者失去了进一步发展自身的动力,最终变成时代的落伍者;作为一个民族,则是不求进取,失去了民族进步的勃勃生机。一些旗人无所事事,贪图安逸,只知提笼架鸟、茶馆闲聊;只知挥霍浪费、鲜衣美食,不知农商为何事。“聚数百万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不兵、不民之人于京师,而莫为之所,虽竭海内之正供,不足以赡”[(12)]就是写照。自然,并非所有的旗人都是不思进取、坐吃山空之辈,旗人中也出现了不少文学家、戏剧家等,但由这种制度所造成的后果是恶劣的。它使众多的旗人子弟不求进步、习于奢华的生活,毫无吃苦耐劳的精神,一些旗人生计的贫困不能说与其长期养成的奢侈浮华的生活习惯无关。另外,不准旗人从事他业的规定,也使得贫困旗人丧失了自谋生计的基本技能,只能赖饷以生。当清政府财政出现危机和官僚腐败加深时,他们则由于缺乏生活自救的手段,只能坐以待毙。
晚清旗人生活的日益贫困与旗人人口的增加也有关系,这一原因在清廷的谕令和大臣的奏章中是必列的一个因素,即所谓的“生齿繁滋”、“生齿日繁”。据1908年民政部统计,当时京师八旗人共约23.3248万人,其中内城22.3248万人,外城1.3523万人。八旗男女人口总数约占全城人口总数70余万的三分之一左右。在八旗人口中以宗室人口的增长最为显著。根据记录清皇室人口的玉牒资料可知,从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至光绪末年,宗室人口增长了四倍。[(13)]宗室每个孩子一出生就有定额的俸禄,且爱新觉罗家族都集中于京师,生活无忧,代代繁衍,形成一个庞大的宗室社会,构成了清财政的重大负担。而一般旗人的职业就是披甲当差,只有当差的旗丁才能领到一份固定的粮饷,但兵有定额。虽然清政府曾采取扩大兵额的方式吸纳了一部分增加的丁口,但仍不能解决问题。伴随着旗人人口的增多,闲散人口的数量日益增加,势必加重家庭生计的困难。
需要指出的是,旗人生活的贫困化,不能一概而论,还有另一面的事实,即旗人社会两极分化和阶级分化现象的加剧。握有实权的皇戚显贵、达官贵族,他们除了清廷所给的俸饷和皇帝的赏赐外,还中饱私囊,仍然过着奢侈豪华的生活。在京城日益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下,权贵子弟却竟相追逐时髦的生活方式,更加走向堕落。
正是由于清末多数旗人的日趋贫困化和清政府日益加剧的财政危机与社会危机,才使得清廷逐步变更不合时宜的八旗制度,从而加速了旗人社会的变迁进程。
二
旗人职业多元化的出现。北京旗人逐渐从事他业的实现,主要是清政府迫于种种压力而不断对八旗制度进行变革的结果。
清初,北京旗人以军职为唯一合法职业,国语骑射、驰骋疆场构成了其生活的全部内容,从事工、商、戏剧等各种行业以及出外贸易被认为是有辱旗人脸面。清初法律明文规定:“在京满洲另户旗人,于逃走后,甘心下贱,受雇佣工。不顾颜面者,即削除旗档,发遣黑龙江等处,严加管束。”[(14)]对旗人演戏之风,也有明文规定:“凡旗人因贫糊口,登台卖艺,有玷旗籍者,连子孙一并销除旗籍。”[(15)]为解决贫困旗人的生计问题,清政府囿于陈旧的思维,固守八旗制度。在财政许可的情况下,采取的是恩赏银两、扩大养育兵额等措施;进入近代以后,随着旗人贫困化的加据和清政府财政的日益困难,依靠拨付国帑救济旗人的方式日感吃力,才开始在较在规模上采取实际变革措施,逐步冲破八旗制度的樊篱,旗人也因此逐步摆脱八旗制度的束缚,开始涉足他业,开辟新的生存之路。
京旗子弟向农民转化。清初的大清法律,并未明文禁止旗人从事农业,但旗人入关后,皇太极对原八旗制度进行了改革,多数旗人放弃了农业耕作。面对越来越多旗人家庭的贫困化,清政府开始进行移京旗务农的实验,这种实验最早出现于雍正年间。不过在鸦片战争以前,这种尝试规模小,人数少,且成效不大。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后,一度停止的移居京师旗人屯垦的行动又向前迈进了一步。原因是十几年的农民大起义给清政府以沉重的打击,财政拮据的清廷只能减成发放旗丁的兵饷,更有大量的孤儿寡母需要救济。1864年,即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被镇压的当年,清政府不得不重申:“旗民生计维艰,听往各省谋生”。[(16)]放松了八旗制度对旗人的束缚,为旗人寻求生存之路提供了前提。同治七年(1868年),山西巡抚沈桂芬上奏也讲:“亲见旗民生齿繁庶,不农不商,除仰食钱粮外,别无生计之策,一丁所领之米粮不敷一丁之食”,以致不少旗人铤而走险,“其强者悍然为非,每陷刑网;弱者坐以待毙,转于沟壑”,他提出求生之上策“无过移屯边方,中策则听往各省而已”。[(17)]光绪二十四年,即1898年,清政府再次谕令:“旗丁生齿日繁,徒以格律定例不得在外省经商贸易,遂至生计维艰”,“现当百度维新,允宜弛宽其禁,俾得各习四民之业,以资治生”。[(18)]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为实施旗丁归农、驻防归农,清政府又宣布旗人可以外出营生,凡是驻防马厂、庄田,分划区域,计口授田,责令耕种;无马厂、庄田之处,于各州县以时价购地,令旗人耕种。[(19)]但是即便是在旗人生计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不少旗人家庭由于长期习惯于坐食俸饷的生活,而不愿走出京师,寻找新的生活。光绪初年,清政府曾在呼兰地区“特留上腴晌地,以备京旗移垦”,后拨去京城旗人十三户。他们“在京有行装资给,在路有驿站供支,在屯有庐舍井灶,在地有牛力籽种,筹备于半年以前,费金至数千以上”,但结果“曾未一纪,并妻子相率而逃,莫可踪踪,仅余三户在屯,泣求将军咨回京旗”。[(20)]由此可见,一种制度使人丧失了进取心,且由此养成了好吃懒做的恶习,要改变它并走向新生是多么的困难。不过,在政府的鼓励下,还是有一些贫困的旗人走向田间,成为自食其力的农业劳动者。
走进工厂、成为工人。鸦片战争后,清政府有感于西洋枪炮的神威,大力鼓励满族旗人子弟学习西洋制造。1864年,清政府派八旗官兵48人到苏州,跟外国人学做炸弹及各种军火、机器与工作母机。1883年,醇亲王奕譞开办了北京神机营机器局,内多用满族旗人,从此出现了第一批近代旗藉工业工人。光宣时期,清政府除了接连颁发有关允许和鼓励旗人就业的谕令外,还从1906年起在北京、热河开办了一些以解决贫困旗人生计为目的的手工业工厂。这些工厂设立的宗旨,在于“以实业教育为重,务养成自谋生活之力,渐去专恃俸饷之心”。另外为改变“我国男子谋生、妇女坐食,久为列邦所讥”的局面,在京师专门为八旗女子设立了工艺厂,“以京师首善之区为八旗荟萃之地,尤应速立女工厂数处,先令京师八旗孤贫妇女入厂练习,藉示各省模范,次第推行。”[(21)]。女工厂的设立,不仅在于为贫困旗人妇女提供了一个自救的生存手段,而且还是一次意义深远的观念变革,反映了晚清时期中国社会传统思想的变化。这一举措有助于改变几千年来女子只能在家坐食的传统观念,女子参加生产劳动有利于妇女自身素质的提高,从而有助于男女平等观念的形成。在广大旗人走向自食其力的过程中,有一部分贫困旗人凭借自己的手艺,主动进入一些私人工艺作坊或手工厂工作,更多的旗人由于没有任何用以谋生的手段,以致步入了小商小贩者的行列;另外,在清政府“推广学堂”、“专重教育”的口号下,八旗闲散人丁被责令进入了清政府设立的初等农工商学堂,学习一些生产技艺,从而为日后自谋生计做了必要的准备。不过晚清时期,虽然旗人生活愈来愈困难,政府也提倡旗人从事他业,但告别寄生、走向自立的还是少数,他们多是那些无固定俸饷的八旗闲散和极其贫困的旗人。旗人职业多元化的全面实现是在辛亥革命之后。
满族旗人的平民化。这里所讲京师满族旗人的平民化,是指广大旗人不断地从法律和生活实际中失去往日政治优势地位的事实。这一平民化进程的展开,是与旗人生活的贫困化、职业化多元化及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日趋激化紧密相联的。
清政府建立大清王朝后,颁布了一系列旨在提高旗人地位的法律条文,这虽然在一定时期内有助于增强旗人社会的凝聚力,但也人为地阻碍了满汉一体化进程,不利于民族间的相互学习和进步。更为严重的后果是,民族的不平等政策激化了民族间的矛盾,构成了清政府稳固统治的不利因素,太平天国运动和辛亥革命都是在反对异族统治的口号下进行的。近代以来,在外敌侵略日益加深、阶级矛盾十分尖锐、满汉之间民族矛盾愈来愈激化、清政府的统治面临种种危机而难以解决的形势下,不得不顺应时代的潮流,变革过去的陈规旧法,以缓和满汉之间的矛盾。早在1898年,康有为就曾提出君民分治、满汉不分以定国是的建议。1907年,即光绪三十三年,面对革命党人反满宣传的不断升温,清政府提出划除满汉畛域的问题,“现在满汉畛域应如何全行化除,若内外各衙门各抒己见,将切实办法妥议具奏,即予施行。”[(22)]反映了清政府在革命运动日益高涨的形势下,为清除危机局面所采取的应急手段,自然也体现了时代的要求。清廷谕令颁布后,一时有不少关于去除满汉畛域的奏章送达朝廷,其中以两江总督端方的意见最有代表性。他提出了化除满汉畛域四条:旗人一律归地方管辖;旗丁裁撤,发十年粮饷,自谋生理;移京旗开垦;旗僚一律,报效廉俸,发补助迁移经费。[(23)]同年,修订法律大臣、法部右侍郎沈家本则提出:“清嗣后旗人犯遣军流徒各罪,照民人一体发配,现行律例各条概行删除,发照统一。”[(24)]同年8月《裁停旗饷》诏书,筹议旗人计口授田,自谋生计,同时规定:“该旗丁归农以后,所有丁粮词讼统归有司治理,一切与齐民无异”。[(25)]清政府制定的《满汉通行刑律》于1909年改名为《现行刑律》发布执行。它规定满汉民刑事案件,一律归地方审判厅审理,从而改变了旗民分治的成规,而统一为州县管辖。1901年,清政府废除了旗民不准通婚的禁令,1905年又重申取消旗民不准交产的禁令。这一切旨在取消旗人法律上的特权、缩小满汉民族矛盾的法令的颁布,实际上是满族日趋平民化的过程,它与伴随广大旗人贫困化而来的职业多元化过程相汇合,加速了满汉等各民族一体化的进程,有利于满汉人民关系的进一步加强。
八旗军的近代化变革。八旗军队以其勇猛顽强入主中原、一统天下,然而入关后没过多少年便渐失勇武之风,难以履行其应负的军事职能。早在平息三藩之乱时(1673—1681年),八旗军的武力已逊于刚入关之时,在平定四川大小金川叛乱时,绿营兵已处于主力地位。以后八旗军平时训练松弛,装备落后,缺乏战斗力。1835年,鸿胪寺卿黄爵滋曾生动刻画过日益堕落的京城八旗军的情形,“近见有三五成群,手提雀笼雀架,终日闲游,甚或相聚赌博。问其名色,则皆为巡城披甲,而实未曾当班,不过雇人领替,点缀了事。”[(26)]这种毫无军纪、只知玩乐的八旗军,根本无法与拥有新式武器和先进战法的西方军队抗衡,以致在历次对外战争中都以残败告终,虽然也不乏顽强抗敌的八旗军队。1851年,曾国藩曾上奏称:“自嘉庆十七年(1812年)至今,不举大阅者四十年矣。凡兵以劳而强,以逸而弱。承平日久,京营之兵既不经战阵之事,又不见搜狩之典,筋力日懈,势所必然。”[(27)]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农民军势不可挡,八旗绿营皆无法抵御,只能靠招自乡勇的团练来对付农民军;当英法联军进攻北京时,专职保卫北京的八旗兵腐败无能,以致皇帝逃出北京。面对大清政局的危机和汉军的兴起,清政府认识到必须对八旗军进行改造,从而才揭开了八旗军现代化的序幕。
咸丰十年,(1860年)清政府准胜保奏,令八旗军加练洋枪洋炮。同治四年(1865年)清廷谕醇亲王建立作为训练京师各旗营官兵的培训机构神机营,从京师各旗营选拔精锐,进行西式训练。1862年从京畿火器、健锐营及圆明园八旗兵中各抽四十人去天津训练,聘美国人为教练,专习洋枪洋炮、西式阵法与步法。1865年神机营又派圆明园八旗营等官兵五百人赴津学习。[(28)]同时又派八旗兵丁到江苏,委托李鸿章负责,专习外洋炸炮、炸弹及各种军火机器与制器之器。[(29)]1883年,还创设了神机营机器局,供应八旗兵军火。1900年八国联军重演三十年前英法联军进北京的故事,再次震撼了大清朝野上下,促使清政府更大规模的训练与改造八旗兵。1903年,清廷命袁世凯挑选八旗兵二万五千人,仿“北洋常备军”建立京旗常备军,并改编为陆军第一镇,担负保卫京师的任务。另外载沣摄政后,用了近两年的时间于1911年建立了一支装备先进的皇族禁卫军,内有交通队、机关炮队和重炮队等。为提高八旗官兵的素质,清政府还专门设立了军事学校,传授近代军事知识,对官兵进行近代军事教育。第一个八旗军事学堂是1887年在北京设立的昆明湖水操内外学堂,学员学习西法、测算、天文、驾驶、行船、布阵及施放枪炮等。以后又有几个用来培训八旗官兵的军事学堂建立,它们主要是1898年在天津仿效武备学堂而设立的旗兵学营,该学营供被选拔来的京旗精壮学习德国武备;1905年在北京设立的陆军贵胄学堂,专招王公世爵四品以上宗室及现任二品以上京内满汉文武大员之子弟学习各种知识和军事;1907年设立的扈卫学堂暨学兵营,到1910年已毕业三班。此外,清政府还派遣一些八旗子弟去出国学习军事,以去日本的为多。
清政府对八旗军的近代化改造,可以说顺应了历史潮流,有其进步意义,八旗官兵的素质和战斗力有一定提高是无疑的。但清政府有限的近代化努力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八旗兵的积弱现象,更不可能以它来挽救大清王朝的命运。实际上八旗兵没有完成向近代化军队的转型,原因是多方面的,满清王朝腐朽的封建专制统治从根本上决定了八旗军不可能被改造成一支近代化的军队。八旗军大小军官贪污成风,没有多少人认真钻研军事,如何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呢!另外八旗兵多为世袭兵,且在旗人生活日益贫困化的情况下,政府练兵也有筹化旗人生计之意图。将一些闲散旗人优先进入改造的军队,使八旗军几乎成为一个救济机关。这些只愿赖饷为生且习于安逸、惯于坐食的旗丁,被选拔学习西操西器也多是为混日子。不过,八旗军毕竟随时代大潮向近代化迈进了一小步,反映了晚清京师旗人生活变迁的一个侧面。
三
辛亥革命推翻了大清王朝的统治,它是满族旗人社会变迁的转折点,使旗人社会在晚清变革的基础上进一步向前发展。大清王朝灭亡后,不少地方的八旗兵丁被解散,驻防制度被取消,多数旗人家庭在失去过去由政府分配给的粮饷的同时自身家庭财产又缺乏保障,生计更加困难。为此,新成立的民国政府颁布了一些旨在维持旗人生计的法令和条例,主要有《优待皇室条件》、《关于清皇室皇族待遇之条件》、《关于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和《保护旗人公私财产文》等文件,旨在保护旗人的财产,维持旗人的一般生活。其中在《关于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中规定,“先筹八旗生计,于未筹定之前,八旗兵弁俸饷仍旧支放。”[(30)]在《保护旗人公私财产文》中指出“上年军兴之际,各省旗人,公私财产,间被没收。现在五族共和,已无畛域之分”,“凡八旗人民公私财产,应有地方官及公正士绅清查经理,以备筹画八旗生计之用”。[(31)]但实际情况却不尽人意。由于当时新政府财政极端困难,许多地方停发了旗饷,裁撤了旗营;北京虽然坚持发饷的时间比较长(至1924年北京发放了最后一次旗饷),但粮食在民国二、三年就不再发放了,且袁世凯死后,饷银渐有拖欠现象,至民国七、八年时,旗饷只在正月、五月、八月三大节时发放,从而成了变相的救济款。[(32)]由于所发俸饷极少,根本就不够旗丁家庭维持家用,再加上多数的旗人由于长期不事他业,缺乏生产的技术,以致于不少旗人家庭陷入了较晚清更加贫困的境地。有不少王公贵族,其皇庄的收入由于佃民的抗租等种种原因而减少,过去由政府所发的俸饷全部裁停,而自己又过惯了奢侈的寄生生活,不思也不愿自谋职业,只能变卖家产维持生计,因此坐吃山空、最后饿死者不少。溥义的堂兄弟溥涧家产吃完,靠卖画为生;庄王的后代饿死在南横街的一个空房子里;睿王的后代锺氏兄弟因生活无着而私掘祖坟。[(33)]另据一份调查各旗官员因饥寒而死的分析册表明,有许多京师满族官员生活极端贫困,平时依靠救济,不少人终因生活困难而饿死,普通旗人生活困难就可想而知了。以致于辛亥后,一时兴起了救济旗人的运动,北京出现了各种名目的八旗生计救济机构。以宗人府为代表的皇族,也成立了宗族生计维持会,它由知名王公贵族发起成立,主要为解决皇室宗室子弟而设。它规定凡皇族男子在20岁以上,并有普通知识者皆可入会。该会首先请求将东陵荒地拨给宗人府,分给无业宗室,招商开垦,利用租金和募来的资金开办教养工厂,以求“收养孤苦幼稚,教以工艺,三年卒业,可以自谋生活”。[(34)]1919年宗人府教养工厂正式开办,分地毯、织工、席、木料等科,收工徒100名,后又办了第二工厂,以生产地毯为主。其他的组织有三旗共和协进社,主要为帮助上三旗旗人的生计而设。1913年成立后,在圆明园开渠种稻,开辟汤泉行宫为公园,迁城内一些旗人安家,在南宛沃地也安排了一部分贫困旗人。还设营业厂,一部分旗人在这里设棚摆摊。民国政府也投资设立了一些工艺厂、教养厂等,直至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仍拨款200万元,开办贫民工厂,优先收容旗人。这些救济措施的实施,为一部分无自谋生计能力的旗人提供了学习技术的机会,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其由寄生生活向自食其力转变过程中所必然遭遇的困境。需要加以说明的是,辛亥革命后,北京旗人生活贫困的原因与晚清时已有所不同。此时旗人生活贫困局面的出现固然与民国政府财政危机以及出现的民族歧视有关,但从根本上讲仍是过去八旗制度遗留的恶果。八旗制度所造成的习于懒惰、无生存之技,从根本上制约着广大旗人由坐食俸饷向自食其力的转化,使得旗人在这一转型过程中承受着更多的痛苦和辛酸。自然由于缺乏政府的支持,从而加剧了旗人生活方式转型的阵痛。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广大的满族人民并未走上富裕之路,在走向新生的同时又饱受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剥削、封建主义的敲诈与压迫以及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之苦,只不过此时的生活贫困已不具有什么特殊性了。
辛亥革命后,满族旗人在政治法律上完全失去优等民族的地位,而成为中华民族中普通的一员。在民国政府颁布的《关于清皇族待遇之条件》中,明确宣布了“清皇族对于中华民国国家之公权及私权与国民同等”。[(35)]在《关于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中宣布旗人与“汉人平等”,“从前营业居住等限制一律蠲除,各州县听其自由人藉,满蒙回藏原有之宗教,听其自由信仰”。[(36)]这些条例的颁布,宣布了包括满清皇族在内的旗人被废除了前清时所拥有的一切特权,彻底完成了从高贵民族向普通民族的转化,旗人这一特殊的群体社会也被融入普通的民众社会之中。
辛亥革命加速了旗人职业多元化的进程。失去政府支持的广大旗人,为了生存,纷纷走上自谋职业之路。由于多数旗人缺乏生产技术而充当了小商小贩和人力车夫,也有一些旗人由于擅长吹打弹唱,成为梨园艺人,为中国的文化艺术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有的八旗子弟充当警察或从事教育;部分宗室子弟则“赴各国游学”,学习军事和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工业不断发展的形势下,有一些有钱有势的满族官僚地主,依靠出租房地产或开设当铺维持生活,也有投资经营工矿企业者,从而其身份开始由封建官僚地主向资产阶级转化。在生活困难的压力下,一些旗人妇女也走出家门,加入了生产者的行列。
在清未民初这一大动荡大转折的时代,旗人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所发生的政治、经济等诸方面的变迁是紧密相联甚至互为因果的,它们是一个过程的几个方面。旗人社会生活的转变历程既充满着新生的曙光,更有痛苦的心酸,它留给后人的是更多的沉痛的历史教训。
注释:
①《清文宗实录》卷62,《清实录》第40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831页。
②甘厚慈辑:《北洋公牍类纂》卷14,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铅印,第25页。
③李伯祥等:《关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鸦片进口和白银外流的数量》,《历史研究》,1980年第5期。
④《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上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75~176页。
⑤《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一辑,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5、9、10、26页。
⑥彭泽益:《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中国财政与经济》,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7~98页。
⑦《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上册,第298页。
⑧《大清会典事例》卷254,第6页。
⑨《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上册,第297页。
⑩《满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下册,第五辑,1963年版,第7页。
(11)《清朝文献通考》卷250,第7093页。
(12)魏源:《圣武记》下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63页。另见《清朝续文献通考》卷6,第7554页。
(13)转见《北京通史》第8卷,中国书店1994年版,第419页。
(14)《清朝续文献通考》,卷26,商务印书馆1955年版,第7769页。
(15)姚雨芗:《大清律例新增统篡集成》卷34,第2、4页。
(16)《大清会典事例》卷155。
(17)《清朝续文献通考》卷7,第7559页。
(18)《清朝续文献通考》卷7,第7560页;另见同书7775页。
(19)《清朝续文献通考》卷9,第7580页;另见《清实录》第59册,卷578,第650~651。
(20)《清朝续文献通考》卷8,第7570页。
(21)《清实录》第60册,《宣统政纪》卷8,第149~150页。
(22)《清实录》第59册,卷576,第619页。
(23)《清实录》第59册,卷576,第630页。
(24)《清实录》第59册,卷577,第639页。
(25)《清朝续文献通考》卷9,第7580页;另见《清德宗实录》卷583,第5333页。
(26)黄爵滋:《敬陈六事疏》,《黄爵滋奏疏许乃济奏议合刊》,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7页。
(27)曾国藩:《议汰兵疏》,《曾国藩全集》奏稿卷1,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22页。
(28)中国近代史资料丛书《洋务运动》第3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97页。
(29)《洋务运动》第三册,第468页。
(30)《宣统政纪》卷70,《清实录》第60册,第1296页。
(31)章伯锋、李宗一:《北洋军阀》卷2,武汉出版社1990年版,第1351页。
(32)《满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下册,第5辑,第8页。
(33)《满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下册,第5辑,第13~15页。
(34)《逊清皇室迭事》,紫禁城出版社1985年版,第13页。
(35)《清实录》第60册,《宣统政纪》卷70,第1259页。
(36)《清实录》第60册,《宣统政纪》卷70,第1296页。
标签:满族文化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八旗论文; 清代论文; 清朝论文; 历史论文; 满族论文; 贫困问题论文; 家庭论文; 八旗子弟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