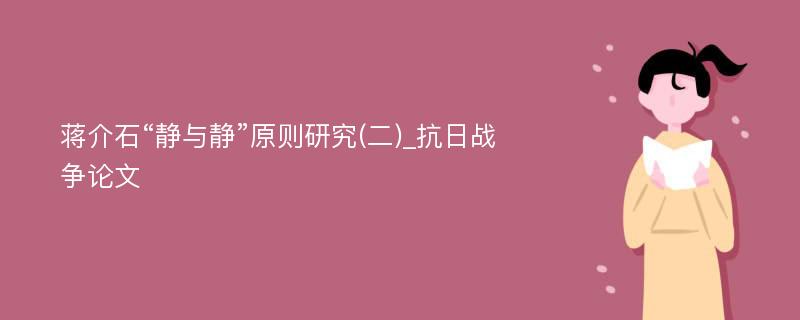
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方针研究(之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攘外必先安内论文,之二论文,蒋介石论文,方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四 “安内”的内涵
“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中,安内始终是这一政策的基本点,而攘外的可能性则取决于安内的判断。因此,安内安什么、怎样安,是“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核心问题。
30年代,蒋介石所说的安内,具体看,大致包括如下数层:首先是以武力镇压中共武装,消弭中共威胁,确立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其次是驯服党内、国内的反对派,削弱地方实力派,扩展中央统一力量,必要时不惜动用武力;再次为安定社会,充实国力,增强抵御外侮的能力。汪精卫曾将之归纳为三条:“一从政治上经济上致力统一,以形成整个的对外体系。二对于赤匪之骚扰后方,牵制兵力,予以扫除,俾无后顾之忧。三尽可能的努力谋物质上之建设,以期抗战力量之增强加大。”(注:汪精卫:《对于黄膺白先生之回忆》,《黄膺白先生故旧感忆录》,第169页。)大致说出了“安内”的基本内涵。
30年代前期“安内”的最主要内容是对付中国共产党。30年代初,蒋介石对这一点强调最多,也最直截。他多次提到:“我们要抗日,必先消灭赤匪,安定国本。”(注:蒋介石:《爱民的精义与教民的宗旨》,《庐山训练集》,第186页。)在蒋反复灌输宣传下, 这一认识在国民政府内一度有相当广泛的市场。张学良表示:“不安内,便不能攘外,要安内,必先剿灭赤匪,只有在扑灭赤匪以后,全国上下才能结成一致的对外战线,才能收复失地。”(注:张学良:《告将士书》,《张学良文集》第2册,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729页。)国民党宣传干将刘健群认为:“‘攘外必先安内’,这是事实。国内社会不安定,政治不上轨道,当然没有力量去抵抗外侮。”(注:刘健群:《热烈的欢迎与诚恳的希望》,《欢迎蒋委员长剿赤凯旋特刊》,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处1933年编印,第1页。)国民党人在中共建立苏维埃政府, 与其全面对抗背景下,以武力“剿共”为理所当然,并视之为安内的最基本工作,“安内的工作,不止一端,而剿灭赤匪,为一切安内大计的前提,也可以说是一切安内大计的预备工作”。(注:饶荣春:《鄂豫皖剿匪军事的胜利》,《欢迎蒋委员长剿赤凯旋特刊》,第9页。)
安内的另一目标是驯服各反对派,稳固中央政府统治。蒋自上台后,即设法削弱民国以来形成的地方长期割据局面,将权力收归中央,中央与地方间不同程度和规模的对立乃至战争持续不断。比较而言,“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成立后,蒋对国民党内部争端相对慎用武力。1931年拘胡事件中,当两广方面集合力量,公开宣告反蒋时,蒋即于5 月亲往探视胡氏,以示退让。6—9月,又数次发布书告,声明:“不愿国境之内,再启战祸。”(注:蒋介石:《为吁求和平告全国同胞书》,《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30卷,第152页。)九一八事变后, 更明确向粤方示好,派人携其亲笔信南下讲和, 为双方实现合作作了铺垫。 1933年察哈尔事件,蒋、汪军事与政治并举,达到威逼冯玉祥离开察哈尔同盟军,使同盟军迅速瓦解的目的。两广事变中,蒋虽也时动杀机,但主旨仍在避免使用武力(注:当时,蒋在有关电文中强调:“今日之国事,厥在巩固国本与力避内战。”“中央不但无加兵两广之意思,而且无防备两广之用心。”表示,如粤、桂不主动进犯湘、赣等省,则“亦决不令其他各省军队越入粤、桂。”(分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第3册,第48、50页。)据徐永昌记载,1935年12月他曾告蒋“中央对两广仍须当心,蒋极言两广毫无问题,并嘱余致意阎先生。”(《徐永昌日记》第3册,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91年版,第348页。)据此看来,蒋之表态当不纯为虚饰之言。),当时奔走蒋、桂间调停的刘斐回忆,蒋的真心“是要和”。(注:刘斐:《两广“六一”事变》,《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 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第26页。)周恩来致蒋介石函中也注意到:“先生解决西南事变,渐取停止内战方针,国人对此,稍具好感。”(注:《周恩来关于大敌当前亟应团结御侮致蒋介石信》,《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版,第141页。 )由于有日本压迫的民族危机,蒋虽然继续从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竭力削弱地方权力,加强中央政府的控制权,但总的看,对党内争端的态度明显和缓。其目标也具两重性,既有集中力量,统一国家的合理要求,也有寻求至上权力的私心。
考虑到攘外“最后关头”的需要,安内的最本质内容实际还应是安定社会、充实国力、培育民族精神,这是在未来民族战争中中国赖以坚持并获胜的基础。对此,国民政府也有所注意。蒋介石指出:“在今日谋国急务,非健全内政、先巩固基本地区及强固基本军队不可。”(注:[日]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9册,第21页。 )将健全内政作为安内的重要方面。1932年12月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集中国力挽救危亡案》,具体阐明了安内的这一层意思,要求尽力达到“全国人力集中,各尽其才,俾得内部相安,共御外侮,及调节中央与地方之关系,消弭一切内战”。(注:《集中国力挽救危亡案》,《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180页。)
根据中国对日防御的战略态势,四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决定将物质建设发展重心放在内地,要求“于经济中心区附近不受外国兵力威胁之区域,确定国防军事中心地”。(注:《确定今后物质建设根本方针案》,《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228页。 )五全大会又明确提出“兴实学以奠国基”、“弘教育以培民力”、“裕经济以厚民生”等“建设国家挽救国难”的十项要计(注:《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293—295页。),在财政、金融、交通、精神文化教育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安内的这一项内容既是政府责无旁贷的责任,也和民众的强烈愿望相应,基本符合对日作战的需要,显然具有积极意义。
“安内”的如上三内涵,决定了其既有维护统治、镇压反对力量的私心,也有充实国力、安定社会、准备对日抵抗的要求。客观地说,作为一个全国性政府,提出安内的主张应无可非议,在急迫的民族危机背景下,安内更是迫在眉睫的基本诉求。要成功抵御日本侵略,统一国家和充实力量的确不可或缺,这也是包括中共在内的各政治力量的共识:“统一之局,迟迟不成,内外人心,惶惑无定,以之对外,如何有力。”(注:《明耻教战》,天津《大公报》1931年10月7日。 )“要抗日就要和平,无和平不能抗日。”(注:《毛泽东选集》第1卷, 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74页。)问题的关键在于, 面对国内动荡不安的现实及日本侵略的步步深入,安内究竟应以什么为中心,并应如何实现。
其实,无论就攘外或就安内言,安定社会,充实国力都是最本质、最迫切的,蒋、汪自己承认:救亡图存“治本则莫急于生产建设”。(注:《蒋汪通电》,天津《大公报》1934年11月28日。)但是,恰恰在这一环节上,30年代前数年的安内实践未见大的成效。当时,每年用于“剿共”及内战的军费开支达全国预算总支出40%以上(注:参见孔祥熙:《敌我财政现状之比较》,《孔庸之先生演讲集》上,台北文海出版社1972年版,第186页;《十六至三五年度国库支出与物价比较》, 国民政府财政部国库署档案,一四九(184),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大量财力物力投诸“剿共”军事和其他内战中,建设经费寥寥无几,致使生产建设及国防准备均乏善可陈。造成这一局面,国民政府武力和高压的安内方式不能不负相当责任,这种“一面准备而一面自相消耗”(注:沈钧儒等:《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生活知识》第2卷第6期,1936年8月。)的安内, 使安内相对进步的一面难以真正发挥。应该说,正是在安内的方式上,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选择有着严重问题。
五 安内的方式
关于安内的方式,早在中国古代社会,即已有人提出,安内不尽为武力,“省刑罚,薄税敛,使民入孝出弟以敬其长上”(注:(明)王鹤鸣:《登坛必究》卷22,《辑夷情说》。),是更本质的安内。换言之,安内不应只是政府以武力和压制方式消弭反对力量,更应是全体合法社会政治力量间的谐调。政府可以也应该在安内中发挥重要作用,但政府行为同样也应接受安内目标的制约。从本质上说,安内是一个社会政治问题,它有赖于各社会政治力量间的共同努力。压制式的安内既鲜有实效,也难孚众望。实际上,当时国内一个重要的不安定因素,正是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执行的专制、消灭异己政策。
在《假如我是蒋介石》一文中,丁文江曾明白宣示“安内”的三条道路:立刻完成国民党内部的团结,立刻谋军事首领的合作,立刻与共产党商量休战。(注:丁文江:《假如我是蒋介石》,《独立评论》第35号,1933年1月。)这篇文章当时在全国激起很大反响, 其中心意思就是安内要求团结而不是以武力。质言之,即所谓“和内始能攘外”。(注:天津《大公报》1932年2月20日。)大多数人相信, “安内非军事进攻之功,政治之成功在于利用环境,顺应大势。”(注:章乃器:《农村破产中之安内问题》,1933年4月8日《申报》。)取消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充分发挥各党各派及全体人民的力量,才能“一扫数年来因专政而致各派倾轧,陷政府于分裂、软弱的险象”。(注:《中国青年党暨国家主义青年团为日军进攻上海告全国国民》,《民声周报》第17期,1932年2月。)相反,顽固坚持自我中心, 坚持武力统一政策,很可能“求统一而反致分裂,求救国难而反增加国家的危机”(注:胡适:《从民主与独裁的讨论里求得一个共同的政治信仰》,《独立评论》第141号,1935年3月。),形成“政府怀疑民众,民众也怀疑政府;中央不信任地方,地方也不信任中央;国民党怕被共产党利用,共产党也怕被国民党利用”(注:沈钧儒等:《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生活知识》第2卷第6期,1936年8月。)的恶性循环。 长期与中央政府同床异梦的两广方面就谈到:“两粤极愿服从中央,若能予以保障,使得居一隅之地,努力建设,不致妨碍国家之统一,至所甘愿。但所以不敢遽然表示服从者,诚恐归顺之后,委员长遇有相当机会,即行下手,毫无保障耳。”(注:《缪云台1935年7月3日致龙云函》,《历史档案》1987年第1期。)这虽不无为自己割据开脱之意, 但确也道出了安内而内不安的部分症结之所在。
安内政策的最大症结在中共问题。中共的武装反抗,代表了专制统治下被压迫者的正义力量,有强大的群众基础和充足的合理性。而国民政府在中共成立苏维埃政权,与其分庭抗礼情况下,也视军事“剿共”为理所当然。但是,在急迫的民族危机面前,如何尽力化解国内政治冲突,形成统一对外的力量,是政府及社会各政治力量均应予以认真权衡的。国民政府作为国家最高权力代表,尤其有义务、有责任将国内局面向这一方向引导。正是从团结对日的认识出发,当时许多人对武力反共政策颇感不满,强调:“‘国内问题取决于政治而不取决于武力’是‘救亡图存’的基础。”(注:吴景超:《中国的政治问题》,《独立评论》第134号,1935年1月。)要求政治解决中共问题。虽然当时中共在左倾中央领导下实行的一些无助于解决民族危机的左倾政策也使一些人深感困惑,但他们还是相信,“以民族作为出发点,无论如何利害错综,然总可以寻得一个一致点”(注:《我们要说的话》,《再生》创刊号,1932年5月。),要求政府行动起来,“立刻与共产党商量休战”。 (注:丁文江:《假如我是蒋介石》,《独立评论》第35号,1933年1 月。)中共问题的成功解决与否,是关系到国家能否真正安定,攘外有无把握的至关重要的大事。舆论的呼吁,虽不一定抓住了问题的症结,但至少提供了如下一种思路,即单纯依靠武力不可能真正解决政治问题,中共问题只能在政治的范围内寻求合理的解决途径。
舆论的强烈呼吁,日本的步步进逼,国内扰攘不宁的现实,国民政府领导人本身认识上所具有的一定弹性,特别是福建事变后国民党内部矛盾的缓和及江西“剿共”军事的初步得手,使蒋介石等对安内的方式、重心及成效的判断逐步发生变化,并于30年代中期开始较大幅度调整政策。1934年间,蒋、汪数次联合通电全国,承诺改革政治,修正政策。11月,蒋、汪联名发出感电,为准备召开的国民党四届五中全会定基调,电文指出:“今日救国之道,莫要于统一,而实现统一,端在乎和平。”强调:“国内问题,取决于政治,不取决于武力。”希望以和平统一“充实国力,树立安内攘外之根基。”同时承诺:“决不愿徒袭一党政治之虚名,强为形式上之整齐划一。”表白:“中国今日之环境与时代,实无产生意俄政治之必要与可能。”(注:《蒋汪通电》,天津《大公报》1934年11月28日。)感电虽仅为一纸电文,没有实质的约束力,但仍可谓是其自“九一八”以来对国事最为积极的一次表态,指示着国民政府总体思路的发展方向。事实上,正是在这一年,蒋介石的政策倾向开始发生明显变化。
六 政策倾向的变化
由于作为民族主义者的蒋介石和日本侵略者之间矛盾的不可调和,随着日本侵略的步步加深,以及国内形势逐渐向有利于抗日方向发展,“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重心或迟或早要转向攘外方面。通常我们认为1935年华北事变是导致这一变化的直接原因,这是从日本的压迫一面看,但从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本身走向看,1934年,这一政策倾向事实上已经开始发生重大变化。这年春夏,随着福建事变的平定及对共军事的初见成效,蒋自认安内已经取得一定成果,对日抵抗逐渐成为他认真思考的问题。
1934年2月,蒋介石在浙江发表讲演, 指出:“现在我们国家和整个民族,已经到了存亡危急的时候,我们全国的同胞……必须个个人要效法越王勾践的‘卧薪尝胆’的精神和‘生聚教训’的方法来救国,然后国家才能救转,民族才可复兴!”(注:蒋介石:《民族复兴之要道》,《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2卷,第24页。)同月,蒋指示有关军事部门立即将“东南国防计划,北至海州、徐州、归德,南至温州、漳州之计划制成”。(注:蒋介石1934年2月13日致贺耀祖电,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第3册,第298页。)3月, 他对陆军大学学员强调:“我们弱国要抵抗强国,不能靠武力而要靠我们的国民尤其是军人的精神和人格。”(注:蒋介石:《将官自强与强兵之要旨》,《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2卷,第53页。)这一系列集中表态,和此前相比,明显更多表现出对日抵抗色彩。
与此同时,蒋介石发起被他视为“救国建国与复兴民族一个最基本最有效的革命运动”(注:蒋介石:《新生活运动之要义》,《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台北中国文化大学1984年版,第810页。)的新生活运动。他指示运动的具体策划者南昌行营设计委员会:“吾人今欲使国家乘机转危为安,转弱为强,必在大战之前夕,竭力准备。予以为此种事业大概有两种,一曰明耻教战,即普遍的国民军事训练。一曰交通及基本工业之建设。”(注:蒋介石:《党政军设计之基本原则》,《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2卷,第100页。 )此中提到的攘外准备的两种事业,前者包含于新生活运动中,后者即为次年春开展的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的张本。(注:关于设计委员会有关情况,参见邓文仪《冒险犯难记》上,台北学生书局1973年版,第158—160页。)另外,1934年间,他竭力向所属官兵推荐《纪效新书》、《练兵实纪》、《洴澼百金方》等古典军事名著,尤其推重《洴澼百金方》,认为:“我们在此时能得到这部书,真好像国家民族得到了一个救星。”(注:蒋介石:《推进保安工作之要点》(二),《南昌行营召集第二次保安会议记录》,1934年6月编印,第35页。 )指示下属“用心研究妥为运用,就可以(找到)抵抗日本最新的方法。”(注:蒋介石:《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第3册,第126页。)《纪效新书》、《练兵实纪》是明代抗倭大将戚继光有关部队训练的军事著作,包含着戚继光抗倭战争中的经验总结,蒋自称“于戚氏遗书,寝馈与俱。心得之益,独深且多。”(注:蒋介石:《合印纪效新书、练兵实纪序》,《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35卷,第165页。)《洴澼百金方》是研究中国历代防御战略、战术及其得失的军事著作,为历史上有关国家防御最为全面的著作之一。(注:参见戚继光《纪效新书》、《练兵实纪》,军事委员会南昌行营编,中华书局1935年版:惠麓酒民(袁宫桂)《自卫新知》(原名《洴澼百金方》),军事委员会南昌行营1933年编印。)蒋介石反复推荐上述几本著作,反映其军事注目焦点确已有所变化。
外交方面,1934年夏,蒋介石也有重要举措。1932年12月,中苏复交,双方关系虽大为缓和,但仍十分冷淡。1934年夏、秋,杨杰、蒋廷黻相继衔蒋介石之意访苏,蒋廷黻在与苏俄副外交人民委员斯托莫亚尼科夫会谈中表示:“在一定的条件下,中国会同苏联肩并肩地抵御来犯的敌人。”(注:《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斯托莫亚尼科夫与蒋介石的非正式代表蒋廷黻教授的谈话记录》,《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莫斯科政治文献出版社1971年版,第644页。)蒋廷黻访苏,打开了中、 苏两国的和解之门,两国关系在对抗日本扩张的共同目标下,迅速有了改善。当时苏方明确表示:“蒋介石的军队同中国红军间不实现统一战线,对日本的侵略进行严重斗争将是不可能的。”(注:《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第646页。)而中、苏关系的改善, 使苏方意见受到蒋介石的重视,这就为其此后寻求与中共接触打下了基础。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攘外必先安内”的提法也逐渐为“安内攘外”代替。7月, 蒋提出:“可以拿我近来所提出的一个口号,作为全国国民和军人共同努力的目标,就是‘安内攘外’四个字,意思就是安内为攘外的唯一前提与必要的准备工作……只要国内真能统一安定,集中力量,攘外就有绝对的把握。”(注:蒋介石:《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第3册,第142页。)“安内攘外”,曾和“攘外必先安内”并同使用, 蒋在此特别强调“安内攘外”,应是有所用心的。“攘外必先安内”强调安内,安内可以攘外,但并不必然指向攘外;而“安内攘外”则将安内与攘外并列,坚持安内,又肯定攘外。两者虽仅是字面变化,倾向性的变化却已露征兆。事实上1934年开始,蒋对“攘外必先安内”已很少使用(注:即使提到也多从安定社会、充实国力积极一面来谈。如第二次庐山训练期间就谈到:“我们要救国,就要攘外,要攘外就先要安内,先要使整个国家能够彻底做到和平、安定、统一、集中。”(蒋介石:《本团学员应有之心得》,《庐山训练集》,第275页。),1935年后, 即基本不再出现。其所反映的思路变化,从两次庐山训练中,更可明显看出。
1933年第一次庐山训练,蒋的注目焦点明显指向中国共产党,虽然他也提到,不能驱逐外寇,收回失地,保护国家的领土主权,是中国军人的“奇耻大辱”,“一定要刻骨铭心的记住”(注:蒋介石:《现代军人须知》,《庐山训练集》,第46页。),但他谈论的政治、军事方针,当时主要是针对中共武装的,“一切的设施,皆要以赤匪为对象”。(注:蒋介石:《军官训练团训练的要旨和训练的方法》,同上书,第18页。)而1934年7月开始的第二次庐山训练,蒋已很少提及中共, 主要是进行民族精神的灌输及对外战争的战略战术教育。他手订的训练任务是:“唤醒中华民国之国魂,继承中华民族之道统……训练官兵,统御所部,奠定我军人救国保种千古不磨之事业。”(注:《蒋委员长手订庐山军官团团员首要之任务》,《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第3册,第105—106页。)这期间, 他先后发表数十篇讲演,详细分析了国际国内局势和中日两国的力量对比,提出御侮图存的几个要诀,要求充分发挥民族精神的力量,与敌人作精神与物质的总体战。同时,要求时时刻刻准备与敌作战,强调:“我们对外作战……从此时此地起,随时随地要战胜敌人,无时无地不是在和敌人作战。”(注:蒋介石:《民族战争取胜的要诀》,《庐山训练集》,第444页。 )
从第二次庐山训练内容看,蒋对未来反侵略战争确已作了认真思考,关于御侮图存几要诀的基本思路在后来抗战具体实施中都有体现,当时提出的强迫敌人近距离作战的设想和淞沪战役的发动就不无关系。同时,其对所部的要求也明显向准备抗日方向转移。8月, 他在庐山与徐永昌谈话时说到:“我们现在讲不到整个国防,须就现地现时随时储粮做工,准备与敌各个抵抗,最小限能做到敌人十分之一的力量。”(注:《徐永昌日记》第3册,第149页。)同时他更曾告诫部下:“中国生死存亡的关头”,已经“临到我们的头上”,“可供我们准备的期间,恐怕最多也只有三年,因此国家民族的兴亡,就完全看我们一般军人,尤其是本团的学员,在这三年内的努力如何。”(注:蒋介石:《军事教育的基础》,《庐山训练集》,第388页。)1936年1月,中国驻苏使馆武官邓文仪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会谈时也强调,庐山训练表面针对中共,实际则针对着日本侵略。(注:潘汉年:《关于与国民党谈判情况给毛泽东等的报告》(1936年11月12日),《党的文献》1993年第5期。)
可以看出,“攘外必先安内”向与其相对应的“安内攘外”转移,1934年前后是一个关键点。“安内攘外”和“攘外必先安内”虽没有绝对的区别,两者间有相当的继承性,但其政策重心的变化还是十分明显的。安内的内涵仍为三点,但重点转向建设;安内的方法向包容性方向有所发展;安内攘外重心则明显向攘外准备方向转移。另外,安内攘外顺序的判断也不再机械地论定先后。正如他在国民党五大上所总结的,民族运动:“对外应向国际为吾民族求独立平等,对内应向民族为吾国家求自立自强。”两个方面“必须同时平衡进展,方有成功之望”。(注:蒋介石:《对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演讲对外方针》,《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第3册,第657页。)从这一意义说,蒋介石后来实施的收束“攘外必先安内”、明确最后关头具体领土界限、与中共谋求接触等措施,实际在1934年都已埋下了伏笔。
七 余论
蒋介石在1934年间开始酝酿重大的政策变化,和其对政策的把握和理解,和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密不可分。“攘外必先安内”的基本判断是安内而后攘外,政策本身也表现出高度的包容性,因此,随着国内形势的好转,政策趋向的变化也实属顺理成章。1935年后,国民政府的攘外准备更大规模地在全国展开,攘外最后关头的具体限度逐渐明确为华北的保全,安内的重心也明显向国家建设的方向转移,这种重心的转变直接促成了1936年中国经济成为20世纪前半段的经济标杆。安内攘外的如上表现,虽然由于“攘外必先安内”所具有的弹性,仍在政策范围之中,但和蒋30年代初强调的“攘外必先安内”内容确实已有相当距离。实质上,抗战前两年,国内各政治力量间的冲突已更多地围绕着如何攘外即抗战路线问题进行,西安事变某种程度上即可看作为不同抗战观念冲突激化的结果。
当然,蒋介石这时加紧攘外准备,并不意味着其已决心对日全面作战,也不排除其继续谋求与日妥协。如他自己所说,中国是弱国、穷国,处于被侵略的地位,中国的任务是尽力避免和推延与强大的日本之间的战争,因此,中日关系的主动权“全在乎日本之本身”(注:《蒋昨日与记者谈话》,天津《大公报》1934年11月28日。),中国的因应终究须以日本的动向为依归。(注:参见《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外交评论》第3卷第11、12期合刊,1934年12月。 )蒋最终走上全面抗战之路,首先是由于日本的步步进逼所致;同时又受到国共关系及国际形势的变化、国内建设的逐步发展、抵御外侮能力的渐渐加强以及日益高涨的抗日热潮等诸多因素的综合影响;而其个人的思想基础和认识发展也和历史大趋势达成了相当的契合。确实,从起初实际是难寻底线的退却,到逐渐以保全华北作为最后抵抗线,到最终奋起抗战;从“攘外必先安内”到“安内攘外”,再到1936年前后的“团结御侮”,蒋介石走过了在他看来是符合历史逻辑不得不走的漫长道路,中国近代历史也经历了极为沉重而痛苦的一段。
附记: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黄春生等许多师友的大力帮助,杨奎松先生督责、鼓励、指导尤多,铭此谨致衷心谢意。
标签:抗日战争论文; 攘外必先安内论文; 蒋介石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历史论文; 日本中国论文; 日本军事论文; 日本政治论文; 大公报论文; 军事研究论文; 国民政府论文; 世界大战论文; 太平洋战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