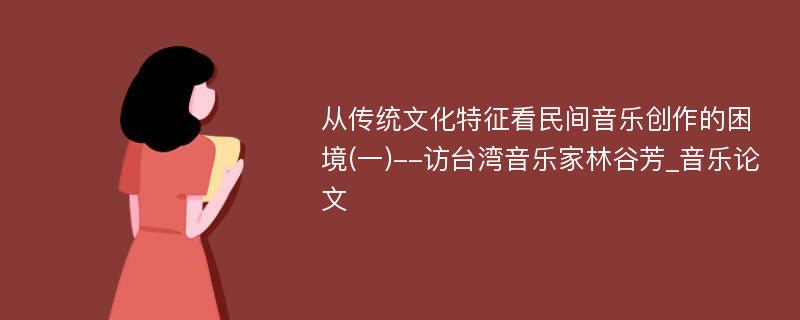
从传统文化的特质看民乐创作之困境(上)——访台湾音乐家林谷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台湾论文,民乐论文,音乐家论文,传统文化论文,特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5年5月17日和21日,我在北京访问了台湾音乐评论家、琵琶演奏家林谷芳先生,请他就民族器乐的创作和乐队发展等问题发表意见。
于:这些年,国外许多音乐家都把目光投向东方,投向中国,中国当代民族器乐的发展也引起了世人的瞩目。但在一些创作问题及与此相关的乐队编制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看法。您认为,当前民族器乐在创作上存在哪些问题?
林:民族器乐的创作及乐队发展问题是一个文化问题,文化问题说到底是个观念问题,这里的人常说是“指导思想”问题。不过“指导”是指自上而下的权威,我不喜欢用。我用“观念”、“观点”,即我们做事都有一个立足点,它决定了我们做事的方向。现在海峡两岸有许多人已经在考虑现代技法如何与中国文化的特征结合这样一个层面的问题了,但常常也还笼罩在一元化的思路中。例如许多人常用音乐的复杂性来分出它的“进化”位阶(即位置、阶段),这是大陆民乐发展的一个很大的障碍。台湾的创作不如大陆,他们也没有什么指导思想,只是迷迷糊糊地干。我们对文化理论的看法是,所谓文化的行为模式(当然指音乐的行为)实际是一个民族面对它的自然和人文环境这样一个综合体所寻求的解决之道。不同的环境有不同的解决之道,相同的环境也可以产生不同的解决之道,从而构成一个文化的有机体。而从解决生命的角度来看,不能解决生命问题的文化设计就会被淘汰,它是因时因地而宜的,所以我们在文化之间并不能完全做横向的对比,很难说某个国家的文化就比另一个国家的文化要好,你只能把它放在它所处的背景中,看它所解决的社会功能和生命功能如何。而人类的文化是否沿着一条单线的轨迹在前进呢?有一种人类学理论产生于19世纪是如此看法的,很多人都读过摩尔根的书,他的论点属于这种人类学理论,他以为人类的历史经历了一个从乱婚、群婚到一妻多夫、一夫多妻,再到一夫一妻的历史,音乐上也是这样,认为最早的是单旋律,后来是和声,再后来是复旋律。然而,人类学从对田野资料的研究出发,认为事情的发展并不一定是如此,文化演化是存在着多元的可能性的。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论证可以说明,单线进化论的看法是太简单了,以音乐而言,有的民族好像生来就是“和声的耳朵”,当然,我不是说他的生理结构与我们不一样,而他从小就习惯听和声,和声无非是一个基音与泛音的结合,他的生活习惯使他养成了这样的听觉,对他而言并非是先有旋律再有和声,而是旋律与和声同时出现,甚至和声比旋律更重要。台湾的布依族人就很少是一个人唱歌的,而当两个人唱歌时很自然地就会用和声关系对置起来。他们唱歌的旋律音也常常是在三和弦的和弦音上来回跳动。
然而,大陆的许多人欠缺这样的观念,因此,尽管他们试图为民乐摆脱困境寻求一条出路,但在思索的同时就已经陷入了某种盲点之中。毕竟,当我们有了一种单线进化的思想时,我们就会把不同文化做一种位阶上的比较,就会把所谓强势文化摆在我们的位阶之上,就会认为只要向他学习就够了。我们今天对待欧美的文化就是这样,认为他们的文化超过了我们的阶段。但是许多人却很少考虑,他们的文化为什么是这样发展的,又体现了他们怎样的价值观?我常常问别人:“什么叫和谐?”你认为是和谐的,在别的民族也许就不存在同样的观念。在古典音乐里,为什么你觉得大三和弦是和谐的?当然这里有它的生理基础,但问题不仅仅止于如此。同样,为什么交响乐一般是四个乐章,而不是三个或五个乐章?这里面有它的背景。以中国音乐来说,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告诉我们,先秦时期我国就已经使用十二律,有复杂的转调系统了,可我国音乐很多时候使用的却仍是五声音阶。这很难从音乐学里找到答案,但我们可以从一些附会中想到它的哲学背景,比如天、地、君、亲、师,仁、义、礼、智、信,金、木、水、火、土,心、肝、脾、肺、肾,宫、商、角、徵、羽。这些表面看来像似一种无聊的附会游戏,但它却呈现了中国人对宇宙、对生命、对各种现象的一种分类,如同我国古代的“八音”,尽管它不符合现代某些物理学的分类,但却体现了我国古代对乐器音色的重视。其实,自然科学也都还有它的主观性,澳洲物理学家海森堡提出了“测不准原理”,他否定了爱因斯坦关于一切东西都可以测定的理论。他写了《物理学家的宇宙观》一书,在其中强调,一个好的物理学家就是一个艺术家,他不是就实际看到的世界来做叙述,而是在虚拟的世界里发挥他的想象力。在他的物理学里已经含有很多主观的、文化范畴的因素,更何况音乐又是那么主观的东西呢!然而我们的音乐家却很少如此思索,很少问西方音乐的美是不是我们唯一的目标?或者至少思索一下,人家定那样的目标,它的背后要成就一个什么样的生命功能?没有生命就没有音乐,生命是音乐的原点。就像古典乐派在乐章的最后都要以一个稳定的三和弦给你一个结束感。为什么?你如果了解基督教的思想,你就会知道,这与它有始有终的宇宙观,与西方纯粹形式的美学思想都有关系。如果我们所追求的生命色彩和文化与西方有所不同,那么他们的音乐形式为什么必定是我们要去追求的目标呢?在这方面,如果我们的思想不解放,在创作上就会绊住自己的手脚。
我们不仅要打破“欧洲中心论”,还要舍弃“单线进化论”的文化观。“单线进化论”是19世纪产生的人类学理论。但这种人类学理论后来不适用了,因为人类的发展实际上要复杂得多。可惜大陆音乐界却还普遍持有这种“单线进化论”的观点。如果从这种观点出发来看我们中国音乐的特征,它的特征就反而变成了它的缺点。例如,人类在用声音表达情感的文化行为里,声调的变化是很重要的,它是人与人之间交流情感的重要手段。可是我们发现,在西方古典音乐里,这种滑音、弹性音几乎是不存在的。这似乎不合乎人类以自然的声音表达情感的方式,但它代表了一种特殊的美学观。如果你了解柏拉图的美学观,你就会知道它为什么会逐渐走上了这样的一条路。因为西方的哲学后来分成了本体和现象的两面,本体是不变的,因此有人希望在音乐里看到本体的结构的美、纯粹形式的美。这在巴赫的音乐里看得很清楚。也因此巴赫的音乐其实是西方的,有人说巴赫的音乐是宇宙的,这指的是他的几何倾向,但是不是大家都认为美,是不是符合几何的就叫美,我看并不尽然,毕竟,一个音乐系统都是合着它的需要在发展的。而如果当我们把别的任何一个音乐系统毫无反省性地看成是我们的学习对象,那么我们就会把自己脚下的东西都看成是缺陷。例如二胡,有人认为它的缺点是没有指板,手指力度不好掌握,音准就难以控制。但我们听听二胡曲《江河水》,它的哭腔表现得那样淋漓尽致,你还能说没有指板是它的缺点吗?我们听小提琴的《梁祝》时,总感到在表现哭腔时还差那么“临门一脚”,这就是受到小提琴本身结构的限制。我不是说小提琴不好,小提琴是按照一定的需要在一个历史过程中逐渐发展、形成的,二胡也是这样。我们应该从这样一个有机的观点看问题,并把它作为解决问题的起点。我并不是不要看别人的优点,我们要像佛教所主张的那样,要看到自家立宗之本。我们的乐器为什么会发展成这个样子?为什么我们有这样的音乐思维?这其中都有我们的宇宙观和生命观。找到了根本,我们才能找到与之相对应的文化发展的点。
一个文化总是要发展的,但谈发展就必须谈到文化中可变与不可变的两个部分。不变的部分是我们有别于其他民族文化的特征,如果变了,就使我们与其他民族文化上的区别消失了;当然,文化还存在着可变部分,因为人类面对生存环境的改变,必须会相应产生一些行为模式的改变。西方音乐对于近代中国当然是一个带有冲击力的因子。但这因子并不意味我们一定要学习它,因为历史中的成败牵涉到太多的必然和偶然的因素,何况音乐文化同时还和一个国家的实力、经济发展等等因素有关。例如现代化传媒手段的高速发展,就必然给西方音乐的传播带来有利的影响。我们到底要不要学西方,若要,学些什么,谈这个问题首先得打破“欧洲中心论”和“单线进化论”这两个迷思,而要打破这些迷思,就必须去探讨一下,音乐与我们的生命、文化发展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但大陆民乐界却很少有人去探讨这个问题。不客气地说,大陆民乐界在谈到民乐的前途时总充斥着太多的狭隘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是一种可贵的情操,但过了头就变成了保守的象征。对于我们创造的文化充满感情,那是必然的,但在考虑发展时,就不能仅仅如此。例如,现在老年人很喜欢民乐,而一些年轻人就不那么喜欢民乐,但你不能因此说他不真诚,因为他总要面对他的生存环境,所以就不能仅仅从民族主义角度看问题,还应该有机地看到,中国人的宇宙观和生命观能够成就怎样的生命情怀和色彩,这样的生命观在现在的社会里有没有价值?如果能这样,一方面我们可以不致因被忽视的感伤,而诉诸一种保守的民族主义,另方面也不致在这表象的民族主义之后,又以西方为尊,以为能像西方就可以扬眉吐气了。
谈到中国音乐里的宇宙观生命观,在这里可以举个例子,例如:我们可以在中国音乐里看到充满自然哲学思想的种种表现,而我们若要考虑中国音乐对中国人生命的意义,对现代的意义,有了这种层次,它的价值其实就会凸现出来。譬如古琴音乐,那么慢,好像很落后了,但以后是不是就不需要了?当大陆进入工商社会时,每天工作十分紧张,你回到家里如果还听“重金属”音乐,那不是精神要崩溃了?你总要寻求一个往内思索的生命空间,这时古琴音乐就有价值了。再如古琴的音量不大,有人认为这是落后的表现,但我们怎能相信一个在两千四百多年前能够制造出那样辉煌、精密的编钟的民族却不能解决一件古琴的音量问题呢!古琴音量的设计自有它的道理,有它的美学含义,以一种内省角度而言,它是个了不得的“设计”,对现代人尤其有启示作用。而如果我们能如此认识到了中国音乐对于成就我们生命功能的意义,我们就会觉得中国音乐不可变的部分在哪里。这些功能又必须借助一家的音乐表现手法,这些手法与思想情感又是怎样的关系?这种种问题清楚了,才能探讨创作和发展的问题。
目前在乐队里,我们所用的是西方的功能和声体系,高音区因此是旋律的主体,也就是在乐队里小提琴是最重要的。但是,照搬到民乐队里,柳琴就会变得比琵琶重要,但它真能够比琵琶重要吗?柳琴的技巧比较少,音色虽然明亮,但它的尖锐度并不适合中国人的美学观念。你要觉得为什么中国人的乐器主要都在中音区?为什么乐器的主要材料是梧桐?梧桐就是中音区发声的好材料。西方的乐器用的是硬木薄板,共鸣箱所占的比例较大,便于声音扩散,如果从西方的音响角度看,琵琶当然不是一件太好的乐器,因为它音色虽然厚,却不够明亮,共鸣箱不大,音量也不大,共鸣壁也很厚,共鸣孔更小,一把琵琶的材料因此可以做四把吉他,但这是它的美学特征,这恰恰与中国的中庸哲学,与艺术不注重外在的扩散而注重内在的情感表现有关。这不是一个纯音响学的问题,而是个美学选择的问题。如果从西方的观点看,琵琶是不良乐器,但我们却认为它非常优秀,它可以奏出我们所要的音色,表现出我们所要的感情,它是胡乐汉化的典型乐器,是历史上唯一可以和古琴抗衡的乐器,但如果照搬西方的做法,柳琴一出来就盖过了琵琶,这是纵向和声结构产生的结果,因此不能盲目地学习西方。
有没有解决的办法呢?日本的雅乐是我国唐代传过去的,它的高音乐器是笙,中音乐器是筚篥,它的主旋律在中音区,并没有被高音乐器“吃掉”,为什么?这是音色搭配的结果,中音区成了音乐的主体,高音区只是色彩性的力量。这比较合乎中国人的美学观念。可是我们这里一些人的做法却不是这样,他们常常把色彩性的乐器削掉,怕它破坏美感,破坏和谐。我认为中国人从来就没有西方人那种单一的和谐观念。中国人强调的是“相生”,即阴阳相生、虚实相生、浓淡相生,只有不同它才存在,而不是相同它才存在。在这里我可能是海峡两岸第一个将这个观念放到本质地位来讨论的人。这也正是我们民乐界需要认真反省的重要问题。当我们把民族乐器音色的分离性当成是它的特色,而不是当成它的障碍时,我们的民乐就会走出一条路来。我们的一些作曲家在为民乐队写作时,尽管也想发挥弹拨乐的作用,但由于习惯写西洋管弦乐队,弹拨乐常常成了他们的障碍,但又无法去掉。如果换个角度看,弹拨乐也恰恰是我们的特点,这个特点还不仅是色彩性的特点,有时还表现出本质性的特长。西方交响乐是很少使用弹拨乐器的,而东方呢,中国的古琴、琵琶,印度的西塔尔和维拉琴,韩国的伽耶琴,日本的琵琶、筝,这些弹拨乐器在东方音乐中都是主要乐器。在这里绝对体现了东方人与西方人不同的美学原则。印度到了本世纪七十年代大学里才有了钢琴课,在他们眼里,钢琴是件蹩脚的乐器。梅纽因和拉维·香卡合作演出,你会看到梅纽因跟得很苦,因为拉维·香卡的演奏太自由了。印度的吹管乐器也是很有特色的,西方人很难掌握。你现在到旧金山、洛杉矶或巴黎等地,凡是像样的唱片行,有两种唱片不会不存在,一是印度音乐,一是日本音乐,反而不是中国音乐。为什么呢?因为你的音乐与西方的相比其实已没有多大差别了,他为什么要你的东西呢?
我们要将表现手法、美学特征和生命情感这三者贯穿起来,成为一个有机的文化系统,由此再来考虑哪些在今天不适用了?哪些要继承、要发展?前几年大陆有的作曲家来找我,表示民乐的创作搞不下去了。我就对他指出,应该在理论和观念上认真进行反省,才能在实践中有所作为。我上面谈的这些问题,大陆民乐界很少讨论,你的观念有问题,创作就搞不下去。你要让二胡去模仿小提琴,干脆去拉小提琴。从西方和声观点看琵琶,它绝对是不良乐器,演奏和声不如吉他,它是“大珠小珠落玉盘”,但一遇到和声就打架。可是一曲《阳春》,哪样乐器能比得了琵琶?所以,首先是观念问题,作曲家要打开心扉,与传统产生对应,与现实产生对应,从文化的、美学的角度进行反省。
于:您认为所谓“单线进化论”在音乐创作上的表现有哪些?
林:“单线进化论”认为,人类社会及其观念的发展是有它一定的进程、一定的路线的,或者说有它一站又一站必然的发展阶段的。这种观点在外面的世界是不被承认的。已经有太多的资料证明,世界的发展不是这样的。在音乐上,假如我们认为和声是晚于旋律出现的,那么旋律加上了和声,我们就会认为这是一种进步。这就是“单线进化论”的思维方式。其实不一定。我们发现有的民族从来就没有出现西方式的和声,但他们的音乐十分复杂,非常丰富。在我们这里,有许多人认为,西方的音乐发展得比我们全面,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在印度则不然,他们认为你的物质文化发展超过了我,但在精神文明上你远远不如我。这在世界上是可能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明的发展并不是平衡的,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都有这种情况。我们常常看到一些物质上十分富有的人在精神文化上是十分贫乏的,他太幸福了,他的思想反而不那么深刻。再如对于“和谐”的观念也一样,认为音乐的发展是越来越和谐,这也是“单线进化论”的思想。还有,把音乐较绝对地分成“乐音”和“噪音”,也是类似的一种表现。其实在现代音乐中,这种观念已经被打破了。台湾的一些现代音乐家听了一些传统音乐后十分惊讶,他们觉得传统音乐里有些十分现代,比西方古典音乐还现代。在传统音乐里,是“无声不可入乐”,而在西方古典音乐里却是有明确唯一的乐音标准的。
于:您认为的这些错误观念在具体作品中有哪些表现?
林:现在手上没有谱子,很难结合具体作品谈。有人在引入西方的和声写作时,往往只注意纵向的结合,而很少做横向式的发展。在民乐界,欠缺这方面能力的人是很多的,常常就是简单配上do、mi、sol或re、fa、la而已。西方音乐中的一个和弦往往就是一个动机,而我们中国音乐旋律发展的思维与西方是不同的,如果简单配上一个三和弦,就会模糊了旋律的特性。我们的旋律中有许多细微的装饰或滑音,是感情的细微变化,但常常为了和声或演奏整齐的需要,而模糊了这些旋律的特性,使它失去了韵味。在配器上也是,作曲家习惯了西方的配器,总是希望色彩性越统一越好,而害怕用分离性的色彩。在曲式上,一些人太爱用西方的曲式。曲式实际上是人对生命、对宇宙的一种认知。我们中国人是有自己的曲式观念的。一种文化行为千百年来一直在反复,一定有它的理论,否则是不可思议的,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去研究它,解读它。同时,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理论放到更深远的背景中去考虑。我在《从传统音乐的特质看国乐交响化的美学困境》的文章中指出,中国‘传统音乐的一些主要表现手法,在这种模拟西方的乐队里遇到了障碍,中国音乐的特质消失了,剩下的就只有一个干瘪的旋律了。例如音色,我们中国音乐的音色是最丰富的,而且音色被认为是音乐的主导性力量,有时它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但现在它被同质化了,音色单一化了。这两天我听的比赛,那么多丰富的音色到哪里去了?音色被单一化了。最为明显的是音色都趋向西方的明亮化。现在还有人懂得用低调门二胡演奏阿炳的《二泉映月》,早晚有一天连这点也要丢掉,好像越高亢越好。还有“韵”的问题,即滑音和弹性音的问题。西方音乐不必考虑这个问题,但我们必须解决这个问题。这是个很头疼的问题,整齐度和即兴性的问题,不要以为有了指挥这个问题就都解决了。还有演奏技法的问题,两个琵琶在一起轮指,严格讲是不一样的,这是特点还是缺点?这要看你是怎样的思维。我看过日本音乐集团在台湾的演出,很受感动。他们用的全部是传统乐器,奏出来是现代音乐。他们也能演奏传统音乐,他们没有西方的音乐思维。如果从西方音乐的和声思维来看,他们的乐器是很烂的乐器,但从独立性的角度来看,每一件的音色都很有特点。作曲家就是利用了这些音色的相生、对比,使八个人的乐队奏出的音乐非常迷人,他们的每一个小动作我们都听得非常清楚。而在我们的乐队中,二胡常常被作为主力,这就是西方的思维。我们觉得它富有悠长的旋律,最容易产生和谐。其实从物理学共鸣的原理来看,它怎样也没有小提琴和谐。可是我们的弹拨乐器到哪里去了?还有竹笛,它的笛膜振动所产生的音色,恰恰是我们的特点,甚至是优异所在。我们只有澄清了这些观念,才能讨论创作问题。
于:现在民乐界的创作队伍大体有三种情况,演奏家业余兼搞创作,演奏家出身的专业作曲家和主要从事西洋管弦乐队创作的作曲家兼搞民乐创作。前两种人常常不大注意您刚才所谈的那些问题,有的人认为自己是搞民乐的,从不“崇洋媚外”,似乎创作中的民族性、民族风格的问题已不在话下了。
林:民族性的问题要从两方面来看,你如果没有反省性地强调民族性,它就是你的习惯性的行为而已;你如果没有反省性地否定民族性,那你其实也就没有触到音乐存在的真相。从某种意义上说,贝多芬的音乐也是民族音乐。你没有西方的美学思维,你就不能欣赏贝多芬。有些学西乐的人讲:“贝多芬的音乐是世界音乐。”这些人应该好好去谈人类学。比如说,管弦乐队的90分贝的音响,澳洲土人怎么会接受得了?准会把他吓昏了,哪里还会欣赏到什么美?因为他们的生活中除了雷声之外,就没有那么大的声音。美与生活环境、思维方式是有关系的。我们有些搞民族音乐学的人常说“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不要离开“民族”去追求“世界”。
于:您对这一论点是怎么看的?
林:现在的文化理论基本是这样看的,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当然“民族”不是静态的,是不断发展的。没有离开民族音乐的世界音乐,如同没有一种语言是世界语言,没有一种绘画是世界绘画一样。所有的绘画都有它的文化背景。为什么音乐没有它的文化背景?联合国以前有“世界语”,现在大家都不用了,因为它反映不出应有的深刻度来。音乐是民族的音乐,只是要看它是哪个民族的音乐。
于:现在流行一种时髦的说法,即所谓“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与您刚才的说法有一定的联系。这一论点是否有些偏颇?
林:“越是民族的就越有世界性”,这种观点具有相对性,他们是想要强调民族性,你有自己的特质就不容易被别人吃掉。当然越是民族的就越有封闭性,这也是相对的。我们应该既要站稳自己的立脚点,同时又不要有封闭性,以此找到我们的定位。
于:问题在于,有些虽然是民族的,但却是封闭的、落后的、愚昧的,说这些具有“世界性”,是否恰当?
林:我们强调民族性,首先是认为人类这个物种虽有共同的体质基础,但文化正是针对特定环境的产物,没有这特定产物,反而看不出这共同体质的作用,也就是说,文化是以其殊异性来彰显人的共同性的,而艺术更是如此,它是在特定事物“聚焦”的作为,由此特定聚焦,我们反而可以触及人类所共同的一些情怀,也就是因为这种普同性与殊异性的有机关系,我一方面会强调民族性,但也承认人类彼此沟通的可能性。
其次,强调民族性在这资讯社会中,有它特殊的意义,资讯的大量交换,使人类的文化趋向同质化,这对文明的发展或个人的生命并不利,因此提供多元的价值选择是我们强调民族性的另一个原因。当然,前面我们提过,封闭与开放间如何有机对话是坚持特质与兼得发展的重要关键。
要有多元选择,我们的民乐创作中,就带有太多的中国文化大一统思想,即总认为应该有一条明确的路,有一个较好的适合中国的形式。其实,“中国”这一概念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它是由不同的层次融合、积累起来的,但我们却常常把它当成单一的概念,于是我们就会发现,北京的民乐团的思维和台北国乐团的思维是一样的。我认为在文化的发展上不应该有这样的想法。
中国音乐有两个层次很重要,即民间音乐和文人音乐。民间音乐是由不同地区的与他们生活紧密相关的音乐所构成。文人音乐是在民间音乐基础上形成的,但那些文人则没有那么强烈的时空色彩,他们趋向一种抽象性的思维。中国音乐要发展,这两个层面都要照顾到。舍弃民间音乐不成,仅有民间音乐也不成,那你就看不到中国音乐博大精深之处。比如,如果我问你苏东坡是什么人,你不会首先回答他是四川人,而是回答他是南宋词人,因为四川人这点对于他不是最重要的。不过我们一些从事民乐的人,目前又太重视这个抽象性、概括性的一面,总要找出一个代表整个中国的形式。没有地方性的基础,哪里来的代表整个中国的?有了地方性的基础,才能抽绎出很难分清是哪个地方的但又有中国特质的音乐来。我们两岸的民乐创作往往盲目追求这种做法,却忘了离开了地方性的基础,你所追求的中国风格从哪里来?中国这样大,还是要从各个地方的特色入手,充分发挥地方的特色,在此基础上才能构成中国的特质。现在中央音乐学院和中国音乐学院的学生太缺少这方面的基础。大陆和台湾的民族乐队形式也是一模一样。
〔未完待续〕
标签:音乐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文化论文; 大陆文化论文; 艺术论文; 西方美学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和声论文; 民族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