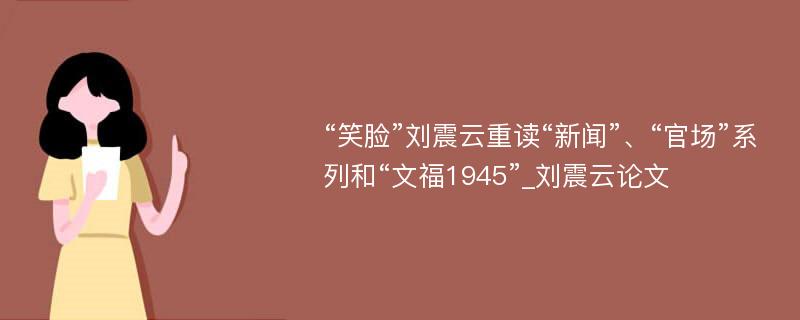
“喜剧面孔”刘震云——重读《新闻》、“官场”系列和《温故一九四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官场论文,面孔论文,喜剧论文,一九论文,系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730(2014)02-0001-06 看生活中刘震云本人的面相,似不苟言笑,一副苦大仇深的模样;观刘震云的小说面孔,冷嘲热讽,嬉笑怒骂,喜剧效果十足——笑:同情之笑,戏弄之笑,讥刺之笑,急智之笑,会心之笑,疼痛之笑,言此意彼之笑——寓庄于谐,此可名之为“刘式幽默”、“喜剧面孔”。刘震云的“喜剧面孔”,走路时身段很低,对目的地的希冀甚高,他似在追求以达刘勰《文心雕龙》中提出的“谐词隐言”(《谐隐》)[1],他似在追求以达李渔《闲情偶寄》中提出的“于嬉笑诙谐之处包含绝大文章”(《科诨》)[2]。 当今的作家评论和多种版本的文学史均将刘震云归于“新写实”作家,这自然有一定道理。他与“新写实”们的“同”,主要体现在“叙事对象”的选择上——以小人物生存困窘和烦恼为图景。他的“草根情结”从来不曾消弭,乃至那“一地鸡毛”,竟成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文学的关键词之一,成为文学疏离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化符号。然而,我们切不可因为表象,便将他草草包裹在“新写实”的“豆荚”之中,看不见他与其他“豆”们的差异。我们更加有必要关注刘震云与“新写实”们的“异”:他以“一地鸡毛”拉近了与现实社会的距离,又以“喜剧面孔”特立独行地完成着有历史责任感的知识分子的社会批判使命,他不屑“情感零度”,他难以“终止判断”,他以“喜剧面孔”揭示、讥刺种种社会历史现象的无价值,譬如:对堕入庸常的麻木,对名实相悖的惯常秩序、法则的依从,对历史可怕的周而复始的熟视无睹等等。与此同时,他的“喜剧面孔”又有着对于情感、倾向性表达的极强控制力。于是,“面孔”与思维指向,表情与价值立场之间,就常常耐人寻味。直面悲剧,或许,正是他的喜剧式的绝望和毁灭,更能给麻木的社会躯体以举重若轻般的掌击,从而摇醒昏睡的人群。倘若一定要将刘震云挽留于“新写实”的队伍之中,那么,他便是“喜剧面孔”的“新写实”和“新写实”中的“喜剧面孔”。 一、“谐词隐言”的《新闻》 《新闻》写刘震云所熟悉的生活,熟悉的同行:一群媒体人的一次新闻采访。此等采访是京城众媒体组团“走穴”到基层,也是地方政府制造宣传效应的大动作,是大事非小情,是工作非儿戏,是正经非闹腾,可刘震云却一步一步消解了正经大事的“神圣”。他首先消解了媒体和媒体人的神圣:报纸各以“甲乙丙丁戊壬癸”名之,记者各以“大头、大嘴、糖果、瘦瓜、小粉面、尤素夫、鱼翅、寸板、大电、二电”等不甚恭敬的绰号名之。《新闻》从令人忍俊不禁又无话可说的“男女之间”——集合地点设在火车站“男女厕所之间”——开始了。小说一一历数这临时组团的团长和团员们那些搬不上台面的公干私情,吃喝拉撒,表里不一,名实不符,由此引出另一类更加搬不上台面的地方政府接待风波,报道对象易主风波。小说情节于嬉笑之间接近了事件的关节点:由报道、宣传市长主抓的“芝麻变西瓜”工程到报道、宣传书记主抓的“毛驴变马”工程。“工程”一词具有戏言成分,更具奇异的联想功能;“芝麻变西瓜”,“毛驴变马”之“变”亦具奇异的联想功能——焉知还有哪些“西瓜”和“马”不是种出来和养出来,而是“新闻”“变”出来的呢?然而,作品指涉的深刻性并没有到此终结,文本的前台是“新闻”的报道者与报道方式,报道对象的一波三折,文本的后台则是左右该事件的官场风云,官场规则和潜规则里的明道暗渠、明争暗斗、利益纠葛、复杂关系等等。小说中,新闻与新闻人的物欲横流和红包;新闻与官员的政绩和升迁;新闻与官场的跟人站队,投奔倒戈,政策多变,虚实莫辨;新闻与真话、假话、官话和民间私话……刘震云以“言非若是”,“说是若非”于倒错之中的笔法,“谐词隐言”的曲笔勾勒浮生百态,表达了小说家的价值判断、价值取向。小说结尾颇有意味:众记者大功告成,返京聚会,实习小记者不胜酒力,酒后吐露心曲,“失望”竟是核心词语。众人开导:“噢,你是怪我们把你带坏了?污染你了?原来把我们想得很神圣,现在不神圣了是吧?告诉你,神圣就是不神圣,不神圣就是神圣,这是生活的辩证法!”[3]那位开篇伊始便一副嘻哈之相的团长大头,不禁也会“泪流满面”——当代知识分子尚有良知未泯,却终未能独善其身,又在“考虑组织下一个采访团”了。 小说在抨击时弊的同时,对本应承担“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自身的媚俗、堕落予以自省。“喜剧面孔”乍看没心没肺,没羞没臊,坐不正站不直,油彩涂抹其肤,谑词裹挟其言,夸饰装扮其行。然而,作家的反省意识,批判意识已然成为“喜剧面孔”之下的那颗“心”。陈思和先生在与他的学生们进行课堂讨论时曾强调:“刘震云的作品是新文学传统一脉相传的‘嫡系’。”[4]174“有些地方让我想到了鲁迅的文学传统。”[4]175陈先生如此评价,可谓一语中的。 二、“于嬉笑诙谐之处包含绝大文章”的“官场”系列 刘震云的“官场”系列小说包括《单位》、《官场》、《官人》,前文所述《新闻》以及《一地鸡毛》也可各算得半部官场小说。我们关注“官场”系列,以下几点不可忽略: 其一,小说发表的时间与叙事方式的关联。《单位》,《北京文学》1989年第2期;《官场》,《人民文学》1989年第4期;《官人》,《青年文学》1991年第4期。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时段,民众享受着变革的果实又经历着变革带来的阵痛,既充满着加速推进改革的理想和激情,又不满于附生其中的官场腐败和社会弊端。面对现实,百姓有话要说,甚至说话的方式也不再像“文革”刚结束时那般吞吞吐吐、心有余悸。作家急于、勇于、敢于代言,其后很快又明白了善于代言的重要。“叙事策略”成为小说家必须要思考的问题。不动声色的“刘式幽默”便是其中有意味的话语方式。 其二,小说的透视点。“官场”系列均以“小林”或隐性“小林”为透视点。“小林”何许人也?《单位》、《一地鸡毛》的主人公,乡下孩子进城读书,学而优则初涉官场——这种身份设计很微妙,以农村出生背景观城市生存环境,以有着丰富底层生活阅历的小民看“上流社会”浮世绘,并且终于步入了“上流社会”,自卑、惶恐、错愕、兴奋兼具;在生活、秩序、规则、权势的重压之下,理想大厦层层崩塌,所憧憬和仰视的对象慢慢揭开了面纱。青年知识分子“小林”身上多少有着契科夫《小公务员之死》的小公务员伊凡,卡夫卡《变形记》里被职场压垮的格里高尔的影子,他更有着中国农民式的生存法则和生存智慧:吃苦、节俭、坚韧、执著,既随波逐流,又坚守着底层社会凡俗的正义感,但最终却是个人难以对抗法则,被环境绑架和异化。于是“自嘲、自解、自乐”成为小公务员底层挣扎、舒缓压力的宣泄方式,否则,“小林”们也许真得被“一个喷嚏”给吓死,或者变成“人虫”,变成那块馊了的“豆腐”。刘震云坦言:“在虚伪卑琐中也有乐趣,这些乐趣构成了支撑他们活下去的精神支柱,他们在自己的生活中插科打诨,这种伪生活也有很多乐趣。”他进一步表明了自己的民间立场:“我对他们有认同感,充满了理解。在创作作品时同他们站在同一个台阶上,用同样的心理进行创作。这同站在知识分子立场上是不同的,创作视角不一样。”[5]正是躬身下蹲的草民视角,可看不该看之事,可说不可说之话,那么,草民式的嘲讽、谐谑即成为顺理成章的表达方式。 其三,文本的游戏性与“幽默”所含的“同情”以及“部分之肯定”。“官场”系列文本的游戏性是显而易见的: 小说有对小公务员生存窘相的戏说:豆腐馊了惹风波,半夜使猫腻偷水,扛着减价可乐去送礼,下班替人看摊卖板鸭赚钱,大男人夜半无人处暗淌自责的“眼泪”(《一地鸡毛》)。信手拈来的细节透露着主人公生活的“心酸”,“窝心”和“提心吊胆”。 小说有对办公室文化的戏说:单位分梨,弄了筐烂的,使人去外处看,回来说:“别的办公室也是烂的。一处是烂的,二处是烂的,七处也是烂的!”之所以烂梨,是拉梨的车坏了冻烂了梨,之所以车坏,是分房没有满足司机班长的心愿。也有几筐不烂的梨却分给了领导,引起众怒(《单位》)。深陷在这等文化氛围里的人,磨损掉了人性最后的一份真诚、正义、良知和锐气,要有怎样强大的能量才能抵御环境,而不被其慢慢霉腐? 小说有对“官人”们的戏说:众县官对即将升官的官说:“你以后成了咱们的领导,咱们先说好,你可别在咱们这些弟兄面前摆牛;你啥时摆牛,咱啥时给你顶回去!”其他几个人都说:“对,对,给他顶回去!到咱们县上,让他吃‘四菜一汤’!”——这样的对话,怎么看都更像相声段子。段子还有续篇:地方对省委书记的接待是“准备两套饭”,“他要是接近群众呢,咱们就复杂一点;他要是坚持‘四菜一汤’,咱就弄‘四菜一汤’!”(《官场》)笔墨至此,以“四菜一汤”为“廉洁”代名词的符号,被嬉戏、滑稽而解构。 小说有对官场生态的戏说:为追逐官场利益,走上层路线,“核心局”路线,小秘书路线,老乡路线,大炮加机谋,奉承加告状,联盟与反联盟,老谋深算与被老谋深算,城府很深和城府更深——《官人》开篇便以厕所坏了,屎尿反涌,蛆虫遍地为图景,对叙事对象讽刺、暗示、寓言化,荒诞意味十足。 美学家宗白华言:“悲剧家常否定一切。Humor为部分之肯定,故其范围所包,实较悲剧为大也。又凡可憎可爱,可喜可哀,虚虚实实,人生之各方面,无不观察周到,较之悲剧,仅见虚伪,不见诚实,仅见悲哀,不见愉快者,其广狭又不同也。”[6]536-537宗白华进一步阐明,幽默要有观察了解后的“超脱态度”,使之成为人生观、宇宙观。在情感方面“一方面明了之,一方面赋以同情,Humor乃成”[6]538。 刘震云对待幽默对象,襟怀颇宽广,心态亦复杂,因而绝不只是一味戏弄、调侃、讥刺、挖苦了事,而是保持了一份“同情”之心,这一点十分重要。他对“小林”们靠底层奋斗改变命运有赞赏,对堕入庸俗有理解,对仕途艰难有同情,对丢失民间立场的价值取向有忏悔。他的确具备了美学家所言:“一方面明了之,一方面赋以同情”。“同情”的出发点是如此的真实、具体和人性:“钱、房子、吃饭、睡觉、拉屎撒尿,一切的一切,都指望小林在单位混得如何。这是不能不在意的。你不在意可以,但你总得对得起老婆孩子,总得养活老婆孩子吧!”(《单位》) 刘震云对“官人”们的游戏和命运也并非只有批判没有“同情”:小说写县官金全礼,仕途一路时而顺风时而逆境,身心俱疲,“感慨万千”,篇末返璞归真,说只想回家“看看老婆和孩子”;小说写位高权重的许年华,以下级对他忽而仰视忽而平视的视角,去理解高官们的甘苦:“看起来是省委第一书记,谁知也有一本难念的经啊!”(《官场》)。小说对单位人事变动中本以为稳坐钓鱼台的正局长老袁,虽然调侃他“一个月六瓶‘五粮液’”,调侃他“巴掌大一个局,你看得比磨盘还大”!然而一朝失势,却也“同情”他顿生悲凉的常人之心:“一想到自己的耗子身份”,“别人像个猫,故意跟临死的耗子玩玩罢了”。(《官人》) 北大科班出身的刘震云很少卖弄理论和理论新名词,即便说理,用的也是个人化的语言与方式。他以“我向往的是‘雪山下的幽默’”为题写过一篇短文,他说:“幽默是无穷无尽的。一种‘幽默’是这个人一说你就笑;还有一种,他说的时候你没笑,出门笑了,回家洗洗的时候又笑了;第三种幽默是说着说着给你说哭了,就像伊拉克绞萨达姆,一个人死了他的弟弟也死了,我们扑哧笑了。我们的人性有问题啊,但是你又不能不笑。悲剧经不起推敲,所以出来一个喜剧;第四种幽默是我比较向往的,说的时候也没笑,或者笑了也不要紧,出门没笑或者笑了也不要紧,回家洗洗睡的时候没笑或者笑了也不要紧,但是多少年后想起来,心里笑了。前三种幽默,笑的是词语,后一种幽默,笑的是细节、事件、话语背后不同的见识。前三种幽默说的是山间的事、登山的事、山头的事;后一种幽默说的是被深山埋藏的事,漫山的大雪把这个山覆盖了,这是雪山下的幽默。”[7] 读过刘震云的“向往”,我们逐渐接近了他作品幽默的真谛,多数人或者只读出了“词语”之谐,进而感受到“细节、事件、话语”的亦庄亦谐,我们实在需要探究其背后的“见识”:理想追求与理想大厦坍塌的心灵痛楚,游戏神圣与神圣背后的难以示人,人性复杂与濒于绝境时释放的丝丝温暖,那是小说家用“同情”所传递的人性本真。他将不愿饶恕的东西和为什么不可饶恕的道理“埋藏”了起来,交与读者自己找寻。 三、历史述说的另一种方式:《温故一九四二》 中篇小说《温故一九四二》不是标准的“喜剧面孔”,它是悲剧的史实,喜剧的史鉴,正剧的史胆。 《温故一九四二》是小说家实录正史,其史实无疑为悲剧: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三年间,刘的故乡河南大旱加蝗灾,饿死三百万人之多。作者述说历史的方式是双线交叉:一条线为叙述人查阅各类档案、文献,彼时彼地的中外新闻报道等,以史料治史,并将其引入小说;另一条线为叙述人采访以“我姥娘”为代表的亲历者们,以民间口述历史治史,使文本更具小说自身的形态。叙述人“我”的思考联想,判断评价,质疑追问,穿梭于双线之间,无处不在。历史本不是一个可以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刘震云虽非历史学家,此刻也绝无“打扮”历史之嫌,因而这部中篇既没有历史小说一度风行的“戏说”的随意,也没有“大话”的杜撰和夸张的嬉闹。 《温故一九四二》,其史鉴或曰鉴史的方式不乏喜剧笔墨。史鉴是需要依循历史逻辑的,当小说家面对“历史逻辑”制定者的逻辑和历史惯常的“经典原则”采取嘲弄姿态,而对史实本身持敬畏精神时,喜剧的空间生成了。 一是“小”和“大”错位的喜剧。执政者、大人物和食不果腹的灾民眼中的大事小情相距遥远,南辕北辙。2002年2月27日,拍了《一地鸡毛》的导演冯小刚在湖南电视台《新青年》栏目《刘震云访谈录》中曾这样评述刘震云:“是刘震云帮助我认识了‘小’和‘大’的关系,文坛都说刘写的是‘凡人小事’,而刘则认为自己写了‘凡人大事’。凡人无小事,你说是涨工资分房子事大呢还是苏联解体事大?”诚然,冯导此言是泛论,回溯到正在讨论的作品,直面“水旱蝗汤”,“饿殍遍野”,小说以反讽笔调写大人物眼中、心中的“小”和“大”: “三百万人是不错,但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无非是小事一桩。在死三百万人的同时,历史上还发生着这样一些事:宋美龄访美、甘地绝食、斯大林格勒大血战、丘吉尔感冒。这些事中的任何一桩,放到一九四二年的世界环境中,都比三百万要重要。五十年之后,我们知道当年有丘吉尔、甘地、仪态万方的宋美龄、斯大林格勒大血战,有谁知道我的故乡还因为旱灾死过三百万人呢?当时中国国内形势,国民党、共产党、日军、美国人、英国人、东南亚战场、国内正面战场、陕甘宁边区,政治环境错综复杂,如一盆杂拌粥相互搅和,摆在国家最高元首蒋介石委员长的桌前。别说是委员长,换任何一个人,处在那样的位置,三百万人肯定不是他首先考虑的问题。三百万是三百万人自己的事。”[8] 而普通百姓口中却是活生生的,一块石头一个坑的苦难:谁个去逃荒;谁个留下给东家种地;谁个被抓丁;谁个亲人失散;谁个“老婆、老娘、三个孩子,全丢在了路上”,五年后独自孤身而返;谁个被“倒卖给窑子,从此做了五年皮肉生涯”……东西方记者的笔墨则更具典型性和概括性:“妇女售价累跌至过去的十分之一,壮丁售价也跌了三分之一”,“卖一口人,买不回四斗粮食”;“当世界上再无什么可吃的时候,人就像狗一样会去吃人”,“易子而食,易妻而食”;“灾荒如此,粮课依然”;“狗吃人”的照片和委员长因照片披露而生恼怒,而停刊,而人头落地……倘若刘震云“凡人无小事”的视点不失为睹物观世的一个重要视点,那么反观大人物,如何就“大人皆小事”?三百万条性命,小如蝼蚁湮灭,天下还有什么不是小事?小说频频穿梭于“小”“大”之间,“包含”的“绝大文章”是:世上真有比黎民百姓活命更大的事么?错位的喜剧揭示了历史真相的残酷。 二是“细节对比”的喜剧。小说中尽管花爪舅舅对采访者愤怒与不解:“人家人都饿死了,你还要细节!”但是,小说的细节仍令人掩面无语。对比之一:灾民吃一种叫“霉花”的野草中毒,牙脸肿起,手脚麻痛,甚至“霉花”吃尽,只能吃“干柴”;重庆黄山官邸,大人物们正喝着“可口的咖啡”。对比之二:“在母亲煮食自己婴儿的地方,我故乡的省政府官员,宴请两位外国友人的菜单(略)”,被西方记者称之为:“这是我所吃过的最好的筵席之一”,“这是我看到的最好的筵席之一”。对比之三:“委员长思索:中国向何处去?世界向何处去?他们(注:灾民)思索:我们向哪里去逃荒?”——不厌其烦的细节,件件意味深长。 三是“记忆”和“忘却”的喜剧。死了三百万人口的巨大灾难,它的亲历者,与世纪同命运的普通中国乡村妇女“我姥娘”,却“已经忘得一干二净”。姥娘“记忆力健全”,“我相信她对一九四二年的忘却,并不是一九四二年不触目惊心,而是在老人家的历史上,死人的事情是发生得太频繁了”。无独有偶,小说中另一位当年曾做过县长“笔录”,主持过赈灾义演的文化人,竟对饿死多少人,“似也没有深刻的记忆”,只对与个人经历有关的“义演”津津乐道。作者显然有足够的理由理解以“我姥娘”为代表的民间记忆的“忘却”,却用“摇头”表达了对知识分子个体或群体“失忆”的不满,更剑指以无数大言、伪言、谎言、不言遮蔽历史真相的历史书写。“我”的叹息沉重而又叩击人心:“历史从来是大而化之的。历史总是被筛选和被遗忘的。谁是执掌筛选粗眼大筐的人呢?”刘震云频繁地、貌似不经意地去写人对历史大事件的“忘却”,小说标题却明明白白落下一个词——“温故”,“温故”如同历史回响的钟声,余音袅袅,不绝于耳。远的不说,仅“我姥娘”所经历的历史,还有哪些事件值得“温故”?谁来“温故”?如何“温故”?若不“温故”,历史何以走出重复的怪圈? 如此悲剧的一九四二年,如此喜剧的后人和史鉴,难怪小说的“我”站在历史面前会一次次“不禁哑然失笑”,“露出自嘲的微笑”,“又是轻轻一笑”,“心里却感到好笑”。 《温故一九四二》的史胆是:将世纪大灾难放置于世纪大背景中考察,以生存逻辑对抗历史书写者的伪逻辑。于是,他推崇当年“揭竿而起”,到地主范克俭舅舅家吃白饭、抢明火、被烧死的“土匪”领头人毋得安,称“这是民族的脊梁和希望”。小说甚至探讨了灾难拯救时,中外媒体功能,中外宗教功能,肚皮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如此等等。刘震云站在平民百姓的立场,去感、去录、去思、去论,小说的“我”申明:“我从一九四二年起,就注定是这些慌乱下贱的灾民的后裔”,于是他不再保持惯常的不动声色,却常常按捺不住疑问、追问、叩问、质问的冲动,我相信那正是小说最出彩和最有价值的文字。 马克思曾说:“历史不断前进,经过许多阶段才把陈旧的生活形式送进坟墓。世界历史形式的最后一个阶段就是喜剧。”[9]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又修正了黑格尔:“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10]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悲剧是镜,笑剧也是镜。“温故”审视悲剧,“温故”试图阻止笑剧上演。 有智慧发掘生活中喜剧因子并将其打造成喜剧艺术的作家,当今是不多的。肤浅的“逗乐”、“搞笑”可以单纯地享受“笑”所制造的生理快感,而不必关注文学对于历史,对于人和人类应当担责。有识见的批评家对当下某些走向“无厘头”端点,以“大话”为新型话语运动的喜剧美学,表达了深深忧虑:“如果仅仅是后现代文化的表象模仿和复制——如果仅仅将后现代文化视为声嘶力竭的嬉闹,那么,这种新型的话语不可能与本土的政治经济学产生密切的联系。这时,语言游戏的意义不会溢出语言之外。”批评家抨击某类作品“无比机智地扩大了语言的喜剧性张力,同时又如此深刻地显示了语言的无能为力。哄堂大笑既是开始,又是结束。某种意义上,这很可能象征了中国版后现代文化的真实命运”[11]。我们正是在后现代的文化氛围中研究刘震云的“喜剧面孔”才更具有现实意义。“刘式幽默”既打开了与经典喜剧相通的道路,又独辟蹊径,不动声色地满足了我们揭露丑,撕毁丑的深刻的快乐。“刘式幽默”在揭露社会丑恶现象时保持了一份先进社会力量的自信和优越感。这份自信和优越感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他在湖南电视台《新青年》栏目《刘震云访谈录》中回顾北大岁月,称“我们那时才叫‘新青年’,现在我和师兄弟们见面,发现他们都是‘老青年’,没有什么他们玩不转的”。新世纪初,他在作品重新结集的《序言》中写道:“历史是一面镜子。通过这次结集,我又重新阅读了自己十多年前的作品。短短的时间虽然有些模糊,但我已经从模糊的镜面中看到了另一个自己。当时你是那么憨厚、忧愤、软弱和无言,当然你也是那么激情和青春。为此,我对你有些羡慕。”[12]我们看到,这正是一副站在“新青年”的队伍里,立在“憨厚、忧愤、软弱和无言”同时又“激情和青春”的场域中才会有的“喜剧面孔”。 当代评论似已习惯于提“黑色幽默”,已忘却了另一个词:“黄金幽默”(“Golden humor”),宗白华美学论著中多处提及这个“德人常名”之词,他说:“悲剧和幽默都是‘重新估定人生价值’的,一个是肯定超越平凡人生的价值,一个是在平凡人生里肯定深一层的价值,两者都是给人生以‘深度’的。莎士比亚以最客观的慧眼笼罩人类,同情一切,他是最伟大的悲剧家,然而他的作品里充满着何等深沉的‘黄金的幽默’。”[13]刘震云骨子里也是悲剧家,但他正努力写着“以悲剧情绪透入人生,以幽默情绪超脱人生”的小说,这便是他的“黄金的幽默”。这便是他的“喜剧面孔”的真谛。标签:刘震云论文; 温故1942论文; 一九四二论文; 喜剧片论文; 文学论文; 一地鸡毛论文; 剧情片论文; 中国电影论文; 战争片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