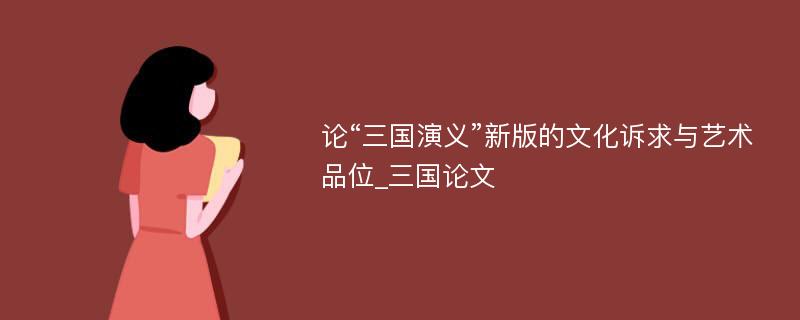
论新版《三国》的文化诉求与艺术品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品位论文,新版论文,艺术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导言:新版《三国》基本上是成功的,这主要表现在场面壮阔、气势恢弘、精雕细刻、人物鲜明等方面,当然也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若以其为典型个案总结古典名著改编为电视剧的经验教训,笔者认为:在文化定位上,应确立“为国为民”这个终极评价标准;在材料取舍上,应坚持思想价值优先于戏剧性的选材导向;在艺术品位上,应兼顾情节奇特与性格逻辑、情理规律三位一体的美学原则。此外,在名著改编的拍摄思路上,可以有忠实原著、当代解读和片段拍摄等不同模式,但无论采用哪种模式,追求目标与评价标准应是一致的:即必须坚持文化价值的丰富性与艺术品位的高水准,全力以赴打造精品。
新版《三国》第一轮热播已结束,从名列前茅的收视率看,电视观众关注的程度超过了其他热门的言情剧、武打剧和警匪剧等题材。这说明重拍基本上是成功的,也又一次证明了中国古典小说名著的无穷魅力。从视觉效果和剧情层面看,《三国》很好看,能够吸引人一集一集地看下去。这对于既熟悉《三国演义》文本,又看过老版电视剧《三国演义》的广大观众来说,已经是非常不容易的了。当然,若细密考察,也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有鉴于此,为了总结古典名著改编的经验与教训,以利于今后多出精品,有必要认真细致地做多角度、多层次的比较研究,深入地探讨一系列理论问题。这已经不仅仅是评价一部《三国》电视剧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如何对待祖先留下的宝贵文学遗产的问题,也涉及到当下应该创造出什么品位的艺术成果留给子孙后代的大问题。纵观新版《三国》播出后的有关评论,随感杂谈较多,全面综合深入论析的文章较少,因此笔者不拟作一般得失性的感想式评论,而是侧重从文化诉求与艺术品位等层面着眼,探讨古典名著改编的某些理论问题。
一、文化定位:“为国为民”乃超时空的终极目标
新版《三国》的成功之处,可略举数端:第一,场面壮阔,气势恢弘。特别是战争场面,壮丽与惨烈交织的宏阔画面,充溢着男子汉大丈夫的英雄气概,具有一种特殊的阳刚之美,不能不令观众怦然心动。第二,创作认真,精雕细刻。如宫室格局设计精致、大气,装潢格调古雅、脱俗,舞美服装色调搭配和谐等等,均产生了良好的审美效果,体现出创作群体精益求精的艺术追求。第三,人物塑造,个性鲜明。这可分三个层次比较论之:吕布、陈宫、鲁肃、司马懿等人物形象的塑造,引人注目,可以说超过了老版《三国演义》电视剧。董卓、王允、袁绍、袁术、刘表、貂蝉等形象也比较成功,与老版相比,各有所长,难分轩轾。刘备、关羽、张飞、诸葛亮、曹操等形象,虽不无新意,但与老版相比,则难免稍逊风骚。这并非说新版表演不出色,而是老版有关形象太突出了,先入为主,难以超越。就表演而言,关羽在兄弟三人中最出色,诸葛亮的外在形象很好,弱在大智大勇的表现与从容不迫、挥洒自如的气质风度方面,给人的感觉是忧郁有余,自信不足。曹操的表演虽收放自如,也有可圈可点之处,但过于随便,表演外露,内蕴不足,给人的感觉是江湖气、痞子气有余而英雄气不足,倘若再深沉、内敛一些,效果会更好。当然,这些表演如何的探讨尚属次要方面,这里着重要谈的是名著改编的文化定位与评价标准等问题。
中华民族是一个重史的民族,中国的小说就源于史传。史家撰写历史著作的文化定位与评价标准是:既要坚守“秉笔直书”的历史评价原则,也要体现“寓褒贬、别善恶”的道德评价目的。小说家的文化定位与评价标准源于史传而又有所不同,乃是道德评价第一,历史评价第二。因此,在罗贯中笔下,刘备的仁义美德与曹操的奸诈恶德都得到了强化。
若认真比较《三国志》与《三国演义》,历史原型刘备的道德面貌本来就大好于曹操,《三国演义》中作为曹操恶德根据的主要事件,大多可在陈寿、裴松之笔下找到原始材料①。因此,士林与大众才把赞誉之情倾注于刘备,在他身上寄寓了道德理想与审美理想。这也是历史原型演变成为“箭垛式的人物”②形象的基础。作为士林精英的罗贯中集前人之大成,将其汇集于《三国演义》之中。因为刘备集团爱民,士林与大众就“褒刘”;曹操集团害民,士林与大众才“贬曹”。总起来看,社会上下一致性的“拥刘反曹”的评价标准,皆是遵循道德评价第一与爱民为首的原则。由此可见,无论以何种艺术形式表现《三国演义》,“尊刘贬曹”的思想倾向是要坚持的,绝不能颠倒过来,因为刘、关、张“桃园三结义”的誓词“上报国家,下安黎庶”,具有超时空的文化价值。“上报国家”,就是报效国家,就是爱国主义,岳飞的“精忠报国”与此一脉相承;“下安黎庶”,就是使百姓安定、安宁、安居乐业,就是爱民。这种文化观念,当下与今后仍然要继续坚持并大力弘扬。老版《三国演义》电视剧抓住了“上报国家,下安黎庶”这八个字,把戏做足了,应该是切中肯綮的正确的文化定位。
总体看,新版《三国》基本上也做到了以为国为民为标准去褒贬人物,但在某些经典情节的处理、某些重要人物的评价上还值得斟酌。比如开篇让董卓、曹操先出场,就不如原著让刘备、张飞、关羽先出场立意高远,主旨突出。与此相关,《三国》淡化了“桃园三结义”这个重头戏,没有突出原著置于卷首显著位置的“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的思想,就有损于原著的思想精华,未免得不偿失。网上有文章批评说,“桃园结义”的画面还不如曹操撒泡尿的时间长。虽然语言有些尖刻,但也说明了观众对淡化“桃园结义”而重视曹操的强烈不满。曹操固然是个英雄,罗贯中也赞扬了他善于用人、长于军事谋略等才干,但是由于他道德层面的“奸”,这个英雄就变成了奸雄,道德评价的“奸”不仅居于“雄”之前,而且起着主导作用。这个“奸”的内涵中并非仅仅指对汉献帝的欺君罔上,更重要的是曹操对百姓的态度。曹操害民与刘备爱民的鲜明对比,就是罗贯中与大众“拥刘反曹”的主要根据。由此可见,无论哪个时代,对于掌权者来说,爱民与否是评价其道德人格的首要标准,特别是在百姓利益与掌权者的集团利益或其个人利益发生矛盾冲突的时候,更要强调“百姓利益高于一切”这个总原则,这是具有超时空意义的终极评价标准。
罗贯中在《曹操兴兵报父仇》中写曹操害民行为曰:“操令但得城池,尽皆杀戮,以雪父仇。”“操大军所到之处,鸡犬不留,山无树木,路绝人行。”③毛宗岗评本第十回改为:“操大军所到之处,杀戮人民,发掘坟墓。”④对曹操害民行为的揭露与批判,更加明确有力。《三国演义》的这些描写是以史书记载为据的:裴注在《荀彧传》中“前讨徐州,威罚实行”语下,引《曹瞒传》云:“自京师遭董卓之乱,人民流移东出,多依彭城间。遇太祖至,坑杀男女数万口于泗水,水为不流。陶谦帅其众军武原,太祖不得进。引军从泗南攻取虑、睢陵、夏丘诸县,皆屠之;鸡犬亦尽,墟邑无复行人。”⑤这就不仅比陈寿贬曹操的“所过多所残戮”等语详细具体,而且贬斥倾向也大大强化了。这条史料也被司马光引入《资治通鉴》正文中⑥,这进一步说明了其可信性。这种滥杀无辜、草菅人命的行径,在任何时代都是应该否定的。这是他“宁可我负天下人,休听天下人负我”的具体体现。这种极端自私自利的人生哲学,是曹操“奸”的思想核心,是历代统治者“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利己主义的典型代表。新版《三国》若能把曹操这些既有史传记载,又有《三国演义》文本根据的害民行径形诸画面,对于揭露以曹操为代表的历代统治者的害民本质、警示后人,皆是具有重要意义的,那就是正确的文化定位。遗憾的是,这些害民的内容被新版《三国》删除了,这未免有美化曹操之嫌。与此相关,新版《三国》也砍掉了《三国演义》文本中详细描写、竭力渲染的刘备“携民渡江”时爱民胜过爱己的一系列表现,淡化了刘备爱民的程度,这应属于文化定位模糊的问题。刘备曾自言:“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这是有史书根据的⑦,也是罗贯中着意强调的曹、刘差别之关键所在。
此外,新版《三国》欲突出曹操建功立业的英雄一面而有意加重曹操戏份的创作意图,也存在不容忽视的负面效应,这容易造成评价标准的错位与观众的错觉,似乎只要有利于个人的建功立业,就可以随心所欲、不择手段,就可以突破道德底线。这种价值观的社会效果是非常可怕的。如果当下社会中的人们皆学曹操,不择手段地去追求权力与金钱,急功近利地获取功业与政绩,那么这个社会就会成为道德沦丧、唯利是图的大染缸。司马光认为:“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⑧以此衡之,刘备是德胜才的君子,曹操则是才胜德的小人。这是陈寿、裴松之、司马光等史家的文化定位,小说家罗贯中继承并发展之,老版《三国演义》电视剧成功地汲取了前人的思想精华,新版《三国》电视剧为追求创新而在某些关键地方忽略了前贤思想精华的继承,似可视之为其思想层面的重大缺陷。我们今天可以重新评价曹操与刘备,但是仍然不能仅以“英雄”模糊二者的本质区别。
二、材料取舍:思想价值应该优于戏剧性标准
新版《三国》属于历史题材作品,必然涉及到面对各种现有材料的取舍、生发问题,也自然会牵涉到与《三国志》、《三国演义》、老版《三国演义》电视剧的关系问题。新版《三国》的改编原则是“人物大于‘是非’、戏剧高于‘道德’”⑨。在此创作原则的指导下,新版《三国》从《后汉书》、《三国志》、《华阳国志》等史书里吸取了大量的材料,对某些小说一笔带过的地方进行了大幅度的增加和扩展,增加了大量的细节,力图突破《三国演义》的束缚。这种总体思路是文艺创作所允许的,有的地方处理得也不错。如诸葛亮一死就马上收尾的整体结构改变,从观赏效果的层面看是比较高明的。有些增添也是具有思想价值的,如刘备解释他救徐州的动机时所说:“天下之大,惟徐州刺史陶公祖最是宽仁厚道,爱民如子。如果连陶公祖这样的仁德之君都无法生存的话,这个国家还有什么指望呢?”这就既有现实针对性,又有思想深度。材料取舍方面应该强调的问题主要在于以下几点:
第一,从当下社会的文化建设层面说,“是非”应该大于人物,“道德”应该高于戏剧。这是文艺工作者的道德良知与社会责任决定的。当下社会道德滑坡、不讲诚信等问题,已经到了泛滥成灾的地步,如果再这样不分曹、刘的是非,“核桃栗子一起数”,那就会倒退到“成王败寇”的价值观层次了。现在百姓需要的是为国为民、长厚善良的刘玄德,而不是自私自利、不择手段的曹孟德。
第二,作为电视剧,新版《三国》追求戏剧性的好看有趣,本无可厚非,但这个追求应该与思想价值的蕴涵统一起来,使二者相得益彰。如果不能两全的话,应该以思想价值为先,而不能削足适履,以牺牲思想价值来换取戏剧性的好看有趣。莱辛在《汉堡剧评》中指出:“剧作家并不是历史家,他的任务不是叙述人们从前相信曾经发生的事情,而是要使这些事情在我们眼前再现。让它再现,并不是为了纯粹历史的真实,而是出于一种完全不同的更高的意图。历史真实不是他的目的,只是他达到目的的手段;他要迷惑我们,从而感动我们。”⑩这种观点可以借用来评价中国史传与历史题材文艺作品的区别。罗贯中就是这样对待历史题材创作的,他的“更高的意图”就是塑造“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的英雄,从而感动广大读者。“三国”题材乃至古典名著改编者也应该通过其创作去实现“更高的意图”,正确引导广大观众,为建构当代先进性的和谐文化大厦添砖加瓦。马克思在致斐·拉萨尔的信中,曾要求历史剧能够“用最朴素的形式把最现代的思想表现出来”(11)。当下这个“最现代的思想”应该比罗贯中的“最现代的思想”有所进步,而不是退步。比如,《三国演义》中的刘备与诸葛亮理想化的君臣关系范型,就是在当时所能够达到的思想制高点。从纵向角度考察,罗贯中继承了陈寿“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12)的君臣关系理想,进而将其推至超越三国而达到古今制高点的理想化境界。但是,若置于今天的社会文化背景上观照,这显然落后了,因为其“忠君”思想中有封建性的元素,因此,在不得不表现这方面的内容时,就应该有批判的眼光,而不能再一味地赞美。相比较而言,新版《三国》在处理刘备与诸葛亮的关系上,总体感觉诸葛亮的地位比《三国演义》大大下降了,诸葛亮的决定权缩小了,作为智慧化身的诸葛亮的睿智、机敏、自信、乐观等方面表现明显不如原著,却常常表现得愁眉苦脸,忧心忡忡,无可奈何。这不能不令仰慕《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形象的广大观众失望。在《三国演义》中,刘备是皇权的代表,诸葛亮是士林的领袖,是士人形象的典型。二人珠联璧合的合作,是“学成文武艺,货于帝王家”的士林从政的良性状态,是入仕士人的最优化选择。“三顾茅庐”的思想价值主要在于:诸葛亮是因为与刘备志同道合,出于为国为民的共同目标而入仕相佐的。其中特别打动诸葛亮的是刘备“先生不肯匡扶生灵,汉天下休矣”的救民保国语言与其“泪沾衣襟袍袖,掩面而哭”(13)的真诚泪水。黄宗羲曰:“不以天下为事,则君之仆妾也;以天下为事,则君之师友也。”(14)这表明罗贯中笔下诸葛亮的出仕思想具有一定的超前性。作为士人的罗贯中,显然是把诸葛亮塑造成了入仕士人的理想化楷模,其中熔铸了他本人乃至整个士林群体“为帝王师”的入仕理想。
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层面考察之,先秦士林的诸家思想皆有对“士”的人生目标与社会理想的要求,而以儒家对士林的影响最大。孟子曰:“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15)这个“恒心”的核心要素就应该是为国为民的社会理想。诸葛亮形象就是这样的“士”的典型,特别是到了后期与刘禅的关系中,其政治地位又有所提高,“诸葛丞相在于成都,事无大小皆是亲自从公决断”。《三国演义》的这个描写是有史书根据的,《三国志·诸葛亮传》明确写着:“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16)这就等于士人精英在掌权,其积极的正面价值在于:可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专制皇权决策的偏差失误。新版《三国》本应以诸葛亮为典型,将三国时代诸葛亮等士人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才智、人格、思想高度全面地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有责任、有义务弘扬文学经典中本来就蕴含的士人的人格精神,进而如马克思所说“把最现代的思想表现出来”,而不应该是比《三国演义》的思想退步。这既是遗憾,也是今后创作的教训,故不能不提出来以引起文艺界的足够重视。
第三,刘备与诸葛亮一定是主角,曹操、司马懿只能是刘备、诸葛亮的对立面,起衬托作用,而不应成为主角。因为罗贯中与士林、大众的道德理想与审美理想就寄托在刘备集团身上,主角变了,主题也自然会随之改变,那样《三国演义》就不存在了,观众也不会接受。
当然,全面考察罗贯中对史料的取舍,在思想价值层面也不无倒退之处,如罗贯中舍弃的能够表现张昭“性刚”的某些史料内容(17),就不无遗珠之憾,因为从历史人物张昭身上,可看到中国古代士林中宝贵的阳刚之美、骨耿之气与人格精神,这是当今士林应该继续发扬光大的。诸如此类的内容,新版《三国》就完全可以补前人之未备,那就可以后来居上了。这里面的再创作空间是相当广阔的。
新版《三国》的编剧认为:“罗贯中你根本就没写完。我们完全可以根据一场战争、一句台词、一些片段,生长出很多很多的东西。”(18)这也是当代再创作所允许的。那么,这些生长出来的诸多内容的客观效果如何呢?实事求是地评价,有的是锦上添花,有的是得失参半,有的是可有可无,有的是画蛇添足。比如,吕布与貂蝉感情戏的增加,其“得”是迎合了当代观众的审美趣味,体现出具有当代色彩的人性内涵,比较好看;其“失”则是降低了貂蝉为国献身的思想境界。
再比如,新版《三国》增加了一系列曹操父子间勾心斗角的情节,这固然有利于表现其人性的复杂与政治斗争的残酷,但尽管编导花费许多笔墨,结果却将曹丕与曹植两个形象搞得颇为不堪,增加部分实属多余。其实,曹丕与曹植争太子的问题,只是写到《三国演义》那个程度就足够了。兄弟二人皆是著名的文学家,在“三曹”的周围,环绕着一批著名的文人,他们诗文唱和,留下了不少为人津津乐道的故事。如《世说新语》记载的曹丕在王粲墓前学驴叫的故事就体现了曹丕重情、真率的一面(19)。类似于这种尊重人才的思想内涵与感情真挚的人性光辉,不仅符合今天人们的审美观,而且还有先贤刘义庆笔下的文字记载为据,完全可以纳入到新版《三国》中去。
又如,有些人物结局的改变也值得考虑。关羽的死改为自杀,显然系模仿《史记》中项羽之死的描写,虽有免去关羽被俘斩首之“得”,但也失去了原著中关羽临死时那种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与思想闪光,应属于得不偿失者。关于汉献帝的结局,《三国演义》只是写到禅让后封山阳公而离开都城为止:“献帝含泪拜谢,上马而去。坛下军民人等见之,伤感不已。”这就恰到好处,留有余味。相比之下,新版《三国》所增加的汉献帝凿船自沉的情节,当属画蛇添足。
此外,还有女人戏的增加问题也值得商榷。其中大乔、小乔戏份的增加与作用的强化,已属赘笔。而虚构出的静姝更是蛇足。静姝历时三朝的潜伏卧底,实属曹丕与司马懿之间低层次的斗智,与《三国演义》智慧含量极高的斗智相比,未免相形见绌。司马懿与静姝的“爱情”也缺乏美感。这些女子形象固然美丽动人,感情表现固然细腻缠绵,但还是属于降雅为俗的媚俗之笔。如果拍的是一般的古装娱乐片,那也就无所谓了,但是对于《三国》这样史诗性的经典作品来说,则不该如此,而应该高标准、严要求,保持原著的艺术品位与高雅格调。
邓芝出使东吴,在《三国演义》中是重头戏。他担负着彝陵之战后修复吴蜀联盟的艰巨任务。邓芝不惧油锅、置生死于度外、“使于四方,不辱使命”的杰出外交家形象,为广大读者熟知且钦慕不已。可新版《三国》却换成了马谡,这种改变,既牺牲了邓芝形象,抹去了其闪光点,也未给马谡增加光辉,且不符合马谡的性格逻辑,也属得不偿失。
其他如不止一次出现的曹操撒尿的镜头,更属蛇足之类的细节败笔。不仅有碍观瞻,无聊无趣,也没有任何思想价值。
三、艺术品位:高标准的确立与“度”的把握
评价新版《三国》的艺术品位,必须首先确立评价标准,笔者拟立的标准是:情节奇特与性格逻辑、情理规律三位一体的美学原则。从《三国演义》的文本看,罗贯中的艺术创作总体上达到了这个标准,这个美学原则也是从其作品中总结出来的,如“草船借箭”、“单骑救主”、“据水断桥”、“空城计”等皆是符合此标准的典型篇章,以此标准评价新版《三国》应该是比较合适的。
试举“单骑救主”为例说明之。从情节奇特的层面看,赵云于百万军中匹马单枪,怀揣阿斗,“杀死曹营名将五十余员”,得全而归,传奇色彩十分浓厚。从人物性格逻辑层面说,这有力地凸显了赵子龙浑身是胆、勇不可挡的性格特征。从情理规律层面看,这是否合理呢?答案是肯定的,其关键在于罗贯中点睛之笔的创造:“操曰:‘不要放冷箭,要捉活的。’”此语出自曹操之口,正是其一贯爱惜人才的性格逻辑决定的。此语一出,赵云脱离虎口便真实可信了,从而使奇异美与真实美达到了统一。这一细节堪称经典,恰如狄德罗所说:“正是这些细节的真实,使心灵容易接受伟大事故的强烈印象。”(20)考之史著,《三国志·赵云传》上只有简略数语:“云身抱弱子,即后主也,保护甘夫人,即后主母也,皆得免难。”(21)《三国志平话》虽有“单骑救主”的奇特情节,但由于没有“不要放冷箭”这个细节,便不合情理,令人难以置信。相比之下,新版《三国》中此情节被改写成:曹操先有“我要生擒他,留有大用”的命令,这是符合曹操爱才的性格逻辑的,也与原著相符。但可惜的是,在部下以关羽为例的劝谏下,曹操改变了初衷,最终变成长叹一声:“杀了吧!”这最后的命令发布以后,赵云应该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冲出重围生还的。但是这样一来,此情节就不合情理了。编导欲把曹操性格、心理复杂化以后来居上的良好意图,难免退至《三国志平话》的客观效果。
包含小说在内的中国叙事文学对故事情节奇特性的追求,有古代美学的承传因素。中国小说以神话超自然为“奇”的幼稚幻想为滥觞,发展到六朝志怪小说的“张皇鬼神,称道灵异”(22),又演进到唐代文人“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23),逐渐形成了“以奇为美”的审美倾向。《三国志》继承了《史记》“传畸人于千秋”的“爱奇”追求,就体现了选择奇人奇事书写的特点;而讲史文学更把传奇性看作其艺术生命之所在,《三国志平话》就是三国故事越传越奇的一个总结。罗贯中在中国小说“以奇为美”的美学传统影响下,在史传、讲史文学所提供的传奇素材基础上,适应着人民大众“好奇”的审美心理,创作出《三国演义》这部奇书。因此,其中的人物和事件不可避免地带有传奇色彩,形成情节奇特曲折、人物超凡脱俗的特征。从心理学与接受美学的角度分析,情节的奇特曲折具有特定的审美价值。清人寄生氏在《争春园全传叙》中说道:“人不奇不传,事不奇不传,其人其事俱奇,无奇文以演说之亦不传。”(24)这就道出了生活之奇与作者传奇、读者赏奇三者辩证统一的关系。从此层面观照,新版《三国》追求人奇事奇的艺术定位,总体是恰当的,其“奇美”的表现也征服了观众,是其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
叙事性文艺作品中人物形象的性格逻辑,是指小说中人物性格在其横向扩展和纵向延伸中表现出来的必然性、可能性和规律性。人物只有按自身的性格逻辑去说话、行动,才能达到性格的真实可信。这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刻画‘性格’,应如安排情节那样,求其合乎必然律或可然律:某种‘性格’的人物说某一句话,作某一桩事,须合乎必然律或可然律。”(25)创作主体要遵循笔下人物的性格逻辑设计人物的语言、行为及心理活动。作品中人物作为对象主体,一旦形成了自己的独特性格,就有按自身性格逻辑去说话、行动的权力,并且可能修正作家的初步设计。读者与观众作为欣赏主体,也会从性格逻辑的角度来评判人物塑造的成功与否。新版《三国》遵循《三国演义》原著中合乎人物性格逻辑的例子自不必说,而其增加的情节就应该以性格逻辑为标准择来检验一下了。
“三顾茅庐”是脍炙人口的经典性情节,新版《三国》遵照原著的部分毋庸赘言,而进一步演绎的部分则可商榷。《三国演义》中张飞只是嫌诸葛亮“傲慢”,故对关羽说了一句:“等我去屋后放一把火,看他起不起!”结果是“云长再三劝住”(毛本第三十八回)。张飞的“放火”语言已足见其粗莽性格矣,无须见之于行动,关羽劝止,分寸适当。但新版《三国》则非要付诸实施,竟然真让张飞放了一把火,这就过“度”了,既违背了张飞的性格逻辑,把张飞误写成李逵了,也损害了关羽形象。还有徐州失陷后刘备要跳崖自杀的行为,均是违背人物性格逻辑的画蛇添足。
叙事文学在追求情节奇特的同时,必须符合社会生活中人情物理的逻辑性与规律性,这就是检验作品成功与否的情理规律。文学作品在作者构思创作至读者阅读欣赏这个完整的实现过程中,无论是作者还是欣赏者,都必须遵循这个情理规律。合于情理规律的作品,就能引起读者强烈的心理共鸣,令“闻者或悲或叹,或喜或愕”(26)。反之,则会令读者产生失真受骗的反感。这正如李渔所说:“凡说人情物理者,千古相传;凡涉荒唐怪异者,当日即朽。”(27)西方美学家也十分注重文学艺术创作是否符合情理规律的问题,别林斯基就曾指出:文艺作品“合理性的标志,即是那一现象的必然性”(28)。《三国演义》原著就达到了“幻既出人意外,巧复在人意中”(29)的艺术境界。新版《三国》中合于情理规律者自不待言,增加部分违背情理规律者,也时有所现,如官渡之战中袁、曹两军鏖战在即,曹操与袁绍竟然在阵前悠闲地对坐饮茶,明显不合情理规律,因此,其艺术效果大打折扣。
新版《三国》为了突出孙权的作用,增加了他出使刘表等情节,这显然与其年龄不符,也属于不合情理规律一类。这种刻意突出,难免揠苗助长的雕琢痕迹,艺术效果适得其反。
关于庞统之死,新版《三国》改为他要以死来换取刘备取四川的出师有名,也属不合情理规律的人为编造。其实刘备取川的理由并非那么难找,《三国演义》原书的处理就恰到好处,没有必要再节外生枝。
总而言之,一部作品的艺术品位,往往就在于一个“度”的把握,合“度”就包括符合以上所言诸方面。表现不到位当然不行,过分了也不行。《三国演义》作为文学经典,对“度”的把握非常到位,其中蕴含的艺术理论与创作经验,还大有总结、挖掘的余地。后继者固然可以进一步生发、拓展,以求后来居上,但若过了“度”,就会弄巧成拙。举个典型例子来说,关羽“华容道放曹”,是《三国演义》全书的重头戏,也是不好把握的艺术难题。关羽在政治集团利益与报恩情感的冲突中,进行着艰难痛苦的抉择。最后,报答曹操的酬恩之情、见“曹军惶惶,皆欲垂泪”的“不忍”之心、“以信义为重”的道德选择、张辽说情的“故旧之心”等多种因素的合力,战胜了政治集团的利益,终于“长叹一声,并皆放之”。其中关羽欲放曹—又拦曹—再放曹的心理变化过程,适中合度,简洁到位,艺术水平相当高。而新版《三国》有意加重情节戏份的折腾来折腾去,既分寸过“度”,又不合情理。这又一次证明了“过犹不及”的辩证法,也是值得认真总结的艺术创作教训。
关于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的电视剧拍摄问题,似可有这样几种思路:一是完整再现原著,其拍摄目的就是再现古典名著的整体风貌,保持原汁原味。应该说,能够把文字成功地转化成电视画面,也是一种艺术创造。二是名著当代解读,即抓住原著中思想价值的集中点、艺术创造的制高点、人物形象的闪光点,以当代文化意识解读之,求精而不必求全。三是名著的片段拍摄,即只选择名著的精彩片段拍摄之,注重点而不是着眼面,以少胜多,重点突破。总而言之,无论哪一种思路与拍法,均应该是文化价值与艺术品位第一,坚持高标准,精益求精,自始至终贯彻精品意识。
注释:
①如:曹操杀害汉太医令吉本与少府耿纪、司直韦晃及救火的汉百官(见《武帝纪》正文及裴注引《山阳公载记》);杀崔琰、孔融、许攸、娄圭(见《崔琰传》);囚毛玠(见《毛玠传》);害死神医华佗(见《方技传》);杀死伏皇后(见《武帝纪》裴注引《曹瞒传》);逼死荀彧(见《荀彧传》裴注引《魏氏春秋》)。以上均见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1982年版。
②胡适:《中国章回小说考证·三侠五义序》,上海书店1980年版,第393页。
③(13)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汪原放标点,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98页,第370页。
④见《三国演义会评本》,陈曦钟、宋祥瑞、鲁玉川辑校,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16页。
⑤《三国志·魏书》,第310页。
⑥《资治通鉴》正文曰:“初,京雒遭董卓之乱,民流移东出,多依徐土。遇操至,坑杀男女数十万口于泗水,水为不流。操攻,不能克,乃去攻取虑睢陵夏丘,皆屠之;鸡犬亦尽,墟邑无复行人。”(见《四部备要》册三七,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版,第715页)
⑦《三国志·蜀书·庞统传》中裴注引《九州春秋》载:“备曰:‘今指与吾为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故而失信义于天下者,吾所不取也。’”(见《三国志》,第955页)
⑧见《资治通鉴》卷一,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14页。
⑨(18)朱苏进:《在我看来,罗贯中根本就没写完》,载《南方人物周刊》2010年第21期。
⑩莱辛:《汉堡剧评》,载《文艺理论译丛》1958年第4期。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40页。
(12)《三国志·蜀书·先主传》,第892页。
(14)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臣》,《丛书集成新编》册二六,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355页。
(15)《孟子·梁惠王上》,见《孟子译注》,杨伯峻译注,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7页。
(16)《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第918页。
(17)《三国志·吴书·张昭传》载:“昭谏曰:‘……。’权与相反复,昭意弥切。权不能堪,案刀而怒曰:‘……。’昭熟视权曰:‘……。’因涕泗横流。权掷刀致地,与昭对泣。……昭忿言之不用,称疾不朝。权恨之,土塞其门,昭又于内以土封之。”(见《三国志》,第1223页)
(19)刘义庆《世说新语·伤逝》曰:“王仲宣好驴鸣,既葬,文帝临其丧,顾语同游曰:‘王好驴鸣,可各作一声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驴鸣。”(见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47页)
(20)狄德罗:《理查生赞》,见《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5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132页。
(21)《三国志·蜀书·赵云传》,第948页。
(22)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5页。
(23)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三六《二酉缀遗中》,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371页。
(24)见丁锡根编著《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595页。
(25)亚里士多德:《诗学》,罗念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49页。
(26)笑花主人:《今古奇观序》,《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第793页。
(27)李渔:《闲情偶寄·词曲部·结构第一·戒荒唐》,见徐寿凯注《李笠翁曲话注释》,安徽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7页。
(28)别林斯基:《伏拉狄斯拉夫·葛尔恰科夫的诗》,见《别林斯基论文学》,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第203页。
(29)毛宗岗:《读三国志法》,《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第923页。
标签:三国论文; 三国演义论文; 罗贯中论文; 诸葛亮论文; 司马懿与诸葛亮论文; 三国人物论文; 曹操后人论文; 三国志论文; 三国志平话论文; 关羽论文; 曹操论文; 刘备论文; 关羽云长论文; 古装剧论文; 中国电视剧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