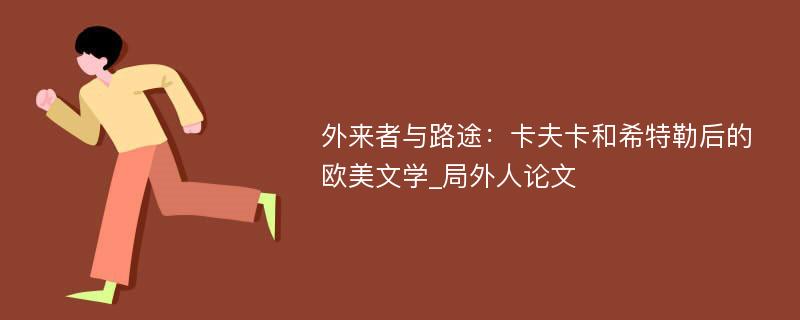
局外人和在路上——卡夫卡和希特勒之后的欧美文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希特勒论文,卡夫卡论文,路上论文,欧美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如果可以将毕加索的《格尔尼卡》看作20世纪历史的一种象征景观的话,那么这种象征无疑是在两个层面上呈现的,即物的层面和人的层面,或者说文明的层面和文化的层面。当毕加索在画面上呈示出炸弹爆炸过后那种碎物纷扬的构图时,同样的碎片在以希特勒为标记的那场战争之后充斥世界充斥历史。破碎的文化空间与破碎的物质世界正好同构,而二战后的文学也就在这双重破碎的挤压下走向边缘,走向流浪。这种文学景观就其人物形象而言可称之为局外人,就其心态和状态而言则可描述为在路上。
在法国存在主义作家加缪推出他那部著名小说《局外人》之后,人们对主人公莫尔索这一局外人形象感到惊异之余,忽略了这个形象就其象征而言的两个关键的文化心理渊源,即卡夫卡小说和希特勒的战争。作为一种审美心理的延续,局外人形象几乎就是卡夫卡笔下的主人公们的主题变奏。这种连续性不仅在性格特征上有迹可寻,即便在社会身份上也基于相同的小职员角色。自从契诃夫小说问世以后,人们对这类小人物形象已经很不陌生了;但卡夫卡的天才在于他能将这类形象经由甲壳虫那样的变型赋予永世常存的形而上意味;而加缪的不同凡响则在于:他虽然没有卡夫卡那种先知般的睿智,但他却具有卡夫卡不曾具有的激情和勇气。卡夫卡的才具是契诃夫所无法比肩的,但卡夫卡的怯懦却与契诃夫笔下的小公务员相去不远;相反,加缪的才华没能遮掩卡夫卡的光芒,当其敏锐的触觉却并没有从卡夫卡的高度降落到契诃夫那种精致考究的平实。加缪经由对西绪弗斯神话故事的天才阐释,将卡夫卡对命运的洞见变成一种以接受命运为前提的对命运的挑战。或者说,加缪接受了卡夫卡预言的命运,但不接受卡夫卡将生存展示为甲壳虫的方式。他不否认象征着命运的石头最终是要滚下去的,但他却看到了西绪弗斯照样将石头推上山的那一面。如果说生命的结果乃是那块下山的石头,那么生命的意义却未必一定随着结果一起滚下山去。同样面对着莫名的审判,但加缪的局外人却以局外人特有的冷漠使审判者连同忏悔牧师一起失去审判的尊严和裸露牧师的虚伪。如果说卡夫卡的甲壳虫所发现的是生存的被抛状态,那么加缪的局外人则基于被抛者的立场揭示出世界的荒谬;也就是说,加缪将整个荒谬的世界从被抛者那里抛了出去,从而,使变成甲壳虫的格里高利站起来成为局外人。
基于这种局外人立场,《局外人》中的莫尔索虽然依旧如同卡夫卡人物那样是一个小职员,却不再是契诃夫笔下的小公务员。一种生存状态的边缘性非但没有在精神上将局外人置于死地,反而使之获得一种旁观者的清醒和超脱。加缪的这位主人公就此确立出一种局外人的立场和目光,或者说,一种局外人的生存状态和生存基点。在此尽管依然为命运和世界之荒谬性所重重围困,但一双局外人的眼睛却在这黑暗重围中点亮了存在的烛光。烛光所至,照出人们习以为常的世界的种种不正常和丑陋虚假连同滑稽可笑。从养老院到法庭,从法官到牧师,人们一起作假,共同清除不作假的异类。不过,人们可以戴上法律的面具将局外人从肉体上消灭,但他们却无法改变使他们感到尴尬难堪不知所措的局外人立场和局外人目光。无论他们在法庭上如何循循善诱,局外人一口咬定,他之所以扣动板机,仅仅是因为中午的阳光。局外人拒绝向人们提供他们所期待的供词和回答。他如同一个天外来客一样基于一个与常人截然不同的世界。面对母亲的死亡,他拒绝悲伤;面对法律的审判,他拒绝认同;最后面对装模作样的牧师,他拒绝忏悔。他不仅拒绝尘世,也拒绝天国。
局外人在世界在命运跟前表示出的这种拒绝,扬弃了卡夫卡那种格里高利式的顺从和听命。尽管拒绝顺从在骨子里同样无奈,但拒绝使局外人获得了曾被格里高利形象遗弃的那个存在的维度,这个维度使局外人以人的形象而不再以虫的模样站立起来,从而显示出一种没有英雄主义色彩的英雄气概。如果说英雄是一种文化处在浪漫的青春时代的人文主义命名,那么这种命名在文化没落的年代却变得极其可疑,因为英雄在这种年代不再是唐·吉诃德或者浮士德乃至齐格飞,而是战争工具或诛杀异类的屠夫和刽子手。这种英雄在卡夫卡小说中由押解约瑟夫·K的两名看守和格里高利的父母及其他亲人扮演,在契诃夫的小说中则表现为小公务员的恐惧对象诸如那位将军之类。而事实上,人物造型一旦发生了这样的变质,英雄已经丧失了原有的人文意味从而消解于某种残酷的现实,就好比人们无法将希特勒如同称呼齐格飞那样誉为英雄一样,任何消灭异己追杀异类的行为一旦被颂扬为英雄主义背后都有残忍和阴险的动机。在这样的相残面前,英雄主义的可能性自然而然地落到了局外人身上。
作为一个英雄,局外人毋庸置疑地丧失了当年唐·吉诃德的稚气和抗争热情,但他具有唐·吉诃德所没有的清醒和冷静。唐·吉诃德走向风车是因为他什么都不知道,局外人敢于一个人面对整个世界是由于他的洞若观火。在此,与勇气相辅相成的不是激情,而是孤独,局外人英勇地一个人面对世界不是由于滚烫的血液或者浪漫的理想,而是因为彻底的孤独。这种孤独的彻底性在于终极的无奈和清晰透明的绝望。局外人不仅意识到自己是偶然被抛的,而且发现他被抛到这个世界上之后无法找到自己的位置。基于自身的这种被抛,他对作为子宫象征的母亲表示冷漠;而出于无以居家的边缘者的绝望,他漠视世界漠视自己;最后在无可慰籍的孤独中一面走向死亡,一面诀别天国。与世界的破碎相应,局外人悬置了自身的孤独,从而以冷漠而不凭借什么浪漫激情杜绝了妥协的可能。正如希特勒努力征服世界那样,局外人以不努力的方式竭力与世界保持距离。或许是因为意志的全面崩溃,加缪在局外人形象上表示出了一种不屈不挠的孤独。这种孤独虽然是边缘的局外的,但却绝不是象当年某些俄罗斯文学人物那样是多余的。
就一种被抛状态而言,多余人是局外人的某种雏形。多余人如同局外人一样,也是因为被抛而导致生存上的边缘性。但与局外人不同的是,多余人没有站在被抛者的立场同时将世界抛出去,而是站在一个急剧变动的社会跟前不知所措。即便就其被抛而言,多余人的被抛也不是缘自形而上的存在性失落,而是很不幸地与一个时代擦肩而过。存在问题在多余人面前似乎并不显得如何紧迫,相反,他们有的是贵族的悠闲,以致奥勃洛摩夫那样的瞌睡虫成了他们最有意味的代表。西方文化携带着日益增长的文明力量经由开明君主彼得大帝之手扑向俄罗斯大地,并且首先覆盖了彼得堡和莫斯科那样的都市连同整个上流社会,致使俄罗斯文化最终不是以文化本身的活力而是借助一场同样来自西方的革命作出了变相的反应。这种无可理喻不可思议的文化冲撞,挤压出了这批多余人形象。他们站在俄罗斯上流社会和苏联十月革命的隙缝间收购死灵魂。然而,如果说革命前的贵族是奥勃洛摩夫式的,那么革命后的贵族却焕发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文化青春,以致于形成一个光彩夺目的流亡文学连同流亡文化。说实在的,要不是十月革命,那些流亡作家和流亡艺术家说不定都是旧俄作家笔下的多余人。革命发掘了俄罗斯人民的热情,也造就了俄罗斯贵族的流亡文化。这场革命真正消灭的不过是一批无所事事却又总是踌躇满志的多余人形象。
然而,相形之下,局外人却不是多余的。正如文化的碰撞产生了多余人一样,文化的终结导致了局外人。作为这种终结的执行者,希特勒及其那场战争乃是局外人形象的历史催化剂。就这个意义而言,希特勒所践行的意志哲学与其说是一股新鲜的反传统思潮,不如说是整个欧洲文化行将没落的回光返照。超人,权力,强者……诸如此类锋芒毕露咄咄逼人的意念不管如何电闪雷鸣,总也显得牵强、生硬,仿佛一个输定了的赌徒在赌桌上作出的最后一搏。从意志哲学到希特勒,从希特勒到世界大战,整个过程如同一颗炸弹从制作到引爆,最后碎物纷扬。希特勒在结束一部文化历史的同时,粉碎了所有的浪漫主义幻想连同种种做梦的可能。塞万提斯,莎士比亚,拉伯雷,哥德,……所有在文化鼎盛时期曾经以其灼人的光芒成为历史标志的名字,在希特勒那场以意志为动力的战争中全部丧失了沁人心脾的芬芳。相反,曾经一度不为人理解的卡夫卡,在战后获得了惊人的声誉。与文化的终结相应,西方人变得成熟了,全然一副饱经风霜的深沉和冷漠。曾经在战争中不堪一击的法兰西民族,在战后不仅站起了加缪、萨特那样蜚声世界的作家,而且形成了一代被称之为荒诞派戏剧的流派。仿佛卡夫卡的深度经由希特勒的战争被传染给了法国人一样,法国作家在战后一起步就是有关人类命运的思考和对存在问题的探究。他们中很少有人仅仅出于祖国遭到入侵的愤怒或者对战争的人道主义情怀乃至对德国人的民族仇恨之类而写作,相反,他们在战争的废墟上所张扬的恰恰是德语作家卡夫卡所奠定的文学和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所阐释的存在论思想。他们或许在意识上对希特勒之战争不无仇恨,但他们在下意识里十分自觉而且不遗余力地继承了德语作家和德国思想家的文化遗产。即便是后来玛格丽特·杜拉那样的新小说派作家,在其名作《广岛之恋》中推出的核心情绪都是耐人寻味的故事:一个法国少女和一个德国士兵的一场恋爱。这个故事的象征意味表明:那场莫名其妙的战争不仅没有加深这两个民族的相互仇恨,反而促进了他们之间在文化精神上的某种契合。如果说,二战之前最具代表性的法国作家普鲁斯特以沉缅往事的方式讲述了一个存在者的忧心忡忡,那么二战之后法国作家不仅把这种忧虑加深到局外人的冷眼旁观,而且他们无一例外地将注意力集中到了自身的当下处境乃至整个人类的生存困境。这种当下性是如此地强烈,致使加缪在《鼠疫》中以一场瘟疫相当形而上地复制了一场战争,致使萨特不仅在《墙》中揭示被审判者自身的荒谬而且在《肮脏的手》中一语道破革命的真相,也致使尤奈斯库将当年纳粹的恐怖上升到《犀牛》那样的寓言故事,甚至致使后来的克洛德·西蒙在《弗兰德公路》中将一大片普鲁斯特式的回忆诉诸了一个色彩斑斓的共时性叙述结构。总之,由于希特勒的那场战争,人们已经不再有做梦的兴趣,因此,文学失去了以往的梦幻色彩,成了有关当下困境的种种讲说和描述。从此以后,当年诸如克尔凯廓尔那样的先行者得到了越来越亲切的认识和理解。
与法国文学从《追忆似水年华》走向《局外人》相应,英国文学完成了从哈代的怀旧经由艾略特的荒原向贝克特的《等待戈多》的过渡。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说D·H·劳伦斯对文明化历程的愤怒和抗议还仅仅是惊世骇俗,而詹姆斯·乔伊斯诉说的失落和迷惘又过于抒情和优雅,那么同样一个爱尔兰籍的作家贝克特则以其《等待戈多》一作与法国作家加缪互为映照,并且由于贝克特的这些剧作被人们归于法国荒诞派戏剧,以致人们在提到这位荒诞戏剧作家时往往忽略了他的籍贯和来历。因为《等待戈多》与其说是《荒原》的续篇,不如说是《局外人》的姐妹作。与《局外人》所揭示的生存边缘状态相应,《等待戈多》阐明了目的和意义之于历史之于个人的全然丧失。当年莎士比亚剧作中的种种自信和浪漫,在《等待戈多》那样的舞台上消失殆尽;无论是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缠绵悱恻,还是奥塞罗的嫉妒,李尔王的疯狂,麦克白斯的谋杀,抑或哈姆雷特深沉而高贵的思考和怀疑,在《等待戈多》一剧中全都变成一棵枯树很有象征意味地伫立在舞台上,既作为舞台背景,也作为有关历史的某种总结。当然,最有意味的是舞台上的主人公既不是国王也不是王子,而是两个来自维也纳街头的流浪汉;与当年的希特勒不同的是,这两个流浪汉既茫然于意志哲学,也不知道瓦格纳的音乐。他们的目光和头脑仿佛仅仅为他们的裤子和靴子所吸引,而他们的全部生存也不再有丝毫野心和梦想,只是一种可有可无的等待。作为等待者,他们从容不迫,不是因为他们等待的戈多肯定会来,而是由于戈多很可能根本就不存在,更是因为戈多来不来在他们已经无所谓,等待就是他们生存的全部内容。整个剧作是如此的透彻和震撼人心,以致于即便是希特勒那样的独裁者看了也会为自己的野心和意志感到荒唐可笑。希特勒不会想到,他的战争没能征服的欧洲人会在他早年的流浪生涯中发现他们共同的生存状态。
事实上,英国作家与法国作家一样,在战后并不将热情和思想倾注于战犯审判那样的政治事务,而是将目光转向了人类处境的关注和思考,这样的醒悟不仅见诸《等待戈多》,而且在戈尔丁的《蝇王》中也赫然可见。《蝇王》所讲的那个寓言故事虽然可以让人联想到纳粹的恐怖,但故事本身探究的却不是纳粹的罪行而是纳粹现象的人性根源。小说超越了具体的历史事件和历史环境,从而将纳粹式的恐怖诉诸了一场孩子们的游戏。从故事结构中人们可以依稀瞥见《鲁宾逊飘流记》的构架,但鲁宾逊的全部自信在此被演化成对人性的彻底不自信。同样是荒岛的背景,但不再是所谓文明人对蛮荒的开发,而是孩子们童稚之心的污染和失落。在此,孩子们中间对异类的指控和追杀不是以消灭犹太人的借口或者以清除反革命为名义,而就是赤裸裸地根植于一种人性的邪恶。格里高利是变成甲壳虫后才遭到追杀的,但在这场残酷而又发生在孩子中间的游戏里,甲壳虫式的异类不是自然出现的,而是被人为地制造和确认出来的。如果希特勒的虐犹可以追溯到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中对犹太人的歧视的话,那么《蝇王》中一群孩子对其中几个小伙伴的追杀却只能归因于人类的某种天性。按照这样的逻辑,人们就可以十分有把握地说,希特勒之所以邪恶不是因为他是希特勒,而因为他十分真实地开掘出了人类的某种本性,也即是说,人们可以在任何人身上发现这种希特勒式的阴影。在希特勒的战争将仇恨推向极致之后,人们一步跨越民族间的互相仇恨而看见了人类天性中的某种真相。由此,卡夫卡的《审判》和《变形记》在英国作家的笔下有了《蝇王》那样的翻版。战争的确教育了人民,但人民与其说赢得了战争,不如说看清了人性的本相,在欧洲,文学随着战争而长大了;文学不再是历史的梦幻,而变成了对人性的洞察和对人类处境的关照。
同样的深刻也见诸美国的战后文学。二战前的美国文学充塞着刘易斯和德莱塞那样巴尔扎克式的粗浅作家,鲜有些许真正具有20世纪深度和20世纪风格的大手笔,其中足以与乔伊斯和普鲁斯特相提并论的当推威廉·福克纳。这位与卡夫卡一样直到战后才受到普遍关注和格外尊敬的伟大作家,以其结构精美而风格沉郁的《喧哗与骚动》著称于世。与乔伊斯和普鲁斯特的追忆相近,福克纳展示给读者的是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悲悼。这种悲凉曾经作为历史的记忆见诸“Gone with the wind”,中文版译名为《飘》,其实更准确的汉译就是无可奈何花落去。相比于这部风行一时的畅销作品,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的深刻在于,小说全力聚焦于南方的没落。作为这种没落标记的南北战争一方面以道德的名义解放了黑奴,一方面又以北方的文明进程取代了南方的庄园文化。福克纳深切地感受到这种文明的喧哗和文化的衰败,从而将斯佳丽式的创业精神诉诸拉斯蒂涅式的杰出形象,将媚兰的贤淑诉诸凯蒂的放荡,将卫希丽的平庸诉诸班吉的先天性白痴,并且以这个白痴的感述意领了整个小说的叙事,由于正常人世界沉溺于生存竞争而导致疯狂,白痴的感觉反而获得了在气氛领略上的准确性。白痴形象的象征意味在多余人和局外人之间并且既具有甲壳虫那样的无奈和悲哀,又具有局外人那样的荒凉和冷漠。白痴形象所显示的那种独特的观照方式使福克纳成为美国文学史上极为鲜见的先知作家。他通过对美国南方没落过程中的洞察和哀挽作出了斯宾格勒式的历史预见。如果说当年麦尔维尔的《白鲸》表现了对命运的恐惧,那么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则显示了对命运的领略和接近于局外人那样的冷漠。
当然,尽管从《白鲸》到《喧哗与骚动》体现了非凡的深度,但美国文学的基调却是从马克·吐温到海明威。欧洲文化在青春时代的回忆和梦想,在美国文学中是由马克·吐温笔下的孩子们诉说的。他们从孩子的方式尝试了亚历山大的历险,使世界象当年展现在战马之奔驰中一样地展现在孩子们充满活力的足迹上。这种历险在历史向度上终结于淘金时代,在审美向度上则为海明威所继承。作为小说自叙性人物,海明威来自马克·吐温笔下的世界。或者说,那些孩子长大后,变成了年轻力壮精力充沛的海明威。我将海明威命名为文化牛仔,他像唐·吉诃德一样冲进世界,不是握着长矛,而是带着钢笔。他在大萧条时期成了迷惘的一代,还说“太阳照常升起”;他在战争将临之际,宣告“永别了,武器”;战争结束之后,他又扮演过一个和大海搏斗过的老人;《老人与海》仿佛是对自身归宿的一个预告,最后一声枪响,六十多岁的海明威像个孩子一样死在自己的猎枪下。海明威终其一生都是一个孩子,他越深沉就越孩子气。他像孩子一样地热衷于斗牛、打猎,像孩子一样地参战,像孩子一样与女人周旋,像孩子一样地写作,最后归结于孩子似的自杀。他那简明的写作风格与其说出自记者的职业习惯,不如说是缘自他那好动的牛仔脾性。从马克·吐温那些孩子的历险到海明威这个牛仔的生命方式,象征性地概括了美国和美国人,当然,是不无稚气充满活力的美国人,他们代表着美国的梦想和美国的青春。自由的土地培育了他们冒险的性格,即便是一场战争,在他们看来都像是一个游戏,至多是一场淘金。福克纳式的悲观主义离我们十分遥远,海明威的小说才是他们的形象的写照。他们好动而不善思索,他们情愿选择唐·吉诃德的莽撞也不愿倾听哈姆雷特的深沉,因为前者简单明了,后者深奥复杂。正如海明威很合他们的脾性一样,在二战中,巴顿成了美国青年军人的偶像。二者一样地好动,一样地粗鲁,一样地孩子气,一样地吵吵嚷嚷。
按说,这种吵吵嚷嚷在文学上很难获得深度模式,但偏偏是这样的喧哗,一种在福克纳笔下无意义的喧哗,跑到凯鲁亚克的《在路上》突然显示出了一种特有的意味深长。《在路上》与其说是一部小说,不如说是一台摇滚,或者说一个没完没了的颠簸。当年维也纳街头那种凄凉的流浪,在此成了一次又一次热热闹闹的远足。希特勒当年的流浪汉好比凡高画面上的星夜空,而凯鲁亚克的在路上则宛如美国七月四日的盛大庆典。一伙青年人以蓬勃的青春和生命将他们自己从都市放逐到高速公路上不停地飞驰奔波。这种吵吵嚷嚷的流浪当然不带有吉普赛大蓬车式的浪漫,而是力图散发内心深处的寂寞和孤独。由于日益增长的文明逐渐物化了那片自由的土地,所以使这伙孩子们不再以汤姆·索耶式的历险而是以没完没了的奔波逃离象征物化的文明的都市,找回那份心灵的自由。高速公路在他们的奔驰流浪下仿佛变成了一种文化娱乐设施,或者说坚硬的文明因为这样的流浪而迸发了精神的火花,闪烁在流浪者的车轮和沥青路面的不断磨擦之中。一种与文明社会相应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因为这种流浪的冲击而遭到怀疑,逐渐走向解体。一时间,不是循规蹈矩,而是疯疯癫癫成了美国青年的流行风尚。人们把他们叫作垮掉的一代,以对应于《太阳照常升起》时代的迷惘。
正如福克纳标记着美国文学的一个高峰一样,凯鲁亚克的《在路上》奠定了美国战后文学的基调。与《局外人》、《等待戈多》一样,《在路上》标画出文学之于世界之于历史的当下观照。这是继卡夫卡之后的三块文学里程碑,经由这些里程碑,卡夫卡笔下的格里高利和土地测量员走进法语文学成为局外人,走进英语世界成为等待戈多的流浪汉,走进美国文学成为在路上的所谓垮掉的一代。相对于局外人的冷漠,在路上的美国青年是疯狂的;当年惠特曼式的浪漫激情算得上气势磅礴了,不想这种激情在金斯堡的诗行中进一步焕发出《嚎叫》式的耀眼光炽。凯鲁亚克和金斯堡他们将如同希特勒在战争中释放的巨大能量一股脑儿地倾注在小说和诗歌中,最后经由鲍勃·迪伦开启出一个摇滚时代。由此,卡夫卡--希特勒以后的文学呈现出一个颇具节奏感的形象区域:先是甲壳虫式的绝望,再是局外人式的冷漠,经由等待戈多式的沉默,最后在垮掉的一代中突然爆发,充沛的生命激情至此犹如火山爆发一般,将抑郁的连同孤独的身影一起冲上天空。
标签:局外人论文; 多余人论文; 希特勒论文; 在路上论文; 卡夫卡论文; 喧哗与骚动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欧美文化论文; 等待戈多论文; 海明威论文; 蝇王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