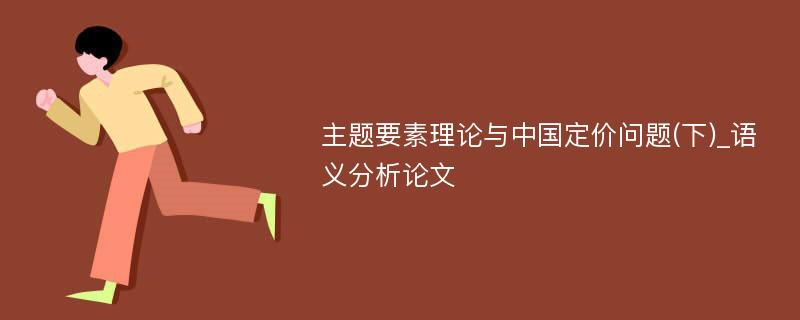
题元理论与汉语配价问题(之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语论文,之二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3.题元理论关于动词的一些研究
3.1动名之间的复杂关系
3.1.1语法结构中哪些名词是“价语”
汉语动名配价关系讨论得更多的是动词性成分。具体说这又有两个相反的观察角度:一方面是怎么从动词看名词;另一方面是怎么从名词看动词。前者指的是,某个结构中有多少个和什么样的配价名词,实际上是作为结构核心的动词(或广义谓词)决定的。前面讨论汉语一共有多少配价名词类和某个具体语义类如何定义有困难,说到底也就是动词比较复杂所致。所以汉语主要就是解决如何从动词入手确定不同的结构中配价名词的数量和类别。目前讨论较多的大致有这样几个问题:首先,哪些名词类型在哪些动词和结构的条件下可以确定为配价名词,哪些名词类型需要排除?其次,在可能确定为配价的名词中根据动词的性质是不是还有核心名词和外围名词、必有名词与可选名词等区别?再者,在可能看作是核心名词或必有名词的配价成分中,相对于动词有没有共现限制、出现条件等的差异?
应该承认配价理论也很注意这类问题,因为要定出某个动词是几价的就不能不考虑动词支配名词的不同性质。(注:关于这一点的表述略有不同。比如有人说主要根据结构框架,有人说主要根据词义搭配。参看韩万衡(1997)。)举例说,德语“Mich friert (我冷)”可出现一个名词,“Ich wohne dort(我住那儿)”可出现两个名词,虽然在传统语法看来“frieren”和“wohnen ”都是不及物动词,但由于二者联系的名词数量不同,从配价角度就可分别定为一价动词和二价动词。又如德语动词“kaufen(买)”可以在结构中与“买者/卖者/货物/价格/方式/时间/地点”等若干名词发生关系,但由于只有“买者(第1格施事名词)”和“货物(第4格受事名词)”是结构上和语义上同时不可缺少的“必有成分”,其他名词都是可以删略或不能独立与动词搭配的“可有成分”和“说明成分”,因此“kaufen”仍可算作二价动词。(注:也有人从语义上考虑把“kaufen”定为4价代词。不过其中仍然是2个必有配价,2个可有配价。 参考韩万衡(1997)。当然再进一步说,虽然“wohnen”类和“kaufen”类都是二价动词,但由于后者可以联系“可有名词”的数量和类型较前者多,各自可能构造的现实句型也就不一样,比如前者只能有一种句型,后者就可以有多种句型。)这套程序当然不是不能拿到汉语中来用,现在有人就建议采用类似的“删略法(elimination)”, 即根据简单动词完整结构中的名词能不能彻底删除确定动词的价;或采用“定性法(determination)”, 即硬性规定与动词搭配的名词是或不是“必有成分(或称核心成分)”来确定动词的价。但不难发现,这套方法和概念对德语可能够用了,但用来说明汉语配价名词的数量、类型和动名结构形式就不一定很灵验。比如本文(2 )的例子就可能有下面相当多的变化形式:
(32)今天(时间)午饭(受事)每人(施事)食堂(处所)五块钱(工具)吃(V)一份(数量)快餐(方式)
→A.今天吃快餐/午饭吃快餐/食堂吃快餐/每人吃一份/五块钱吃一份/午饭吃了/吃了
→B.今天吃了/午饭吃了/食堂吃了/我们吃了/吃午饭/吃食堂/吃快餐/吃一份/吃五块钱
→C./今天午饭吃食堂(-五块钱/一份/快餐/)/每人快餐吃一份(-五块钱/午饭/食堂)
(32A)说明如根据“删略可能性”来确定动词支配的配价名词,汉语名词的删略常常是任意的,即使只剩下动词也能构成自由结构;(32B)说明如根据“搭配合格性”来确定动词联系的必有名词,汉语动词差不多与任何类别的名词都可以自由搭配;(32C )说明如根据“语义选择性”来确定配价名词等级,有时看起来语义上不重要的名词能与动词共现,而语义上重要的名词反倒不能与动词在同一结构共现。因为汉语有这样一些特点,所以简单套用德语的办法来确定汉语中哪些名词是与动词联系的配价成分事实上一定会遇到困难。
3.1.2带介词的名词是否算题元
在类似问题上题元理论的研究也要深入些,或者说更多考虑到了各种语言中动名支配关系的复杂性。首先的问题是根据什么说某个名词是动词的题元,而另外某个名词不是题元。目前对这个问题的普遍看法是,虽然一般说动名结构形式的合格性或动名语义联系的重要性都可以作为确定题元的依据,但二者毕竟在很多时候并不一致,因此确定题元就应首先把动词的语义选择和句法选择区别开。Grimshaw(1979)曾论证很多语言的动词在语义上能带什么和在句法上能带什么是两回事。Chomsky(1986)用“S选择(S-select)”和“C选择(C-select )”来定义这两种关系。概括说就是动词与名词的关系可以有两种性质:一种是动词与名词的语义关联,即“题元角色”;另一种是动词与名词的结构形式,即通常说的“子语类化特征”。(注:暂不考虑动词带从句的情况。例如动词“说服”,语义上除主语名词题元外,还需要一个“目标/对象(Goal)名词题元”和一个“命题(proposition)”, 即“说服什么人干什么”;句法上分别选择一个NP(什么人)和一个S/IP(干什么)来担任宾语和兼语小句。这样如果定义“说服”为二价动词当然在句法和语义上也会不一致。)这两种关系有时一致,有时可能并不一致。例如英语的动词“melt”,在句法上既可以选择名词“ice”在前作主语(The ice melted),(注:主语名词严格说不是由动词选择的,但也可以认为句子结构必须含有主语(Chomsky 1982)。)也可以选择它在后作宾语(Bill melted the ice”,但语义上“ice”作为该动词的“Theme(客体)”题元却是不变的。
如果承认动词对名词的句法选择和语义选择可能不一致,那么根据动词来确定哪个或哪些名词是题元,就无非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只考虑句法选择,即主语名词和其它名词(也包括介词短语中的名词)是不是题元,要依靠一套句法程序来确认,比如只有能直接受动词支配(作动词宾语)的名词和某些强制介词结构中的名词才是真性题元,其他名词(包括某些非强制介词结构中的名词)就不算。 例如下句中只有“thecar (那辆车)”才是题元名词:
(33)John tOOk the car from Mary for 3000 doLLars 约翰花了3000美元把那辆车从玛丽那儿要了来
另一种是只考虑语义选择,即不妨把能够出现在动词结构中又与动词具有某种语义关系的名词都看作题元,而不管有没有介词。因为用不用介词是语法问题,不是语义问题。用生成语法的话说,介词只指派格,动词才指派题元。以上两种方法得到的结果不一定相同,比如(33)的动词“take(拿)”,句法上可以看作二元动词(V+施事/客体),另有若干附加语(adjunct), 而语义上则可以干脆说是四元或更多元的动词(V+施事/客体/来源/工具等)。
3.1.3必有题元和可有题元
其次的问题是要不要分出“必有(必要)题元”和“可有(可选)题元”。因为即使把所有与动词有关系的名词都看作题元,也需要在其中划分等级。这种题元语义等级一般说主要是根据动名语义关系的紧密程度确定的。目前一般的看法是,如果完全从语义概念考虑,任何动作状态都一定发生在某一时间和空间,这样动词的“时间”题元和“处所”题元(注:表示运动终点的处所(即Goal)除外,因为它与一般说的表示事件发生所在的处所不同。前者明显受到动词的支配和影响。)在句子中不予表达也不要紧,可以不看作“必有题元”。但因为并不是每个动作都有“施事”或“受事”,所以不是每个动作状态都联系的“施事”或“受事”类题元反而就应该是某些动词的“必有题元”。至于动作的“工具”、“方式”等题元则介乎两类题元之间,要看具体动词的不同语义要求。按照这个思路,宽泛一些说就是把所有题元分出需要或可能列入某类动词的题元表和不需要或不可能列入某类动词的题元表几个大类;具体一些说就要一个一个动词分别列出自己的题元表(假如能对前述一共有多少题元和怎么定义题元达成共识的话)。例如“jump(跳)”虽然可以带直接宾语,如“jump a fence(跳过篱笆)”,但一定不会有“受事”,“受事”就不在其题元表上。但“跳”有没有“施事”则不一定,像“the children were jumping (孩子在跳)”带“施事”,“the typewriter jumps(打字机跳漏字)”就不带“施事”。再如同样是动词后边表示“度量”的名词:
(34)A.He swam 130 meters他游了130米
B.He weighs130 pounds他重130磅
C.This TV costs 130 dollars电视值130元
(34)中动词后边都带度量名词,但有的在语义上必须带,因此是题元,有的就不一定。可见要建立这种题元表实际上更多属于“词汇语义”范畴,即它与词库中动名词语义项搭配的要求相关。应该说汉语研究中也有人根据不同动词把名词分出“环境价(situational role)”、“外围价(circumstantial role)”等,差不多就是类似的作法。
与此相关的是怎么处理“不出现”的题元。因为就算根据名词的语义性质或指派程序都可以定出“必有题元”,还必须考虑被认定的“动词V”的“必有题元T”在“句子结构S”中是否一定要求出现, 或者说定出的题元是否都始终与某种结构形式相联系。“不出现”的题元中最受注意的就是主语和宾语。这方面各种语言的句法表现是很不相同的。比如拉丁语、澳州Dyirbal 语等语言的动词与名词的联系有明显的强制性,这些语言的主语和宾语名词作为题元绝不能省略;英语在主谓一致(agreement)和动宾黏合(bound)方面虽然比德语等弱一些,但主语宾语也大多不能任意省略或不出现。对这些语言的所谓“必有题元”当然用“删除法”来判定还有点用。但另有很多语言的动词其实只是“可以”而非“必须”有主语和宾语。如西班牙语、意大利语,也包括汉语,都可以省略主语名词,有人称为“删略型空主语(pro-drop)”;另外像斐济Fijian语等,几乎所有及物动词都不一定带上宾语名词,汉语也属这一类,即存在“自由型空宾语(free empty object)”。 对这些语言要根据“删除”来确认句法上有所体现的“必有题元”根本就办不到,这对所谓“必有题元”,甚至是不是存在动词的题元都是一种威胁。所以要解决这些语言中题元位置是否出现题元名词和出现什么题元名词的问题,就需要换一种角度来考虑了。
3.1.4内部论元与外部论元
与上面问题相联系的再一个问题就是,是否所有的题元都可以看作是由动词硬性指派的?对此有人说是,有人说不是。Williams(1981)提出把所有句法上可认定的题元分成“内部论元”和“外部论元”两大类。内部论元大致就是动词子语类成分,或者说是由动词V 作为“指派语(assignor/donor)”指派的名词; 外部论元通常指动词短语VP投射之外的名词,或者说是由VP整体指派(注:另一种定义是“主语”由作为句子S中心语的INFL(即动词的形态形式)指派。参看Chomsky(1981)和徐烈炯(1988)。)的题元。外部论元只有一个,一般指施事性主语名词;而内部论元可以有多个,包括宾语名词(直接内部论元)和结构中其它名词以及非施事主语名词(间接内部论元)。例如下面的结构中可以这样标注外部论元和内部论元:
(35)see看(A.施事,Th.客体)下面加横线表示外部论元
在这个问题上也存在争论:有一种意见认为可以取消外部论元和内部论元这条界限。理由是像主语、宾语这样的名词在句法地位上应该没有太大区别。Koopman &Sportiche(1988 )就提出把主语名词也处理为由单词语类(比如V)指派, 具体作法是假设施事性主语名词原先也是在VP投射之内,后来才从VP的Spec (某种介词短语位置)移至IP 的Spec(主语位置)。但WiLLiams(1994)第4 章提出了一些理由批评移位分析法,证明此举用处不大。此外WiLLiams还提出除了动词之外,其它语类也可以指派题元。
3.1.5题元指派的方向
还有一个问题是题元的指派有没有方向性。目前很多人坚持认为题元的指派有方向性(theta-role aSSignment directionality), 即有些语言中动词把题元派往其右边的成分,而有些语言中动词把题元派往它左边的成分。题元指派方向的不同可以造成该语言语序的不同。有些研究题元的学者还认为可以以此解释汉语某些语序现象。 Travis (1984)假设汉语动词把题元派往右边,所以凡充当题元角色的名词可以位于动词之后,而不充当题元角色的名词不能出现在动词之后只能位于动词之前。这样就可以说明下面(36A)和(36B)的区别。例如:
(36)A.他跳到桌子上(“桌子上”表示运动的终点目标,是题元)
B.他在桌子上跳(“桌子上”表示事件发生的地点,不是题元)
李艳惠(Li,1985)却认为汉语动词把题元派往左边。她把汉语看作“主—宾—动语言”,以此说明为什么汉语对出现在右边的名词数量有限制。不管她们谁对,可以看到大家都在寻找动词与题元名词之间关系的规律性。
3.2动词的分类
3.2.1怎样根据题元给动词分类
汉语动名配价关系中动词性成分的讨论还关注另一个问题:既然结构中配价名词的数量和类型是由动词(或广义的谓词)的不同性质决定的,那么能不能反过来从名词看动词。具体说就是如何根据特定结构中名词的种种不同,比如是不是配价名词,是不是配价名词中的必有名词,又是必有名词中的哪种语义类名词等等,来确定不同结构中动词的性质和类别。目前汉语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有两种作法:一种是根据“价量”或者“价形”对动词进行分类,即把动词的类与动名搭配形式和句型结构分析相结合。比如先建立一价动词、二价动词等大类;大类动词内部再区分简单二价(如“我洗衣服”)、套合二价(如“水我浇了花/花我浇了水”)、准二价、准三价(如“我为你服务”、“我跟他打招呼”)等次类;简单二价动词内部可再区分二价X动词(施事/受事, 如“我买书”)、二价Y动词(施事/终点,如“我去上海”)等次类。 还有一种是根据“价类”或者“价义”对动词分类,即把动词的类与动名的特定意义和特殊句式分析相结合。比如在二价动词内部分成“处置义二价动词”、“存在义二价动词”、“破损义二价动词”等等。像汉语静态存在句“门口贴着一幅画/桌上放着一摞书”等中动词(贴/放)的类就可以说是表示“存在(附着)义”的二价动词。
3.2.2根据“价数”给动词分类
欧洲配价理论在动词分类上实际上主要是一种偏重价量或价形的研究。其中法语配价研究走的更是比较极端的路子。例如GroSS等(1975)开始进行的《法语动词配价词典》的编写工作就是根据所谓“足句(completed sentence)”的要求,把几乎所有动词前后可能出现的成分(不限于名词)都看作是动词的“配价/依存成分( dependency components)”, 然后再用罗列出来的这种搭配特征来区别各个动词的不同句法表现。不过这样得到的结果只是一套反映动词全部区别特征的资料性(informative)“信息词典”。(注: 关于法国配价语法研究的情况,可参看M.GroSS ( 1975 ) Methodes en Syntaxe ,Regime des Constructions .Paris:HermaNN.另外刘涌泉、 乔毅《应用语言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1年)和郑定欧“法国句法配价20年”(《现代汉语配价语法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也有介绍和讨论。)德语配价研究给动词分类要抽象些,比如《德语动词配价小词典》里就只根据必有名词的数量定出某个动词几价,然后在同价动词内部再根据选择名词类的情况区别不同格式。但这种工作的结果也只是编写出供语言教学用的“教学词典”。(注:事实上德国学者也认为德语配价研究目前的成果就是编写出了“动词配价词典”并应用于对外德语教学。这种配价词典的用例取自计算机处理的语料库,书后附有归纳出来的配价句型表。参看袁杰(1991),韩万衡(1997)。)由于这些对动词的分类基本上是一种基于具体动词搭配形式的相对琐碎的词汇性工作,所以不能反映出比较系统的动词的类的特性。汉语配价研究中也有人做这种偏重价量分析的工作,包括也编出了基于动名搭配格式的《现代汉语动词大词典》(林杏光等,1995)一类的书。但如果说法语、德语动词的这种分类描写基本上就能反映动词的结构类的话,汉语用同样的方法就显然不够用了。因为汉语中即使是同价动词,即使一一列出了可能的各种动名搭配格式,仍然不一定能反映汉语大量的特殊句式的动词类别,像“把字句”、“存在句”等就是这样。比如当我们说包含处所名词的二价和三价动词可能构成“存在句”时,并不足以揭示存在句动词的特性。例如为什么不是所有的二价和三价动词或包含处所名词的动词结构一定就能构成存在句(在邮局里寄信/*邮局里 寄着信;箭射在靶子上/*靶子上射着箭), 就不是仅靠分出几价动词或只讲动名搭配形式能够说明的。
3.2.3根据“价义”给动词分类
题元理论对动词的研究应该说就是偏重上述汉语动词分类研究的后者,即走“价类”或“价义”分析的路子,也就是更重视按照动名的意义关系给动词分类。
从题元意义关系的角度给动词分类的工作Levin(1985 )做得比较仔细。她主张把动词分成几个类,同类的动词要求在句子结构中出现相同的题元,而且这些题元有相同的句法表现。其中有的类别的界限很清楚。例如:
(37)come(来)/descend(下来)/ ascend(上来)/faLL(落)
(38)bring(带来)/take(拿去)/raise(提高)/lower (降低)
(37)类动词都要求有一个名词,语义上作为动作的“客体”,在语法上充当主语。(38)类动词还要求另一个语义上的“施事”名词,“施事”作主语,而“客体”作宾语。这种类别还可以分得更细。比如以下几类动词都可以带三个题元(有些题元体现为介词词组),而各类动词所带的题元不同;即使所带的题元相同,也还有更细致的语义差别和句法形式的差别。Levin著作中没有给这些动词的类命名, 我们为了叙述方便加上名称。例如:
(39)放置类:put(放)/place(置)/stand(站)/sit(坐)/insert(插入)
(40)赠送类:give(给)/send(遣送)/lend(借出)/seLL(卖出)
(41)接触类:attach(附)/bolt(闩)/glue(粘)/nail(钉)
(42)创造类:build(造)/carve(刻)/weave (织)/bake(烤)
从语义上看这几类动词有所区别:放置类动词和赠送类动词都有个语义上属于“客体”的名词,但放置类动词的“客体”有明显的位置移动,而赠送类动词的“客体”的移位可能只是较为抽象的所有权的变化。接触类动词的“客体”往往没有明显的位移。而创造类的动作都会产生一种“结果”。同时这几类动词的的句法表现也不尽相同:赠送类动词和创造类动词可以用与格(dative)结构,也可以用斜格(oblique )结构;其他两类则不可以。Levin 认为动词分类工作在语法理论上的价值是不必列出一个个词项的题元,只须把它们归入某一类,就可以知道其题元类别和句法特点。当然实际情况可能更复杂些,Levin也注意到,有时动词之间的区别不能用题元归类加以穷尽,而且同一类的动词也还难免有个别的特点。
JackendoFF(1987/1990)后来提出的“概念结构”是按照动名意义关系对动词进行分类的又一种方案。他认为动词的特性可以表现为基于词库建立一种概念结构,像句法结构层面包含名词、代词等语类一样,概念结构也有相应的“事物(Thing)”,“事件(Event)”,“动作(Action)”,“状态(State)”,“地点(Place )”, “性质(Property)”,“数量(Amount)”等概念类,这些概念要素要放到动词结构中才能确定,进而再把由此确认的题元角色映射到句法层面,得到所谓句法体现。例如下面两个例句在句法上结构相同,但在意义上却有所不同,就是因为动词分别属于不同的概念结构类。比较:
(43)A.John touched the bOOdcase约翰碰到了书柜
B.BiLL hit the car(with a crash)比尔撞到了车子
(43B)中有一种语义关系同(43A),只表示“动作和事件”,即“施事(Bill)”通过动作涉及“受事(the car)”,“a crash”可看作“工具”;但另一种语义则不同于(43A), 而表示“位置和状态”,即“客体(Bill )”的位置发生变化到达“终点( the car)”,“a crash”是“结果”。 这两种题元关系就反映了不同的动词概念结构:前者称为“事件层结构(action tier)”, 其中应包括“施事”和“受事”;后者则称为“状态层结构(thematic tier)”, 其中还应包括“客体”和“终点”(注:顾阳(1994)对此有过介绍。另参看徐烈炯(1990)。)。
3.2.4几个特殊的动词类别
有几类动词在题元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首先是大家注意到某种主宾语自由的结构中的动词。这种动词传统上都归入不及物动词,但该类结构中的名词毋需移位操作就可以改变在结构中当主语或宾语的句法位置,同时仍保持受动词指派的题元角色不变。例如:
(44)A.(BBLL)broke the window (比尔)打破了窗户( the window 在主动结构中作宾语)
B.The window was broken窗户被打破了(the window 在被动结构中作主语)
C.The window broke窗户打破了(the window在主动结构中作主语)
(44)中的名词“the window”从动名语义关系看始终是“客体”,但无论在被动结构(B)还是在主动结构(C)中却都可以作主语;同时还可以作另一种主动结构(A )的宾语。 这类动词在英语中很多, 如“break(打破)/close(关)/drop(落)/freeze(冰冻)/melt(融化)/open (开)/turn (转)”等等。
根据这种情况, 从Perlmutter(1978)起,大家都倾向于把传统的不及物动词分成两类,分别称为“非作格动词(unergative verb )”和“非役格动词(unaccusative verb)”。非作格动词指“ cry(哭)/run(跑)”类一般的不及物动词,从语义上说该类动词只指派一个“施事”题元;而从句法上说这个题元只能作主语。而非役格动词的共同点是都只指派一个“客体”题元, 但内部又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如“ die (死)/aPPear(出现)/aRRive(到达)/sit(坐)”等动词, 该小类动词的“客体”题元的结构位置类似非作格动词,即只能当主语;另一种就是刚才举例提到的那些特殊不及物动词,该小类动词的“客体”题元除了可以当主语(此时不出现宾语名词,如(44C)), 还可以当宾语(此时另有主语,如(44A))。 上面说的几种情况在句法形式和语义关系上互相交叉,也正因为这些题元结构的情况给动词分类带来很多新的问题,才引起越来越多的人的兴趣和重视。
RaPPaPPrt & Levin(1988)认为可以这样概括, 即非作格动词只有外部论元,没有内部论元;而非役格动词只有内部论元,没有外部论元,即使“客体”作主语也是一种特殊的内部论元。也有人想把非役格动词的题元现象统一作句法操作。比如Bowers(1988)就提出两种非役格动词都可以解释为内部题元名词的“提升(raising)”, 即这些动词本身不能指派外部题元,但当结构未出现其它主语名词时,受动词指派的唯一“客体”题元就提升作主语。(注:这一小节的问题可参看顾阳(1994/1996)的详细介绍。)
从类似的角度进行观察, Grimshaw ( 1990 )提出“心理动词(psych-verb)”也应该没有外部题元,并以此来解释“fear (害怕 )/frighten(恐吓)”这对动词的对立。这两个动词虽然都联系两个题元角色(感受者Y,客体X),而且从题元等级的显著性顺序看(见本文第5页),“感受者”应位于“客体”之前,但为什么frighten 结构只能“客体”当主语,fear结构只能“感受者”当主语,这是因为fear结构表现简单事件,只包含状态,而frighten结构表现复杂事件,必须包含活动和状态,后者即必须有两个或以上的题元参与才足以表示诸如“X对Y的影响使Y处于某种状态”的语义关系。Grimshaw 还据此给各类动词总结出以下用多层括弧表示的题元表,其中嵌得越深的题元越不显著,而外部论元的左边只能有一个括弧。见下表:
(45)A.Transitive agentive(施事及物动词)
(x:Agent (y:Theme))
B.Ditranstive(双宾动词)
(x:Agent(y:Goal(z:Theme)))
C.Unergative(非作格动词)
(x:Agent)
D.Psychological state(心理状态动词)
(x:Exp.(y:Theme))
E.Psychological causative(心理役使动词)
(x:Agent(y:Exp.))
F.Psychological agentive(心理施事动词)
(x:Agent(y:Exp.))
G.Unaccusative(非役使动词)
(x:Theme)
4.运用题元理论研究汉语语法问题
上面我们针对汉语配价研究中较多关注的关于名词和动词的一些问题介绍和评论了题元理论的相关讨论意见。不过话说回来,这些讨论毕竟大多是基于英语语料的,而从汉语研究的角度或许大家更关心的是,白猫黑猫能不能抓住老鼠,即题元理论的这一套能不能推广到汉语?我们当然不能指望靠题元理论来解决汉语的所有问题。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即与配价理论比较起来,在与汉语的实际结合方面也是题元理论做的工作更多,而且事实上已经有了很多以汉语为研究对象的具体成果。这对汉语研究当然就有更直接的借鉴价值。
单从汉语这头看,近年国内把“配价”应用于汉语的研究确实也很多。除了研究动词和名词的配价性质,也开始有人用配价处理汉语特殊句式等复杂现象。但应该指出,如果说汉语这类工作也是“配价”研究的话,那基本上是汉语独立的发展,与“配价理论”其实并没有太多关系。因为至少到现在为止好像国外配价圈子中还没有人真正碰过汉语,文献中也没有见到使用欧洲配价理论讨论汉语复杂句式等汉语问题的具体研究成果,汉语配价学者与国外配价理论界就汉语问题的交流讨论当然就更谈不上了。(注:参看韩万衡(1997)。韩文中提到德国有人写过关于汉语配价的博士论文,但由于未发表影响并不大。韩说国内配价学者不了解德国配价研究,其实德国配价界和国内外语学界搞配价研究的人更不知道汉语学界做的工作。)
题元理论当然最初也不是建立在汉语研究基础上的,但事实上它却是一开始就很关注与英语等印欧语不同的语言特别是汉语的题元现象。这既是该理论所追求的普遍解释的目标使然,也有赖于海外大批汉语语法学者的努力。近年美国、香港、台湾有不少学者应用题元理论研究汉语问题,而且已经发表了数量可观的相关论著。总体上看,题元理论的汉语研究主要有两种作法。其中一种常见的作法就是把汉语作为某种语料来验证理论原则,重点在“理论”。另一种工作则是直接运用题元理论处理汉语材料,重点在“材料”。我们首先应该承认这两种研究都很重要。
前一种工作在汉语学界常常不被重视,理由不外是“隔靴搔痒”、“削足适履”之类。其实这种看法是片面的,也不是科学界的正常观点。因为就如同生物学家一定认为发展生物学理论比单单描写某种生物的习性更为重要一样,语言学的这种工作除了把汉语的某些语法现象纳入题元理论框架从而得到更全面的理论认识外,也一定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后一种工作虽然会引起更多搞汉语的人的兴趣,但客观地说,由于这类文章多半是用英文发表在国际学术刊物上的,国内汉语学界看的人并不多。近年来在国内的刊物上也出现了一些介绍或研究题元理论而又结合汉语事实的著作,例如顾阳(1996),不过由于发表在外语学界或语言学理论的刊物上,汉语学者恐怕对其中大量研究工作的情况还是了解得很不够。
据我们了解,近年海外以汉语为语料研究题元理论和题元现象的成果主要反映在以下这些问题上(这里当然只能举例,不可能都提到):非役格动词;反身代词所指;从句中空位主语的控制;量化名词的辖域;题元指派方向;题元重合,等等。其中非役格动词、反身代词所指、空位主语控制等与题元的密切关系在其它语言中也有发现,在汉语中的表现与在其它语言中的表现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题元重合的现象在其它语言中虽然也有,在汉语中却更加突出,更值得引起注意。
顾阳(1996)讨论了汉语非役格动词与及物动词的题元关系,如“船沉了”和“水手们沉了船”。类似现象已经通过英语句子作了仔细研究,而汉语中这种“及物—不及物”的对应更多体现在某些特殊结构中,如带结果补语的复合动词结构“甲队打败了乙队”和“乙队打败了”;带“得”字的结果补语结构“那场接力赛跑得孩子们上气不接下气”和“孩子们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等。顾阳在文章中探讨了如何处理各种役使结构的共性和个性。
徐烈炯(1994)研究了汉语反身代词与英语反身代词的不同。英语和汉语的反身代词一般都要有先行语,但是两种语言确定先行语的标准很不一样。英语根据词语距离的远近和句法层次的高低来判定。而汉语则主要根据题元层级,如果句中有“施事”,反身代词往往以施事名词为先行语。徐烈炯(1985)指出,汉语从句中空位主语的所指也与题元有关,不能完全根据句法结构来确定。
有关题元指派方向问题,上文3.1.5 节已经举过例。 这项研究由KOOpman(1984)开始,Travis(1984)接着做了很多工作。 这两位都不会汉语,但她们了解到汉语句子有时名词在动词之前,有时动词在名词之前,而对这种现象过去有人试图从纯句法结构角度作解释但都不太成功,于是她们提出可以从题元指派方向的角度来说明。虽然后来大家找到了很多无法用题元指派方向处理的语料,但讨论汉语类似问题时,这两篇著作大家还是都会提到。
题元重合可能是汉语的一大特色。比如“打跑了狗”之类结构中,“狗”既是“打”的“受事”,又是“跑”的“施事”。Chomsky 的“题元理论”不允许同一词语身兼二职,那么对汉语的这种现象如何处理?黄正德(1988)较早就已经讨论过“你气死我了”、“这瓶酒醉得张三站不起来”等动结式中题元与句法成分之间的关系。李亚非(1990)用“格理论”和Grimshaw的“题元结构理论”来解释为什么“题元”数量可以超过“论元”数量。他还解释了为什么“他骑累了马”这样的结构会存在题元歧义,如既可指“他累”,也可指“马累”。他认为虽然这些是汉语特殊句式,却并不一定需要另外建立一套理论来处理,当代生成语法在研究其他语言基础上创立的理论原则已经足够说明这些汉语题元现象。
标签:语义分析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