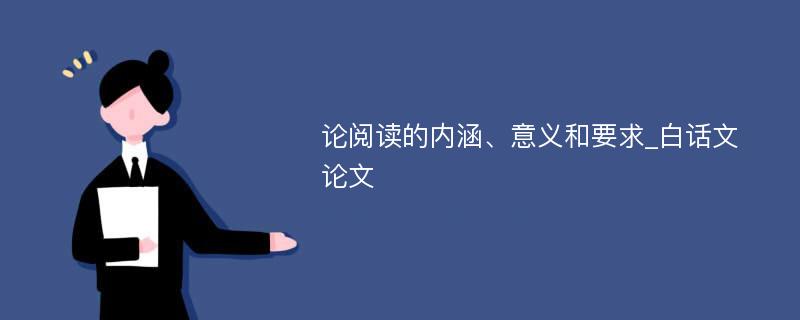
论诵读的内涵、意义及要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内涵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0年颁布的《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试验修订版)》、2001年颁布的《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2003年颁发的《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均出现了“诵读”的提法,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教学大纲和课程标准都没有对“诵读”的内涵进行界定,又引发了不同的解读。人们弄不清它与“背诵”“朗读”等概念之间的关系,有人认为诵读在上世纪逐渐消亡,在教学大纲和课程标准中再次出现是回归传统。因为“诵读”的内涵不明,造成了目前对“诵读”概念的解读十分混乱,以此为名的教学也较为盲目。其实,在不同时代,“诵读”概念的内涵及所指对象也不相同。我们通过逐步梳理的方式来辨析其内涵的演变,然后探讨其在教学中的意义及要求。
一、诵读的内涵演变
1.古代“诵”“读”的内涵
因为文言一个字往往就是一个词,所以在古代“诵”与“读”是两个概念,它们有联系,又有区别:
(1)从词典解释看“诵”“读”的涵义
“诵”与“读”都指出声地念,但又有所区别,“诵”《说文》释为“诵,讽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注为“倍文曰‘讽’,以声节之曰‘诵’。‘倍’同‘背’,谓不开读也。诵则非直背文,又为吟咏以声节之。”“读”《说文》释为“读,籀书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注为“抽绎其义蕴至于无穷,是之谓读。”[1]90(下)“讽诵亦可云读,而读之义不止于讽诵。讽诵止得其文辞,读乃得其义蕴。”[1]91(上)
可见,“诵”侧重通过“声”(音韵、节奏等)而“背”,目的在于“得其文辞”;“读”包括“诵”,又侧重通过“抽绎”(感悟、理解),目的在于“得其义蕴”。
(2)从所指对象看“诵”“读”的涵义
“诵”与“读”的涵义从所指的对象来看有所不同:(1)单用。如“诵诗三百,授之以政”(《论语·子路》),“诵诗三百,弦诗三百……”(《墨子·公孟篇》),这里的“诗”指《诗经》;“公读其书”(《左传》)这里的“书”指的是文。有时“读”也用来指有韵的诗,如“读诗讽术,虽千篇以上,鹦鹉能言之类也。”(《论衡·超奇篇》),或者有韵的文,如“能读千赋,则能为之”(《答桓谭论赋书》),或者整本的书,如“书读百遍,其义自见。”(2)对举。如“颂(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孟子·万章下》)“春诵、夏弦……秋学礼……冬读书。”(《礼记·文王世子》)“始乎诵经,终乎读礼”(《荀子·劝学》),这里“诵”的是《诗经》,“读”的是《尚书》《周礼》等。(3)连用。“诵”“读”二字在古代极少连用,连用有时专指文,如“旦日视其书,乃《太公兵法》也。良因异之,常可诵读之。”(《史记·留侯世家》)。有时泛指诗和文,如“故人凡有所当读书,皆当自十五以前使之熟读,不但‘四书’、‘五经’,即使天文、地理、史学、算学之类,皆有歌诀,皆须熟读,若年稍长,不惟不肯读书,必不能诵读矣。”(《桴亭先生遗书》)
可见,“诵”的对象多为有韵的诗,故“诵”的涵义偏重“以声节之”;“读”的对象多为无韵的文,故“读”的涵义偏重“抽绎其义”。
有论者认为古代的“诵读”经历了先秦之前的诞生、宋元时期的成熟和明清时期的深化三个阶段[2]。如果从以上的概念梳理来看,我们现在所说的古代的“诵读”是一个泛指概念,其实在古代还有与“诵”和“读”概念相关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概念,如讽诵、吟诵、朗诵、记诵、吟咏、吟唱、吟哦、朗读、熟读等,因为都与“诵”“读”有关,我们一般将其统称为“诵读”。这有点类似于维特根斯坦所提出的“家族相似”理论,他认为语言在使用过程中,因为不断地突出各自概念的某一特征,而产生相似而不同的特征,这样就由一两个概念衍生出众多与之类似的概念,这种现象好比“家族相似”,虽然成员各自不同,却存在“各种各样的相似性:如身材、相貌、眼睛的颜色、步态、禀性,等等,也以同样的方式重叠和交叉。”[3]281就“诵读”这个概念来说,“诵”和“读”的原始意义,就像这个家族的男、女两位始祖,而其他与之相似的概念只不过是其繁衍的子孙后代。换句话说,在古代只要是通过出声地念以获得对诗文意义的理解和文辞的习得,都属于“诵读”的范畴。
2.近现代“诵读”的内涵
1902年清政府制定的《钦定学堂章程》规定:“凡教授之法,以讲解为最要,诵读次之,至背诵则择紧要试验,若遍责背诵,必伤脑筋,所当切戒”[4]7,1904年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规定:“凡教授之法,以讲解为要,讲解明则领悟易,所诵经书本应成诵,万一有记性过钝不能背诵者,宜于实验时择紧要处令其讲解。常有记性甚劣而悟性尚可者,长大后或渐能领会,亦自有益。若强责背诵,必伤脑力,不可不慎。”[4]10 1929年颁布的《小学课程暂行标准小学国语》规定:“精读,选用适当的教材,(由教员拣定读本,或师生共同选定课文)诵习研究”。有人感叹“从此‘诵读’一词淡出了各种课程标准”,[2]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因为1936年颁布的《小学国语课程标准》中有“诵读,低年级朗读多于默读,中年级朗读默读各半;高年级默读的时机,要较朗读为多”的规定[4]37,1941年颁布的《小学国语科课程标准》中有“读书教材的欣赏、诵读、理解、体味、表演及应用”的规定[4]55。另外,关于“引领现代语文教学航程的叶圣陶先生论及阅读教学,鲜用‘诵读’一词,他把诵读法分解成了‘宣读’和‘吟诵’。现代语文教育家的著作中也很少出现诵读一词,‘诵读’这一概念被现代语文教育遗忘了”[2]的说法也是不恰当的。如前所述,“诵读”本来就是一个泛指概念,如果按“家族相似”的理论来看,“宣读”“吟诵”同属于“诵读”,况且,在近现代文言文教学时代,语文界除使用“诵读”名称外,还兼用古代的如讽诵、吟诵、朗诵、记诵、朗读、吟咏、吟唱、吟哦、熟读等名称,更何况在1946年12月23日,魏建功还在北京大学主持召开了“中国语文诵读方法座谈会”,邀请了28位著名的语言学家和文学家专门讨论“诵读”问题。另外,1949年之后颁布的历次语文教学大纲都有“朗读”“背诵”等相关要求。
不过和古代相比,自1902-1904年后,在实际教学中,“诵读”的地位确实在下降,正如黎锦熙所说的,“自废科举、创学堂以来,在语文教学上对诵读问题就渐渐淡漠了。”[5]首先是在新式学堂中基本是“先生讲,学生听”,教师讲得多学生读得少,反对像旧式私塾那样“摇头摆尾地”读;其次是1920年初小学“国文”改为“国语”,白话文进入语文教科书之后,产生了三种倾向:一是认为白话文不像文言文那样讲究音韵、节奏,不便于诵读,如叶圣陶、朱自清所说的,“大家都不知道白话文应该怎样朗读才好”[6];二是认为白话文是口语体,读白话文就等于说话,也不需要什么诵读,如沈百英(1925)认为:“从前文言时代,读出来的字句,不就是说话,要熟悉几句语句,使读得的音调常常残留在耳朵里,一旦做起文来,好像看人对你说话的样子;有的人曾会咿唔咿唔发出一种小声音来,就是朗读得出来的经验,须用达出来的表现。现在白话文的时代,读的字句,就是说的话,虽不能完全统一,却比从前要多占几分。所以学会说话,就可以作文,学会读文(从下文看指默读——引者),就能使说话有条理”[7]①;三是认为朗读不如默读效率高。当时有人认为:“中国旧教育家,类多赞成朗读,所谓高声朗诵,吟咏铿锵,常以书声传之户外为美谈。新教育家则与之相反,皆倾向默读”。[8]教育心理学家庄泽宣(1933)认为朗读是中世纪教育的产物,那时无论是外国的古典式学校还是中国的私塾,都强调所谓“弦歌之声,不绝于耳”,朗读“到了二十世纪的现代,也早就应在打倒之列。朗读到底有什么用处?除了悠闲阶级拿来消闲以外,实在一丝一毫的用处也没有。”不仅无用,而且有害,“朗读成了习惯不但不能帮助默读而且要妨害默读”,因为“口里发音决没有用眼睛来看得快,所以朗读成了习惯默读一定不能快”,“研究读法心理的专家都以为发声或嘴动是默读速率最大的阻碍,而发声或嘴动就是受了朗读习惯之赐!”[9]唐现之(1933)还翻译了Parker和temple合著的《Unifed Kindergarten and Fisot-Grade Teaching》(《幼稚园和一年级的教学》,文中书名拼写似有误——引者)中的一章《幼稚园和一年级的读法教学法》,其中提到小学“到了三年级以后,在许多进步学校中几乎完全把默读代替了朗读。”[10]②1934年教育部的汪懋祖描述了当时学校的情形,“今学校每不主朗诵,谓其妨害他人作业,而教室内除教员讲解,学生无暇朗读,即在讲授之余,学生亦惟枯坐默诵,生趣索然”,甚至某省有个督学视察学校,“见教室内合声朗诵,率为纠正”,结果弄得这个教员拂袖而去[11]。诵读在实际教学中的情形,于此可见一斑。
1946年,在台湾主持国语推行委员会工作的魏建功召集语言学界和文学界28个著名学者讨论“诵读”问题,目的是为在光复后的台湾“借重语文诵读以促进国语的推行”[5]。这些学者对“诵读”概念的理解各不相同,许多人谈的是文言文诵读,不过白话文的诵读问题就此成了人们的关注和讨论的焦点。就笔者所见,所发表的直接以“诵读”为对象的文章有10余篇,几乎没有引起现在讨论诵读的人的注意。这里着重比较朱自清、黎锦熙的观点,因为他们同时又是语文教育家,而且在这次会议前后各自发表论述诵读教学的专文,更因为二位学者探讨了“诵读”作为一个白话词语的概念内涵。
(1)朱自清的“诵读”涵义
朱自清在1942年的《论朗读》一文和本次座谈会发言中,都认为白话文不宜“诵”,适宜“读”,所以他认为不宜用“朗诵”“诵读”“吟诵”之类的概念,而用“朗读”比较合适。在本次座谈会后,他又发表《诵读教学》《诵读教学与“文学的国语”》《论诵读》等文章来讨论“诵读”,还专门辨析了“诵读”的概念。
他认为“诵”与“读”是有区别的[12]95-97:(1)目的不同。从词源上判断,本是“背诵文辞”的“诵”和“抽绎义蕴”的“读”,虽然可以通用,但目的不一样:“‘高声朗诵’正指背诵或准备背诵而言”,“吟诵诗文,从那吟诵的声调或吟诵的音乐得到趣味或快感,意义的关系很少”,而“白话诗文的朗诵,特别注重‘义蕴’方面”。(2)腔调不同。“所谓‘诵’的腔调便是私塾儿童读启蒙书的腔调”,即两字一顿的“诵”腔,而白话文宜用“读”腔,因为“小学国语教科书,无论里面的‘国语’离标准语近些远些,总之是‘语’,便于上口。文宜吟诵,因为本不是自然的;语直宜读或说,吟诵反失自然。”(3)手法不同。朱自清认为“朗诵其实就是戏剧化,重在动作上”,而“诵读和朗读却不相同。……自然也讲究徐急高下,却以清朗为主,用不着什么动作。”所以,白话文的读“称‘朗诵’,不如称‘朗读’的好。”
另外,在提倡诵读教学的语境中,朱自清往往用“诵读”来替换“朗读”,什么是“诵读”?他说:“我在别处说过‘读’该照宣读文件那样,但这句话还未甚明显。李长之先生说的才最干脆。他说‘所谓诵读一事,也便只有用话的语调(平常说话的语调)去读的一途了’。宣读文件其实用的是说话的语调。”[12]113尤其是对于那些有意用口语体写的白话文、话剧以及一些作品中的对话,“应该就像说话一样,虽然也还未必等于说话。说是未必等于说话,因为说话有声调,又多少总带着一些面部表情和肢体动作”。[12]114
可见,在朱自清看来,“诵读”即将声音和意义结合起来,侧重理解意义,注意采用说话式。
(2)黎锦熙的“诵读”涵义
黎锦熙在《中小学诵读教学之重要》中说:“说到小学,现在国语课本的诵读更不成话了,简直完全消灭了诵读的技术训练。第一是用土音读国语,别扭可笑;第二是读字不成书,没有句读,不管意义,两个字复合的词可以砍成两截,字字拉长,没有一点儿轻重高低,抑扬顿挫。”[13]203-204可见,诵读首先要注意发音标准;其次要注意音义结合。他在《新著国语教学法》中认为,“诵读就是儿童将声音与意义结合的一种‘发表’”,他提出“要声音真与意义相结合,便要练习论理的读法——注意词类和句读的断续和轻重;要表现文学的意味和兴趣,就要练习审美的读法——注意声情的抑扬抗坠。”[13]441其中“审美的读法”就是他在《国文讲读教学改革案(纲要)》中所说的“美的说话式”,“白话文对文朗读”要“文字音调不误,高下、徐疾、抑扬、气度又与自然的审美的说话无殊,斯为上等。”[13]520
和朱自清一样,黎锦熙也认为诵读是声音和意义的结合,而且强调表达方式要用说话式。但他提倡诵读主要是强调要“统一的国音,标准的国语”,而朱自清不提,是因为还没有“统一的国音,标准的国语”,在朱自清看来,虽然当时“诵读教学不得法和无标准”,而“加速‘文学的国语’的成长,就得注重诵读教学,建立诵读的标准。”[12]109
如果把朱自清、黎锦熙两人的观点结合起来,我们会发现,在白话文语境中的特指概念“诵读”,是指将声音和意义的结合起来,用标准的语音,采用说话的方式来读白话文。
(3)当代“诵读”的内涵
2000年后,语文教学大纲和课程标准在原有的朗读、背诵的要求上,提出了具体的诵读的要求。2000年颁布的《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试用修订版)》要求“诵读古代诗词和浅易文言文,能借助工具书理解内容,背诵一定数量的名篇。”[14]2 2001年颁布的《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在每个学段的目标中都提出了诵读的要求,并在“实施建议”里提出“有些诗文应要求学生诵读,以利于积累、体验、培养语感。”[15]17 2003年颁发的《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在课程“目标”中提出要“诵读古代诗词和文言文,背诵一定数量的名篇”,在课程“实施建议”里提出“教师应激发学生诵读的兴趣,培养学生诵读的习惯”[16]8。
因为目前对“诵读”一词的理解较混乱,我们依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和《语文课程标准》的规定来分析。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和默读的无声相比,诵读、朗读、背诵都是出声的。“诵读”为“念(诗文)”[17]1298,“朗读”为“清晰响亮地把文章念出来”[17]814,“背诵”为“凭记忆念出读过的文字”[17]80。可见,诵读和朗读的区别有两点:一是对象不同,前者是专指诗文,后者泛指文章;二是出声要求不同,前者不明,后者要求咬字准确、声音响亮。诵读和背诵的区别在于前者是看着文字念,后者是不看文字念。
就《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来看,同时出现了诵读、朗读、背诵三个概念。但是所指对象却不同,如“诵读儿歌、童谣和浅近的古诗”[15]5“诵读优秀诗文”,“能用普通话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15]7“背诵古今优秀诗文”[15]9。“课文”当然包括“优秀诗文”,也就是说诵读的对象范围小于朗读。课标注明要求背诵的“优秀诗文”包括“古诗文”,“也包括中国现当代和外国优秀诗文”,那么从行文上看,诵读的“优秀诗文”只指古代的文言文和古今诗歌,显然不包括白话文。
如果将《现代汉语词典》和《语文课程标准》结合起来看,当代的“诵读”概念指的是念古代的文言文和古今诗歌。而“念”《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读”。[17]997也就是说,当代的所谓“诵读”,只是在对象上部分回归了传统(不含白话文),而其内涵还不如原始的“诵”(通过“声”而“背”,“得其文辞”)和“读”(包含“诵”,并通过“抽绎”,“得其义蕴”)以及20世纪40年代的“诵读”(审美式地说、美的说话式)那样清晰。
如果要尝试给“诵读”下一个定义,我们可以结合对其内涵演变的梳理、辨析来这样界定:诵读是一种用标准的普通话,注意声音与意义的有机结合,用略带夸张的语调读文言诗文,用说话的语调读白话诗文的读的方式。
二、诵读的意义
1.增强对母语的感情
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认为民族语言与民族精神是二而一的关系,人类语言结构之所以有种种差异,就是因为民族精神特性各不相同[18]52-53。中国人的感性直觉思维方式重在整体感悟,西方人的理性逻辑思维方式重在局部分析。所以,英语、俄语等通过严格的“格”“性”的规定以求明晰准确,而汉语则通过相应语境采取“意合”的方式组织语言,以求言简意丰。所以,汉语和其他语言相比更需要诵读,在诵读中可以感悟汉语特有的言语形式,进而感悟其言语内容。另外,汉语特有的发音方式和声调,也需要通过诵读去感悟、体味,正如洪堡特所说“为什么母语能够用一种突如其来的魅力愉悦回归家园者的耳朵,而当他身处远离家园的异邦时,会撩动他的恋乡之情?在这种场合,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并不是语言的精神方面或语言所表达的思想、情感,而恰恰是语言最不可解释、最具个性的方面,即语音。每当我们听到母语的声音时,就好像感觉到了我们自身的部分存在”[18]71。总之,通过诵读母语可以让我们寻找到本民族的精神家园。
2.增加对文本的理解、体验
朱自清说:“诵读这种写出来的话,得从意义里去揣摩,得从字里行间去揣摩。而写的人虽然想着包含那些,却未必能包罗一切的;揣摩的人也未必真能尽致。”[12]114也就是说诵读时的声音表达是建立在理解文意的基础上的。首先,要理解作者所表达的言语内容的表层意思与深层意蕴及其经营言语形式时的匠心所在。其次,文本语言具有私人性、多义性、不确定性等特点,也不像口头对话那样具有现场情境的制约性和可用动作、表情的辅助等特点,所以读者在诵读的过程中可以通过自身的理解、体验,采取相应的声音表达方式,在揣摩作者口气的基础上变得如出己口。反复的默读固然也能加深理解和体验,但效果不如诵读,这种无声的读更多的是“能知道它们的意义”,不如有声的读“能体会它们的口气”[12]99
3.增进口头和书面表达
首先,诵读可以促进口头和书面表达的相互转化。诵读在口头和书面表达相互转化中能起到一种桥梁的作用。黎锦熙认为文言文做不好,白话文也做得一塌糊涂,是因为“作文和说话失去了联系,文字和语言脱了节”[13]202,诵读这种“说话式”的读“自然影响到写作,因为从耳到口,从口到心,就是所谓‘声入心通’;然后言文一致,从心到手,就是所谓‘得心应手’了。必须在讲读时训练了‘声入心通’的技术,然后到作文时才有‘得心应手’的妙处。这就叫做‘写作以外的诵读技术训练’。”[13]203就像上文沈百英所说的“一旦做起文来,好像有人对你说话的样子”,或者像众多论者所说的,有一种语感。
其次,诵读可以优化口头和书面表达。诵读的对象无论文言文还是白话文,都是书面语言。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最大的不同就是书面语言讲究修饰,具有典雅、明确、合逻辑等特点,从内容方面看,需要对题材进行增删、位移等,从形式方面看词语的选用、句式的选择、段落的安排、修辞方式(记叙、议论、说明等表达方式和各种修辞格式)等都需要斟酌;而口头语言追求通俗,不免啰嗦拖沓,也讲究现场效果,因为对话有动作、表情的辅助,表达有时也不甚明确,又有及时的反馈修正,表达有时也不尽合逻辑。多诵读自然可以丰富、纯净、理顺自己口头和书面语言表达,提高表达的效果,所以朱自清说“诵读不但可以帮助写,还可以帮助说,而说话也可以帮助写。”[13]112“朗诵对于说话和作文也有帮助,因为练习朗诵得咬嚼文字的意义,揣摩说话的语气”。[12]112
三、诵读的要求
诵读基本要求是,要发音正确不用土音、吐词清晰不能含混、读字准确不能增减;要注意语音的高低、语速的快慢、语流的停连等。有关这些,论者多有提及,兹不赘述,只是特别补充强调两点:
1.要注意“口诵”与“心惟”结合与反复
诵读不仅仅是为了训练读的形式方面的技巧,更重要的是体会作者的情思及文本语言的运用。只有真正进入文本,“入乎其内”才能体会到作者在文本中的情感、思想,进而“出乎其外”体会作者在采用相应语言形式表达时的匠心用意,最终才能诵读得恰切。“讽诵之际,务会专心一志,口诵心惟,字字句句,演绎反复,抑扬其音节,宽虚其心意”(王守仁《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所以诵读要特别注意过程中“口诵”与“心惟”的结合,朱熹强调读书要“心到、眼到、口到”,黎锦熙强调讲读要“耳治”“目治”“口治”都是这个意思;另外,要注意诵读之后的“沉潜”“涵泳”,如古人强调“沉潜乎义训,反复乎句读”(韩愈《进学解》)“诗须是沉潜讽诵,玩味义理,咀嚼滋味,方有所益”(魏庆之《诗人玉屑》),这样才能做到“口诵”与“心惟”交替推进。
2.要注意语体和文体的区分
文言本不是自然语言,所以我们在上文说要用略带夸张的语调读文言诗文,但需要注意,读有韵的诗歌应该略带吟唱的调子,读无韵的散文可以像现在的说话的调子,不过也要注意语言风格,如读《六国论》应该声音高、语速快,而读《项脊轩志》则应声音低、语速慢。白话是比较自然的语言,但“写的白话不等于说话,写的白话文更不等于说话”,[12]114所以对于小说、散文、话剧中的人物对话等可以去“说”,而其他部分只能说是用说话的调子去读;白话诗歌如果是口语体的可以去“说”,如果是书面语体的也只能说是用说话的调子去读了,甚至“还可以稍带一点从前吟诗读文的调子。”[13]441
注释:
①“文言文是古人的话,要熟读到机械化了,才可以应用。现在改用白话,无须拉起高调,摇头摆尾的唱了。白话是现代语,是现在人说的话,只要照说话直说好了。……总之以少用为妙,以说白代朗读。”沈百英.《老方法还可以用吗》.小学教育月刊,1926年第2卷第3期。
②唐现之在“译者识”中提到“全书已译竣,不日付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