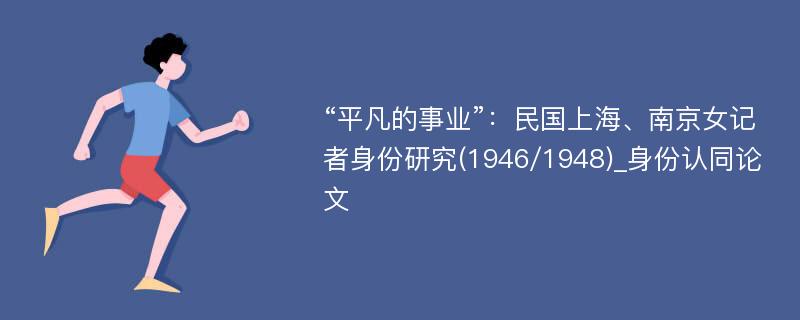
“一份平凡的职业”:民国沪宁女记者的身份认同研究(1946—1948),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国论文,女记者论文,沪宁论文,平凡论文,身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当今中国,除了偶有炒作“美女记者”之类的噱头外,“女记者”早已没有多少“特殊性”可言。即使这种炒作,也重在对“美女”二字的低俗消费,而非记者职业本身。但在民国时期,“女记者”被视为一个“特殊”的职业群体,其所受的关注程度和社会非议都非常之大。目前,关于民国女记者的研究还较少,而关于女记者职业群体身份认同的研究则更非常之少。探寻民国沪宁女记者职业群体旧事,不仅可以为今天的新闻学术史研究增砖添瓦,更可阐幽发微,从中窥见中国记者百年发展历程之一斑。本研究主要从抗战后的民国报刊中关于沪宁女记者群的形象建构入手,阐释其中对立的话语体系,展现“他者”对女记者形象的建构。在此基础上,笔者拟从女记者将记者工作自我叙事为一种“平凡的职业”中,阐释民国沪宁女记者职业群体的身份认同建构问题。 一、民国新闻学界对女记者的职业身份界定 民国时期,职业女性远没有被社会普遍接受。抗战之前,女性从事记者工作还是少之又少。1937年,全面抗战前《大公报》进行的上海职业妇女访问称,“谈到我国的一般职业妇女,献身于新闻事业者,至今还属渺小的很”,“我国妇女插身新闻记者中,犹如凤毛麟角”。[1]根据任白涛的梳理,抗战前见诸报端女记者的主要有郑毓秀博士、李小可、蒋逸霄、王雪莹、邹云涧等人。[2]但抗战结束前的民国新闻学术界已经对女记者的职业身份在学术上予以呼吁,为女记者作为一个职业群体登上历史舞台作了必要的铺垫。 早在1923年,邵飘萍出版《实际新闻学》之时,就专设有“社会部之妇女记者”一章。他认为,社会新闻形形色色,范围广大,其中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妇女部或家庭部。妇女部和家庭部专门记载关于妇女或家庭的事情,即应以聘任女记者为主。这些记者以从事采访女科学家、名流之夫人小姐、女性名伶等为主,以及报道家庭儿童教育、流行服饰、烹饪、家庭娱乐、女学校和幼稚园新闻等,以及搜集报道有关名伶美人的写真或者诗文作品。同时,当时为树立女界模范,大家闺秀和名人眷属提倡参加的夜宴、舞会和游艺会等社交活动,也适宜派女外勤记者采访。尽管邵飘萍对女记者工作活动范围的认识还比较局限,主要是从女记者从业的便利性和性别特征出发,设计职业角色。但他也同时指出,随着女子参政问题的渐次实现,“妇女所注意者不仅家庭与社交二者,其将来之趋势范围必目见扩大无疑矣。”[3]在1925年伍超出版的《新闻学大纲》中,他的观点颇近于邵飘萍,在肯定女记者职业的同时,为女记者设计了大致相类的职业角色,书中称:“余今且据个人之私意,答之曰:妇女之家政,美术,音乐等之评论,纪事及文学类之作品,则男记者往往不及女记者成绩之优良,以其笔致纤丽,观察明细故也。”同时需要指出的是,伍超还有不及邵飘萍之处,他又认为“苟令妇女冒风雪于深宵,作险阻之踽行,以从事百般社会之访问,就其体质论之,甚不适当。即勉强为之,非惟不能与男记者竞争,且恐易于丧失妇女之尊严,是乃女记者不及男记者之处。此系天然之缺陷,非人力所能补救也”。[4] 如果说邵飘萍、伍超对女记者的职业认可还比较保守,立论还带有俯视的色彩的话,那么任白涛则是极力肯定女记者工作权力的学者。1922年,任白涛出版的《应用新闻学》一书就专设“女记者”一章。在1928年第三版修订时,任白涛对“女记者”一章作了大的修改。并且任白涛专门言道,就根本上说,“女记者”这个名词是没有意义的,不通的,他本想在修订时将这个“陈腐的语句”删掉,但想着在男性本位的世界没有改造之前,又有着暂时存在的必要。[5]在这本书中,任白涛认为女记者与男记者“同执一业”,但在某些范围内的活动和功能远超过男记者的作用,比如关于文学、美术范围的述作,又比如关于“女界”事务的采写。 在后来的《综合新闻学》中,任白涛对女记者的职业作了更多的阐释。他重申对“女记者”这个称谓的不认同。[6]他回顾说在八年前《应用新闻学》出版时,即想能取消“女记者”的称谓,但没想到八年后还得继续来这么“一大套”。促使他大量增幅写作“女记者”的缘由,很大程度上即在于当时民国女记者的职业境地不容乐观,社会上存在很大的偏见。 为了给女记者正名,任白涛还借助“外国女记者”的榜样作用,论证女记者职业群体的正常性。在《应用新闻学》中,任白涛专门提出“最近二十年间,英美新闻事业之进步,所得于女记者之力者,实不少也”。[7]在《综合新闻学》中,他又描述了美国女记者的起源,介绍了美国女记者关罗谟夫人、斯特朗、白朗、汤姆森女士等人的事迹,以此展现女记者亦可成就新闻事业。[8]同时,任白涛还援引美国85岁女记者爱丽丝凡昔克夫人的事例,以此说明所谓家庭生活的不足以成为女性从事新闻职业的障碍的。[9] 像任白涛这样以“外国女记者”作为榜样反衬女记者职业群体的正当性,是很多民国报刊常用的做法。早在民国初年,《民国汇报》的《世界潮音》栏目就曾对荷兰女记者爱衣拉女士从军,参加巴尔干战争的新闻进行报道。[10]而《繁华》杂志则在报道此新闻的同时,更称爱衣拉女士“喜骑马、精枪术、又能文学,英姿飒爽,见者莫不称为巾帼须眉也”。[11]值得一提的是,有一位因抵抗纳粹而闻名的法国女记者塔布依夫人,受到当时报刊的广泛关注。1939年至1941年间,有《西风副刊》、《国际间》、《战时记者》、《北京新闻协会会报》、《妇女月刊》、《妇女生活》等多家媒体发表了关于塔布衣夫人讲述自己从业故事的译作。比如张十方称赞塔布衣是当时政论家与名记者中数一数二的人物,“我国是迫切需要着像塔布衣夫人这样的记者的”。[12]《妇女生活》杂志则认为“她是欧洲妇女新闻职业界中最著名的人物,英德意俄诸邦的报纸,因为她的言论不但公正而且有独到的见解,所以常常提及她并引用她的言论”,所以在“欣羡颂扬”之余,更呼吁姐妹们要“极力去争取地位,磨练实力”,在这方面,“塔布夫人确实给了我们不少的提示和勇气”。[13] 在民国时期的学术论著和刊物中,对外国女记者也予以了特别的关注。胡道静于1930年出版的《新闻史上的新时代》中,专门提及美国罗丝女士详细介绍美国各个著名女记者故事的《女记者》一书。他认为这是一本很好的书,应该为新闻史长编工作学习,并不局限于记述女记者的故事。[14]在黄天鹏于1930年编著的《新闻学刊全集》中,收录有黄一天的“英记者蒿女爵士来华”专文。文中指出国外的新闻媒体被视为“宪法上的第四之威力”,常有左右政府外交政策的能力,因此记者在沟通国家之间相互理解的作用不亚于国家间特派的大使,只是可惜不被国人所重视。他称“蒿女爵士”在欧美报坛执笔多年,其政论文章尤为时人所称颂。此次来华,“蒿女爵士”有意探寻中国的实情和真相,沟通中英之间的理解和感情,消弭以往的一切误会。在黄一天看来,“蒿女爵士”的这种见解和抱负,“已非今日英格兰人之所常有,而特得吾人之欢迎矣”。因此,他对英国女记者“蒿女爵士”来华访问表达了极大的热忱,并希望“蒿女爵士”能将中国的真实国情昭示国外,以促进国家间的亲善和世界和平。[15]1940年的一份《新闻学报》曾在“报人活动”栏目中刊登了“美国女记者的活动”一文,介绍美国女记者从事新闻行业的各种英勇举动。[16]从中可见,在新闻学术界对国外女记者的引介中,看不到有关“女性”的特殊看法,而是完全以一种去性别化的视角来看待,基本以一种正面形象出现,希望给国内的女性解放提供支持的证据。 那么,针对中国女记者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如何建构女记者平等的职业环境?在这方面,民国新闻学术界也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任白涛指出一方面要打破男性轻视或者玩弄女性的观念。他明确反对将女记者加以“社花”、“社后”,或者“报花”、“报后”的“奇怪头衔”,认为若是如此则只是使女性报人给新闻界增加一个“无冕皇后”的噱头而已。[17]同时,另一方面他认为也要靠着女性的自我觉醒,学习新闻学的理论和实际技能,“知识即权力”,依此方可获得“与男性共同担负合适于性能的职分”。[18]同时,任白涛还赋予女记者这个职业以更大的意义。他认为“女性须知做这职务不是单纯的个人生活问题,而是全部的妇女问题”,女记者应该怀着服务于女性的心态去工作,“女性如果能够勇往直前的参加新闻事业,至少那任意侮辱女性的新闻报道是不会发生的”。[19]在这里,他赋予了女记者的职业以更崇高的责任,在普通的职业意义之外,力图推动其承担起女性权益维护和女性解放的任务。 应该说,任白涛对取消“女记者”这一称谓的认识是深刻的,也是将女记者纳入记者职业“内群”的关键。但需要指出的是,他对女记者职业意义的捧扬,表面上看似是颇有道理,力图通过女记者自身起到维护女性权益的作用。但赋予特殊使命的背后,其实质也是一种将女记者职业特殊化的表现。 二、沪宁女记者群的媒介镜像 抗战期间,随着全民抗日运动的开展,女性投身新闻事业的情况日益增多,比如彭子冈、浦熙修、杨刚和戈扬被称为后方新闻界的“四大名旦”。在战时陪都重庆有三十多家报社和通讯社,大多都有女记者,并且作出了很好的成绩,“令很多老资格的记者们都感到惭愧”。[20]抗战结束之后,重庆女记者南北纷飞,主要是分赴沪宁和京津。[21]其中相当大一部分女记者返回了国民政府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沪宁一带。在1946—1948年间,南京和上海一带出现了短暂的和平,报业再度繁荣。毕铭曾经在“上海女记者群像”专栏中指出,胜利后的上海新闻界呈现着分外的蓬勃,除原有各报均先后复刊,新办报纸如雨后春笋般出现。[22]在这种背景下,除从重庆返回的女记者之外,又有大量女性投身新闻行业,汇聚成了中国女记者从业的第一次高潮。新闻学术界多年来呼吁的女记者职业群体,终于在沪宁一带开花结果,正式初登历史舞台。据王素红的研究,1946年在南京派外勤的女记者有十位左右。[23]而在上海,据当时的调查,女记者在四十名左右,平均每一报纸有女记者两名以上。[24]同时,伴随着女记者职业群体的涌现,沪宁等地的报刊将女记者视为新兴职业群体,进行了广泛报道。像《海燕》杂志在1946年新1期开设了“女记者专页”[25],《周播》开设了“上海女记者群像”专栏,《海涛》杂志开设了“海上女记者群专栏”进行大规模报道。在报刊媒体这一“他者”的眼中,女记者呈现出多面化的职业形象。 冯剑侠曾在研究中指出,民国女记者被媒体呈现为“交际花”的形象,而她们自身则重建为“无冕皇后”的职业身份。[26]实际上,民国女记者的媒介职业形象远没有这种“二元化对立”模式这么简单,女记者也未必赞同视自己为“无冕皇后”。观诸抗战后的民国报刊,可以发现,社会上对女记者有讥诮者和窥视者,也有维护者和鼓励者,在媒体上形成了一种对立的话语,由此呈现出了对立化的媒介想象,具体表现为三种形象: 一是“交际花”。所谓“交际花”,主要是指在交际场合活跃而且有名的女子,其语多带贬义。冯剑侠的论文中对“交际花”的媒介想象已经有所阐释,认为在文人们嘲讽与调侃的口吻中,女记者的“交际花”形象更被固化下来。[27]在笔者看来,所谓“交际花”的形象定位仅是表象,这背后所隐含的则是对女记者职业能力的怀疑和不承认。举例来说,马北异曾经在《快活林》杂志报道了一个因记者陈霞飞采访不实引发的“假新闻”事件,但因记者是女性,新闻标题中特意予以突出,题为“女记者信笔乱挥一篇报告文学引起轩然大波”。在文章中刻意指出陈霞飞为“艺人”出身,讽刺为“徐娘风韵犹存于一扭一捏之间,谈时,摇头眼动,十足艺人派头。”并称她所写的财政局的情况报道严重失实,并且在受到财政局反驳之后,不仅不认错,而且工作态度极不端正。[28]可见,马北异对女记者的实际工作能力包含质疑。一个笔名为“铜兄”的作者在所写的“各报拟停用女记者”一文中称,上海各报社四十多个女记者中,真正有采访能力的也就寥寥数人,其余的都可以说是“打扮的花枝招展,利用门面,博取所欲获得的消息,回头叫男记者捉刀交卷而已。”[29]而更有人在报纸上大唱衰歌,认为女记者的职业是玩票的性质,终将不能长久存在。如梅子在文章中将男记者和女记者区分为不同的群体来对比,声称男记者“为生活而工作,为事业而生活,当然为切身问题,着重事业”,而女记者则是“随随便便,任意欲为,做做就做做,无所谓一件事”,并直称“上海女记者,已成落叶秋扇,将为末落时代,其原因终感到女记者之能力太弱。”[30] 二是“无冕皇后”。“无冕皇后”是相对于记者职业“无冕之王”的比喻而言。冯剑侠在文章中称,民国女记者在自我的职业认同中建构了“无冕皇后”的形象。[31]但实际上,这种比喻并不能过于认真的对待。观诸史料,也鲜见女记者自身会以“无冕皇后”自况。个中缘由,主要在于“无冕皇后”这种称谓更多地是一种新闻“噱头”,有时候还多带讥诮之义。其真正的含义更接近于“交际花”,而非真的是褒扬记者的社会地位。上述对女记者职业大唱衰歌的“铜兄”即在文章中以“无冕帝后”称呼女记者。毕铭在谈及女演员梅萼弃影从事新闻记者工作时,刻意说她不过是“无非慕‘无冕皇后’之一顶桂冠耳”[32]。而《辛报周刊》在报道这则新闻时,也使用了“话剧业余红演员,梅萼做无冕皇后”的标题为噱头。[33]更有一篇题名为“无冕皇后”的文学作品,作者易窕刻画了一个叫“赵馨”的女记者,打扮的像“舞台演员涂了油彩一样鲜明”,在采访中热衷于和男记者插科打诨,并且自身不学无术,甚至将“米苏里”新闻学院混谈为“米许林”牙膏,但长袖善舞,是周旋于男记者和要人之间的“交际花”,被众多男记者众星捧月般围绕,通篇充满了讽刺意味。[34]更为露骨的则是《周播》曾经登载所谓揭露南京女记者的“香艳故事”,黎立以“白下无冕帝后,艳事流传记”为文章标题,更称“此一群‘无冕帝后’,终日相处,其中腻事,笔不胜数。客自南京来,述南京无冕帝后腻事,极为香艳动人。”[35]此文主要写一两个女记者的香艳故事,并极尽想象之能事。南京别称“白下”,作者黎立以偏概全的宣称此一群“白下无冕帝后”,就有对南京全部女记者一棒打死之嫌。由此可见,其实“无冕皇后”和“交际花”类似,同样是一种污名化的称谓。 三是女性职业者。除了上述“交际花”、“无冕皇后”等形象之外,还是有些媒体力图持客观的态度对待女记者,将她们视作新女性职业群体来看待。1946年《海涛》杂志推出“海上女记者群”专栏,介绍上海各报女记者情况。在开篇伊始,作者圈外人就指明:“此刻在上海各报各通讯社服务的女者,大概有十几位,其中一大部分毕业于圣约翰,他们不但学业好,口才好精神好,而且跑出来的卖相好,采访新闻的技巧更好,对于这些小姐的活跃成绩,不可无文点缀,爰写‘女记者群像’,以实史乖。”[36]虽然作者在开篇之时说共有十几名女记者,但实际上共写40余人次。尽管这种做法还是将女记者作为报道客体来处理,并且也不可避免在某些文章中有调侃谢宝珠等女记者感情生活的话语,[37]调侃身兼“教授”和“记者”两职的杨惠文笔肉麻,[38]甚至有专门报道邵琼感情故事的花边新闻。[39]但总体上看,这些调侃最多为花边新闻的性质,并无恶意。纵观“圈外人”的系列文章,整体持论比较中肯,对女记者的学历学识和工作能力多有肯定之语。如称赞《联合夜报》的姚芳藻为“了不起的女英雄”;[40]称《前线日报》的蒋蕴薇是很可造就的人才,前途有着“璀璨的希望”;[41]称《大晚报》的张蔚文是杰出人才,风度、口才和写作这些外勤记者的才能她无一不具备。[42]称《时事新报》的麦少楣是报社所需要的人才,在改善该报“偏硬”的风格方面是“前进的、成功的”,而麦少楣的“前途估计是无量的”。[43]称《大英夜报》的池廷熹有男性所不及的活动力、有正确的思想、有丰富的学识,在该报的成绩“已使男记者倒相顾失色。”[44]又称《新民晚报》的周光楣的文字和努力的成就足让男记者自愧不如,男记者如不努力起来,则有被女记者们淘汰的可能。[45]当时的国民党中央党报《中央日报》针对社会上对女记者的偏见,刊发了《南京的女记者》一文,介绍南京女记者突出的工作成绩,并指出女记者们要想做出和男性同业者一样的成绩,往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甚至做出一定的牺牲,她们在工作上,并没有比男记者逊色,而家庭,儿女和健康,对于一个女记者的发展是很大的阻碍。[46] 综上可见,在以上媒介想象中,显现出现了两种对立的话语:一方面,“交际花”和“无冕皇后”的贬义呈现。呈现这种形象的媒体多是《快活林》、《辛报周刊》之类的小报,以刊载趣味新闻提供娱乐为主。其实质都是基于范畴资格而产生的“刻板印象”推论,通过这种“刻板印象”的描绘界定了女记者群体,并使之特殊化,以与“(男)记者群体”区分开来,[47]使女记者的职业邪狭化,成为可供“窥视”赏玩的对象。而另一方面,有关“女性职业者”和“外国女记者”的正面媒介形象,则主要是由如《中央日报》、《海涛》这样的综合新闻媒体、像《新闻学报》这样的学术刊物,或者《妇女生活》、《妇女月刊》这样的女性媒体塑造的。这些媒体持论相对严肃,力图打破因性别不同而产生的群体区分,将“女记者”纳入“记者群体”的范畴,呈现她们不但能够胜任工作,而且还可能比男记者做得更好,所体现的是一种争取女记者正常职业身份的话语。这其中,女性媒体的呼吁自不待言,像综合新闻媒体和学术刊物的呼吁,则代表了社会上要求女性解放,支持女性职业化的正面声音。 三、沪宁女记者群的自我职业认同建构 无论是媒介的形象认知,还是学界对女记者职业的认可,本质上都是一种他者的“镜像”。在有关认同的研究中,“他者”起着重要的映衬作用。这种“镜像”构成了沪宁女记者群自我身份认同的一种背景。而进一步探究抗战后沪宁女记者职业群体的认同建构,更要研究其自身如何应因这些“他者”的看法,界定自身的职业身份认同观念。 观诸当时沪宁一带女记者的自述,可以看出,当时多数女记者既力图摆脱“交际花”、“无冕皇后”之类的噱头,也没有刻意追求“新女性”、解放妇女之类的崇高理想。女记者们所展现出是一种更为成熟的职业理念,即将之视为一份“平凡的职业”。 女记者杨惠在文章中曾经抱怨,真不懂的为什么许多人对女记者都另眼相看,觉得她们属于一种特殊的“型”,实际上你一旦当了新闻记者,就得忘了自己是女性,去从事各种艰苦的工作,而在写作方面无论是男记者还是女记者根本没有区别。她恳请社会“把我们当作普通的工作者吧”。[48]这是一种直抒胸臆的表达,要求将女记者视为普通的职业群体。而像蓝羽报道女记者蒋友玫刻意穿着朴素,不愿意因穿得五颜六色而被视为“交际花”的表现,[49]像女记者陶冰在文章中多次描述作为一个有孩子的母亲,怎样去跑政府新闻、怎样去报道有危险性的新闻等等辛苦,[50]没有“交际花”的风流浪漫,也没有“无冕皇后”的纵横捭阖,则是力图通过呈现职业生涯的具体表现和艰辛,展现一种平凡的职业形象。 女记者不仅对外界力图表达这样的形象,在对同时期的女性叙述自己的职业时,也是以一种平凡的职业来定位。女记者段奇珷的认识非常深刻,她直指赞誉和轻视两种不正常的认识,其实都是将女记者“异化”的表现。她指出,女记者在中国是一个够新鲜的名称,女人参加人生大舞台充任角色的,还是凤毛麟角,普通的职业头衔前,一旦加上一个“女”字就会引起注意和猜测。一般人都对职业妇女,投以好奇的眼光。但是段奇珷强调指出,“这里,我要说女记者的本身是一个平凡的新闻从业员,但社会上往往寄予两种极端的批评——赞誉或轻视,将女记者形成异于平常的的人物。”而实际上,女记者“同男记者们一样能会晤着一般人不能会着的人,她有优先权去先睹奇异的事务,她负着对社会正确报道的任务,她不愿意人们将她与男子在装束去引起好奇与评判,她宁可用一支有力的笔,去激起人们对女记者的认识和熟悉”[51]。 在此,当时的沪宁女记者群力图摈弃“交际花”和“无冕皇后”的污名化形象固然容易理解,但为何并没有像学术界呼吁的那样为“妇女事业”奋斗,而是选择了阐释为“一份平凡的职业”?个中缘由,值得我们深思。 作为一个职业群体,真正的认同应当是无差别化的。从认同理论上来讲,“某一具体的群体成员被认为在本质上与其他内群体成员是相同的,或者被当作彼此相同的来对待。”[52]在实际工作中,一般民国女记者所面临正是如何将自己“内群体”化的困境。金紫曾经借“一个记者朋友”的口指出,女记者在职业生活中所面临类似“花蝴蝶”之类的指摘都还是细枝末节的,关键是工作中的“异化”,比如女记者正常的采访或同学聚会的电话,便会被说成是“交际电话”,而要是男记者的话“谁会加以注意呢。”[53]陶冰在自述中曾经说,为了证明已婚的妇女能和男子同样的工作,她常主动去跑一些被人认为不适合女性采访的新闻,力图打破男子脑海中对女子能力的藐视,比如去命案现场采访、在当时还是“红灯区”的南京夫子庙一带获取很多新闻。同时,她还针对部分男记者认为女性在采访妇女集会之类新闻有便利条件看法,指出记者应该忘记自己的性别,单纯以一个新闻记者的身份工作。[54]实际上,张静庐在1928年就曾经从区分记者的社会地位和职业定位的角度指出,民国时期记者职业是“一种很辛苦的职业”、“一种极低微的极辛苦的职业”,新闻记者“可说是一个劳力而又劳心的苦工”。[55]因此,作为一个职业群体,女记者亟需使自己成为像男记者一样的普通工作者,呈现自己同样努力的工作,工作中面临同样的艰辛,而不是呈现自己的特殊性,更不是将自己呈现为一种特殊使命的代言人,从而使得自己真正纳入记者内群体。以此,实现女记者群体的去魅化,获得本应正常的社会身份认同。 值得特树一笔的是,尽管民国女记者在职业化的道路上面对着各种困难,但她们不畏人言、勇于开创,表现出成熟的职业理念,为中国女性的职业化作出了筚路蓝缕的贡献。如金紫所言,“有一天,女记者的人数超过了男记者,而且阵容坚强,在质的方面也是无懈可击的时候,深信这些麻烦也会不期而消了。”为了实现这样的目标,“但愿这一辈的‘无冕皇后’,能够任劳任怨,努力耕耘,为下一代播下优越的种子。[56]今天的中国,男女记者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已均等化。从最新的统计数据看,新闻记者男女性别比例基本持平,男性记者141707人,女性记者110469人,男女比例为56:44。[57]我们在向民国女性记者致敬的同时,似也可以告慰前辈们的夙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