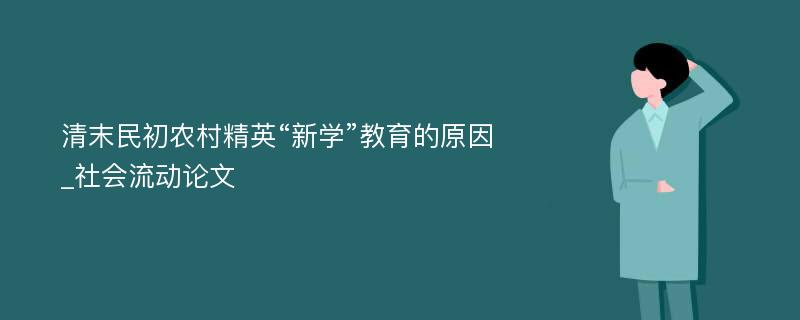
清末民初乡村精英离乡的“新学”教育原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初论文,清末论文,乡村论文,原因论文,精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11-4721(2002)05-0145-06
近代以前中国以传统的旧学教育一统天下。1905年(光绪31)9月2日,清廷上谕宣布:“著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举考试亦停止。[1](P5392)至此,延续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完全覆灭了,适应时代需求的“新学”教育制度取得了彻底胜利。“新教育的改革,激起了农村的一场大的波澜。从某种意义上讲,清廷的新政再没有比废科举兴学堂之举对农村社会影响更大了。”[2]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它大致类同于集中体现了转变时代开始的俄国1861年废除农奴制,以及1868年明治‘复古诏书’颁布不久的废藩革新”。[3](P643)教育体制的变革引发了乡村精英结构性的社会流动,[4](P78)而这种流动的趋向从地域范围来讲则表现为从乡村到城市的单程迁移,[5](P238)就造成了农村精英人才的流失。[6]
学术界对中国近代以来农民离村问题的研究已取得相当丰硕成果,可谓成绩斐然,但是从近代“新学”教育角度去分析乡村精英离乡的原因的论著却近付阙如。鉴于此,笔者试图在参阅和吸收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近代“新学”教育为视点对这一问题进行粗浅的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一
社会流动指“人们在社会结构体系中从一个地位向另一个地位的转移,它包括了人们的身份、职业、阶级、阶层关系的变动”。[7](P147)社会流动是任何一个社会结构在任何历史时期都存在的、极为普遍的社会现象;只要有社会存在,只要有社会分工、社会差别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分层,就必然要出现社会流动,尽管社会流动的形势、规模和特征因时代变化而各有不同。[4](P53)影响社会流动的因素,社会学家已识别出许多,概括而言,主要有五类:社会结构因素、社会出身或家庭背景、个体特征、自然因素、教育因素。[9](P121-122)法国社会学家布栋认为,学校就学率的增长与教育机会的扩展是增加社会流动的一种手段。[9](P235-237)
近代以前中国以传统的“旧学”教育一统天下。近代“新学”教育是伴随着19世纪中期西学东渐进程逐渐展开的。早在鸦片战争之前,澳门、香港、广州等地就已经出现了由西方传教士开设的企图“通过文化的渗透来达成文化霸权的民间渗透”的教会学堂。随着《望厦条约》、《黄埔条约》和《天津条约》的签订,外国在华办学变相合法化,各通商口岸教会学堂纷纷设立,至1859年,教会已在各地设立学堂50所,学生达1000人。[10](P226)在来自外部世界的生存挑战和现代化示范面前,中国被迫踏入现代化的门槛。1861年洋务派官员在“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指导下设立京师同文馆,次年设立上海广方言馆,是为新式学堂发展之嚆矢,标志着本土近代“新学”教育的发端。随后洋务派兴建了一批新的工业技术学校、外语学校和军事学校。在随后的40年间,“新学”教育继续发展,但这颗稚嫩的幼苗始终处于逆境之中,并没有茁壮成长为一颗参天大树。据不完全统计,甲午战争前,中国人开设的新学堂不过25处,从地域范围来说,仅仅分布于沿海7省;维新运动期间,也仅推出了150所新式学堂。[11](P2)
20世纪初,西方列强给予中国的巨大耻辱使清政府痛下决心进行政治革新,大规模的、制度性的教育改革就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1901年9月清政府下诏:将“所有书院,于省城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12](P4717)兴学正式成为国家政策。次年,清政府颁布《钦定学堂章程》,以京师大学堂为最高学府,以近代西方学制为蓝本,“以小学、中学、高等学堂(大学预科)与大学三级学校为主干,辅以师范学校与职业学校的近代“新学”教育制度在中国正式确立。1905年(光绪31)科举废止,近代“新学”教育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彻底胜利。由是,新式学堂在全国如洪水般不断涌现。从恢复、扩建京师大学堂开始,各省先后创办了高等学堂、中等学堂和小学堂,基本形成了大学、高等专科-都市省垣,中学、师范-府治,高小-县城,初小-乡镇这样的学校与行政梯次配备的体系,构成了初具规模的教育网。同时,新式学堂学生数量也直线上升。据统计,1902年全国新式学堂共有222所,学生6804人,[13]到1915年全国的新式学校增至129739所,学生达4294257人。[14](P364)1922-1923年全国各级学校数为178981人(除专门学校外其他教会学校未列入),学生数为6819486人(包括基督教会学生数在内)。[15](P926~927)从整个民国初期来看,1912-1928年新式学堂学生年均增长率为6.89%,远远高于同期中国人口年均增长率0.46%。[16](P30-31)
作为一种正式的社会化空间,“新学”教育以一种完全不同于旧学教育制度下旧式私塾、书院的新文化品格,大大扩展了普通民众的教育机会。旧学教育制度下,“国家崇儒重道,各地方设立学宫,令士子读书,各治一经,选为生员,岁式、科式、入学肄业,朝廷复其身,有司接以礼,培养教化,贡明经、举孝廉、成进士,何其重也!”[17]可见朝廷之所以谆谆言者,无非谓学校为士子入仕的阶梯。而“新学”教育跳出了传统“旧学”教育以科举取士、造就少数出类拔萃的仕宦人才为目的窠臼,以全体社会成员为教育对象,目的在于通过不同层次的教育,发挥每一个人的潜能,使之找到各自的最佳位置并培养其社会意识和国民精神。[11](P44)1904年《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明确规定“启其人生应有之知识,立其明伦理爱国家之根基,并调护儿童身体,令其发育”,最终使国家“识字之民日多”,为初等小学的教育宗旨。民国建立后,教育部公布《小学校令》,强调小学校以“留意儿童身心之发育,培养国民道德之基础,并授以生活所必需之知识技能”为宗旨。[18](P111-117)
新式学校的迅猛增加和“新学”教育机会的拓宽,无疑为绅士阶层提供了社会流动资源。与此同时,“新学”教育也失去了往日旧学教育制度的社会整合机制,成为乡村精英离乡的一种强大推动力。
传统旧学是一种与皇权结构相互支持的官学制度,是传统社会的一种独特的整合与凝聚机制。在典型的封建社会结构中,绅土阶层的社会流动基本依循由“贵而富”(即由社会权利而获取财富)的方向发展,他们通过传统旧学的科举制度(或其他非制度化途径)获取“功名”、“身份”,“学而优则仕”固然可以立于庙堂之上,学而不优也可凭藉已有的“功名”、“身份”回到乡村社会控制基层权力,“二者巧妙的运用使中央和地方都能受同一阶层的支配”。[19](P167)因此,传统乡绅都以其祖祖辈辈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死于斯的家乡故土为其根之所在。同时,科举时代,由于官僚职数的限额只能保证具有较高“功名”的士子进入官僚阶层,对于大多数绅士而言,只能以功名身份居处乡野。“沉积”乡间的绅士,事实上是一个庞大的“闲居”乡村的社会精英集团,约占绅士总数的96%,[7](P155)而参与社会流动的绅士阶层只占其总数的4%。
随着科举出仕制度的废除,通向上层特权的途径被彻底切断,地方绅土失去了晋升的希望和政治的屏障,不合时宜的“功名”身份渐渐失去了维系其基本社会地位的作用,后顾之忧已成现实。在这种情况下,“闲居”的绅士不得不寻求新的出路,完成自己应有的“社会角色”。他们或转向能够捞取新的社会资格的新式学校,并以此为中介,获得新的政治、经济、教育、工商、科技、军事、司法等适应社会结构变动需求的专门知识和技能,从而流向了社会各个层次;或向社会下层流动,舍弃“功名”而充任兵士,甚至流向秘密社会;[7](P175)或从权力空间日益狭小的村落视野中淡出,加入具有新时代特征的近代社团组织如农会、商会、教育会等,甚至直达省市县议会组织,投身于推动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民主化的洪流,企图寻求更广阔、更自由、更正式的权利空间。[20]据统计,湖北地区在清末20年间的4万绅士中,至少有2万余受过新式教育,约占绅士人数的43%。[21](P408)据民初《最近官绅履历汇编》统计,江苏地区具有双重身份的功名之士约占半数。[22](P530)在新学教育体制的驱使下传统绅士阶层的社会流动已从规模和流向上呈现出结构性社会流动的态势。
二
“新学”教育及新式学堂为旧式功名之士的社会流动和地位的重新选择提供了基本途径。而当时“新学”教育偏向城市、疏离乡村社会的历史特征,又成为乡村精英脱离“草根”,驻足城市的一支强效催化剂。
1.“新学”教育布局向城市倾斜
旧学教育制度下,教育的重心在乡村。政府设立的官学系统和书院系统,数量容积十分有限,其生员总数约为童生士子的1/10。[23]而且这些生员入学完全是名义上的,无需到学校,也没有规定学习课程,“平日则习礼于庙,研经于斋,课艺于庭,校射于圃,旁及书算法律”。[24]其余童生士子大多散漫居乡,或在私塾中受业,或闭门苦读,只在科考时汇聚应试。“新学”教育兴起后,教育布局偏重城市。这一点,从教育经费的分配比例即可明显看出。据1930年统计,初等教育平均每一学生经费只有8.14元,中等教育每一学生经费有94.70元,而高等教育每一学生经费达688.96元。[27]可见,中国政府对于为乡民大众而设立的初等学校,较之中等学校,尤其较之高等学校异常忽视。
如此,在政府的引导下,城市教育渐次发达,乡村教育则望尘莫及,随之教育基地重心也就逐渐从乡村转移到了城市。这样,整个中国的教育布局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京师大学堂、高等学堂、专门学堂、实业学堂、师范学堂等全部集中在京城、省城或其他重要的城市,中学堂基本上都设在各府、厅、直隶州的所在地,连小学堂也多设在州县所在地,乡村学校仅占全国学校总数的10%,[26](P167)即使是服务于乡村社会的农业学校也有将近80%设在城区。[3](P551-563)以民国二十年度(1931)为例,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共103所,建于上海的22所,北平15所,广东8所,仅这三座城市的高等学校就占总数的44%。全国大学和独立学院共75所,绝大部分建于北京等大城市,占总数的一半以上。[27](P770-777)以学生数计,北平、南京、上海、广州、杭州、武昌等6个城市共有大学生27506人,约占总数4/5以上。[28]大学教育集中于少数大都市的现象,实属可惊。再以初等教育为例,1930年全国各省市小学幼稚园平均密度为每一千公里9.6所,其密度最大者仍为上海、青岛、威海、北平、南京这几座大城市。而我国的大部分内陆省份以农村社区为主,现代化都市并未兴起,其新式学堂的密度远远小于前者。新式学堂如此布局基本上将农村排挤出去了,“教育变成了城市中的新专业”。[3](P646)
虽然“新学”教育推行之后,近代文明新风也吹入了广大乡村腹地,乡村“新学”教育取得了一定进步,但“新学”教育如此布局,结果又确立起大城市对中等城市,中等城市对小县城的文化支配。同时由于面向乡民大众的初等教育很少受到关爱,相对于“新学”教育蓬勃发展的城市而言,乡村社会的教育发展无异于小脚女人走路。有人估计清末民初中国共有乡村10万,村落100万。(注:世界著名农业经济学家白德菲博士Do.L Butterfield曾于民国十年(1921)莅华调查所得,中国当时至少有乡村10万,村落100万。)以此计算,至1922年,全国中小学校共178847所,平均每6村才有一所学校。至1931年,全国中小学校共262889所,平均每4村才有1所学校。(注:《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统计1922年全国国民学校及小学校177751所,中等学校1096所;1931年全国国民学校及小学校259863所,中等学校3026所。)可见,在广袤的中国农村大地新式学校远未普及。以河北省为例,到1928年为止大约有1/4村社尚未设立小学,有些县份甚至高达70%以上。[29]农村“新学”教育如此滞后,旧式私垫则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时至1935年,华北地区冀、鲁、豫3省共有私塾16827所,塾师16853名,学生257950名。若以县计算,平均每县有私塾48所,塾师48人,学生735人。考虑到当时很低的入学率,显然这是一个不小的比例。[31]不仅如此,有些地方虽有一二所初等小学,“不过刚有一形式”,[31](P453)其办学模式、教学内容基本上还是沿袭私塾那一套,虽非如“前清时私塾之教法,将所读之书日夜记诵,以为将来应试作文之材料”,但与正规、健康的教育还有相当的差距,即使孩子入学,他们也只不过稍微学点字了事。1919年11月,著名教育家经亨颐在山西晋祠参观一个学校,“牌上写着国民学校、义务学校并列的两行”,当他们进去,“只听得学生高声朗读起来,读的是什么?进去看看,才知道是修身教科书第一册第一页的目录。第一课父母——第二课兄弟—一第三课朋友……”[32](P216)义务教育普及率在全国首屈一指的山西尚且如此,其他省份可想而知。
“新学”教育重心向城市转移,乡村教育发展严重滞后,使得从前分散在乡、村、镇的学校集中于城市。如此则“新学”教育越是发展,离家进城的求学者就越多。30年代中期中央农业实验所对全国22省农民离村后的去向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农民个人离村到城市者共占离村总数的65.3%,而到城市求学者就占到了17.5%。[33](P177-178)这在以前是从未有过的。而接受了西洋文明洗礼的通都大邑与农村的习俗不尽相同,求学青年在长期的教育过程中必然要受到都市习俗的熏染,终至不能与农村的习俗协调,因此他们不再把家乡看做人生的最终归宿。
2.新式学校的教学内容与乡村社会疏离
科举时代教学的主要内容如四书五经八股帖式等虽和农业生产没什么直接的关系,但全国一律,并无什么城乡的分别,因此单从教学内容尚不足以造成城乡地域上的脱节,而且儒家经典所宣扬的人生标准“本能地引导吾们怀疑都市文化而倡导乡村文化”。[34](P321)饱受儒家经典熏陶的传统绅士,自然以乡村社会为其安身立命之所,或耕或读,将大半生时间留在乡间。诚如粱漱溟先生说:“在中国读与耕之两事,士与农之两种人。其间气脉浑然,相通而不隔。”[35](P11)
“新学”教育将过去八股经义一类的教学科目变为近代学校的许多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课程。据统计,在清末的普通学校里,传统知识的读经课程只占比重27.1%,数理化外语等新知识课程已占72.9%;到民国初年,传统的读经课程已经减少为8.4%,而新知识类课程竟达到91.6%。[36]从1933年全国专科以上学校课程种数与每周授课时数情况来看,“新学”教育的课程内容以法政、文哲、工程类所占比重最多,而与乡村社会密切相关的农林课程所占之比重则异常轻微。
受过“新学”教育熏陶的知识分子,在获得了新的适应工业化社会需求的专门知识和技能后,其事业模式与社会价值取向便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再也不可能像以前的乡绅那样把根深深地扎在家乡,或耕或读或什么也不干“到处闲逛”了。[37](P121)当然再也没有人“把一生的经历消磨在毛笔字、四书五经上了”,[35](P68)而是将近代社会中新兴的“商”、“学”、“法”、“工”乃至各种“自由职业”作为他们选择的方向。而这些职业机会多限于都市,在少数都市以外的地方无法施展其本领。由此,在城市里求学和从事自由职业的人则日益增多。仅以山西为例,民国元年自由职业者和学生的人数仅为300898,占总人口的2.98%,民国九年增至732947人,占总人口的6.4%。[38](P323)这充分证明了知识分子在城市与日俱增以及“新学”教育疏离乡村社会的事实。三四十年代关心乡村教育的费孝通、潘光旦、粱漱溟等人都认识到“新学”教育从一定意义来讲是工业文明的产物,加速了乡村精英外流的趋势,为乡土社会断送了人才,驱逐了人才。
3.各类专业学堂比例严重失调
从“新学”教育体系内部各类专业学堂的数量来看,其比例也远远疏离了乡村社会。据统计,1912年全国法政、工商、医学、外国语类专门学堂共有20所,而农业类专门学堂有10所,[14](P365)仅占所有专业学堂的33%。相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来讲,与农耕社会密切相关的农业学校在数量上实在少得可怜。不仅如此,随着“新学”教育的发展,农业专门学堂数量日益呈现出减少的趋向,而工业、法政学堂数量则与日俱增。到1923年全国法政类专业学堂增至33所,工业类专门学堂也增为13所,而农业类专门学堂则只有7所,[38](P419-420)占所有专业学堂的10%。此外,从专业学堂学生和教员的数量来看,在农校者远不如在工商法政者多。以1933年为例,全国专科以上学生共44167人,学法政者为16487人,占学生总数的37.2%,学文哲的有10064人,占22.6%,而学农林者只有1413人,仅占学生总数的3.2%。从教员的情况来看,在法政、文哲、工商等学校任教者远远多于在农林学校任教者。
当时,无论是教员还是学生都热衷于工商法政。不仅如此,就是仅有的几所农校里的学生也难以摆脱“学而优则仕”观念的影响,他们虽身在农校,志趣却不一定在农,其“入学校也,非以之为立身之本,乃藉以为扬名发财之具”,[40](P196)而且入学一二学期后相率转学的现象相当普遍。[41]即使勉强卒业,有很大一部分并不事农。据教育部调查,1917年全国农校学生毕业后务农者仅占55%。[42]河北定县62所村内肄业于中学以上的学生共267名,其中农校卒业生只有9名,就是这仅有的9人中只有4人事农,1人养蜂。[43](P233)由此看来,新式学校往往趋于培养适合城市文明的新型人才,而“不是为乡土社区造人才的”。[44](P72)
三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清末民初的“新学”教育失去了往日旧学教育制度内在的社会整合机制,而且“新学”教育制度较之旧学教育向普通民众提供了更为平等的教育机会,为绅士阶层提供了社会流动资源。同时,“新学”教育在很大程度上使各级新式学堂的地理分布、新学堂的教学内容、各专业学堂的比例等等都远远地疏离了乡村社会,这些都成为乡村精英离乡的强大推动力。此外新学教育的启蒙性,也使得接受新学教育的读书人在需要、利益等现代化观念的影响和激励下义无反顾地流向了城市。就这样,在教育体制的转轨过程中,乡村的读书人纷纷离去,有钱的出国留学,其次进了都市,再次的也去了城镇。乡村精英们在城里受过新教育,取得新资格后便再也不愿回到自己的家乡了,因为在那里不但没有他们享受更高教育的条件,而且没有他们谋生的机会。他们在都市求职定居,将乡居生活方式、文化价值观念一古脑儿抛弃掉,甚至死后也安葬在城市,不像以前一样要落叶归根了。
乡村精英大量外流对乡村社会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其一,中国城乡一体的传统文化从此出现了难以弥合的裂痕;其二,乡绅继替出现中断,基层政权日益地痞化,社会控制逐渐失范,社会矛盾尖锐;其三,乡村经济衰退,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本已衰败不堪的农村社会陷入了全面危机之中。这一系列互为因果的负面影响反过来又进一步加速了乡村精英离乡的步伐。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农村破产,日益剧烈,农民痛苦,日益深刻,各乡村普遍有一种兀臬不安的现象”。[45]鉴于农村社会破产的种种现实,一批有识之士开始将视野从城市转向中国广袤的农村,纷纷提出“到乡村去”、“到民间去”的口号。进步教育家陶行知、黄炎培、晏阳初、梁漱溟等发起、组织并领导的中华教育改进社、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乡村建设学院等社会团体,试图从改造农村教育入手,达到改进农村生活,建设美好新农村的目的。一些党政团体也鉴于农村问题的重要性,提出了“农村改革”或“农村改造”的政治主张,连国民党政府和一些地方军阀当局,也高喊要“救救农村”和“复兴农村”。一时间,打着各种旗号的农村活动或农村试验的乡村运动在中国大地上蓬勃兴起。据国民党政府实业部统计,30年代初期,全国从事乡村改良运动的团体达600多个,他们建立的乡村试验点或试验区有1000多处。[46](P19)轰轰烈烈的乡建运动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然而,对于满目疮痍的农村,他们的努力无异于精卫填海。“走向农村去”的急切呼唤,既不能改变农村精英人才流失的困境,又不能挽救乡村政权日趋退化的趋势。农村依旧贫困,农民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绿色的农村已经成为社会革命的温床。“如果与这个政治体系站在一边的城市上层分子不能引导农民奋起,反对派集团便有机可乘,他们会在农民的支持下,通过革命夺取政权,并以沟通农村与城市隔阂的单一政党的形式建立一个新的体制框架。”[47](P83)当中国共产党走向农村,发动农民反抗旧军阀的统治时,当时的社会状况对他们十分有利。1925年10月,中国共产党发表了第一个对农民的公开宣言《中国共产党告农民书》,明确地把解决农民问题与中国的前途联系起来。1927年大革命受挫后,在革命步履极其艰难的困境中,中国共产党在深刻的历史教训中更清醒地认识到了中国的基本国情,果断地把革命的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开始了土地革命、创建农村革命的根据地的伟大斗争。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在南方各省所辖区域内,普遍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试图以暴力革命的手段解决农村问题,从而为革命走向最后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