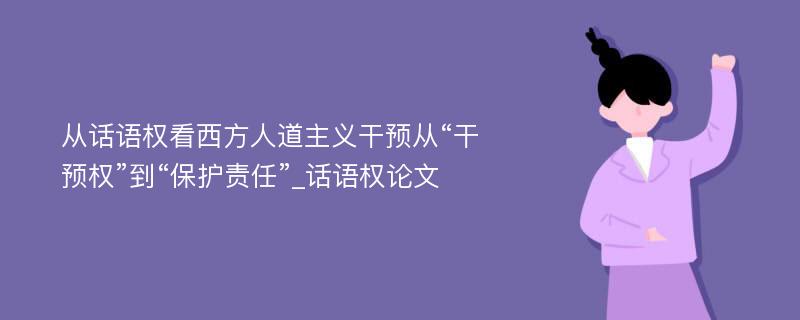
从“干涉的权利”到“保护的责任”——话语权视角下的西方人道主义干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道主义论文,视角论文,话语权论文,权利论文,责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前,人道主义干涉已成为国际关系中最具争议且广受关注的重要议题。从科索沃到伊拉克再到利比亚,人道主义干涉甚嚣尘上,已对现行国际秩序造成了重大冲击。从“干涉的权利”(the right to intervene)到“保护的责任”(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理论辩护不断推陈出新,人道主义干涉的合法性基础从而得以强化。人道主义干涉的理论与实践总是与国际政治的基本特征联系在一起的。冷战后,国际政治在一定程度上已成为“话语权政治”,例如,人权标准、恐怖主义的界定、核武器扩散以及气候谈判等诸多问题基本上都是以话语权之争的形式体现出来,人道主义干涉也不例外。“话语权”关系到国际事务的定义权,其对国际标准的制定权、对国际议题的设置权、对是非曲直的裁判权以及对国际行为合法性的构建都具有重要意义。 冷战结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围绕人道主义干涉构建了较为系统的话语体系,试图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赢得话语权,从而更加顺利地推行其人道主义干涉。20世纪90年代,西方国家以“人权高于主权”为依据塑造了“干涉的权利”,引发了科索沃战争与伊拉克战争。21世纪初,为了更好地主导在人道干涉领域的话语权,西方世界推进话语创新和话语升级,以“责任主权”为由建构了“保护的责任”,介入了利比亚危机,并试图在更大范围予以深入推进。那么,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是如何具体构建在人道主义干涉领域的话语权,其发展趋势又将如何?本文将从以下三方面予以回答:(1)“干涉的权利”的话语构建及其影响,以伊拉克禁飞区的设立和伊拉克战争为例;(2)“保护的责任”的话语构建及其影响,以利比亚危机为例;(3)中国如何应对西方国家在人道主义干涉领域的话语霸权。 一、为干涉辩护——人道主义干涉与话语权 随着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西方“自由民主主义再也不存在有力的意识形态竞争对手”。①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冷战后的国际格局中确立了前所未有的优势地位,得以按照自身需求重新塑造世界秩序。它们把向世界其他地区推广西方价值理念视为其使命和特权,对于敌视和反抗这一进程的国家,不惜动用武力加以干涉。当干涉行动侵犯他国主权,与联合国宪章的主权平等和不干涉基本原则相抵触时,“捍卫人权”就成为西方国家进行“人道主义干涉”最有力的依据。换言之,“为干涉辩护”是西方国家构建人道主义干涉话语的根本原因。 在南斯拉夫、伊拉克和利比亚,西方国家置和平解决危机的可能于不顾,认定“人道灾难”已刻不容缓,执意将武力干涉强加给当地民众;而20世纪90年代,美国在联合国已明确获知卢旺达将有种族屠杀发生的情况下,却阻挠、拖延增派联合国维和部队前往制止,致使80万平民在屠杀中丧生。②西方国家之所以能够无视联合国“国家主权平等和不干涉内政”的基本原则,根据自身价值观裁定危机的性质和当地政权的合法性,并自由选择干涉手段,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凭借其在人道主义干涉问题上的话语垄断。基于人道主义干涉话语霸权,西方国家塑造了强烈的道德优越感,在有关人道主义干涉的问题上,依据本国利益予取予求,使人道主义干涉成为实现西方国家私利的工具。 西方学者也不讳言人道主义干涉理论的辩护作用。“保护的责任”的发起人,干涉与国家主权委员会主席加雷斯·埃文斯(Gareth Evans)就明确指出,“保护的责任”的提出就是要改进极富争议的“人道主义干涉话语”(the discourse of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使人道主义干涉行动同时获得“正当性”(legitimacy)和“合法性”(legality)。③此后,西方学术界进一步将研究重点转向人道主义干涉理论,尤其是构建“保护的责任”话语体系,使其成为普遍、重要的国际规范。④结合西方国家在伊拉克、利比亚和达尔富尔等地的干涉行动,一些研究已经开始涉及人道主义干涉话语体系构建的利弊得失,着重探讨“保护的责任”能否成为具有实际约束力的国际规范,为西方国家的干涉行动提供更牢固的合法性基础。⑤ 国内相关研究则主要集中于人道干涉理论和西方人道干涉实践的发展历程评析以及相应的对策研究。早期的研究侧重于围绕人权、主权、霸权、国际秩序、国际法等核心概念对人道干涉理论进行基础性介绍与评析。⑥随着西方国家在人道干涉过程中“假人道、真干涉”的特征日益凸显,国内学者着力于揭示西方人道干涉行动背后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实质,并开始探讨限制滥用“人道干涉”的措施。⑦近年来,人道干涉理论进一步推陈出新,“保护的责任”得到了国际社会更广泛的接受和认同,深刻影响了西方国家的人道干涉实践。特别是在2011年以来的中东变局中,西方大国依据“保护的责任”对利比亚、叙利亚等中东国家实施了大规模干涉,而中国“不干涉他国内政”的立场则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相应地,西方国家人道干涉理论和实践的新变化以及中国的对策成为当下国内研究的重点。⑧ 其中,在“保护的责任”被国际社会广泛接受并得到实际应用后,国内学者逐渐开始有意识地关注其作为一个国际规范兴起和扩散的过程,并试图解释其背后的影响因素和动力机制。⑨一些学者认为,玛莎·芬尼莫尔(Martha Finnemore)和凯瑟琳·斯金克(Kathryn Sikkink)提出的“规范生命周期”理论,⑩能够通过国际规范兴起、普及和内化的生命周期模型来阐释“保护的责任”规范的演进,进而在“框定理论”(framing theory)的框架下,剖析规范倡导者是如何使用适当的“框定战略”,推动“保护的责任”规范在国际社会的扩散。(11)另一些研究则以“框定竞争”机制来解释国际规范演进过程中行为体的“话语交锋”是如何导致规范本身发生变异的,以此剖析“保护的责任”的发展路径与内涵变迁。(12) 大体而言,现有的研究已在某种程度上触及了人道干涉问题的话语权实质,认识到无论是“干涉的权利”还是“保护的责任”,其目的都是要调和人权与主权的矛盾,为干涉行动提供道义和理论支撑,但这些研究的重点大多是对西方人道干涉的既有理论和实践的静态分析,虽有助于正确认识和理解西方人道干涉,却无法有效阐释其因果机制,揭示其规律性特征,改变中国在这一问题上被动因应的尴尬处境。例如,国内学者以“规范生命周期”和“框定理论”为分析框架对“保护的责任”规范的兴起和扩散进行了动态分析,有其积极意义,但关注点集中于具体“话语内容”的演进与推广,未能系统地解释在人道干涉领域中国际话语权的构建与作用机制。就当前而言,从话语权的视角审视人道干涉仍是国内相关研究的薄弱之处。因此,本文认为,有必要从话语权的视角为西方人道主义干涉话语体系的构建提出一个完整而系统的分析框架,并以此为基础,对西方人道主义干涉话语及其干涉实践进行案例追踪,为改变当前中国在人道干涉问题上面对西方话语霸权时“失语”的被动状态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以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 二、“干涉的权利”的话语构建及其影响 话语权的概念最早由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提出。福柯认为,话语绝不仅仅是一种中性的表达工具,话语背后体现的是一种权力关系,是权力决定了“由谁说”、“说什么”和“怎样说”。(13)简言之,“话语即权力”。话语权的构建涉及话语主体、载体(话语内容和平台)以及客体(话语对象)三大基本要素,具体表现为话语主体通过一定的话语平台有效传达符合自身利益的话语内容,并得到话语对象接受和认同的过程。(14)在人道干涉问题上,西方国家便是遵循这一模式,以多元的话语主体构建高质量的话语内容,将特殊利益诉求塑造为“普世性”的价值理念,并借助以联合国为主的权威话语平台寻求国际社会的认同,使其干涉行动“师出有名”。基于此,本文将依照“话语主体—话语内容—话语平台—话语认同—干涉实践”的基本逻辑剖析西方人道干涉话语的构建过程及其影响。 为了论证人道主义干涉的合法性,西方国家在冷战后初期构建了以“干涉的权利”为核心的话语体系,伊拉克则是其最初和长期的“实验场”。从1991年和1992年分别在伊拉克北部及南部设立“禁飞区”,到2003年发动伊拉克战争,西方国家不断强化人道干涉话语以支撑其逐步升级的干涉行动。而正是美英等国对伊拉克的军事入侵,最终破坏了国际社会对“干涉的权利”的话语认同,推动了西方人道干涉话语的创新。因此,伊拉克问题是追踪西方人道主义干涉话语构建过程时不可忽视的重要案例。 (一)话语主体 作为冷战后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是最具意愿和能力进行人道主义干涉的国家,但西方人道主义干涉话语的构建却并非由美国政府独自推进。美国的重要智库和西方盟国都参与了这一进程。美国和平研究所(The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早在1992年就组织了有关“人道干涉”的讨论会,并出版了题为《海湾战争后联合国集体安全体系的挑战:人道干涉问题上的三种观点》(Post-Gulf War Challenges to the UN Collective Security System:Three Views on the Issue of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的研究报告。(15)同年的《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杂志对人道干涉问题也予以特别关注。罗伯特·库伦(Robert Cullen)在该杂志撰文指出人权在冷战后美国对外政策中的关键地位。他认为,苏联解体后一系列新生国家对集体权利(collective rights)或者说民族自决的渴望将威胁世界稳定,美国只有强调个体人权(individual human rights)方能避免卷入冲突,超然应对。(16)而在《外交事务》的《美国与世界1992/93》专刊的10篇文章中,有4篇论及人道干涉问题,对西方国家和联合国在南斯拉夫、波斯尼亚、索马里和利比里亚等地干涉行动的效果、正当性和必要性进行了全面分析和反思。(17) 人道主义干涉的首次官方阐述是由时任英国首相布莱尔于1999年在芝加哥经济俱乐部发表的“国际共同体主义”(Doctrin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讲话中提出的。而美国政府对人道干涉的表态却一直有所保留,强调美国的卷入只是“在某些情况下”才是“促进美国安全利益的有用工具”,因而美国的干涉应当是“有选择的”。(18)由此,美国便可不被无条件的道义承诺绑架,在选择干涉时机时掌握主动,根据美国国家利益决定是否介入。总之,智库、学术机构和政府等多元话语主体的相互配合,使人道干涉话语得到充分和严谨的学理论证,保证了话语内容的质量,增强了话语认同度。这样一来,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就能够扩大在干涉实践中的回旋空间,为西方人道主义干涉话语霸权的确立奠定了牢固基础。 (二)话语内容 话语权的构建还有赖于高质量的话语内容。西方人道主义干涉话语有着深刻的思想渊源并得到了系统的学术论证,具备较强的说服力,易于被国际社会接受。 正义战争理论是人道干涉话语最主要的思想渊源。该理论肇始于基督教和自然法学说对战争正当性的论述,以“何时诉诸武力”和“如何使用武力”两大问题为核心,回答了正义战争的标准问题。基督教神学家圣·奥古斯丁(Saint Augustine)和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从宗教视角出发,强调战争的理由和意图的正当性,认为只有以惩恶扬善、匡扶正义、维护人类和平和秩序为目的的战争才具有正义性。而自然法学家雨果·格劳修斯(Hugo Grotius)则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正义战争标准,包括:正当理由、对等性、成功的可能性、宣战、正当的权威以及战争作为最后的手段。(19)更为重要的是,格劳修斯曾明确指出:“对人类的暴行一开始,国内管辖的专属性就停止。”这被认为是关于“人道主义干涉原则最早的权威声明”。(20)进入20世纪,美国学者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对正义战争理论进行了更为系统的阐释。他认为,正义战争应是对诸如侵略、滥杀无辜这些显而易见的邪恶的一种回应以及对于使用武力时的某种限制,如避免诉诸强奸、向平民发动战争、酷刑和恐怖主义等暴行。(21)简言之,无论上述思想家或学者的具体标准有何不同,他们对战争正义性的共同理念是,武力的合法使用必须具有正义的理由和正义的手段,而这正是西方人道干涉话语构建的终极诉求。 西方国家对人道干涉的理论论述也充分反映了以上诉求。首先,为了塑造干涉行动的“正义理由”,西方学者和政治家在冷战后提出“新干涉主义”,以突破主权和不干涉原则的束缚。联合国宪章第一章第二条将主权平等和不干涉原则确立为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据此,任何国家都无权干涉他国内政。但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在安理会确定出现“和平之威胁、和平之破坏或侵略行为”时,由安理会授权便可“采取必要之空海陆军行动,以维护或恢复国际和平及安全”。(22)这条“例外”便成为新干涉主义的突破口。他们继承了格劳修斯的思想,提出:“当一个国家的政府严厉压制本国人民的人权,或者当中央政府的腐败行为造成无辜人民容易遭受攻击的时候,干涉(包括来自外部的军事干涉)就是合理的,甚至是必须的。”(23)布莱尔在“国际共同体主义”讲话中进一步指出,全球化使得各国成为相互依赖的命运共同体,国际国内事务已无法完全分离,一国内部若出现“人道灾难”不可避免地会影响他国人民。因而,人道灾难尤其是种族屠杀应被明确界定为“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其他国家和人民自然拥有“干涉的权利”。(24)这就将西方国家对发生“人道灾难”的国家或地区的干涉塑造为符合联合国宪章的正当行为。 其次,为了论证干涉手段的正义性,沃尔泽的“双重效果”原则成为西方人道干涉的直接理论依据。沃尔泽提出,在作战过程中,如果能够满足如下四个基本条件,那么即便导致了伤及无辜的后果,也是情有可原的。(1)采取的行动本身是好的,或者说是合法的战争行动;(2)行动导致的直接后果在道德上是许可的:摧毁军事补给或消灭敌人;(3)行为体的意图是好的,它只想获得许可的结果,并非要寻求邪恶的结果或将之作为得到这一结果的手段;(4)好的结果能够完全弥补恶果。(25)依照这种观点,只要能以“保障人权”的正义借口得到干涉授权,西方国家便可自由把握干涉手段的尺度,即便给被干涉国家或地区的人民带来新的“附带损害”也是可以接受的。总之,上述话语内容以崇高的道义诉求和全面的理论论证为西方干涉行动提供了系统的合法性辩护。但高质量的话语内容并不能自动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西方国家在话语平台上的优势地位也不可或缺。 (三)话语平台与话语认同 在人道干涉问题上,话语认同的构建与话语内容在话语平台上的表现效果联系密切,本文将二者结合起来加以论述。如前所述,联合国安理会是对外干涉、特别是武力干涉行动的唯一合法性来源。因而,联合国自然成为人道干涉话语必须争取的权威性话语平台。1991年4月2日和4日,土耳其与法国政府接连向安理会紧急要求讨论解决土伊边境的库尔德难民问题,认为伊拉克政府对库尔德人的镇压导致大量难民流离失所并危及地区稳定。4月5日,安理会通过了688号决议,“谴责对伊拉克境内许多地区平民的镇压……其后果威胁到该区域国际和平与安全”。(26)这是安理会首次确认一国内部事务会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也是联合国首次公开干预一国内政,标志着联合国原则上认同了一国国内的“人道灾难”将赋予国际社会以“干涉的权利”,对西方人道干涉话语的构建具有里程碑意义。 此外,大众传媒是话语传播最直接和有效的载体。西方国家利用占绝对垄断地位的媒体进行政策宣传,并将敌对国家及其领导人刻画为“反人类”的“暴君”,以争取民众的支持。这在伊拉克战争前夕表现得最为充分。战前的美国媒体抛弃了“价值中立”的新闻原则,为战争张目。美国的电视和网络“突然间出现了大量退伍军官和支持战争的专家在解读新闻”。(27)萨达姆被塑造为邪恶疯狂的独裁者,残酷镇压和屠杀境内的库尔德人,是基地组织和九一一事件的幕后支持者,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WMD),随时准备进攻美国。这种宣传取得了较大成功。统计表明,战前有45%~66%的美国人相信伊拉克为九一一袭击提供了援助,70%~90%的民众认为伊拉克将用WMD进攻美国,更有高达95%的民众从确信伊拉克至少正在制造这些武器。最后,有74%的民众支持对伊拉克开战,而到2003年3月,有55%的民众支持在没有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攻打伊拉克。(28) (四)对伊拉克的干涉实践 尽管拥有多元话语主体和较高质量的话语内容,西方国家在伊拉克的干涉实践却破坏了苦心经营的“干涉的权利”话语体系。 首先,联合国并未给予“干涉的权利”完全的支持。在表决688号决议时,中国和印度弃权,也门、古巴和津巴布韦三国则投了反对票。这些国家坚持认为伊拉克没有跨越边界与他国发生战事,目前局势属于伊拉克内政,安理会不应干预。此外,688号决议没有明确授权采取任何军事行动。但美英等国在伊拉克设立禁飞区时却都援引该决议。1996年9月4日,联合国一位官员表示:“在伊拉克境内设立‘禁飞区’是部分国家根据自己对安理会688号决议的解释做出的,并非得到联合国的直接授权。”(29)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Javier Perez de Cuellar),也认为美英执行的人道援助行动都应事先得到伊拉克当局的同意。(30)这表明第三世界国家仍非常重视主权平等和不干涉内政原则,担心“干涉的权利”将成为西方社会肆意干涉他国的工具,而安理会对人道干涉中武力的使用也十分审慎。 其次,美英等国以伊拉克政府与基地组织勾结和拥有WMD为由发动伊战。而当战争结束,它们却未能找到决定性证据支撑当初的开战理由,于是,对伊拉克境内的“人道灾难”进行干涉、惩罚萨达姆对库尔德人的屠杀便成为证明伊战合法性的最后依据。然而,所谓“干涉的权利”,应是在大规模的侵犯人权事件发生之前或当时采取干涉,从而阻止事态恶化,捍卫人权,显然不应用于事后惩罚。(31)在人权已经被侵害后才进行军事干涉是毫无意义的。不仅如此,伊拉克战争造成了巨大的平民伤亡,从2003年3月至2009年底,共有28.5万人伤亡,至少10.9万人丧生,其中63%为平民。(32)战争中,伊拉克的众多宝贵文物遭到损毁和抢劫,美军虐待战俘事件频繁发生。所谓的人道干涉却给伊拉克带来了更大的人道灾难。 综上所述,西方国家围绕“干涉的权利”初步构建了一套完整的话语体系,获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同(如安理会的688号决议),但这种共识是有限度的。第三世界国家对“干涉的权利”对国家主权的侵蚀非常警惕,联合国安理会也从未依据“干涉的权利”授权开展任何军事行动。尽管西方国家一直试图以“干涉的权利”证明其行动的合法性,但不论在科索沃还是伊拉克,西方国家的军事干涉都未得到安理会的授权,事实上都不合法。然而,凭借西方国家的实力优势和大众传媒塑造的民意支持,美英等国一再根据自身需求随意解释和引用安理会决议,自由决定干涉时机和方式,甚至绕开安理会发动单边军事行动。伊战的爆发最终瓦解了国际社会对“干涉的权利”的脆弱共识,使美英“人道卫士”的形象难以为继,促使酝酿了十多年的“保护的责任”走上前台,并在利比亚战争中得到了全面实践。 三、“保护的责任”的话语构建及其影响 2001年12月,干预和国家主权委员会(ICISS)向联合国秘书长提交了《保护的责任》报告,该报告系统地阐释了“保护的责任”理念,希望以此替代一般意义上的人道主义干涉的权利。根据这份报告,“保护的责任”是指国家有责任保护本国公民免遭可以避免的灾难——免遭大规模屠杀和强奸、免遭饥饿等,而当国家不能或者不愿意提供这种保护时,国际社会必须承担起相应的责任。(33)此后,时任秘书长安南及其任命的“威胁、挑战和改革”高级别名人小组对该报告给予了积极回应。2005年9月,“保护的责任”被写入联合国《世界首脑会议成果文件》,被国际社会所接受。在2011年开始的西亚北非动荡中,“保护的责任”成为西方国家干预危机的主要依据,利比亚战争则成为“国际社会”以军事手段实施“保护的责任”的第一次实践。(34) (一)话语主体 在话语主体方面,“保护的责任”同样不是以美国政府为唯一主体构建,智库和基金会等非政府组织在该话语构建过程中的作用更为显著。其一,“保护的责任”的概念是由加拿大政府会同一批基金会所组建的干预和国家主权委员会提出的,瑞士和英国政府也提供了相关经费支持。(35)其二,智库和非政府组织在“保护的责任”话语的构建与宣传中发挥了更加积极的作用。2004年底,“美国和平研究所”的研究团队向美国国会提交了《美国利益与联合国改革》报告,在第二章专门阐述美国政府对“保护的责任”的立场。2008年,美国大屠杀纪念馆、美国和平研究所和美国外交学院又联合推出了题为《预防“种族灭绝”:美国决策者的蓝图》的报告。这两份报告都提议美国主动承担落实“保护的责任”的使命,支持联合国将“保护的责任”确立为国际社会的“规范”。(36)而美国大屠杀纪念馆历来就是通过展现诸如纳粹屠杀等悲惨历史,向民众宣传美国价值观的伟大以及美国对世界和平自由所负责任的机构。它们的报告不仅起到了论证和政策建议的作用,更扩大了“保护的责任”的群众基础,增强了话语认同。 (二)话语内容 从话语内容来看,“保护的责任”的构建从一开始就是对“干涉的权利”有意识的改良与话语升级。在《保护的责任》报告的第二章,ICISS以《辩论用语的改变》为题专门阐述了传统的“干涉的权利”话语的不足。ICISS认为“干涉的权利”至少有三个缺陷:第一,必然更多地关注潜在干预国的权利和特权而不是这一行动的潜在受益者的迫切需求;第二,仅仅将焦点对准干预行为,并未充分考虑事先的预防性努力和后续援助的重要性;第三,容易形成“干预可以压过主权”的错误印象,过度表达了对主权的公开攻击。(37)ICISS强调应当转换关于“干涉的权利”的疲劳争辩,重新“刻画”这一概念。(38)为了调和人权与主权的矛盾,消除第三世界国家对西方大国利用“干涉的权利”侵犯他国主权的疑虑,转变西方人道干涉在伊拉克和科索沃所遇到的“合理但不合法”的尴尬处境,该委员会认为应该主要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改进。 第一,重塑主权概念。强调“国家主权意味着责任”,保护国内公民的生命和安全首先是国家本身的职责。而“一旦人民因内战叛乱镇压或国家陷入瘫痪且当事国家不愿或无力制止或避免而遭受严重伤害时不干预原则要服从于国际保护责任”。(39)国际社会的干涉由此成为协助国家主权履行保护责任的重要补充,弱化了干涉与主权的对立。第二,提出“保护的责任”的“三要素”。ICISS认为,“保护的责任”绝不仅仅涉及干涉行动,它应当包含“预防的责任”、“作出反应的责任”和“重建的责任”三部分,其中预防是最为重要的责任。(40)这一改进将关注点由干涉者的权利转向被保护者的利益,完善了人道干涉的行动链条,防止“保护的责任”被当作干涉的借口,一旦决定干涉,就必须负责到底。第三,提出军事干涉“六原则”,包括正当的理由、合理的授权、正确的意图、最后的手段、均衡性以及合理的成功机会。(41)只有在这些条件都满足时,军事干涉才是合法的。这些原则继承了格劳修斯正义战争标准的有关论述,使得武力干涉的适用条件更加严格,通过谨慎选择军事干涉的时机,保证干涉行动得到国际社会最大程度的支持。 总之,ICISS全面重塑了西方人道干涉话语,不再从干涉方立场出发强调“权利”,而是关注于保护被干涉国民众的“责任”,同时对武力干涉的条件作出了更加严格的限定。这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人权与主权的对立,转而强调二者的一致性,希望在完全不违反联合国宪章原则的前提下,强化人道干涉的合法性,并试图将“保护的责任”确立为被世界各国广泛接受的国际规范。 (三)话语平台与话语认同 同样,联合国依然是塑造“保护的责任”话语认同的关键话语平台。总体来看,ICISS的目标部分得以实现。与“干涉的权利”仅在安理会的相关决议(688号)中得到间接承认不同,“保护的责任”在未付诸实践之前就得到了联合国大会、安理会和联合国秘书长的积极支持,原则上为国际社会大多数成员所接受。 2004年12月,联合国“威胁、挑战和改革”高级别名人小组向秘书长安南提交了题为《一个更安全的世界:我们的共同责任》的研究报告。该报告首次接受“保护的责任”理念,指出“威斯特伐利亚体系首次提出国家主权概念,不管当初盛行的理念如何,今天,这一概念显然含有一国保护本国人民福祉的义务……但是,如果它们没有能力或不愿意这样做,国际社会就应承担起这一责任,并由此连贯开展一系列工作,包括开展预防工作,在必要时对暴力行为作出反应,和重建四分五裂的社会”。(42) 2005年10月24日,第60届联大通过了《世界首脑会议成果文件》,该文件第138和139条确认“每一个国家均有责任保护其人民免遭灭绝种族、战争罪、族裔清洗和危害人类罪之害……如果和平手段不足以解决问题,而且有关国家当局显然无法保护其人民免遭种族灭绝、战争罪、族裔清洗和危害人类罪之害,我们(国际社会)随时准备根据宪章,包括第七章,通过安全理事会逐案处理,并酌情与相关区域组织合作,及时、果断地采取集体行动”。(43)这是目前有关“保护的责任”最为重要的联合国正式文件,标志着“保护的责任”开始向国际规范转变。 2009年1月12日,秘书长潘基文向联大提交了《履行保护的责任》报告。这是联合国秘书处有关“保护的责任”的首份文件。其目的是要将“保护的责任”转化为政策性纲领,提出具体落实“保护的责任”的战略。报告认为,“国家的保护责任、国际援助和能力建设、及时果断的反应”是履行“保护的责任”的“三大支柱”,同时指出,“该战略强调预防的价值,而在预防失败时,根据每一局势的具体情况及早作出灵活反应,也十分重要”。(44) 从各成员国对联合国上述文件的反馈来看,《世界首脑会议成果文件》得到了150多个国家的签署,而在联大对《履行保护的责任》报告的讨论中,94位发言人中有2/3以上持肯定态度。(45)这表明,“保护的责任”已经得到了世界大多数国家的认同。正如埃文斯所说,“我们现在所讨论的是‘如何’,而非‘是否’要执行保护的责任,(因为)当前已经没有任何国家质疑这项原则了”。(46)然而,联合国并非毫无保留地接受了“保护的责任”。《世界首脑会议成果文件》缩小了“保护的责任”的适用范围,明确限定为灭绝种族、战争罪、族裔清洗和危害人类罪四种情况。(47)文件强调本国政府保护公民的责任以及国际社会以和平手段进行援助的责任,但同时规定,只有援引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由安理会授权后才可使用武力,且安理会必须“逐案处理”决定是否授权。(48)这些限制条款表明,各国对“保护的责任”的共识仍是脆弱的,国际社会在人道干涉的实践层面,特别是武力使用上的分歧和疑虑依旧,绝大多数国家仍将安理会视为军事干涉的唯一合法性来源,不愿赋予他国依据“保护的责任”使用武力的自由。 (四)对利比亚的干涉实践 2011年西方国家在北约框架下对利比亚的干涉是“保护的责任”的首次实践,也被视为“保护的责任”一次“教科书式”的应用。然而,与伊拉克问题相似,西方国家在取得安理会对利比亚的干涉授权后,擅自升级干涉目标,以军事手段推动利比亚政权更迭,使国际社会对“保护的责任”的脆弱共识再次趋于瓦解。 西方媒体在建构北约干涉利比亚的合法性过程中同样发挥了关键作用。从危机一开始,西方媒体就以大量带有明显倾向性的报道将利比亚局势定义为卡扎菲政府对手无寸铁的反对派民众的血腥镇压与屠杀。以2011年2月15日班加西爆发抗议示威为起点,2月16日至3月19日,英国《卫报》对利比亚的报道主题量居前三的分别是卡扎菲及其支持者通过暴力与非暴力方式维护权力统治、反对派的失利与求助国际社会和利比亚人民的苦难。直至利比亚战争结束,在《卫报》161篇涉及卡扎菲行动的报道中,除了3篇涉及卡扎菲的某些政绩,其余158篇都是卡扎菲的负面行为,涉及比例最高的行为是向平民派遣军队与使用重型武器,占37.9%。(49)但事实上,利比亚政府在抗议活动初期对反对派使用的都是非致命性武器,如橡皮子弹和高压水枪。联合国利比亚国际调查委员会的报告表明,“直到示威者获取了武装后,卡扎菲政府才开始使用实弹”。(50)此外,西方媒体在危机初期还过分夸大了反对派和民众的死伤数量。法新社曾采访了一名2月21日从班加西回国的医生,并根据他所在医院的伤患情况报道称,班加西及其周边地区至少有2000人以上死亡。(51)然而,人权观察组织的记录显示,在该名医生回国之前,利比亚仅有223人死亡。(52) 正是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下,卡扎菲政府“残酷镇压和平示威”的行动遭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谴责。联合国安理会于2月26日通过第1970号决议,“斥责严重、有系统地侵犯人权,包括镇压和平示威者,对平民死亡深表关切,并明确反对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政府最高层煽动对平民的敌意和暴力行为”,明确指出“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当局有责任保护其人民”,并对利比亚实施包括武器禁运、移交国际刑事法院审理、旅行禁令和资产冻结等非军事的强制手段。(53)但上述制裁并未能阻止利比亚局势的持续恶化,3月17日,安理会通过第1973号决议,“重申利比亚当局有责任保护利比亚民众”,并“认为目前在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发生的针对平民人口的大规模、有系统的攻击可构成危害人类罪”,“授权已通知秘书长的以本国名义或通过区域组织或安排和与秘书长合作采取行动的会员国,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便保护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境内可能遭受袭击的平民和平民居住区……决定在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领空禁止一切飞行,以帮助保护平民”。(54)3月20日,北约联军在阿盟成员国的协助下在利比亚建立“禁飞区”。 危机伊始,包括秘书长在内的联合国官员就使用“保护的责任”话语评估利比亚局势。2011年2月22日,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纳维·皮莱(Navi Pillay)就利比亚危机发表声明时称:“国家有责任保护公民的生命、自由和安全……在维护秩序和法治时,保护平民应永远是最优先的考虑。”(55)此后,安理会1970和1973号决议也全面贯彻了“保护的责任”的基本精神。而北约依据1973号决议建立“禁飞区”更是完全符合2005年联合国“成果文件”中所隐含的关于国际社会实施武力干预的所有条件:反人类罪、和平手段无效、安理会授权、地区性国际组织支持、集体行动。(56)更为重要的是,这是安理会首次在未得到当事国同意的情况下以保护人权为由授权使用武力。(57)相较于前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有关“美英的人道干涉应得到伊拉克当局同意”的表态,“保护的责任”显然为北约对利比亚的干涉提供了更强的合法性和道义支撑。如果北约在此基础上以保护平民为最终目标,切实履行其责任,此次干涉的确能够成为“保护的责任”的典型实践。 但事实却并非如此。如果只是为了保护平民,北约应在建立“禁飞区”后消灭威胁平民生命安全的军事力量,最终促使冲突双方达成停火协议。然而,干涉行动开始后不久,北约的目标就已经演变为推翻卡扎菲政权。北约军队在发动干涉后不到两周便对驻扎在卡扎菲故乡苏尔特的利比亚政府军进行轰炸,而这些部队实际上是不可能对平民造成伤害的,因为当地民众都是支持卡扎菲政权的。(58)不仅如此,北约国家不但不寻求实现停火,反而不断为反对派提供武装支持,扩大战争。2011年3月4日,在安理会授权之前,英国就宣布向利比亚东部的反对派武装派遣军事顾问;4月中旬,卡塔尔开始为反对派运送法国的反坦克导弹;而到了5月初,法国直接为利比亚西部的反对派空投武器。(59)最后,北约还无视甚至破坏实现利比亚政治和解的进程。非盟一直在卡扎菲政权和反对派之间斡旋,5月底,卡扎菲表示愿意接受非盟的和平路线图,美国却认为这一表态不可信任。7月初,利比亚政府军节节败退,卡扎菲提出愿意无条件谈判、交出权力,美国却要求卡扎菲必须下台。(60)针对北约干涉目标的转移,加雷斯·埃文斯在3月24日发表评论,认为北约干涉的唯一正当理由就是保护利比亚平民免遭卡扎菲屠杀,“政权更迭”应当由利比亚人民完成,而不应由北约推动。(61) 事实证明,“保护的责任”的话语构建只是改变了争议的措辞和辩论的视角,而言辞的改变并不能回避争议,也不能解决实质问题,(62)干涉与主权的矛盾依然存在。西方国家在利比亚复制了它们在伊拉克的行动模式:以捍卫人权之名展开干涉,在达成保护平民的目标后却继续扩大战争,直至实现政权更迭,这直接导致利比亚民众承受了更为严重的人道灾难。2012年3月2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组建的调查团就利比亚危机期间出现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发布报告称:“利比亚内战双方均犯下了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行……冲突期间,该国平民遭受了大规模的攻击,平民遭受的暴行包括谋杀、强迫失踪、酷刑、任意逮捕和掠夺。”(63)作为“保护的责任”的首次实践,北约对利比亚的干涉只能是一部反面教材。利比亚战争后,“1973号决议中所体现的国际社会对‘保护的责任’的共识正在走向崩溃”。(64) 四、解构西方话语霸权——中国的应对之道 通过政府、智库、基金会等多元话语主体的共同推动,西方国家构建了高质量的人道干涉话语。从“干涉的权利”到“保护的责任”,以正义战争理论为基础,经由系统的学术论证,人道干涉话语的说服力和认同度得以提升。尤其是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ICISS对人道干涉话语进行了有意识的改良。2004年起,联合国在其正式文件中逐步接受并应用“保护的责任”概念,世界大多数国家对“保护的责任”的基本原则达成共识。 尽管西方人道干涉话语构建不断完善,但西方国家自冷战结束以来的人道主义干涉实践却并未发生实质性转变。在发起干涉之前,美英等国利用国际舆论,或伪造事实(伊拉克拥有WMD),或夸大事态(利比亚的平民伤亡),宣称危机已迫在眉睫,以获取安理会的干涉授权。一旦得到授权(即便不是明确的武力干涉授权),便对安理会相关决议文件作出符合本国利益的解释,以远远超出“必要”的手段滥用授权:在建立禁飞区并保证了平民安全后,却无视安理会的禁飞令和武器禁运,延续并激化冲突,直到彻底推翻敌对政权为止。其后果便是干涉的“附带损害”过高,大量平民和非军事设施并未得到真正的“保护”,反而成为“人道干涉”的牺牲品。西方国家扶植的新政权又无法长期掌控局势,导致被干涉国持续动荡,国家重建遥遥无期。 总之,西方人道干涉话语本应以提升干涉行动的正义性与合法性为目标,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干涉实践中却仅仅将其视为实现国家利益的工具。表面上看,“干涉的权利”和“保护的责任”对干涉时机和手段的选择都有所限定,但西方国家在执行干涉时却处处模糊其行为。迄今为止,西方国家通过有意识的话语构建巩固了人道干涉的道义基础,提升了国际社会对这一话语的认同,并使其初步成为得到大多数国家接受的国际规范。然而,它们在阿富汗、伊拉克和利比亚等地进行的人道干涉在本质上却更多地受其国家私利的驱动而非基于真实的人道危机。依靠话语霸权,西方国家得以根据自身利益需要选择干涉对象,其干涉实践不仅偏离了“捍卫人权”的根本目标,反而在多数情况下导致了更严重的人道危机,侵蚀了其苦心经营的话语认同。 一方面,西方国家在人道干涉过程中“言行不一”;另一方面,一贯坚持主权平等和不干涉内政原则的中国在有关人道干涉的问题中依然处于被动地位。在苏丹,中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与其展开经贸和能源合作,帮助苏丹建立了基本完整的石油工业体系,使其从石油进口国变为出口国。2005年5月,中国积极响应安理会1590号决议,成为首批向苏丹派出维和部队的国家。2007年9月,联合国苏丹特派团分别授予中国维和部队工兵分队、运输分队和医疗分队“集体特殊贡献奖”。但西方国家却无视中国促进苏丹和平与发展的种种努力,称中国对苏丹的援助与合作是对“流氓国家”的支持,是“新殖民主义”式的资源掠夺,破坏了非洲国家致力于民主改革和追求良治的努力。(65)2012年2月4日,中俄否决了安理会叙利亚问题决议草案。美、英、法等国再次无视中国提出的“尽快推动启动叙利亚人民主导的、各方广泛参与的包容性政治进程,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分歧和矛盾,使叙利亚形势恢复稳定”(66)的合理主张,指责中俄不顾叙利亚民众人权,包庇巴沙尔政府。美驻联合国代表宣称,“数月以来,安理会一直为两个成员所挟持”,并认为中俄两国的否决是“执意出卖叙利亚人民而庇护一位懦弱的暴君”。(67) 话语权的缺失是中国在人道主义干涉问题中面临如此困境的关键原因,而西方人道干涉话语构建与实践之间的上述矛盾则为中国扭转在人道干涉问题中的被动局面提供了契机。作为崛起中的大国,中国必须打破西方国家的话语垄断,变被动应对为主动塑造,积极争取话语权,从人道干涉话语构建和干涉实践两个层面介入人道主义干涉国际规范的构建,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以促进国际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第一,重视话语主体多样性,提升话语内容质量。在话语构建层面,相较于西方国家政府与智库、基金会等多元话语主体的密切配合,中国人道干涉话语主体单一,过度依赖政府。这一方面使中国人道干涉话语内容多为官方政策宣示,难以获得国际社会较高的话语认同度;另一方面也使中国人道干涉话语缺乏理论支撑,削弱了话语说服力。因此,着力培育话语主体的多样性,为人道干涉话语的构建提供智力支持,是建立中国人道干涉话语权的重要基础。政府应引导相关智库和学术机构进行有意识的人道干涉话语研究,经由严谨的学理论证,在系统批判西方人道干涉话语缺陷的基础上,使中国人道干涉话语得到国际社会的理解和认同。 就话语内容而言,“保护的责任”的基本理念目前已经得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的接受,而“保护的责任”将主权国家作为保护平民的第一主体,并通过严格限定干涉时机和动武条件以提升西方干涉行动合法性的思路实际上也与中国的立场部分契合。但必须指出,当前“互不干涉内政”作为中国处理对外关系的基本原则不会动摇。因此,在实践层面中国所接受的只能是受到最严格限定的“保护的责任”,它必须满足以下条件:(1)主权国家是履行“保护的责任”的第一主体;(2)“保护的责任”仅在灭绝种族、战争罪、族裔清洗和危害人类罪四种情况下才可适用;(3)基于“保护的责任”所进行的武力行动,只能依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由安理会逐案审理,决定是否授权。在此前提下,中国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用西方人道干涉话语揭示西方人道干涉实践的虚伪性,提升中国在人道干涉问题上的话语权。 具体而言,中国可围绕以下两个核心理念展开话语内容的构建:其一,强调主权国家在保护人权中的首要地位。当前,面临人道危机的国家皆为发展中的新兴民族国家,它们或是旧帝国崩溃后的遗产(如南斯拉夫、伊拉克、利比亚等),或是在西方殖民体系瓦解后获得独立(如卢旺达等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这些国家民众的基本人权得不到保障的根源在于缺乏一个健全的国家和有效的政府。因此,将主权与人权对立起来的“干涉的权利”无法解决这一问题,而从“保护的责任”视角来说,要想彻底消除这些国家的人道危机,根本手段应当是帮助这些国家建立起足以担负起保护公民基本人权责任的主权国家。如果出现真正的人道危机,国际社会的行动必须是建设性和辅助性的,在制止人道灾难后,应将被干涉国的前途和命运交给本国民众,而非一再以超出必要的军事行动干扰甚至破坏它们的发展进程。 其二,利用西方人道干涉话语的发展新趋势,坚持要求西方国家完善干涉链条。中国虽然坚定主张“互不干涉内政”原则,但当西方国家以“人道”为由展开干涉行动,与其消极因应、放弃话语权,不如主动利用西方话语约束其行为,确保相关行动真正有利于人道危机的解决,这也符合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68)从“保护的责任”的“三要素”理论来看,西方国家在实施所谓人道干涉时,只注重“作出反应的责任”,而忽略了“预防的责任”和“重建的责任”。中国应坚定立场,主张人道主义干涉务必以维护遭受人道危机的民众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预防、作出反应和重建缺一不可。主权国家与国际社会的首要责任是“预防的责任”,防止人道灾难的发生是保卫人权的最优选择。当未能事先阻止人道灾难而必须采取行动,尤其是军事行动加以干预时,就必须保证干涉的“后果可控性”,干涉的“附带损害”应降至最低,更不能造成超出原有人道灾难所造成的伤害。被干涉国平民的安全一旦得到保障,军事干涉行动即告终止,绝不允许干涉国为私利继续扩大战争。最后,实施干涉的相关国家和国际组织应制定完整的重建路线图并切实履行重建责任,直至被干涉国家或地区恢复秩序为止。 第二,主动掌控话语平台,重塑人道干涉国际规范,有效监控西方人道干涉实践。话语平台是话语的表达渠道,是一国话语权的关键载体。高质量的话语内容只有在适当的话语平台得到有效的传播和扩散,才能被话语对象了解,继而获得理解和接受。在人道干涉问题上,话语平台的重要性更加凸显。现存国际秩序中,联合国不仅是人道干涉话语传播的核心渠道,更是人道干涉行动的权威合法性来源。一国的人道干涉话语唯有进入联合国的议事日程,并得到绝大多数成员国的认可方能产生影响力,进而影响人道干涉实践。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有理由也有责任介入联合国这一权威话语平台,在有关人道干涉的问题上塑造中国的话语权。具体方式便是以安理会为核心,推动联合国框架下的人道干涉授权和监督机制的建立与完善,将中国立场融入新型人道干涉国际规范。 首先,根据2005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文件》,联合国可在安理会的框架下设立以五个常任理事国为主导的专门的人道干涉授权和监督机构,将定义人道主义危机、确定人道干涉手段的权力掌握在安理会手中,由安理会逐案处理人道干涉问题。2009年潘基文在《履行保护的责任》报告中提出的“狭窄而深入”的原则应成为上述机构在落实“保护的责任”时的指导精神。具体来说,“保护的责任”只能适用于灭绝种族、战争罪、族裔清洗和危害人类罪四种情况,不可过度扩展这一概念,丧失其实际作用。在使用范围保持狭窄的同时,国际社会的反应却需深入,决定干涉后需动用联合国成员国、联合国系统、区域组织和次区域组织以及民间社会现有的各种预防和保护工具,(69)以保障目标的达成。 其次,在建立了由中国参与主导的人道主义干涉授权和监督机制后,中国可倡导确立一系列人道干涉的具体实施规范。目前来看至少应包括以下几项:第一,人道干涉授权的唯一合法来源是联合国安理会,且安理会须结合实际情况逐案处理干涉授权,决定是否以及如何干涉,不设立普遍通用的授权标准;第二,干涉行动开始后,联合国需派遣调查组进驻相关国家或地区,全面监督干涉执行情况,并向联合国提交报告;第三,安理会可讨论设定一套具体标准,明确限定干涉的“附带损害”上限和终止干涉的标准。一旦联合国调查组认定干涉行动对平民和非军事目标造成过度伤害,或干涉方在实现干涉目标后继续军事行动,即可宣布相关国家或组织的行动非法;第四,军事干涉结束后,执行干涉的国家或国际组织务必制定并向联合国提交重建路线图,并由联合国监督实施。 综上所述,面对西方国家的话语霸权,中国应以西方人道干涉话语构建和干涉实践之间的矛盾为突破口,重塑有关人道主义干涉的国际规范。利用“保护的责任”中所包含的西方国家创立和鼓吹但却未能实际履行的核心理念(如“作为责任的主权”和“预防、作出反应和重建的责任”),在限制西方国家干涉行动的同时增强中国人道干涉话语的认同度。在联合国框架内,建立由中国作为重要参与者,并由安理会主导的人道干涉授权与监督机制,剥夺西方国家根据本国私利选择人道干涉时机和手段的自由,使人道干涉真正成为预防和阻止人道灾难的有效途径,从而真正维护国际公平与正义,彰显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 (本文曾在上海交通大学国务学院与江苏省发改委合办的“全球治理与中国的国家转型青年论坛”上宣读。感谢刘丰、曾向红、陈拯、魏英杰等对本文提出的修改意见,同时感谢《当代亚太》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建设性修改意见。文中错漏由笔者负责。) 注释: ①Francis Fukuyama,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New York:Free Press,1992,p.211. ②张睿壮:《“人道干涉”神话与美国意识形态》,载《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第109~117页。 ③Gareth Evans,"From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to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Wisconsin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Vol.24,No.3,2006,pp.703-722. ④Gareth Evans,Ramesh Thakur and Robert A.Pape,"Correspondence: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and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7,No.4,2013,pp.199-214; Carsten Stahn,"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Political Rhetoric or Emerging Legal Norm?"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l.101,No.1,2007,pp.99-120; Louise Arbour,"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as a Duty of Care in International Law and Practice",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34,Issue 3,2008,pp.445-458. ⑤Alex J.Bellamy,"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or Trojan Horse? The Crisis in Darfur and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after Iraq",Ethics &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19,Issue 2,2005,pp.31-54; Paul D.Williams and Alex J.Bellamy,"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and The Crisis in Darfur",Security Dialogue,Vol.36,No.1,2005,pp.27-47; Carlo Focarelli,"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Doctrine and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Too Many Ambiguities for a Working Doctrine",Journal of Conflict& Security Law,Vol.13,No.2,2008,pp.191-213; Thomas G.Weiss,"The Sunset of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in a Unipolar Era",Security Dialogue,Vol.35,No.2,2004,pp.135-153; Mahmood Mamdani,"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or Right to Punish?" Journal of Intervention and State Building,Vol.4,Issue 1,2010,pp.53-67; Alex J.Bellamy,"Libya and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The Exception and the Norm",Ethics &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25,Issue3,2011,pp.263-269; Thomas Weiss,"R2P Alive and Well after Libya",Ethics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25,No.3,2011,pp.287-292. ⑥李少军:《干涉主义及相关理论问题》,载《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年第10期,第19~28页;张春、潘亚玲:《有关人道主义干涉的思考》,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7期,第71~75页。 ⑦张睿壮:《“人道干涉”神话与美国意识形态》;时殷弘、沈志雄:《论人道主义干涉及其严格限制——一种侧重于伦理和法理的阐析》,载《现代国际关系》2001年第8期,第56~61页。 ⑧邱美荣、周清:《“保护的责任”:冷战后西方人道主义介入的理论研究》,载《欧洲研究》2012年第2期,第123~138页;刘波、戴维来:《中东剧变与人道主义干预的新发展》,载《现代国际关系》2012年第4期,第38~45页;赵广成:《从禁飞区实践看人道主义干涉的效力与局限性》,载《国际问题研究》2012年第1期,第95~107页;骆明婷、刘杰:《“阿拉伯之春”的人道干预悖论与国际体系的碎片化》,载《国际观察》2012年第3期,第22~26页。 ⑨阮宗泽:《负责任的保护:建立更安全的世界》,载《国际问题研究》2012年第3期,第9~22页;曲星:《联合国宪章、保护的责任与叙利亚问题》,载《国际问题研究》2012年第6期,第6~18页。 ⑩Martha Finnemore and Kathryn Sikkink,"International Norm Dynamics and Political Change",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2,No.4,1998,pp.887-917. (11)黄超:《“框定战略”与“保护的责任”:规范扩散的动力》,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9期,第58~72页。 (12)陈拯:《“框定竞争”与“保护的责任”的演进》,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2期,第111~127页。 (13)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54页。 (14)参见梁凯音:《论国际话语权与中国拓展国际话语权的新思路》,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9年第3期,第110~113页;叶淑兰:《中国战略性外交话语建构刍议》,载《外交评论》2012年第5期,第68~81页。 (15)张睿壮:《“人道干涉”神话与美国意识形态》,第110页。 (16)Robert Cullen,"Human Rights Quandary",Foreign Affairs,Vol.71,No.5,1992,pp.79-88. (17)Stephen John Stedman,"The New Interventionists",Foreign Affairs,Vol.72,No.1,1992/1993,pp.1-16; Josef Joffe,"The New Europe:Yesterday's Ghosts",Foreign Affairs,Vol.72,No.1,1992/93,pp.29-43; Marguerite Michaels,"Retreat from Africa",Foreign Affairs,Vol.72,No.1,1992/1993,pp.93-108; Jeffrey Clark,"Debacle in Somalia",Foreign Affairs,Vol.72,No.1,1992/1993,pp.109-123. (18)"The Clinton Administration Policy on Reforming Multilateral Peace Operations" (PDD 25),released by the Bureau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ffairs,U.S.Department of State,February 22,1996,转引自张睿壮:《“人道干涉”神话与美国意识形态》,第110页。 (19)Mohammad Taghi Karoubi,Just or Unjust War? International Law and Unilateral Use of Armed Force by States at the Turn of the 20th Century,Burlington:Ashgate Pub.Ltd.,2004,pp.73-75,转引自韦宗友:《西方正义战争理论与人道主义干预》,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10期,第32~48页。 (20)黄海涛:《人道主义干涉的历史进程评析》,载《国际论坛》2012年第4期,第1~6页。 (21)韦宗友:《西方正义战争理论与人道主义干预》,第36页。 (22)《联合国宪章》第七章,联合国官方网站,http://www.un.org/zh/documents/charter/chapter7.shtml。 (23)理查德·哈斯:《新干涉主义》,殷雄、徐静等译,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15页。 (24)Tony Blair,"Doctrine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ty",Speech to the Economic Club of Chicago,April 22,1999. (25)韦宗友:《西方正义战争理论与人道主义干预》,第40页。 (26)联合国安理会第688号决议,1991年4月5日,http://www.un.org/zh/documents/view_doc.asp?symbol=S/RES/688。 (27)Danny Schechter,"Selling the Iraq War:The Media Management Strategies We Never Saw",in Yahya R.Kamalipour and Nancy Snow,eds.,War,Media,and Propaganda:A Global Perspective,Lanham,MD and Oxford:Rowan and Littlefield,2004,p.28. (28)Chaim Kaufmann,"Threat Inflation and the Failure of the Marketplace of Ideas:The Selling of the Iraq War",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9,No.1,2004,pp.5-48. (29)刘明:《国际干预与国家主权》,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6页。 (30)Nicholas Wheeler,Saving Strangers: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2000,p.161. (31)Gareth Evans,"From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to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p.717. (32)《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造成大量平民伤亡》,新华网,2011年4月11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1-04/11/c_121287485.htm。 (33)黄海涛:《人道主义干涉的历史进程评析》,第4页。 (34)汪舒明:《“保护的责任”与美国对外干预的新变化——以利比亚危机为个案》,载《国际展望》2012年第6期,第64~77页。 (35)包括卡内基公司、威廉和弗洛拉·休利特基金会、约翰与凯瑟琳·麦克阿瑟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和西蒙基金会等。 (36)汪舒明:《“保护的责任”与美国对外干预的新变化——以利比亚危机为个案》,第68~69页。 (37)干预和国家主权国际委员会:《保护的责任:干预和国家主权国际委员会报告》(中文版),2001年,第12页。 (38)黄超:《框定战略与“保护的责任”规范扩散的动力》,第68页。 (39)干预和国家主权国际委员会:《保护的责任:干预和国家主权国际委员会报告》,第Ⅸ页。 (40)同上。 (41)干预和国家主权国际委员会:《保护的责任:干预和国家主权国际委员会报告》,第Ⅹ页。 (42)《一个更安全的世界:我们共同的责任》,威胁、挑战和改革问题高级别小组(名人小组)报告,A/59/565,2004年12月,第29段、第201段。 (43)UN General Assembly,World Summit Outcome 2005,Resolution A/RES/60/1,October 24,2005. (44)UN General Assembly,Sixty-third Session,"Implementing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Report of the Secretary-General,January 12,2009. (45)邱美荣、周清:《“保护的责任”:冷战后西方人道主义介入的理论研究》,第135页。 (46)Gareth Evans,Ramesh Thakur and Robert A.Pape,"Correspondence: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and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p.201. (47)Ibid. (48)Alan J.Kuperman,"A Model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Reassessing NATO's Libya Campaign",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8,No.1,2013,p.106. (49)赵士林、黄柳叶:《战争“合法性”与媒体建构——以〈卫报〉利比亚战争报道为例》,载《今传媒》2012年第6期,第27~30页。 (50)UN Human Rights Council,nineteenth session,"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Inquiry on Libya",A/HRC/19/68,advance unedited version,March 2,2012,p.53. (51)Gérard Buffet,"French Doctor Recounts 'Apocalyptic' Scenes in Libya",interview,Agence France-Presse,February 2011,http://www.youtube.com/watch?v_JwHUqPoEPs. (52)Human Rights Watch,"Libya:Governments Should Demand End to Unlawful Killings:Death Toll Up to at Least 233 over Four Days",February 20,2011,http://www.hrw.org/news/2011/02/20/libya-governments-should-demand-end-unlawful-killings. (53)联合国安理会第1970号决议,2011年2月26日,http://www.un.org/zh/documents/view_doe.asp?symbol=S/RES/1970(2011)。 (54)联合国安理会第1973号决议,2011年3月17日,http://www.un.org/zh/documents/view_doc.asp?symbol=S/RES/1973(2011)。 (55)"UN Human Rights Chief Pillay Calls for International Inquiry into Libyan Violence and Justice for Victims",Press Statement,February 22,2011. (56)汪舒明:《“保护的责任”与美国对外干预的新变化——以利比亚危机为个案》,第71页。 (57)Alex J.Bellamy,"Libya and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The Exception and the Norm",p.263. (58)Praveen Swami,Rosa Prince and Toby Harnden,"Coalition Forces Strike Sirte; Leader's Home Town",Daily Telegraph,March 28,2011. (59)Alan J.Kuperman,"A Model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Reassessing NATO's Libya Campaign",p.114. (60)汪舒明:《“保护的责任”与美国对外干预的新变化——以利比亚危机为个案》,第74、75页。 (61)Gareth Evens,"When Intervening in a Conflict,Stick to U.N.Script",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March 24,2011. (62)邱美荣、周清;《“保护的责任”:冷战后西方人道主义介入的理论研究》,第137页。 (63)UN Human Rights Council,Nineteenth Session,"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Inquiry on Libya". (64)Gareth Evans,Ramesh Thakur and Robert A.Pape,"Correspondence: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and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p.206. (65)罗建波、姜恒昆:《达尔富尔危机的和解进程与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载《外交评论》2008年第3期,第44~50页。 (66)联合国安理会第6711次会议记录,2012年2月4日,http://www.un.org/zh/documents/view_doc.asp?symbol=S/PV.6711。 (67)同上。 (68)潘亚玲:《从捍卫式倡导到参与式倡导——试析中国互不干涉内政外交的新发展》,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9期,第45~57页。 (69)UN General Assembly,sixty-third session,"Implementing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Report of the Secretary-General,January 12,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