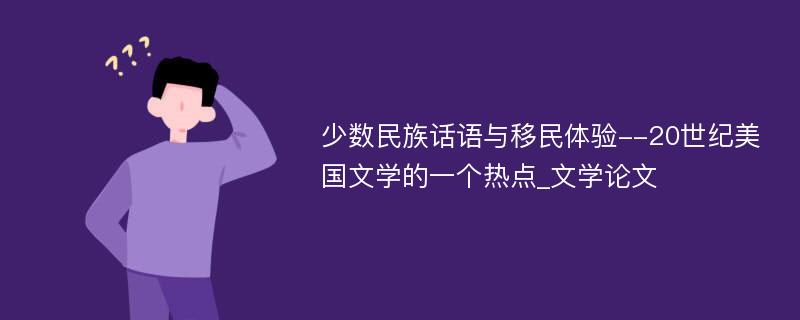
少数话语与移民经验——谈20世纪美国文学中的一个热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热点论文,美国论文,移民论文,话语论文,经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少数话语”(Minority discourse)近年来已经成为美国文学研究中的一个热点,但是这个词语的内涵并不为一般读者、甚至一些美国文学研究工作者足够了解与认识。记得1992年秋在武汉举行的中国美国文学学会第六届年会上有人提出这个问题,一些与会代表对此感到相当陌生。因此会议经讨论决定,把它作为下一届年会的主题。但是对于“Minority discourse”这个最近在美国文学批评理论中出现的概念,在我国还没有一个为大家一致接受的译名。时至1994年3月,北京出版的《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刊载了王逢振先生写的一篇文章,标题为《什么是Discourse?》,直接用了英语“discourse”一词,因为作者认为目前该词的一些中文译名,包括“话语”在内,都没有充分表达出这个词的原意。王先生从约定俗成考虑,在文中暂且使用了“话语”这一译名。本文作者无创新之意,随波逐流,搬来“话语”,冠以“少数”或“少数族群”(minority),缀合为“少数话语”或“少数族群话语”。
那么,“话语”的原意究竟是什么?“少数话语”的含义又是什么呢?笔者参阅了一些有关资料,并作了长时间的揣摩,“少数话语”这个词是否可作这样的表述:“少数话语”是当代西方批评理论研究,特别是美国文学批评理论研究中经常出现的一个概念。它发轫于后结构主义的“话语和权力”理论,探讨黑人文学、移民文学、妇女文学等各种处于少数地位的“边缘文学”的演变及特征。它们是对占支配地位的主体文学的一种挑战与威胁,是对欧洲文化中心论、殖民文化和男权主义的一种反动。具体地说,首先它是一个文学批评的理论问题,它像当前其他许多新的文学批评理论一样具有跨学科的性质。“话语”一词最先为语言学所采用,后来这个时髦的术语渗透到了文学领域,并产生了新的意义,但即令在文学批评理论范围里,它的意义也是在不断演变发展的:从“新批评”时期用于表示文类差异与确立特性,强调“话语”的意义本质,到后结构主义的着重研究“话语”与权力的关系,强调“话语”的生成和作用。而“权力”一般是属于政治学、伦理学、社会学等学科讨论的问题。因此,“话语”是一个涉及到多种学科,包括文学、哲学、历史、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复杂的理论问题。正在美国兴起的“少数话语”研究是“话语”理论研究的一支。由于它以“话语”和权力关系为研究的切入点,加之处于边缘地位的少数文学对主体文学的对立与反抗,“少数话语”研究具有鲜明的政治性与现实意义。
本文拟就以下三个问题作一些探讨。
第一、“少数话语”的含义是什么?
第二、作为一个概念,作为美国文学一个特点,“少数话语”产生的原因何在?
第三、研究“少数话语”对于美国文学研究的意义。
一
“少数”(minority)是“多数”(majority)的反义词,泛指在一组人或物中,其数量不足半数者,又专指在一个国家或地区,人数居于少数的民族。但是我们这里的“少数”不单指少数民族,如美国的印第安人、黑人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还包括妇女以及一切处于“少数地位”的群体,如同性恋者、环保主义者等等。这个扩大的概念是近年来逐步发展形成的,也逐渐为人们所接受。在很长的时间里,美国文学史家不是忽略或无视黑人、移民、妇女等创造的文学作品,便是简略地提一下他们中的几个代表人物,仅此而已。近年来,情况有了一些改观,一些新出版的文学史列有专门的章节,讲述黑人文学、移民文学与妇女文学,甚至还出了专著。在一些文学选读中,这类文学作品也陆续入选,开始占有一席之地。1978年美国巴纳斯和诺布尔图书出版公司出版的题为《20世纪美国小说》(The American Novel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一书中,作者迈尔斯·唐纳德(Miles Donald)把20世纪的美国小说分成四大类:传统小说(traditional novel)、幻想小说(fantasy)、少数小说(minorities)和通俗小说(popular fiction)。这种分类方法虽有其独到之处,但也可能有不臻完善与科学之处,不一定为大家所接受。值得注意的是,作者给予处于少数地位的族群较大的重视,尤其对美国的黑人文学和犹太文学作了充分的肯定。作者在“少数文学”一章中,给“少数”(minority)一词作了新的界定。他说:这里“少数”一词相对而言是一个较新的词。它开始是所谓的“纯”美国人对黑人和黑人社团的一种客气的称呼,在某种程度上它代表说话人态度的改变,承认像黑人那样一类少数民族整体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偶然进入他们社会的、不受欢迎的游离分子。作者进一步补充说,这个词的社会含义变得愈来愈丰富了,“少数”已不仅仅用于种族或民族,它还涵盖了一切处于少数地位、强烈要求社会承认的群体。作者在当时(1978年)就预言,今后十年,任何介绍“少数小说”的书几乎都不可能不提到同性恋者与女权主义者,不可能不考虑他们在社会上的作用与影响。作者甚至预言,可能有一天我们会面对一个个处于少数地位的单独群体的顽强对抗,因为现代社会显示,处于支配地位的多数或者大的群体在有计划地把这些小群体驱向死亡。也许正是这种濒临灭绝的危险迫使他们要作出反应,并必然地要顽强表现他们自己。美国黑人文学和犹太文学本世纪的巨大发展就是明显的例子。唐纳德在当时还没有可能来论述其他少数民族的文学,也没有具体介绍同性恋文学或妇女文学。但是,他的预言已经为历史所证实了。1988年,恰好是唐纳德一书出版后的十年,埃默里·埃利奥特教授(Emory Elliott)主编的《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Columbia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States)问世了。这本观点新颖、编写方法独特的文学史书则又向前迈了一大步,辟出专门的章节,深入讨论“少数文学”,除美国印第安人文学、黑人文学与众多移民文学之外,作者还较详细地阐述了同性恋文学在美国的崛起与其日益增大的影响。他不拘一格为诸如反战文学、青年运动文学、环保文学等这些处于少数地位的文学留出了篇幅,让人们一睹它们的风采,听到它们的声音。
至此,我想“少数”一词在“少数话语”这个特定上下文中的意义是比较明确了。它的含义是很丰富的,它不仅指民族、种族和性别,也指政治倾向、思想倾向以及宗教信仰和道德主张等。
至于“少数话语”中“话语”一词的含义如前所述要复杂一些。英语“discourse”一词原意是就某个题目作的谈话或讲解。此词后为现代语言学采用,指围绕一定的话题展开的、语义上有联系、结构上相互衔接的一连串语句。在我国出版的一些语言学书刊里常采用“语篇”或“话语”来表述。在当前文学批评理论中这个词也非常活跃。以《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一书为例,什么“社会话语”、“政治话语”、“女权主义话语”、“殖民话语”、“种族话语”、“文学话语”等等,俯拾皆是,唾手可得。综观这众多的搭配,这里的“话语”不仅仍保留该词的原意,又有现代语言学的含义,也许这正是现代语言学与当代文学批评理论相互渗透的表现。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在其《文学理论入门》(Literary Theory——An Introduction)一书中有一段很精彩的话:
总的来说,结构主义是企图把这个语言学理论(指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运用到语言之外的物体和活动中。你可以把神话、摔跤比赛、部族的亲属体系、餐馆的菜单或者油画,全都看成是一个符号系统……。它在很大程度上不考虑这些符号上“说”什么,而专注于它们之间的相互的内在关系。结构主义,正如语言学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说的那样,是试图“运用语言学的观点来重新思考一切事物。”它给我们传递一个征兆,表明语言连同它的各种问题与奥秘的含义,已经成为20世纪思想生活的规则和难以摆脱的顽念。[①]
在一定的语境中,“话语”可以用传统文学理论中的“题材”(subject)、“主题”(theme)、“话题”(topic)、“专题讨论”(disquisition)等作为同义词来替代。但任何同义词不可能完全相同。“话语”与这些同义词比较,除了含义上的区别外,还带有更多的时代气息、跨学科的品质和理论风味。
上面分别谈了“minority”和“discourse”两个词的含义及其在当代文学理论中的运用。本来逐可产生一个恰当的译名,几个月来每每好像在脑子里摸到了开箱子的钥匙,但落笔时却茫然无从。诚如严又陵说的那样,“一名之立,旬月踌躇”。对于我来说,“Minority discourse”一名,数月踌躇,而仍未立。最近读了王先生的文章,我决定放弃创新的努力,采用“少数话语”了事。这个译名看来是属于“直译”或“硬译”,但是“决不欺骗读者”,只是希望读者不要停留在字面意义上,而要去了解“少数话语”的含义。
二
下面我们就来谈谈最近在美国兴起的“少数话语”研究,观察它的历史根源和现实情况。
前面曾提及,所谓“少数话语”中的“少数”是指种族、性别以及社会地位或政治思想倾向上处于少数地位的人或群体。在这三者中种族(race)和性别(gender)两者尤为重要。[②]
1993年9月美国杜克大学出版的《美国文学》季刊第3期发表了一组讨论美国文学中种族和性别的文章。在编辑部为这组文章写的“前言”中说,这是该杂志创刊65年来第一次出这样的专刊,因为编辑部收到了不少讨论这类问题的稿件。这些稿件的作者不仅提出了美国的种族问题,而且对于“种族”的定义和美国一词的意义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现在正是解决这些大的概念问题的时候了。这些文章把“种族”问题作为重点来讨论是必然的,因为正如199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尼·莫莉森雄辩地指出的那样:在美国文学中或美国社会中,没有哪一个问题比之种族问题更重要的了。因此,我们在讨论“少数话语”,探讨所谓“边缘文化”与“主体文化”的关系时,把“种族”问题作为重点也是理所当然的。
美国素有“移民国家”之称。“我们是一个移民国家”(We are a nationof immigrants)。这一口号不仅是政治家们在不同种族人聚会上的口头禅、教科书上的老生常谈,而且也确实是一句反映美国历史与现实的至理名言。对于美利坚合众国来说,根本没有一块什么先人祖传的土地,或者哪个民族可称为立国的祖宗先民,拥有的仅是从“那里”迁移到“这里”的共同的祖传经验。1669年一名英国传教士曾这样写道:“上帝筛选出一个国家,把优良的种子撒播在那块荒野上。”[③]这些种子来自世界各国,也就是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麦尔维尔说得好,“美国人不是一泓清水,我们的血像亚马逊河的洪水,由千百条支流汇集而成。”[④]
但是,“移民国家”之说最近却受到了挑战。1993年美国总统克林顿提名佐伊·贝尔德为大法官候选人,在进行资格审查时,有人检举这位候选人和她的丈夫曾经雇佣过两名“非法移民”来帮助他们临时照看小孩和做家务。为此克林顿无可奈何地撤回提名,另择他人。此事和后来的“金色冒险号”偷渡船事件使美国的“移民问题”又成为一个热门话题,有人公开提出美国是否还应该像过去那样向移民敞开大门。更有人宣布美国不再是一个移民国家。反移民的喧闹,甚嚣尘上。但是,历史是不容篡改的,现实是不容逆转的。移民是构成美国躯体的血和肉,没有移民便没有美国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有移民就必然有移民经验,产生移民文化。近年来,移民经验、移民文化、移民文学愈来愈得到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们的注意。1993年6月出版的《美国文学》季刊就美国文学选读本的编辑与使用问题进行了专题讨论,讨论非常热烈,普遍要求扩大选题范围,尤其是扩大长期被忽视的移民文学。密歇根大学的史蒂芬·苏密达教授(Stephen H.Sumida)写的《我如何教亚太裔美国作家的文学》一文就代表了这种声音。他为大学本科生与研究生开设了多门有关亚太裔作家的文学课程。他讲授的作家与给学生开列的阅读书目丰富多采,有华裔、日裔、菲裔等许多移民作家的作品,让人大开眼界。但更使人受益的是他的教学方法,他不断启发学生从历史与文化的角度来理解这些作家与作品,譬如他给学生出了这样一道论文题目:你准备论述的亚太裔美国作家是如何看待不同人之间的冲突与关系,是看成文化之间的冲突与关系,还是看作文化的改变、历史的延续。
这里苏密达教授提出了美国少数民族文学或者移民文学中最重要的一个主题,即移民经验。关于移民经验,美国帕克赛德的威斯康星大学约翰·比恩克教授(John D.Buenker)曾经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认为在过去一个半世纪中,进入美国的几千万移民都经历了一个与现存社会和文化相互作用的复杂过程。这个过程又包括同化(assimilation)和适应(acculturation)两个具有不同概念和不同进展速度的变化方式,尽管这两个词往往被交替使用。“同化”是指移民在结构上被吸收进大社会的过程,其结果是原来种族带来的在工作就业、居住环境、亲情友谊、文化娱乐、政治活动以及恋爱婚姻等方面的联系格局最终消失了。文化适应的过程则是指新来的移民逐渐放弃他们原来种族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待人接物与处世办事等传统,而采纳了主流文化的新观念、新方式、新传统。[⑤]简言之,前者强调总体结构,后者强调思想观念。两者放在一起就构成了“移民经验”。移民经验是一个渐变的过程,通常要经过几代人的演变发展。了解移民经验是了解现代美国社会和文化,也是了解美国少数民族文化的一个关键。托马斯·韦勒(Thoms C.Wheeler)在《移民经验:美国化的痛苦》一书中说:在某种真正意义上说,移民经验无论就其活力和张力而言都代表了美国的经验。尽管时光流逝、世代更迭,美国仍然是一个“移民国家”,只有面对这个现实,无论个人还是社会才能获得如何建设性地对付城市生活与工业社会产生的各种错综复杂的情况所必要的智慧。[⑥]
美国的“移民经验”在传统上归纳为三种模式:顺从盎格鲁模式(Anglo-conformity),即与所谓的核心文化一致。主体社会要求少数民族移民几乎全盘接受它的文化习俗,“全盘美国化”。但是究竟什么是美国特色或美国文化并没有一致的认识或确切的定义。因此,主体文化的鼓吹者从未想到或希望众多的少数民族都与盎格鲁文化一致起来。第二个模式是“熔炉”模式,这个模式的信念是:“共收同创”,把进入美国这座大熔炉的各色人种、各个民族所提供的原始材料经过熔炼成美国文化,炼就具有美国特色的文化。但是,由于外来的移民文化,每一次的“投料”,其数量总是有限的,难以对主体文化产生质的变化,可谓“熔而不化”,所以当前有一些学者对熔炉说提出质疑,认为此比喻不甚确切,不符合实际。于是就产生了第三种模式——“多元文化”模式。它把美国看成是一个单一的政治与经济单位,而存在着多种多样的次文化,俗称“色拉碗”。
运用上述“移民经验”的观点和美国文化模式发展的历史来观照美国文学,我们就可以较好地理解美国文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多样性。“移民经验”是造成美国文学内容庞杂、风格各异、色彩鲜明的重要原因之一。翻开美国文学史,“移民经验”贯彻始终。最初的殖民时期的美国文学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记述了早期来到美洲这块土地上的移民为了求得生存与发展,跟大自然和殖民主义统治者进行斗争与自我成长的经验。到了南北战争前后,蓄奴与废奴之间的斗争则是集中反映了非洲黑人移民在这个新生国家所遭受的苦难,是对种族歧视与种族压迫罪恶的揭露与控诉。美国的黑人文学在这时开始萌芽。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的移民高潮,特别是欧洲大批移民的经验为这个时期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涌现了一批杰出的移民作家。这个时期的乡土文学和西部文学也无不饱含移民的经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文学更是标志着移民经验的成熟与发展。犹太人文学与黑人文学是在少数民族文学中较早成熟的两个品种。亚裔文学此时也初露头角,出现了一些颇有影响的作家与作品,如华裔女作家马克辛·洪·金斯顿(Maxine Hong Kingston)的《巾帼英雄》(Woman Warrior),谭·埃米(Tam Emy)的《灶神的妻子》(The Kitchen God’s Wife)等,表明了亚裔移民作家的日趋成熟。
“移民经验”不仅使美国文学具有多样性的特点,而且还极大地丰富了美国文学的形式与题材,深化了美国文学的主题思想。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出现了新的“移民潮”,大批移民涌入美国的城市,在那里形成了许多移民聚居区和贫民窟。史蒂芬·克莱恩的《街头女郎玛吉》(1893)、亚伯拉罕·卡恩的《耶克尔:纽约犹太人区的故事》(1896)、厄普顿·辛克莱的《屠场》(1906)以及其他许多描写移民经验和都市低层人民生活的小说在这个时期相继问世决非是一个巧合。这些小说充满了对美国社会的悖论和反讽。它们向当时十分畅销的小霍雷肖·阿尔杰等人写的所谓“穷人发财”(rags-to-riches)小说提出了挑战,向那些陶醉在“美国梦”中的人们吆喝一声,唤醒他们去正视美国社会的现实。“美国梦”这个词语给美国的历史、社会、心理、文学等等方面都赋予了异常丰富的内涵。对“美国梦”的不同态度反映了人们对自由、机会和成功的不同态度和价值取向;从本质上说,它也反映了人们对世界、生活和人生的感悟。在美国文学中,对“美国梦”的形成、发展以及或圆全或破灭的观察和描述成了一个重要的题材,也成了与“移民经验”不可分割的部分。在20世纪美国文学中,这个题材不断在发展,从东欧移民,尤其犹太移民,扩大到拉美移民,直至亚洲移民。移民的不同文化背景产生了不同的移民经验与各具特色的文学作品,从而形成了美国现代文学的一道绚丽多彩的风景线。而且,我们有把握地说,只要美国继续有移民,美国文学的这一特点将会延续下去。“少数话语”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当前美国文学研究中的一个热点。
注释:
①Terry Eagleton,Literary Theory——An Introduction,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3,P.97.
②Subjects and Citizens:Nation,Race,and Gender From Oroonoko toAnita Hill,In:American Literature,Vol.65 No.3,1993,P.413.
③④Bernard A.Weisberger,A Nation of Immigrants,In:AmericanHeritage,February/March 1994,P.77.
⑤⑥Stanley Coben and Lorman Ratner(ed),The Development of anAmerican Culture(2nd ed.),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83,P.313.
标签:文学论文; 美国社会论文; 移民欧洲论文; 美国文学论文; 移民论文; 社会经验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黑人文化论文; 艺术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