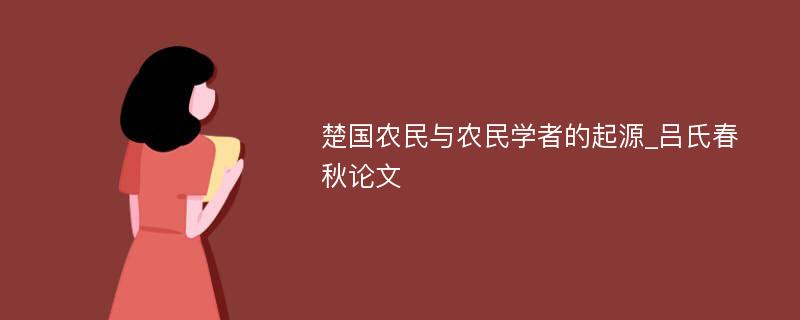
农家源流与楚国的农家学者,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楚国论文,农家论文,源流论文,学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2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7387(2013)03-0105-08
“农家”是先秦诸子中的一个重要思想流派。对于这个学派,清代以来的学者作过不少考辨,如崔述以农家为墨家之流别等[1]。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史学界也曾对农家及“为神农之教者许行”的学派归属展开过激烈的争论。钱穆认为许行为南方之墨者,钱玄同以之属道家派别,孙次舟反对钱穆之说,坚持农家为一独立学派,而刘汝霖则以农家学派与法家相近,同出于关中。[2]近年来,亦间有学者论及农家学说,则以为“战国有重农之社会思潮,而无农家学派之实。[3]”
那么,中国的先秦到底是否有一个作为独立学派的“农家”,其思想渊源和发展历史又到底如何?这的确是先秦学术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值得我们进行认真的探讨。不过,本文不准备如以往的研究者那样就事论事,而是拟将农家学派的渊源、形成、发展及其思想特点,放在整个先秦农业思想、特别是楚国农业思想发展的具体背景下加以考察,以期能对这一问题有更为深入的探讨。
一、先秦农家源流考辨
从现有文献来看,“农家”一名,殆首出于刘向的《别录》、刘歆的《七略》,而班固的《汉书·艺文志》承之。《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叙“农家”曰:
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播百谷,劝农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货。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长也。及鄙者为之,以为无所事圣王,欲使君臣并耕,悖上下之序。
《汉书·艺文志》这段对“农家”的“叙录”应该包括有三层意思:第一,它说明“农家”亦出于“王官”——“农稷之官”;第二,它说明“农家”学派的特点在“播百谷,劝农家桑,以足衣食”——即重农;第三,它对“农家”思想进行了正反两方面的评价——从正面看,它符合儒家经典将“衣”、“食”列入“八政”和孔子“重民食”的观点;从另一方面看,它又变成了“鄙者”的“以为无所事圣王,欲使君臣并耕”,这是“悖上下之序”的。
不难看出,和《汉志》对其他诸子学派的“叙说”一样,此处也持“诸子出于王官”之论的。唯一不同的可能是,因为农家思想中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是关于“播百谷,劝农桑”的具体农业生产知识的,故而说它始于国家负责农业的“农稷之官”,这一点应该比说其它思想性较强的诸子学派“出于王官”有着更强的说服力。
但或许由于后代的学者们对所谓“诸子皆出王官”说心存疑虑,故他们讨论“农家”时并不因为上古即有所谓“农稷之官”而接受《汉志》关于“农家”起源的观点,也不大相信《汉志》关于“农家”思想即是“播百谷,劝农桑,以足衣食”的成说[4],而是差不多都只将对农家学派及其思想的讨论限于战国中期的许行、陈相等人,或认为“农家”属“墨家派别”,或认为属道家支裔,或认为属法家近亲——更有甚者,乃至于否定“农家”作为先秦诸子中一个独立学派的存在,而认为其实只是战国时期的一种“重农的社会思潮”。
那么,“农家”到底与先秦诸子学派中的其他学派是怎样的关系,它是否可以作为先秦诸子的一个独立学派而存在呢?
我们认为,尽管农家学派的思想与先秦诸子中的道、墨、法、阴阳等家有某些相同或相近之处,但这并不足以否定“农家”作为一个独立学派的存在,更不能因此而怀疑“农家”与上古“农稷之官”的渊源关系。
现代考古学与先秦史研究表明,大约在新石器时代的早期,我国社会即已由采集、狩猎经济向农业、畜牧业经济转化期,故有神农氏发明农业的种种传说。如《易·系辞下》曰:“神农为耒耜鉏耨,以垦草莽,然后五谷兴助,百果藏实。”(《绎史》卷四引)《礼纬·含文嘉》亦曰:“(神农)始作耒耜,教民耕,其德浓厚若神,故为神农也。”(《太平御览》卷七八引)在随后的新石器时代中期,即传说中的尧、舜、禹时代,种植经济进一步发展,“已有了繁盛的农业”[5]。故《国语·周语上》谓“夫民之大事在农”,而尧以后稷为典农之“天官”。《礼记·祭法》及郑注、孔疏皆曰神农氏后世子孙代为农官,“夏之衰也,周弃(后稷)继之”,承农官之职。西周则有“司稼”之官,专“掌巡邦野之家而辨穜稑之种”。在三代,“学在官府”,国家有关农业生产——“播百谷,劝农桑,以足衣食”的知识也就为农官所专有。直到春秋战国之际,学术下移于民间,普通的士人才有传习这些专门知识的可能,而这才衍生农家学派来。从这个意义上讲,说“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应该说也是合乎情理的。那种视农家附属于墨、道、法等家,甚至根本否定农家独立性的看法,都是不能成立的。
1.就农家属于墨家流别的观点而言,虽然《孟子·滕文公上》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其徒数十人,皆衣褐,捆屦织席以为食”的记载,又有其倡“君臣并耕”之说,但“衣褐”既不等于墨家之节俭,主“君臣并耕”也只是为了斥滕君“厉民以自养”,同样不等于墨家之兼爱。——退一步说,“衣褐”即使等于墨家之节俭,主“君臣并耕”即使等于墨家之兼爱,但农家“播百谷,劝农桑,以足衣食”的根本思想也与墨家无涉。故早有学者指出:“(孟子)于杨、墨两家,排斥特甚……设许行果系墨家,则孟子斥陈相弃儒学就许行,适可痛诋墨道之‘无父’,何乃无一语及墨耶?”且“墨家法禹,亦不法神农也。”[6]故只可以说农家在个别思想观点上与墨家有相近之处,而不能由此断定许行的农家之学属于墨家之流别。
2.就农家为道家别派的观点而言,虽然如《汉志》所云,农家中之“鄙者”主张“无所事圣王”,道家的《庄子》之书也称“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相害之意。”(《庄子·盗跖》)但道家更关心的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而不是农家的“播百谷,劝农桑,以足衣食。”故农家很难说算得上“道家的别派”。
3.就法家与农家的关系而言,虽然法家亦以重农耕而闻名,李悝、商鞅、韩非等人亦将神农之世视为理想社会,曰:“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刑政不同而治,甲兵不起而王。”(《商君书·画策》)并反复强调要推行“尽地力之教”,“禁游宦之民而显耕战之士”,使“丈夫尽于耕农,妇人力于织纴。”(《韩非子·难三》)但法家和农家至少有两点根本的差别:
其一,法家“劝农桑”的目的并不止于使民“以足衣食”,而是为了便于封建统治者的统治。过去学者一般都认为《吕氏春秋·上农》、《任地》、《辨土》、《审时》四篇是先秦农家的佚篇,但却忽视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即这些佚篇“也只是战国时候的东西”,而且这些东西还“在吕书的编辑中有所割裂和增减”。[7]故《吕氏春秋·上农》曰:
克先王之所以导其民者,先务于农。民农非徒为地利也,贵其志也。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民农则重,重则少私议,少私议则公法立,力专一。民农则其产复,其产复则重徙,重徙则死处,而无二虑。
这里所谓“主位尊”、“力专一”、“无二虑”,无一不是针对统治阶级的统治而言的,根本不同于农家的“以足衣食”。
其二,农家有相当一部分人——至少是其中的“鄙者”们认为,统治者真正重视农耕就应该不分君臣都要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君臣并耕而食,饔飧而治,”甚至君主应该率先垂范,带头耕织(如古代帝王常有所谓“耕籍田”之举,详见下文)。但这却是法家所绝对不能允许的。法家认为:“夫必恃人主之躬亲而后民听从,是则将令人主耕以为食、服战雁行也民乃肯耕战,则人主不泰危乎?而人臣不泰安乎?”(《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而这,显然违背了“贵贱不相逾”的“天下之常道”的,故也是法家所要坚决反对的。(同上,《有度》)因此,可以说农家和法家虽然在重农主张上有相同之处,但二者的根本目的和实现目的的手段都绝不相同——农家是不能归入法家的。
其实,农家不仅与墨、道、法诸家在思想主张上有相近之处,而且与儒家、阴阳家等其他诸子学派也可以找到某些共同点。如儒家的经典《尚书·洪范》中叙“八政”:“一曰食,二曰货。”《周礼》中又有“三农生九谷”,司稼“掌巡邦野之稼”等说,这都说明儒家也有重农的主张。阴阳家“敬顺昊天”,“敬授民时”;而农家也认为“凡农之道,厚(候)为之宝。”(《吕氏春秋·审时》)“举事慎阴阳之和,种树节四时之适,无早晚之失、寒温之灾,则入多。”(《韩非子·难三》)但这同样并不表示农家与儒家或阴阳家有渊源关系,而只是如班固在《汉志》的自注中所云,只反映了“六国时,诸子疾时怠于农耕”,故而“道耕农事”的史实而已。至于作为先秦诸子之一的农家,则如《汉书·艺文志》所言,是一个源远流长、有着自己思想体系的独立的学术派别。
二、先秦农家的基本思想
研究先秦诸子思想的最好办法,自然就是研读他们的著作。研究先秦农家的学术思想,当然也不能例外。《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农家著作共“九家,百一十四篇”,其中能确定为先秦农家著作的,则只有三家五十四篇,其余都是汉人的作品。《汉志》中的三家先秦农家著作是:“《神农》二十篇”、“《野老》十七篇”和“《宰氏》十七篇”。“《神农》二十篇”,颜师古注引刘向《别录》云:“疑李悝及商君所说。”班固原注则说:“六国时,诸子疾时怠于农耕,道农耕事,托之神农。”可知该书是先秦农家的著作。惜其书早亡,自清末马国翰以来,辑佚家多辑《孟子·滕文公上》、《汉书·食货志》及《管子》、《吕氏春秋》、《淮南子》诸书中“神农之言”或“神农之教”以为辑本。“《野老》十七篇”下班固自注:“六国时,在齐楚间。”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亦因马骕《绎史》有“盖古农家野老之言而吕(不韦)述之”等语,因取《吕氏春秋》中《上农》、《任地》、《辨土》、《审时》四篇合为一卷,题曰“《野老书》”。张舜徽认为马氏此辑佚“非也”,属“无识”,因为《绎史》所谓“野老”,乃泛指老农,“非《汉志》之野老也。”“《宰氏》十七篇”下班固自注:“不知何世。”但叶德辉谓《史记·货殖列传》之裴駰《集解》中“计然,姓辛氏,字文子,其先晋国亡公子。”一本作“姓宰氏,字文子”,故可知“宰氏即计然”,《汉志》云“不知何世”,“盖班所见,乃后人述宰氏之学者,非计然本书也。”[8]但此书无疑亦属先秦农家著作。
《汉书·艺文志》中虽然共有九家百一十四篇先秦的农家著作,但这些著作却无一例外地亡佚了,后人只能从《管子》、《吕氏春秋》、《淮南子》等书中进行辑佚。但正如我们刚刚所指出的,如保存于《吕氏春秋》中的《上农》、《任地》、《辨土》、《审时》篇,它们虽然都“是战国时的东西”,但它们在编入《吕氏春秋》一书时是“有所割裂和增减”的。(《上农》篇中的“主位尊”、“力专一”、“无二虑”之说,就明显是属于法家的主张。)因此,这些作品不仅不能指实为《汉志》中的《神农》或《野老》篇,而且也不能说它们的全部内容都属于农家——只有其中被冠以“神农之教”或“神农之言”、“后稷曰”等语者才能肯定为农家作品,而其它部分则是难以断定的。而我们今天论农家之思想特点,则必须将这些片言只语与《汉志》中的农家“叙录”结合起来加以考察。而结合《汉志》关于农家的“叙录”和先秦两汉典籍所引神农、后稷之言来看,先秦农家的思想殆不出以下数端:
其一,强调农业的重要性,倡导“务耕织”。《汉志》所谓“播百谷,劝耕桑,以足衣食”。即是此意。而《吕氏春秋·爱类》、《淮南子·齐俗训》、《汉书·食货志上》等书引神农、后稷之言,亦多与之同类。
神农之教曰:“士有当年而不耕者,则天下或受其饥;女有当年而不绩者,则天下或受其寒矣。”
——《吕氏春秋·爱类》
后稷曰:“所以务耕织者,以为本教也。”
——《吕氏春秋·上农》
神农之法曰:“丈夫丁壮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饥者;妇人当年而不织,天下有受其寒者。”
——《淮南子·齐俗训》
神农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无粟,弗能守也。”
——《汉书·食货志上》
《吕氏春秋·爱类》、《淮南子·齐俗训》所谓夫妇不耕织,或受饥寒,《吕氏春秋·上农》所谓以“务耕织”为“本教”,《汉书·食货志上》所谓无粟则坚城“弗守”,其实都是在强调务农的重要意义,劝人耕桑。
其二,有关农田耕作之法和如何调剂丰歉(农业保障制度)。这方面的内容《汉志》中无明文,而传世文献中则多有。如《管子·揆度》曰:
神农之数曰:“一谷不登,减(何如璋注:‘减其所积而散之’)一谷,谷之法什倍。二谷不登,减二谷,谷之法再什倍。夷疏(郭沫若注:‘夷疏’乃糶之意,‘夷’谓平其价,‘疏’谓通其有无。)满之。无食者予之陈,无种者贷之新,故无什倍之贾(價),无倍称之民。[9]”
这是讲歉收之年如何赈灾和调剂。而《吕氏春秋任地》引后稷言则皆是关于如何耕种的问题:
后稷曰:“子能以窐为突乎?子能藏其恶而抑之阴乎?子能使吾土靖而甽浴土乎⑩?子能使保温安地而处乎?子能使雚夷母淫乎?子能使藳薮节而茎坚乎?子能使穗大而坚均乎?子能使粟圜而薄糠乎?子能使米多沃而食之彊乎?无之若何?”[10]
后稷的这段话,完全以问句的形式出现,并没有对自己的提问一一作答,但可以推见其原文中在这些问句之后,应是对这些问题的一一解答。而就这些问题的具体内容而言则都是关于如何“任用土地种植”,“然后可得美稼而丰收也”的[11]。
其三,主张帝王亲耕,王后亲织,为百姓耕桑率先垂范。《汉志》所谓“鄙者为之……欲使君臣并耕。”即指此而言。《孟子·滕文公上》陈相道许行之言曰:“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雍飧而治。”《吕氏春秋·爱类》篇引“神农之教曰:‘士有当年不耕,则天下或受其饥矣;女有当年而不绩者,则天下或受其寒矣’”之后,接着又说,“故身亲耕,妻亲绩,所以致见民利矣。”《上农》篇引“后稷曰”所“以务耕织者,以为本教矣”之后,也说:“是故天子亲率诸侯耕帝籍田,大夫士皆有功业……后妃率九嫔蚕于郊,桑于公田。”这些都说明提倡“君臣并耕”,确实是先秦农家的重要思想主张。故蒋伯潜在其《诸子通考》中曾谓“君臣并耕”之主张,并不如班固所斥为“鄙者之所为”,“此正农家之特见。”[12]
对于农家思想的以上特点,只有第三点历来存在争议。自班固著《汉志》以来,即以为“帝王躬耕”的主张只是农家中的“鄙者”之所为,而非农家思想之正宗。但根据我们的研究,“君臣并耕”实只是原始农业社会包括部落酋长在内的所有氏族成员共同劳动的一种生产和生活方式,到夏、商、周三代则演变为天子“耕籍田”的礼仪制度。现代史学家的研究认为,大约在新石器或野蛮时代的下期,“为传说中之神农、黄帝时代”,“正是由采集、狩猎经济转化到农业、畜牧经济的时代”,亦即原始农业开始的时期[13]。但由原始农业时期,人类尚处于原始的共产主义社会,部落酋长(如农业的发明者神农、后稷等)和全体氏族社会成员共同劳动、平均分配劳动果实,此即所谓君臣“并耕而食,饔飧而治”。后来,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这种君臣共同劳动的形式也随着社会脑力劳动(“劳心”)与体力劳动(“劳力”)的分工而逐渐改变,演变成为了所谓“耕籍田”的礼制。《左传》“昭色二十九年”曰:“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自夏以上祀之;周弃亦为稷,自商以来祀之。”《礼记·祭法》曰:“是故厉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农,能殖百谷。夏之衰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世,能平九州,故祀以为社。”就都是说的这一演变过程。在这演变过程中,似乎先是将君臣共同劳动变成了“方里百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田百亩,同养公田”(《孟子·滕文公上》)的形式,天子、诸侯或农官带领农奴(“野人”)耕种经营庄园,而后则是天子、诸侯平日里不再带领农奴(“野人”)耕种,而只是在孟春正月举行一种象征性的典礼。《礼记·祭法》郑玄注:“(厉山氏),炎帝也,起于厉山,或曰烈山氏。弃,后稷名也。”孔颖达疏:“厉山氏其子曰农,能殖百谷者。农,谓厉山氏后世子孙,名柱,能殖百谷,故《国语》云‘神农之名柱,作农官,因名农’是也,‘夏之衰,周弃继之’者,以夏末,汤遭大旱七年,欲变置社稷,故废农祀稷。‘故祀以为稷’者,谓农及稷皆祀之,以配稷之神”。对这一演变过程有更多的猜测。
《礼记·祭法》及杜注、孔疏中的这段话,虽然重在追溯社稷祭祀的来源,但无意中多少也道出了“君臣并耕”由原始社会的部落酋长与全体氏族成员共同劳动,到设置农官耕种“公田”,再到成为一种祭祀礼仪的演变过程。而这种祭祀典礼,又是与所谓“耕籍田”的活动联系在一起的。上引《礼记·祭祀》杜注及孔疏都说明了这一点。而且《诗经·周颂·载芟序》:“载芟,春籍田而祈社稷也。”《毛传》曰:“籍田,甸师氏所掌。王载耒耜所耕之田,天子千亩,诸侯百亩。籍之言借也,借民力治之,故谓籍田。”《汉旧仪》曰:“春始东耕于籍田,官祠先农。先农即神农炎帝矣。祠以一牢,百官皆从。”还对“耕籍田”的礼制有较详细的解说。
根据上引《礼记·祭法》杜注及孔疏来看,由原始农业的部落首领与全体氏族成员的共同劳动,到天子、诸侯只是象征性地耕籍田、并祭祀神农、后稷的礼仪制度,似乎形成较早。孔疏说在夏初神农氏“能殖百谷”的儿子柱之后,人们已开始祀“农”;到了夏朝末期,周人的始祖后稷继任农官,商初因“遭大旱七年,欲变置社稷,故废农礼稷。”一直到西周,这种制度一直不废,只有如周宣王这位的统治者才有不遵守这一典制之举。《国语·周语上》曰:
宣王即位,不籍千亩。虢文公谏曰:“不可。夫民之大事在农,上帝之粢盛于是乎出。……古者太史顺时覛土……太史告后稷曰:‘自今至于初吉,阳气俱蒸,土膏其动。弗膏弗渝,脉其满眚,谷乃不殖。’稷以告王曰:‘史帅阳官以命我司事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动,王其衹祓,监农不易。”王乃命农大夫咸戒公卿、百吏、庶民,司空除坛于籍,命农大夫咸戒农用。……及籍,后稷监之,膳夫、农正陈籍礼,太史赞王,王敬从之。王耕一墢,班三之,庶人终于千亩……’”
这段文字虽然是为了记录虢文公对周宣王“不籍千亩”的箴誎,但其实是详细说明了后稷时代天子“耕籍田”的制度。由此可知,此项礼制实行年代的久远。故韦昭在“宣王即位,不籍千亩”下注曰:“天子千亩,诸侯百亩,自厉王之流,籍田礼废,宣王即位,不复遵古也。”东周以往,春秋战国,天下纷争,礼崩乐坏,籍田之礼则无由得闻。两汉帝王偶有重农者,如汉文帝、汉明帝,尝躬耕籍田。《汉书·食货志上》曰:“于是上(汉文帝)感(贾)谊言,始开籍田,躬耕以劝百姓。”《后汉书·显宗孝明帝纪》载:“四年春二月辛亥,诏曰:‘朕亲耕籍田,以祈农事。’”但由于一般人对“耕籍田”之礼的真正源流并不清楚,故即使如班固这样的硕儒也极诋农家“君臣并耕”之说,以为乃“鄙者”之所为,“悖上下之序”也。其实,如果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所谓“君臣并耕”,只是上古原始氏族社会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劳动和夏、商、周三代“天子”(最高统治者)派农官监督农奴耕种“公田”的遗风,而与道家所谓“高尚其事,不事王侯”是并不相同的。如果说孟子因对当时儒家之外的其他诸子学派有些神经过敏而斥之的话,班固则是在不明就里的情况下跟着孟子起哄。
三、农家学派与楚国的关系
在先秦诸子中,农家是学派创始人、主要成员和发展历史都不甚清楚的少数几个学派之一。鉴于春秋战国之前,我国的学术皆在于官府,故《汉志》有“诸子皆出王官”之说。所以农家学派的产生,也应如儒、道、墨、法各家一样,都是春秋之末学术下移、士阶层兴起的产物。春秋时期以前本由农官所掌握的有关农业知识和思想主张,随着农官的“失职”而带到了民间,而民间也有部分士子在求学的过程中对农业生产知识产生了兴趣,有“学农”、“学圃”的要求。《论语·子路》即有“樊迟请学稼”和“请学为圃”的记载,足见当时热心“农学”者有人。故从理论上讲,农家的成立必有赖于农家学者的出现;而从《汉志》及部分先秦文献的分析来看,作为一个农家学者应同时满足如下三个条件:
第一,他必须是一位“学士”。樊迟是孔子的学生,虽被孔子斥为“小人”,但也应该在“贤人七十二”之列(《论语》有樊迟“问仁”的记载),称他为“学士”大概也说得过去。像他这样的人又对农学有兴趣,故可以说他已具备了农家学者的初步的条件。只是由于史料乏载,我们无法知道樊迟后来是否从他处学得过农业知识,所以他实际上应还不是一位农家学者。
第二,他不仅是有学问(特别是农业知识)的士人(“学士”),而且还应是一位农业生产的实践者,或者说他还必须是一位躬耕于垄亩的士子。我们虽然说樊迟是一位想学农的“学士”,但他却不能算是一位农家学者,这除了不知道他最终是否还从别的渠道学到农业知识之外,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他肯定没有躬耕的实践,不曾亲自耕植、播种和收获,所以他算不得是一位农家学者。如果单就具有相关的农业知识,或认识到掌握与农业、农作物相关知识的重要性而言,不仅樊迟,即使是贬斥学农,但却被别人斥为“五谷不分”(《论语·微子》)的孔子,也未必完全不重视或不懂得农业知识的重要性。孔子在教他的儿子孔鲤学《诗》时就曾说,学《诗》可“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但因为孔子“四体不勤”,所以不论他再怎么博学,也是没有人会把“农家学者”的源头往他那里追溯的。
第三,我认为,甚至是最重要的,就是作为一位“农家学者”,他必须有“君臣并耕而食,饔飧而治”主张。因为我们知道,先秦诸子虽然彼此思想互异,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他们都喜抬出往古的“圣人”来立论。儒家的孔子以尧、舜、文、武、周公为“圣人”,认为这些“圣人”的特点是讲“仁义”;墨家墨翟推崇的“圣人”是夏禹,他“尚贤”、“尚同”,“身执耒鍤以为民先”;道家和法家的“圣人”虽与农家有些相似,都是神农、羲皇之类,但道家强调的是“无为”与“不争”,法家的“圣人”则是依“法”、“术”、“势”而获得了“无为而治”的王者,与道家纯粹的“无为”并不相同。农家要建立自己的思想主张,自然也要塑造自己的“圣人”,那就是神农、后稷,前者是原始农业社会的部落首领与全体成员共同劳动的典范,后者则是早期阶级社会带领“小人”们与帝王共“耕籍田”的农官——总之,其特点是“君臣并耕而食,饔飧而治”的。故我们在上文曾经指出,这是农家区别于其他诸子学派的最大思想特点,并不是所谓“鄙者”之所为。
由于现存文献中没有农家学派传承人物的明确记载,遂使对农家学派传承源流的考察成为历代学术界的一大难题。但如果以我们所确定的农家学派人物的三个条件来看,对先秦农家学派的形成、传承及学者群的考察,还是可以找到一些线索的。
由于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真正做到了“有教无类”的平民教育家,他改变了此前学在官府的教育格局。所以,虽然严格地说来,中国先秦农家思想的因素和农业知识的积累,固然可溯源至远古的神农氏及后稷等三代“圣人”和农官,但直至孔子本人和他的学生,是都不能算作是农家学者的——那时自然还没有农家学派。因为他们并不符合我们此处所说的作为农家学者的三个条件。从现有文献来看,比较接近于我们所说的作为农家学者条件的,应该是孔子游楚时和弟子所遇到的长沮、桀溺及荷蓧丈人。《论语·微子》载:
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之孔丘与?”曰:“是也。”曰:“是知津矣。”问于桀溺。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孔丘之徒与?”对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辍。子路行以告。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以与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在《论语》的同一篇还记有一位荷蓧丈人。从《论语》的这篇记载可知:(1)长沮、桀溺、荷蓧丈人称孔子为“辟(避)人之士”,而自称为“辟(避)世之士”,他们和孔子一样属于有学问的“士人”,这是可以肯定的;(2)但他们与一般的隐士(“隐者”)又有不同,即他们不是那种有着优裕的生活条件、随时准备东山再起的“隐士”或“道士”,而是肢体勤劳、身执农具耕耘田间的劳动者,因此他们必然积累了一定的关于农业生产的经验和知识;(3)虽然他们没有明确提出所谓“君臣并耕而食,饔飧而治”的主张,但从他们批评孔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可知他们是不赞成将书本知识与实践活动(或者说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完全分离的,因此他们对“君臣并耕而食,饔飧而治”的主张至少应该是不会反对的。因为这些人很像“隐士”,《汉书·艺文志》中说农家学派中的“鄙者为之,以为无所事圣王”,很可能就是指他们而言的。而从他们生活的时代来看,他们被孔子及其子弟称为“丈人”(何晏《集解》引包咸曰:“丈人,老人也。”)可见他们或许还要年长于孔子,至少得与孔子的年龄相伯仲——这也就是说,先秦农家最早的出现当在孔子时代,长沮、桀溺和荷蓧丈人之类,应该是现在可知的最早的一批农家学派的代表人物。
而如果从地域上来考察,我们则又会发现,先秦这批最早的农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应该与战国中期的许行、陈良、陈相等人一样,同样都是“楚产”。所以我们似可以进一步推断,先秦的农家学派也应该是源于楚国,并兴盛于楚国的一个诸子学派。
首先,长沮、桀溺、荷蓧丈人这些农家学派的先驱者们都是楚国人。
长沮、桀溺、荷蓧丈人等人虽然《论语》、《史记》等书都没有言及他们的籍贯,但他们都是孔子“自蔡如叶”或“去叶,反于蔡”途中所遇,故其地理方位可定。《史记·孔子世家》:“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以为隐者,使子路问津焉。”裴駰《集解》云:“郑玄曰:‘耜广五寸,二耜为耦。津,济渡处也。’”张守节《正义》曰:“《括地志》云:‘黄城山俗名菜山,在许州叶县西南二十五里。’《圣贤墓记》云‘黄城山即长沮、桀溺所耕处。下有东流,则子路问津处也。’”如果按照这一记载,孔子师徒遇长沮、桀溺、荷蓧丈人之处,当在今河南南阳的叶县境内。叶县是楚国县公沈诸梁的采邑,自然属楚地,则长沮、桀溺、荷蓧丈人也就属于楚人了。因此,可以说,先秦农家学派最早应该是兴起于楚国的。
其次,农家学说的思想渊源及主要传播地域也主要是在楚国。
夏、商及西周三代学在官府,关于农业的知识和文化亦为朝廷的农官所掌握,春秋战国时期学术下移于民间,儒道是主要的知识或学术的传承者。但是,孔门儒家自知于农、于圃不如老农,不仅他们的教学的内容中无此类知识,而且还斥责求学此类知识者为“小人”。道家则高卧东山、坐而论道。故从现有文献来看,关于农业方面的学术和知识显然并不是由邹鲁礼乐之乡的知识群体所继承的。《史记·五帝本纪》张守节《正义》引《帝王纪》云:“神农氏,姜姓也。……人身牛首,长于姜水。有圣德,以火德王,故号炎帝。初都陈……又曰列山氏。”列山,即厉山。《括地志》云:“厉山在随州随县北百里,山东有石穴。(曰)[昔]神农生于厉乡,所谓列山氏也。春秋时为厉国。”我们知道,在《孟子·滕文公上》曾明确提到“陈良,楚产也。”则先师事陈良、后师从许行的陈相、陈辛等亦应为“楚产”明矣。许行,孟子斥之为“南蛮鴃舌之人”,许行固当为楚人。《通志·氏族略二》曰:“许氏,姜姓,与齐同祖,炎帝之后,尧四岳,伯夷之子也。周武王封其文叔于许,以为太岳之后,今许州是也。”而根据《春秋·成公十五年》的记载:“许迁于叶。”孔颖达疏:“许畏郑,南依楚,故自迁为文。叶,今南阳叶县也。”这就进一步证明了许行确属楚人。换言之,在春秋以后,农学既不再由官府掌握,民间一般的儒生也颇轻视之。农学只能在神农氏原先生活的地区、由他们的后世子孙在祖宗祭祀或祖先崇拜的形式下所继承。故有学者曾经指出,春秋战国农家学说“形成于荆楚之地,是有一定的思想根源和社会根源的。”[14]
第三,由现有文献来看,不仅农家学派的先驱者是楚人,其思想根源和社会根源在神农氏居处的楚地,而且其形成、传播和兴盛之地也主要在楚国。
上文我们曾经说到先秦农家的先驱者应是春秋末期的楚人长沮、桀溺、荷蓧丈人等,战国中期楚人许行、陈相等人则将农家学说的发展推向高潮。许行“其徒数十人,皆衣褐,捆屦织席以为食。”(《孟子·滕文公上》)他在楚国收徒授学,传授农家学说自不必说;其弟子陈相、陈辛兄弟更远至于滕,不仅自己实践农家学说,并且还成功说服了滕君。上引《吕氏春秋》、《管子》等各书中所记的“神农之教”、“神农之法”或“后稷之言”,学者们一般认为“是战国时候的东西”[15],《汉书·艺文志》在录“《神农》二十篇”、“《野老》十七篇”时,班固又自注曰:“六国时,在齐楚间。”①故可知先秦农家学说的传承、兴盛之地主要皆在楚国。
综合以上几个方面,我们似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农家学说实际乃是原始农业社会部落首领与全体氏族成员共同劳动的遗风,在夏、商、周(西周)三代,它演变为农官引导君臣并“耕籍田”(包含“祀先农”之礼)的制度。春秋战国,礼崩乐坏,学术下落民间,原始“君臣并耕”的遗风和“耕籍田”、“祀先农”的礼仪主要为原居于楚地的神农氏后代所传承,故先秦的农家学说主要形成、传播和兴盛于楚地,它的先驱者可追溯于春秋末期的楚人长沮、桀溺、荷蓧丈人等“隐士”,战国中期的许行、陈相师徒的学术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则代表着先秦农家学派的发展达到了鼎盛期。
注释:
①案:《汉志》于“《神农》二十篇”下原注:“六国时,诸子疾时怠于农业,道耕农事,托之神农。”刘向《别录》并“疑李悝及商君所托”。但如果从农家学说的思想渊源程序来看,我以为当属于楚国神农氏后人所记“神农之教”或“神农之言”的传本,属之李悝及商君是无根据的臆测。
标签:吕氏春秋论文; 儒家论文; 淮南子·齐俗训论文; 法家思想论文; 先秦历史论文; 汉书·艺文志论文; 经济学派论文; 国学论文; 孟子·滕文公上论文; 绎史论文; 炎帝论文; 墨家论文; 道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