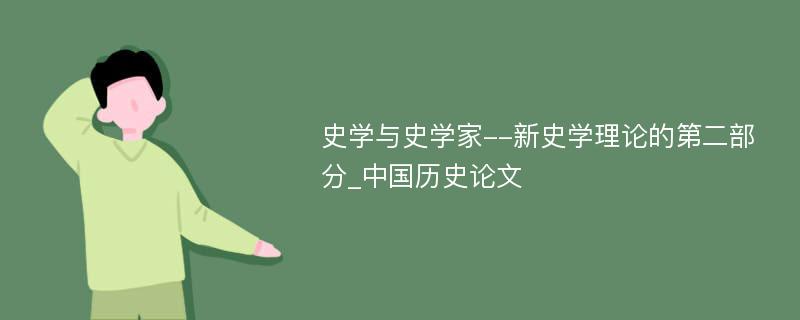
史学与史家——《史学新论》之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史家论文,新论论文,之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历史学是在历史学家的作坊里完成的,但历史学家的创作场景并不在历史学家的作坊里,而是人类社会的全部历史。人类社会的历史包罗万象,就看历史学家如何取景进行创作了。历史学有不同的范型,不同范型的历史学首先是由历史学家如何取景决定的。例如,只取历史上的精英人物,就只能创作出英雄传记;只取政治事件,就只能创作出政治事件史;只取某一事类,就只能创作出单一的叙事史;如此等等,不作备举。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要求我们摄取人类历史的全部场景,从总体上把握人类社会的历史,包括人类历史活动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把人类历史尽可能全面地再现出来。记得马克思说过这样的话,我们只知道一门科学,这就是历史科学。历史可分自然史和人类史。研究自然史,是各门自然科学的任务;研究人类史,是各门社会科学的任务。由此可见,社会科学的各门学科所研究的是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而历史学科所要求的是从总体上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的全过程。作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必须有全面考察并把握人类社会历史的能力。不具备这种能力,是不可能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创作出合格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著作来的。
对人类历史,可以作纵向考察,也可以作横向考察。横向考察,就是要研究人类社会各个方面,这是要由相关的社会学科来帮助完成的。如经济学、人口学、文化学、政治学、民族学、社会学、伦理学,等等,等等。纵向考察,就是上下贯通,古今贯通,研究人类历史的由来、发展阶段、从历史到现实的演变和未来的历史走向。人类历史好比是一条巨大的长河,有主流、有支流,有湖泊,有港湾,曲曲折折,倾泻而下。所谓纵向考察,是就历史的主流而言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根本要求,是把握历史的主流,同时兼顾其相关的支流,湖泊、港湾,等等,即进行全流域考察。因此,作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就必须具备多学科的知识,对人类社会的历史进行多方面多层次的研究,包括自然界的变化对人类历史进程的重大影响。例如,地球板块结构的变化,冰期和间冰期,大气环流的变化,等等。不具备多学科的知识,特别是和历史学科有亲缘关系的那些学科,只凭从书本上抄来的几个公式和一些理论标签,再找一些材料,相互捏合在一起,是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举两个例子来说吧!
研究中国古代社会,除古文献之外,还必须具有考古学、古文字学、民族学以及其他相关学科的知识。不具备这些知识,只凭手中的一点可怜的材料和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抄来的几句话或从马克思主义二道贩子那里搬来的公式,能对中国古代社会进行全面地科学研究吗?我所以推崇郭沫若对甲骨文和金文的系统整理和考释,是因为没有一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能像他那样对材料下过这么大的功夫。有人认为郭沫若轻视文献,甚至认为他用的文献材料是从别人那里抄来的。岂不知,郭沫若青年时代是熟读过经书的。
再如中国经济史,除经济学的知识外,还应有人口学、资源学、财政学、货币学、商业学、法学以及其他相关学科的知识。不具备这些知识,仅凭一大堆材料和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简单理解或受斯大林歪曲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理论,能对中国经济史进行全面地科学研究吗?为什么直到现在还没有一部较好的中国社会经济史呢?材料不足是一个原因,更重要的是我们始终没有摆脱所谓奴隶制、封建制;不发达奴隶制、发达奴隶制;领主封建制、地主封建制、封建农奴制、封建租佃制,等为框架的公式经济体系。
举一反三,不多说了。即此可见,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不具备多学科的知识,是不行的。要想成为马克思历史学家,就必须具有多学科的知识。当然,历史学家并不一定是其他学科的专家,但由此并不能说,历史学家不需要其他学科的知识。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学科可谓交叉学科。这是由人类历史本身的特性决定的。我曾经说过,历史是一部百科全书,故而历史学身兼百科。人类历史的发展不只是有点、有线,还有纵横交错而成的面。为什么直到现在历史研究多点与线性研究,而很少全面地系统研究呢?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但应注意,历史学科并不是一门综合学科。作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具备多学科的知识,对历史进行多学科的交叉研究,尽管是必要的,然而又是远远不够的。如果我们仅仅对历史进行综合研究,历史学很可能成为杂学。这样,历史学家就要成为杂家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决不是杂家。其所以然者,在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能抓住历史的主流,在历史长河的主航道中行进,通古而及今,由今而知来。这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能够作到而其他历史学家所作不到的。他们也可以有自己的体系,但他们不可能有科学的历史体系。为什么呢?
前面我们把中国历史比作一条巨龙,这条巨龙的龙脉是什么呢?我们必须抓到这条线索。抓到龙脉,这条巨龙就活起来了。只抓龙须,不行;只抓龙爪,也不行;只看到龙鳞,更不行。具体地说吧!
我将中国历史划分为洪荒时代、族邦时代、封建帝制时代。这三个时代各有其主脉。如洪荒时代,其主脉是从生物人到社会人的衍化过程。或者说,最初的人猿是如何从生物圈中走出来,跨进人类历史轨道的。这是一个极其漫长的历史过程,时间以数百万年计。如果划分几个阶段,则是:生物人阶段,能人阶段,直立人阶段(即猿人),智人阶段。智人阶段又可分为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晚期智人已经和现代人无甚差别了。我不用石器为线索,也不用劳动为线索,因为总的看来,这个时代的人类还处在生物圈中,进行生存竞争,人类是靠生存竞争诞生于世的。
族邦时代的历史主线是什么呢?曰宗族的兴衰降替。据此,我将这个时代分为四个时期:万邦时期(尧、舜),族邦联盟时期(夏代),族邦体系形成和建立时期(商、周),族邦体系瓦解和宗族全面衰亡时期(春秋至战国初)。
封建帝制时代的历史主线是什么呢?曰:三次历史大循环。其表象是三次分裂和统一,其基础是土地关系的三次大循环(小循环不算)。这三次大循环包括诸多方面,各有起讫,就不在这里多说了。我反对按朝代编写中国历史,或者按朝代分段编写中国历史,因为朝代的更迭不足以反映中国历史的规律。我也不赞成按其他线索和文化传统来编写中国的历史,因为这不是中国历史的主线。
依据上述规律,中国已经迈入它的第四次大循环,即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大循环。中国将由此以新的姿态走向世界。这,就是我提出的通古及今的中国历史发展体系。
我不敢说已经完全抓住了中国历史的龙脉,但我敢说,在运用多学科的知识研究中国历史时,必须抓住中国历史的龙脉。如此,才能纲举目张,弘扬历史主旋律,兼有多样化,把中国历史有筋有骨有血有肉地谱写出来。否则,历史的主流将被淹没,变得杂乱无章,好象一大块漫无边际的混交林,即使能走进去,也是出不来的。作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必须具备处置历史学科和其他相关学科的交互关系的能力。
二
人类历史的场景是无法再现的。这是因为,历史的场景多半是一次性的,时过境迁,原来的场景就不复存在了。比如说,现存的高级类人猿还能不能进化为人呢?不能。因为,现在已经没有从生物人衍化为社会人的场境了。我是相信有野人存在的。所谓野人,就是从生物人到社会人的衍化过程中落伍的人。落伍之后,失去境遇和时机,就再也无法衍化为社会人了。我曾经说过,中国历史上只能有一个孔夫子,一个秦始皇,在汉代去找先秦儒家或法家,纯属白费气力。说句不客气的话,这叫瞎子点灯,白费蜡!我认为,郭沫若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是因为他打响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第一炮,而且这一炮打得很出色,很有生气。如晴天霹雳,振聋发聩,令中国史坛别开生面。现在有些人再说长道短,还是得沿着郭沫若开拓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方向前进。这是历史,不服不行。譬如说,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有谁能否认呢?对历史事实,必须有历史主义的态度。不能抹杀,不能歪曲,不能夸大,不能缩小,搞非历史主义。更不能口中念念有辞,大谈特谈历史主义,但做起来却违背历史主义。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必须以事实为依据,离开事实,空谈历史主义,终不免于非历史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必须是实实在在的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者。
但是,人类历史的场景又是不能重现的,这该如何是好呢?我看别无它途,只有老老实实去搜寻人类历史的场景的遗迹和遗物了,这些遗迹和遗物,有载诸典籍的,记录在案的,是谓历史文献;有典籍失载,散失在各个角落的,是为史料。广义的史料可包括历史文献,但不限于文献,而是一切能够见到的东西。包括口碑史料、私人传记、航海记、旅游记,等等,等等。可以这样说,史料是无所不包的,任何历史遗迹和遗物,不管是见诸文字的和文字所无的,都是史料。我们应当重视史料搜集整理的工作,并学会运用现代科学所能提供的一切手段和方法去搜集和整理史料。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恢复已逝去的历史场景,把过往的历史再现出来。治史不等于治史料,但不治史料是无从治史的。治史料不应有什么先验的框框,如什么大胆假设和小心求证之类,只须把用科学方法搜集到的史料加以科学整理就行了。如果在收集和整理史料时预设这类框框,按这类框框收集并整理史料,还谈什么科学性和客观性呢?人类的历史活动不可能按我们的假设来进行,自然不会按我们的假设留下史料来。把自己的假设加诸古人,或者说加诸古人留下的史料,在治史料时候就难免主观主义,更不要说按自己的假设来治史了。我们在治史料时不应有这类前提,而应以无条件地恢复人类历史活动的全景为宗旨。人类社会活动是多方面的,对收集到的史料也要按不同的系列进行整理。治史是史学家的工作,治史料同样是史学家的工作。人人都能治史,就用不着史学家了。治史须要史家有治史的能力,治史料同样须要史家有治史料的能力。例如,辨别史料的能力就不是任何人都能具备的。史学家这种能力是主观性的,不是史料本身所具有。所以,说治史料用不着史家的主观认识,这是自欺欺人之谈。问题在,史家的主体认识是不是和客观相一致,如果彼此相一致,这种主体认识就应该说是客观的、科学的;反之,则是不客观,不科学的。作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不仅应当重视史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而且要力求提高自己治史料的科学识辨能力和综合能力。这样,在治史料时,主体认识和客体就可处于一致的状态,要恢复历史场景,进行历史创作,就比较好办了。
当然,把史料整理好,只是完成了治史的初级工作。从历史学家的工作程序来说,可称第一道工序。第一道工序是很重要的,没有这一道工序,就动手治史,只能在史学阵地上打零工,搞点小打小闹的活计,是不可能对历史学科有所建树的。打零工有时也能出真活,关键在于所用材料和解说是不是准确无误。如果用的是不经审核的二手资料,拼凑成书,生产出来的就很可能是残次品了。天下文章一大抄,此之谓也。不过,这样的人是谈不上历史学家的。这样的文章,这样的书,写得再多,也只能算个历史杂家。专家之文,必成系列;专家之书,必有体系。杂家则不然,无一定之规,无一定之见,东拼西凑,铺陈成文,理把成书,只费功夫,不费心血,章法虽可,但无真知灼见在其中焉。
治史不能没有史料,史料必须加工,而后才能成文,才能成书。对搜集到的史料,按其类别,分类排比,归纳成文,合成文集;或按事类系统归口,考其源流,连贯叙述,作为专著。此类著作,可称专家矣。因此我们说,专家之文,必成系列;专家之书,必有体系。系列者,对史料分类排比归纳之系列也;体系者,事类之系统考释连缀叙述也。能为此者,要化工夫,也费心思;文有规矩,书有条理,足备一格,非专家不足以成之。这类专家,也有层次,有文有书,是其高档者。但其高档者,也不过能按事类连缀成书而已。
历史专家和所有专家一样,都是可贵的。贵在其专,贵在其精,贵在其独具一格。然而,历史专家又是有局限的,限于一格,专于一偏;只知有此,不知其他。较之历史杂家,他们自有其出类拔萃之处。杂家之短,在于其博杂而缺少精品。文章一大箩,拳头之作不多。书籍一大堆,传世之作绝少。样样俱全,样样平平。他们不是一专多能,而是无一专者。开杂货铺,制售的全是大路货。当然,杂家也有其可取之处,作个编书匠或教书匠,可胜于专家。
在历史学家中,其上乘者要数大家。大家治史,在一个自然历史时段里,能抓住主流,进行全流域考察,其为文也,必着眼于要害环节,条分理析,破疑解难。如此成集,自成系统。其为书也,必有主线,层层展开,面面剖析。为文为书,都以恢复这个时段内的社会构成和社会整体为指归。我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就是力图这样作的。结果如何?不敢自必。但我认为,这样进行研究,就认识论和方法论来说,是无可非议的。我力图从总体上把握这个时段内的历史全景,也是无可非议的。在这里,不仅仅是如何全面地占有史料和驾驭史料的问题,而是如何运用这些史料恢复中国古代社会全貌的问题。时过境迁,难得其全。但这个社会阶段的轮廓、脉络、骨骼、肌肉、关节、机理,总还是可以复原的。破碎的器物可以复原,逝去的社会同样可以复原。我们应力争成为复原过往历史的大家。
杂家、专家、大家,其差别的根源在哪里呢?曰:史家主体认识之等差也。史家的品格,不是取决于史料、历史文献和史实,而是取决于史家对历史文献和史实的主体认识,取决于史家对客观历史的主观解析能力,取决于史家对史料的制作改造工夫。所以,否认史家的主体认识介入历史客体,以为这样就会失什么客观性和科学性,是根本错误的。如前所说,史家治史料是离不开史家的主体认识的,更不要说史家之治史了。能治史料才能掌握史料,没有这方面的专门知识和本领,搜集到的史料不过是个破烂摊子,乱七八糟的旧货库。有些人以自己搜集到不可胜计的史料而自豪,然而对自己的旧货家底,连自己也是不清楚的。史料无数,史家心中也无数,这只能说是不会治史料了。排比史料,归纳成文,这也是一种主体认识,难道史料不经史家之手,能自动分类排队吗?按事类联缀成书,更是一种主体认识,因为历史事类是不会自行串联的。对历史文献和历史事实,必有所见,必有其解,必有其说,而后才能成为史家。读书万卷,一无所见,一无其解,一无其说,当历史文献和史料的搬运工,不经消化就吐出来,这能叫史家吗?史家之能事,在于对历史文献和历史事实,解释得当,说明透析,能透过历史文献和历史事实复原过往的历史。历史文献和史料不等于历史实际,只有通过对文献和史料的精细加工,才可见到历史实际。历史学家的头脑就是一部特有的加工机器。所以,一个历史学家的知识结构和思维结构,是非常重要的。我将历史学家的思维结构分为三个层次:第一是感性层次,第二是理性层次,第三是悟性层次。悟性者何?豁然贯通之谓也。这一点很是重要,要发现历史规律,没有悟性不行。因为规律是深藏在事物内部无形象可察的。研究哲学和宗教,也要有悟性,因为哲理和教理都是在高空的精神传递中进行的,非讲习修炼所可得也。知识结构很重要,应博学以成之。思维结构更重要,应从认识规律入手反复循环以成之。研究历史不能行不由径,更不能思不由径。人的行为是受其思想支配的,史家治史也是受其思想支配的。有各忠各样的思维模式,实证主义是一种思维模式,事证主义也是一种思维模式,主观感知又是一种思维模式,传统史学之义理何尝不是一种思维模式。当然,马克思主义哲学更是一种思维模式,我是信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之所以然,是因为我还没有发现比马克思主义哲学更好的思维模式。马克思主义思维模式可以含概其他思维模式,其他思维模式不可能含概马克思主义。所以,用事证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是非常滑稽可笑的。这种人既不识货,也不识相,坐井观天,夜郎自大,足见其不自量也。当然,也有搞章句马克思主义的,也有搞公式马克思主义的,但这种作法本身就是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不相容的。我们不能因为反对章句马克思主义、公式马克思主义而抛弃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模式。什么主观不主观,凡是思维模式都是主观的。因为,这是史学家的思维模式,存贮在史学家脑海里的东西。史学家不是机器人,更不是机械手,要人操作才能活动,才能运转。即使是史学家有一付机械思维的脑袋,也不能说他是机器人,因为这付机械思维的脑袋是勿须别人操作的。什么三论,什么新三论,还不是要由人来操作吗?金观涛把中国历史简化为专制主义、小农经济、儒家官僚网三个要素,编成程序,进行运算,结果就得出了超稳定社会结构说。这不是什么三论,也不是什么新三论,而是金观涛的思维模式里只有这三股线,只能作出这三要素论。但是,要用这样的思维模式代替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模式,肯定是不行的。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模式是多维型的,不止有感性思维模式,还有理性思维,更有悟性思维,逐级提高,循环进行。所以,用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模式,可以找到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还原过往的历史。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无往而不胜,其要害就在这里。历史包罗万象,我们只能用多维型的思维模式,才能认识历史。客观的历史资料被摄入主观的超精密型思维模式,反复进行高精度的加工,才能还原历史。在这里,主体认识和历史客体是高度一致的,合而为一的。还分什么主观和客观吗?作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我们应当不断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不断强化自己的思维结构和认识功能,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规律化入自己的脑海里,落实到自己的研究实践中,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献出毕生的精力。
三
应当承认,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来说,有一个二次创业的问题。所谓二次创业,简单地说,就是破除公式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历史体系,建立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历史体系。我们强调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强化自己的思维结构模式,都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且非如此不足以达此目的。我们之所以要更新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并不是因为有些人在明里暗里反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而是由于:一、公式化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原本就不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为指导建立起来的;二、公式化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是不符合或不完全符合中国的历史实际的;三、公式化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根本上说是脱节的。我们要破除旧式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是为了建立新式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而有些人反对旧式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是为了建立什么三论史学(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或再度恢复实证主义史学以及与实证主义史学类似的史学,还有一些连自己都说不出名目的史学,等等,等等。但我可以断言,这些人是成不了大气候的。何以言之?
我们当前面临的,并不是什么学派之争或建立何种学派的问题。我们的问题,是要不要对中国历史进行系统的全面的再认识?如何进行系统的全面的再认识?如何从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寻求解决现实问题的启示?如何把握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走向?我们说是研究历史,实际上研究的是过往的社会。过往的社会不能再生,要由历史学家把过往的社会复制出来,回归原位。为什么要费这样大的劲?因为现实社会是从过往的社会转过来的。不认识过往的社会就不能了解现实社会,反之亦然。解决这些问题,是历史学家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历史学家要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回避这种责任和义务,就不配作历史学家。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要心系国家,心系中华民族,心系全体人民;心系祖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心系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他们承担的是人民的事业,应以撰作中华民族的历史丰碑为天职。撰好之后,写上自己的名字,也不过表示对中华民族负责而已。但愿我们的历史学家,都有这样广阔的历史胸怀,满怀热情投身到自己承担的事业中去。
我们的责任是重大的,任务是艰苦的。如何才能圆满完成自己所承担的任务,交出一张合格的答案呢?这就看我们的知识结构和思维结构模式如何了。用乾嘉考据行不行呢?不行。用实证主义行不行呢?不行。用事证主义行不行呢?恐怕也不行。用“三论”史学行不行呢?看来还是不行。因为论之再三,中国被论扁了。用主观感悟行不行呢?那就没个准了。鹦鹉学舌,照般西方,如什么酋邦之类,行不行呢?缺乏中国味,不行。恢复中国传统史学行不行呢?当然更不行了。这不行,那不行,如何而可?!如何是好?!
环顾西方史学,惟以年鉴派为代表的新史学有足资我们借鉴者。西方新史学原本是从主观经验主义出发的。但后来对着历史大屏幕做文章,在人类历史的广阔天地里,发挥主观认识论和方法论,历史学就为之改观了。我们应学西方新史学派的长处,改写中国的历史学。但在中国食坛上占统治地位的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这样做,岂不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吗?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就看我们如何估价以往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进行反思了。经过冷静的思索,结果发现:我们以往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虽成绩斐然,焕乎其有文章,但无一能逃脱公式主义、教条主义者。如,我们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总以看到马克思写的《资本主义以前的所有制形式》为满足,以为凭此就可以研究中国古代社会了。这且不说,对这篇文章又只摘取其中的“普遍奴隶制”一类名词,妄加发挥,著书立说。这能说不是教条主义吗?再如,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含义,马克思本来是有说法的,后来斯大林修正了马克思,而我们却不顾马克思,只用斯大林的说法。寻章摘句,用以治史,能避免教条主义吗?对人类历史,开列一张公式,中间插入一条阶级斗争的杠子,这能不叫公式主义吗?歪嘴和尚念经,马列本是好经,被一些歪嘴和尚念糟了。一句话,只背词句公式,忘掉精神和实质,这就是以往史学界不少人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奇怪的是,有些人不读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却起劲反对马克思主义;有些人没读多少马克思主义著作,却以马克思主义权威自居,对别人乱打棍子。现在应该是在历史研究中恢复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的时候了!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年鉴派之所以能取得优异的成就,是和他们不自觉地吸收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有关系的。年鉴派的代表人物勒高夫说:“大多数法国历史学家对历史哲学抱有敌意是没有疑问的,费弗尔和布洛克也这样,但他们在自己的研究实践中,锐敏地感觉到即使不是理论探索的必要性,至少也是方法论和认识论探索的必要性。”这就是说,年鉴派是反对历史哲学的,但他们在研究实践中又用了历史哲学。我看,正是从这个高度,他们才推崇马克思为新史学的重要先驱。他们从马克思那里得到了历史认识论和方法论。否则,他们不可能取得如此优异的成就,占据西方史坛的支配地位。
会学学个门道,不会学学个热闹。我们不应只看到他们的多学科交叉研究,而应抓到他们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自觉地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认识论和方法论,建立新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说什么马克思主义不灵了。灵得狠!就看你会不会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认识论和方法论是历史学家的心脏起勃器,心之官在思,就请装上这付心脏起勃器吧!
毛泽东说过,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目的全在于应用。那么,我们应怎样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透视中国的历史呢?我认为:
首先应取消人为地按五种生产方式划分中国历史发展过程的方法,也不要按朝代划分中国历史,如什么先秦史、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宋元明清史,等等。怎么划分呢?按中国历史自然形成的发展阶段来划分。具体地说,人类起源时期,即从生物人到社会人的演进过程,可划分为一个阶段。我称这个阶段为洪荒时代,称人类起源时代亦可。不要再用什么原始群、旧石器时代之类的说法。如果从社会进程来说,则这个阶段应从生物人社会到氏族社会为止。原来我们说的氏族社会或原始社会只是从洪荒时代向族邦时代的转变期,不能视为一个独立的社会发展阶段。故此类名称也可弃之不用。
其次是族邦时代,这是根据中国古代社会的特点提出来的。世界历史上的古代社会都是城邦社会,中国古代社会由族邦构成。这个问题,我写了不少文章,也有专著问世。现在我还没有看到对此持异议者,见到比较多的是引用或发挥我的看法。
应当指出,所谓奴隶制社会的说法是不确切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均无此说。他们用的是古典古代或亚细亚古代。这个时代虽有奴隶,但整个社会并非由奴隶和奴隶主构成。所以,中国族邦时代虽有奴隶制,但不能称为奴隶制社会,古典古代社会亦然。如果用奴隶制社会的说法,则这种奴隶制是哪个时代、何种社会的奴隶制?何种样式的奴隶制?就说不清楚了。我们过去讨论古史分期问题,长期聚讼不决,就是因为只在奴隶制上做文章的缘故。所谓奴隶制社会或奴隶社会之说,偶见于列宁著作,而足成其说者为斯大林。现在看来,这个名称是不能成立的。我的几本书都不以此命名,而是以古代社会名之。如《古代社会形态研究》、《古代社会形态析论》、《古代社会断代新论》、《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史论》,就是出于这种考虑而发的。
在中国历史上,继族邦时代之后,则是封建帝制时代。为什么我不直称其为封建社会呢?我认为,这种说法只适用于欧洲中世纪和斯拉夫人。对中国封建帝制时代的历史来说,是不适用的。为什么呢?欧洲封建社会是单程性的,即只经过一个历史过程。中国封建帝制时代的历史是多程性的,经过大致雷同的三个历史过程。所以不能以一个历史过程论之,迳称之谓封建社会。如然,这三个大致雷同的历史过程就变成同一历史过程的三个阶段了。由于我们视三程为一程,所以许多问题说不清,道不明,现在应当如实地还其本来面貌了。我提出的封建帝制时代历史发展的大循环论,就是据此而言的。有些人感到奇怪,这不是历史循环论吗?我不想讨论循环论的问题,如要绞汁,我可以举出中外历史上许多循环式的例子,进行讨论。我只想证明,中国封建帝制时代的历史确有三个大致雷同的过程。按三程说,许多问题就可迎刃而解了。也有人建议,要我改用螺旋式发展,我想来想去,好像不行。因为螺旋式是就一程而言的,三程怎么是螺旋式发展呢?如果一定要找这三程的联系,恐怕只有绝而复续一语可以当之。
总的来说,原来我们确定的社会发展程序,只适用于欧洲历史。中国历史远较欧洲历史为长,应当有其本身的发展阶段。我提出如上五个阶段,而且每个阶段都有一个从前者到后者的转折时期。经过近代的转折,我国历史开始走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对我所划分的阶段可以讨论,但按历史的自然发展过程划分历史阶段的方法,我认为是完全正确的,符合马克思主义长时段划分的原则。
按历史的自然发展阶段划定之后,我们就可以进一步分段研究了。怎么研究呢?我的意见是:首先要抓到两个历史阶段之间的转折时期,如洪荒时代到族邦时代的转变。过去我们习惯上是按母系氏族社会和父系氏族社会两段处理的,而且一再移动上下限。经我对各地考古资料的研究,结合古代传说,实际并不如此。此说原出于摩尔根《古代社会》,恩格斯在《起源》中赞同此说。我们食而不化,照搬到上述转折时期,结果在考古资料面前老吃败仗。例如,我们原来称仰韶文化为母系氏族社会,龙山文化为父系氏族社会。结果如何呢?现在谁都同意我提出的龙山文化已进入铜器时代早期说,再也不谈什么父系氏族了。龙山文化时期实即中国历史上的万邦时期,还谈什么父系氏族呢?龙山文化而上如仰韶文化,裴里岗文化等,也说不上是什么完全的氏族社会,因为当时的社会,除少数例外,都是以家庭为生活单位的。而氏族则是以相互群婚为特征的。据此,我将这个期间的社会分为前后两个小段:前段为家庭、家族、氏族、部落;后段为家庭、家族、宗族、姓族。上接氏族社会,下接族邦时代。现在有些人又出花招,把族邦时代的萌生阶段单砍下来,作为酋邦期,不知令人说什么好。
其次说族邦时代到封建帝制时代的转变。我们认为,这里有一次社会结构的大变动,应从各方面予以说明。象过去那样,仅仅抓个奴隶制,或按个别材料凑个封建租佃关系,是说不明白的。怎么研究,我和藏知非写了一本书,题曰《周秦社会结构研究》,共约40万字。有兴趣者,读一读此书。这里就不再说了。
在封建帝制时代的三次历史大循环中,每一次都是从土地再分配开始的。我称之为土地关系的三次大循环。如此等等,说明这个时代的历史是呈周期性循回发展的。最近我应《学术月刊》之约写了一篇文章,从10个方面谈了这个问题,可以参看。也不在这里多说了。
对每个自然历史阶段,我主张对其间的社会进行多方面的研究;有阶级的社会,也不能只按阶级和阶级斗争一条线,或什么生产方式,作简单化的研究。如战国至魏晋这个阶段,我在给学生讲课时提到了9个方面,分别进行研究。再找出各个方面的交互关系,进行综合研究。拿阶级关系来说,汉初至武帝就是有变化的,军功地主衰落了,一批新地主取而代之,于是出现了田宅逾制的问题,出现了室庐舆服僭上无限的问题。如此等等,只有进行全面地分析与综合,才能把这个阶段的社会研究清楚。简单化了不行,照比欧洲也不行。如东汉时的地主庄园,以往我们都将之比拟于欧洲中世纪的农奴制庄园。经我研究,二者迥然不同。不同者何?东汉庄园乃农商一体化、城乡结合之庄园也。这里只讲研究方法问题,过多地就不说了。
对每一阶段的社会,都要全面研究,不能只抓一点,不及其余。要点、面、线三者结合起来。有点、有线、又有面,复原一个社会的整体面貌。只抓一点不行,只抓一线不行。可是我们过去的研究,或有点无线,或有线无面,只顾找材料套公式,证明公式就完事。上下左右不相连,缺乏社会网络。这能说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吗?说句不客气的话,这和实证主义的方法是没有什么本质区别的。有些作法,和梁任公之说,也是无大区别的。
当然,我们不可能对一个阶段的社会各个方面,一下子全研究清楚,但从全局着眼,从局部入手,在研究局部时不忘记全局,这总应该可以做到吧!兼则明,偏则暗。单打一,有时连一个小问题都是很难说清楚的。如《史记·陈涉世家》中提到的“发闾左”,如不从当时的社会基层组织进行考察,就说不清楚。说什么闾左贫民,富人住在闾右,当时有这样的基层社会组织吗?孤立地、静止地、片面地看问题,这叫形而上学,不符合马克思主义。
还可举一个例子。欧洲封建社会只经过一程就转为资本主义社会,为什么中国封建帝制时代的历史反复了三程还没有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呢?我的回答是:这三程中每一程都有相当发达的工商业,但就是产生不了资本主义。至于萌芽,每一程中均有之。为什么会是这样?原因在:中国始终没有商人社会,而欧洲中世纪的社会是二元的,既有领主农民社会,又有商人市民社会。在中国历史上的商人队伍中,诸色人等无所不有。有农民,有工匠,有地主,有僧侣,有官僚,有贵族,有时还有皇帝老子。多方参与,缺乏专业商人。专业商人也依附于官府,和农村脱离不了关系。多方参与,自然很是热闹;缺乏专业商人社会,必然产生不了资本主义。中国的农民也多有兼业,如木匠、如铁匠、如石匠、如染匠、如做豆腐,等等,等等。所以,说农民是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纯自然经济,并不符合实际。不符合实际之说,是谓主观主义。
社会是复杂的,我们的脑子也要复杂一些。而要有复杂的脑子,只能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装备起来。有人说,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是灌输式的,但愿灌输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和公式,而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思维精神。
末了,简单谈两个问题。一个是读书问题:中国史书那么多,而且六经皆史,怎么读得好读得了呢?我的意见是:读书要有轻重主次,主要的重点书,要多读,要精读;次要的书则略读,有些只须浏览就行了。我对《左传》和《国语》,是下过功夫的。对前四史,也下过一点功夫;再有就是《资治通鉴》。这里的关键是能不能触类旁通,重点书读熟了,其余的书也就可以旁通了;重点书中所无的,在其它书中一见就记住了。读书的过程也就是对史料分类清理的过程。不要总是忙于抄卡片,抄的越多忘得越多。总之,要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用在读书上,那样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我是不抄卡片的,有时只作点索隐。有的人说我只读过一部书,有的人不知道我为什么读书少而著书多,实则读书也有方法论问题。方法对头,则读书少而得益多;方法不好,读得多了就糊涂了。
另一个是史学理论问题,学此道者,切不可脱离史学研究的实践,只在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辞句上打主意。理论要能回答历史研究中碰到的一些重大问题,不能空对空,谈了一大套而不解决任何问题。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理论应来自实际,而又高于实际,这样对历史研究才有指导意义。我的学生中,有研究史学理论的,我经常提醒他们,不要作空头理论家,不要当马路评论家,说了老半天拿不出一个史学研究的章法来。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把历史唯物主义视作史学理论,这是不对的。历史唯物主义只是历史观,属于哲学范畴。史学理论应是史学家如何治史的理论与方法。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家,就应研究马克思主义史学应有的理论与方法。如: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对象,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任务,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程序,马克思主义史学如何搜集和处置史料,马克思主义史学如何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马克思主义史学与其他各种史学之异同,马克思主义史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应具备的理论素养、知识结构、研究方法,等等。总之,史学理论应是培养史学家的理论,是论述史学家如何治史的理论与方法。历史学家之可贵,贵在多出高质量之产品;史学理论家之可贵,贵在培养出高水平的人才。好比一个体育教练,本人不一定是运动员,但却可以训练出高水平的运动员来。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家,不应介入各派之争,支持一派反对另一派,而应冷静地观察各家各派的理论与方法,考其得失,提出更好的理论与方法。史学理论家应该解决的问题,应是如何改善我们的研究方法,提高我们的研究水平;如何改进史学研究的章法,强化史学研究的品质;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维,思索史学研究中的问题。我常对自己的学生说:我传授不了多少知识,只能讲一些获取知识的方法,考虑问题的方法,解决问题的方法。我给学生讲的第一课,就是我的治学方法。我的学生中有研究史学理论的,在作论文时,我提醒他不要偏向一家,要把各家各派放在同一杆天平上,从其治史的理论与方法,衡量其轻重大小,分出个档次来。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家,应有其特有的品格;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家,也应有其特有的品格。我也搞点史学理论,但我不是史学理论家。有人说我是史论学家,这倒差不多,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就应据史实而论理,把纷杂的史实理出个明白来,就象检察官调查分析案情一样。我们说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一定要落在实处,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解决一些重大的历史问题。中国历史上的重大问题多得很,就看你抓不抓得住,能不能解决,解决多少了。历史是人类智慧的宝库,走进历史,探采中华民族的智慧宝藏,观照现实,解决现实中的重大问题吧!
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一个伟大的新时代,伟大的新时代需要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要由新一代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来完成。新一代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要有超高型的历史哲学思维,多学科的知识结构,渊博的历史知识和获取知识的手段。这样,才能完成新时代赋予我们的创造马克思主义新史学的任务。吾老矣,虽不能大有作为,但愿作新史学的前驱,为振兴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而努力。
标签:中国历史论文; 历史学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中国模式论文; 历史知识论文; 知识体系论文; 古代社会论文; 思维模式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