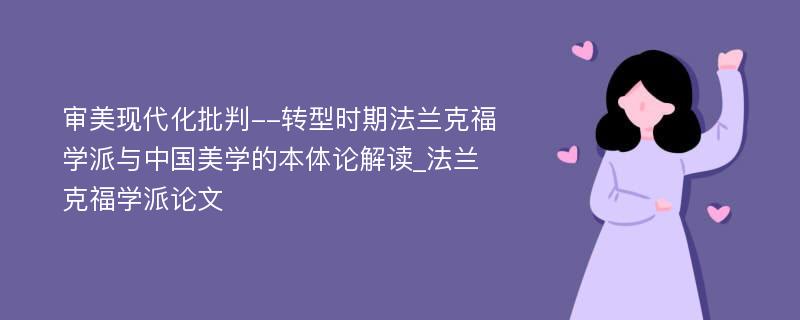
审美现代性批判——法兰克福学派与转型期中国美学的本体论阐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法兰克福论文,本体论论文,现代性论文,转型期论文,学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1 B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1(2001)01-0099-05
现代性是一个内涵丰富而又争议颇多的概念,要准确厘定它的内涵是相当困难的。但是,关于现代性,尤其是审美现代性的讨论,起到了促使转型期中国美学诸多深层问题浮出水面的作用。同时,只要作为实体结构的政治经济制度的转型——现代化仍然是新世纪中国社会的主题,有关现代性、审美现代性的讨论就不会是毫无现实意义的。
从1990年代中国的现代性言说中我们可以发现一种共通的话语范式,即援引卡林奈斯库在《现代性面面观》中对两种现代性——启蒙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的区分,将现代性看成一种充满矛盾的张力结构[1]。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审美现代性的基本内涵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以人为本位,以感性为本体。就前者而言,它是现代性自身的认同力量,是俗世的个体生命在失去彼岸支撑后寻求此岸的支撑;就后者而言,它是现代性的反抗力量,即以审美感性对抗技术理性与工具理性;而将感性的作用推至极端,以感性的原则取消康德意义上的科学与伦理原则,将个体生命的当下沉醉提高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即是审美主义。
从审美现代性角度探讨中德美学的关联,已有一些学者做了有意义的开创性工作。张辉在《审美现代性批判》中论述了20世纪上半叶德国美学东渐中的现代性问题,而本文则将讨论对象锁定在德国法兰克福学派与20世纪末的转型期中国美学,并在审美本体论层面上论述二者的现代性关联。
一
“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这句阿多诺的名言似乎是对艺术与审美的否定,正如马尔库塞在《文化的肯定性质》(1937)一文中揭露艺术的欺骗与慰藉作用一样,然而问题的复杂性是:艺术的否定功能与乌托邦潜能同样是法兰克福学派所坚持的。对艺术的欺骗作用的揭示同样不妨碍他们把艺术与审美看成是消除人的本质异化,走向人性复归的最佳途径,从而营造美妙无比的审美乌托邦。在阿多诺的另一篇文章《许诺》(1962)中,他再度提到了文学与奥斯维辛的关系:“我不想淡化我过去的立论——‘在奥斯维辛之后写抒情诗是野蛮之举’……然而艾森伯格的反驳也确为真切:‘文学必须抵制这个宣判’……实际上现在只有在艺术中,苦难才能找到它的声音与慰藉……艺术作品无言地承担政治所无法负荷的责任。”
显然,阿多诺反对的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艺术,而是被资产阶级肯定文化(affirmative culture)物化为虚假的幸福允诺的艺术。在法兰克福学派美学中,艺术与审美的乌托邦功能是与它作为形式自律的否定功能联系在一起的,霍克海默写道:“艺术,自它成为自律以来,就已保存着从宗教中脱胎而来的乌托邦”。[2](P260)
在法兰克福学派美学的审美乌托邦营建中,一个重要的理论逻辑起点是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有关人的感性解放问题,这也是80年代中国美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起点。与法兰克福学派美学不同的是,80年代中国美学坚持了马克思人的本质是实践的观念,并以此批评法兰克福学派将感性、爱欲本体化的倾向。
马克思在《手稿》中说:“人作为对象性的、感性的存在物,是一个受动的存在物……情欲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3](P122)马尔库塞认为,“这里所讲的感性是用以解释人的本质的一个本体论概念”[4](P111)。从对马克思《手稿》的人本主义解释出发,马尔库塞考察了感性一词在鲍姆加登、康德及席勒美学中的演化历史,他认为:从“埃斯特惕克”(Aesthetic)一词的发展历史看,它反映了对感性(因而对肉体的)认知过程的压抑对待。在康德那里,审美之维是一中介,它调和着感性与理性、实践理性与道德理性等多种心灵能力的二律背反。马尔库塞认为,康德仅仅把这些范畴当成心灵的过程去论述,而席勒则冲破了康德先验哲学构制的藩篱。在席勒美学中,借助于一种基本冲动,即游戏冲动,审美将废除理性的专制,把人引向自由之中。“自由应该到感性的解放中而不是理性中去寻找。”[5](P60)
在此,马尔库塞改造了弗洛伊德学说中有关文明发展与本能压抑的观点,并将弗洛伊德的性力比多扩展为爱欲。他认为,在理性压抑占统治地位的现实世界中,唯有艺术能够提供高度的力比多满足;在审美活动中,人们依据的是快乐原则而不是现实原则行事。这样,马尔库塞就以Eros(爱欲)取代了席勒的"Sinnlichkeit"(感性),并最终提出了“新感性”的概念。
在康德和席勒那里,审美活动虽然被置于中心地位,但它仍然是沟通纯粹理性与实践理性、调和感性冲动和形式冲动的中介。席勒认识到科技理性对人的生存状况的威胁,但他并不反对理性本身,席勒的理想仍然是理性与感性的统一和平衡;而马尔库塞则赋予审美感性以本体论、生存论的地位,以感性、爱欲冲动废黜理性。从席勒到马尔库塞的演进过程,标示着古典理性主义已逐渐衰落,而审美现代性思潮澎湃,其中的主题即是把审美感性本体化并导向审美主义。
在80年代中国美学中,以李泽厚为代表的一代美学家,既继承了康德、席勒对感性的重视,又反对马尔库塞将感性本体化的审美主义倾向。李泽厚将康德的主体性哲学与马克思的实践概念结合起来,提出了“美是自由的形式”说、“积淀说”。
在《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中,李泽厚试图抛弃康德——黑格尔——马克思的公式套用,而代之以康德——席勒——马克思的美学理路:“贯穿这条线索的是对感性的重视,不脱离感性的性能特征的塑形、陶铸和改造来谈感性与理性的统一。”[6](P414)在李泽厚美学思想中,对康德、席勒的钟情是与他对黑格尔历史总体性的批判联系在一起的。李泽厚对黑格尔的总体评价是:“历史总体的辩证法是黑格尔所长,个体、感性被淹灭于其中则是黑格尔所短。”[6](P408)试图重新拯救被黑格尔历史理性所淹灭的个体感性,正是李泽厚请出康德的主要原因。
但是,在对马克思《手稿》的具体解释中,李泽厚与法兰克福学派产生了分歧。李泽厚认为,马克思所说的人作为自然的、感性的存在物应该理解为具有具体的社会历史性质,通过漫长历史的社会实践,自然人化了,人的目的对象化了,“理性才能积淀在感性中,内容才能积淀在形式中,自然的形式才能成为自由的形式,这也就是美。”[6](P415)李泽厚用“积淀”一词取代了马尔库塞的“爱欲”,这样就将他对主体感性的强调与对马克思实践概念的坚持调和起来。
在后来的《美感谈》一文中,李泽厚明确提出了“新感性”的概念,并认为它与马尔库塞的“新感性”是完全不同的。李泽厚认为,他的“新感性”是理性与感性的统一,是社会、理性、历史的东西积淀为个体、感性、直观的东西,这是通过自然的人化过程实现的。而马尔库塞则从弗洛伊德主义出发,将感性泛性欲化,这恰恰是对《手稿》的一种误解。[7](P387)
凭心而论,李泽厚在80年代提出的“美是自由的形式”说、“积淀说”综合了康德与马克思的观点,在理论建构上是较为稳妥的。但是在80年代后期的自由主义美学风潮中,李泽厚的实践美学受到了挑战。在《选择的批判——与李泽厚对话》中,刘晓波批评李泽厚用“积淀”来规定美的本质是“面向过去的、保守的”。而真正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理论建构是潘知常的《生命美学》。在《生命美学》(1991)中,潘知常认为,实践美学在几个方面存在着重大失误,在研究对象上,注重“历史规律”“必然性”“本质”之类的字眼,而不关心生命的有限带来的不幸人生;在研究内容上,以对象世界为核心,忽视人内在的生命活动,如审美体验及人的生命意义的探寻。因而“美学必须以人类自身的生命活动作为自己的现代视界。”
在对以李泽厚为代表的实践美学的解构中,转型期中国美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以标举感性解放为旗帜的审美现代性取得了合法地位,如果说实践美学更强调人的类本质解放的社会历史过程,生命美学则注重个体感性生命的当下沉醉。随着市场经济转型与大众文化、消费文化的勃兴,人们淤积已久的感性能量得到了空前的释放,而理性则成了“受人嘲弄的过时玩意儿”。这样,在社会心理层面就极易导向贝尔所说的“及时行乐”倾向,人的感性生存论入世俗化的无深度的感官化日常生活。从北岛、顾城到崔健、王朔的流变过程,尤其是顾城之死与王朔现象,典型地表征了90年代的后现代症候:主体的死亡与乌托邦的幻灭。人们又开始寻找新的诗意栖居的家园。
二
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技术理性的统治导致了对感性、欲望的弃绝。在《启蒙辩证法》(1937)中,霍克海默、阿多诺提到了奥德修斯和塞壬妖女的神话。奥德修斯为了抵御塞壬妖女的诱惑,用蜡堵住了水手们的耳朵,让人将自己绑在桅杆上,这个神话实际上暗示了资产阶级社会控制的心理逻辑。根据这种逻辑,工人为了勤奋工作和增加工资,就不得不否定和升华他们的情感。这样,法兰克福学派对启蒙现代性的批判,就包含了对现代资本主义压抑人的感性欲望的批判,并将爱欲解放视为社会解放的潜在力量。
马尔库塞试图将马克思与弗洛伊德融合起来。与弗洛伊德不同的是,马尔库塞认为现实社会中的压抑主要表现为施行原则的额外压抑。另外,他认为,爱欲并不象弗洛伊德理解的那样,是一种反社会性力量,解放爱欲并不必然导致社会的混乱和文明的毁灭。在幸福观上,马尔库塞认为幸福应该建基于快乐原则之上,并将个人感觉的解放看成普遍解放的起点。在写于60年代末的《论解放》中,马尔库塞从嬉皮上运动和性革命浪潮中看到了他的“新感性”已成为政治实践,并断言美学将成为一门社会的政治科学:“审美对政治的入侵,表现在对丰裕的资本主义社会反抗的另一极上,即表现在不妥协的青年人身上。”“同样,还表现在抗议歌声中的爱欲挑战、披头士的长发给人的感受,以及通过形体卫生来使肉体洁净的做法”[8](Pll7)
在60年代末期席卷欧美的学生抗议运动中,法兰克福学派弗洛伊德的马克思主义成为学生的行动口号:“我越想谈恋爱,我就越要造反,因而我也越要谈恋爱。”[9](P50)西格尔的小说《爱情故事》即是以这场新情感运动为背景的。在小说的第一集中,主人公奥列弗对父亲的反抗,更多的是一种生物学意义上的反抗,近似于弗洛伊德所说的俄狄甫斯情结的泛化;而在第二集中则被纳入社会学范畴,成了儿子对资产阶级父亲的反抗。西格尔试图从文学角度触及60年代造反学生的哲学精神,那就是马尔库塞的弗洛伊德的马克思主义[10]。尤有意味的是小说结尾处儿子与父亲的和解,这种和解表明造反学生由对现实的叛逆走向了对现实的认同,60年代的文化激进主义已开始衰颓,保守主义正在回流。而站在文化保守主义立场上对60年代文化情绪的有效批判来自于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
在贝尔的名著《资本主义文化矛盾》(1976)中,贝尔用“六十年代文化情绪”指称以下内容:吸毒的幻觉、沉溺于性反常、热衷于暴力和残忍、反认知和反理智的情绪、抹煞艺术与生活的界限、熔艺术与政治于一炉等等。贝尔认为,60年代的文化激进主义运动“虽然打着攻击技术官僚社会的幌子,实则在于攻击理性本身”[11](P194)。现代主义文艺思潮把理性主义当作过时的玩意儿,追求审美距离的消蚀,重视充满本能冲动的梦境与幻觉。在宗教衰竭以后,人们企望从文学艺术中寻求刺激和意义以此顶替宗教的作用,然而现代主义也已衰竭。贝尔认为,“现代主义的真正问题是信仰问题。”[11](P74)为了重建信仰,恢复秩序,贝尔期望整个社会重新向某种宗教观念回归,“重新找回神圣意义的发掘”[11](P40)。
贝尔的保守观念遭到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传人哈贝马斯的批驳。1980年,哈贝马斯发表了《现代性:一项未竟工程》的重要论文。指出后现代主义瓦解了人的主体性,把传统意义上的“理性”抛诸脑后,哈贝马斯认为这种完全抛开理性的取向是不可取的,而正确的做法是按照启蒙现代性工程的原初设想,使科学、道德、艺术三个领域协调运转,从而达到对理性的重建,建立新的合理的交往理性。哈贝马斯对后现代主义贬低理性的批判,同时也是对审美中心主义的感性至上论的批判。哈贝马斯认为,审美乌托邦有一个致命的错误倾向,这就是把整个生活世界审美化,从而把现代性由工具理性主宰一切转变为审美感性主宰一切。
综观法兰克福学派从马尔库塞到哈贝马斯的演进过程,从一个侧面看,是从激进的爱欲解放——新感性走向对审美主义的批判,并重估理性的历史价值。国内有学者认为,哈贝马斯可能是保守的,但它重提康德、韦伯对知识领域的三大划分,试图限制审美主义的疆域,这对传统上就习惯走审美之路的中国人,不能不是一种警示[12](P225)。而在转型期中国美学中,对审美感性优先性的推崇与对审美主义的批判性考察几乎是共时性地展开的。
前已指出,在马尔库塞美学思想中,存有将感性本体化的审美主义倾向,并因此遭到李泽厚的批评,但90年代中国美学并未停下审美主义的脚步。在潘知常的生命美学建构中,对实践美学的超越不仅表现在他对实践本体的理性主义的批判之中,而且表现在他对西方生命美学的理论资源(尤其是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美学)与中国古典美学(如在禅美学、意境论等)的创造性互释上面。在审美乌托邦的建构上,生命美学更加注重个人有限生命的当下的安身立命,即海德格尔所说的“诗意的栖居”,或如中国古典美学中的“天地境界”。应该承认,个体感性生命的当下沉醉是审美体验的主要特征,因而生命美学将之作为审美活动的本体论内涵加以发掘,确实触及了实践美学的不足之处(即对实践活动与审美活动的区别照察不够)。但是,在漫长的人类历史进程中,审美活动从来就不是孤立存在的。人的审美感性先是受到宗教形而上学的束缚(在中国,则是受到儒家道统思想的压抑),继之在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技术理性统治对人的审美感性形成了巨大的威胁,因而审美就总是承担着解放的乌托邦功能。生命美学与其说是一种审美体验论,不如说是一种审美人生论。对有限人生、烦恼人生的解脱与超脱,将审美境界看成人生的最高境界是生命美学的真谛所在。
进而言之,以转瞬即逝的、飘忽的生命体验作为现代美学的本体论视界,极有可能导致哈贝马斯所批判的审美主义。在生命美学中,无论阿波罗的梦幻静观,亦或狄奥尼索斯的沉醉狂欢,诚如尼采所言,“只有作为审美现象,人世的生存才有充足理由”[13](P275)。在倭铿看来,这种宣扬超越于社会环境之上的“审美个体主义”,由于把一种纯然表面化的“心境的生命”看成是真正的现实存在,并不比某种幻象真实多少[14](P195)。其次,倭铿认为,审美个体主义体系中感官体验的强烈会导致精神的退化,“这对于反对一种粗俗的愉快的闯入是无济于事的”[14](P201)。弗洛伊德也说,“有些障碍对于使力必多进入高潮是必不可少的”[15]。在生命美学服膺的本能、爱欲冲动中,力必多的无原则释放会导致生命的疲软与苍白。
诚如马尔库塞最终以“爱欲”(Eros)取代席勒的感性一样,在转型期中国的文学、艺术、影视领域,从宣扬感性解放到以身体、爱欲取代感性,弥漫着浓厚的弗洛伊德主义色彩。即以小说而言,如果说张贤亮的《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还站在马克思的立场上渗透了弗洛伊德主义的因素(它描绘了人的生物性本能受到压抑之后的返祖现象),在王安忆的“三恋”(《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绣谷之恋》)中则抹去了“性”背后的社会历史内涵。此后,对身体的迷恋已使传统意义上的感性解放成为了一具空壳。葛红兵在《非激情时代的暖昧意象——晚生代小说的主题》中认为,“身体”是晚生代小说的重要主题,晚生代作家表现出对身体的强烈的自恋倾向。
在杰姆逊看来,弗洛伊德主义无论如何还是一种深度模式。而在身体崇拜中,本我、自我、超我的深度模式被平面化了。在后现代主义的复制文化中,人的身体只不过是一种抽象的符号。刘小枫认为,审美感性的在体论基础是身体。他以时装表演为例说明了审美主义带来的价值虚无和幻灭感:在身体的扭行中,人身的意义和目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的身体在此世的舞台上行走过[16](P332)。这种对20世纪末的审美主义趋向的现象学把握大致是准确的。重要的是,这种价值虚无和幻灭感与世纪末流行的“本世论”、“千禧年主义”相结合,会进一步否定科学理性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卡尔·曼海姆认为,乌托邦思想总是与人们无法实现的愿望满足联系在一起的。千禧年主义作为乌托邦思想的早期形态正是人们的愿望满足通过投射于时间来进行的。然而,对于千禧年主义者来说,他并不关心将要到来的千禧年,“对他来说,重要的只是太平盛世的千禧年在此时此地发生。”[17](P221)因而对他们来说,“感官体验总是表现得极为强烈”。曼海姆引用中世纪神秘主义者埃克哈特的话说:“如果灵魂要领悟上帝,它必须超越时空。”“进入对自身和自己行动的否定,它便是通过了皈依……”[17](P220)这样,对乌托邦千禧年的狂热体验使人们放弃了科学理性,并最终导致了对自身生命与身体的毁弃。
正是在世纪末弥漫的虚无主义与乌托邦焦虑的氛围中,与哈贝马斯对欧洲泛审美主义的批判并试图重估理性的价值相呼应,转型期中国美学也开始重新确立理性的历史地位。钱中文从文学理论的角度明确提出重建“新理性精神”的口号。韩德信则从审美文化角度考察了“理性”的历史进程,并试图确立它在当代审美文化中的地位。他认为,西方忽视或否认“理性”,只强调感性的非理性主义审美文化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如果我们把追求感官刺激、个人情感的无限制渲泄、否认“理性”的作用等作为审美文化的主要特点的话,这势必影响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18]。这显然是看到了自尼采、弗洛伊德以来对“理性的激进批判”(哈贝马斯语)所致的虚无主义和信仰危机的负面影响。
从法兰克福学派和转型期中国美学对审美现代性的反思中,我们可以发现审美现代性的内在矛盾主要表现为感性与理性、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之间的矛盾。如果说法兰克福学派设定的感性与理性、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之间的张力结构源于康德、韦伯关于“三大划分”(科学、伦理、艺术)的现代知识模式,审美在其中起到中介与桥梁的作用;那么,当它面对现代社会中的工具理性与技术理性压抑时,便不能不将审美个体感性的作用推至极端,从而忽略了审美的多元价值取向,也偏离了康德、韦伯关于现代性工程的原初设计。因而,哈贝马斯对现代性未完成的坚持,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法兰克福学派审美中心主义的纠正,也是对转型期中国美学现代性的提示。
收稿日期:2000-12-28
标签:法兰克福学派论文; 现代性论文; 哈贝马斯论文; 理性与感性论文; 美学论文; 西方美学论文; 本体论论文; 乌托邦主义论文; 文化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康德论文; 李泽厚论文; 弗洛伊德论文; 席勒论文; 形而上学论文; 哲学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