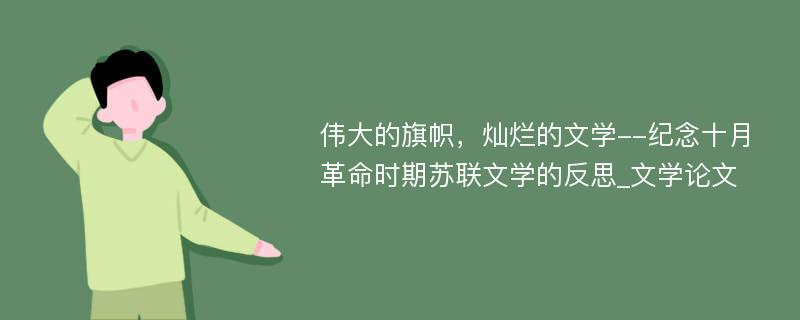
伟大的旗帜,光辉的文学——纪念十月革命 反思苏联文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联论文,文学论文,旗帜论文,光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十月革命80周年来临之际,心里百感交集。目前,在有些人的心目中,苏联已经解体了,还谈什么纪念十月革命呢?似乎十月革命不仅已经褪色,而且根本不屑一提了。我倒依然认为,十月革命这面旗帜是光辉的、伟大的,它所开创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是一条阳关大道,也许方式不同,但全人类迟早是要走上这条大道的。
苏联文学是在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烈火中产生的,它跨着赤卫队员“强有力的步伐”向全世界宣告了自己的诞生。新型的苏联文学以其特有的光华闪耀于全世界整整70年,即便是苏联解体以后,它的光华也没有减色。这是因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变革,它的夺目光辉是永远不会熄灭的。它不仅使俄罗斯人民彻底摆脱了沙皇专制的农奴主义统治,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而且影响了20世纪整个人类生活的进程。它在俄国文化史上也开始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十月革命是一次推翻剥削阶级私有制度的改天换地的革命,它不能不触及、震撼包括知识分子、作家在内的每一个人的灵魂。革命后,俄国的所有作家都必须首先在政治上作出抉择。作家队伍的分化是不可避免的。除在革命前就站在无产阶级一边的高尔基、绥拉菲莫维奇、别德内等作家外,文艺界当时率先站出来拥护、支持革命的是勃洛克、勃留索夫、叶赛宁、马雅可夫斯基等诗人。勃洛克在十月革命刚开始就写出了颂扬革命的长诗《十二个》,并号召人民“用整个身躯、整个心灵、全部意识去倾听革命”。勃留索夫说,“1917年的大变革,对我个人来说是最深刻的变革。”叶赛宁也说,“在革命的年代里我完全站在十月革命的一边”。他欢呼“革命万岁!”马雅可夫斯基更是把十月革命称作是“自己的革命”他要用“头号大嗓门鼓动家”的最强音歌唱革命,赞颂“人类的春天”。随着新的作家队伍的成长,苏联文艺界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呕歌革命的重要文学作品,如富尔曼诺夫的《恰巴耶夫》、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革拉特科夫的《水泥》、法捷耶夫的《毁灭》、马雅可夫斯基的长诗《列宁》和《好!》以及高尔基、阿·托尔斯泰、肖洛霍夫的一批革命史诗作品,如《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苦难的历程》、《静静的顿河》的最初篇章。它们颂扬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塑造了全新的社会主义的新人形象。
但是,与此同时,也有一批作家对十月革命始终坚持反对,甚至诅咒、辱骂的态度。季纳伊达·吉皮乌斯早在1917年10月24日的日记中就写道:“一句话,‘社会革命’即将发生,这是有史以来的一场最黑暗、最愚蠢、最肮脏的革命。需要随时恭候它。”革命后,1919年在《无词歌》一诗中,更是凶相毕露:
在这些狂人的身上,
该死的标志明显确凿,
但我们惩处他们时,
却不必过分张扬,
不需复仇的呼唤,
和欢天喜地的叫嚷,
准备好绳索,
在无声中把他们送上刑场。
这首诗充分表达了女诗人对俄国革命者,对布尔什维克的满腔仇恨和强烈的复仇心理。不仅如此,她还身体力行。在内战时期,她为白卫军写了许多行军歌、诗体传单、流行歌谣,公开号召反革命力量团结在白军的旗帜下,击溃和消灭红军。
吉皮乌斯的丈夫梅列日科夫斯基也是从一开始就极端仇视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新政权,希望外国干涉军打败布尔什维克,拯救他们。流亡国外后,他仍旧与世界上最反动最黑暗的势力沆瀣一气,投靠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并在巴黎电台发表广播演说,希望希特勒打败苏联红军。
俄罗斯作家中激烈反对十月革命的还有布宁、什梅廖夫、雅勃洛诺夫斯基、契里科夫、阿尔志跋绥夫、艾亨瓦尔德等。布宁本来与高尔基的关系是不错的。1917年十月革命期间,他却单方面与高尔基决裂了。他写道:“高尔基依照德国人的教鞭把俄罗斯引向了如此的灾难,怎么能原谅他呢?他直到现在还和布尔什维克在一起。不,这不行,不能饶恕他。”他甚至宣布,如果他遇见高尔基的话,“手里有什么就用什么朝他的脑袋打过去”。〔1〕其实, 高尔基在十月革命期间在许多方面都同布尔什维克和列宁有分歧。布宁对高尔基的愤恨是直接冲十月革命而发的。后来他在《该诅咒的日子》一书中也尽情地发泄了他对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的怨气和怒气。尽管布宁反对十月革命,但他至少还是爱国的,而且还是一位有才华的现实主义作家,特别是革命前他写了不少优秀的小说,如《乡村》、《从旧金山来的先生》等。不论在人品上还是在艺术成就方面,他同梅列日科夫斯基等人还是有区别的。
否定、反对十月革命,诋毁列宁主义等的文学作品在后来作为“回归文学”出版的还有: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格罗斯曼的《一切都是流动的》、田德里亚科夫的《革命,革命,革命》、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等。
现在大家都在热烈讨论重写俄苏文学史的问题。我想到的是,首先不能忘记苏联文学是十月革命所诞生的。离开这一其赖于产生、赖于生存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去谈论苏联文学,乃近乎妄说。有人说,苏联文学中的“苏联”已“不是政治概念”,而是一个“历史地理与文化的概念”。我认为恰恰相反,它首先是一个国家概念和政治概念。如若我们把上述吉皮乌斯、梅列日科夫斯基,乃至布宁等侨民作家也纳入苏联文学这个框子(概念)里去,那是不可思议的,不仅苏联方面不允许,就是这些作家本人也决不会答应。但是,若用“20世纪俄罗斯文学”这个术语,情况则不一样。这个概念倒可以说是一种历史、地理和文化概念,它既可以包括十月革命后的整个苏联文学,也可以包括侨民文学,以及十月革命前一段时期的所谓“白银时代”文学和苏联解体以后最近几年的文学。因此我们应当梳理一下目前使用的某些混乱的概念。比如,有人把目前很流行的所谓“俄罗斯文学大厦的三大基石”,即“显流文学,潜流文学和侨民文学”,说成“都是苏联时期所特有的”。这显然也是不合适的。因为,如前所说,侨民文学不应归在苏联文学这个范围里。顺便还要提及的一点是,拿诺贝尔奖金来作为衡量苏联文学及其作家作品的重要性的标准,恐怕也是大大值得商榷的。
在“20世纪俄语文学笔谈”中,有人提出“以文学为本位的取向”来架构俄罗斯文学史的新方案。它受到颇多人的赞赏。具体说就是“以文学语言为本体,以诗学品格为中心,以文化精神为指归”,强调要从语义分析、形式批评和文化研究等纯文学的角度来研究、撰写俄苏文学史。有支持者说,在目前中国俄语文学研究界,“谈文学尤如谈政治的现象”还存在的情况下,很有必要大声疾呼一番“文学本位观”。我倒觉得,在目前,谈论俄苏文学研究及其文学史时,如果不注意它的社会政治历史特点,只去说“以文学为本位的取向”,倒着实是对俄苏文学的不了解。回眸历史,苏联文学中,哪一桩重大的文学事件,哪一部重要文学作品的争论,不是和复杂的社会政治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呢?不论是过去和现在,不论是国内和国外,不论是苏联文学的拥护者和反对者,有那一个研究者、评说者不是首先从其社会政治方面着眼的呢?迄今为止,海内外有没有一部从纯文学角度去论述、去撰写的文学史著作呢?关于这个问题,连西方学者也曾十分肯定地说:“鼓励人们从纯文学角度讨论苏联作品,现在还为时过早。对一些新作品所引起的异常激烈的争论,都是其社会、政治和哲学方面的内容而展开,而还不是从文学的角度出发的。”〔2〕
在文学史分期问题上,也有类似的情况。有位论者说,“信奉庸俗社会学的研究者们每每以政治斗争的分期标准来切割文学史进程乃至作家的创作道路,把艺术理解为政治附庸……我们当然不可步其后尘。”但发人深思的是,这位论者在提出其新的分期方案时,恰恰又步了自己所反对的“庸俗社会学”的后尘。所提出的“变迁时代”、“解冻时代”、“停滞时代”、“改革时代”、“解体时代”等都是道道地地的苏联各个时期的政治历史阶段的概念,而不是文学自身发展的概念。这就再次说明,苏联文学与苏联社会政治生活结合之十分密切。过去有些学者从政治历史方面去划分苏联文学史的时期,是有一定的客观理由的,决不是简单地扣上一顶庸俗社会学的帽子就能解决问题的。这里,我完全不是主张按原来的那种政治历史的分期原则,我只是想强调一下问题的复杂性和困难性。它要求我们作更认真的研究,有更严肃而科学的态度。诚然,十月革命以来已经过去80个年头了,特别是今天,苏联的实体也已不存在了。因此有些过去敏感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的变迁,是可以淡化一些了。但是,作为史实,有些东西却是不能淡化的。我们今天修史,首先必须尊重历史。
我想强调的还是那一个思想:苏联文学是一种具有特殊性质的特殊类型的文学,它与十月革命及苏维埃政权有着超乎寻常的血肉关系。十月革命和新政权是在世界资本主义的包围与攻击之下产生和成立起来的,它要建立的又是与人类历史上一切剥削制度截然不同的社会主义社会。这样的历史环境和严酷现实,构成了这个社会的严峻而悲壮的特点。同时它的一切工作都带有试验性质。在无经验可循的情况下,某些风险和错误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在这样的一个社会中,有新生儿也有血污,有成就也有错误,有欢乐也有悲愁,有喜剧也有悲剧。这就是苏联的社会现实,也是苏联文学史的现实。避开这一活脱脱的现实去侈谈“纯文学”,就等于天方夜谭。
在分析、评价苏联文学作品的文章和著作中,有些观点也是不能苟同的。有人说,“很难说在表现革命的作品中,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恰巴耶夫》,还是《日瓦戈医生》更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
十月革命在列宁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在俄国广大工农群众艰苦卓绝、流血牺牲的共同奋斗下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接着苏联人民又以忘我的精神和顽强的劳动,真心实意地建设社会主义。尽管付出了代价,经受了挫折和痛苦,却无疑地建成了世界上第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后来又粉碎了希特勒德国的疯狂进攻,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这一切是不是时代的历史真实呢?抑或这不过是一种“先验的观念”?到底是《母亲》、《恰巴耶夫》、《铁流》、《毁灭》、《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表现了那个时代的真实、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精神,还是《日瓦戈医生》“更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呢?
我们并不把《日瓦戈医生》看作如洪水猛兽式的作品,也不把它的主人公看作是一个自觉的反革命(他不过是一个艺术形象)。但是,作品从反对一切暴力的抽象人道主义出发,通过主人公一系列的言论和遭遇,过分地渲染了十月革命的负面和挫折,散播了对十月革命的怀疑和厌恶情绪。这却是事实。诚然,像日瓦戈这样的知识分子(出身贵族豪门,受过旧俄上流社会的教育和基督福音的熏陶),类似他的思想情绪,在当时的革命现实中是存在的,但他们的这种社会心态和作品中表现的某些现象决不能代表该时代的主流。这类题材的作品也是可以写的,关键是如何写。高尔基的《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在某些方面与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有相似的地方:同是写旧知识分子的主题,也都写了两次革命,而且两部作品的主角都不是正面的时代英雄。然而两部作品的最大区别在于,高尔基是站在批判、揭露的立场上描写他的主人公的,而帕斯捷尔纳克却对自己的主人公满怀同情,甚至肯定。正是这一根本性区别,决定了两部作品的不同思想倾向。这里,归根到底是作家的立足点问题。
批评家,文学史家也有一个立足点问题。现在苏联解体了。如果由此便得出“十月革命是不合时宜的、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完全是错误的”——这样一个“先验的”结论的话,那么,你当然就会认为只有像《日瓦戈医生》这样的作品才“更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所谓见仁见智,盖由于立足点的不同,文学观念的不同,价值取向的不同。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不一样,超阶级、超现实的所谓第三者的超然立场是不存在的。诚如鲁迅先生所说,“要做这样的人,恰如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
应当承认,在过去的苏联文学史籍中,确实存在不少弊端。由于政治色彩过重,观点偏狭,不少作家,特别是一些现代派作家和持不同政见的作家,受到了过分的贬抑。这是客观事实。因此站在今天的高度,重新审视俄苏文学史是必要的,关键的问题是依据什么原则来治史。我们决不能以偏纠偏,用片面性去反对片面性,而是必须采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
注释:
〔1〕转引自奥夫恰连科《革命与文学》一文, 《莫斯科》1987年第11期。
〔2〕见《西方论苏联当代文学》第2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
标签:文学论文; 十月革命论文; 高尔基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文化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艺术论文; 日瓦戈医生论文; 读书论文; 作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