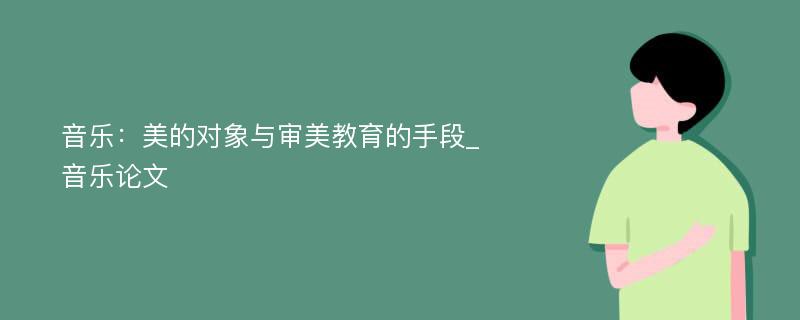
音乐:作为美的对象和作为美育的手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育论文,手段论文,对象论文,音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本文认为,要音乐真正美并发挥其美育作用,就不能满足于音乐的直觉美,更不能把音乐作为一种单纯的娱乐手段,而应该重视音乐的理性内蕴,努力使音乐形象包蕴的情绪情感闪烁着美好社会人生理想的光辉。要反对蚀心丧志、令人心性浮动狂乱不仁的音乐,善于区分思想情感尚属健康的缠绵悱恻的音乐和“靡靡之音”以及昂奋向上的强烈音乐与“嘈杂音乐”的不同,让音乐成为使人性自由和谐地趋向于完美的“桥”。
关键词 音乐美 直觉美 理性内蕴 人性
音乐,作为美的对象,是人的本质力量特别是人的情绪情感的直接显示。它虽然不象雕塑、绘画等造型艺术那样具有形象直接性,但它毕竟是靠人的耳朵这一仅次于眼睛的感官来把握的,所以它的美又仍然具有强烈的个人直觉性。一般地说,凡是通过旋律、节奏、和声以及复调、配器、曲式等音乐语言来显示出人们优美或崇高的思想、情感、趣味、理想,表现人们高尚的精神情操和智慧、勇敢、才能,能确证和肯定人的积极本质力量的,这音乐就是美的。凡是美的音乐,都体现着一种对于人的富有情感性的精神价值关系。它一方面表现为以富有个性的音乐语言愉悦人的听觉感官,同时又表现为以它与生活的某种对应性诱人想象和联想,使人在思想上得到某种启迪,在道德情操上得到某种陶冶,在情绪情感上得到某种宣泄,使人的内心世界更加充实、丰富和完善。惟其如此,优秀的音乐家都非常重视把健康的情绪情感和高尚的理想情操的抒写和表现作为音乐美的生命内核。其中,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代表。
大家知道,贝多芬是从1817年开始这部交响乐的创作的,到1824年春才完成。可是,从1816年起,贝多芬的耳朵就几乎全聋了。(从这年起,他开始用谈话手册与人交谈)而且,从这年起,他接连患重伤风、(医生说他得的是肺病)重关节炎、黄热病、结膜炎,在肉体上经受着巨大的痛苦。于此同时,在精神上,他也经受着巨大的磨难:一是经济上的拮据,(作品卖不出去,对出版商负着重债)使他日夜为金钱的烦虑而弄得疲惫不堪;二是侄子过继给他后,弟媳不断与他打官司,侄子又不听从他关于做“一个于国家有益的公民”的教导,不愿读书,硬要从商,还出入赌场,负了不少债;三是维也纳的音乐口味变了,莫扎特和他的音乐都被认为是“老学究”的东西,他的歌剧《费德里奥》甚至被看成一堆垃圾,而意大利音乐特别是罗西尼的歌剧却风行于时;四是拿破仑的弟弟乘人之危,企图用重金聘他去当宫廷乐官。然而,他却战胜了这一切从肉体到精神的痛苦和折磨,坚持把《第九交响曲》的创作进行到底,并终于将他踌躇了一生的把歌颂欢乐作为一个大作品的结局的构思写进了这个交响曲。整个乐曲不仅有欢乐的主题,讴歌了欢乐之美,而且使人感受到了生命的力量怎样征服了痛苦与哀伤,感受到了作者的顽强意志和坚定的信念,感受到了他那崇高的爱国精神和作为一个人所具备的伟大道德品格。从形式上看,这个交响曲也有重大的突破性建树。因为按照传统的交响乐作法,要在曲中引进合唱,有着巨大的技术上的困难。可是,由于他采用了先把欢乐主题给乐器奏出,然后忽然中止乐队的演奏,出乎意料的静默,接着才出现人声的写法;在旋律的运行上,先由低音表现出一种严肃而受压迫的情调,然后出现“摇篮曲”的音调,慢慢地让欢乐抓住“生命”,表现欢乐对痛苦的征服,接着是进行曲节奏,男高音热烈急促的歌,以及斗争后的欢乐的呼喊;再用赞美诗的音调表现对天空王国、思想王国的神往与沉醉,用以表明进入了一个极乐世界,等等。这一切又使人感到他确实象罗曼·罗兰所说的,是“音乐家中的第一人”,具有“近代艺术最英勇的力”。正因为这样,当这首交响曲1824年5月7日在维也纳首次公演的时候,竟出现了空前的轰动:贝多芬出场时,观众五次鼓掌欢呼;演出一结束,观众又再三欢呼喝彩,许多人甚至激动得哭了起来;当耳聋的贝多芬由女高音演员牵着手从指挥台上转身面向观众,看到全场起立的观众正在挥舞着帽子、鼓着掌向他欢呼致意的狂热、骚动的场面时,他也感动得晕了过去。在这里,音乐的直觉简直达到了一种极致。
不过,这种音乐直觉美的极致,又是建立在由经验积淀、升华并潜伏下来的理性意识之基础上的。然而,有的音乐作家和音乐表演家对此却缺乏应有的理解,以为音乐既然是音乐家的情绪情感的直接表现,它的美就必然百分之百是靠个人听觉感官把握的,以为听觉的愉悦就是个人听觉上的热闹和舒适,或者是经过个人听觉感官的快适而达到的个人心性的放纵和平衡。于是,描述和抒写个人狭隘的生活感受,甚至放纵对性爱以至整个人生的迷惘、狂放或玩世不恭的吟咏歌唱,便一度充斥市场,成为令人心性迷乱飘忽,甚至令人感到气闷窒息,令人对世界对人生感到无可奈何的一张“音乐网”,成为诱人及时行乐的催魂剂。很显然,这种对音乐美的片面理解所导致的音乐美的迷失,实际上是夸大音乐美的个人直觉性而忽略了音乐美的理性内蕴的结果。
其实,音乐美除了具有个人感官直觉性以外,它还具有一种超越个人听觉感官和听觉经验的社会属性。因为音乐毕竟是一种特殊的声音运动,或者说是一种情感与思想相统一的乐音运动。音乐诉诸人们的听觉,主要不是为了通过音强、音高、音色来比拟个人曾经经验过的因运动而发出类似声音的事物的形象,从而制造一种属于个人的听觉画面,而是要通过富于个性的旋律、节奏、和声等传达和表现个人对生活的感受,并以此暗示或象征一种社会性的心理情感经验,唤起听众产生相应的情绪情感体验,使他们对一定的生活产生一种既带有强烈的个人主观感受又趋向于与社会规范相一致的审美评价。很明显,在这个意义上,音乐美既是感官直觉的,又是理性抽象的,既是个人的,又是社会的。事实上也只能是这样。因为作为参与音乐形象美创造的音乐作家和音乐表演家,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动物,而是“类的存在物”,“社会的存在物”,是处在非常具体而且常常又在流动变化着的复杂社会关系中的人,他们个人的情绪情感,既建立在个人的生活感受和生活经验的基础上,又受到特定社会关系制约下所形成的文化氛围、物质利害感、精神利害感和道德规范、价值观念的影响,受到社会生活实践前进要求的制约。因此,无论是音乐作家,还是音乐表演家,他们由生活感受引发的乐思,就决不可能是纯个人的东西,他们观念中流动变幻的乐音系列及其引起的想象和联想,也决不只是有关自然事物或社会生活事物的自然属性的东西,而是一种带有社会属性、社会意义的既具体又抽象的东西。所以,对于第一度参与音乐形象创造的音乐作家特别是对于第二度参与音乐形象创造的音乐表演家来说,心理情感经验的传达和表现,就要特别注意个人听觉的感官直觉性与有关社会生活的既具象又抽象的想象联想之间的统一。惟其如此,要使音乐真正成为一种美的对象,无论是音乐的旋律、节奏、和声等等的建构,还是表演者的具体传达表现,就都必须接受社会的正确健康向上的人生观、道德观和价值观的指导和规范,努力使音乐形象所包蕴的情绪情感闪烁着美好的社会人生理想的光辉,这样,才不致于对听众的生活联想产生误导。在这方面,古曲《和尚思妻》的创作与演奏,对我们是颇有启发的。
按照常理与常情,相思是苦涩的,单相思则尤甚。然而,古曲《和尚思妻》却写得很甜,很欢乐。表现思妻的题旨,用缠绵的甚至涩滞的旋律行不行呢?当然可以,但弄不好会让人更强烈地感受到单相思的苦痛。那样,就会导致两种不理想的审美效应:一是陷入迷惘,趋向沮丧和颓废;一是堕入“悟空”,无异于鼓吹遁世,诱使人们逃避现实,死心塌地当和尚。既然如此,又何必思妻?而思妻既属多余,这首古曲的题旨也就难以具备美的意义。大概就是出于对这种负面审美效应的避忌,这首古曲写“和尚思妻”就特意写出相思的甜和乐。这首古曲之所以美,就美在这一点上。再加上在演奏上,它遵循中国的传统音乐美学思想,“以和为贵”,通过高音潮州短笛和扬琴以及潮州高音胡琴等乐器,用轻松明快的旋律和节奏,反复奏出南方民间婚嫁中常可听到的“八音”音调(与广西玉林地区的“八音”中的《白鹤游》极为相似),渲染一种和谐欢乐的气氛。这样一来,这首古曲就成了对人们在婚嫁中曾经体验过的那种“淑女贤妻,其良夜何”的甜密幸福欢乐的思想感情的一种形象的确证和肯定(使人们重新体验)。因为这是对人的类本质而不是对已经异化了的人——和尚的本质的确证和肯定,所以,它就具有巨大而普遍的美的感染力。试设想一下,假若这首古曲传达和表现的不是带有普遍性的情绪情感即人们向往和谐自由幸福生活的情绪情感,不是人的积极的本质力量,而是象现代酒吧中某些爱得死去活来的如泣如噎的歌曲那样,它再独特,再富有个人感官直觉性,又有多大美的意义呢?
音乐作为一种美育手段,我们觉得,席勒关于美育就是为了“人性的完美实现”的格言,是很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他认为,“通过美,人们才可以达到自由”,因为美可以召唤人们“避免规律和需要的强制”,使人性自由地趋向于完美。[①]但是,由于音乐美育涉及表演艺术的特性,涉及音乐美的三度创造,问题又比较复杂,并不是只要有了音乐作品和音乐表演,音乐美育就会万事大吉了。美国的L.P.维赛尔在他的《席勒与马克思关于活的形象的美学》中说得好:“生活或感性需要是人的受动性的一种反映,也就是说,为了维持他的现实生活和他对经验对象的依赖。当人在其贪婪的粗陋形态中被感性需要所支配时(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他会发觉自己与类本身、与他的活动和创造力相异化。……在一种粗陋的物质或感官需要的状态中,人被剥夺了他的‘神性倾向’,(按:此处指席勒说的‘神性倾向’,即人的形式本能)他的类的普遍性。……其感性生活异化了的人仅仅被连续不断的物质需要所束缚。他等同于原始的自然界。”在考虑音乐作为一种美育手段时,让音乐给人们提供什么,维赛尔这段话是不能不深而思之的。当然,音乐本身并不能给人们提供任何物质的感性需要的东西例如面包奶酪之类,但它却可以给我们的心灵提供如同上述物质感性需要的东西所引起的感觉、情绪、情感甚至思想和观念。因此,在这个意义上,音乐既可以使人颓废堕落,也可以使人“超脱愚人社会而得到净化”。(司汤达语)正是有鉴于上述名言和可能存在的事实,要使音乐成为一种真正的美育手段,就不能停留在满足人的粗陋的感性需要之上,而必须使音乐提升到满足人的高尚精神需要的高度,使人的“神性倾向”、人的类的普遍性,在新的历史高度得到复归。我们在前面强调音乐美必须超越个人感官直觉性而蕴含社会的理性内容,也正是出于这种提高人们心灵的考虑。
当然,要使音乐成为一种真正的美育手段,音乐本身必须美。而美是包含着真和善的。换言之,音乐不仅必须反映客观现实生活的面貌的真,更必须反映客观现实生活的内在的真即生活的本质、规律、发展趋向;同时,它还必须反映作为生活实践主体的人(包括音乐作家、音乐表演家和音乐听众)的个人与社会相统一的功利需要,反映他们对至善至美的人和人的生活境界的追求。当然,音乐作为一种美育手段,它的表现,还有赖于音乐家对生活的感受、体验和传达,有赖于音乐听众的再感受和再体验。而感受,又总是表现为主体对于对象的感性面貌和本质特征的富于个性的认同、共感和净化,它既不是单向的摄取,更不是自我的膨胀和扩张。因为,正如我们前面强调过的,任何主体的个性都是要受到特定的社会关系特别是社会物质利害关系和社会精神利害关系,以及社会生活实践的前进要求这些属于真或善的因素的制约影响的。还是席勒说得好,感官对普遍性的感知构成审美体验的本质。因此,无论是音乐作家对生活的感受,体验和传达,还是音乐表演家对音乐作品及其相对应的生活的感受、体验和传达,抑或是音乐听众对音乐作品本身以及对表演艺术家的传达表演和与之相对应的生活情感的感受和体验,都只有上升到对普遍性的真和善的感知,使其获得一种深刻而普遍的社会理性内容,音乐的审美本质才真正被把握住了。这时,只有这时,音乐才不再是一种单纯的娱乐手段或仅仅供人把玩的工具,才能成为寓真、善于一体的真正的美育手段。台湾中华音乐文化教育基金会董事长陈功雄教授力倡“纯正的音乐”,力主音乐应“对人格具有建设性”,反对“粗俗的、趣味低级的‘靡靡之音’”和“嘈杂的、超大音量的‘热门音乐’”,反对音乐使人“蚀心丧志”或使人“心性浮动、狂乱不仁”,[②]正是从审美体验本质的高度对作为美育手段的音乐的一种现实要求,是值得音乐同道同好深思深省的。自然,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采取谨慎的态度,要善于区分思想情感尚属健康的缠绵悱恻的音乐和“靡靡之音”的不同,区分昂奋向上的强烈音乐与“嘈杂音乐”的差别。美的音乐并不排斥缠绵悱恻的风格或印象强烈的风格;阴柔与阳刚,优美与崇高,悲剧性与喜剧性,甚至喜剧中的滑稽,在音乐的创作和表演中自然也应有它们各自的位置。问题是,不能把缠绵悱恻的界限“缩小到小市民式的狭隘性或千篇一律的感伤性”;不能把强烈的音乐印象等同于“反艺术的印象”,因为听到“一群狗在撕裂自己的牺牲品,所产生的印象是强烈的,但也是不愉快的”[③]在这里,关键还在于真、善、美是否统一,能否提高人们的心灵。
总之,音乐不应该是束缚甚至扭曲人性的“网”,而应是引导人们向真、向善,使人性得以自由和谐地趋向于完美的“桥”。这就是我们对音乐作为美的对象和美育手段的基本看法。
当然,音乐作为美的对象和作为美育手段的实现也有着自身的难度。这主要是因为它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问题,而是复杂的实践问题。再加上诉诸听众听觉的音乐形象是一种经过音乐作家和音乐表演家两度创造的产物,它所具有的非个人感官直觉性常常表现为某些模糊的不确定的东西,而作为参与音乐形象第三度创造的听众,要获得充分的美的享受,往往又要通过想象和联想来寻找乐音的流动变幻与生活之间的通路,由音乐的内部“对位”转向与外部世界的“对位”,把模糊不确定的东西变得相对地明晰和确定。这种音乐形象再创造特性,不但使它可以这样或那样地和个人或社会的过去的经验图式相联系,而且,当人们的记忆痕迹一旦被音乐的语言描述激活起来,在丰富自由的想象与联想的作用下,原来模糊的略图就会变成这样或那样的具体生动的表象。如果这些表象是跟音乐欣赏者的错误经验图式相联系的,那么,音乐的美育作用就有被消解的危险。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音乐作为一种美的对象和美育手段的实现,又还有赖于对音乐听众的“音乐耳朵”的训练和培养。因限于篇幅,这个问题只好留待以后探讨了。
注释:
①参见席勒的《美育书简》。
②参见陈功雄教授主编的《主人翁之歌·主编的话》。
③参见《世界艺术与美学》第2辑《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创作札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