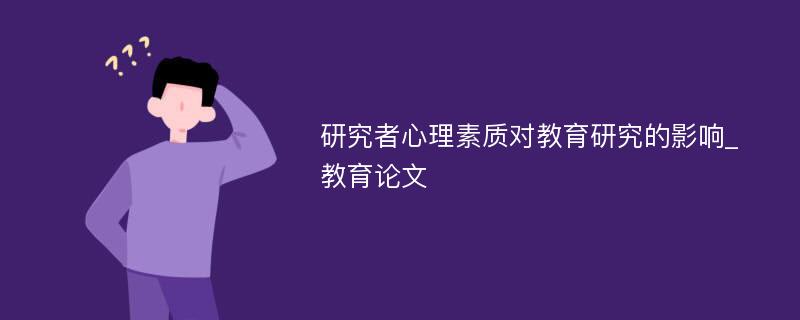
研究者的心理素养对教育研究之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研究者论文,素养论文,心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比较而言,身体素养、文化素养和道德素养对于不同国别的教育研究者而言不可能有太大的差距,而心理素养则会因社会环境的不同、传统文化的制约和民族特性的影响出现整体上的差异。本文无意对心理素养进行全方位的探讨,仅就一些较为重要而又常易为人忽视的心理因素对教育研究的影响作一些具体的分析。
一、研究者的思维方式对教育研究的影响
思维方式对于科学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教育研究的方向和水平,并最终制约着教育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我国的教育研究者在这方面存在一些误区。
其一是“中庸之道”和“调和主义”。也许是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制约,在教育研究领域经常出现形似“全面、辩证”而实为“中庸、调和”的现象。如关于教育目的的“个人本位论”和“社会本位论”,一般都认为只有将个人需要和社会要求统一起来才较为全面、合理。至于二者怎样统一、在什么条件下才能统一、统一到什么程度较好、最终能否实现完美的统一,则关心甚少,似乎深入的探讨和具体的研究与己无关。又如对于“教学规律”的表述和研究,有人认为单方面的表述不太科学,只有从联系、统一的角度界定才较为妥当,于是“简约性规律”变成了“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相统一”,“发展性规律”变成了“传授知识与发展能力相统一”,“教学的教育性规律”变成了“知识教育与思想教育相统一”等。这种“统一”的状况究竟是教学本来如此或客观如此,抑或不过只是一种主观的猜测和人为的要求则未加深究。表面看起来是全面了、辩证了,但结果却是主观和客观相混淆,“规律”和“原则”分不清。还有“形式教育”和“实质教育”、“教师中心”和“儿童中心”、“集体教学”和“个别教学”、“学科课程”和“活动课程”等方面的研究也存在类似的现象。这使得教育研究只是停留于感性的探讨和经验认识,达不到对事物深层的、本质的把握,既对实践无益,又于理论无补,做的只是“拼凑”、“嫁接”的工作。因此,教育研究者要敢于突破,敢于创新,甚至敢于偏激,非如此不能达到认识的极致!同时,也才可能产生影响和引发争鸣,促使更多人去思考、去探索,从而达到规律性和真理性的认识。倘磨棱去角、八面玲珑、左右逢源,其理论也就不成其为理论了,还有什么价值可言?教育理论的突破亦无望矣!因此,“中庸之道”和“调和主义”实是教育研究之大敌!
其二为“非此即彼”和“矫枉过正”。具体表现为“一好俱好、一错皆错”,要么全面地肯定,“爱屋及乌”、“为尊者讳”,要么全面地否定,“泼洗澡水时连孩子也一起泼掉”。如讲“教育超前”,似乎现在教育的一切方面都要超前,超前就对,滞后就错。其实,教育超前是有条件、有限度的,因为教育总是要受社会制约的,无论怎样也不能超越社会所能承受和允许的范围,倘不加考虑盲目超前,势必带来不必要的损失和混乱。又如“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一讲转轨,便对素质教育大加赞美,而对应试教育付以不屑,似乎一无是处,至于二者是否存在联系和共性则很少予以探讨。是研究中的疏忽还是思维上的误区?抑或只是从众心理?“素质教育”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必然也有其滋生的条件和土壤,而且和“应试教育”及早已提出的“全面发展教育”有着一定的联系,只有对各个方面进行全方位的探讨,才可能透彻地把握各自的本质与内涵、联系与区别,顺利实现“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轨。还有“跨世纪问题”研究,似乎一到21世纪什么都不同了,教育的继承性也不存在了,且不说“跨世纪”本身的界定较模糊,其理论探讨也大多为主观臆测,无多少客观依据。再如关于高等教育的管理权限,针对计划体制下统得过多、管得太死的状况,有人早就主张全面放权,完全让高校自主管理,实际上这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任何改革都有一个过程,不可能一步到位或一蹴而就,而且还要注意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随着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社会功能的拓展,教育权的国家化正成为一种世界性的趋势,政府对高等教育完全放权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在思考问题的时候要突破线性思维或单向思维,打破定势,不唯上,不媚俗,多角度,全方位地考虑问题,在辩证分析的基础上全面、深刻地把握事物的本质与规律。
其三,“主观支配客观,理论限定实践”。具体体现在对教育概念、本质、起源及规律的探讨和界定上。如关于“教育的本质”,往往不是从丰富多彩的教育实践、通过对教育现象和问题的观察与思考来进行探讨,而是从“教育”二字的原始意义和历史上教育家的有关论述来进行研究,即从主观到客观,这样是否有欠科学?又如关于“教育的起源”,现在一般都认为教育起源于生产劳动,教育的生物起源论和心理起源论都是错误的。得出这个结论的前提大致有:教育是一种有目的、有意识的活动;断定动物没有意识,而且儿童对成人的摹仿也是无意识的,因为恩格斯说过“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表面看起来顺理成章且持之有据,其实仔细考证,这些前提有的是很不确定的。如动物究竟有没有意识?尤其是那些高级灵长类动物?那些看来颇为聪明甚至比较高明的行为难道真的只是一种本能?又如儿童对成人的摹仿真的全无意识?或者一切摹仿都只是出自本能?倘如此,那些追星族、球迷、影迷对偶像的刻意摹仿又作何解释?教师之所以要为人师表,难道不是因为学生会有意无意地摹仿?可见,界定摹仿全无意识既不科学也不符合事实。对于教育研究,我们必须本着客观、求实的态度,通过科学考证和客观分析去发现隐藏在现象背后的规律和本质,不要单凭抽象的思辨和主观的臆测来推断丰富多彩的教育实践。
二、研究者的情感与态度对教育研究的影响
随着“非智力因素”、“情商”和“心力”概念的提出,情绪、情感和态度等心理因素在认识和实践中的作用愈来愈受到人们的重视。有人认为,事业成功的关键是情商而非智商。从比例来说,前者占80%,后者占20%。较新的看法甚至认为,分析力及理性的智能对生活的成就而言,只不过是排名第五位的影响因素罢了。对于教育研究,情感和态度等方面的作用同样不容忽视,它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研究者对研究方向的选择和研究内容的确定,而且直接影响其从事研究的动力及克服困难与挫折的程度。
但是,目前的教育研究却有一种不好的倾向(而这又直接与研究者的情感态度有关),即“赶时髦、随大流、功利主义和从众心理”,具体表现为过分追求热点、一味注解政策、随声附和、人云亦云等。如教育的“三个面向”一提出,便有众多的文章为其喝彩和作注;“四有新人”一出台,便标语满天飞、文章铺天盖地。还有“德育为首”、“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教育先行”和“素质教育”,哪一次不是应者云集、盛况空前?似乎一下子都成了这方面的专家,且多为溢美之词,很少反对和异议。难道这些提法或政策真的如此科学,如此完美且不容置疑?我看未必。如“德育为首”,只不过是从当时的社会需要和时代特点而作出的一种教育决策,从其“实然状态”而言,这种提法是不科学的,因为作为全面发展教育的组成部分,每个方面都同等重要,没有主次之分和轻重之别,一如空气和水于人的生存一样。有人说,“德育为首”并不是“德育第一”,这只不过是为注解政策而作的狡辩,一种低劣的文字游戏而已。其实大可不必这样遮遮掩掩,在特殊的时期,作为一种政策,“德育为首”是可以提的,一如战争时期以军事教育为主一样,只是我们在进行研究和阐释的时候必须予以界定和说明,否则不仅会造成理论上的混乱,同时也不利于实践。现在人们趋之若鹜的是素质教育,这方面的文章真是汗牛充栋,其实真正有价值的又有几何?直接后果是导致人力、物力、财力的巨大浪费,因为大批的文章要发表、众多的书籍要出版、大量的稿费要支付,而从事的大多是重复的工作。同时,基础研究领域门可罗雀,而热点研究、政策研究却既多且滥,从而直接影响教育理论水平的提高和教育学的科学化进程。另外,由于此类文章大多为主观臆测和抽象思辨,缺乏对问题本身深入的研究且可操作性差,从而使实践者难以明了其中的实质和内涵,显得无所适从。正如素质教育讲了几年,其实验研究时间更长,但很多实践工作者还不太清楚何谓素质教育,至于怎样操作更是感到茫然,结果口里喊的是素质教育,具体实施的还是应试教育。
一个教育科研工作者要明确自己的方向和目标,要善于固守自己的阵地,不要轻易动摇和放弃。虽然也应密切关注教育热点、教育政策和教育动态,但若一味随波逐流,终不免流于平庸,难成大器。纵观历史上的教育“大家”,往往是因一篇文章或一本著作成名,而其文其书则很少为应景而作或政策注解。因此,为文宜精不宜多,只要是精品,只要有所突破,有所建树,一文一书便也能流传久远!
三、研究者的意志品质对教育研究的影响
意志品质的优劣往往决定着一个人的成长和事业的成败。当前,教育研究中的急功近利、浅薄浮躁在一定程度上就与研究者的意志品质有关,并突出表现于理论与实践的脱离。当然,这有多方面的原因,如物质条件的制约——实践、实验、调查、测量、统计等都要花费一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而教育科研经费的匮乏则由来已久;认识上的误区——认为在高校或研究机构从事理论研究条件比较优越,不愿下到基层开展实证或应用研究等。但更重要的还是一个意志品质问题,即不愿吃苦,害怕受累,贪图安逸,耽于享乐,视实践研究为畏途。我们是十三亿人口的大国,教育事业应是世界上最庞大的事业。比较而言,教育研究人员也是最多的,但却为什么总是实践上不去,理论下不来,难以产生自己的教育大师(即理论上卓有建树,实践上成绩斐然,有别于纯粹的教育学家和教育实践家)?有人认为这是实践工作者缺乏科学理论的指导,从而不能正确地开展教育实践并把自己的经验上升为理论的缘故,但我觉得主要还在于理论工作者不愿全身心地投入到实践研究中去。回溯教育发展史,真正的教育家并不是产生于斗室,而是脱颖于实践,从夸美纽斯、杜威、苏霍姆林斯基到赞科夫都概莫能外。闭门造车、胡思乱想既不可能孕育出教育大师,也不可能产生有影响的教育理论流派。教育理论工作者必须明白自己的使命,要有一种紧迫感和责任心,不能让我国的理论研究总处于思辨状态,更不能让教育实践只停留于经验水平,而要认真寻找二者的结合点,力争在理论上有所突破和创新,并给教育实践以科学的指导。此外,还须保持一定的恒心和韧性,具备为了既定目标耕耘不息、探索不止的精神。教育实践或实验研究有时会很辛苦,需要忍受长期的寂寞与孤独,如赞科夫的“教学与发展”研究就持续了20年之久,没有坚定的信念和超人的毅力,谁能坚持始终?作为一个卓有成效的大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能一辈子呆在中学,又有多少人能够效仿?还有中国的陶行知,也是这方面的典范。因此,坚定的信念和良好的意志品质应是教育研究者最可宝贵的素养。
以上只是从感性方面对教育研究者的心理素养及其影响作了粗略的探讨和简要的分析,也许并不尽然,但倘能切中一些时弊,并对教育研究者有所启迪,也就不违本文的初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