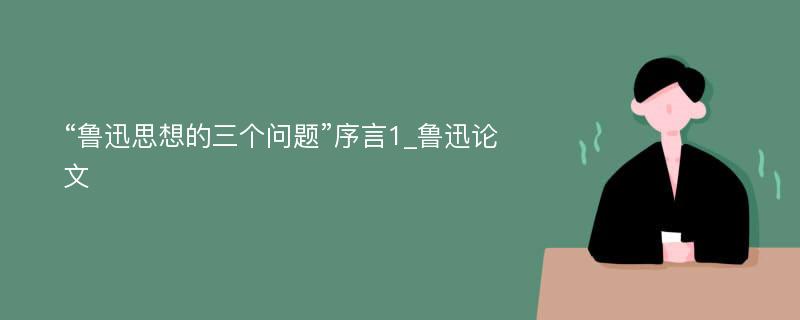
《鲁迅思想三题》序论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序论论文,鲁迅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这一组鲁迅思想三题,是我求索什么是“鲁迅思想”的发现。鲁迅研究首先是发现事实及其意义,以及存在的问题、是非、利害与功过。就思想而言,鲁迅有没有思想?有什么思想?是怎样的思想?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思想?他的思想根本特质是什么?这些都属于事实层面。鲁迅研究有如天文学家研究宇宙,发现星球、行星、恒星、彗星、星座、星系、星云等等。然后加以分析、解释、评议与评估。
三个题目是:
一、“根柢在人”[1](P38):鲁迅思想的元点。
二、“立人”[1](P38):鲁迅思想的核心。
三、“一要生存”——“不是苟活”;“二要温饱”——“不是奢侈”;“三要发展”——“不是放纵”[2](P54-55)及“自他两利”[1](P124):鲁迅思想的纲要。
鲁迅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是,中国在英国反人道的输入鸦片,引起两次“鸦片战争”之后,以及列强恃强凌弱,步步侵略,企图瓜分中国;而国内“戊戌变法”遭到镇压,丧失了和平改革的机遇,激起汉族推翻清帝国的革命。
1902年鲁迅从矿路学堂毕业,“因为绝望于孔夫子和他的之徒”[3](P326),东渡日本留学,跻身于“除学习日文,准备进专门的学校之外,就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3](P578)的留学生之中。当时的舆论,试检阅《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就可以发现大体分三个类别。一是延续“洋务派”兴办工业、商业、军备。如:《论中国路矿尽归外人》、《论世界经济竞争之大势》、《论中国商业不发达之原因》。二是革命与保皇的论争。如:《论立法权》、《辨革命书》、《论专制政体有百害于君而无一利》、《论满洲虽欲立宪而不能》、《驳“新民丛报”最近之非革命论》。三是关注国人的精神问题。如:《新民说》、《箴奴隶》、《中国人之缺点》、《民族精神论》、《民族的国民》、《三纲革命》。② 革命是当时的潮流。不仅是政治革命,还有民族、经济、思想、文化、道德以及文艺诸多方面的革命。鲁迅赞成革命。这一历史大势决定了鲁迅思想革命的取向。鲁迅追求“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更何有于肤浅凡庸之事物哉?”[1](P57)它的逻辑蕴涵及其发展决定了鲁迅思想的根本特质。
在这一历史背景下,鲁迅的知识结构,价值取向和思想性质,对革命根本问题的思考,全面地初步展示在他1907—1908年发表的五篇文言论文中。这五篇论文奠定了后来称为“鲁迅思想”的基石。
第一篇《人之历史》,认同人类的起源与进化的史实。认识到人类与动物,人性与动物性的联系和根本区别。提炼出“在进化的链子上,一切都是中间物”的卓识。领悟到人在自然与社会中的地位,自觉立志于革命、改革和发展。
第二篇《科学史教篇》,认识到:一是科学是推动物质生产发展的强大动力。二是科学,“时泰,则为人性之光”;“致人性于全”[1](P35)必须既有科学理性,又有文艺情操。这正是鲁迅把思想和人心融汇的根源。
第三篇《文化偏至论》,陈述文化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偏至”,借鉴必须有所选择,提出了“根柢在人”和“首在立人”的思想。
第四篇《摩罗诗力说》,倡导“反抗者”精神。唯有“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精神,人才能成其为人,而不是苟活的奴隶,乃至奴才。
第五篇《破恶声论》,具体批评当时流行的“恶声”。包括“汝其为国民,汝其为世界人。”破“破迷信者”。破“崇侵略者”,指出“崇侵略者类有机,兽性其上也,最有奴子性”[4](P33)。可惜,这篇论文注明“未完”。
鲁迅立足文艺,沿着这一思路在中国革命艰困、复杂、曲折的过程中,不断进行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自我解剖,坚守、放弃、补充和完善自己的思想。这里勾勒的三个命题,我认为具有纲领的性质。
一、“根柢在人”:鲁迅思想的元点
这里的“元”,取《尔雅·释诂》中“初、首、基、元,始也”及“元、良,首也”[5](P2568-2577)的词义,蕴涵比现在通行的“原点”丰富。
鲁迅提出“根柢在人”,出于三点考量。
第一,他对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坚信。“鲁迅与进化论”是一个专门的题目,需要专门梳理与评议。这里只说明一个事实,即鲁迅是终身信奉进化论的。鲁迅曾解剖自己,说:“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并且因此译了一本蒲力汗诺夫的《艺术论》,以救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6](P6)是怎样纠正的呢?鲁迅在《〈艺术论〉译本序》中说:“并非人为美而存在,乃是美为人而存在的。——这结论,便是蒲力汗诺夫将唯心史观者所深恶痛绝的社会,种族,阶级的功利主义底见解,引入艺术里去了。”[6](P269)可见,鲁迅接受阶级论,是将阶级论补充到他的思想中,而不是取代原来的思想。鲁迅所持有的不是“唯阶级论”,而是包含社会、种族、阶级等多元因素的思想,是坚守着人性的阶级论。他说:“在我自己,是以为若据性格感情等,都受‘支配于经济,(也可以说根据于经济组织或依存于经济组织)之说,则这些就一定都带着阶级性。但是‘都带’,而非‘只有’。”[6](P128)1935年,鲁迅在《名人和名言》中批评德国的细胞病理学家维尔晓既不相信进化论,又不深研进化论,自视很高,随意发表反对进化论的演讲,给大众不少坏影响。[3](P375)鲁迅终身坚守着进化论这一生命科学的基石。
第二,是常识与常理。鲁迅指出武器不是根本,根本在制造、掌握武器的人。“举国犹孱,授之巨兵,奚能胜任,仍有僵死而已矣。”[1](P46)北伐战争的时候,鲁迅在给友人的信中说:“现在我最恨什么‘学者只讲学问,不问派别’这些话,假如研究造炮的学者,将不问是蒋介石,是吴佩孚,都为之造么?”[7](P199)“制造商估”,追求最大利润,多唯利是图,是自私的。“国若一日存,固足以假力图富强之名,博志士之誉;即有不幸,宗社为墟,而广有金资,大能温饱。”[1](P46)而“立宪国会”,可能“思鸠大群以抗御,而又飞扬其性,善能攘扰,见异己者兴,必借众以陵寡,托言众治,压制乃尤烈于暴君”[1](P46),而走向民主的反面。
第三,世界各国的现实状况。鲁迅指出:“今敢问号称志士者曰,将以富有为文明欤,则犹太遗黎,性长居积,欧人之善贾者,莫与比伦,然其民之遭遇何如矣?将以路矿为文明欤,则五十年来非澳二洲,莫不兴铁路矿事,顾此二洲土著之文化何如矣?将以众治为文明欤,则西班牙波陀牙二国,立宪且久,顾其国之情状又何如矣?若曰惟物质为文化之基也,则列机括,陈粮食,遂足以雄长天下欤?曰惟多数得是非之正也,则以一人与众禺处,其亦将木居而芧食欤?此虽妇竖,必否之矣。然欧美之强,莫不以是炫天下者,则根柢在人,而此特现象之末,本原深而难见,荣华昭而易识也。”[1](P58)这是鲁迅注重世界各国发展的历史教训的认识。鲁迅曾经翻译世界史③,可惜未见出版。
“根柢在人”的思想,是常识,是常理,看似没有什么深奥与创新;其实,这很像传说中的哥伦布的鸡蛋,当立在餐桌上了,人人都会,人人都能。但要像哥伦布那样想到,做到,却并不容易。1925年,鲁迅总结辛亥革命的失败教训,说:“最初的革命是排满,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要国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于是就不肯了。所以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8](P31-32)鲁迅论“革命文学”的创作,认为“为革命起见,要有‘革命人’,‘革命文学’倒无须急急,革命人做出东西来,才是革命文学”[2](P437)。又说:“我以为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2](P568)鲁迅想写的一部中国史,是“人史”[9](P248);鲁迅对中国并不绝望,他看到了“脊梁”,就是“人”:“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前仆后继的战斗,不过一面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3](P122)这是事实,也是常识:小到个人创业,两人婚恋,大到民族振兴,国家制度、法律的创建与实行,最后决定的力量都在人。
“根柢在人”是鲁迅观察社会、回应人生问题的元点,把握这一元点,大体掌握着解读鲁迅文章的钥匙。
二、“立人”:鲁迅思想的核心
1981年我那篇关于“立人”的论文,只说明:“鲁迅独特的思想是什么呢?是不是可以这样来概括:以‘立人’为目的和中心;以实践为基础;以批判‘根深蒂固的所谓旧文明’为手段的关于现代中国人的哲学,或者说是关于现代中国人及其社会如何改造的思想体系。”[10](P39)当时我着重从鲁迅“后期”作品中罗列他的言论,证明:“‘立人’是鲁迅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立人’的思想贯彻于鲁迅一生的始终。”“‘立人’的思想遍及鲁迅思想的各个方面。”“鲁迅对如何‘立人’的认识和实践。”当时的目的只是在证明两点:其一,鲁迅是有思想的,并且“鲁迅思想”是有系统的。这个系统是以“立人”为核心的。他无愧于从20年代就被誉为“思想界的权威者”。④ 鲁迅这个伟大的思想家不是任何人吹捧起来的。其二,鲁迅思想是一以贯之的,“腰斩”鲁迅,割裂为“前期”与“后期”,不符合鲁迅思想的实际。批判其前期思想,只肯定其后期思想是严重的失误,是另有所图的假命题。
其实,关于“立人”,有三个问题。一是为什么要“立人”?二是怎样“立人”?三是“立”怎样的“人”?当时只回答了第二个问题的一半,而且是危险比较少的一半。现在试着给出完全的答案。
为什么要“立人”?就因为“根柢在人”。已如上述。这不仅仅在政治、军事、法律、文化、道德、宗教诸方面是如此,日常生活也是如此的。鲁迅曾经记载一次买药的经历,遭遇药店店员兑水掺假,感慨地说:“这是人的问题。做事不切实,便什么都可疑。吕端大事不胡涂,犹言小事不妨胡涂点,这自然很足以显示我们中国人的雅量,然而我的胃痛却因此延长了。”[2](P328)
类似的事,鲁迅遇到的颇多。鲁迅在《热风·事实胜于雄辩》中记买鞋也是这样。许寿裳回忆留学日本的时候,鲁迅和他探讨“中国民族中最缺乏的是什么?”的问题,写道:“当时我们觉得我们民族最缺乏的东西是诚和爱,——换句话说,便是深中了作伪无耻和猜疑相贼的毛病。口号只管很好听,标语和宣言只管很好看,书本上只管说得冠冕堂皇,天花乱坠,但按之实际,却完全不是这回事。”[11](P487)一百年过去了,命也革了两次了,新中国成立60多年了,我们这个汉族最缺乏的“诚和爱”,“作伪无耻和猜疑相贼”如今怎么样了?
怎样“立人”呢?鲁迅当时提出来的是:“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假不如是,槁丧且不俟夫一世。”[1](P58)
“尊个性而张精神”在同一篇论文中又表述为“掊物质而张灵明”及“任个人而排众数”。[1](P47)它包含四个问题。
第一,“个人”、“个性”的性质问题。人的生命是个体性的,人的心智是个体性的。人的资产、权利、利益和自由等也都以个体性而实现。人是群居的,人的生存又是群体性的,因此“个体”与“群体”确实存在着天然的矛盾。个人的性质表现在人际关系中,焦点在人我彼此利益的损益。鲁迅在定义他的“重个人”、“尊个性”的“个人”时,理论上是排除“害人利己”的:“个人一语,入中国未三四年,号称识时之士,多引以为大诟,苟被其谥,与民贼同。意者未遑深知明察,而迷误为害人利己之义也欤?夷考其实,至不然矣。”[1](P51)
而实际的情形却非常复杂。鲁迅曾经概括道:“现在做人,似乎只能随时随手做点有益于人之事,倘其不能,就做些利己而不损人之事,又不能,则做些损人利己之事。只有损人而不利己的事,我是反对的,如强盗之放火是也。”[12](P404)鲁迅的选择是“随时随手做点有益于人”的事情;并盛赞柔石“无论从旧道德,从新道德,只要是损己利人的,他就挑选上,自己背起来”[6](P497)。至于“任个人而排众数”则是指个人与众数的意见和意愿而言;并非指资财、权利、利益与自由等权利。
第二,多数、众数、众庶、大群的意见与意愿是否一定正确?鲁迅是质疑的。“理若极于众庶矣,而众庶果足以极是非之端也耶?……彼之讴歌众数,奉若神明者,盖仅见光明一端,他未遍知,因加赞颂,使反而观诸黑暗,当立悟其不然矣。一梭格拉第也,而众希腊人鸩之,一耶稣基督也,而众犹太人磔之,后世论者,孰不云缪,顾其时则从众志耳。”[1](P49-53)鲁迅在《习惯与改革》中指出:“改革一两,反动十斤”,“多数的力量是伟大,要紧的”;但他们的意见、意愿和习惯,并不一定是“正确的”、“合理的”。[6](P228)由于传统思想中正统思想的教化,甚至往往是不合时宜和不正确的。历史上的改革、移风易俗是在与大群的斗争中实现的。这就是鲁迅认为的“由历史所指示,凡有改革,最初,总是觉悟的智识者的任务。但这些智识者,却必须有研究,能思索,有决断,而且有毅力。他也用权,却不是骗人,他利导,却并非迎合。他不看轻自己,以为是大家的戏子,也不看轻别人,当作自己的喽罗。他只是大众中的一个人,我想,这才可以做大众的事业”[3](P104)的深层原因。
至于“多数决定”的选举,只能是一时的民意,并不一定正确。独裁和专制绝对不行,到近代人道、人权觉醒更是犯罪;“多数决定”也可能错误,并不一定可靠:这是人类群居而或一群体必须作出决策时候的两难处境。两害相权取其轻,在专制与代议制民主之间,也只有把选举权给予大众,庶几对于独裁者是一种必须的制约。
第三,“个人”与“众数”,以谁为本位?是怎样的路径?“尊个人”,这是以“个人”为本位,为出发点,是没有个人就没有群体的思路。这虽然要面对人的损人利己行为,但目的并不是为了每个“个人”,而是由个人通往群体,通往“集体”。对于这一点,鲁迅青年时期就是明确的。他明确说明:“盖惟声发自心,朕归于我,而人始自有己;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觉近矣。”[4](P26)“诚若为今立计,所当稽求既往,相度方来,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以兴起。”[1](P47)
“尊个人”,发展个性,由个人通往多数,没有个人就没有集体是合乎人心、合乎人情、合乎人性的常理。个人为群体牺牲,除日常生活外,最重要的是牺牲意见和牺牲生命,是特例,是非常情况;这有时是必要的,但不是常态。孔子已经慨叹:“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水火吾见蹈而死者矣,未见蹈仁而死者也!”(《论语·卫灵公》)这就是没有顾及人心、人情和人性,甚至人的生物性本能的教训。再好的理论,再美的理想,违背人的常情与常理,乃至违背人的天性,是非人道的,也不为大众所践行的。
个人和大群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纠缠着的。没有个人就没有大群;没有大群也没有个人。个人是渺小的,大群才有伟力。都持之有故,都言之成理,然而各有利弊。必须选择的是哪个利大,哪个弊小。历史所指示的常态是:以个人为本位,才可能落实个人以及“人”的资产、权利和义务,利益、责任、自由、平等以及权力,一个个个人才可能维持和提升大群;以大群为本位,最后必然导致某个强人及几个强人以“集体”之名垄断权力和权利,而架空义务和责任。集体必然强调牺牲个人成全集体,从而淹没个人。老子曰:“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13](P3)“刍狗”者,不是“人”;是工具,是机器,是机器上的螺丝钉。
第四,“张精神”是人的物质需求与精神追求的关系。人对于物质,从婴儿求乳的本能开始,衣食住行是生存、温饱和发展所必需的。而“人往高处走”,“水涨船高”,人的需求推动物质的生产与创造,被生产与创造出来的物质既满足了人的需求,又刺激着人的更多更大的欲求,刺激着更进一步的生产与创造。它的负面影响是物欲横流,人唯物质是求。鲁迅认同对这种物欲的自制,而支持发扬人的精神。
三、“一要生存”——“不是苟活”;“二要温饱”——“不是奢侈”;“三要发展”——“不是放纵”及“自他两利”:鲁迅思想的纲要
1925年,这艘“共和号”中国巨轮,依旧陷入内忧外患,颠簸摇晃航行在急流险滩、疾风骤雨之中。1913年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意图推翻合法总统——政敌袁世凯,被袁世凯击败。1915年袁世凯悍然解散国会,篡改约法,宣布次年改称“洪宪元年”,企图称帝。蔡锷将军发动“护国战争”,迫使袁世凯取消帝制。1917年张勋进军北京,扶持清废帝溥仪复辟,旋即失败。自1913年至1926年,13年间先后有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曹锟等五六位总统,一位国务委员黄郛摄行总统职,一位临时执政段祺瑞。其混乱可想而知。鲁迅极富政治敏感。1912年,他从故乡光复后一年的变化中,即痛感“狐狸方去穴,桃偶已登场”[14](P449)。到1925年即发出沉痛的呼吁:“我觉得仿佛久没有所谓中华民国。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我觉得有许多民国国民而是民国的敌人。我觉得有许多民国国民很像住在德法等国里的犹太人,他们的意中别有一个国度。我觉得许多烈士的血都被人们踏灭了,然而又不是故意的。我觉得什么都要从新做过。退一万步说罢,我希望有人好好地做一部民国的建国史给少年看,因为我觉得民国的来源,实在已经失传了,虽然还只有十四年!”[2](P16-17)这种痛感是出于对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的严重失望产生的。当时复兴儒家正统思想的文化保守主义已经达到要立儒家为国教的地步了。在这样的恶劣的复古环境中,鲁迅提出:
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2](P47)
半个月后,鲁迅作了进一步说明,如下:
但倘若一定要问我青年应当向怎样的目标,那么,我只可以说出我为别人设计的话,就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有敢来阻碍这三事者,无论是谁,我们都反抗他,扑灭他!可是还得附加几句话以免误解,就是:我之所谓生存,并不是苟活;所谓温饱,并不是奢侈;所谓发展,也不是放纵。[2](P54-55)
鲁迅为避免“误解”而作的这个说明,是极其重要的。生存、温饱和发展是人的天性,不教而会,不教而能。这是事实。这是常识。鲁迅的“一要生存”,正是建立在这一常识——现代生命科学的知识之上的。他坦言:“我现在心以为然的道理,极其简单。便是依据生物界的现象,一,要保存生命;二,要延续这生命;三,要发展这生命(就是进化)。”[1](P135)不幸的是,人类经过数十万年进化到今天,依旧是一个不能把人当做人的社会,依旧是一个权贵可以草菅人命,贫富两极严重分化,弱势群体控诉无门的社会。鲁迅把“生存”放在“温饱”之上,既是人类生存的困境所致,也是一种深刻的揭示。人在“被”允许生存之后,才是温饱问题。
但是,如果人仅仅是为了生存、温饱而生存,只不过是一种生物性的生存,生物本能的生存,物质性的生存。这种生存固然有其人性的意义,必须也应该给予人道的理解、同情与支持;但毕竟是生物性的;极其可能沦为“非人”的境地,成为一种“苟活”;还没有升华为独立的“人”,自由的“人”,“真的人”。鲁迅的进一步说明,排除了“误解”,发出了警示:人要自觉成其为“人”。人要自觉做一个“人”,自觉地把自己当“人”,而不仅仅是一个“生物”。鲁迅所说“合理的做人”[1](P135),就是合乎“理想的人性”的、有精神追求、不苟活、不“吃人”的“真的人”。
“生存”——“不是苟活”,这是一个纲要。这个纲要的核心,是反对做奴隶,更反对做奴才,以及为统治者效命的“聪明人”,即“帮闲”、“帮忙”和“帮凶”。鲁迅有大量文章阐释这一思想。他的《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提供了一个活生生的范本。
“生存”——“不是苟活”的重点之一是反专制。鲁迅对于专制有一系列的揭露与论述。如:“自由之得以力,而力即在乎个人,亦即资财,亦即权利。故苟有外力来被,则无间出于寡人,或出于众庶,皆专制也。国家谓吾当与国民合其意志,亦一专制也。”[1](P52)这里提到的“个人”的“自由”,涵盖个人的“资财”、“权利”、“意志”,以及思想和言论。如:“约翰弥耳说: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我们却天下太平,连冷嘲也没有。我想:暴君的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愚民的专制使人们变成死相。大家渐渐死下去,而自己反以为卫道有效,这才渐近于正经的活人。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2](P45)鲁迅根据自己生活在“共和”时代的经验,更提出:“约翰穆勒说: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而他竟不知道共和使人们变成沉默。”[2](P554)鲁迅对于“专制”压制言论,特别敏感、沉痛与愤怒,就因为这是摧毁民族精神、民族灵魂的罪行。一个民族一副“死相”,没有声音,没有思想,没有意志,就是行尸走肉,一群动物。《庄子》曾记述孔子的话说:“恶!可不察与!夫哀莫大于心死,而人死亦次之。”[2](P130)这也是鲁迅写《无声的中国》,写《老调子已经唱完》,并喊出“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2](P292)的深邃的历史教训。
“暴君的专制”、“愚民的专制”是从专制的手段立言。名为“共和”也可能实行的是专制,鲁迅透视制度观察到了“民主”的复杂性。从制度立言,鲁迅已经揭示了“寡人”专制,“众庶”专制,“托言众治,压制乃尤烈于暴君”[1](P46)的“立宪国会”等多数决定的民主形式,以及用“国家”名义实行的专制。尤其令人警醒的是,鲁迅提出“家庭专制”[15](P114)问题。这是每个人每天生活于其中的问题。中国的“家庭专制”制度历史悠久,而儒家正统思想为它奠定了理论基础。这就是“夫为妻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妻子必须绝对服从丈夫,绝对忠于丈夫。丈夫死后妻子必须活着守节或殉死成烈。鲁迅的《我之节烈观》深刻批判了这种“吃人”的单方面强加在妇女身上的“不德”的理论。“父为子纲”,儿子必须绝对服从父亲,绝对忠于父亲。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说:“‘父子间没有什么恩’这一个断语,实是招致‘圣人之徒’面红耳赤的一大原因。他们的误点,便在长者本位与利己思想,权利思想很重,义务思想和责任心却很轻。以为父子关系,只须‘父兮生我’一件事,幼者的全部,便应为长者所有。尤其堕落的,是因此责望报偿,以为幼者的全部,理该做长者的牺牲。”[1](P137)鲁迅呼吁建立“父范学堂”,“因为我们中国所多的是孩子之父;所以以后是只要‘人’之父!”懂得“生了孩子,还要想怎样教育,才能使这生下来的孩子,将来成一个完全的人”[1](P312)。鲁迅曾经以史家的笔墨自我评论《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却比果戈理的忧愤深广,也不如尼采的超人的渺茫。”[3](P247)《狂人日记》中的“家族制度”其根本特质就在“家庭专制”。
“生存”——“不是苟活”的重点之二是牺牲问题。“牺牲”的内涵是很丰富很复杂的。鲁迅曾叹息:“我的生命,碎割在给人改稿子,看稿子,编书,校字,陪坐这些事情上者,已经很不少。”[8](P199)这无疑是一种牺牲。鲁迅是主张父亲,理应为子女即后起的生命作出“牺牲”,以实现进化的。总之,凡是“损己利人”的行为都包含着一定的“牺牲”。但不苟活,是对于压制、损害自己的外力作出抗争。抗争就可能出现牺牲。这种牺牲,最大的是牺牲生命。对于这种“牺牲”,鲁迅有着严格的限制条件:“为社会计,牺牲生命当然并非终极目的,凡牺牲者,皆系为人所杀,或万一幸存,于社会或有恶影响,故宁愿弃其生命耳。”[16](P88)而在一般条件下,一般意义上,鲁迅反对“轻死”,反对“牺牲”,以敬畏的心对待牺牲。1926年3月18日,段祺瑞执政府公然开枪屠杀和平请愿的青年学生及北京市民,爆发“三·一八事件”。当天,鲁迅“出离愤怒”公开谴责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2](P280)。随后又劝导青年:“会觉得死尸的沉重,不愿抱持的民族里,先烈的‘死’是后人的‘生’的唯一的灵药,但倘在不再觉得沉重的民族里,却不过是压得一同沦灭的东西。中国的有志于改革的青年,是知道死尸的沉重的,所以总是‘请愿’。殊不知别有不觉得死尸的沉重的人们在,而且一并屠杀了‘知道死尸的沉重’的心。死地确乎已在前面。为中国计,觉悟的青年应该不肯轻死了罢。”[2](P283)1927年,国民党背叛盟友中国共产党,发动“四·一二政变”,鲁迅再次目睹政府血腥屠杀共产党员和青年,他再次劝导青年学生,恳切地呼吁:“危险的临头虽然可怕,但别的运命说不定,‘人生必死’的运命却无法逃避,所以危险也仿佛用不着害怕似的,但我并不想劝青年得到危险,也不劝他人去做牺牲,说为社会死了名望好,高巍巍的镌起铜像来。自己活着的人没有劝别人去死的权利,假使你自己以为死是好的,那末请你自己先去死吧,诸君中恐有钱人不多罢。那么,我们穷人唯一的资本就是生命。以生命来投资,为社会做一点事,总得多赚一点利才好;以生命来做利息小的牺牲,是不值得的。所以我从来不叫人去牺牲,但也不要再爬进象牙之塔和知识阶级里去了,我以为是最稳当的一条路。”[4](P229)
“一要生存”——“不是苟活”,就必须反抗,挣脱奴隶的枷锁,做一个独立的人,自由的人。绝不苟且偷生,心甘情愿做奴隶,更不做“聪明人”和奴才。但同时又必须珍惜生命,牢记“生命是第一义”,绝不“轻死”,慎之又慎地对待自己的生命以及他人的生命。
“二要温饱”——“不是奢侈”,人在贫穷困苦中是可以吃苦耐劳的。鲁迅从饮食文化的视角揭示贫富两极饮食的巨大差别:“近来外国人也时常说,中国人礼仪好,中国人肴馔好。中国人也附和着。但这些事和民众有甚么关系?车夫先就没有钱来做礼服,南北的大多数的农民最好的食物是杂粮。有什么关系?中国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的人的痛苦换来的。”[14](P326)但是中国的富人,或“暴发户”,往往“奢侈”起来。以饮食为例,古代就有“八珍”之说,如今依旧有醉虾、猴脑、熊掌、驼峰,无尽的山珍野味。种种穷奢极欲,暴殄天物,不仅超出“温饱”的需要,而且损害健康,戕贼生命;是对个人“人性”的扭曲、异化。它的极致“只是纯粹兽性方面的欲望的满足——威福,子女,玉帛,——罢了”[1](P372)。
“放纵”的根本特质和“奢侈”是一样的。
人类的生存是群居的。每一个人都生活于一定的人群之中,有一个人我关系问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
人类是雌雄异体,生命的繁衍是有性生殖;人类发展的基础在繁衍,繁衍终止,人类自然灭绝。因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最基本最自然的是两性关系,男女之间的关系。男女之间关系的根本特质是文明的天然尺度。不幸,中国有文字以来的历史,是一部歧视、压迫女性的历史。古代伟大的圣人孔子的教导就是:“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论语·阳货》)孔子之徒进一步发展而成为“男帅女,女从男,夫妇之义由此始也。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5](P1456)。再简化并建构成为“三纲”中的“夫为妻纲”,迫使女性处在最受压迫的底层。鲁迅引用儒家经典评论说:“我们自己是早已布置妥帖了,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因为倘一动弹,虽或有利,然而也有弊。我们且看古人的良法美意罢——‘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但是‘台’没有臣,不是太苦了么?无须担心的,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而且其子也很有希望,他日长大,升而为‘台’,便又有更卑更弱的妻子,供他驱使了。如此连环,各得其所,有敢非议者,其罪名曰不安分!虽然那是古事,昭公七年离现在也太辽远了,但‘复古家’尽可不必悲观的。太平的景象还在:常有兵燹,常有水旱,可有谁听到大叫唤么?”[1](P227-228)
“自他两利”,虽然是鲁迅针对男女之间关系提出的道德准则,我以为也是同样适用于普遍的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准则,并且是一条人与人之间的基本的、具有普世价值的道德准则。从逻辑讲,既然对于最受压迫、出于最底层的女性都必须是“自他两利”,那么,对于其他人不也理应是“自他两利”吗?而且,鲁迅说过:“我们自己想活,也希望别人都活;不忍说他人的灭绝,又怕他们自己走到灭绝的路上,把我们带累了也灭绝,所以在此着急。”[1](P330)这是最大最根本的“自他两利”。这正是鲁迅思想的一个根本特质。
长期以来,鲁迅研究在理解、阐释鲁迅的价值观,价值取向,特别是主张斗争的正当性,斗争的尖锐性和激烈程度诸问题上,陷入尴尬的境地。需要“斗争”的时候,强调鲁迅的“横眉冷对千夫指”;需要“和谐”的时候,强调他的“俯首甘为孺子牛”[14](P151),虽然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但并未从思想的深层结构理解鲁迅思想的统一性,鲁迅人格的完整性。
首先是鲁迅斗争的非暴力性。人类社会的发展,无论改革,还是革命,是多方面的,如政治的,军事的,法律的,文化的,思想的,宗教的和道德的,等等,运用多种手段或方式如暴力的,和平的,等等进行的。它们互相联系,却不能混同。即使在暴力革命时期,也不能斥责学校的教员,医院的医生没有拿起武器上前线,不能简单裁判他们是不革命的,非革命的,甚至是反革命的;或只有成为“地下工作者”才是革命者。鲁迅是个文学家,思想家,他的工作性质是非暴力的,非直接决定对方的生死的。他的热烈的爱憎,分明的是非,是通过非暴力的文艺分野和思想斗争表现和实行的。其力量在文艺,在思想。所以鲁迅说:“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2](P442)又说:“即使是正面的敌人,倘不死于战场,就有大众的裁判,决不是一个诗人所能提笔判定生死的。”[6](P405)鲁迅批评论敌说:“我想,辩论事情,威吓和诬陷,是没有用处的。用笔的人,一来就发你的脾气,要我的性命,更其可笑得很。先生还是不要暴躁,静静的再看看自己的信,想想自己,何如?”[9](P551)鲁迅说:“文人的铁,就是文章,魏先生正在大做散文,力施搏击,怎么同时又说是‘手无寸铁’了呢?”[3](P386)“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6](P592-593)一目了然,这不过是比喻,并不是说文人的笔就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冷兵器。
要之,文学斗争,思想斗争,乃至政治斗争,在鲁迅思想中,都是非暴力的斗争,不应该“你死我活”,直接决定对方的生死。鲁迅作《文艺与政治的歧途》揭露并抨击“革命的政治家”杀害文艺家,是愚蠢的,无用的,决不能阻遏社会的向前发展。[14](P115)
其次是鲁迅斗争的目的。鲁迅说他之所以写小说,是:“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6](P526)
鲁迅写杂文,擅长讽刺,他指出:“讽刺作者虽然大抵为被讽刺者所憎恨,但他却常常是善意的,他的讽刺,在希望他们改善,并非要捺这一群到水底里。”[3](P341)又说:“我自己也知道,在中国,我的笔要算较为尖刻的,说话有时也不留情面。但我又知道人们怎样地用了公理正义的美名,正人君子的徽号,温良敦厚的假脸,流言公论的武器,吞吐曲折的文字,行私利己,使无刀无笔的弱者不得喘息。倘使我没有这笔,也就是被欺侮到赴诉无门的一个;我觉悟了,所以要常用,尤其是用于使麒麟皮下露出马脚。万一那些虚伪者居然觉得一点痛苦,有些省悟,知道伎俩也有穷时,少装些假面目,则用了陈源教授的话来说,就是一个‘教训’。只要谁露出真价值来,即使只值半文,我决不敢轻薄半句。但是,想用了串戏的方法来哄骗,那是不行的;我知道的,不和你们来敷衍。”[2](P260)
鲁迅参加辛亥革命,支持国共合作北伐推翻北洋军阀的统治;支持中国共产党推翻国民党“一党专制”的“党国”政权。他说明自己目的和创造社们不同。他批评说:“将革命使一般人理解为非常可怕的事,摆着一种极左倾的凶恶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对革命只抱着恐怖。其实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这种令人‘知道点革命的厉害’,只图自己说得畅快的态度,也还是中了才子+流氓的毒。”[6](P304)又说:“无产者的革命,乃是为了自己的解放和消灭阶级,并非因为要杀人。”[6](P405)
总之,鲁迅反对做奴隶,为自己和同类挣脱奴隶的枷锁,摆脱奴隶的地位,坚忍不拔地斗争,要争取做一个“人”,不吃人的“真的人”[1](P454),“致人性于全”[1](P35)的“完全的人”[1](P312)。
就是对于国民党统治的“国家”,鲁迅逝世前写道:“我的爱护中华民国,焦唇敝舌,恐其衰微,大半正为了使我们得有剪辫的自由。”[3](P576)因为“国家”与“政党”、“政府”不是同一的东西,毕竟中华民国是中国历史上结束几千年皇权专制创建的第一个共和国。鲁迅生活在其中。鲁迅痛感它未能实现共和,所以要向它展开斗争,乃至革命;但目的在实现共和,并非复辟或退回到专制制度。
鲁迅的斗争是坚决的,坚毅的,至死不渝的。他逝世前一仍旧贯,宣告:“又曾想到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3](P635)他清醒地洞察到,他的“怨敌”决不会在他死后就“宽恕”他;他为什么要屈服、委曲,“宽恕”他们呢?但是,如果别有洞天,“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14](P157)。对待侵略我国的异族是这样,对待政治、文化、思想、文艺上的对手能不是这样吗?
“救救孩子……”这是鲁迅根本的思想,一以贯之的思想。我们中国的希望在“救救孩子”,在“立人”。这一思想:普通,却博大;简明,却深邃。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喊出这句话;他几乎是临终前的杂文,还是喊出这句话:“真的要‘救救孩子。’”[3](P659)
这就是我心中的鲁迅思想的大纲。
2011年5月3日定稿
收稿日期:2010-05-08
注释:
① 本文修改过程中,得到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程振兴、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周佩瑶和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鲍国华诸位学友的重要帮助,谨此深深致谢。
② 具体篇目参见张枬、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三联书店,1977年版。
③ 《340506致杨霁云》:“又曾译过世界史,每千字五角,至今不知道曾否出版。”参见《鲁迅全集》(第13卷),第9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④ 自鲁迅发表《狂人日记》以后,他的思想即引起很大关注。不仅朋友间有“托尼思想,魏晋文章”的赞誉,报章也多有强调。1925年4月26日邵飘萍登出广告,用了:“思想界的一个重要消息:如何改造青年的思想?请自本星期五起快读鲁迅先生主撰的《□□》周刊。”同年8月初北京《民报》在《京报》和《晨报》上刊登的广告中,又有“特约中国思想界之权威者”用语。凡这些都引起鲁迅不悦。他将邵语斥为“写得那么夸大可笑”,立即要求改正。而这些用语,也成为攻击鲁迅的口实。鲁迅在《不是信》中反批评说:“至于‘思想界的权威者’等等,我连夜梦里也没有想做过。”并发表《所谓“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启事》,声明:“我也不是‘思想界先驱者’即英文Forerunner之译名。此等名号,乃是他人暗中所加,别有作用,本人事前并不知情,事后亦未尝高兴。倘见者因此受愚,概与本人无涉。”对于此类称号的态度,鲁迅还有《辞“大义”》、《革“首领”》等文章的说明。我觉得:舆论是一回事;别人利用舆论攻击是另外一回事;鲁迅自己的看法又是一回事,必须加以区别。我这里引用“舆论”的看法,只是说明:“思想家”、“伟大的思想家”不是鲁迅死后出现的,20年代就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