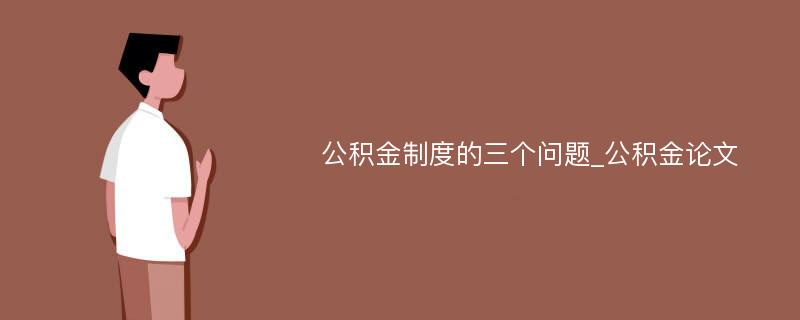
公积金制度三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公积金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实现公司储备主要是通过提取公积金来完成。关于公积金制度的产生,有人认为,法律上的规定最早见于1807年的法国商法[1],也有人认为最早出现在1867年的法国公司法中[2]。
一、大陆法国家公积金制度的特点──强制性
大陆法国家的公积金制度的突出特点是其规定的“强制性”,特别是关于法定公积金(盈余公积金和资本公积金)的规定。各国公司法都要求应按规定的比例提取盈余公积金,如法国、德国法规定应从盈余中提取5%作为公积金[3];日本商法典的公司编规定按盈余分配额的10%提取[4];我国台湾公司法第237条,也规定按10%提取盈余公积金[5]。此外,对盈余公积金总额已达到公司资本的一定比例时,即不再要求公司提取,如法国法规定盈余公积金已达公司资本10%时,公司不必再提取;日本规定25%[6];我国台湾公司法规定,“法定盈余公积金已达资本总额时”(100%),可不必再提[7]。
资本公积金是由公司的某些剩余资本而构成的,例如溢价发行股票而收入的溢价款;公司减少的资本额等。资本公积金的增减与公司的经营策略及特殊行为有关,因此对积累金额的增加没有具体规定。这一点与盈余公积金不同。
与法定公积金相对的,是任意公积金。任意公积金也来源于公司盈余,但提取的数额由公司章程或股东大会决定,法律不予强行规定。但各种专用金的用途一旦决定,如弥补损失公积金、折旧公积金等,非经股东大会决议不得挪作它用。
法定公积金的主要用途是填补亏损和充实资本。如用于充实资本,几种公积金在使用上并无顺序限制。但在弥补亏损时,应按规定的顺序。王书江的《外国商法》一书中写道[8]:“弥补亏损时,应先使用任意公积金,再使用资本公积金,最后使用盈余公积金”。然而,《日本民法典》[9]第289条第二项以及台湾公司法[10]第239条第二项,均明确规定在弥补损失时,先使用盈余公积金,如不足时,才能动用资本公积金。由此可断定,是《外国商法》一书出现了笔误。而且,盈余公积金来源于公司的盈余收入,其累计增加的形式较固定,所以,在填补损失时,理应被优先拨付使用。
二、英美法国家公积金制度的特点──任意性
英美公司法公积金制度与大陆法相比,其最大差异在于它的“任意性”特点,即它的取得和使用并不是依照公司法的直接的强制性规定,而是由公司董事会根据经营情况而决定的,因此,也就不存在类似大陆法中的“法定公积金”与“任意公积金”之分。
英美公司法更注重“实用性”,表现在储备金制度上,把对其提取、使用、取消的权利交给公司董事会。美国特拉华州公司法(Delaware Corporation Law)第49节规定[11]对可用于分配股息的任何资金,公司董事为用于任何适当之目的,均可从中提取储备金,也可以将其取消。这里的“董事”其实际意义应理解为“董事会”,因为只有公司董事会才有权决定储备金的增减。英国公司法[12]第117条明确了这项属于董事会的分配权,规定在股息分配之前,董事会不仅可以从盈余中“提取他们认为适当的数目作为一项或多项储备金”,而且,有权“自由决定把储备金使用于最适宜于使用盈余的任何地方”。
那么,上述规定的“任何适当之目的”、“任何地方”指的是什么呢?英国公司法第117条中列举了“公司的业务”和“合适的投资”。这种概括所涉及的范围已很广,说明法律赋予了董事会较自由的储备金使用权。但是这种“自由决定”的使用权,仅限于把储备金用作经营资本使用。如果公司想用于支付股息分配,则不存在这种自由使用权。
因此,第117条又不得不提醒董事会:为谨慎起见,可“将他们认为不宜分派的任何盈余结转下届而不提作储备金”。这一点,我们至少可以从以下三点认识:
其一,董事会享有结转“不宜分派的任何盈余”之权利,无疑也包括当年的可分利润。这一制度与大陆法国家公司法的规定不同,后者一般将提取盈余全部作为公积金,而前者的“结转下届”可不存入储备金中。
其二,英国判例法上,对股息分配之前,是否要补足各种实际的亏损,存有较大争议。英国上诉法院的许多判例均认定这样的规则,即“在确定可分利润之前,不需对固定资本的亏损先行补足”。而在1902年的《邦特诉巴洛赫马泰忒钢铁公司》一案中,法惠尔法官主张:“正当的途径是在公布股息之前,要补足各种实际的亏损”[13]。从第117条的上述提醒以及对判例的分析[14],上诉法院的规则已占了上风。这样,结转的盈余如用于股息分配,可不受出现资本亏损的影响。
其三,英国1948年公司法及许多判例对公司储备金的使用,也已形成严格限制,除弥补亏损和充实资本外,不能用于盈余分配。因此,才有必要提醒董事会,在提取储备金时,应谨慎从事。
综上可见,两大法系的公积金制度尽管体现了各自的特点,具体操作时的规则要求也有差别。但在保证公积金(储备金)发挥其内在的功能方面,两者又有本质上的统一。
三、我国公司法公积金制度问题评析
我国公司法总体上采用了大陆法的公积金制度,但具体规定又有不同,现就几个特点及问题评述如下:
第一,我国公司法没有采用“盈余公积金”之称,而直接称作“法定公积金”。这样,在我国法中,法定公积金与资本公积金是并列关系,而在大陆法国家中二者是包容关系。但是,从我国公司法第178条的规定来看,资本公积金的变动也是根据法律的规定,具有“法定”性质,因此也仍是一种“法定公积金”。比较来看,我国公司法采用“法定公积金”名称极易使人产生歧义,而大陆国家的做法,逻辑上较严密。
第二,创设了“法定公益金”。无论是大陆法系国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其公司法的公积金制度中都没有“法定公益金”规定。由此可见,这的确是我国公司法的一个特色。
但是,围绕着应不应该制定这一规定,却有着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15]。持反对观点者认为,这一规定与国际通例不一致,且涉及到股东的利益问题;赞同的观点认为,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应当使职工集体福利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提高。从直观上看,似乎两种观点均有道理。然而稍加分析,便会发现:赞同者的愿望是好的,但这一规定运行的结果并不一定令人满意。原因在于:首先,股东的收益明显减少。按照公司法第177条的规定,公司在分配当年利润时,先要按税法规定扣除所得税;如上一年有亏损的,再弥补亏损,在此前提下,再提取10%的法定公积金和5~10%的法定公益金。而且,经股东会决议,还可能需要提取任意公积金。这样一来,用于分配股的利润所剩无几,甚至“无利不分”。股东如果得不到较满意的收益,必将抑制股份制的生机,使公司不仅失去市场信誉,集资不灵,而且也会使本公司的内部股东失去信心和积极性。其次,强制公司提取法定公益金,不利于公司灵活使用资金从事市场竞争。当公司亏损较严重时,假如其公积金(法定公积金、资本公积金、任意公积金)全部已用于弥补亏损,此时仍急需为扩大生产而增加资本,但根据第180条之规定,法定公益金只能用于公司职工的集体福利。因此,即使是面对着一大笔资金(每年按税后利润5~10%提取,且没有最高累积额限制),公司的经营者也只能望梅止渴,这无疑束缚了公司法人的手脚。再次,实践中,企业为职工发放集体福利,大都采取平均主义的做法,不利于调动职工的积极性,这多少受到计划体制时某些做法的影响。而且,由于公益金只能用于集体福利,这样在企业的发展一方面需要节约财力、渡过难关时,另一方面又很难杜绝浪费行行──因为“法定公益金”确实助长了企业大多数人孳生“有钱不花,积累白搭”的心理。
实际上,公司职工福利的提高及劳动条件的改善,最终取决于公司自身的实力和发展前景。因此,应该首先从如何建立真正的现代企业制度上思考,而决不应捆住公司的手脚。否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综上所言,作者认为,法定公益金制度不利于体现“法人自主经营”的原则,在一定程度上抵销了公司制度内在活力。且它只着眼于职工的眼前利益,而忽视了激励机制将会给企业和职工带来的长远受益的机遇和利益。
其实,问题的解决并不在于是否关心职工福利本身,而是怎样才能更好地解决问题。依作者所见,公司可通过提取任意公积金的办法,根据公司经营效果、发展需要等要求,自行决定“福利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因为,如果公司真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法人,那么在这个问题上,股东和市场能够告诉公司经营者如何去关心职工的福利问题。
第三,关于我国公司法公积金制度的几个问题:
问题之一:法定公积金累计额超过公司注册资本50%的部分,其性质如何?
公司法第177条第1款规定,“公司法定公积金累计额为公司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可不再提取,”至于超过部分属何性质,没有明确。但按照大陆公司法的一般理论[16],法律已不再将“超过部分”视为“法定公积金”。因此,既然法律对“超过部分”已不再强制提取,所以它已无“法定”可言。作者认为,可将其视为任意公积金,但一经提取,未经服东会决议,也不应随意挪用。
这一问题还涉及到另一个疑点,即:按公司法第177条第1款规定:法定公积金累计额达到其注册资本50%的公司,可以不再提取,亦即可以不从税后利润中提取10%作为法定公积金,这无疑问。疑点出在:假如累计额还没有达到注册资本50%的时候,而这时只要再提取10%以下(如3%)便可达到50%的规定,那么法律是否允许公司按低于10%(如3%)的比率提取呢?不仅我国公司法未加以规定,从所掌握的资料来看,几乎大陆法国家所有公司法及研究理论,均未提及这一细节。如何解决这个疑点,自然也可找出“不允许”和“允许”两个对立观点。反对者主张,既然法律已有10%的明确规定,就应一律按10%提取;且如果允许公司自行掌握,也就不存在超额提取的问题了。赞同者也有充分理由:既然“超过部分”已不属于“法定的”公积,那么是否提取“超过部分”则应由公司法人自行决定,因此,如果此时提取3%,便可使公司法定公积金的累计额达到注册资本的50%这一要求,法律就没有必要再做出前后矛盾的强制性规定。
作者认为,后一种主张更可取。理由为:其一,法定公积金的意义,“乃为巩固公司之财产基础,加强公司之信用起见”[17]。同大陆法国家的公司积累规定相比较,我国算是主张公司实行较高资金积累的国家。各国对法定公积金累计额的规定一般为公司资本的10~25%(如法国10%、意大利20%、日本25%[18]。而我国是50%,实行“高公积”政策利于公司树立起良好信誉,积累雄厚的财力基础。但是也有不利的一面,因为达到积累的最高限额的周期较长,且我国公司法还有法定公益金(5~10%)的强制规定,这就意味着我国公司要在很长时期内承受着强制积累的重负,使企业难以根据市场需要,灵活运用资金。如果公司经营上没有活力,那也就谈不上建立起良好的信誉。其二,公司在长时期强制积累,使股东获得的股利减少,这也会直接影响公司的形象。另外,我国公司法并未规定可以使用公积金支付股利的特殊情况,如为维持股票价格而以公积金支付股利等。因此,关于上述“细节”之争论,我认为应该允许公司在保证使其法定公积金达到公司资本50%的前提下,自行决定提取比例,把这一权利交给公司股东会或董事会。这样,由于减少了公积金的比例,股东的股利相对增加,就有利于维持股票的价格。当然,公司如果认为有必要压低一下股价,或增加公积金,也可以按较高比例(如10%)提取。总之,在这个“细节”上,选择权还是交给公司更好。
问题之二:“法定公积金”代表“法定公积金和法定公益金”吗?
按我国公司法第177条第1款、第2款规定,公司在弥补亏损、交纳所得税之后,即可以该余额为标准,各提取10%的法定公积金和5─10%的法定公益金。但是该条第3款又补充到:“公司从税后利润中提取法定公积金后,经股东会决议,可以提取任意公积金。”这里的“法定公积金”是否是等同于第1款中的“法定公积金”呢?在此将两种不同之理解分析如下:
第一种理解:第3款中“法定公积金”实际上是指第1款中的“法定公积金”和“法定公益金”。因为第1款中的两个“法定”比率是以同一个“税后利润”为标准进行提取。所以,第3款的意思是指,在提取这两个比率之后。经股东会决议,公司才可提取任意公积金。
第二种理解:第3款中的法定公积金”就是指第1款中的“法定公积金”,并不包含“法定公益金”,这是法律条文明确规定的。正如该条第2款的作用一样,用规定先将利润弥补亏损,再提取两“法定比率”的方法,来补充第1款,以免产生“先提法定比率而后弥补亏损”的异义。因而,第3款也是对第1款的补充,即认为:在从税后利润提取10%作为法定公积金后,如股东会决议,可先提取任意公积金,最后再从余额中提取公益金。反映了“公司积累优先于集体福利”的思想。
显然,两种理解都有道理,但两种方法在实践中的核算结果是有差别的。例如,假设某股份公司当年实现利润130万元,上年亏损10万元,当年交纳所得税20万元。扣除两者后还余100万元。现在假定提取法定公积金、法定公益金及任意公积金各10%:
则按第一种理解,核算结果为:
法定公积金:100万元×10%=10万元
法定公益金:100万元×10%=10万元
任意公积金:(100万元-10万元-10万元)×10%=8万元
如按第二种解释,计算结果为:
法定公积金:100万元×10%=10万元
任意公积金:(100万元-10万元)×10%=9万元
法定公益金:(100万元-10万元-9万元)×10%=8.1万元
显然,两种方法使法定公益金和任意公积金的提取金额出现差异,第一种计算方法同第二种相比,法定公益金多出1.9万元,而任意公积金减少1万元。不仅如此,提取的“三金”总额也不等,前者共提28万元(股利分配额72万元),后者共提取27.1万元(股利分配额72.9万元),因此股东最终获得的股利同样不等。
由此可见,公司法第177条第1款和第3款,在规定上出现了漏洞,使公司的财务核算人员在实际操作上,产生两种不同的理解。
笔者认为,为了消除这种模棱两可的解释,必须对这两款加以修订,使立法者的意图明确地表达出来。具体办法,要么修订第1款,要么修订第3款。如果立法意图是第一种理解,则第3款应改为:“公司在税后利润中提取法定公积金和法定公益金后,……。”如果按第二种理解,那么应修改第1款为:“公司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应当提取利润的百分之十列入法定公积金,如股东会决议,可提取任意公积金,再提取利润的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列入公司法定公益金。……”可以看出,按第一种理解,修订第3款较为简单、明确,且两个“法定比率”都以“税后利润”为同一基数标准,容易操作,至于任意公积金是以同一基数标准提取,还是以提取两“法定金”后的余额为标准,则无关紧要,可由公司掌握。且因为任意公积金是否提取,及提取多少,本来就是公司的事。如果采用第二种解释,修改第1款,除了条文表述变得复杂之外,还要对每次提取的“利润基数”作出规定。否则仍会出现不同的财务核算结果。因此,笔者倾向于按第一种理解,修改第3款。
注释:
[1][18]见周友苏:《公司法律制度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19页,第320页。
[2][16]见王书江:《外国商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年10月第1版,第73-74页。
[3][6][8](同上)第74页。
[4]见丁耀堂(译):《日本商法典》,法律出版社,1982年4月第1版,第90页。
[5][7][10][17](台)郑玉波:《公司法》,三民书局印行,1980年,第154-156页。
[9]见丁耀堂(译):(同[4])第91页。
[11]见姜风纹(译):《美国公司法选择》,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84年8月第1版,第48页。
[13][14]R·E·G·佩林斯和A·杰弗里斯:《英国公司法》,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84年3月出版,第321-322页。
[15]参见张桂龙、周敏:《(公司法)释解》,人民法院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187页。
标签:公积金论文; 法定公积金论文; 法定公益金论文; 公积金提取论文; 公积金上海论文; 任意盈余公积金论文; 盈余公积论文; 董事会论文; 公司法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