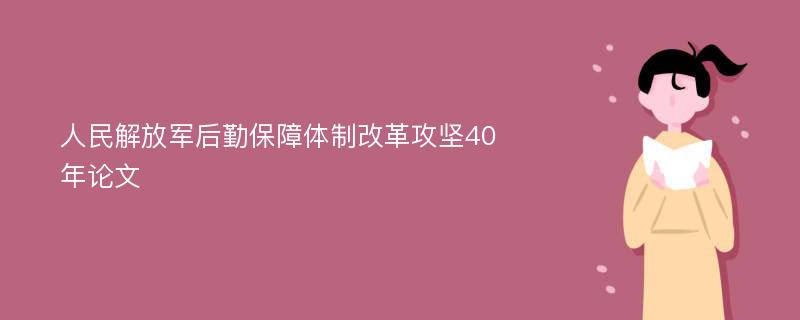
人民解放军后勤保障体制改革攻坚40年
★ 农清华
摘要 :中国人民解放军40年后勤保障体制改革历经三个阶段:1978年至1998年的改革,致力于突破应对大规模战争的分区保障模式,不仅夯实了三军联合保障的根基,也催生了初步的联勤体制;1998年至2012年的改革,致力于探索适应局部战争的联合保障模式,不仅见证了对一体化保障体制的不懈追求,也显示了改革过程的无比艰辛;2013年至2018年的改革,致力于把握后勤保障体制变革的客观规律,不仅成功构建了现代联勤体制,也提升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的综合保障能力。
关键词 :改革开放40年 后勤保障体制 保障体制改革
Reform of PLA Logistic Support System in the Past 40 Years
后勤保障体制,是后勤保障的组织系统、机构、单位设置和职能、权限区分及相互关系制度的统称,是军队后勤的基本框架和根本制度。它对于后勤各种物质要素组合成有机整体,保证后勤保障活动有序进行,形成和增强后勤整体保障能力,具有全局性影响和根本性作用,是后勤改革的主体,也是改革的最大难点。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结以往改革试点的经验教训,顺应国家经济体制和军队领导指挥体制改革的大潮,在新的起点上奋力攻坚,几起几落,矢志不渝,最终突破体制障碍,成功构建起适应信息化战争需要的现代联勤体制。
在这种正玩得热闹的时候,翠姨也来参加了。翠姨弹了一个曲子,和我们大家立刻就配合上了。于是大家都觉得在我们那已经天天闹熟了的老调子之中,又多了一个新的花样。
一、从单一战区试点到多地多战区试点,1978年至1998年的改革,致力于突破应对大规模战争的分区保障模式,不仅夯实了三军联合保障的根基,也催生了初步的联勤体制
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保障体制是在战争年代分区保障基础上形成的。1949~1950年海、空军等军兵种部队组建后,为适应“帝国主义入侵的大规模战争”分区作战、独立保障需要,确立了“总后勤部领导下的三军分供保障体制”,从战争年代的地区式补给形态,变为“上统下分”的垂直分供补给形态。1952年中央军委在《关于全军后勤组织原则与领导关系的决定》中明确,“全军后勤工作,在由总后勤部统一的业务领导下,按照陆、海、空军三个系统进行之”,即“平时由各系统按建制组织保障”,“战时,按照作战区域以陆军后勤部位主体,组织战区联勤指挥部,在战区首长统一领导下,统一该战区陆、海、空军的供应工作。”① 贾宪文、金国华:《联勤理论研究》,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第8~9 页。 这种“平时不联战时联”的保障体制,对组建不久的空、海军后勤建设和军事行动后勤保障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局限性也很明显:主要是力量分散,重复建设,保障功能浪费;“尤其不适应战区内组织三军协同作战的要求”。为此,军委常务副主席周恩来在签发《决定》时批示:“要探索三军统供联勤之路,实行三军联勤体制。”有鉴于此,在实行分区保障的同时,联勤改革试点持续展开。1955~1965年和1970~1971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在旅大(今大连)和粤东组织了两次统供联勤试点,其中旅大试点持续达十年。然而面对大规模战争战区独立作战的保障需求和以陆军后勤为主体的力量布势,不仅统供联勤收效有限,试点进程也因特殊事件半途而废:第一次试点因“文化大革命”爆发而中止;第二次试点因林彪“九一三事件”而停止。
改革开放优化了军队建设的外部环境,为后勤保障体制改革提供了难得机遇,致使改革进程不断加快,力度进一步加大。1980年,针对中越边境自卫还击战后勤保障得到的经验和暴露出的问题,总后勤部明确提出:“供应体制要适应战时要求”“由于保障体制对保障效益影响极大,……要把保障体制改革作为后勤改革的主体”“要实行统供与专供结合的联勤保障体制”。① 《洪学智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第742 页。 由此,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在新起点上筹划从一个地区到一个战区范围的改革试点。
1983年3月,经过近两年准备,在供应实力25 万人的济南战区展开了第三次联勤改革试点。这是改革开放以后的首个试点,不仅试点规模大,方法也有新的变化。试点后勤领导机关由以后勤系统为主,改为由总参、总后和军种领导联合组成“改革试点领导小组”负责,注重三军干部的混合编组,并赋予试点地区解决标准外经费物资特殊问题的权力。此外,在通用与专用物资划分上进一步细化,具体到物资的名称。然而,试点方案刚刚运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战略性转变和“百万大裁军”开始孕育启动,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帝国主义入侵的大规模战争”的认知已发生根本性改变,“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思维淡出人们视野,试点外部环境已发生重大变化,为此试点体制运行半年后即宣布“暂停”。尽管半途而废,但通过试点,明确了联勤发展方向及通用保障体制建立的思想和统一供管范围,提出了供应关系和保障接口及其运行机制建立方式方法,明确了联勤机构三军组成人员和军区后勤双重职能,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保障体制改革的飞跃性进步。
2)收集资料内容:本次收集资料内容主要有测站概况、实测流量成果表、实测大断面成果表、逐日平均水位表、逐日平均流量表、洪水水文要素摘录表等。
如果说1983年刚展开即停止的改革试点只是传统改革思维和模式的延伸,其出发点仍不适应战区独立作战和三军协同作战由军区统一指挥的要求,那么历经1985~1987年军队建设指导思想战略性转变和“百万大裁军”之后的第四次联勤试点,从某种程度上讲更具重大转折的标志性意义:即致力于突破传统的应对“大规模战争”分区保障模式,向着构建适应现代战争的现代联勤保障体制艰难迈进。
被称之为“网络型划区保障改革”的第四次联勤试点,是在认真吸取以往试点经验教训基础上进行的,不仅试点时间长,从1988年到1998年,历时十年且范围分布广,1988年首先从海南岛地区三军部队展开,1990年又扩大到沈阳、济南两个战区。在改革设计上,军委明确了分阶段推进的思路,即首先实行以“三代”(代供、代医、代修)为主要内容的网络型划区保障,以提高经济效益和保障效能;再有步骤地实施三军联勤统供,逐步向联勤方向发展② 参见《洪学智回忆录》,第742 页。 。中央军委还要求改革后勤保障体制,逐步推行陆海空三军统供与分供相结合、以统供为主的划区供应体制,使已有后勤设施效能得以充分发挥。
以军区为基础的联勤,结束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半个世纪的三军独立保障体制,在就近供应、就近医疗、就近运输、就近保障部队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据统计,改革后军兵种部队数千个单位的通用保障,改由联勤系统组织,绝大多数得到就近就便保障,缩短了物资流和信息流的流时与流程,提高了保障时间和效率;经费物资保障效益也达到较好水平。联勤启动当年即节省经费2.3 亿元,减少不合理运输6000多万公里,节省油料1.4 万余吨。联勤还使保障资源得到优化,整合并收缩了保障摊子,减少重复建设,使保障力量布局渐趋合理。通过调整保障关系,多数部队实现了就近就便保障;通过展开联勤优质服务,保证了经费物资及时足额供应;通过建立协调协作机制,为平时联合训练和战时联合保障创造了条件。
由于保障体制改革成为新时期后勤改革的主线,并关系军队改革的全局,因而此次试点也引起军委主要领导的关注和推动。1990年1月,江泽民在听取总后勤部汇报时提出:“先搞‘三代’(代供、代修、代医),最终目的是实现联勤。现代化的军队后勤保障需要立体交叉,搞矩阵式管理,也就是要纵横结合,多边协作。中国历史上的诸侯割据,各管一摊,喜欢垂直管理,不会立体管理。我们在后勤保障的观念上要更新。今后的努力方向还是实行联勤,提高效益。”③ 黄本海:《军队联勤论》,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6年,第308~309 页。
201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加速推进。遵循“‘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原则,以领导管理体制、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改革为重点,协调推进规模结构、政策制度和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改革”③ 《中央军委关于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意见》,《解放军报》,2016月1月2日。 。2015年底印发的《中央军委关于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意见》明确,改革领导管理体制,主要是调整优化机关职能配置和机构设置,将总部制调整为多部门制,剥离具体管理职能,发挥军种机关的建设管理保障职能,以加强中央军委的集中统一领导;改革联合作战指挥体制,主要是构建“中央军委、战区”两级的联合作战指挥体制,重新调整划设战区,将7 大军区调整划分为5 个战区。《意见》还提出,要“调整改革后勤保障领导管理体制,以现行联勤保障体制为基础,调整优化保障力量和领导指挥关系,构建与联合作战指挥体制相适应,统分结合、通专两线的后勤保障体制”④ 《中央军委关于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意见》,《解放军报》,2016年1月2日。 。
试点过程中的2006年下半年,中央军委决定,为系统总结评估试点工作,同时做到公平公正评判,由军事科学院领导牵头组成专家组对改革试点情况进行全面评估,得出的结论是:“济南战区大联勤试点体制顺利建立,有效探索了三军后勤一体化保障的经验,试点是成功的,但深化改革的任务仍很艰巨。”③ 廖锡龙:《亲历济南战区大联勤改革》,《解放军报》,2008年12月16日。 存在的主要问题与矛盾,是与军队领导指挥体制关系,即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领导指挥体制、军兵种后勤领导机构、军区联勤部的建制领导关系不变的大背景下,实行突破传统保障体制大联勤,必然会给后勤保障的运行带来不畅。总后勤部同期开展的调研结果也显示,大联勤试点是在军队领导指挥体制未变,军费供求矛盾和标准化供应程度未变,海空军和二炮大单位的后勤领导机构未变的背景下展开,决定了大联勤改革的局限性,比如,如何保持后勤指挥体制与军队领导指挥体制的从属关系,如何做到在标准加补助情况下的等同等距保障,如何划分条条与块块的供应管理职能等,都受到很大制约。为此,试点领导小组提出:“如果急于在更大范围推开改革,可能欲速不达;如果继续在济南战区深化试验,又似乎改革进度较慢。……应先把试点体制搞完善,适当时机在更大范围推开改革。”④ 廖锡龙:《亲历济南战区大联勤改革》,《解放军报》,2008年12月16日。 2007年2月,胡锦涛批示:“先在济南战区正式实行大联勤体制,要继续深化改革,搞好理论研究和实践验证,为下一步在全军推开积累经验。”⑤ 廖锡龙:《亲历济南战区大联勤改革》,《解放军报》,2008年12月16日。 至此,中国人民解放军形成两种联勤体制并存格局。
在浇铸过程中,浇铸口与模子间的水平距离会发生变化,为此设置一个行走机构来进行水平距离调整;采用钢轨和四轮小车来实现,并采用液油缸驱动[2]。
福建师范大学胡志刚教授主编的教材《化学课程与教学论》,已经由科学出版社2014年10月出版,2016年1月第五次印刷。该教材是依据我国当前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需要,在总结同类教材经验的基础上,根据《普通高中化学课程标准》和《教师教育课程标准(试行)》的相关要求,汲取了我国化学课程与教学论的新成果,为化学教师教育人才培养提出的新要求编写的。
2.传染源:是被HIV感染的人,包括HIV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HIV主要存在于传染源的血液、精液、阴道分泌物、胸腹水、脑脊液、羊水和乳汁等体液中。
大范围的网络型划区保障试点和两次联勤实践,催生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初步的联勤体制。1998年4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决定,自从2000年1月起,全军实行以军区为基础的联勤体制。对此,1998~2003年,江泽民多次强调,我军的后勤保障体制,长期是三军自成体系,条块分割,机构重叠,与军队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战争的要求明显不相适应,造成的浪费也很大。现在,国家经济建设发展很快,物资比较丰富,供应渠道也比较多,实行联勤的条件已经具备。③ 黄本海:《军队联勤论》,第310 页。 这次改革,使中国人民解放军向三军一体、集约化后勤保障的方向迈出了一大步。
二、从以军区为基础的联勤到两种联勤。体制并存,1998年至2012年的改革,致力于探索适应局部战争的联合保障模式,不仅见证了对一体化保障体制的不懈追求,也显示了改革过程的无比艰辛
1998年军委扩大会议之后,经过近两年的筹划部署,2000年1月,致力于探索“高技术局部战争”联合保障模式的以军区为基础的联勤体制正式运行。这一体制的基本模式是:在中央军委和总部统一领导下,区域保障与按建制保障相结合,通用保障与专用保障相结合,以军区为基础组织联勤。其特点,一是以军区为基础组织通用保障。以军区后勤部和后勤分部为基础,分别充实军兵种后勤人员,形成军区联勤部和联勤分部两级联勤机构;将军兵种后勤通用保障实体归并重新组合,形成联勤基本保障力量,负责组织战区内军兵种部队通用物资和通用勤务的保障,并通过联勤分部就近就便保障到军兵种部队。二是以分部为力量按区域组织保障。每个战区联勤保障区内,划分若干联勤分部保障区域,分别由联勤分部负责对该区域内的三军部队实施保障。三是专用物资和专用勤务按建制组织保障。即各军种部队特殊需要的专用物资和专用勤务,按建制系统组织实施,实行专用物资专门供应。同时,通用保障的计划,按现行联勤体制,仍由军兵种后勤系统逐级提出计划上报。
1988年7月,中央军委批准《驻海南岛部队试行网络型划区保障实施方案》,海南地区部队的统供联勤试点随即展开。与试点相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全面实行油料代供和伤病员划区医疗。1990年3月,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国人民解放军又在沈阳、济南两个战区扩大网络型划区保障试点。这次试点方案的设计全面具体,联勤的内容和程度进一步提高,包括军需、卫生、军械、军交、车船、油料、物资、通用装备修理等8 个专业。对通用部分,实施相互代供、代医、代修;专用部分则按建制系统组织保障;交通运输则统一组织实施。
在军种层面,首先是调整组建陆军后勤部,同时整编海军、空军、火箭军后勤部,主要负责组织指导本军种部队的后勤建设,组织专用后勤保障和部分区域联勤保障。调整组建战略支援部队参谋部战勤计划局,负责所属部队的通用后勤和通用装备保障的计划协调。
在确立“三军保障一体化”改革思路之际,中国人民解放军对“现代战争形态”的认识也不断深化,经历了由“高技术战争”到“信息化战争”的跃升。2002年底,军委扩大会议提出:“战争形态的演变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社会历史过程。回过头来看,我们十年前把当代战争的形态界定为高技术战争,把中国人民解放军未来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从应付一般条件下的局部战争转变为打赢一场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高技术战争的本质就是信息化,人类战争形态正在进入信息化战争阶段。……基本趋势是要搞三军联合保障、综合保障和军民一体化保障。”② 《江泽民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48 页。 为此,适应信息化局部战争的“三军联合保障、综合保障和军民一体化保障”,开始成为保障体制改革的新目标。
格拉斯说,“在中国,由于老龄化加剧和医保体系尚未完善,阿尔茨海默病的防治将要面对更为复杂的困境,这是任何公共卫生专家和政策制定者都需要着力应对的局面。”
围绕信息化局部战争的新要求,党的十六大以后,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提高后勤保障能力和保障效益为标准,以实现“三军联合保障、综合保障和军民一体化保障”为目标,从2004年7月起,在济南战区进行了空前力度的改革试点——大联勤改革试点,以尽快建立适应信息化局部战争的联勤保障体制。对此中央军委提出:“这次改革试点的目的,是进一步探索建立三军后勤保障一体化的路子。”
大联勤改革试点,就是在战役层次,彻底打破军种界限,从体制上解决以军区为基础的联勤体制“统”得力度不大、“联”得范围偏小,综合保障能力较弱问题。与以军区为基础的联勤体制比较,大联勤改革试点致力于实现三个方面的突破:一是在联勤机构设置上,战区联勤部及联勤分部由三军人员按比例组成,实现了机构编成三军一体化。以往军区联勤机构中,军兵种干部数量占比不到一成,而且都是营以下干部。此次试点,联勤部军兵种干部占比将近半成,且在副部长以下领导干部中,配备一定数量的军兵种干部,使联勤部和联勤分部,成为三军联合的后勤领导机关。二是在保障力量的整合上,战区内战役层次的仓库、医院等保障实体,全部由联勤系统集中统管,实现了保障力量三军一体化。战役后勤保障力量的集中统管,三军共有,三军共用,就使战区范围的主要后勤保障资源达到最大限度的集约化。三是在保障活动组织实施上,战区内三军部队的后勤保障,全部由联勤系统统一组织,实现了保障渠道三军一体化。这就改变了“通”“分”结合的保障模式,做到了保障内容“通”“专”一体实施,保障计划两线合一运行。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采取实编、实兵、实转方式进行如此规模和深度的改革试验,还是第一次。
“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当房子恢复其本来的居住属性,住宅设计意识再苏醒。现代生活不仅仅是物质生活的富足,还代表着技术进步与文化融合带来的全新生活理念。从宜家、无印良品到“好好住”,越来越多的家居品牌在扩张市场的同时,也把设计理念、生活方式等带给国人。
后勤体制从属于军队领导指挥体制,并受其制约。大联勤试点开始后,由于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领导指挥体制、军兵种后勤领导机构、军区联勤部的建制领导关系不变”的背景下变革后勤体制,因而战略、战役层面掣肘较多,议论较多,阻力较大,运行艰难。对此,胡锦涛和中央军委对大联勤改革试点高度关注。2005年4月,胡锦涛指出:“要做好济南战区大联勤体制改革统一思想的工作,对保障对象单位提出的意见要认真研究解决,三军后勤保障一体化的改革方向必须坚持。”①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理论学习读本》,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6年,第142 页。 在同年年底的军委扩大会上,胡锦涛又指出:“建立三军一体化后勤保障体制的目标不能动摇,济南战区的大联勤改革试点要继续推进。”②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理论学习读本》,第208 页。
适应高技术“局部战争”的改革思路提出后,在联勤试点和几次三军联合演习中,各级各部队对联合作战保障体制进行研讨,并取得诸多成果。总后勤部成立了后勤编制体制研究论证机构,对21世纪后勤编制和保障体制进行研究规划,保障体制改革步入着眼全局、重点突破的新阶段。为此,1996年经过充分论证,中国人民解放军决定,在新组建的驻港部队“建立统专结合的联勤保障体制”,即“通用物资统一供应、普通伤病员统一收治、维持性经费统一保障、通用勤务统一组织、通用保障实体统一建设和管理、通用保障力量统一使用”② 张连松:《改革开放30年的军队后勤》,第189 页。 ,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支实行联勤体制的部队;1998年夏,中国长江、松花江和嫩江流域发生特大洪水。为保障参加抗洪抢险的三军和武警部队数十个师旅的救灾行动,总部后勤采取打破建制、就近供应、方便部队的办法,对抗洪救灾部队实施全方位、不间断、多建制、远距离的联勤保障,战时联勤保障机制紧急启动,始终保持装备物资供应不断,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又一次新的联勤保障实践。
三、从重塑战略、战区后勤体系到组建联勤保障部队,2013年至2018年的改革,致力于把握后勤保障体制变革的客观规律,不仅成功构建了现代联勤体制,也提升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的综合保障能力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人民代表会议后,中国共产党确立了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围绕这一目标,习近平在2012年底一次重要会议上指出,将“建设保障打赢现代化战争的后勤、服务部队现代化建设的后勤和向信息化转型的后勤”①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习近平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重要论述选编》,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4年,第61 页。 ,作为“现代后勤三大建设任务”②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习近平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重要论述选编》,第217 页。 ,为后勤保障体制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为此,在从2013年到2015年的三年多时间里,中国人民解放军按照“三大建设任务”要求,筹划保障体制改革:围绕建设保障“能打仗、打胜仗”的后勤,在军队的联合作战指挥体制、领导管理体制改革的基础上,大力提升“后勤指挥、后勤装备和经费物资保障、卫勤保障、运输投送、工程保障、后勤动员等六种能力”,具体途径是通过加强后勤机关战备设施和指挥通信装备配套建设,提升后勤指挥能力;成建制梯次补充配备第二代新型后勤装备,提升后勤装备和经费物资保障能力;加大海上和空中救治后送手段建设力度,提升卫勤保障能力;围绕应急投送、岸滩装卸载、大型保障装备等机制,加强运输投送能力;围绕战场设施综合配套、抽组工程保障力量训练、小而精的一线突击力量与大而强的机动支援力量建设,加强工程保障能力;围绕基础设施、大型保障装备的贯彻国防需求,提升后勤动员能力。以上“六种能力”的建设与深化联勤体制改革的结合,为现代联勤体制奠定了基础。
1993年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确立后,“高技术局部战争”取代“大规模战争”成为新的作战牵引和保障需求,网络型划区保障试点也与此相适应,开始融入联合保障、军民兼容的新内涵。在1994年中央军委批转的《后勤改革纲要》中,中国人民解放军不仅把保障体制改革作为后勤改革的首要任务加以明确,并提出:“后勤保障体制改革要坚持军民兼容、三军一体的方向;要在全军推行‘三代’,采取计价供应、增拨物资周转金和补偿费等办法,解决谁代谁吃亏的问题,并视情逐步扩大三军统一保障的范围和比重,增加联勤的因素和成分;同时,把军事经济寓于国民经济之中,充分利用国民经济包含的军事保障功能,尽快建立起平战结合的后勤动员体系。”① 张连松:《改革开放30年的军队后勤》,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9年,第188 页。
在军队领导指挥体制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长期受其制约并停止不前的后勤保障体制改革,开始迈出实质性步伐。2016年,经过科学调查论证、周密部署安排,中央军委决定组建联勤保障部队,并于9月13日成立,“标志着具有中国人民解放军特色的现代联勤保障体制正式建立,在联合作战、联合训练、联合保障的制胜之路上迈出关键性步伐”⑤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军后勤建设发展综述》,《解放军报》,2016年11月9日。 。习近平在联勤保障部队成立大会的训词中指出:“组建联勤保障基地和联勤保障中心,是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着眼于全面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作出的重大决策,是深化部队领导指挥体制改革、构建具有中国人民解放军特色的现代联勤保障体制的战略举措,对把中国人民解放军建设成世界一流军队、打赢现代局部战争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⑥ 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习近平论强军兴军》,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7年,第493 页。 从基本架构上看,现代联勤保障体制体现在三个层面上:
一般合理的饲养密度是:断奶仔猪0.5~0.8 m2/头;育肥猪1~1.2 m2/头;繁殖母猪1.5~3.2(带仔母猪) m2/头。种公猪应依据实际情况稍大一点,以创造宽敞的活动空间。
在中央军委层面,将总后勤部调整改编为军委后勤保障部,作为军委的“参谋机关、服务机关、执行机关”;主要职能是,履行全军后勤保障的规划计划、政策研究、标准制定、检查监督,同时,派出部分人员组建“军委联指”的后勤保障部门,使后勤要素融入作战要素之中。成立军委联勤保障部队,是此次联勤改革的最大亮点。就是以原武汉后方基地机关为基础,纳入原7 个大军区的联勤部机关和各军兵种的部分人员,调整组建新的武汉联勤保障基地,归中央军委建制,接受“军委联指”指挥。以各个联勤分部及相关联勤保障力量为基础,分别在无锡、西宁、桂林、沈阳和郑州,调整组建5 个联勤保障中心,归联勤保障基地建制领导,接受相关“战区联指”的指挥。
以军区为基础组织联勤,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发展过程中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但辩证地看,以军区为基础组织联勤,无论是理论基础还是实践基点,是建立在“军区”的根基之上,根子仍然在军区,实质是“陆军负责制”的联勤,联的权威不高,联的功能不全,联的条件有限,这种过渡性体制必然存在着一些自身难以克服的问题和矛盾:一是统供范围较小。纳入统供范围的比例,全军财务、被装、医疗、公路运输未超八成,油料则不足五成。基建营房保障、物资采购、卫生防疫等,还是三军各搞各的。二是统管程度低。军区联勤系统和军兵种部队之间的联勤工作机制是一种松散的“感情型”工作机制,缺乏必要和可靠的组织基础。三军的保障资源,依旧是各自拥有,多头管理,分散使用,体制性的资源浪费和结构失衡突出。三是联合保障难。此阶段联勤形成了“双流”格局,计划和供应两线分流,头绪多,环节多,关系复杂,协调困难,保障效率低。对此,江泽民指出:“目前的联勤体制还是初步的,统供的范围比较小,专供的范围还相当大,只能说在过去‘代医、代供、代修’的基础上前进了一步。真正意义上的联勤,是把三军部队所有的通用物资和通用勤务全部统起来,只有少数专用物资和专用勤务由军兵种建制系统负责。这是我们必须坚持的改革方向,要根据条件的成熟继续积极稳步地推进,最终实现三军保障一体化。”① 黄本海:《军队联勤论》,第312~313 页。
在战区层面,战区联合参谋部编设战勤局,负责保障战区首长指挥协调战区的后勤保障和装备保障,包括指挥“联勤保障中心”,遂行联勤保障和战役支援保障任务;战区军种及其以下部队的后勤机关与装备机关合一,组建新的保障部(处)机关,负责所属部队的后勤与装备建设,以及后勤与装备保障,同时,肩负指定区域的联勤保障。
这期间,以“三代”为主要内容的网络型划区保障试点,立足于现行保障体制,围绕保障内容、保障方法和保障渠道,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军兵种部队自我保障的条块分割界限,通过合理划分保障区域,统一调整保障任务,扩大代供范围和内容,就近就便的原则,取得了明显的军事经济效益。十年间,试点单位共调整逾千个单位的保障关系,仅油料每年就通过减少不合理运输,节约油料近万吨、经费数千万元。驻内地部队90%以上的官兵就医,从成百上千公里缩短到几十甚至几公里,大大方便了部队,提高了后勤保障的时效性。在保障需求牵引下,增大了三军间的交往和联络,增强了合成保障观念,形成了合成保障机制,提高了联合保障能力。通过改革,统一调整任务,统一使用力量,使既有资源利用更加合理,有利于三军的统一规划和建设。另外,由于此次试点时间跨度长,涉及范围大,几乎涵盖了后勤的所有专业,摸索出平战时后勤保障的一套有益做法,取得了一批有价值的成果。
2018年初,随着国防和军队改革的发展,中国人民解放军又对军委联勤保障部队的体制编制,做了进一步的调整,将武汉联勤保障基地升格为副战区级,行使大单位权限,接受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的业务指导,从某种意义上形成了独立的联勤兵种。至此,中国人民解放军“统分结合、通专两线的现代联勤体制”构建,已经取得重大进展。
2016年9月开始运行的现代联勤体制,近两年多来在保障模式,力量配置,指挥关系上实现了重大突破,展示出了新的特点。
一是统分结合、通专两线的保障模式。保障模式,作为衡量联勤保障体制先进性的重要指标,核心是确立物资经费的通用与专用的划分标准问题。中国人民解放军现代联勤体制,改变了济南战区大联勤体制实行“通专一体”的做法,在物资经费的通专划分上,实行“能统则统、宜分则分、就近就便”,不再强调统的越多越好,而是根据物资经费的性质、联勤部队的保障实力,来合理划分通用、专用的范围;对于各军种部队平时的基础性、维持性、通用性较强的经费物资,均由联勤保障部队实施一体保障;对于发展性的经费物资,则由军种分别按照各自的建制渠道,实施分散的建制保障。同时,中央军委机关负责制定各类的通用、专用保障划分的总细目和总标准;各个战区,则根据不同保障需求和联勤保障中心的不同实力,报经审批后,也可在总的规定基础上进行合理的调节,以便实现后勤保障活动的灵活机动和节约高效。在运行模式上,新的联勤保障体制,区分为平时与战时、通用与专用,分别按不同的渠道,上报下达计划和组织实施保障。这样,在供应保障活动中,相对于以往的通专一体的大联勤体制,可以减少供应环节,做到在平时,后勤能够管用、好用和方便用;在战时,后勤做到能用、敢用和随时用,提升了经费物资保障的效能与效率。
二是以联勤保障部队为龙头的力量配置。现代联勤保障体制,遵循习近平明确的“努力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联勤保障部队”① 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习近平论强军兴军》,第494 页。 的目标,按照中央军委关于“提高一体化保障能力,确保随时拉得出、上得去、保得好”的实战要求,立足于构建“一切为了打仗的后勤”,优化升级传统的联勤力量、科学编组新质联勤力量,突出运输投送、应急保障、保障基地等体系建设,明确联勤保障的职能定位和使命任务,以打造新质精锐的联勤保障体系为责任担当;把保障打仗作为组建联勤保障部队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发展理念上,强调“聚焦作战、凸显集约、强化服务、拓展领域”,走“联战联训联保”之路,致力于把专司联勤保障的组织体系建强,以便为部队提供优质的支援保障和后勤服务,同时推动军民融合由传统领域向新型领域延伸,以联合、精干、高效为目标,建强联勤保障力量,整合形成“通用联保、专用自保”的新的保障力量体系,实现了对中国人民解放军传统后勤保障力量的优化配置。
三是实行指挥与建设管理的相对分离。中国人民解放军现代联勤体制,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领导管理体制和指挥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本着方便部队、利于管理、节省资源的原则,在某些方面实现了飞跃性的发展。一是联勤保障部队第一次调整升格为独立的兵种,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保障力量编成的一个历史性进步;二是第一次区分为“战时作战指挥”与“平时建设管理”的两条链路。在“战时作战指挥”链路上,融入了联合作战指挥体系重构的“联勤指挥链”。就是通过“军委联指后勤部门、军委后勤保障部——战区联指后勤部门、联勤保障机构——联勤保障部队”三级联勤指挥链,确保联勤指挥融入联合作战指挥体系,实现统一指挥、分域控制、联合保障。在“平时建设管理”链路上,按照领导管理关系,理顺联勤建设的管理链:就是通过“中央军委——武汉联勤保障基地、军种后勤——联勤保障中心、战区军种后勤——联勤保障部队”的联勤建设管理链,实现后勤建设与管理活动的优质高效。新形势下,联勤力量在“从军委、军种到部队”的领导管理体系中,进行建设管理;在“从军委、战区到部队”的作战指挥体系中,进行编组运用,政令军令相对分离;联勤部队承担主要的联勤保障任务,军种则分担部分联勤保障任务,通用保障任务则进行重新划分,表现出了“建用适度分离,建管一体、平战一致、战训保一体”的特色。新体制的这种指挥与建设管理相对分离模式,较好解决了中外军队在联勤保障上历来存在的“注重保障效率与讲求保障效益”的两难局面。
“千呼万唤始出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现代联勤体制,形于实体“联”,实于力量“合”,适应了信息化局部战争军种联合作战的保障需求,是迄今为止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保障体制在适应战争形态发展上的最新探索。它的建立与发展,推动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保障体制实现了新的飞跃,展现着信息化时代后勤保障的特性,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保障体制40年发展演变的最新模式。
指导2型糖尿病病人建立预防骨质疏松的健康生活方式是提高病人生活质量的有效途径。医护人员作为健康知识的教育者和传播者,应积极将自我效能理论应用到健康教育实践中,提高2型糖尿病病人健康知识掌握程度和疾病预防保健技能,应重视2型糖尿病病人骨质疏松发生的危险性,积极进行相关健康知识宣教,提高2型糖尿病病人生存质量。
综上所述,现代联勤体制,是21世纪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保障体制成功变革的结晶。对信息化战争本质的科学把握,既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对战争形态认识的升华,也是催生现代联勤体制的直接动因;突破以军区为基础的联勤体制的局限,是由初步联勤走向高级阶段联勤的必然,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保障体制改革艰巨性、曲折性的体现;国防和军队改革的不断深入,一方面为突破传统大陆军保障体制模式准备了基础要素,另一方面也是现代联勤体制破茧成蝶的充分而必要的条件。
构建现代联勤体制,道路曲折,历程坎坷。组织大联勤试点,探索一体化联合保障之路,是建立现代联勤体制的一次较为曲折但却是十分有益的实践探索,也是当时军队指挥体制和领导管理体制不变条件下推进变革的无奈选择;从两种联勤体制并存到探索建立现代联勤体制,是建立现代联勤体制的必要过渡和基本前奏,为现代联勤体制的构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组建联勤保障部队,实行统分结合、通专两线,既是现代联勤体制构建的高潮阶段,也是推动中国人民解放军保障体制适应信息化局部战争要求的关键环节。从此,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保障体制开始进入三军联合保障、一体化保障的新阶段。
现代联勤体制特色鲜明,亮点纷呈。统分结合、通专两线的保障模式,符合联勤改革大方向,既能够发挥联勤优势,又兼顾军种特性,是一种较为现实、积极稳妥的选择;以联勤保障部队为龙头的力量配置,既便于打造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战略和战役支援保障的主体力量地位,又便于优化资源配置、统筹力量建设,实施公平公正、集约高效保障;实行指挥与建设管理相对分离,体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对现代联勤规律的科学把握,标志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保障体制的改革逐步走向成熟,是后勤保障体制改革的一种螺旋式上升。
当然,现代联勤体制从实践探索到平台搭建,只有很短的历史,其成效还有待跟随现代联勤保障实践作进一步检验。我们坚信,这种新的后勤保障模式必将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发展不断向前推进,实现全面优化。
本研究共收集到不同产地的蜘蛛抱蛋属植物19种104个样品(表1),植物新鲜叶片经变色硅胶迅速干燥后常温密封保存。样品由贵阳中医学院何顺志教授鉴定。其中17种引种栽培于贵阳中医学院,凭证标本存放于贵阳中医学院标本室。
中图分类号 :E297.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4883-(2019)01-0010-08
[作者简介] 农清华,国防大学联合勤务学院联合勤务指挥系讲师。
[责任编辑:刘向东]
标签:改革开放40论文; 年论文; 后勤保障体制论文; 保障体制改革论文; 国防大学联合勤务学院联合勤务指挥系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