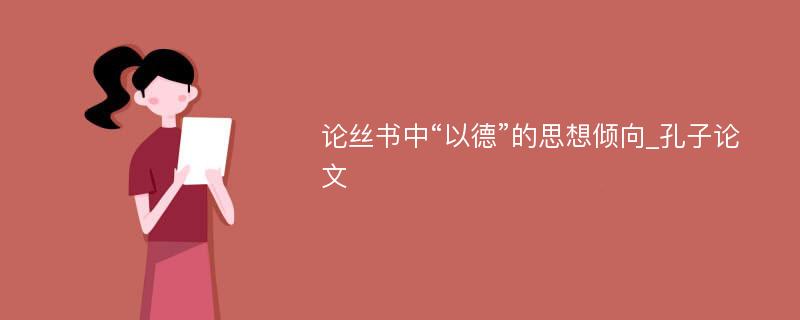
帛书《要》以德论《易》的思想倾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帛书论文,以德论文,倾向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4)02-0177-04 《要》篇在帛书《易传》中占有重要地位,出土时,它与《系辞》《衷》《缪和》《昭力》抄写在同一张帛上。从思想内涵上看,《要》最集中、最典型地体现了孔子的易学思想,通过它,人们可以看到孔子对《周易》的基本观点。 一、《要》与《论语》论《易》文本比较 现在人们研究孔子思想的主要依据是《论语》。根据《论语·述而》的记载,孔子曾经说过“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的话,说明孔子晚年充分认识到《周易》的价值,并对《周易》下了很大的功夫。帛书《要》的出土恰好印证了《论语》的记载。 从《要》的内涵方面看,孔子论《易》的主要倾向是重德义。《要》开篇不久便论及祝巫卜筮与《易》的关系,说明孔子并不否认《易》为卜筮之书。然而,《要》所重视的并非《易》之卜筮功能,故其文云“……无德,则不能知《易》,故君子尊之”。君子之所以重《易》,是因为君子重《易》之德义内涵,而非其他成分。《论语·子路》曰: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 “恒”为恒常意。“人而无恒,不可以做巫医”这句南国之人的言语,孔子认为说得极为正确,因为它将卜筮与人的品德联系在一起。此处孔子借南人之言谈恒德的重要。在孔子心目中,人无恒,就做不成巫医。《礼记·缁衣》云“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为卜筮’,古之遗言与?”这段话说明《论语》中孔子所说的“南人之言”是习语,盖古代卜筮之事,是由巫祝即神职人员掌管的,对这些人还有个人品质的要求,不仅仅是懂得卜筮的知识和技巧就能胜任的。“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是恒卦九三爻辞。《二三子问》中已经有关于它的论述,其说云“此言小人知善而弗为,攻(?)维而无止”,显然是以“恒”为善、为美德,人无善德善行,必然要有忧患或羞辱。由此看来,卜筮与人的德行密切相关,它具有目的性。《要》所云“无德,则不能知《易》”的观点,与孔子所重视的南人之言是一个意思。《论语·宪问》云: 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亦是做人必备的品德。孔子告诫学生做事要守本分,要按照礼的要求做,不要僭越,这种说法具有礼的内涵。因此曾子说“君子思不出其位”,是君子应该具有的品德。曾子所云与《大象传》相同。艮卦《大象传》云“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曾子言此,是对孔子的话进一步解释。《论语·泰伯》云“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子罕》云“牢曰:子云:‘吾不试,故艺’。”程树德《论语集释》引翟氏《考异》说“此与《子罕》篇‘牢曰’同例”。《论语》中的《泰伯》《子罕》《宪问》都有此说,可见孔子对此的重视。“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可以从标明人的社会地位的礼的角度说,亦可从利害关系的角度说。《孟子》有“位卑而言高,罪也”的观点,《中庸》有“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和“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的主张,与孔子的思想是一致的,都具有礼的内涵。先秦儒家的这些思想与《周易》联系在一起,最直接的根据就是曾子“君子思不出其位”。至于其与《大象传》相同,是因为孔子论《易》重德义的思想影响了孔门后学,《大象传》的突出特点就是以德论《易》。从文本现象上说,《要》并没有出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君子思不出其位”的话,但其论《易》的精髓就是重德义,这一点与《论语》论《易》是完全一致的。 二、从《要》看孔子论《易》“观其德义”的思想内涵 《要》在帛书《易传》中的自然排列位置处于《衷》之后,《缪和》之前,全篇大约二十四行。第一、二、三行全缺,第四、五、六行仅剩个别文字,第七、八行文字亦残缺多半,自第九行开始文字基本连缀成章。基于这种情况,《要》开端部分的内容人们无法确知。这里所做的,只能是大致地按内容进行分析。《要》的主要内容是强调“无德则不能知《易》”,这是孔门易学的核心。 《要》有部分内容通过孔子与子贡的对话,阐明孔子论《易》“观其德义”的主张。“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这段话的学术价值,在于证明孔子晚年确实倾心研《易》。《史记·孔子世家》和《田仲敬完世家》有与此相同的记载,《要》的出土使世人确认《史记》所言不诬。孔子为什么对《周易》感兴趣,通过他对子贡所提问题的解答,我们可以有清晰的认识。这一部分记载了孔子与子贡三段相互问答之言。第一段记载子贡以孔子以往所教弟子之言发问。孔子以往曾教育弟子,没有德行的人才趋向神灵,缺少智谋的人才精于卜筮。子贡对此很以为然。但令其困惑的是孔子何以晚年喜《易》。孔子的回答阐明他自己是言行一致的(所谓“言以榘方”)。“《尚书》多於”的“於”当通“疏”,《尚书》所记多有疏漏阙失[1](P134-138)。《周易》一直没有失传,其中有古之遗言,因此孔子才喜《易》。其喜《易》的原因并非在其尚筮之用。第二段子贡仍然引用孔子以前的教诲来提出问题。孔子曾说过“孙正行义,则人不惑”的话。子贡的疑问在于孔子对《周易》乐其辞,岂非用奇于人?“正”与“奇”是相反的概念,“孙正”与“用奇”是相反的行为。孔子认为子贡的责难是荒唐的,他指出《周易》可以纠正人偏颇的行为,引导人向善。最重要的是孔子指出文王与《周易》的关系,其意与通行本《系辞》相同,通行本《系辞下》云“《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两相对照,应该能够证明孔子对《周易》的看法。第三段对话云: 子贡曰:“夫子亦信其筮乎?”子曰:“吾百占而七十当,唯周梁山之占也,亦必从其多者而已矣。”子曰:“《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又仁者而义行之耳。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之史。史巫之筮,向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涂而殊归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后乎?”子贡的发问针对筮占而来,因为《周易》本为卜筮之书。孔子的回答并未回避这个问题。“吾百占而七十当”,说明孔子亦有过占筮的实践。周梁山之占是周初的一次占筮。梁山在周地,《史记·周本纪》记载古公亶父“去幽,度漆、沮,逾梁山,止于岐下”。有学者认为梁山之占是周文王的一次重大占筮[2](P61),孔子指出周梁山之占也是从占筮结果的多数得出结论。从孔子的言论看,占的次数越多,就越容易出现重叠的结果,因此,孔子对占筮的神秘性并不相信。正是因为这种理性的态度,孔子才会说“《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孔子认为《易》的应用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德义层次,这个层次由数进到德。包容了象数,但又不停留于象数,而是将其作理性与道德的提升。这也是孔子所达到的层次。第二个层次是史巫的层次。赞而不达于数,是巫的层次;数而不达于德,是史的层次。孔子阐明他自己虽然懂得史巫之筮的方法,但却与他们有不同的价值取向,“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涂而殊归者也”。君子依靠德行、仁义立身于世,反求诸已,不求诸人或具有神秘色彩的卜筮,这是孔子与史巫的本质区别。通行本《说卦》云“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意思与孔子所言相同,只不过在义理方面更加抽象化一些。《要》篇第三部分与第一部分内容是相互关联的,但在帛书中却被分隔开来,中间插入了第二部分的内容。李学勤先生认为是错简所致,这个看法应该是正确的[2](P62)。 《要》篇所论,前面孔子反复申说其论《易》重德义,后面则专门强调损益两卦。《要》篇记述孔子论损、益两卦,主要内容是:损益之道与四时;损益之道与天、地、人三才之道;损益之道与君道。损益之道上通天地之变,下至人情得失,可谓重要之极。孔子论损益之道,按照天地人的顺序进行。这一点与其他典籍的记载不同。《淮南子·人间》云“孔子读《易》,至损、益,未尝不愤然而叹,曰:‘益损者,其王者之事与’”,《说苑·敬慎》云“孔子读《易》,至于损益,则喟然而叹。子夏避席而问曰:‘夫子何为叹?’孔子曰:‘夫自损者益,自益者缺,吾是以叹也。’子夏曰:‘然则学者不可以益乎?’孔子曰:‘否,天之道,成者未尝得久也。……’”后面还有一些关于损益之道的论述。《孔子家语·六本》亦有相同记载。《淮南子·人间》与《说苑·敬慎》《孔子家语·六本》的内容有所不同,但其核心思想无异,突出的皆为人事的损益之道。 《要》篇论此二卦内涵的顺序是:先益卦,以春夏之时相配;后损卦,以秋冬之季相配。春天为万物萌发的季节,秋天是万物萧瑟的季节。故云“[益之]始也吉,其终也凶。损之始凶,其终也吉”。随着四季周而复始的流转,大地上的生物亦由生至盛至衰至败,萌生者必然走向衰败,衰败者必然走向新生,落实到人事上就是始吉终凶、始凶终吉。春夏秋冬的变化属于自然现象,本无所谓吉凶,但在这里,孔子将其与人事比附,才有吉凶。虽然表面上是在谈自然,但骨子里却有人间关怀在其中,否则人何来损益、何来吉凶?这样的损益之道,《要》篇认为可以观天地之变。这个天地之变是对四时变化的概括,反映了作者的天道观。由此天道观所描述的变化现象,抽象地可以概括为阴阳二气的交替变化。也就是《要》所描述的益卦对应春夏,损卦对应秋冬。春夏万物生长,秋冬万物衰亡。《要》对损益两卦的描述,与阴阳观念相关。至于《易》究竟是怎样道阴阳的,《要》篇孔子论损益之道提出了一种解释。就损益二卦与四时对应的观念看,益卦本身具有增益之义,孔颖达《正义》、朱熹《本义》都以增益释之。从益卦卦爻辞看,与四时中的春夏之季没有任何关系,故《要》篇中孔子将其与春夏两季相对应必然是后起的释读方式。从易学研究的历史来看,以阴阳观念解《易》,当发生于战国时代[3](P38)。我们所见的《周易》经文没有阴阳观念,春秋时期亦没有以阴阳解易的记载。《庄子·天下》篇中出现了“《易》以道阴阳”的观点,这是道家的易学观,也可以说是战国易学的一个特点。以阴阳观念解释事物的诸多变化,从史料记载看,始于西周末年,其中一种主要的说法是以阴阳二气说明气候的变化。后来又有老子,将阴阳作为哲学范畴,解释天地万物。《老子》四十二章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这里的阴阳,显然指阴阳二气,万物是由于阴阳二气的交和才产生出来。这种学说对战国时期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影响,尤其是《管子》中的阴阳说。《要》篇中损益二卦与四时对应的观念,与上述阴阳学说产生、发展的时代背景和思想渊源都是有关系的。已经有学者认为,《要》篇孔子论损益两卦,“其文字风格与前三部分不同,显系另有来源”[2](P62)。其实,不止是文字风格的不同,论述内容上亦另有来源。这里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孔子虽然重《易》之德义,但并未完全排斥筮占,他说“吾百占而七十当”,说明他对筮占也是懂得的。春秋以来的阴阳思想虽然在《论语》中没有出现,但是在与《易》相关的问题上,孔子运用阴阳观念解释一些人类生活现象,也不是绝对不可能。当然这仅仅是推测,还没有可靠的文献根据。另一种可能是孔门弟子在记录孔子言论时,根据自己的理解,将当时的一些观念揉合到孔子思想中,造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文本事实。那么,回过头来看孔子对损益二卦的论述,与之关系最密切的就是四时说。季节的转换与阴阳二气的盛衰有关,将这种观点与后面的天道和阴阳对应联系起来看,显然体现的是天道观,这一重意蕴是不容忽视的,它应该是战国时期思想融合的产物。《管子·形势解》说:“春者,阳气始上,故万物生;夏者,阳气毕上,故万物长;秋者,阴气始下,故万物收;冬者阴气毕下,故万物藏。故春夏生长,秋冬收藏,四时之节也。”《要》将益卦与春夏两季、与万物生长对应,损卦与秋冬两季、与万物衰老对应,与此非常相似,只是没有明确提出阴气阳气的观点,然而暗合阴阳二气说。所以这一段孔子关于损益之道的论述,应该对汉易的卦气说产生一定的影响。因为卦气说以八卦或六十四卦配四时、十二月、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突出的是六十四卦与阴阳消息、四季变化的关系,是一种系统的象数易学。《要》篇论损益二卦只是卦气说的苗头。至于《管子·乘马》所云“春秋冬夏,阴阳之推移也。时之长短,阴阳之利用也。日夜之易,阴阳之化也,然则阴阳正矣。虽不正,有余不可损,不足不可益也。天地莫之能损益也”。此处和《要》相似之处在于以四时与阴阳相配,以损益描述阴阳的彼此消长。而且在这段论述中,它将四时、阴阳、损益完整地联在一起,比《要》更系统、更全面。但是,在哲学思想取向上,二者并不相同。《要》篇在将损益两卦与四时对应之后,强调的是损益的相互转化,即益极必损,损极必益,而非《乘马》的“有余不可损,不足不可益”。这是因为《要》篇在承认天道阴阳的前提下,更加注重人的主体性,即落实到具体的人间事物上,人要发挥主观能动性。所以,在谈完损益与四季的关系之后,《要》立即回到六十四卦的吉凶之说上来。接下来,孔子云“损益之道,足以观天地之变,而君者之事已”。这是说通过损益二卦,可以观天地的变化。所谓损益之道,除了自然运行的规律,或者直接说春夏秋冬四季有规则的转换,是人的意志无法左右的,人应当遵循其法则外,孔子还讲了另外一层意思,就是物极必反,人应守中,处于中庸状态。这与阴极阳生、阳极阴生的自然现象有关,即《要》篇受自然规律启发,得出人类行事不可走极端的结论。人不能控制、改变自然法则,但却可以而且能够控制、改变自己的行为,使其朝着有利于自身的方向发展,这才是孔子论损益二卦的核心。如果这样看问题,那么孔子论损益二卦与四时相关的部分就不应将其孤立起来,而应该将它与《要》全篇贯穿在一起讨论。从“益之为卦也”至“故曰产”一段,毋庸置疑是在阐述天道自然变化。孔子说这段话有两重用意,一层是讲人应遵循自然法则,随时而变;另外一层就是讲人应该从自然变化中受到启发,这就是盛极而衰、物极必反,并以此为戒,在实际的行为中调整自己。总括一句话,就是人要努力达到顺时守中的修养境界,以期立于不败之地。这段话虽然未必为孔子所云,但与孔子的思想并不构成矛盾。 孔子论损益二卦的内涵亦是其德义说的一个体现,虽然其中有天道观的东西,而且可以说是以天道统人事,要求人类行事要遵守一定的自然规律。只是这里有一个现象要搞清楚,即孔子以损益配四时,究竟要说明什么问题?有的学者认为是要“观天地之变”,有的学者认为是要观“君者之事”。其实二者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观天地之变”的目的是观“君者之事”,如果没有人事,“观天地之变”就失去了目的性,亦非中国传统文化的性格。所谓儒家、道家、阴阳家的区别,主要在于其学说侧重点的不同,这种不同不容忽视,但也绝非互不相容,不可贯通。《要》篇孔子论损益二卦,应该是孔门后人在记述孔子论《易》言论时,吸纳了道家、阴阳家的天道自然的学说,将其融入孔子的易学思想所得的结果。从论损益二卦的内涵看,其中有与时偕行、人道贵谦的思想,归根结底,体现的还是一种忧患意识。从孔子论损益之道的文本顺序看,最先将损益二卦与四季相配,然后说明益始吉终凶,损始凶终吉。这里有对立面相互转化的辩证法因素。而后将体现天道的自然物象归结为阴阳;将体现地道的自然元素定性为柔刚;将体现人道的社会关系与家庭关系概括为上下。从孔子对天地人三才之道的概括性表述来看,显然与人类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认识和把握相关。天体运行对应于阴阳,与天文学知识有关;五行对应于柔刚,与人对大地物质属性给予人的感受有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应于上下,与人类社会组织形态有关。这三才之道并非源自六十四卦本身,而是属于《易传》系统,是《要》篇对《周易》经文的解释。 接着是关于阴阳、柔刚、上下的论述,《要》篇又指出随着四时的变化,万物也会产生不同情状,所以用八卦概括之,即八卦是对自然界万物的抽象化产物。进而说明《易》是为了体现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诸多现象而作,突出《易》的变易之义。后面所谓君道,孔子认为五官六府不足以将君应尽的职责包罗进去,五正所做之事亦不足以将君应为之事做到完善,而传世的诗书礼乐篇幅也不够,很难将其表达完整。如果不求教于古人的法度,就不能有顺达的辞令,不能实现达到善的道德意愿。《要》篇在记述孔子答子贡问时,提到《周易》“有古之遗言”,与此处的“古法”所指应一致,它是后人求善的依据。最终孔子指出杂多难以致知、致善,“能者由一求之,所谓得一而群毕者”,就是《易》之损益之道。 综上所述,从《要》篇的记载,人们可以发现,以德论《易》是孔子易学的核心思想。标签:孔子论文; 易经论文; 周易八卦论文; 阴阳学论文; 论语论文; 国学论文; 大象传论文; 子罕论文; 儒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