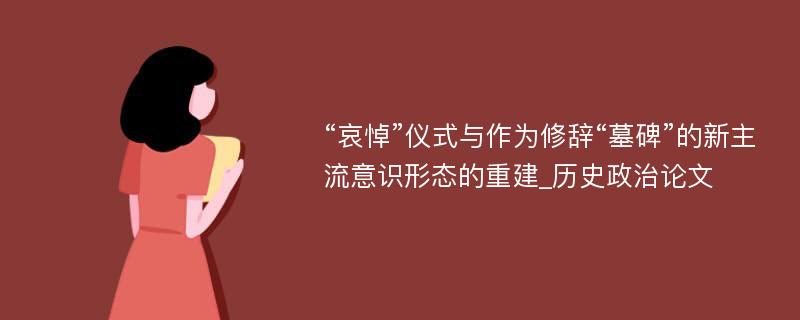
“哀悼”仪式与作为修辞的“墓碑”———种新主流意识形态的重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修辞论文,意识形态论文,墓碑论文,仪式论文,主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几年来,在中国大众文化的景观中,新主流意识形态的重建成为重要的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主流价值观就处在一种危机、无效和断裂的状态中,这尤其体现在外在的政治干预与自发的市场秩序之间的内在冲突上,从文化生产的角度则呈现为主旋律作品往往没有市场、拥有市场的作品又不承担“政治”功能,正如近期关于“反三俗”“限娱令”的争论,可以看出国家意识形态(精英的、道德化的)与大众文化(低俗化、庸俗化)之间的不协调。不过,这种政治/市场的不兼容已非常态,更为有趣的症候在于新世纪以来政治(威权、一党执政)与市场(自由竞争、多元化利益分割)的“双套车”越来越经常奏出和谐的主旋律,恰如中国崛起的基本事实就是强有力的政治调控和充分市场化的资源配置之间密切结合的产物。在这个意义上,既实现经济效益,又具有主流价值观功能的作品越来越多。
可以说,这种社会共识的积聚建立在双重前提之下,一方面,“外在的政治”已经从阶级政治、共产主义理想变成了一种依法治国背景下的民族复兴,爱国主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内核;另一方面,都市中产阶级被建构为和谐社会的和谐主体,也是中国经济崛起获益最多的群体。需要指出的是,在高房价、高物价的压迫下,“中产”面临着“被消失的”窘境,①在中国关于中产阶级的想象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话语事实,尤其是相比人口学意义上占据绝大多数的弱势群体来说。本文主要通过2008年以来国庆日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篮、重大灾害之后举行“全国哀悼日”以及近期的影视剧中“墓碑”被作为重要的文化修辞方式,来呈现当下主流意识形态的重建是通过一种悼亡仪式和国家对死者/旧有牺牲者的重新祭奠来完成的,最后再以《唐山大地震》为例来分析一种个人/家庭的创伤记忆如何被弥合的故事,这种给创伤记忆寻找伤口的工作实现了一种新主流意识形态与中产阶级主体之间的内在和解。
一 国庆日、哀悼仪式与“2008年”
自2008年以来每年的国庆日多了一项纪念仪式,就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与首都各届代表集体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篮,“深切缅怀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②这样如此隆重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篮的仪式此前并不常见,只是在特殊纪念日如纪念反法西斯战争时才偶然出现(更为经常的行为是清明时节各地政府组织大中学生举行烈士陵园扫墓活动)。在这个意义上,这种重新发明出来的国家哀悼仪式与10月1日国庆日结合起来,给国庆典礼赋予了一种新的政治文化含义,即国家通过对死者/“人民英雄”的祭奠/祭拜来告慰生者,通过凸显建国英烈的丰功伟绩来重塑合法性。人民英雄纪念碑作为天安门广场的中心,在中国政治空间中占据着格外重要的位置,其政治含义在于确认中国革命的历史合法性,如毛泽东主席所撰写的碑文:“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这既确立了中国革命的历史主体是“人民”,而且把新民主主义所缔造的“新中国”作为1840年以来追求民族/国家独立的产物。在此背景之下,人民英雄纪念碑毋庸置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图腾。有趣的问题在于,为什么在中国经济崛起的时代会需要一种悲情式的国家哀悼仪式来作为国庆大典的重头戏呢?或者说在取得如此辉煌的经济、社会成就的当下,为何需要采用政治危机时代的叙述策略,即通过重返艰难建国和付出巨大牺牲的时刻来获得一种想象性的政治认同呢?③
在一种回望的视野中,2008年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大悲大喜之年。年初南方遭遇的特大冰冻雨雪灾害,拉开了2008年多灾多难之年的序幕,接着5月遭受新中国成立以来震级最高的地震“5·12汶川特大地震”,6月华南、中南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9月山西襄汾县“9·8”溃坝事件。不仅仅如此,2008年还是多事之秋,如3月有西藏“3·14”,事件4月有奥运火炬海外传递受阻等,可以说,这一年充满了悲情色彩。与此同时,2008年还是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北京成功举办、“神舟七号”载人航天飞船成功飞行并实现中国宇航员首次太空行走,以及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重要时刻。所以说,这一年又是彰显“盛世中国”、“中国崛起”的年份。仅仅两年之后,中国经济就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戏剧性”地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从这个角度来看,2008年可谓“悲情中国”与“盛世中国”相互交织的一年。就在这种爱恨交织中,一种关于中国的国家认同和某种社会共识开始浮现,自然灾害(如大地震)与政治危机(如“藏独”破坏奥运圣火)反而激发、培育了中国民众尤其是青年一代的国家认同和爱国精神。在这个意义上,2008年具有重要的标志意义,是20世纪80年代后毛泽东时代国家认同获得重建的转折点。
“3·14”事件引起海外反华势力破坏奥运圣火传递,由此海外华人发起护卫奥运圣火的运动,如“4·19反对国际媒体恶意指责中国,支持北京2008奥运”的海外华人大游行,这些积极参与者很多都是“80后”留学生,他们从“‘西方中心论’的普世价值的迷雾中清醒过来,同时又不陷于盲目排外和自我封闭情绪”,被认为是“最全球化的一代,也是最爱国的一代”,④这些爱国运动使“80后”摆脱了“小皇帝、小公主”“独生子女一代是不负责任的一代”的恶名,第一次自发地表达出对于中国/国家身份的由衷认同。不久,这种海外留学生的爱国激情在“5·12汶川大地震”中被国内青年一代所继承,他们成为救灾志愿者的主力军。汶川大地震实现另外一种全民总动员,不管是政府调配一切资源全力救灾,还是中产阶级/普通市民踊跃捐款、献出大爱,在这一危机/危难时刻,官方/体制与民间/市场达成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少有的共识,有媒体惊呼“汶川震痛,痛出一个新中国”。⑤紧接着,8月盛大而华丽的奥运会完美落幕,超过百万的奥运志愿者被命名为“鸟巢一代”,出色地向世界展示了现代、包容、自信的中国青年一代。
正是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不久,国务院发布了为地震遇难者举行为期三天的“全国哀悼日”,这也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因重大公共灾害造成国民伤亡而设立的哀悼日,之前只有在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去世时才会举行全国哀悼活动,如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重要领袖逝世。这次汶川哀悼日采用了民间“头七”之日的方式,充分显示了新世纪以来“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和对传统民间伦理秩序的认同。在这一举国同悲的时刻,国家通过对无辜死难者的悼亡,来实现一种普通国民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内在结合。如果说人民英雄纪念碑是纪念那些1840年以来为民族独立、解放而献身的烈士/人民,那么汶川哀悼日所纪念的死难者则是普通的、无名的中国人,他们并非民族/国家的献身者,而只是不幸的遇难者,他们唯一可以共享的身份就是中国人。在这里,不管是向人民英雄纪念碑献花,还是举国哀悼灾难遇害者,都呈现了一种国家对于个体、生命的尊重,一种民族国家身份成为当下最为重要和有效的命名方式。于是,全国哀悼日也成为此后国家为重大公共灾害遇难者所举行的固定仪式,如2010年4月为青海玉树地震遇难者举行“全国哀悼日”、8月为甘肃省舟曲县特大泥石流灾害遇难者举行“全国哀悼日”。在这种举国哀悼的仪式中,国家及民族/国家的身份获得彰显,一种个人与国家的认同借助对死者的哀悼和祭奠来完成。
与此相关的政治文化事件是,就在2008年党和国家领导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篮两个月之后,隆重召开的“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官方把改革开放30周年的历史明确地书写为与20世纪所发生的辛亥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相并列的第三次革命,“改革开放这场新的伟大革命,引领中国人民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广阔道路,迎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⑥从而把20世纪现代中国/革命中国的“三次革命”实现了一种“通三统”,即“三次革命始终贯穿一个主题,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⑦,或者说“三次革命是递进式的超越”,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三次革命的共同主题”⑧,这就为把中国近现代历史重写为不断走向“复兴之路”的历程提供了内在的理论支持。而建立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基础上的历史论述在建国庆典中,又经常呈现为一种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剧,其中最著名的是1964年的《东方红》(庆祝新中国成立15周年)、1984年的《中国革命之歌》(庆祝新中国成立35周年)和2009年的《复兴之路》(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这三部作品都处理了1840年以来的中国近现代历史,却已然发生了重要的改写。
如果说《东方红》是从人民作为历史主体的角度来把近现代历史书写为一部反抗史、革命史,《中国革命之歌》凸显了中国近代所遭受的屈辱与诸多挫败,以一种失败的悲情来映衬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繁荣富强的话;那么《复兴之路》则采用一个国家/民族的视角来把近代史叙述为从国破家亡到国家崛起的历史,这是一段中华民族由辉煌灿烂因遭遇外辱(不是内部原因)而衰败再走向繁荣的伟大复兴之路。在这场盛大的舞台上,得以串联起每一个历史转折年代的固定修辞就是“土地”、“江山”、“家园”和“田野”,如开场字幕引用艾青的诗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序曲演唱《我的家园》、第一章是历史老人吟诵《山河祭》(1840年)、第三章“创业图”以歌曲《我们的田野》作为开始(1949年)、第四章“大潮曲”演唱的是《在希望的田野上》(1978年)等,可以说这些自然化的土地意向成为民族国家/中华民族认同的基本元素。在这样一个没有敌人和他者的舞台上,历史老人、被蹂躏的母亲、现代化/工业化的建设者(从20世纪50~70年代的工人、农民到90年代的打工者)成为不同时期承载民族国家叙述的主体。
二 作为修辞的“墓碑”
与国家在国庆日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篮以及为重大灾害遇难者举行哀悼仪式相似的是,近几年来在大众文化的影视剧中,也出现了一种以墓碑为重要修辞的论述策略。与哀悼日对当下遇难者祭奠不同,这些讲述革命历史故事中的墓碑,往往是一种事后追认,让曾经被遗忘或遭受屈辱的个人/英雄重新获得历史/体制的命名,这种墓碑式的表述已经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书写的症候。
2007年年底贺岁档放映的冯小刚导演、华谊兄弟制片的《集结号》是第一部使用“墓碑”作为修辞策略的电影。这部影片不仅改写了新世纪以来商业大片“叫座不叫好”的局面,而且创造一种商业与主旋律契合的典范。《集结号》讲述了一个“组织不可信”的故事,一种国家历史对于个人、小团体的欺骗和牺牲。其成功之处不在于重述革命英雄人物的故事,也没有使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常用的人性化、日常化的方式来书写英雄、模范及领袖人物,反而借用了80年代把革命历史荒诞化的方式来消解历史的政治性,却最终达成了一种对革命历史故事的重新认同和谅解。恰如《集结号》海报中的一句话“每一个牺牲都是永垂不朽的”,不再是用那些死去的无名战士来印证革命、战争及历史的倾轧与无情,而是通过对死去的无名英雄的重新确认,从中获得心灵的偿还和对那段历史的认可。影片结尾处,在战场上从没有吹起的集结号也在烈士墓碑前吹响,曾经的屈辱以及被遗忘的历史得到了铭记。这些被遗忘的牺牲者,终于获得了墓碑/纪念碑式的命名和烈士身份,通过上级领导说出的一句“你们受委屈了”的话来表达一种组织对个体的愧疚与追认,使得这些无名的英雄获得了名字和墓碑。这部电影与其说讲述的是为革命牺牲的故事,不如说是使这些无名的牺牲者重新获得历史命名的故事。因此,重新竖起的墓碑成为修补革命历史裂痕的有效修辞,而对50~70年代及其左翼历史的墓碑和纪念碑化既可以铭写“激情燃烧的岁月”,又可以化解历史中的创伤与不快。
2009年,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献礼片之外出现了一部小成本艺术电影《斗牛》,这部影片讲述了一个农民与一头牛的故事。尽管这部电影被导演管虎阐释为“一部绝境求生的故事”和“表现出人性的美”的电影,但不期然地同样讲述了历史向个人偿还记忆的故事。这部电影与另外两个文本形成了有趣的互文关系,一个是余华90年代初期的小说《活着》及同名电影,一个是90年代末期姜文的电影《鬼子来了》。《斗牛》虽然与这样两个文本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它们却处理了相似的问题。《斗牛》被放置在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国际支援中国抗日根据地一头荷兰奶牛,为受伤的战士提供营养,由于日军来袭,八路军只好把这头牛委托给当地老百姓保护。结果全村人被日军杀害,只有死里逃生的牛二为了信守村里与八路军签订的诺言,冒死周旋于日军、流民、土匪之间,最终与这头外国奶牛在山上相依为命。就如同小说《活着》中福贵在经历了中国现当代史中的诸多灾难(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全家人都死光之后,只剩下他和一头老牛相依为命地生活,面对20世纪诸多把个人与国家、民族相联系在一起的政治实践,个人、普通人的命运是脆弱和微不足道的,“活着”是最平凡也是最重要的道理。电影版《活着》基本上延续这种80年代形成的用平凡人生来对抗历史及政治暴力的典型命题,这种叙述借个人的名义完成了对外在的历史及政治的批判和拒绝。而姜文的《鬼子来了》也带有80年代的印痕,武工队给挂甲屯的村民放下两个俘虏之后就消失了,这种革命者的缺席(在影像上“我”也没有出现)无疑是为了批判那种被革命者动员的人民奋起反抗侵略者的革命故事。对于以马大三、五舅老爷、二脖子等为家族伦理秩序的人们来说,无论是游击队长还是村口炮楼的日本兵,都是外来的力量,或如五舅老爷的话“山上住的,水上来的,都招惹不起”。这种以村镇来隐喻中国的叙述方式来自于80年代把中国想象为“黄土地”式的封闭而传统的空间。对于挂甲屯的村民来说,他们不是启蒙视野下的庸众,也不是革命叙述中的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主体。从这个角度来说,《鬼子来了》恰好处理的是一个左翼叙述的困境,在外在的革命者缺席的情况下,以马大三为代表的“人民”能否自发自觉地占据某种历史的主体位置。《鬼子来了》在把“日本人”还原为“鬼子”的过程中,也是马大三从一个前现代主体变成独自拿起斧头向日本鬼子砍去的抵抗或革命主体的过程。这种觉醒不是来自外在的革命动员,而是一种自我觉醒的过程。最终作为拯救者的武工队并没有到来,更没能兑现诺言,也没有替百姓复仇,这无疑是对革命及左翼叙述的否定。
《斗牛》似乎也讲述了这样一个“活着”和被八路军“欺骗”的故事,牛二照顾八路军的奶牛,如同挂甲屯的村民,成了被遗忘的群体,作为拯救者的八路军迟迟没有到来,当初的许诺变成了一种谎言,而牛二信守诺言与其说是一种革命信仰的内在支撑,不如说是一种对民间伦理(签字画押)或个人欲望(牛二把奶牛作为新婚爱人的替代物)的坚持。但是与《活着》《鬼子来了》最大的不同在于,《斗牛》采取了《集结号》式的偿还历史的策略,在影片结尾处,匆匆赶往前线的解放军终于为保护荷兰奶牛的牛二写下了“二牛/牛二之墓”。墓碑再一次成为埋葬与承认的标志,尽管这是一个略显荒诞、随时都有可能被风刮走的墓碑。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说《活着》《鬼子来了》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一种左翼的实践及拯救,那么《斗牛》在呈现历史的荒诞与悲凉的同时,也得到了历史的偿还和铭记。
更为有趣的是,在2009年主旋律大片《建国大业》流水账式的历史叙述的间隙,依然使用了一个历史细节,就是毛泽东为因抢救饭菜而被敌机炸死的伙计鞠躬立碑,这是一个在历史中没有名字的小人物,却是影片中唯一一个获得墓碑的人,历史不是无名英雄的纪念碑,而是写着个人名字的墓碑。而2009年被广电总局评价为年度最佳电影的《十月围城》中,也使用了墓碑式的影像策略,当这些为了护卫孙中山而慷慨赴死的义士牺牲的时候,摄影机如上帝之手般在画面渐隐后抚摸过牺牲者/献祭者的身体,然后屏幕上显影出死者的姓名、籍贯及生卒年月,使得这些稗官野史中的无名小卒也获得了墓碑式的铭写。这种为历史中的无名者寻找名字的工作成为当下颇为有效的意识形态书写方式。如2010年10月纪念朝鲜战争爆发60周年,《南方周末》使用“每一个烈士都有名字”来报道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从2001年就开始的一项持续10年的工程,即为18.3108万志愿军烈士寻找名字⑨。
这些叙述策略也延续到2011年最为热播的两部电视剧《永不磨灭的番号》和新版《水浒传》中。前者是带有喜剧色彩的抗战剧,后者则是经典名著重拍,两部看似南辕北辙的电视剧却达成了相似的意识形态效果。《永不磨灭的番号》(北京华录百纳影视股份有限公司出品)是2011年口碑与收视率最好的抗战剧,这部剧播出之时即在北京卫视、安徽卫视接连创下收视率第一的佳绩,随后登陆央视一台。这部剧也被称为抗日版《水浒传》,如许多红色经典《林海雪原》《新儿女英雄传》《吕梁英雄传》《铁道游击队》等一样,都借用草莽英雄的传奇演义来讲述革命故事。如果说20世纪50~70年代的红色经典是把民间传奇故事革命化,那么新世纪以来新革命历史剧则是把革命叙述再度传奇化。《永不磨灭的番号》通过李大本事带领一群难兄难弟与被弱智化、定型化的日本鬼子周旋,在嬉笑怒骂中凸显兄弟情义和抗日救国的宏大主题,可以说是少有的带有喜剧色彩的抗战剧。李大本事带领游击队在掩护主力部队撤退的阻击战中几乎全军覆灭,他们临死前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够成为正规军,获得正式的命名和番号。几十年后烈士的遗骨被找到、重新安放在烈士陵园,这些没有番号的、非正规抗战部队终于获得了上级和组织的认可,成为中华民族(这一当下最为重要的、重塑的历史主体)的抗战英雄,从而最终实现了个人/英雄奉献、牺牲与民族大义/国家认同之间的和解。可以说,这与其说是没有名字的小人物、无名之辈向历史索回番号/命名的过程,不如说是当下的主流意识形态通过重新或再次命名、指认个人/英雄的崇高价值来获得政治认同的过程,只是这里的政治认同已经从革命变成了以中华民族为主体的国家叙事。
新版《水浒传》作为一部年度大戏,由郑晓龙任艺术总监,香港导演鞠觉亮执导,全剧共86集,投资约1.2亿元。自年初该剧在浙江卫视等地方频道播出,随后进入各大卫视,尽管在改编细节上存在着许多争议,但收视率还是一路飙升。《水浒传》并非仅仅是一部古典名著,而是与中国当代史密切相关的作品⑩。在20世纪50~70年代被解读为一部农民起义小说,而关于宋江是否是投降派的讨论曾经是“文化大革命”后期重要的思想文化论争,而80年代以来对于《水浒传》的改编也与这些特定意识形态解读形成了有趣的对话。如80年代电视剧《水浒传》只拍到宋江逼上梁山、108位好汉齐聚忠义厅,而有意回避宋江招安的段落。1998年再次重拍《水浒传》,这部剧的后半段则淋漓尽致地呈现了宋江带领众兄弟走向屈辱的招安之路的过程,梁山英雄成为皇权体制的受害者和牺牲品。2011年第三次重拍《水浒传》,最大的变化在于把这种反映农民起义的现实主义小说还原为一部神话故事。新版一开始就呈现了原著中“张天师祈禳瘟疫,洪太尉误走妖魔”的场景,从而把水泊梁山108位英雄造反的故事解释为天罡星、地煞星等“妖魔”重返人间“造孽”的故事。相比1998版李雪健扮演的宋江的唯唯诺诺、卑躬屈膝,新版中张涵予扮演的宋江则更为硬朗和足智多谋。在结尾处,宋江等虽然被奸人毒死,却受到皇帝的恩典,成为忠义之臣,这些被招安的“反贼”通过为朝廷效力而获得体制/秩序的最高嘉奖。在宋江被命名为“大英雄”(而不是投降派/造反派)的时刻,也是认证、确认这份命名的体制获得合法性的时刻。可以说,这部作品非常恰当地呈现了个人/英雄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的和解关系。因此,这是一部回归原著、还原历史的作品,同时也是一部重建历史记忆的作品。
就在这些历史中的牺牲者/无名者获得命名的时刻,另外一个群体却处在一种“无名”“无碑”的状态,如知名打工作家王十月的小说《无碑》讲述了作为“中国制造”主力军的“农民工”外出打工的故事。在大众传媒所参与建构的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公民社会话语中,以农民工为代表的弱势群体只能处在一种被遮蔽或者被救助的状态,而无法占据“主体/主人”的位置。而这种给历史中的牺牲者、殉难者、无名者找回名字的工作,从某种程度来说是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所建构的“个人是历史的人质”的批判的有效回应。在这里,不再是无名者的墓碑建构着一种民族国家的认同,而是通过把“个人”墓碑化来偿还历史/政治/权力对个人的戕害与倾轧(把抽象的政治/历史还原为一个个有名有姓的“个人”),在承认个人遭受宏大历史伤害的前提下实现一种和解。这种文化行为在完成一种纪念碑式书写的同时(铭刻),也在达成一种忘记死者的哀悼工作(埋葬)。可以说,这些个人的墓碑/纪念碑充当着铭刻/埋葬的双重功能,在标志曾经的牺牲与光荣历史的同时,也达成了历史的谅解。
三 伤口、记忆与主体
2010年暑假,冯小刚执导的《唐山大地震》没有意外地创造了中国电影票房的“奇观”(内地票房6.2亿元),不仅打破了《建国大业》刚刚在2009年刷新的国产电影最高票房纪录(4.4亿元),而且作为出资方的唐山市政府(地方政府)、华谊兄弟(民营公司)和中影集团(国有公司)实现了“多赢”效果:唐山市政府既营销/宣传了新唐山,又获得了文化政绩(这部电影在最高政府奖华表奖中收获颇丰),华谊兄弟也获得超额利润,而身兼政府/企业双重身份的中影集团也实现了经济和社会双重效益,把这些不同投资主体或者说社会资源聚合在一起的“牵线人”正是国家广电总局(11)。因此,从这部电影的生产机制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政府(文化/意识形态宣传)/资本、国有集团/民营企业如此“和谐”地共创、共享同一个“华丽”的舞台。这不仅改变了80年代中后期所形成的主旋律(政府投资)、娱乐片(商业片)、探索片(艺术电影)三足鼎立的电影生产格局,而且实现了主旋律与新世纪以来商业大片的完美嫁接,可以说是《集结号》之后又一部“主流大片/主流电影”(12)的典范之作。
如果参照新世纪以来讲述“泥腿子将军”的新革命历史剧和“无名英雄”的谍战故事,分别对应着当下的双重主体——开疆扩土、勇战沙场的“成功者”(“这个时代最成功的CEO”)和隐忍的、对职业无比忠诚的、有教养的中产阶级(“潜伏在办公室”),那么《集结号》和《唐山大地震》与此不同,不仅没有出现如此正面的英雄,反而呈现了个人在历史中的委屈、创伤和伤口。也就是说,无论是解放战争时期或50~70年代,还是唐山大地震之后所开启的改革开放的时代,都不是充满怀旧的“激情燃烧的岁月”或者怀着笃定信仰而潜伏敌营的惊险生活,而是如《集结号》中失去了身份/档案的抗敌英雄受到种种怀疑和误解以及如《唐山大地震》中忍受亲人离丧而内心愧疚的苦情母亲独自背负历史之痛。从某种意义上说,谷子地和元妮都处在相似的位置上,他们都是个人困境、历史苦难的承载者,同时也是被放逐在家庭秩序之外的人。不过,这种“落难公子”和“苦情母亲”的形象往往出现在社会转折和危机的时刻,发挥着召唤观众一起共渡难关(“分享艰难”)的意识形态效应。正如七八十年代之交的右派故事(电影《牧马人》《天云山传奇》《芙蓉镇》等)以及八九十年代出现的“苦情妈妈”(台湾电影《妈妈,再爱我一次》、电视剧《渴望》和90年代初期的苦情主旋律《焦裕禄》《蒋筑英》等)都成为各自时代最为有效的意识形态实践。如果说右派故事以受害者的身份把50~70年代叙述为遭受迫害的历史,仿佛那个时代就是男性/知识分子的内在创伤,那么苦情母亲则充分回应了八九十年代之交的社会悲情,把一种社会创伤投射到永远伟大的大地母亲身上。有趣的是,在这样一个和平崛起、走向复兴之路的时代(即使全球遭遇金融危机,风景也是这边独好),《唐山大地震》为什么依然需要使用苦情母亲来获得意识形态整合呢?
这部电影改编自加拿大华人女作家张翎的中篇小说《余震》,这篇小说讲述了经历唐山大地震的女作家小灯(小登)在震后/“余震”中治愈心灵创伤的故事。小说以笔记/日记的形式呈现了小灯接受心理治疗的过程,中间穿插着小灯关于过去历史的记忆,但是记忆经常变得“模糊”或被“生生切断”:“小登的记忆也是在这里被生生切断,成为一片空白。但空白也不是全然的空白,还有一些隐隐约约的尘粒。在中间飞舞闪烁,如同旧式电影胶片片头和片尾部分。后来小登努力想把这些尘粒收集起来,填补这一段的缺失,却一直劳而无益——那是后话。”(12)除了地震中母亲选择救弟弟的决定给小灯造成了巨大创伤,此后还经历继父性骚扰、丈夫外遇、女儿离家出走等一系列伤害,不仅留下了头疼病,而且留下了心灵创伤。如果按照小灯的说法,“余震”给自己身体留下的创伤/症状是一种“来得毫无预兆,几乎完全没有过度”的“无名头痛”(“一分钟之前还是一个各种感觉完全正常的人,一分钟之后可能已经疼得手脚蜷曲,甚至丧失行动能力”),而心理医生所提供的治疗方式则是给这种“无名头痛”找到具象化的替代物。在催眠中,小灯说出了自己看到的“场景”,就是一扇又一扇“上面盖满了土,像棉绒一样厚的尘土”的窗,可是“最后一扇”却怎么也推不开,因为这是一扇被“铁锈”锈住的窗。于是,医生告诉小灯,“有一些事,有一些情绪,像长年堆积的垃圾,堵截了你正常的感觉流通管道。那一扇窗,记得吗?那最后的一扇窗,堵住了你的一切感觉。哪一天,你把那扇窗推开了,你能够哭了,你的病就好了”。因此,治愈头疼的唯一方式就是“除锈”工作。
这种被锈住的、被堵塞的记忆,就是唐山大地震中母亲抛弃自己的时刻。小灯被治愈的时刻,就是回到地震所在地唐山,看到母亲和弟弟的孩子生活在一起的场景,这座在小灯心中永远放不下的“墓碑”终于在她回到唐山看到母亲的时候获得释怀。或者说这种回归母体的行为终于打开了锈住的铁窗,心结一下子就被解开了。而小灯的职业是写作(作者的自指,弗洛伊德意义上的神经官能症患者),写作也是帮助其治疗的方式,一种通过书写来偿还记忆的过程。小说结束于小灯被治愈的时刻,也就是终于“推开了那扇窗”。在这个意义上,这是一个关于记忆、创伤以及治愈创伤的故事。电影把小说中以小灯为主的叙述转移为母亲与女儿的双线叙事把小灯治愈地震创伤的故事转移为母亲怀着愧疚之情含辛茹苦地抚养儿子长大的故事。相同的是女性再次成为小说、电影中灾难、创伤、困境的承载者,不同的是电影中的单亲母亲取代小说中的女作家/某种意义上的独立女性成为苦情主角(先是地震中失去丈夫和女儿,后是遭遇下岗)。而且电影比小说更为具象化地把1976年到当下的历史书写为一部改革开放30年的变迁史。小说和电影都把唐山大地震与毛泽东逝世并置在一起,使得1976年作为社会转折的意味更为明确,就是用个人/家庭创伤来指涉七八十年代之交的政治、社会创伤,或者说把一种政治地震转喻为一种个人/家庭的伦理故事。这是一个遭受自然/政治“双重地震”的时刻,也是“双重父亲”死亡的时刻。父亲死亡之后,“大地母亲”和充满怨怼的女儿开始各自的生命历程,女性成为历史之痛的承载者和受害者。有趣的是,这些受害的女性在影片中并没有以受害者的身份出现,反而更像是施害者,如小说中患有精神病的小灯伤害了周围所有的亲人。母亲不仅是地震的幸存者,而且也是遭受下岗并“自主创业”的女工,这符合“苦情母亲”遭受一切自然与社会灾难的叙述成规,可是母亲在影片中却如同带有原罪不断愧疚的“施害者”(为什么“全家就我一个好好的?”)。母亲一方面承载了社会及历史的苦难,另一方面又把这份苦难转移为一份深深的愧疚,似乎这一切都是“她自己”造成的。
在这个意义上,推不开的窗、被锈住的历史、被堵截的记忆就成为七八十年代作为历史断裂的表征,前30年/毛泽东时代就“像长年堆积的垃圾,堵截了你正常的感觉流通管道”,而此刻小说创作和电影放映的时代则是疏通管道、推开被锈住的窗的过程,正如心理医生的“忠告”:“小灯,以后再见到这些窗户,就提醒自己,除锈,除锈,一定要除锈。记住,每一次都这样提醒自己。每一次。”这种意识形态的“除锈”工作与其说打开了被阻塞的记忆,不如说给这30年历史中出现的“无名头痛”寻找到一个原罪式的根源。正如心理医生沃尔佛在小灯说出“铁锈”之后“抚案而起,连说‘好极了,好极了’”,因为这就是“无名头痛”的“病根”。在“无名头痛”获得“命名”和指认之后,接下来小灯要做的就是“除锈”了,或者说一旦找到“精神病根”,或者说说服病人接受这个“病根”,所谓“无名头痛”也就被治愈了。因此,与其说“锈住的”历史造成了小灯此后的“无名头痛”,不如说这部文本的意识形态功能恰好在于给“无名头痛”寻找到一个“病根”,一个早就存在的旧伤疤。之所以要重新启用这处旧伤疤,是因为今天,或者说“震后”余生的幸存者,终于找到了治愈旧伤疤的方法。从这个角度来说,小说及电影与其说是为了除去“被锈住”的历史,不如说恰好完成了重新把前30年“锈住”的过程。
电影开始于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结束于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把两次地震作为32年历史变迁的标志,仿佛改革开放的历史是从一次地震到另一次地震。如果说1976年在自然/政治双重地震/浩劫之下,中国开始了新时期的艰难转折和阵痛,那么2008年这一悲喜交加之年,却成为印证中国崛起和中国认同的重要时刻。同样是地震,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具有完全不同的含义。唐山大地震一方面被作为伟人陨落的征兆,另一方面也被作为那个时代的悲剧(不仅是天灾,也是人祸(14)),而汶川大地震却实现了国家紧急动员与民间志愿救援的结合。正如冯小刚坦言,他在2007年改编剧本陷入困境之时,不知道该如何安排电影结尾处姐弟俩的相遇,汶川地震发生了之后,导演找到了结尾的方式,在这样一个全民动员的时刻,姐弟俩以志愿者的身份相遇在汶川救灾现场,地震成为姐弟俩重逢的空间,小登内心30年的积怨也终于释怀。
有趣的是,此时的小登和小达作为自愿参与汶川救灾的志愿者,已拥有清晰的中产阶级身份。于是,30年的历史被浓缩为残疾人小达由辍学打工变成开宝马的新富人,以及小灯由怀孕退学到成为旅居海外的中产阶级家庭主妇(在花园中浇花)的过程,也就是说,通过30年之后的“人生成功”与“大国崛起”的并置来化解七八十年代之交的“余震”。如果说《唐山大地震》以相当简化的方式书写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那么影片主要呈现了从工人阶级职工家庭的毁灭(震前的市井空间也是一个原乡式的社区空间)到中产阶级核心家庭(彼此分离、独立的家庭内景)的重建。影片选用大量的中景和室内场景,试图把故事封闭在家庭内部,也正是这种中产阶级核心家庭(完美的三口之家)成为化解历史积怨的前提。在这里,意识形态的“除锈”功能不仅再一次把“故事所讲述的年代”(七八十年代之交)书写为历史/个人的伤痕/创伤时刻(被锈住的窗),而且更重要的是把“讲述故事的年代”叙述为一种化解积怨、家人重逢的时代。与《集结号》相似,在《唐山大地震》的结尾处,一座纪念遇难者同胞的墓碑墙建成,片尾曲是王菲演唱的《心经》(歌词为《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原文),在超度24万唐山大地震罹难者灵魂的同时,也抚慰着“余震”中幸存者的内心。巨型墓碑上清晰地刻着密密麻麻遇难者的名字,仿佛1976年的遇难者直到影片播出的这一刻才最终获得命名而安息。
从这个角度来说,冯小刚式的主流影片以不同于新革命历史剧的方式完成一种对革命历史及当代史的重述,为人们揭开历史的纠结或死结,使得历史断裂处的伤口能够痊愈。在这个意义上,虽然《唐山大地震》对原小说做了重要的改编,但其意识形态功能却是相似的,正如《余震》的结尾,小灯(小登)终于推开那扇被锈住的窗。虽然淤积了如此多的困难和痼疾,但是在当下的时刻、在放映影片的时代纠缠在人们心中的那份愧疚也和解了。在这个意义上,冯小刚的这两部电影承担着双重功能,一方面是呈现历史的伤口,另一方面或更重要的是进行治愈伤口的工作,从而使得革命/当代史与当下作为主流社会主体的中产阶级终于可以达成“谅解备忘录”。
注释:
①《中国新闻周刊》2010年第3期策划了《“被消失”的中产》的专题(2010年1月18日),讲述“不再中产”的故事:“中国中产阶层向上流动困难,大部分向下沉沦为中下产,中产的后备军成长堪忧,难以补充这个阶层,中产阶层壮大之路越走越艰难。”而《南方人物周刊》(总第199期)也策划了一个《80后失梦的一代》的专题(2010年2月6日),讲述这些准中产阶级主体“逃离北上广,回归体制内”的“梦想难以照进现实”的处境。可以说,这是一个公民获得命名的时代,也是一个中产阶级“人人自危”的时代。
②《党和国家领导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篮》,中国网络电视台,2010年10月1日,http://news.cntv.cn/china/20101001/101128.shtml。
③如戴锦华在《消费记忆与突围表演》中对八九十年代之交突然涌现大量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主旋律的分析,“创造一套定期重演,以重现国家初创时期的‘创伤情境’的民族叙事,以便使国家回到一个特殊的时刻(刚刚建立自己的国家),一个决定民族命运的关头。它不仅是一种‘再确认’,而且是在不断的重述中重返那一艰难时刻,‘藉此来定期地重新召唤国家创始初期的那股力量’”,以度过八九十年代的政治危机(戴锦华:《隐形书写——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第83页)。
④《“四月青年”的历史使命》,《中国青年报》,2008年10月20日,http://news.xinhuanet.com/theory/2008-10/20/content_10221407.htm。
⑤南方周末编辑部:《汶川震痛,痛出一个新中国》,《南方周末》,2008年5月22日,http://www.infzm.com/content/12439。
⑥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8年12月19日,http://cpc.people.com.cn/GB/64093/64094/8544901.html。
⑦王宜秋:《中华民族复兴的三次伟大革命》,《红旗文稿》,2009年12月12日,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4411668/2725/93/80/4_1.html。
⑧齐卫平:《“三次革命”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光明日报》,2009年2月11日,http://news.xinhuanet.com/theory/2009-02/11/content_10798206.htm。
⑨秦轩:《每一个烈士都有名字——寻找18.3108万抗美援朝亡灵》,《南方周末》,2010年10月28日,http://www.infzm.com/content/51859/1。
⑩戴锦华:《重写红色经典》,陈平原、山口守编《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新世纪出版社,2003,第531~538页。
(11)从媒体报道中得知《唐山大地震》最初由唐山市委书记创意,广电总局牵头、落实,集合华谊兄弟(冯小刚)、中影集团来投资拍摄这部影片,其投资比例为54%、40%、10%。《〈唐山大地震〉:一次主流价值观的主题策划》,《三联生活周刊》2010年第29期,http://ent.sina.com.cn/m/2010-07-16/19463019747.shtml。
(12)“主流大片/主流电影”是指以《集结号》《建国大业》《十月围城》《唐山大地震》《建党伟业》等为代表的主旋律商业大片,这些电影打破了自2002年《英雄》以来始终伴随着古装大片“叫座不叫好”的怪圈。关于“主流大片/主流电影”的讨论开始于2006年(参见贾磊磊《中国主流电影的认同机制问题》,《电影新作》2006年第1期;饶曙光:《改革开放30年与中国主流电影建构》,《文艺研究》2009年第1期;张法、王莉莉:《“主流电影”:歧义下的中国电影学走向》,《文艺争鸣》2009年第5期等),尤其是2007年1月在全国电影工作会议上,广电总局领导提出要积极发展主流大片。主流大片的意义在于中国电影终于可以像好莱坞大片那样既能承载美国主流价值观,又能取得商业上的成功。这不仅在于革命历史故事找到了某种有效讲述的可能,而且在于七八十年代之交所出现的以革命历史故事为代表的左翼讲述和对左翼文化的否定而开启的改革开放的意识形态叙述之间的矛盾、裂隙获得了某种整合,或想象性的解决。在这个意义上,主旋律已经失去了20世纪80年代的含义,取而代之的是主流大片的命名。
(13)本文中的小说引文皆来自张翎著《余震》,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0。
(14)“唐山大地震”因瞒报、救灾不力,而被作为与反右、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大饥荒以及“文化大革命”中的暴力相并列的控诉毛泽东时代的民族灾难,直到最近还有一部纪录片《掩埋》讲述唐山大地震震前曾被准确预测而被掩盖的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