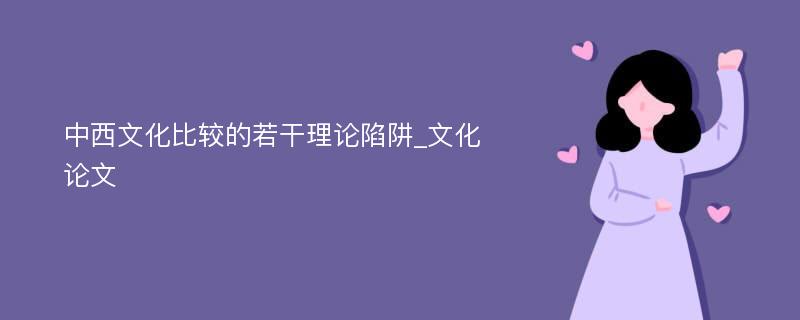
中西文化比较的若干理论陷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西文化论文,陷阱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310(2013)-10-0086-07
一 引言
1993-1994年间,季羡林先生发表一组文章,对天人合一作了“新解”。大意说,西方哲学的思维模式是分析式的,故以自然为敌,所以天人对立;东方则是综合式的,故以自然为友,所以天人合一。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西方不亮东方亮。方今之时,环境危机有目共睹,西方已经没落,人类希望在东方。以前之“拿来主义”就不对,我们现在应当是“送去主义”。①
季老先生之登高一呼,学界是否应者云集,不得而知。但有一点绝对可以肯定,老先生因其高论俨然成为东方文化或中国文化的一面旗帜。蹊跷之处在于,我们的文化比较,难道最终就是为了证明中国文化之高明?为什么从事文化比较之初,允诺要摆脱文化优劣论的圈套,要等量齐观平心若镜,但最终得出的却是文化优劣论的结论?
假如我们翻阅一下国内林林总总的《中国文化概论》之类的书籍、或者再费点气力,翻检一下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就会发现季老先生的“新解”一点也不“新”,甚至很“旧”了。既然结论如此陈旧,论者为何还以为“新”?既然中西文化比较之结论如此单调,为什么中国学人一个世纪以来乐此不疲?中西文化比较之背后,有着怎样的思维陷阱,以至于我们深陷其中而不自知?
二 中西对立
凡“谈东说西”之人,都给我们留下这样一个印象,即世界除了西方以外就是东方。这个西方是秉承希腊的西方还是秉承希伯来的西方,抑或二者兼而有之,这都因人而异。不因人而异的是,这个东方一般都是或主要是指中国。当然,比较研究者也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其他文化存在,但好像都甚无足观。这是上世纪90年代我国学者的断言:
按照全世界人类文化以往的成绩而论,现在文化便只有西方欧洲文化和东方中国文化两大系列,源远流长,成为人类文化的两大主干。[1]
中西美学是最为古老、最具特色而至今仍最有影响和活力的两大思想体系。[2]
我们且让历史后退50年,回到民国时期,钱穆先生笔下也有几乎一模一样的话:
若照全世界人类文化以往成绩而论,便只有西方欧洲文化和东方中国文化两大系列,算得源远流长,直到现在,成为人类文化的两大主干。[3]
再向前追溯50年,回到晚清,看看“开眼看世界”的启蒙先驱如何看待中西:
黄白智,红黑愚;黄白主,红黑奴;黄白萃,红黑散。(唐才常《各国种类考》)
于全世界之中,银色之人种横绝地球,而金色之人种尤居多数,是黄白二物据有全世界。(康有为《大同书》)
彼夫印度之不昌,限于种也。凡黑色、红色、棕色之种人,其血管中之微生物,与其脑之角度,皆视白人相去悬殊。惟黄之与白,殆不甚远。故白人所能之事,黄人无不能者。日本之规肖西法,其明效也。日本之种,本出于我国。(梁启超《论中国之将强》)
撇开有些语句中的种族歧视因素不论,姑且假定种族歧视是白种人的事。横跨百年的这些语句的共同主题是:只有中西才处于同一个重量级,其余均不足挂齿。这类文字极易令人想起“青梅煮酒论英雄”这出戏中,曹操对刘备所说的那句话:“天下英雄,唯明公与操耳。”差别只在于,这句话现在不是“曹操”说的,而是“刘备”说的。
《三国演义》没有写当年孙权、袁绍等人听到曹操的话是怎么个反应,当然我们更无从知道,假如此语出自刘备之口会如何。但完全可以确定的是,假如印度、拉美、伊斯兰等世界听了我们的这种说法,心里会很不舒服,如果我们会设身处地为他们想。
“比较的规模决定着比较的性质,当然也决定着比较的结果。”[4]文化人类学告诉我们,人类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思维习惯,就是二元对立(dichotomy)。②假如我们认定只有中西之间才值得比较,那么,得出中国如此西方如彼之类的结论就是极其自然而然之事了。再加上1840年以来的历史扰攘,我们以中西对立之思维模式来从事文化比较,就基本成了定局。
我们的文化比较基本上都是“中西对立”这个模子套出来的。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如此西方如彼,因为我们的思维模式认定,中国如此西方必定如彼。③如有学者在对史前社会研究之后,提出了以下两个命题:1.史前中国人的食物以植物为主,而西方人则以肉食为主。所以中国人对自然是亲和的态度,而西方人则与自然对立;2.欧洲人偏重于用左脑进行思维,中国人偏重于用大脑两半球的平衡作用进行思维。故欧洲科学发达,中国审美发达;西方人在思维方式和心理性格上有一种男性倾向,中国人则有一定的女性偏向。[5]
“一阴一阳之谓道”,中西在这个概括中恰好占据了阴阳两极。我们无法知道其他文化地域在“植食”与“肉食”、“女性”与“男性”这样的二元对立中又处于一个怎样的位置?当然更无法知道,“植食”和“肉食”和性格有什么关系,也许对于狼和羊来说是如此吧。这个例子也许可以提醒我们注意,中西对立的思维模式会带领我们走多远?
三 一言以蔽之
许多中西比较,都仿佛在以一种上帝口吻说话,仿佛一下子就看到了民族的骨子里面,一下子就看出了“民族精神”,仿佛天人对立就是西方思想不可摆脱的宿命,而天人合一则是中华文化的不二法门。
假如我们扪心自问,我们到底对西方了解多少,也许我们就不会那么言之凿凿了。正如一位艺术史学者所说:“把欧洲的艺术看作是一个单一的整体,简直就是语言的滥用,因为单要弄清欧洲当时有多少国家就非易事一桩。”[6]既然连欧洲有多少民族国家都不好弄清,我们又哪来如此胆量和勇气谈东说西?
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对于《诗经》中的305篇来说,是否“思无邪”是一回事,是否能“一言以蔽之”是另一回事。如果我们回顾一下近代以来中西文化比较,我们就会发现,说法虽然林林总总,却都有一种“一言以蔽之”雄心壮志,仿佛中国文化或西方文化都可以用一个词概括似的。这类概括就像“无商不奸”、“无官不贪”、“男人都是好色的”、“女人啊,你的名字就叫脆弱!”一样,虽然流行或正因为其流行,我们最好反问一句:能否“一言以蔽之”?许倬云先生曾说:
中国人在讨论西方文化时,常常笼笼统统以“西方”二字,概括一切,忽略了欧美地区文化内涵的复杂性,也无视于西方世界在近百年来,本身经历的种种变化。[7]
假如我们顾及西方文化在地域和历史方面的多样性,我们自然会问自己,谁是“西方”?也可以接着问,谁是“中国”?
然而,这样的问题,我们是从来不问的。正因为不问,所以我们在文化比较之前,首先已经进行了一系列的“打包处理”。比如新儒家所从事的东西文化比较,究其实只是中西比较;中西比较里的所谓中国文化,其实是汉文化;汉文化,其实又只是儒家文化;儒家,也仅仅是思孟一系;思孟一系的儒家,又更多偏爱心学一脉。我们且舍去汉文化之多元性不论,且不管曾与儒学敌对的学派会怎么想,也暂时不论儒学内部纷争,我们只需要问一下自己,把汉文化等同于中国文化,其他兄弟民族如何想?我们的这类概括里面,是否有汉族中心主义之嫌?梁文道曾提醒我们,别忘了,汉族也是一个民族。[8]
而且,从逻辑上讲,没有天人对立的痛楚经验,没有天人二分的理性分析,又何来天人合一?陈启云先生曾说:
中国思想家常说:“人我两忘”,“物我两忘”、“事理无碍”、“知行合一”、“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说的乃是高悬的理想,并不表示他们心中没有人我、物我、事理、知行、天人之分的观念。正是因为他们有人与我、物与我、事与理、知与行、天与人之间分离分割的观念,才会产生把二者“合一”的理想。如果本来是“同一”的,便无须高悬“合一”为理想了。[9]
遗憾的是,以“天人合一/天人对立”这组二元对立来对中西文化“一言以蔽之”的学者们,从不提及中国古代对自然的大规模征服,[10]也很少谈及中国哲学里的源远流长的“天人之争”,更很少谈及其他民族文化或哲学里的天人合一。④
事实上,天人之争是人类哲学的永恒课题。[11]天人二分乃至对立的痛楚体认,大致从人类诞生之时就会有了。否则,人之自我意识从何而来?换而言之,正如婴孩之成长必然涉及“欲”“矩”之冲突,人类文明永远面临着征服自然与敬畏自然、天道与人道之类的矛盾。能如孔圣人一般“从心所欲不逾矩”,当然最好,但是在大多数人心里“欲”“矩”之冲突,还是结结实实地存在着。更何况,孔圣人只是说他“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既如此,我们又如何将冲突一面划给西方,把和谐一方独属中国?
假如我们非得用“天人合一/天人对立”这组二元对立来对中西文化“一言以蔽之”,那么,至少犯了两种谬误:
其一,“强人政策”。杜维明先生曾说:“在西方学术界,特别是在比较文化研究领域,有一种大家都应该回避的禁忌,即‘强人政策’。具体地讲,就是为了加强我们对自己的文化的信念,加强我们自己的文化意识,乃至对自己文化的感受,我们就用我们文化中的精英来同其他文化(特别是敌对文化)中的侏儒来比高低。”[12]假如说鲁迅先生全面否定中国文化,是“反用”了这种强人政策的话,那么,文化民族主义往往是“正用”这种强人政策。
其二,“历史为逻辑让路”。事实上,我们的大部分文化比较研究,都是结论在先,然后去挑选对自己有利的证据。对于与此相悖的证据,要么视而不见,要么干脆没有见过。以此路数从事文化比较,用俗话说,其实是举例说明;用中国古语说,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套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则是“历史为逻辑让路”,虽然声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在逻辑学领域,上述两种谬误其实是一种逻辑谬误,即“遮盖论据”(suppressed evidence)。这种谬误,常常有意去遮盖或无意中忽略对结论不利的论据,使人误以为结论确凿。[13]
四 民族主义
笔者曾区分了“文化”(culture)一词的三种用法:
1.古典时期的隐喻用法,意为教养。culture的词源义是耕作,隐喻义是教养。农人借“cultured”一词,瞧不起非农人。Culture一词里所蕴含的本族中心主义,与古代汉语“文”或“文化”一词所蕴涵的华夷之辨,毫无二致。
2.现代时期的民族主义用法,意为民族心性。这是德国人的发明。1800年前后,相对于英法两国,德国政治上之四分五裂及经济之落后,使德国人产生了强烈的“认同危机和不充实感”,他们系统发展了用以彰显民族精神或民族特质的文化概念,以克服民族心理危机,并从而和英法对抗。
3.现代时期的文化人类学用法,旨在把所谓的“原始人”当人看,旨在寻求关于人的知识。文化人类学用法和民族主义用法的区别在于:前者旨在走出种族中心主义,旨在寻求人类普遍知识,故而其目光是“向外的”,热衷于其他种族的生活方式,尤其热衷于所谓的“原始人”生活方式;后者旨在寻找民族身份,在于提高民族自尊心,故而其目光是“向内的”,热衷于本族的生活方式,更热衷于本族的独特的民族精神。[14]
可以说,三种用法在中国当代都有,只是分量不同而已。华夷之辨意义上的“文化”用法,虽然伴随着中国之进入现代,早已上不了台面,但在我们的潜意识里,还是隐隐约约地存在着一点半点的。不少朋友或同事在日常言谈中,对有色人种或少数民族的那丝不屑,也许就说明我们要克服这类顽疾。文化人类学在中国一直叫作“民俗学”,可见“文化”一词的人类学用法的板凳地位。
至于“文化”一词的民族主义用法,在现代中国则蔚为大观。由于我们热衷于中西比较的原因,与德国当时没有什么区别。冯友兰先生1922年说过这样一段话:
我说中国人现在有兴趣之比较文化之原因,不在理论方面,而在行为方面;其目的不在追究以往,而在预测将来。因为中国民族,从出世以来,轰轰烈烈,从未遇见敌手。现在他忽逢劲敌,对于他自己的前途,很无把握。所以急于把他自己既往的成绩,及他敌人既往的成绩,比较一下。比较的目的,是看自己的能力,究竟够不够。这一仗是不是能保必胜。好像秀才候榜,对于中不中毫无把握,只管把自己的文章,反复细看,与人家的文章,反复比较。若是他中不中的命运,已经确定,那他就只顾享那中后的荣华,或尝那不中后的悲哀,再也不把自己的文章,与人家的文章反复比较了。[15]
这种“秀才候榜”的不安与焦虑,使得我们的“文化比较”从一开始就被“文化较量”意识支配,或者干脆就变成了文化较量,而不是平心静气地审视东西。一旦文化比较蜕变成文化较量,那么,在中西对立的框架里展开比较,以“一言以蔽之”的气概去探讨国民性或民族精神,就是自然而然之事了。所以,文化比较学者虽也想固守等量齐观平心若境之律例,最终却无法摆脱文化优劣论之圈套。
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法国学者Del Vecchio说:“我们研究及讨论亚里斯多德、格劳修斯、霍布斯、史宾诺莎、洛克、孟德斯鸠,但卢梭则不同,我们爱他,或我们恨他。”⑤从事文化比较的中国学人对中国文化的情感纠结,与法国人眼中的卢梭相比,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打造民族精神的学者在“爱”,反思国民性的学者则在“恨”。二者虽然得出相反之结论,但民族主义情绪却是一以贯之的。
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使得任何有价值的思想探讨很快落入中西文化家数。五四时期的科玄论战转变为文化论战即是明证。科学与人生观的问题,本是一个“关于知识与价值分殊的富有哲理性的讨论”,是一个很好的哲学问题。但从讨论伊始,就夹杂着甚至偷换为文化问题,最终为“构建终极真理的意识形态论争”所淹没。[16]326
哲学问题与文化问题的区别在于:前者关注人类共同课题,后者关注民族文化课题。卡西尔之哲学冠名为“文化哲学”,他沿着苏格拉底的理路继续追问“人是什么”,这是哲学问题。新儒家也从事文化哲学,他们顺着文化民族主义的理路追问“中国人是什么”,这是文化问题。维柯从事文化比较,寻找各不同民族心头所共有的“心头词典”(mental dictionary),从而“来替发音不同的各种语言找到根源”,[17]这是哲学问题。季羡林从事文化比较,寻找中国文化特质或发掘中国精神,这是文化问题。提问方式决定了,哲学问题的承担者是踽踽独行的个体,文化问题的承担者则是蠢蠢欲动的群体;哲学问题的根本在于追问,而文化问题的根本在于答案。前者的正确性是“学术的”,而后者的正确性是“政治的”。周国平说:“民族文化与其说是一个文化概念,不如说是一个政治概念。”[18]余英时说:“从某种角度看,国学的重点似不在学,而在于‘国’字。”[19]可谓探本之论。
20世纪中国哲人对人类思想贡献甚少,也许与文化问题压倒哲学问题、“政治正确性”压倒“学术正确性”不无相关。前者对后者的这种压倒性的优势,来源于民族主义的压倒性优势:
在现代中国的变迁过程中,民族主义成为现代化的最有效的社会动员,成为凝聚人心、整合社会意识形态的象征。谁抓住了民族主义这面旗帜,谁就占据了领导现代化的精神制高点,掌握了统治中国改朝换代的合法性资源。[16]6
对中国现代思想界的左中右三派来说,民族主义是恐怕是其共有之意识形态,只不过面向不同而已。⑥
五 强分中西
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怀、中西对立之思维模式以及一言以蔽之的勇气,给中西文化比较带来的直接遗产就是强分中西。
有些事情本无中西之分,我们的中西文化比较却要把它分为中西两橛。20世纪流行的“西方主纵欲,东方主禁欲”、“西方重物质,东方重精神”、“西方重争斗、东方重和谐”、“西方对自然是征服,因而破坏环境,东方有天人合一思想,因而顺应和保护自然”之类概括,就是强分中西。因为强制分开的这两个方面,恰好是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
应该说,对人的原始兽性和物欲进行一定的克制,形成道德自律的准则,是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的标志,并非那个民族的特色。强制过分,则扭曲人性;纵欲过度,则社会失序。这方面中国在两个极端之间看不出比西方社会处理得更加成功。追求享受和纵欲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决不亚于任何国家,只是一则比较隐蔽,没有西方人那么坦率;二则不平等,一方有无限权利,另一方尽无限义务。[20]
事实上,假如我们虑及中国古代在天理人欲问题上的尴尬这一事实,我们也许就不那么言之凿凿了。
有些事情则原有中西之分,但因文化融合却再也无法或没有必要分出中西。熊梦飞先生在1935年曾调侃道:
中西两种文化,见面于明代中叶以后,订交于清代同光之际,到了最近三十年,乃发生了同居关系,亲亲密密,捏作一团,不免令人纳罕,于是有许多人们,要想从这“乱作一堆”中,分别出个谁是“你”,谁是“我”来。自来从事此种分析工作者,代不乏人,便是所谓“中西文化比较论”。[21]
事实上,中国自近代以来,或者更确切地说自五四以来,至少有两个传统,一为“中学”,一为“西学”。我们非得把这两个传统置于敌对位置,甚至事事都分出中西,其实就像是左手跟右手过意不去。
关于中西文化比较之强分中西,钱锺书先生在1933年所写的《中国文学小史序论》中,举了一个更调皮的例子:
我们常说,某东西代表道地的东方文化,某东西代表真正的西方文化;其实那个东西,往往名副其实,亦东亦西。哈吧小狮子狗,中国通俗唤作洋狗,《红楼梦》里不就有“西洋花点子哈吧狗儿”么?而在西洋,时髦少妇大半养哈吧狗为闺中伴侣,呼为北京狗——北京至少现在还是我们的土地。许多东西文化的讨论,常使我们联想到哈吧狗。[22]116
钱先生不大喜欢重复自己,但在这条“哈吧狗”身上,我们发现了例外。1945年12月在上海美军俱乐部给美国大兵讲中国诗时,他不小心又想到了这条狗。不同的是,这次不但想到了,而且还希望这条狗去咬人:
有种卷毛凹鼻子的哈吧狗儿,你们叫它“北京狗”(Pekinese),我们叫它“西洋狗”。《红楼梦》里的西洋花点子“哈吧狗儿”。这只在西洋就充中国而在中国又算西洋的小畜生,该磨快牙齿,咬那些谈中西本位文化的人。[22]167
这条狗能否听钱先生的话,去咬谈中西本位文化的人,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却必须谨记钱先生的告诫:“每逢这类人讲到中国文艺或思想的特色等等,我们不可轻信,好比我们不上‘本店十大特色’那种商业广告的当一样。”因为,“中国诗只是诗,它该是诗,比它是‘中国的’更重要。好比一个人,不管他是中国人、美国人、英国人,总是人。”[22]167
假如我们非得因为某一思想出自西方学人之口,就强调其西方性,那么,我们只能将自己的民族带向封闭。事实上,这种强分中西的思维习惯,其实与根据阶级成分定终身的做法毫无二致。二者都犯了视起源(origin)为本质(essence)的发生谬误(genetic fallacy)。20世纪的历史,似乎也早已告诉了我们,这类谬误会导致何种人间灾难。
六 结语:加法与减法
谁都承认,对于20世纪以及未来之中国,中西文化之交流与会通是一个恒久课题。要完成这一课题,我们必须做加法,而不是做减法。
王国维所言“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即开,互相推助”,[23]即是加法。而在民族主义支配下,强分中西,并在中西对立框架里展开的“一言以蔽之”的文化比较,则是减法。因为,浓重的民族主义情绪,使得文化比较蜕变成文化较量;强分中西的思维习惯,使得我们无法面对终极问题;中西对立的思维模式,则使得二者绝不相容;至于“一言以蔽之”的理路,则使得文化比较变成了打旗帜站立场。
做加法,意味着我们在争议儒家能否开出民主及自由之前,先认真研究一下什么是民主及自由;在争论中国古代有无哲学或宗教之前,先研究一下什么是哲学或宗教;在追问何为中国人之前,先追问什么是人。换言之,做加法就意味着我们不掉入中西家数,直面人类终极问题本身。否则,本应是理性探索的文化比较,变成了民族体力较量;本应是个人不断追问的理性探索,变成了先祖如何如何的“拼爹”游戏。
记得几个月之前,一个学生很激动地问我,中国人为什么要信洋教?我明白他的意思。我反问,那么美国人为什么要成为儒教徒或佛教徒?这让我想起了前些年乘出租车时,那位的哥看到街上的一对男女甚是亲密,男为白种人,女为黄种人。他很是愤愤然,说他就看不惯这个。我也明白他的意思,他认定那个白种人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国民,这个黄种人是中国人。我反问,假如是一个中国男人领着一个美国女人,看得惯否?掉入中西文化家数的文化比较,不但会使我们忘记问题本身,而且会使得我们变得浅陋狭隘。说句极端的话,误中国至深者,非义和团和红卫兵式的爱国主义莫属。很悲哀的是,思想界好像也出现了许多红卫兵和义和团。
还是回到文章开头所引出的环境危机上来吧。做加法,把环境危机当作人类文明自身的危机,而不是趁机就说西方已经没落,人类的希望在东方。否则,我们对中国古代生态智慧的发掘,就会像梁启超《欧游心影录》一样,难逃“幸灾乐祸地渲染欧洲思想界的悲观惶恐情绪,并且毫不掩饰其对中国文化充满自豪感的乐观”[16]316之嫌。
总而言之,中西文化比较与其寻找中国文化特质或发扬民族精神,不如提出一些有份量的终极问题或根本课题,带着此终极问题上去从事文化比较,苦心孤诣地去询问。因为对于思想来说,提出问题比找到答案更重要。因为任何对话或理性交流,都是以“问题”为中心。我们耳熟能详的“辩证法”之真意就在于此:
这种“辩证法”探求方式,从逻辑上说,中心之点是怎样提出一个“论题”或“问题”。因为要讨论的是一些重要的意见及其分歧,如多数人同哲学家之间的分歧,哲学家之间的分歧。讨论首先要把这些分歧意见集合在一个恰当的“位置”上才能进行和有效。亚里士多德指出,哲学研究首先要考虑的方法,就是要研究和知道安排好一个论题,使分歧的意见能够相遇,形成一个恰当的问题,以便分别真理与错误,有助于探究真理。[24]
假如我们以为关于环境危机,中国古人的“天人合一”就是答案,等着我们去发扬光大,那么又何苦去从事中西文化比较?我们解释一下、翻译出来,然后“送去”就是了。这样也许一下子轻松了许多,然而,思想退化也许往往从此种轻巧开始。
收稿日期:2013-09-10
注释:
①诸文均收入《东西文化议论集》,季羡林、张光璘主编,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
②参见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图腾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等书。
③张灏先生认为,中西对立之思维模式自“五四”始:“是从五四开始,知识分子一方面把西方近代文明简化为科学和民主两大要素,另一方面把传统视为一个单一的整体而与西方近代文明对立起来。”([美]张灏:《五四运动的批判与肯定》,《张灏自选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第233页。)私意以为,中西对立至少可以追溯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时代。至于始于何时,这无疑是一个特别有趣的思想史题目。
④何兆武先生曾说:“当代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们,有些人每好谈天人合一乃是中国思想的特征。其实这是一种无征不信、似是而非之说。因为古今中外一切哲学讲到最后,没有一家不是指向天人合一的,宇宙和人生最后终究是要打成一片的,天道和人道终究不可能不是一以贯之的。也可以说,凡不如此的,就不是哲学。问题只在于每个人各有其不同的讲法,这就成为了不同的哲学。”([德]康德:《论优美感和崇高感》,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译序”第4页)
⑤转引自苑举正:《卢梭思想在近代中国政治的意涵》,《世界哲学》2002年增刊,第65-66页。
⑥关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诸副面孔及其压倒性之优势,参见沈松侨:《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政治社会哲学评论》(台北)第3期,2002,第49-11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