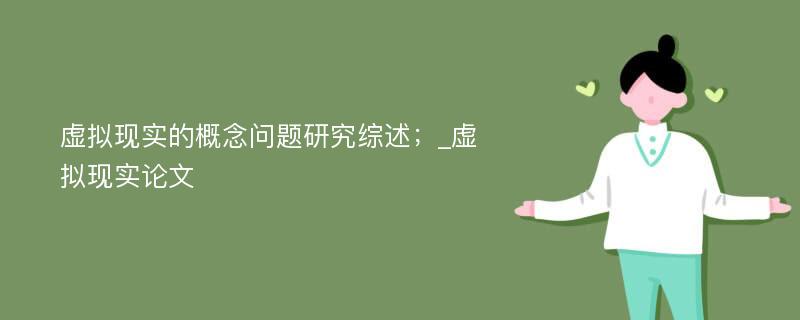
关于quot;Virtual Realityquot;概念问题的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概念论文,quot论文,Virtual论文,Realityquot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31 文献标识码:A
近些年来,对"Virtual Reality"的研究引起了学者们的极大兴趣,研究范围从虚拟技术扩大到虚拟空间和虚拟生存,研究的视角也从技术应用的社会学层面上升到虚拟本身的哲学层面,然而,对于"Virtual Reality" 的哲学探讨——特别是在几个基本概念上——仍存在很多争论和分歧,甚至可以说,这仍是一块有待开垦的处女地。
1 关于译法上的争论
每一个名词的译法往往包含着译者对该词的理解,而译法上的分歧又往往引发出哲学观点上的分歧。对Virtual Reality的争论正是因此而起。
最开始提到"Virtual Reality"时,技术专家们将之译为“虚拟现实”,“钱学森同志为了使人们便于理解和接受'Virtual Reality'技术的概念,按中国传统文化的语义称VR技术为‘灵境’技术。这个‘灵境’概念正越来越多地被中国科技界的人士所引用”[1]。但“灵境”实际上并没有“虚拟现实”易于理解,大多数专家学者还是同时采用“虚拟现实”这一译法。1996年,金吾伦在《光明日报》上撰文指出,“灵境”是一种意译,与原意相距较远,而"Reality"一词只能译为实在,不能译为“现实”。他认为:“只有在把现实理解为等同于实在的极端情况下,虚拟实在也就是虚拟现实。”[2]这篇文章发表后,引起了业界和学界的争论,随后,《光明日报》将四种有代表性的意见发表在1997年1月16日的报纸上。北京大学的朱照宣、刘华杰、潘涛等认为:“'Virtual Reality'就是身临其境、临摹出来的‘境’。”而“灵”字不宜用在科技术语里,因此他们主张将"VR"译为“临境”;中山大学的关洪建议用简单一点的名字,叫“虚实”,即虚的实;北京昂蓝技术发展有限公司的总裁王可提出,在学术领域保留“虚拟实在”的译法,而在日常生活和大众传播中可以用“电象”来表达VR,因为中国的“象”字所表达的正是抽象的或虚拟的实在,而“电”字则表达了实现VR的物理实在——电子、电场和电波;另外,四川科技咨询中心的钱玉趾认为,“大至世界、小至细胞,都是客观外界的一种真实存在,一种境象”,因此,将VR译为“虚拟境象”要比译为“虚拟实在”更容易让人理解。
在1998年第1期的《科技术语研究》上也刊载了对Virtual Reality汉文规范名的讨论,在这一讨论中,钱学森认为,"Virtual Reality"是指用科学技术手段向接受的人输送视觉的、听觉的、触觉的以至嗅觉的信息,使接受者感到如亲身临境。但这临境感不是真地亲临其境,而只是感受而已,是虚的。所以他认为,可以用我们传统文化中的“灵境”这个词来表达这种情况,这比“临境”好,也是实事求是的。然而何祚庥却表示赞成金吾伦的意见,他认为,“如果对‘现实’一词还要加入一个解释,‘实际存在的事物’,就不如直截了当地译作实在了。”
另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Virtual一词还有“实际上起作用的”、“事实上存在的”、“因内在力而能产生作用的”等意思,译为“虚拟的”仅体现它的其中一层意思,可能会对中国人产生“误导”[3]。
目前,除了常见的“虚拟现实”和“虚拟实在”之译法外,我们还可以看到诸如“实境技术”、“人工现实”、“模拟现实”、“虚拟实境”、“拟真”或“虚拟真实”等译法,应该说,以上种种译法都各有其可取之处。因为英语和汉语都是活的语言,坚持对VR作任何精确的诠释是狭隘的,也不符合约定俗成。但同时,为了便于学术交流和学术规范,我们有必要从各种译名中挑选出一两个最好的来。虽然当前关于"Virtual Reality"的译法主要集中为“虚拟现实”和“虚拟实在”的分歧,但笔者以为“虚拟真实”这一译法也是比较恰当的[4]。因为“现实”和“实在”作为哲学范畴的概念本身就多有歧义,而“真实”这个词似乎更贴近生活,更通俗易懂些。
2 "VR"的实质
前文已经指出,一个词的译法总是蕴含着译者对这个词的理解。尽管每个技术专家对VR技术的表述都有所不同,但大致与汪成为教授下的定义没有太大出入:即VR技术是指“在计算机软硬件及各种传感器(如高性能计算机、图形图像生成系统,以及特制服装、特制手套、特别眼镜等)的支持下生成一个逼真的、三维的,具有一定的视、听、触、嗅等感知能力的环境,使用户在这些软硬件设备的支持下,能以简捷、自然的方法与这一由计算机所生成的‘虚拟’的世界中对象进行交互作用。它是现代高性能计算机系统、人工智能、计算机图形学、人机接口、立体影像、立体声响、测量控制、模拟仿真等技术综合集成的成果。目的是建立起一个更为和谐的人工环境”[5]。然而,这个技术性的定义却不能告诉我们VR是什么。学者们对于什么是"VR"仍说不清,道不明。
有些学者并未意识到VR与VR技术的区别,在论文中将VR等同于VR技术(注:如章铸、吴志坚《论虚拟实践》文中的第一句话:“在已经过去的半个世纪中,计算机虚拟现实(VR)和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与融合,……”,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年第1期。)。正如信息绝不能等同于信息技术一样,VR和VR技术也不是一回事。目前,在论文中被引用最多的对VR本质的经典性概括是由美国学者迈克尔·海姆作出的。他在《从界面到网络空间——虚拟实在的形而上学》一书中,将VR的本质用七大特征来表达:模拟性、交互作用、人工性、沉浸性、遥在、全身沉浸和网络通信。他还指出:“如果西方文化被实在的意义困惑了2000年,那么我们也不能指望我们在2分钟内,甚或20年内弄清楚虚拟实在的意义。”[6]迈克尔先生所提供的回答显然不能令人满意。下面介绍几种由我国学者提出的观点。
(1)金吾伦先生分三个层次讨论VR的本质。首先从技术上看,VR是一种以动态形式创造一种可选择的数据表达的系统。VR系统的基本特征即3个"I":Immersion-Interaction-Imagination(沉浸-交互-构想)。第二,从社会层次上看,VR是由技术创作的,不同于精神或意识的人造物,VR是实在的。第三,从哲学层次上看,VR是计算机创造和生成的一种新的实在。它表明了世界的多元性(注:参见刘吉,金吾伦《千年警醒——信息与知识经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161-168.)。金先生的视角是全方位的,但他并没有说清楚这种新的实在与精神或意识的人造物有何联系与区别,它又如何表明了世界的多元性。
(2)胡心智先生在《信息网络技术的哲学思考》一文中认为VR“应该是场,是一种电子场,在这里既有物(电子),又有物发现出的信息(声音、图像、文字、符号)。虚拟现实实际是电子象征物,是以信息形式再现的现实”[7]。他在后来的一篇文章中又指出:“虚拟现实的本质,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它是兼有物质和意识的中性物,电子这个载体就是物质,而各种声像、图形、文字、信息,应该是物发出的物息,而物息就已经开始跨入了意识的门坎,物息的进一步发展就形成了意识,因此,虚拟现实既有物质成分又有意识成分,它是由物质向意识的过渡,是物质向意识转化的中间环节。”[8]虽然胡先生实际上是对"VR"的本质在物质与意识之间作了一个折中,但他的见解还是富有新意。
(3)杨富斌先生也试图解释VR与客观实在的关系,他在《虚拟实在与客观实在》一文中指出,从物质和意识相对立的意义上说,虚拟实在属于客观实在的范畴,而在物质和意识相对立的意义和范围之外,虚拟实在和客观实在又是有区别,甚至是相对立的。他认为,虚拟实在是具有客观实在性的物质现象,但它本身还不直接就是客观实在,它不是指在虚拟过程中所必需的物质设备本身,“而是指这些设施的耦合所突现出来的一种整体功能,即对客观实在的‘数字化模拟’,或者说是客观实在的‘数字化模型’”[9]。然而,杨先生并没有解释,物质和意识相对立的意义和范围之外是指什么,因而他也无法回答虚拟实在究竟是什么。
(4)蔡曙山先生则认为:“一切认识对象如数字、字符、声音、图形、图像等等都可以被数字化,从而被虚拟化。由于数字化对象的客观实在性,它在数字化时空里又具有明确的现实性。”他肯定地说,“Virtual reality无论从辞源意义上说,还是从实际意义上说,都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现实”[10]。
另外还有学者认为:“虚拟现实技术的全方位渗透引起了人类文化的虚拟现实现象,我们就称该现象为‘虚拟现实’(VR)。”“虚拟现实时空为人类营造了一个既是物理又是心理的空间,它的本质应该是‘人类想像力付诸实施的感觉空间’。”[11]
从学者们对VR本质的多种见解,我们不难感受到,VR已经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最基本的物质范畴提出了挑战,只有以一种开放的、科学的态度对它进行深入的哲学思考,我们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断丰富、不断向前发展。
3 "Virtual Reality"和"Internet"
VR之所以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与互联网是分不开的。正是由于VR技术的介入,互联网再次焕发出活力。今天,人们已经意识到网络生活的虚拟性对现实生活的真实性构成了威胁。但电脑网络上的各种虚拟事物与VR究竟是什么关系呢?学者们对此各抒己见。
第一种观点认为目前电脑网络的虚拟性与VR无关。
章铸、吴志坚认为目前VR技术主要应用于少数高难度的军事和医疗模拟训练,一般都是在一个封闭的电脑化空间实现的,要把VR接到Internet上还只是一种梦想。他们认为在Internet和VR之间有着根本区别,前者本质上是一个全球计算机通信系统,后者则是一个人工合成的模拟仿真系统,绝不能把这两个既有重大区别又有技术联系的概念混为一谈,并在行文中当作同义语交替使用。他们还指出:“这也是当下网络文化讨论中许多论者将所有的计算机相关技术系统纳入国际互联网‘框子’然后‘一网打尽’的通病。”[12]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电脑网络的虚拟性与R 密联系在一起。
何明升、李一在《网络生活中的虚拟认同问题》一文中明确表示:“网络生活的虚拟性,是建之于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虚拟现实技术之上的。通过虚拟现实技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转换成了人-机互动或人-机-人互动,从而使网络生活具有了明显的虚拟性。”[13]杨富斌在《虚拟实在与客观实在》一文中也开门见山地说:“虚拟实在技术导致产生了一个崭新的世界——虚拟世界。就目前已经实现或部分实现的方面而言,已有虚拟驾驶、虚拟企业、虚拟银行、虚拟办公、虚拟旅游、虚拟情爱、虚拟友谊、虚拟医疗、虚拟购物、虚拟游戏、虚拟图书馆、虚拟团体、虚拟社区,甚至虚拟国家等。”[14]按照这种理解,VR包括了网络上存在的一切虚拟性事物。
笔者认为,同人们一般的社会行为相比,网络行为无疑具有一种虚拟性的特征。但这种虚拟性,是指网络行为得以依附的行动空间是一种不同于现实物理空间的电子网络空间,并不是说网络行为不构成人们的一种特殊而真实的社会行为。人们在互联网中的社会交往行为不像在现实物理空间中所进行的社会活动那样,具有实体性和可感知性,具有外在的可触摸和可察觉的时位置与形态,而只具有一种功能上的实在性和可重复性。在互联网这样一种数字化世界的环境之中,人们特殊的社会行动即网络行动也就成为了一种虚拟的行动。而对于VR系统来说,人们行为的虚拟性不仅表现在要依附于数字化的电子空间,更重要的是它还表现在人们的行动作用的对象可以是在真实世界中并不存在的。比如说,在虚拟驾驶训练中出现的公路或发生的紧急情况在真实世界中并不存在;而对于虚拟社区来说,社区里的人肯定是也在现实世界中存在的人,只不过他们在网上并不以真实身份出现。因此,VR的虚拟性与网络的虚拟性虽然都由数字化衍生,有其本质上的相似之处,但它们的根本出发点却并不一样,互联网重在讯息交流与沟通,VR技术则重在数字化世界的创造。
4 从"Virtual Reality"到“虚拟”
随着VR一词的频繁使用,“虚拟”这个词也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关于这个问题陈志良先生发表的一系列文章:《虚拟:哲学必须面对的课题》、《虚拟:人类中介系统的革命》和《超越现实性哲学的对话》等,在哲学界造成了不小的影响。陈先生在文章中写道:“虚拟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虚拟是指规则文明,指各种规则的合成、选择及其演化,随着多样化时代的到来,人的行为规则也将更多地虚拟化;狭义的虚拟是指我们时代的数字化虚拟,数字化虚拟正在成为我们时代的主体色彩。”他指出,“在我们时代,虚拟特指用0-1数字方式去表述和构成事物以及关系,具体地说,虚拟是用数字方式去构成这一事物,或者用数字方式去代码这种关系,从而形成一个与现实不同但却有现实特点的真实的数字空间。”[15]陈先生还认为,“虚拟这一方式,是人类中介系统的深刻革命,是数字化革命”,它将使我们这个时代的哲学框架发生巨大的历史性转换,即从现实性哲学转换到虚拟性哲学[14]。
张世英先生十分赞同陈先生提出的要突破传统的现实性哲学框架,重新审视现实性范畴的观点。他说:“这不只是一个重要的学术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十分迫切的现实问题。”[17]
殷正坤先生也同意陈先生所说的哲学面临一场革命的提法,并且也认为这场革命将是由人类中介系统所引起的,但他反对这场革命是对以现实性哲学的根本扬弃。他指出:“虚拟虽然可以超越现实,但并不是使现实性的范畴变小了,而是人类通过虚拟不断拓展着现实性的空间,尤其是‘数字化方式构成’的虚拟更是极大地拓展了这个空间,从而给哲学提出了许多值得认真研究的重大课题。”[18]
当学者们从VR思考到虚拟给传统哲学带来的挑战时,他们已经远远超越了VR技术本身的意义,他们实际上更多地是在思考这个变化的时代。
VR带给人们的震撼是巨大的,人们对它的研究视角也是多种多样的。究竟它会对人类社会产生怎样的深远影响?会不会导致传统哲学的历史转变?这些都还有待于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有待于学者们对VR的本质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
收稿日期:2001-09-26
标签:虚拟现实论文; vr技术论文; 虚拟技术论文; vr医疗论文; REALITY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virtual论文; 数字化时代论文; vr购物论文; vr游戏论文; vr眼镜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