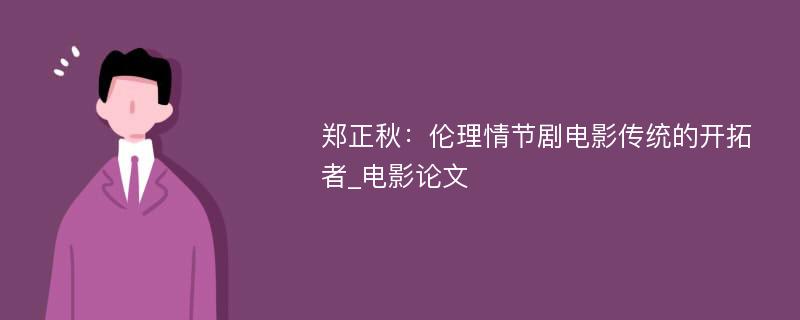
郑正秋:伦理情节剧电影传统的开拓者,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开拓者论文,伦理论文,情节论文,传统论文,电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348(2002)10-0018-08
一
情节剧电影在西方,尤其在美国,是一种普遍流行并至今盛行不衰的电影样式,许多 电影大师对其进行了探索和发展,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创作模式。中国情节剧电影, 是受西方,特别是受好莱坞情节剧的影响,经过早期电影创作者的努力探索,在本民族 文化传统的土壤中开花结果的。早在20世纪初,西方电影还在其幼年的成长阶段,就与 情节剧结下了不解之缘。情节剧本来是18世纪末与19世纪前半期,在欧洲流传的一种戏 剧样式,曾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一种宣传工具,有着新的道德和美学观念,在渗入 戏剧与文学之后,随着电影这种大众文化载体的日益发展,又以一种受大众普遍接受的 结构形式和叙事方式逐渐进入电影。至1908年,法国“艺术影片公司”拍摄了世界电影 史上第一部情节剧电影——《吉斯公爵的被刺》。此影片无论是人物性格的塑造,还是 故事情节的发展都具有了引人入胜的情节剧的基本特征,上映后极为成功。因此,情节 剧电影便在向戏剧和小说情节剧吸取经验的同时,自身也获得了发展。
但是,由于“情节剧是美国电影最主要的根源,”[1]况且“格里菲斯的作品与情节剧 的相近是显而易见的,”[1]所以,美国情节剧电影对中国情节剧的影响也较明显。美 国电影之父格里菲斯拍摄的《一代国家的诞生》、《走向东方》、《暴风雨中的孤儿》 等优秀影片,为情节剧电影“创立了风格、基调和实质,”[2]格里菲斯作为默片时期 的一个大师,通过他的实践与探索,使情节电影这一新型样式逐渐成型。经过西席·地 密尔、亨利·金、冯·斯特劳亨等一批情节片导演创作的一系列家庭情节剧电影,都以 家庭为核心来表现生活问题,对情节剧电影的内涵、形式与手法加以丰富和发展,并使 美国好莱坞电影在三四十年代达到了鼎盛阶段。情节剧电影的创作特点也更加明显,在 题材、主题、人物、情感、结构等方面形成了一套模式:“1.偏向男女主人公;2.强调 观众的认同;3.按照善与恶的概念而不是按照阶级来划分等级;4.为高潮而制造高潮; 5.观赏场面,戏剧性动作,悬念段落;6.无动机,无准备,出乎意料和直接性;7.愿望 满足,不是解决戏剧冲突而是回避冲突。”[1]
中国早期电影基本上是在商业利润的驱使下自发地生长。它自己没有明确的目标,时 代对它也没有严格的要求,显得庞杂混乱。加上“由于电影最早是作为帝国主义的殖民 主义经济文化政策的产物而传入中国的,因而资本主义的电影意识一开始便在中国有着 广泛的市场,加上近代中国经济的贫困,政治的腐朽以及科学的落后,这就必然造成中 国电影的先天不足。”[3]根据有关统计,从1896年到1937年,有5000多部外国影片在 中国上映,其中大部分是美国电影。[4]当然,其中也包括像格里菲斯这样的世界级导 演的影片在内。因此,早在20世纪初期,中国观众和电影工作者,就已经熟知了早期美 国情节剧电影在结构、人物、主题以及主导动机等组成方面的特点。虽然在好莱坞情节 剧的影响下,中国情节剧电影也开始起步,但是,由于中国传统的强大的文化背景,对 外来文化形成的排斥心理,限制了中国导演对西方文化的借鉴视野,所以没有人从文化 的借鉴角度去认识电影自身的规律,往往是把中国传统的观念与西方电影文化观念相对 立或凌驾于西方电影文化观念之上:中国早期电影创作者多数从事文明戏的编导或评论 工作,在创作方法上习惯于照搬当时文明戏舞台剧的编剧方法,这样势必造成用中国传 统的戏剧观念代替电影自身的规律。中国早期的电影创作者,绝大多数在电影观念上又 只是一门心思地追求商业利益,而对电影本体特征却没有研究兴趣,从而使西方的电影 文化特质被中国强大的戏剧文化消融掉了。这也就决定了在文化取向方面,必然地朝着 本土化的方向发展,“中国电影的最初形态,便承袭了文明新戏的‘艺术’而出现。” [5]中国电影之父郑正秋,就是其中的主要代表之一,他的一系列重要影片具有文化价 值取向的本土化、生活故事的戏剧化、人物形象的类型化、叙事策略的大众化和创作主 题的伦理化等审美特征,基本确立了中国电影注重社会伦理教化,审美教育与戏剧性表 现手法相结合的创作传统。
二
早在1913年,郑正秋就开始了中国家庭伦理故事片的探索,由他任编剧的短故事片《 难夫难妻》(与张石川联合导演),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短故事片,已有了完整的故事 情节和较鲜明的人物形象,从内容到形式,体现了家庭伦理情节剧某些因素的萌芽,以 及走向本土化的创作倾向。《难夫难妻》“在中国电影史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6](P9 ),成为中国电影发展的极为重要的分水岭。影片的主要内容是以封建买卖婚姻为题材 。故事表现了乾坤两家,一男一女,门当户对,由父母作主,“从媒人撮合起,经过种 种繁文缛节,把素不相识的一对男女送入洞房为止”[7]的全过程,按照情节剧的创作 倾向,该影片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具备了情节剧的某些特征:
第一,具有了初步完整的电影故事。影片展示了买卖婚姻的主要过程。故事有头有尾 ,层次清晰,体现了用剧情来承载社会批判的创作倾向。人物命运与外部环境(社会习 俗)的冲突与对立也有体现。男女主人公屈从于父母之命,他们不幸的婚姻同父母的旧 观念,以及封建习俗的顽固势力形成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第二,影片的主题鲜明,富有进步性。郑正秋以家乡潮洲的婚姻习俗为题材,具有深 远的文化渊源。在人们习以为常的文化习俗中,通过电影的手法,启发人们对社会问题 的思考,产生了教化和改良社会的影响,影片内容获得了观众的认同。故事内容展示了 父母包办婚姻给青年男女带来痛苦,这在当时的中国具有普遍性,由此讽刺了旧式封建 婚姻的压抑人性和虚伪丑恶,所表现的反封建的进步倾向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
第三,在叙述方式上,运用了“直叙式”。以纵向的单向发展的结构形式来展开故事 情节,表现人物命运,而不采用穿插叙述或运用强烈对比。电影富有观赏性的场面和戏 剧性的动作以及悬念段落。如把互不相识的一对男女送入洞房本身就充满了悬念和戏剧 性。
但是,《难夫难妻》毕竟只是一部短故事片,由于其内容含量的限制,所以对情节剧 特点的表现是很有限的。首先,从题材内容上看,并没有充分表现出吸引观众的险恶多 变的戏剧情境与矛盾冲突。其次,对人物的刻画不够鲜明,没有表现男女主人公对不幸 婚姻的反抗行动。再次,故事情节起伏不大,没有充分利用偶然及巧合的手段,展现事 件的复杂多变,从而未能给观众出乎意料的惊奇。最后,影片的思想观点也欠深刻,追 求影片的娱乐性与消遣性,讲究滑稽逗趣,也在《难夫难妻》中初显端倪。男女主人公 的软弱,从反面体现了封建势力的强大,并不能对社会产生多大的积极影响。
郑正秋创作了《难夫难妻》之后,因与导演张石川意见不一,而一度离开了电影界, 专事戏剧活动。而当时的影坛,虽然已经开始了长故事片的创作,但是在总体上并没有 什么大的发展。例如长故事片《阎瑞生》(1921)、《海誓》(1921)、《红粉骷髅》(192 1)等,其内容只是一些以“情杀”、或融色情与凶杀于一炉为内容的,猎奇与媚俗的煽 情故事,迎合了小市民的思想情趣,有着明显的保守意识和追求奇趣的创作倾向。这些 影片只有一个使观众感兴趣的情节曲折的故事,往往忽视了思想性和艺术性。在人物形 象以及思想内涵等方面都很薄弱,其承载的文化旨趣有时成为主流文化的对立物。尽管 如此,到20世纪20年代,中国电影冲破政治和经济的重要障碍,“进入了独立经营的大 制作时代,在模仿西方电影的同时,它也融入了中国文化的特色。这表明电影已经在中 国扎下了根,中国电影的成熟将为期不远。”[3]而这一历史重任自然地落到了郑正秋 的身上。
郑正秋是一位有着自己的审美观念和创作追求的电影艺术家,并具有丰富的戏剧与电 影创作经验,非常熟悉观众的审美情趣。因此,他能把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和娱乐性 较好地结合起来。他把“影戏”当作戏剧的一个变种,认为创作“影戏”首先必须故事 要好,情节要曲折,富有刺激性,能催人落泪。其次,立意和表现要浅显明白。所以, 他自1922年复出影坛后,吸取了中国影坛已出现的长故事片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以“ 影戏”美学观念作为自己创作的理论规范,创作了一系列家庭伦理情节剧电影。在取材 及表达方式上,既成功地借鉴外国情节剧的叙事经验,突出了情节剧的大众性特征,又 颇具民族化的倾向,实现了他“创造人生”、“教化民众”、“改良社会”[8]的审美 理想,为中国家庭伦理情节剧模式的形成,做出了更为成功的探索。
郑正秋自1923年至1927年,连续创作了十几部影片,如《孤儿救祖记》、《苦儿弱女 》、《玉梨魂》、《盲孤女》、《最后之良心》等长故事片,其内容的含量明显增大, 都以家庭生活、社会伦理为题材内容,以人物的悲欢离合为中心,借曲折动人的情节剧 故事,承载并实现了由家庭伦理折射的社会性主题的表达和批判。这些影片的思想性和 艺术性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审美表现,从而形成了家庭伦理情节剧模式的基本格局。正如 有人在分析20年代郑正秋等电影艺术家的创作时所指出的,“对情节剧的追求,和由此 产生的旧派剧作情节多变的共同风格,构成了旧派创作的情节剧特征。”[9]由于当时 以能否编写一个很吸引观众的故事,作为决定一部影片成败的最重要因素,因此,影片 的编剧技巧的高低也决定了其艺术成就的优劣。郑正秋在20年代的电影界,就是以编剧 的身份赢得了极大的声誉。以他编剧的影片《孤儿救祖记》为例,试分析该片在家庭伦 理情节剧的剧作模式方面所作的成功探索的主要特征。
在叙述方式上,《孤儿救祖记》虽然同样采用了“直叙式”的传统叙事方式,但是情 节内容更为丰富多样,环环相扣,悬念迭起,运用了起承转合、层层推进的结构形式, 叙事完整。剧情的发展过程完全体现了生活中的事件的变化顺序,剧情高潮的设计也十 分自然、巧妙。整个剧情以少年余璞为主线和叙事中心,故事情节和人物关系都是围绕 他来安排和展开的。故事的开端交代了情节发生的起因,富翁因独子道生不幸坠马身亡 ,于是立其侄儿道培为子嗣。但是,情节的发生则从间接、侧面的角度来表现余璞。由 于道生的遗孀余蔚如怀有身孕,后来又被品行不正的道培发现,道培害怕余蔚如的儿子 将来会夺了自己的财产,就诬陷蔚如不贞,把她赶出家门。余蔚如的不幸,从表现上看 ,是由道培的贪财引起的,其实不然,真正直接的原因还是由于余璞的存在,构成了对 道培独占杨家财产的威胁。随着情节的发展变化,余蔚如回到娘家后,果然生下余璞。 母子相依为命,历尽艰辛。从此,剧情开始转为正面、直接地表现余璞的行动。余璞作 为作者的理想人物,千方百计地把他塑造成传统美德的化身。因此,余璞恰好进入了富 翁捐资修建的一所义校读书,他因待人礼貌,聪明好学,深得富翁喜爱,情节的高潮是 道培由于无恶不作,被富翁断绝钱财,于是,他企图谋害富翁性命。余璞不顾安危,救 了富翁性命。情节的结局则是真相大白,翁媳之间的误会彻底消除,全家团圆。
以上各个方面的原因决定了郑正秋前期(1932年前)编导的主要特点是:围绕“改良社 会”、“教化人生”的目的,注意影片的大众性,既倾向于迎合观众,又注意引导和提 高观众的欣赏趣味。他凭着自己丰富的戏剧经验和人生阅历,结合传统戏剧的舞台艺术 和表演手法,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影片大多以普通人物的日常生活和伦理关系为主 ,把下层人物的喜怒哀乐与悲欢离合,通过一个个富有传奇色彩的戏剧性故事,以及借 助通俗流畅、章法严谨、细腻真实的导演方法,让观众亦悲亦喜亦忧亦乐,深深地为影 片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所感染,对中国的家庭伦理情节剧电影模式的建构,起了开拓性的 作用。
三
不可否认,郑正秋始终是一位有社会责任感,十分重视电影的教化功能,具有民主主 义思想的进步艺术家,特别是他后期(1932年以后),受到了30年代左翼电影的影响,思 想倾向有了更为明显的进步。他曾公开提出了“反帝”、“反封建”、“反资”的“三 反主义”[10]的创作口号,并紧跟时代的前进步伐,不断扩大自己的艺术视野,突破以 前创作模式的局限,于1933年又编导了一部在思想性和艺术性等方面,都更为成功的家 庭伦理情节剧影片——《姊妹花》。这部影片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在题材内容上,突破 了以往的家庭伦理情节剧,只侧重反映某一个家庭与婚姻的内容范围,《姊妹花》通过 透视多个家庭生活的内容,折射了具有时代特色的社会现实。它在艺术表现方面显得更 为丰富多样,标志着中国家庭伦理情节剧电影,从亦步亦趋的模仿进入了自主自立的成 型阶段。
为了表现人物矛盾冲突的尖锐激烈,郑正秋安排了曲折多变、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内 容:一对十分可爱的孪生姐妹,由于后来生活境遇的不同,妹妹二宝在城里成了军阀钱 督办的七姨太,过着奢侈淫逸的生活;而姐姐大宝则在乡下嫁给了一个穷木匠,生活难 以为继,不得不到钱公馆去当奶妈。姐妹互不相识,成为仇人。大宝因生活所迫,在万 般无奈之下,偷了小少爷的金锁,由于意外,发生人命案,而被关进牢房。而审讯大宝 的军法处长竟是她的父亲赵大。后来在赵大的安排下,母女、姐妹、夫妻相见,二宝用 车把母亲和姐姐接走。从故事的内容看,作者通过展示两家不同的生活状态,深刻地揭 露了贫富悬殊、充满对立的社会现实:大宝和桃哥一家的不幸命运和遭遇,是当时下层 民众苦难生活状况的真实而典型的反映。而对二宝和钱督办一家的豪华奢侈的生活条件 ,则作了全面而有力的暴露。可以说,作者对社会现实中的“善”、“恶”的表现倾向 非常鲜明。无疑,郑正秋对贫、富对立的现象的揭露,确实触及了矛盾产生与激化的阶 级根源。
郑正秋在《姊妹花》中的人物形象的塑造,也比以前影片中人物性格的刻画更为鲜明 和生动。郑正秋主要通过较细腻地展现姐妹俩不同的命运遭遇,以及她们在不同的生活 环境中的具体行动,来表现各自不同的性格。大宝是作者创作着重刻画的人物形象,在 她身上,作者寄予了深厚的同情。她虽然身处贫困的家庭,但是她与家人和睦相处,从 不埋怨,体现了传统妇女的温柔与贤惠。她为了减轻丈夫的负担,主动要求去钱公馆当 奶妈,即使对方要求她三年不得与家人来往,她也答应,由此可见她性格的坚韧与刚强 。而当她被迫偷金锁时,则既惊惶又胆怯。当她最后与妹妹、父亲相认时,她也对他们 不留情面,敢于当场揭露他们的卑劣行为。大宝的形象总体上显示了比较突出的个性和 较为丰富的内涵,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形象刻画的转变,体现了作者对社会现实的 新认识,以及审美价值的增扩。大宝形象的意义在于,在她之前郑正秋所塑造的大部分 妇女形象,都是贤惠柔顺有余,而刚烈不足。她们尽管遭蹂躏、受压迫,但是,没有想 到和没表现不满的言行。除了让观众对她们的懦弱和不幸充满同情之外,却没有多大的 艺术感染力和社会影响力。因此,大宝的形象的内涵,具有了新的文化含义,标志着由 负重到反抗的传统妇女形象的转变,适应了时代精神的要求。再如作者对赵大这一反面 形象的刻画也富有新意。郑正秋早期所刻画的上流社会的人物,往往蒙上一层温情脉脉 的面纱,尽管他们开始作恶多端,但是发展到最后,受伦理道德所感化,良心发现,可 是赵大的形象却具有他劣迹的清晰表现。他因私贩军火坐过牢,但贪心未改,后以出卖 自己的女儿,来作为投靠军阀钱督办的资本。他只顾自己升官发财,把妻女丢在一边, 不管她们的死活,使其鄙薄丑陋、贪婪无耻的形象非常生动。而更为突出的是《姊妹花 》在编导艺术上精益求精,为家庭伦理情节剧的创作模式,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创作经 验。
一是情节的巧妙安排。故事情节曲折变化,充满了许多偶然及巧合的因素,给观众以 出乎意料的惊奇的戏剧性效果:姐妹两人由于生活的环境的差异,一个是穷得无法生存 的乡下农妇,一个是有钱有势的军阀太太。前者为了生活不得不去后者家中当奶妈,并 受尽种种欺侮,最后发现竟是亲姐妹。这些离奇的情节的设计,充分利用了误会、偶然 、巧合的手段,不断制造悬念,因而富有很强的观赏性和吸引力。
二是对比的恰当运用。运用对比的手法,突出了不同人物在性格、品质、感情等方面 的差异。如大宝温柔、刚烈的性格,善良、贤惠的品质,以及对丈夫的关心、体贴等优 良美德,成为美与善的象征;而二宝的骄奢淫逸与专横跋扈则是丑与恶的化身。另外, 不同环境与生活状况的对比,扩大了影片表现内容的范围,加深了主题的含义:农村的 衰败与城市的堕落的对比,穷人的生活的苦难与富人生活的奢侈的对比等,都体现了极 强的批判力量和感情色彩,增强了影片的艺术穿透力。
三是细节的精心设计。影片往往在情节进展的过程中,通过生动的细节来刻画人物的 复杂心理。如大宝偷金锁与藏金锁的细节表现了她惊惶和胆怯的心理特点。而二宝的骄 横也是用一系列细节来体现的。例如二宝稍不如意就责骂仆人,因为急于外出打牌,对 大宝借钱之事,不但不理睬,而且出手打了大宝一记耳光。即使当赵大向她说明了真相 ,要她认自己的母亲和姐姐时,她还是用鄙视的眼光,不看她们一眼。
总而言之,郑正秋的顶峰之作《姊妹花》,从内容到形式都集中体现了家庭伦理情节 剧模式新的创作特点。如果说早在1913年的《难夫难妻》,只是一部家庭伦理情节剧的 试验片,还只具备情节剧某些因素的萌芽,而《孤儿救祖记》算是较为典型的家庭伦理 情节剧,已经“真正奠定中国电影艺术地位”[11],那么,《姊妹花》对家庭伦理情节 剧模式的探索,则由此朝前迈进了一步,标志着中国家庭伦理情节剧模式正在走向成熟 。有人曾这样评价郑正秋的创作,他“任导演十年来始终是写实主义的,所编剧本寓教 育于娱乐之中,力求浅显,感动力量极大。”[12]在整个默片时代的编导艺术家中,郑 正秋的地位十分突出,他“为早期中国电影建立过荜路蓝缕的拓荒之功”,“拥有数量 最为众多的同时代的观众,而对当世或后世导演亦有既深且远的影响。”[13]不过,由 于郑正秋毕竟是以戏剧家和戏剧评论家转入电影的,并不通晓电影技术,对此也无什么 兴趣,他的电影观众只强调戏剧与电影在艺术形式和社会功能的相似性,“将戏剧的一 整套结构、叙事方式,诸如冲突律、情节结构、人物塑造等剧作经验和戏剧场面调度、 造型、表演经验搬用到电影中来。缺少镜头观念,而以类似舞台剧分幕分场的戏剧性场 面和段落,作为基本叙事单元。”[6](P11)所以,郑正秋对电影语言的探索并无多大创 新,而他“将艺术本体、艺术技巧和艺术社会功能平列而熔于一炉”的整体思维方式, 正显示这种观念“缺乏科学范畴和严密的推理形式。”[6](P12)
20年代初以郑正秋为代表的中国伦理情节剧的出现,除了西方情节剧电影在艺术形式 和表现手段上的直接影响之外,还有中国本土文化和社会影响以及创作者本身的艺术个 性和审美追求等原因。
首先,文化和社会原因。其一,中国几千年来的历史发展有着自成体系的文化传统, 它一直对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和历史进程发生影响,不仅成为稳定中国各个时代社会政局 的重要因素,而且对中国文化艺术的发展有比较明显的促进作用。在中国多样的传统文 化思想中,尤其以儒家的仁义伦常思想影响最为久远,成为统一民族精神的纽带、代代 共守的基本信条,以及意识形态的基础。因此“传统的道德观念、伦理思维、行为准则 ,至今仍然在社会上占有很重要和特殊的地位,也为中国人所遵奉和崇拜。”[14]儒家 强调和谐与秩序的传统文化观念,对20世纪20、30年代中国混乱和动荡的社会现实具有 一定的凝聚作用。
其二,我国丰富多样的史传文学和宋元话本以及明清的小说、戏剧等,在叙事上讲究 层次分明、结构清晰,在人物塑造上具有鲜明的、类型化的性格,在起承转合、曲折多 变的戏剧性情节中,呈现出扬善惩恶的道德伦理倾向,尤其是“苦情戏”的煽情方式比 较突出。这些形式多样的叙事文学和表现手法,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不仅 其内容具有文学性、趣味性、观赏性和大众性,而且所叙述的主人公大多数承载了儒家 思想,宣扬了儒家重义轻利、忠贞不贰、自强不息的精神,符合中华民族的传统观念、 道德标准和欣赏心理。郑正秋开创的家庭伦理情节剧电影样式,不但使其成为电影艺术 中的一个类型,而且也结合了积淀了中国观众潜意识中的叙事要求和观赏心理,是民族 精神和文化传统在大众喜闻乐见的现代艺术中重现的必然结果。
其次,创作者的艺术个性和审美追求。从创作者郑正秋的学养经历看,也使他与传统 叙事文艺和时行通俗艺术有着密切的文化联系。他有着丰富的新剧创作和表演经验,促 使他着眼于大部分观众的欣赏水平,灵活运用适应和征服观众的叙事策略,从而获得广 泛的社会影响。由于郑正秋本人对观众审美心理的理解和审美情趣的重视,在创作上追 求通俗化、大众化的风格,认为“戏剧趋势之良善与否,戏馆与影片公司之营业发达与 否,……唯我则以为其权大半操自观众,编剧者往往因观众之倾向以变更其原有之主张 焉”,要“缘观众心理”[15]进行创作。因此,郑正秋以家庭伦理情节剧电影样式创作 的一系列影片深受观众欢迎,在他以后延续不断,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无论是30-4 0年代的蔡楚生,还是50-90年代的谢晋,他们各自的电影创作都与郑正秋开创的创作模 式一脉相承,体现了社会/历史/政治伦理化的特点,并由此逐渐演变成中国电影史上一 种主流类型。无论是《渔光曲》、《一江春水向东流》,还是《舞台姐妹》、《天云山 传奇》、《芙蓉镇》等影片,这种“具有与主流意识形态的机制同构的主流性、伦理价 值取向的正统性和审美趣味上的大众性”[16]的创作特点,都是对郑正秋创作规律的发 扬光大。可以肯定,郑正秋所开拓和探索的家庭伦理情节剧的成功经验,在中国当今和 以后的电影创作中,都有不少艺术经验值得学习和借鉴,对中国电影的发展会有不可忽 视的影响。
收稿日期:2002-06-18
标签:电影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郑正秋论文; 伦理论文; 家庭观念论文; 叙事手法论文; 孤儿救祖记论文; 难夫难妻论文; 姊妹花论文; 剧情片论文; 中国电影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