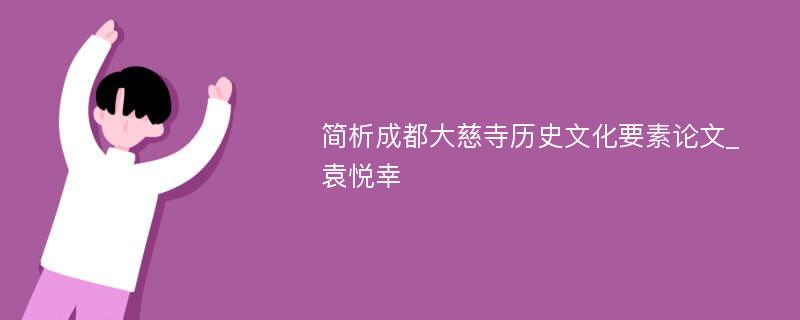
(成都市锦江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课题名称《成都市大慈寺历史文化元素》项目编号:2015z372015年成都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
项目负责人:袁悦幸
摘要:历史上的大慈寺香火鼎盛,人口流动频繁,也因此酝酿出一个商业兴盛之地。盛唐时期,凭借东大街的交通干道优势,寺门前首开集市,每月一市,各不相同,造就了“蜀中首街”东大街的千年繁荣。2007年,唐宋江南馆遗址的出土,更加证实了大慈寺片区远自千年的繁华。大量考古发现拼凑出唐宋时期这一区域的盛景,可见当时的兴旺。
关键词:成都市;锦江区;大慈寺;历史
大慈寺历史文化片区地处成都市中央商务区核心区,占地约110亩。区域内的大慈寺始建至今已有1600余年历史,被誉为“震旦第一丛林”,是蜀地著名的禅宗道场。鼎盛时期,大慈寺占地千亩,建96院,规模蜀中最大。寺内源于唐代的壁画亦为一绝,先后有67位名家于此留下手迹,共有壁画千幅。禅茶也是大慈寺佛教文化的重要构成,贵在于禅,以茶艺昭显佛法广大。历史上的大慈寺香火鼎盛,人口流动频繁,也因此酝酿出一个商业兴盛之地。盛唐时期,凭借东大街的交通干道优势,寺门前首开集市,每月一市,各不相同,造就了“蜀中首街”东大街的千年繁荣。2007年,唐宋江南馆遗址的出土,更加证实了大慈寺片区远自千年的繁华。大量考古发现拼凑出唐宋时期这一区域的盛景,可见当时的兴旺。
一、佛教文化深远
1.建寺历史悠久,规模宏大,影响深远
大慈寺现位于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东风路,始建于魏晋时期,世称“震旦第一丛林”。据宋代普济《五灯会元》记载,魏晋时期,印度僧人宝掌东游到成都,就曾住在大慈寺。唐玄宗御书“敕建大圣慈寺”,古代大、太二字相通,由此民国傅崇矩《成都通览·成都之寺庙》等书中也将大慈寺称作“太慈寺”;初建时已占田千亩,之后不断扩建,宋人范成大在《成都府古寺名笔记》中曾记载,大慈寺“自中三门,北至水陆院,东至如意轮正觉院,系高力士同僧英干建”;大慈寺大殿东廊的三学延祥之院,系昭宗乾宁年间王建下令修建;同时,大慈寺不断得以重修或修缮。唐代时就认为大慈寺所处位置风水极盛,镇守四川的韦皋在德宗贞元十七年指出:“观其左压华阳之胜,中据雄都之盛,岷江灌其前址,玉垒秀其西偏,足以彰会昌之福地,弘一方之善诱”。以后历代,大慈寺均为成都著名寺院,与文殊院、昭觉寺并称“成都三大寺”。
2.历代高僧辈出
大慈寺历史悠久、高僧辈出。魏晋时期,印度僧人宝掌禅师东游中土,入蜀参拜普贤菩萨,住在成都大慈寺。唐代佛学大师玄奘是中国古代四大优秀小说《西游记》中“唐僧(三藏)”的原型,佛教法相宗的创始人,著名的旅行家、翻译家。玄奘俗姓陈,名祎,洛州缑氏(今河南偃师)人,家贫,父母早丧,13岁出家,高祖武德五年(622),“法师年满二十”,在成都的空慧寺“受具”(受比丘戒)。由于玄奘西游归国后,长期居于太宗下令新建的大慈恩寺进行佛经翻译,时人尊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后来逐渐被误解为玄奘在成都大圣慈寺“受具”。大慈寺是培养玄奘大师佛学悟性和勇气毅力的圣地,也是西行取经促进中外佛学交流的起点。
3.大慈壁画世间一绝
大慈寺不仅是宗教圣地还是一座壁画宝库。唐玄宗、唐僖宗先后避难幸蜀,许多宫廷画家也随之聚集成都,使绘画之风大盛。自唐以来,曾有67位画家在寺内留下精美壁画(见附录),宋代文学家苏轼观赏大慈寺壁画后惊叹其“精妙冠世”。大慈寺壁画数量众多,拥有各类壁画1.5万余壁,约3万平方米。大慈寺壁画题材广泛,包括宗教画、人物画、花鸟画和山水画。据李之纯《大圣慈寺画记》统计,佛教绘画共有13996幅。包括诸佛、如来1215幅,菩萨10488幅,帝释、梵王68幅,罗汉、祖僧1785幅,天王、明王、大神将262尊,佛会经验变相158幅。以内容而言,则主要是各种佛像、菩萨、罗汉、天王、明王图及各种佛经变相、西天乐土与地狱画、佛本生故事等,如晚唐左全在大慈寺极乐院所绘的“金光明经变相”壁画,反映了佛经《金光明经》所述摩诃萨陲太子舍身饲虎的内容。明朝末年,大慈寺壁画大多毁于战火,但从一些壁画残本中,我们仍然能够感悟到大慈寺壁画的神韵。
4.寺庙建筑精美
唐宋时期,大慈寺占地千亩以上,是蜀中最大的佛寺,寺院范围南越糠市街,北抵布后街,东临府河,西至现在的总府路四川省图书馆。当时的大慈寺占地千亩以上,加上后部园林,其墙垣绵延当时城东之小半,大体分为前寺、中寺、后寺三部分,规模极大,整体建筑宏伟壮观,雕梁画栋,金碧辉煌,属院众多,共有96个院,如鲜于院、玄宗御容院、三学延祥之院(简称三学院)、雪峰院、中和院、寿宁院、竹溪院、玉溪院、百部院、千部院、白马院、承天院、水陆院、如意轮正觉院、西大悲院、大将院、药师院、六祖院、保福院、极乐院、石像院、慧日院、吉安院、寿宁院、华严院、兴善院、西林院、揭谛院、弥勒院、宝胜院、锦津院、东律院、灌顶院、楞严院、承天院、超悟院等;阁、殿、塔、厅、堂、房、廊之数在8524间以上,如华严阁、金绳阁、大悲阁、罗汉阁、普贤阁、文殊阁、观音堂、大轮堂、四绝堂,其中包括了大慈寺内的甘露寺、韦公祠、供奉造纸术发明者蔡伦的小庙等。大慈寺的多处院、阁,曾为皇帝行宫。《唐书•崔宁传》曾记载鲜于院为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建,“院宇甚华丽”,玄宗曾以为行宫。据《大慈恩寺画记》记载,李之纯曾任成都府路转运使,在任两年多的时间中“晚暇与朋僚游(大慈寺),所观者才十一二”,可见当时大慈寺之大。
宋以后,大慈寺历经兴废,多次毁于兵火,如明代宣宗宣德十年毁于火灾,英帝正统十一年重修,明代后期天启年间大慈寺仍在“府城东门内,唐至德间建,玄宗书‘大圣慈寺’四字尚存”,明代末年的战争使大慈寺毁为平地,荒凉了一段时期。据《华阳县志》记载,清朝顺治年间曾重建,嘉庆时期的大慈寺已初具规模;至同治六年大慈寺陆续大规模重建,占地40多亩,奠定了现今大慈寺的规模。晚清宣统年间大慈寺中一座刻有“永镇蜀眼”秦篆的古佛像、一尊高二丈五尺的接引佛像仍存。民国时期,曾有一支军阀的队伍驻于寺内,毁大铜佛数座以铸铜元;后在三十年代军阀爆发“成都巷战”等,大慈寺遭到了较大破坏。1949年,蜀都大道等城市建设,占用了大慈寺的部分地段,今锦江区政府对面原为大慈寺的花园,大慈寺的正门原正对笔帖式街、顺城东街方向。目前大慈寺的主体建筑有山门、弥勒殿、大雄宝殿、说法堂、观音堂、藏经阁等。其中,大雄宝殿、藏经阁以四川所产峡石为柱,尤为雄伟壮观,藏经阁高敞爽朗,重檐歇山顶,阁上四壁原供奉脱纱小佛千余尊,蜚声四海。
大慈寺门前矗立着一座焚字炉,上书“惜字得福”四个大字。《颜氏家训》认为文字是“古圣贤心迹”,所以字纸不可秽用,废弃的字纸应该焚化。这反映了成都人尊崇文化、敬字惜纸的传统美德,也是大慈寺作为成都文化中心的重要见证。
5.无相禅茶
大慈寺的禅茶堂,早在1300年前的唐代就已兴建,堪称成都历史最悠久的“茶馆”。当年无相禅师在参禅悟道的过程中,为了提神醒脑、解困除乏,养成饮茶的习惯。他倡导以茶会禅,将禅机融入茶艺,以茶艺来昭示佛理,开创“无相禅茶之法”,并在寺中修建了专供品茶悟道的禅茶堂。大慈寺禅茶共有12道程序:静禅心、入禅堂、焚香祈愿、圣水涤凡(涤具)、佛祖拈花(观茶)、菩萨入狱(投茶)、漫天法雨(泡茶)、菩萨点化(分茶)、普渡众生(敬茶)、禅茶一味(闻香观色)、即心即佛(品茶)、畅叙禅机。禅茶的每一道程序都融汇一个佛理,昭示一种禅机。由无相禅师开创的禅茶之道,不仅国内广为流传,还远渡重洋传到了韩国、日本等地,成为韩国、日本茶道的起源。如今传承大慈寺千年禅茶文化的禅茶堂依旧古朴典雅,清香弥漫,许多来大慈寺参拜的市民游客在此品茗,听禅,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体会禅茶所蕴含的淡泊宁静。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
6.佛法交流
大慈寺佛法精湛、声名远播,形成以佛法交流为内容的中外文化交流的平台。许多朝鲜半岛、东瀛列岛的佛门弟子,不远万里来到成都大慈寺求法问道。唐玄宗开元十六年,朝鲜半岛的新罗三太子(新罗国盛德王金兴光之第三子)与新罗“遣唐使”一同渡海到中国寻师求佛。为深造佛学,他云游至蜀,在大慈寺广开讲席,所传“无忆,无念,莫妄”的三句法门,慧人无数。今天的大慈寺秉承唐宋遗风,多次接待国际佛教团体,举办佛教活动,成为中外佛学文化交流的中心。
二、商业文化积淀厚重
1.码头繁荣,促成大慈寺周边贸易集市
唐宋时期,成都水运码头由万里桥移到东门大桥,唐朝韦皋镇蜀时,开凿解玉溪等水道会入城中,经城中斜向东南至大慈寺,白敏中拓宽金水河,在大慈寺一带与解玉溪汇合,向城东直入内江。大慈寺东邻东门码头,南近东大街,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迅速成为繁华的贸易集市。大慈寺片区迅速成为商贾、工匠、倡优杂戏、医巫僧道等各种人进行商品交易和献艺表演的之地,被称为成都“东市”,是唐代中后期成都著名商业区“三市”——东市、西市、南市之一。当时成都三市出售各种农副产品、药材、盐、铁制品、纺织品、马匹及其他物品,是四川地区最大的物资集散中心与商业贸易区。此后,雪锦楼、锦官楼等毗邻建筑先后建成,大慈寺一带更成为四川地区药材交易的中心、繁荣的百货市场及热闹的娱乐场所。《宋代蜀文辑存》记载,唐宋时代的大慈寺“地居冲会,百工列肆,市声如雷”;《嘉庆华阳县志》也有“据阛阓之腹,商列贾次,茶炉药榜,篷占筵专,倡优杂戏之类,坌然其中”的描述,寺院成为了戏场商肆、行医卖卜、终岁市集游乐之处。所谓“药榜”,即四川地区的“药市”,每年九月就在大慈寺和玉局观前举行,唐代时四川就盛产药材,不少药物作为土贡进呈朝廷;当时“成都故事,岁以天中、重阳时,开大慈寺,多聚人物,出百货其间,号名‘药市’”;“医人鬻艾,道人卖符,朱索彩缕长命辟灾之物,饭筒角黍,莫不咸在”,大慈寺一带成为四川地区药材交易的中心。
2.月开一市,各不相同
宋人祝穆所著《方舆揽胜》记载,大慈寺前还有季节性集市,如正月灯市、二月花市、三月蚕市、四月锦市、五月扇市、六月香市、七月宝市、八月桂市、九月药市、十月酒市、冬月梅市和腊月桃符市。每年春季的二月八日、三月九日大慈寺前开始“蚕市”,宋代成都知府田况赋作《成都遨乐诗》一组,中有《二月八日大慈寺前蚕市》《三月九日大慈寺前蚕市》二诗;柳永吟咏成都风物的《一寸金》词也提到了成都蚕市,盛颂“井络天开,剑岭云横控西夏。地胜异,锦里风流,蚕市繁华,簇簇歌台舞榭。雅俗多游赏,轻袭俊,靓妆艳治,当春昼,摸石江边,浣花溪畔景如画”,蚕市声名之远,使未曾足履成都的大词人都向往不已。因此大慈寺一带成为各种商品的贸易集市,规模逐渐庞大。“野氓集广廛,众贾趋宝坊”,“倡优杂戏之类,坌然其中”,也就是“四方之人,至于此者,徒见游手末技,憧憧凑集,珍货奇巧,罗陈如市,只以为嬉戏炫鬻之所”。清代,大慈寺前成了成都“菜市所在”;并且以出售“三义公之红纸”等商品而闻名,寺后建有广生庙,供奉着送子神。
3.蜀人好宴游之风,形成大慈寺区域繁华
每逢元夕、上元、寒食、端午、七夕、中秋、重阳、冬至、春节等传统及施盂兰盆会等佛教节日,皇帝王公、名流学士、地方士绅及四井香客、八方商贾云集寺中,或赏画吟诗,抒怀叙物,宴饮集会,或进香供佛,诵经施食,游览诸区,不仅增添了寺中的墨宝碑刻,加深了文化积淀,而且诸色人等各取所需,皆大欢喜。如五代后蜀明德元年夏,先主孟知祥率臣下至大慈寺 “避暑,观明皇、僖宗御容已,宴群臣于华严阁下”;后蜀广政元年,后主孟昶率臣下“游大慈寺,宴从官于玉溪院,俳优以王衍为戏”,大慈寺又成为表演戏剧之所;田况《成都遨乐诗》有《三月十四日大慈寺建乾元节道场》《七月十八日大慈寺观施盂兰盆》《冬至朝拜天庆观,会大慈寺》三诗,表现了大慈寺在不同时节的热闹。故唐宋时代的大慈寺成为四川及成都官吏经常举行宴集之处。除此之外,当时宴请官吏的官署厅事为“设厅”。《岁华纪丽谱》等古书称“早宴大慈寺之设厅”“晚宴于大慈寺之设厅”,相当于把一部分官署搬到了寺中。
4.夜市兴起,更添繁华
唐宋以来,大慈寺一带就是兴盛的商业之区,不仅白昼进行商贸交易,而且有“锦江夜市”,分布于沿锦江一带和大慈寺等地,一直要交易到三更时分。大慈寺在佛教节日往往“燃灯”诵经,更添喜庆氛围。宋代诗人陆游赋有《天申节前三日,大圣慈寺华严阁燃灯甚盛,游人过于元夕》诗;田况《成都遨乐诗》有《七月六日晚登大慈寺阁观夜市》;当时官吏在“七夕”(农历七月初七夜,相传牛郎织女银河相会之期)登大慈寺门楼宴饮观赏夜市,吟诗作文成为一种风尚,如“七月七日,晚宴大慈寺设厅,暮登寺门楼观锦江夜市,乞巧之物皆备焉”,传世有李焘《十五日同登大慈寺楼》诗,以至北宋徽宗政和六年下诏禁止,但未完全取得成效。到了近现代 ,“锦江夜市”仍热闹非凡,徐心余《蜀游闻见录》记录了东大街一带“夜市”的景象。
翻阅典籍,浏览关于大慈寺佛教文化、商贸文化的记载,可以看出当时的岁时土俗、民间物态、山川风物,是一幅成都版的《清明上河图》。
5.庙市合一,太古里传承经典,显别样时代魅力
大慈寺庙市合一的形态自唐宋一直延续至今。2013年,成都国际金融中心建成投运,成为成都的地标性商业建筑。2014年,紧邻大慈寺的高端商业综合体成都远洋太古里开业运营,“里”是中国城市发展进程中一个重要的概念,它的含义类似于西方文化中的“巷”和“小路”。对于成都远洋太古里而言,“里”更代表着开放式购物街区的建筑理念,成都远洋太古里将成都的文化精神注入建筑群落,通过保留古代街巷与历史建筑物的方式,用川西风格的青瓦坡屋顶与大面积落地玻璃幕墙营造体现开放自由理念的城市空间。现代商业体与大慈寺的完美融合,使大慈寺再现庙市合一的盛况。
唐宋江南馆遗址位于成都市江南馆街北侧,东为大慈寺片区、西与红星路相邻,北为蜀都大道,面积约5万平方米。唐、宋堆积最为丰富,发掘面积共4800平方米。共发掘唐宋时期大小排水渠16条、铺砖面路4条、泥土支路4条、房址22处,明清时期道路1条、房址8座、井3口。唐宋时期主次街道、房址和与其配套的地下排水系统是本次发掘的重大发现。成都在唐代经济十分发达,誉称“扬一益二”,在宋代诞生了世界最早的纸币——交子,无不昭示成都在唐宋时期中国经济社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遗址是繁荣发达的唐宋成都城重要的实物见证。遗址发现纵横交错长达数十余米的铺砖街道在中国城市考古史上十分罕见,在现代化都市中心发现如此大规模的唐宋时期重要遗存堪称独一无二。
在成都市确定的四大历史文化保护区中,大慈寺片区以其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为锦江区现代服务业、文化创意产业、社会文化事业发展提供支撑。
参考文献
[1]王川:《神秘的宗教》,广州出版社,1997年版。
[2]范成大:《成都府古寺名笔记》,载明人冯任修、张世雍等纂:《天启成都府志》卷44。
[3]傅崇矩:《成都通览》上册,巴蜀书社,1987年版。
[4]傅崇矩:《成都通览》,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5]成都市锦江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锦江名片》,新华出版社,2011年版。
[6]成都市锦江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锦江街巷》,新华出版社,2009年版
论文作者:袁悦幸
论文发表刊物:《知识-力量》2019年2月下
论文发表时间:2018/12/19
标签:大慈论文; 成都论文; 锦江论文; 唐宋论文; 壁画论文; 成都市论文; 时期论文; 《知识-力量》2019年2月下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