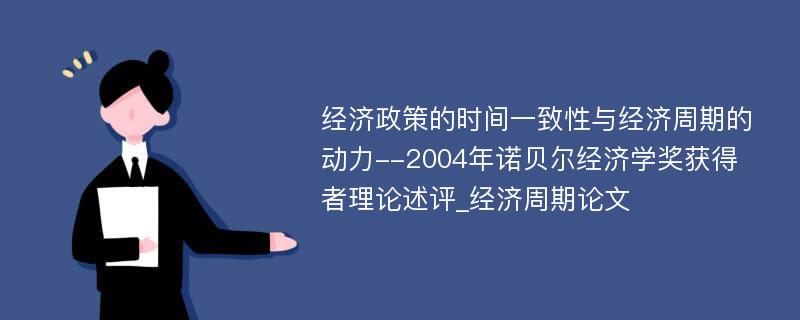
经济政策的时间一致性和经济周期的驱动力量——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理论评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政策论文,得主论文,力量论文,理论论文,经济周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瑞典皇家科学院将2004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挪威经济学家芬恩·基德兰德(Finn Kydland)教授和美国经济学家爱德华·普雷斯科特(Edward Prescott)教授,以表彰他们在动态宏观经济学的两个重要领域——经济政策的设计和经济周期的驱动力量——作出的开创性贡献。并且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的理论研究对许多国家的金融和货币政策的设计和制定产生重要影响。他们的学术成就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对宏观经济政策运用过程中的“时间一致性难题”的分析研究,为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的实际有效运用提供了思路;二是在实际经济周期的研究中,通过对引起经济周期波动的各种因素和各因素间相互关系的分析,加深了人们对于这一现象的认识。同时他们的分析方法也为后续研究者开展更广泛的研究提供了基础。
一、时间一致性和经济政策的设计
20世纪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期,宏观经济研究特别关注私人经济主体的预期问题。一方面,弗里德曼(1968)和费尔普斯(1967,1968)强调了预期是经济产出的重要决定因素,并在基于菲利普斯曲线的失业理论的分析上,指出实际的通货膨胀和失业的关系是依赖于预期的通货膨胀。另一方面,卢卡斯(1972,1973)在理性预期假说的基础上,探讨了在给定可获得信息的基础上经济主体如何作出对未来经济事件的最优可能预测。而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对经济政策设计的分析为预期的形成又增加了一个研究的维度。他们指出政府经济政策的设计和制定是受制于时间一致性问题(time consistency problem)的。所谓的时间一致性问题是指,预先是最优的政策,在单个经济主体对其形成理性预期并影响个体行为后,此政策就不再是最优的。在政府不受约束的条件下,政府将可能选择其他的政策。当宏观经济政策是时间一致性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宏观经济政策始终是最优的,经济政策成效明显;而当宏观经济政策是时间不一致性的,原先最优化的宏观经济政策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成为次优政策或非优化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政策可能会失效。
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在他们1977年合作的论文《规则胜于判断:最优计划的不一致性》(“Rules rather than discretion:The inconsistency of optimal plans”)中首先提出了上述问题,并且考察了产生此问题的原因。他们的模型通过假定政府选择政策是为了使公众的社会福利最大化从而将政府决策制定内生化。他们继续沿用了弗里德曼和费尔普斯关于预期是经济产出的重要决定因素的假定和卢卡斯的理性预期假说,在博弈论框架中研究了经济政策的时间一致性问题,从而在理论研究、政策实践和方法论三个方面取得了重要的进展。
理论研究上,他们是通过比较有约定条件下的均衡解和没有约定条件下的均衡解来分析产生最优政策的时间不一致的原因的。所谓有约定的条件是指:政府首先一次性地选择一种政策,然后单个经济主体相应地决定自己要采取的行动,这种情况类似于公众可以用某种手段迫使政府遵守事前的约定。而没有约定的条件是指:单个经济主体首先选择自己的第一期行动,接着政府相应地选择自己的第一期行动;然后单个经济主体再选择自己的第二期行动,如此循环往复进行序列决策,这种情况意味着公众缺乏有效的手段来约束政府的行为。如果在有约定的情况下得到的均衡解与在没有约定的情况下得到的均衡解是一致的,那就不存在最优政策的时间不一致问题。因为对政府来说,无论是否受约束,它都会选择同样的最优政策。反之,则会出现时间不一致问题,这会导致政府在没有约定时宁愿选择别的最优政策。正是由于政策制定者是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里寻求短期政策目标,因而会面临这样的两难选择:当经济偏离政策目标时,要么政府采用规则的政策会被公众的理性预期所抵消,从而难以达到政策目标;要么政府为了追求政策目标,通过相机抉择来“欺骗”公众。但在政策起到作用的同时也使政府遭受到信誉问题,可能会导致政府此后的政策不再被公众所信赖,而缺乏可信性的结果导致了非帕累托最优。可见,政策的时间一致性和政府的信誉之间存在着交替关系。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在理论上的最大贡献就在于将宏观经济政策设计问题建立在微观经济个体的行为模型之上,积极探寻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
政策实践上,关于经济政策的时间不一致问题的讨论有助于人们区分相机抉择的政策与规则一致政策之间争论的实质。可以认为,规则一致政策描述的是有约定情况下的政策,而相机抉择政策描述的是没有约定情况下的政策。按照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的观点,社会不能在有约定的均衡和没有约定的均衡之间自由选择。因为约定的手段要么可以得到,要么不可以得到,它本身不是可供选择的目标,因此社会也不能在规则一致或相机抉择政策之间自由选择。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还得出结论,认为在不同时点决策中的时间不一致性会对社会产生严重的不利影响。他们考察了在较难改变的长期规则下执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可能性,指出长期规则的缺点就在于限制了制定经济政策的灵活性,尤其是在面对未预期的突发事件时(主要是经济周期冲击)。他们的研究被广泛地应用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方面,对许多国家(如新西兰、瑞典、英国和欧元区)政策的设计和制定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货币政策方面,他们较好地解释了20世纪70年代治理通货膨胀失败的原因;在财政政策方面,分析了政府在税收政策方面的时间一致性问题。这都使得时间一致性问题成为了现代经济政策研究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方法论上,由于政府和公众的关系可以理解为一种相互依赖的博弈关系,因此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就尝试采用博弈论框架来分析经济政策的时间一致性问题。在重复博弈框架中,信誉(Credibility)机制是单个经济主体迫使政府采取时间一致性政策的关键。重复博弈使博弈者的行动依赖于过去的行为。在这种博弈中,一个总是在过去表示承诺的政府可能会决定通过采用意外的货币冲击来愚弄公众。诚然在货币冲击阶段政府得到了产出收益,但同时政府信誉受到了损害,因为单个经济主体会预期有较高的通货膨胀率。于是在重复博弈环境里,政策制定者就不得不在欺骗带来的当前收入与较高通货膨胀预期的信誉损失之间进行权衡。所以说,信誉具有惩罚竞争对手不良行为的威慑力量,并使博弈达到均衡。他们运用不同的博弈均衡概念分析不同的模型和实例。例如,引入纳什(1950)的博弈均衡概念分析政府和公众的博弈过程。在研究基于连续理性的所有经济个体(包括私个体和政府)的预期时,认为其与不考虑当期选择的未来均衡行为一致,因此使用了泽尔腾(1965)的子博弈完美均衡。另外,他们在考察无限时间维度的博弈模型时,定义并运用了一种特殊的均衡,即马尔可夫完美均衡。这一研究运用了更符合实际的博弈论框架来解决经济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时间一致性问题,突破了传统宏观经济政策分析中的最优控制理论范式。
二、实际经济周期及驱动力量
关于经济周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对长期统计资料的整理分析研究经济周期的规律和特征,并根据周期时间长短之不同划分类型;二是对于经济周期原因的探讨,可分为外生经济周期理论和内生经济周期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经济学家们都延续了凯恩斯的传统,从二分法的角度分别研究长期的经济增长和短期的经济波动,坚持认为长期的经济增长是受总供给决定的,技术进步是重要的驱使力量;但短期的经济波动被认为是受围绕着长期增长趋势的总需求驱动的。因此,传统的经济周期理论基本上是把经济增长与经济周期看作是两种相对独立的现象。且当时现实中的有周期无增长及有增长无周期的现象,也为传统经济周期理论分别研究经济增长与经济周期这两种现象提供了一定的支持。因为经济增长注重于资本的积累和技术的进步,而经济周期则注重于存量资本及劳动力的利用程度,所以二者具有不同的研究对象。但到了20世纪的80年代,宏观经济学呈现出显著的发展态势,其中之一就是实际经济周期理论(Real Business Cycle Theory,RBC)的出现。它是继70年代货币幻觉假说引起经济周期的理论之后现代经济周期理论的两个主要发展方向之一,另一个方向为粘性价格周期理论(Stick-Price Business Cycle Theory)。当时有许多经济学家试图用实际因素去解释经济周期波动的根源,而基德兰德—普雷斯科特模型被认为是所有用实际因素解释经济周期的模型中最有名的一个。基德兰德与普雷斯科特在1982年合著的《置备新资本的时间和总量波动》(“Time to build and aggregate fluctuations”)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基德兰德—普雷斯科特模型(以下简称基—普模型)。普雷斯科特与基德兰德在此方面的重大贡献就在于他们运用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分析了经济周期背后的驱动力量。
实际经济周期理论所建立的是完全的瓦尔拉斯形式的模型,因此又称均衡经济周期模型。他们的理论主要基于以下基本假设和前提条件:第一,经济主体是理性的,即在现有的资源约束条件下追求各自的效用和利润的最大化;第二,理性预期假设成立;第三,市场有效性假设成立(即市场能够出清,不存在市场失灵问题);第四,就业变动反映了工作时间的自愿变化,非自愿失业不存在,工作和闲暇在时间上具有高度替代性;第五,货币中性假设成立。在这些假设和前提之下,实际经济周期呈现出以下特征:一是,技术冲击替代了货币冲击成为主导的冲击因素,即认为总产量和就业的波动是由可应用的生产技术的随机变化引起的,并且各种传导机制将使最初的技术冲击扩散开来;二是,不再关注有关总物价水平的不完全信息,而这一点曾在卢卡斯的早期货币幻觉模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三是,通过整合经济增长理论与经济周期波动理论打破了宏观经济分析中的短期与长期的二分法格局。
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将以索洛残值(Solow residuals)表示的技术进步看作是产生经济周期的主要驱动力量,因此把经济增长和周期波动这两种现象看作是相同过程的不同方面,进而强调了同时解释两种现象的可取性。他们通过研究技术进步率在经济不同方面的短期变化的传导,将经济增长与经济周期分析进行了整合。并将模型构建在典型的微观模型(效用最大化消费者和利润最大化厂商)的假定上,关注预期因素的应用。研究表明了投资和相对价格变动传导了经济中技术进步率的变动效应,因此产生了围绕经济长期增长路径的短期波动。根据基—普模型的分析,经济周期波动的根源是实际因素即经济供给方面的波动,其中最主要的是技术冲击。技术冲击具有随机性质,它使产出的长期增长路径也呈现出随机的跳跃性。当技术冲击最初发生于某个部门时,由于社会生产各部门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因此会通过传导机制(propagation mechanism)引起整个宏观经济的波动。另外,宏观经济的持续波动可能是由连续的单方向的技术冲击造成,也可能是由一次性的重大冲击带来的。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在一个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基础上,指出了引起经济周期的背后驱动力量正是供给方面的技术冲击,从而对宏观经济的理论分析研究产生了深远的推动意义。
尽管实际经济周期模型体现出经济周期的上述某些质的方面的特征,但还需要确定它是否能从数量方面解释经济波动。因此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从测度技术冲击和对模型进行检验两个方面对波动的数量方面进行了分析。一是,探讨了区分和测度技术冲击(即技术进步率)的问题。他们的分析是建立在索洛残值法的基础之上的。在给定模型的结构时,主要的参数是技术冲击的方差。根据索洛的方法就是把技术变化定义为总产量的变化减去劳动和资本投入的加权贡献之和,也即索洛残值测度总产量中不能用资本和劳动投入的可测度的数量变化来解释的那部分变化。遵循着索洛的方法,他们把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测量为总生产函数的剩余,同时选用了马尔可夫随机过程来求得这些序列中的序列相关关系。他们在最新的一项研究中发现,战后美国产量方差的大约70%可以由索洛剩余的变差来解释。二是,对模型进行了检验。在实证研究过程中,他们运用所谓的校正(calibration)方法进行研究。校正是一种估计方法的简单形式,它通过给模型中的某些参数选择适合数据子集的运算法则从而为其确定一个“合理的”数值,然后从美国经济周期的经验数据估计出模型中其它未定的参数。然后为未观察到的生产率扰动选择一个外生决定的方差值,最终说明经济中主要总量的实际周期行为。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通过借鉴其他领域应用研究中的行为参数估计,对他们模型中的自由参数进行了限制。例如,他们利用劳动份额的恒定对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的参数进行限制;在对金融市场进行分析后,他们对控制时际替代/不愿承担风险程度的偏好曲率参数进行了限制。其中最关键的参数是资本生产率的方差,它表示对经济的初始技术冲击的大小。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发现他们的模型与资料吻合得很好,并且这种吻合在他们的重要假设变化时也同样是牢固的。这种方法非常实际且具有可操作性,它无需解决模型中所有参数的确定问题,而且能为模型的特殊变化是否能更好地解释数据提出明确有用的方向,从而改进了宏观经济分析的方法。
综上所述,基德兰德与普雷斯科特的研究改变了传统的宏观经济理论,为宏观经济政策的设计和经济周期波动理论的改进提供了基础,对动态宏观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他们的分析也加深了人们对现代宏观经济理论和政策的理解,为探寻宏观经济理论的微观基础开辟了一种全新的思路。
标签:经济周期论文; 诺贝尔经济学奖论文; 凯恩斯经济周期理论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 经济模型论文; 宏观经济学论文; 预期理论论文; 市场均衡论文; 诺贝尔奖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