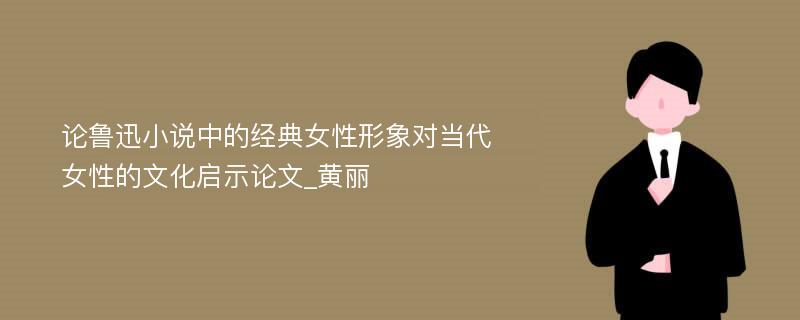
——从波伏娃《第二性》视角反观鲁迅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黄 丽 青岛大学文学院
【摘要】本文试图从法国女权主义作家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的理论性代表作《第二性》出发,反观鲁迅小说中的三个有代表性的女性——子君、祥林嫂和爱姑,深入到一个更深层次的思想层面中去,分别来分析家庭主妇、寡妇和离婚女性的心理与处境,以期对当下女性的文化处境有所启示。
【关键字】鲁迅;波伏娃;《第二性》;子君;祥林嫂;爱姑
在当代学术界,有关鲁迅小说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已经形成了多视角规模化的研究体系。起初,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从作家和人物的视角来揭示女性悲剧命运的社会根源,并以此来批判当时的黑暗社会与麻木的民众。新时期以来,已有学者开始离开作者创作的本体意义,转而关注女性主义视角下的人物解读,或分析男权中心主义下这些女性的悲剧原因,或赋予这些女性以妇女解放的积极意义,我认为这还远远不够。解读此类人物的目的应该是多样化的,特别是在当代这个可以说已经逐渐步入男女自由平等的时代,女性人物形象本身所包含的意义应该给当代女性一些有益的启发与警示。本文就将从波伏娃的女性主义理论著作《第二性》的有关客观理论视角出发,重新剖析鲁迅小说作品中的三位经典女性形象,试图解读她们传达出来的、不为人知的一面,进而发掘出学术界不曾明确探讨的女性视角。
一
鲁迅在《伤逝》中塑造的女性人物子君,一向被认为是鲁迅笔下知识分子女性的代表,她与涓生都有着男女平等、爱情自由等新思想,为了争取个人幸福,他们勇敢地向封建势力展开挑战,家庭的束缚、社会的非议全被他们置于脑后。然而,子君身上是否真的存在女性的进步?我们需要分析她的反抗动力及其结果。
小说中谈到子君来到涓生的住处,屋里充满了“我的语声”——涓生的语声,子君“总是微笑点头,两眼里弥漫着稚气的好奇的光泽。”子君此时俨然是站在一个倾听者的位置上扮演着一个崇拜者,而且在涓生看来,子君是没有脱尽旧思想束缚的,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就像波伏娃所说,“当少女尚处在她的家庭的庇护下时,她尽可能地利用她所拥有的去反抗和期待变化,去赢得婚姻本身。”子君受到五四新思潮的浸染,并利用这一思潮去反抗礼教以赢得婚姻,所以当子君说出“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力”时,是盲目的爱情力量在驱使她反抗礼教,新知识新思想成为她当时唯一能拿来实现婚姻的工具。而当他们真正拥有了彼此,拥有了家庭,子君立刻被自身固有的传统观念拉入不平等、非自由的境地——沦为日复一日无所事事的家庭主妇。由此看来,女人“尽管获得了新的见解,尽管鹦鹉学舌地嚷嚷着原则,可是对事物仍保留着自己的特殊观点”,子君成为家庭主妇所引起的悲剧命运也因此而不可避免了。
关于婚姻在女性生活中所起的转折作用,波伏娃提到了这样的一个普遍现象:作为女孩子的时候她一无所有,“但她在梦想中期待一切”,而当进入婚姻生活以后,她“总算有了自己的一点点地盘,却会苦恼地想,永远只有这么一点点,永远就是这个丈夫,这个住处。…没有任何重要的事情可盼望的了。”子君对于这一点采取了绝对的顺从态度,她养鸡、养狗、做饭、打扫,“管了家务便连谈天的功夫也没有,何况读书和散步。”家变成了世界的中心,外部世界对于她来说仿佛消退了,女人总是喜欢用做家务来证实自己的存在,“通过她占有的东西来实现自我。”子君没有工作,也没有孩子,她自认为所占有的东西就是她的油鸡和阿随,她非常重视它们,以至于为了油鸡与房东太太暗斗,为了让阿随吃胖而把本应该给涓生吃的饭菜先给了狗。或许这在平常人看来着实过分,但对于子君,这似乎是她自我实现的唯一途径。就像王富仁先生所说的,“他需要有精神的慰藉,需要维护自己的尊严,需要在人们的蔑视中找到自己的精神支撑点,而喂狗饲鸡便成了她不能不有的精神需要。”
在当代的大众认知中,真正解放思想的女性应该有自己的职业,但《第二性》提出了这样一种女性心理:即使女人很解放,“她也由于男人们有经济优势而宁可结婚也不愿意有职业,她倾向于找一个地位比她高的丈夫,或者希望丈夫能比她获得更大、更快的成功。”可以说,婚姻对女人来说是一种比其它许多职业都更有利的职业,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情况存在的前提是丈夫的成功。子君呆在家中做着千篇一律的工作,当涓生被局里辞退,子君便显出凄然的神色,她所依赖的丈夫正面临生存危机,她自然也感到自己的这份家庭主妇的职业受到了威胁,但是听天由命的思想使她只是沉默。小说中三次写到涓生被辞退以后子君的沉默,第一次是在涓生向她说明不要在他工作的时候来叫他吃饭时,“她明白之后,大约很不高兴罢,可是没有说。”子君用沉默在做无声地抗议,毕竟做饭也是女人的一大功业,子君的自尊由此受到了伤害,这与他后来将涓生的饭菜给了阿随也有一定的关系。第二次是在涓生把阿随送出去之后,子君仍回应以沉默,正如前面分析的,涓生作为一个男性,他并不能懂得阿随对于子君来说是她心理上自我实现的途径这一事实,也就是说涓生送走了阿随是在否定子君的自我价值,这是导致子君态度转向冰冷、甚至于麻木的重要原因。第三次是涓生告诉子君他的真实想法——“我已经不爱你了”以后,“…只有沉默。她脸色陡然变成灰黄,死了似的。”到此,子君的家庭主妇命运也宣布走到了终点。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子君虽然是知识分子,却仍牢牢地固定在传统女性思维的枷锁中,这是在任何时代包括现在都无法避免的,女性和男性的分工永远是明显的,无论她有没有知识与职业、是否进步,都逃脱不了社会加给她的女性使命,就像男性也自始至终要承担自己的男性使命一样。当代女性要认清这一点,尽量平衡各方面 的利弊,而不是盲目追求所谓的“男女平等”。子君的悲剧给当代女性的教训是:作为一个家庭主妇,你可以没有职业,但也要继续丰富自己,让自己在男性世界里保持话语权,而不是只有沉默,这样才能找到自我实现的正确途径。
二
谈到鲁迅小说中的女性,不得不谈到的一个重要人物便是祥林嫂——《祝福》中那个勤劳、本分却不幸的寡妇形象,给读者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寡妇也是鲁迅小说中的一组重要描写对象。诚然,祥林嫂的遭际必然引起人们的同情与批判,或者像某些学者认为的,鲁迅在写作时由于自己的母亲是寡妇,所以对祥林嫂倾注的只有同情没有批判。而如果完全站在女性角度来剖析寡妇的心理,我们可以从这一早已固化的形象中展开新维度的探索。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
波伏娃认为,“女人之所以在经济上重新取得了重要地位,是因为她走出了家庭,……只有寡妇才享有经济独立的地位,……而独身使他降到寄生者和贱民的地位。”我们知道,女人未出嫁之前生活在父母的家庭,出嫁之后生活在丈夫的家庭,显然只有寡妇在一定意义上摆脱了家庭的束缚,由此看来,寡妇的身份也不是全无是处。起码对于祥林嫂来说,即使她的寡妇身份遭到厌恶,她依然非常享受自己在鲁四老爷家“经济独立”的“贱民地位”。她“整天的做”,“食物不论,力气是不惜的,”这是一种受剥削的奴隶生活,本来是极为不公平的生活待遇,“她反满足”。然而被迫改嫁却剥夺了祥林嫂的独立生活,她被迫投入了一个不再需要独立的生活环境。最初的反抗无疑受到贞洁观的影响,可也不能忽视,顺从也是女人的天性,“舒舒服服的已婚的或被人供养的女人,对打算依靠自己成功的女人是一种诱惑”。虽然祥林嫂受传统观念的影响要保持忠贞,但既然这潜在的诱惑已成现实,顺从的奴性也便跳出来延续了她的生活。这大概能解释祥林嫂“为什么后来又肯了”,当然不是像她说的“他力气大”。
照这样看来似乎一切都还过得去,那么祥林嫂的悲剧到底起于何时何地?波伏娃深信“给女人造成过分沉重负担的不适和疾病,基本上由于心理原因造成的。”小说中祥林嫂在后来也的确呈现出了心理不正常的迹象——逢人便讲她儿子阿毛被狼叼走的故事。她久久走不出这件事给她造成的心理阴影,是源于对她母性的剥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对一个贫弱无依的守寡妇女来说,子女是残存着的唯一的精神寄托,唯一的希望所在。”失去阿毛对祥林嫂来说最起码在心理上是致命的。按照波伏娃的观点,孩子是母亲的第二自我,是一种拥有支配权的充实,失去孩子使祥林嫂既坠入了空虚,又失去了自我,这直接导致了她精神的压抑、心理上的苦闷麻木。而在当时她所面临的环境中试图重塑自我是相当艰难的。“女人不被允许做一些积极的工作,因而无法赢得做一个完整的人的资格。”祭祀对于鲁四老爷家来说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然而祥林嫂却被禁止沾手,文中出现的四婶多次对祥林嫂说的“祥林嫂,你放着罢”,体现了对祥林嫂自我人格的打击,她也因此再也无法找到自己作为一个女人的位置。
寡妇作为女性的一种特殊存在,在当代这个婚姻自由的时代或许并不那么常见,也并不那么受鄙视,但我们须从对祥林嫂的遭际的分析中得出,独身对于一个能找准自我位置的女人来说并不是一件坏事,它反而能激发女性的独立意识。一旦她找不到属于自己的位置,便会被束缚自己的巨大心理障碍所吞没。
三
鲁迅小说《离婚》中的爱姑,作为一个敢爱敢恨的女性,在她的这场“离婚案”中,似乎尽情向我们展示了她据理力争的反抗精神。长久以来,爱姑的反抗被视为对封建宗法制度的公然反叛,甚至被视为中国近代社会男女思想平等的萌芽,然而在这种反抗里面也投射出现代社会离婚案中的女性心理及其处境,让我们带着当代的目光重新审视爱姑的反抗。
既然丈夫已经出轨,婚姻必然破裂,否则妻子将受到更大的不公,爱姑不是不知道这一点,那她非要闹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回到夫家,还是将丈夫与公公投入牢房?闹到这一步,前者显然没有太大的希望了,对于后者这种报复心理能否得逞,我们需要分析当时社会道德舆论的倾向。王富仁先生认为,“从她一口一个‘老畜生’、‘小畜生’的话语来看,她也绝不是一个‘三从四德’的‘好媳妇’。”就算是普通老百姓也会因为这些称呼而大概得出爱姑的品性如何,更何况七大人饱读诗书,听到爱姑的言辞自然捕捉到了解决此事的舆论倾向,就连爱姑也看出了事情不可改变的发展方向。既然如此,那似乎经济上的补偿是没有余地的选择了。进而推及到当代社会,夫妻往往非要将离婚闹上法庭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最大限度的争取自身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这一赤裸裸的目的对于已经即将陌路的离婚双方无疑都存在巨大吸引力。
不管爱姑在不在乎这赡养费,他爹庄木三肯定是在乎的,庄木三当天便带了红绿帖,最后识趣地清点了赡养费的数目。爱姑“要闹得他家败人亡”的直接结果,也不过是涨了十块赡养费而已,爱姑之前在堂上对慰老爷的公然不服,也在最后拿钱走人慰老爷留他们喝酒时变成了“是的,不喝了。谢谢慰老爷”这样一句不痛不痒的客套话。单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爱姑的“闹”还谈不上是彻底地反抗,在一定程度上反而让我们更容易把爱姑放在一个可怜的位置上。
“一夫多妻制一向程度不同地被公开容忍,……但丈夫必须尊重合法妻子的某些特权,如果她受到虐待或侮辱,妻子有权回到娘家,自己提出分居或离婚。”这是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提出的当时法国的婚姻状况。从中我们可以领悟到,这才是把离婚女性放在了正确的位置上,是妻子有权利提出离婚,离开欺凌她的丈夫,而不是丈夫出轨后还理直气壮地提出休妻。女性由于生理上的种种原因,被定位为一个弱势群体,连女性本身也这样认为。“结婚,是社会传统赋予女人的命运”,也是女人总是试图借以改变命运的手段,毕竟结婚代表她可以得到丈夫理所应当的供养,当然这以她对家、子女和丈夫甚至是公婆的细心照料为代价。在女人看来,相对于她以自身付出的代价来说,她得到的这份供养实在是微不足道的,她甚至认为这是一种牺牲。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遇上了男方过失离婚,女人会觉得自己受到了莫大的伤害,她们的力量是弱小的,她们的利益更容易受到侵害,在真正受到侵害时往往也就更容易引起反抗。在男方过失离婚案中,女性由于站在正义一边而把自己定位在主体位置上,想把曾经自己作为客体所受的欺凌统统公之于众来获取自己因此而损失的利益,甚至要远远超出这些利益。这种反抗很显然是利己主义的,至于因此而带来的社会影响,也不应该掩盖女性的这种心理与处境。
通过解读波伏娃对女性问题的理论性论述,我们展开了对鲁迅笔下典型女性形象探讨的新视角,而人物形象本身在新视角中呈现的心理和处境并不是我们探讨活动的终点,她们对当代女性所产生的启示和警醒作用才是我们作此关注的重心,这也应当成为我们重读和反观经典作家作品的当代使命。家庭主妇、寡妇或者说是独身女性和离婚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的文化处境应该引起我们特别是正身处其境的女性的关注。同时,鲁迅笔下的各色人物都有作此相应探讨的价值,值得当代学者持续关注。
参考文献:
[1]王富仁.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1
[2]【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2
[3]鲁迅.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作者简介:黄丽(1991-),女,汉,山东青岛人,青岛大学文学院,在读研究生,硕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论文作者:黄丽
论文发表刊物:《文化研究》2016年1月
论文发表时间:2016/6/17
标签:女性论文; 鲁迅论文; 自己的论文; 祥林嫂论文; 寡妇论文; 当代论文; 丈夫论文; 《文化研究》2016年1月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