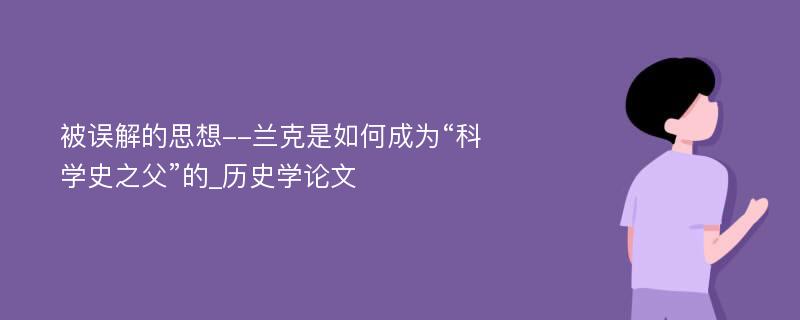
被误解的思想——兰克是怎样成为“科学历史学之父”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学论文,是怎样论文,之父论文,误解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们在了解或评价一个思想家时,往往会碰到思想与时代的关系这个一直难于理清的问题。每个思想家的思想一旦进入历史的长河,都会发生某种变化:它要么只有一部分经得起时间的冲刷与磨砺,要么被导入思想家本人始所未料及的方向,有的甚至被篡改得面目全非。此外,每个观察者由于角度、立场的不同,对同一个思想家也往往会得出迥然不同的结论。兰克留给后世的思想遗产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生动的例子。
自19世纪80年代中期始,随着兰克史学的影响不断扩大,人们对兰克史学的理解也开始产生严重的歧异,并逐步具体化为两种形象:在德国,无论是赞成或反对他的史学思想的人都将他看作“德国唯心主义传统的继承人。”〔1〕在国外,尤其在美国, 他却成为“科学的”历史学之父。〔2 〕这两种相互矛盾的形象在西方学术界存在了半个多世纪。一直到本世纪50年代后才逐步有所改变。笔者拟对兰克的第二种形象:即“科学历史学之父”的形象的形成作一番历史的考察,以求更深入地理解思想与时代的关系。
(一)
将历史学当作一门科学的思想大致出现在19世纪中期。当时欧洲正处于自然科学飞速发展的时期,科学对社会的主导作用日益明显,科学的方法和概念也不断地渗透到其他学科领域。一切不能经受科学方法考验的东西就有失去存在依据的危险。受其影响,在历史学领域,许多学者也开始调整自己的视野与研究手段,将许多原来被认为专属于自然科学所使用的方法运用于历史研究领域,以使历史学跟上时代的步伐。
最早试图以“科学”的方法研究历史的是产生于法国的实证主义史学。该学派认为:历史研究应分为两个阶段,初始阶段是弄清史实,第二阶段是发现规律。这也是史学研究的目的所在。该派的代表人物,法国史学家泰恩在《英国文学史》一书中就直言不讳地说:“历史是一个机械学的问题,唯一的差别是不能以同样的手段来测量或同样精确地下定义。”〔3〕英国实证主义史家亨利·托马斯·博克尔在1857 年出版的《英国文明史》中也公开声称:本书的目的是“叙述历史研究的方法和人类活动之规律性的证明,……不借助自然科学,历史学便不能建立。”〔4〕
可见,在19世纪,“科学历史学”有其特定的内涵,与我们一般意义上的历史科学有很大差别,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更有本质的不同。
如果按照这种“科学历史学”的标准来衡量兰克史学,我们不难发现,二者之间无论就对历史的看法还是就研究历史的方法与目的而言,都存在很大差异。
首先,兰克的历史观中所包含的浓厚的宗教思想与这种科学的历史观有矛盾。早在大学时代,兰克就开始对正统的路德教中占主导地位的理性神学与官方教条表现出明显的不满。在此过程中,他通过研究路德的著作和个人感悟,发展了一种独特的宗教思想。和路德一样,兰克渴望排除个人与上帝之间直接沟通的任何障碍与限制,与上帝直接交流。但他比路德更进一步,甚至认为圣经都不可能成为人与上帝之间沟通的中介。在他看来,宗教是一种通过内省感受到的无限真理,它不能通过先验的观念加以理解。人类追求真理的终极目的就是接近上帝,只有上帝才是一切的创造者。正因如此,“对永恒真理的追求”只有通过“了解上帝在所有事物上的体现”才有可能实现。而历史研究正是通向此途的捷径。〔5〕
历史研究的目的主要是通过展现过去的生活发现上帝的精神及其创造性。这是兰克终生坚持的信念。这一点在某种程度上对他的历史观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他认为,人类历史体现为非线性的个体展现的图式。各个时代只是上帝创造性的不同体现,因而具有同等的价值,不可比较。“每个时代都直接与上帝联系在一起,它的价值并不在于它创造了什么,而在于它自身的存在,在于其自身”。因此,除了那些永远不变的主导观念外,每个时代都有其特定的倾向和理想。在人类历史中不存在一种推动一切事物走向必然结果的力量。各个时代、各个个体之间只有通过上帝之手才会产生一种历史的关联性。人类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活动,总是围绕一个尚未发现的轴心,不断地展现不同的领域和侧面。因而,“真正的进步依赖于人类精神的某种运动在每一个时期的表现”而不是体现在各个时代的依次递进当中。〔6〕
其次,兰克史学中与其历史观紧密相联系的个体性原则明显与科学历史的原则相悖。兰克强调所有的历史形式都是独特的和自为的存在。它们各自作为历史单元有其完整的个体性。因而是唯一可以历史地确定的对象。在他于30年代撰写的《普遍的历史观念》这本手稿中,兰克写道:“趋于特殊”是历史学的天性使然。“当哲学家在过程中,在发展中,在整体中追求无限时,历史知道无限存在于每一个存在物中。”〔7〕
兰克对个体性的强调与自赫尔德以来的德国历史主义传统一脉相承。在《尚有另一种历史哲学》这本书中,赫尔德对历史主义的个体性原则曾有过初步的论述。他认为,每一个时代都应作为人类精神的独一无二的贡献来理解,历史不是一个在当代简单地达到最高点的过程,……单个时代既是工具,又是目的。“人类完美的每一种形式,在某种意义上是民族的,受时间限制的,并且,从最具体的意义上来说,是个体的。”〔8〕
兰克通过抬高个体性原则,不仅使历史摆脱了对哲学的从属地位,使之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且发展了德国历史主义的传统,使之在德国最终成为一股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潮流。它使德国19世纪以后的思想发展慢慢与西方的主流文化脱节。对此,恩斯特·特勒尔奇和迈纳克都有深刻的认识。〔9〕
然而,兰克在高扬个体性原则的同时,并不排斥哲学。他反复强调,“认为我对哲学或宗教缺乏兴趣”这种看法是何等“可笑”。“因为恰好就是这方面的兴趣才使我转向历史”。“历史不是对哲学的否定,而是对哲学的完成。”〔10〕更重要的是,兰克认为,历史个体的意义在于它是理解历史普遍性的关键,而后者才是他追求的目标。因为只有“普遍历史才能全面地涉及人类过去的生活……人类只有通过历史才能作为一个整体意识自身。”〔11〕总之,对兰克来说,个体性原则是历史学区别于其他学科,尤其是哲学的重要标志。但是,对个体的研究并非历史学的目的而是手段。历史学的最终目的在于通过透析个体,探求“精神的轨迹”。〔12〕
第三,兰克史学所表现出的明显的政治取向也不符合科学历史学的精神。他认为:国家是“上帝理念”的体现,是一种特殊的个体,通过它可以探寻人类共同的历史命运。因为每个国家都以自己的方式表达了“鼓舞和决定整个人类体制的观念”,“体现了可以发现的生长的规律”。〔13〕就兰克个人而言,历史研究是他参与政治生活的一种方式。他的研究方向的确立,他的历史观的形成无不有时代和政治的烙印。他自己也承认,“政治因素”使他由古代转入近代史的研究。〔14〕而正是在19世纪中期欧洲风云迭起的政治革命与斗争中兰克的历史观才最终臻于成熟。
第四,兰克终生标榜的客观性原则与科学历史学的治史原则亦不可等量齐观。兰克的客观性原则以及由之而发展的一整套历史资料的考证方法是他学习和总结修昔底德、赫尔德和尼布尔等人的历史批判方法以及当时语文学家的考据方法的结果,与科学的影响毫无关系。更重要的是,兰克的客观性原则并不意味着对事实的简单陈述。虽然他强调要“消灭自我”使主体“汇入客体”,但并不否认历史学家作为主体的创造性作用。他写道:“既然每一件事都来自上帝,重要的不是存在的物质而是对物质的眼光。当我们剥除事物的外壳,发现其本质的存在时,在我们自身,上帝的本质、上帝的精神、上帝的灵魂、上帝的气息开始如插上双翅般遨游起来。……神圣的真理不仅客体化于历史过程中,而且主体化于历史学家”〔15〕。因此,揭开历史的迷雾,从事物的表象之下发现真实的存在,是历史学家的职责,也是其主体性的表现。
由此可知,兰克的客观性原则内含有两重意思:一方面,历史学家的职责就是“汇入客体”理解事物赖以表现自己的外在形式,并通过形式了解本质。在此,历史学家仅仅是一个发现者;另一方面,客观的历史真相与其说存在于过去所产生的行为和观念中,毋宁说是一种与历史的表象不同类型的存在,只有历史学家才能从表象中将之提炼、鉴别出来。因此,兰克认为:“与真理世界相对,有一个表象的世界,它也有其根源,并发展了一种日益繁复的表面形象,直到虚无……。”为了在这种虚假的“表象世界”之外去发现真理,必须通过最主观的“预感”和“神入”〔16〕。在此,客观和主观都只具有相对的意义。
综上所述,无论是兰克的历史观还是他的治史原则,都深深地根植于德国的文化传统之中。他继承并加以发展的历史主义的治史原则与科学历史学的原则从根本上是互不相容的。甚至他一生追求的“客观性”原则与所谓“科学的”历史学的方法也有很大的差距。
(二)
然而,终其一生都未走出德国唯心主义传统的兰克,在自己的故土之外竟然成了一位“科学历史学之父”或“客观主义史学家”。
最早将兰克与“科学历史学之父”的形象联系起来的是美国历史学家。1884年,H·B·亚当斯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历史与政治学研究》杂志上发表《历史研究的新方法》一文,首次将兰克称为“科学历史学之父”。1885年,史学家A·D·怀特、W·F·阿兰在《历史教学法》中进一步推广了这一称呼。由是兰克开始被当作“科学历史学之父”受到大部分美国史学家的顶礼膜拜。这批历史学家中,有些人是曾在德国师从于兰克的门徒,其中奥斯古德曾作过兰克的学生。但在一开始,他们对兰克的理解就是片面的。他们只是一味地强调兰克对史料的考证方法以及习明纳尔(seminar)制度对于培养历史专门人才的意义。 在他们看来,兰克史学的精髓就在于:以客观的态度探求历史的真实性,对历史事实不作任何归纳,严格地排斥哲学。H·B·亚当斯曾写道:“兰克决心严格地把握历史事实,不作任何说教,不强调任何道德观念,对叙述不作任何粉饰,而仅仅是阐述简单的事实。他唯一的愿望就是按事物的本来面目对之进行阐述。真实与客观是兰克的最高目的。在他看来,历史不是为了怡情或启迪,而是为了教育,……他不相信历史学家有义务去指出人类历史中的神佑。”〔17〕
1908年,H·B·亚当斯在出任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时的演说中,更进一步强调兰克史学就在于通过“严谨的科学调查的方法”寻求对过去历史确定性的证明。兰克最宝贵的精神遗产就是“调查的科学”和“一种训练历史学家的方法”。在兰克的影响之下,历史学家都把“尽可能探明并精确地记载所发生的一切”作为自己的“第一职责”。〔18〕虽然当时在美国也有部分史家认识到兰克史学远非仅仅是确证具体史实,但大多数人都将兰克等同于这样一种形象:如实直书,注重历史的细微末节,排斥哲学。这也是他们心中所设想的作为一个“科学的”历史学家所应具备的最基本的素养。
大约与此同时,欧洲史学界〔19〕也掀起了一股兰克热。兰克的史料考证方法经过德国史学家伯因海姆的整理,最终于1889年写成《史学方法论》一书。此书一经出版,立即在欧洲产生巨大的影响。兰克史学一时之间成为欧洲史学的楷模。英国历史学家、兰克的门徒阿克顿由此感叹:“我们每走一步都要碰到他,兰克对我们的贡献比任何人都大。”〔20〕
然而,欧洲史学界所发现的同样只是兰克的片面的影子。兰克首先被当作一个客观主义史学家,进而又变成实证主义史学的实践者,人们所关注的是兰克的方法,而不是兰克的史学思想。兰克史学被简单地等同于兰克的史学方法。例如,在英国、阿克顿所创立的“剑桥学派”即以史料考证而著名。阿克顿在《致〈剑桥近代史〉的撰稿人的信》中提出的方法只是兰克方法的再现。他说:“我们将竭力获得任何文献的复制本。”“我们的方案要求所有的作者不能显露他所属的国家、宗教和党派”〔21〕1886年,《英国历史学评论》杂志在创刊词中声明说:“历史的任务是发现和陈述事实。为了避免党派之嫌,本刊拒绝接受与当代论争有关的问题的来稿”〔22〕阿克顿在上面发表《德国的历史学派》一文,将客观主义作为兰克史学的精髓而大加赞赏。 在法国, 早在1876年,史学家莫诺在德国学成归来后,便与同仁一起模仿德国的《历史杂志》创办了《历史评论》,并将兰克史学与实证主义史学结合起来。他号召历史学家们专注于发现史实,抛弃一切哲学和政治论争。著名历史学家朗格罗瓦和瑟诺博斯于1898年出版《史学研究法导论》,内容与伯因海姆的《史学方法论》异曲同工。这本书长期以来一直作为法国培训历史专业学生技能的教科书。〔23〕
20世纪初,伴随着各种新的社会思潮的涌动,历史学也开始突破旧有的格局,寻找新的研究角度与视野。这方面开先河的是美国的新史学。新史学倡导“依据现时的社会利益”研究“过去”,将历史学从单纯的资料搜集与整理中解放出来。然而,美国史学界的这种转变并未导致对兰克评价的变化。新史学派的学者们没有去努力发掘兰克思想中丰富的精神财富,而是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将矛头对准由前代史学家所塑造的兰克的形象,对之大加鞭挞。他们认为,兰克“如实直书”的理想只是一种天真的假定;〔24〕兰克的理论除再现过去这一目的外,没有更多的内涵。他主要关心的是“对细节具体的确定的搜寻。〔25〕他们宣称:“现在的思想已抛弃了兰克所创立的观念,即有可能如实地描述过去,犹如工程师描述一台单个的机器。”〔26〕在他们眼中,兰克成为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史学的代表。
在欧洲,兰克的命运与在美国一样,当人们反对实证主义史学机械的、实证的史学观点时,兰克又成为人们首选的攻击对象。新黑格尔主义哲学家克罗齐的观点极富有代表性。在他于1915年发表的《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一书中,克罗齐将兰克视为反对历史哲学的史学家的代表。他认为:这群史学家具有如下共同特征:偏爱特殊事实,不愿涉足理论领域,推崇可以从细节方面充分地加以研究的民族史和其他专题史,强调历史学家的领域是事实的实在性而不是它的价值,对史实不偏不倚等等。他把他们称为实证主义的历史学家。〔27〕
二战前后,由于大批德国学者为寻求政治避难而远走英美以及德国独特的历史与现状日益引起史学界的兴趣,欧美史学界有机会深入了解德国的思想传统。通过这一契机,兰克在欧美史学界的形象逐步发生变化。在美国,三位来自德国的学者首先使史学界了解到德国人自己对兰克的评价。他们是哈约·霍尔波恩,恩斯特·卡斯勒和恩格尔·雅诺西。在欧洲,战后西德史学界所爆发的研究兰克的热潮对英法史学界也有很大触动。人们开始从德国的文化传统中重新审视兰克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地位。然而,这种转变非常缓慢,历史哲学家柯林武德在1946年出版的《历史的观念》一书中,虽未将兰克看作一个“科学历史学之父”,但和克罗齐一样,仍然将兰克史学当作实证主义史学的一部分,认为以他为代表的历史编纂学接受了实证主义纲领的第一部分,即“收集事实”,把它们当作分别独立的或原子式的来加以研究。〔28〕直到50年代,瓦尔特·P·韦布(美国史学家)在一篇文章中, 仍将兰克看作“科学的”历史方法的代表。他写道:兰克“与莱伊尔、华莱士、达尔文、勒南同时代,他们在各自领域中都使用了分析与批判的方法,并取得了惊人的成果。他(兰克)将课堂变成一间实验室,只不过以资料取代了蚌”。〔29〕
兰克史学传入我国后的历史命运大体与它在美国的遭遇相仿。自封为兰克的信徒的傅斯年认为兰克史学的精髓,便是历史资料的搜集与整理。他宣称“史料便是史学”,并号召历史学家们“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一时之间,兰克史学在中国成为科学历史学的楷模〔30〕。对兰克史学的这种片面的看法,直到今天在许多有关西方史学史的书籍和文章中仍能找到。
(三)
纵观兰克史学被“科学化”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这种历史现象的出现,是诸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首先,欧美史学界对“科学历史学”的片面理解以及对德国历史传统的缺乏了解是兰克史学被“科学化”的根源。在科学历史学兴起之时,西方史学界对之就有两种理解。一部分史学家如泰恩、博克尔、美国史家安德鲁、怀特、亨利、亚当斯等,受孔德和达尔文的影响,认为科学的历史学如自然科学一样,主要在于将一般规则应用于历史研究中,找出历史发展的规律。但许多自封为科学历史学家的人则只是将简单地对史实进行客观的证明,如实记载历史事实当作科学历史学的全部要义。而这一点正好与兰克“如实直书”这一流传甚广的名言相吻合。于是他们就将兰克的史学方法从他的整个史学体系中隔离开来,将之奉为“科学的方法”。由此进而将兰克史学等同于“科学的历史学”。
其次,兰克史学本身的因素促使对他的学说体系不甚了解的史学家只注意他的治史方法而忽视了他的史学思想。兰克从未标榜要建立一套独特的历史学说,他身上的许多特点往往会使人对他产生相互矛盾的印象。诸如,作为教师,他终生都在讲授“世界史”;但作为历史著作家,他笔下出现的却是地方史或国别史。在他的笔记、通信以及未发表的手稿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历史理论家、思想家、德国历史主义传统的守护神;但在习明纳尔上,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个勤于考据、注重史料的“客观的”学者。此外,由于兰克从未系统地阐述他的史学思想,大多数观点都是随感而发或出于辨护或反击的需要,如30年代有关个体性理论的阐述,50年代对历史进步观的质疑等。这些都使得他的史学思想在表面上看来缺乏一个一以贯之的体系,很多地方甚至显得自相矛盾。更重要的是,兰克虽然想排斥哲学对历史的主导地位,但他在论述历史理论时,又不得不借用当时流行的哲学概念与范畴,诸如个体(Individium)、特殊(Besonderhiet)、个别(Einzelheit)、普遍(Universal)等。但他在使用这些概念时, 从未去对它们作任何界定与分析,这很容易使人产生混淆。其中尤为突出的是“个体”的概念。兰克的本意是指构成一个文化整体的历史单元,绝非个别的事件。在兰克看来,个别的事件只有与个体的生命联系在一起才被赋有历史的意义。但在别的史家看来,个别与个体在兰克史学中几乎可以混用。因此,许多史学家就将兰克对个体的强调误以为对殊特事件的爱好。
兰克唯一清楚地表达的是他的史学方法。这种方法通过习明纳尔制度深深地影响了一代史学家。它虽然非兰克首创,但他使之系统化了。经过他的学生的宣传和推广,这种方法日益为广大的史学家所接受。于是,兰克方法逐渐取代了他的思想成为兰克史学的象征。在科学主义高唱凯歌的时代,它又被披上“科学”的彩衣,成为科学历史学的象征。
第三,德国思想界长期相对孤立的状况使得兰克的这种被误解的形象得以长期存在。兰克虽然生前在德国也被当作一个“客观的”史学家,但他去世后,随着他的遣稿大量问世,他的史学思想开始引起史学界的注意。人们已不再认为兰克仅仅是一个“客观的”历史学家,而是一位富有深刻的史学思想的人。一大批著名学者,如息贝尔、汉斯·普鲁茨,阿尔弗莱德·都弗等都认为,兰克的本意远非仅仅是对过去史实的重建,而是对现实内省式的反思。息贝尔说:“兰克并不满足于具体的描述而是力求透析生命最深沉、最神秘的运动。”〔31〕更多的学者从本国的文化传统中寻找兰克史学思想的根源,将兰克与赫尔德、尼布尔等人的思想有机地联系起来。
因此,当兰普勒希特孤军奋战,企图用“科学的”方法改造德国史学之时,他首先将矛头对准了兰克。他认为,兰克史学建立在过时的、前科学时代的方法论基础之上。兰克研究历史的目的既非简单的搜集史实,亦非提出普遍的规则,而是对理念的确认。他的史学思想与德国唯理主义的传统一脉相承。因此,兰克不能称为现代意义上的科学的史学家。他的历史观远远未摆脱思辩哲学的桎梏。〔32〕
然而,在德国之外,西方史学界对德国史学界的这些改变却漠然无知。从某种意义上说,德国史学界对兰克的评价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兰普雷希特本人曾于1906年到美国去讲授德国史学,其结果只有一个名叫E·W·都沃的学者对他的思想有所领悟,并以兰普雷希特的观点为依据,对兰克史学进行了重新解释。但他的观点很快被湮没无闻,欧美史学界对兰克的评价长时期内依然故我,没有任何改变。
综上所述,“科学的历史学”只是一个历史名词。兰克被奉为“科学历史学之父”更是一种历史的误解。兰克眼中的历史学既是一门学问,更是一门艺术。历史中的真理在他看来从来不受规律的支配,它只是理念的体现。
由此可以看出,被歪曲的思想一旦找到自己生存的土壤,它便会具有自己的生命。只要时机合适,它还有可能获得发展,最终成为一种独立的存在。此外,不仅思想是时代的思想,对思想的评价也是时代的评价。正是这一点赋予历史学以常新的意义。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尊师金重远教授的悉心指导,特此致谢]
注释:
〔1〕〔2〕 见:G.G lGGers:The lmage of Ranke in American and German Historical Thought,History and Theory,1962,No.1.
〔3〕 转引自古奇:《十九世纪的历史学与历史学家》, 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405页。
〔4〕 H.T.Buckle: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England,P.604。转引自张广智、张广勇:《史学, 文化中的文化》, 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16页。
〔5〕 参见:Carl Heinrch,Rankes Lutherfragment von 1817 und der Ursprung seiner Universal- historischen Anschauung,im Fesfschrift für Gerhard Ritter,(里查得· 纽伯格编)图宾根,1950年版。
〔6〕 转引自Leonald Krieger,Ranke,The Meaning of History,艺加哥大学出版社1977年版,第228—229页。
〔7〕 Ranke,Geschichte und Philosophie,pp.291—292.参见E.Kessel,Rankes ldee Historische Zeitschrift,1954.
〔8〕 参见哈多克:《历史思想导论》,华夏出版社1989 年版,第121页。
〔9〕 请参考:Meineck:Die Entstehung des Historimus,柏林1931年版;Ernst Troeltsch,Das Stoisch-christliche NatuRRecht and das Moderne profane NatuRRecht.
〔10〕 1830年6月给海因里希·里特尔的信:Ranke,Briefwerke(瓦尔特·P·福克斯主编),汉堡1949年,第216页。
〔11〕 引自E.KeSSel,Rankes ldee。
〔12〕 参见Ranke,The Meaning of History,p.140.
〔13〕 转引自Ranke,The Meaning of History,p.7.
〔14〕 Ranke,Briefwerke,P.59.
〔15〕 Ranke,Briefwerke,P.38.
〔16〕 Ranke,Briefwerke,P.252.
〔17〕 H·B·Adams,Leopold von Ranke,见:E·G·波尔耐主编:ESSays in Historical Criticism,PP.109—105,纽约1901年版。
〔18〕 见C·Becker,Some Aspects of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Probtems and Ideas upon the study and Writing of History,《美国社会学杂志》第18期(1912—13),p.641
〔19〕 指除德国以外的欧洲史学界。
〔20〕 转引自张广智、张广勇:《史学、文化中的文化》。第95页。
〔21〕 古奇:《十九世纪的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下册,第617页。
〔22〕 转引自《史学,文化中的文化》,第100页。
〔23〕 请参见郭小凌主编:《西方史学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31—332页。
〔24〕 A·B·Hart,lmagination in History,《美国历史评论》(1909—10),第245页。
〔25〕 J·T·Shotwell,The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美国历史评论》(1912—12),第703页。
〔26〕 参见《美国历史评论》(1933—34),第221页。
〔27〕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30—232页。
〔28〕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48页。
〔29〕转引自Iggers,The Image of Ranke in American andGerman Historical Thought.
〔30〕转引自张广智、张广勇:《现代西方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65—366页。
〔31〕Sybel:Leopold von Ranke,PreSSisches Jahr buch,1886,No.48.
〔32 〕Lamprcht,Alte und Neu Richtungen
in
derGeschichtswiSSanschaft,柏林,1896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