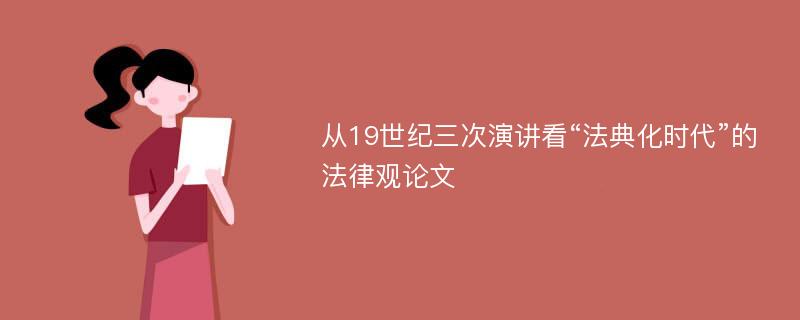
从19世纪三次演讲看“法典化时代”的法律观
朱明哲*
摘 要 19世纪法学的中心议题是法典化。在围绕法典展开的讨论中,形成了以法律创造论、法律进化论和法律工具论为内核的法律观。法律人通过编纂法典、解释法典,开始普遍认为法律是人类的创造,从而总是有改善的空间,并且可以服务于人的目的。三次著名的演讲分别在19世纪的不同阶段明确阐发了法律人普遍接受的法律观。1801年波塔利斯在《关于民法典草案的演讲》中指出习惯应当通过立法保留其内容、判例可以细化法典的规定,说明立法者所创造之规则成为最主要法律渊源的时代已经到来。1847年基尔希曼则在《作为科学的法学的无价值性》中提出社会在不断进步,法律也自然应该随之进步,法学家应该研究的就是未来的法律。1897年霍姆斯则在《法律的道路》中则提出法律不仅应该顺应社会进步,而且可以作为法学家的工具引领社会发展。在法典化的时代,法律的创造论、进化论和工具论也逐渐深入人心。
关键词 法典化 法律创造论 法律进化论 法律工具论
目 次
一、法典化与法观念的演进
二、《关于民法典草案的演讲》与法律创造论
在进行单一层次判断矩阵的一致性检验之后,利用单层次排序的影响因子权重计算各层次影响因子的组合权重,计算完成后再对组合权重计算结果进行一致性检验[10-12]。若结果不满足一致性要求,则对判断矩阵进行调整。
三、《作为科学的法学的无价值性》与法律进化论
四、《法律的道路》与法律工具论
五、结论
作为CDM的各参与方,项目业主、咨询机构、第三方审核机构、金融机构等主体,应及时关注国内碳交易市场建立的相关政策和进展,夯实自身基础,尽早布局国内市场,为将来扮演好各自角色做好充分准备。
一、法典化与法观念的演进
值此《民法典》表决通过前夕,本文想回溯到19世纪这一“法典化的时代”,考察伴随法典的编纂、解释、修订出现了哪些法学思想。民法学界同仁不仅探讨了篇章结构、各章内容设置、《民法典》与其他部门法之关系等法律技术问题,还积极讨论着这部法典应当承载怎样的时代精神。一种立场认为每个国家、每个时代的民法典有其独特的任务和目的,也体现着不同的价值取向——“法典是政治性的”。〔1〕 代表性观点参见刘征峰:《家庭法与民法知识谱系的分立》,《法学研究》2017年第4期,第56-73页;韩大元:《宪法与民法关系在中国的演变——一种学说史的梳理》,《清华法学》2016年第6期,第151-167页;谢鸿飞:《中国民法典的生活世界、价值体系与立法表达》,《清华法学》2014年第6期,第17-33页;薛军:《“民法—宪法”关系的演变与民法的转型——以欧洲近现代民法的发展轨迹为中心》,《中国法学》2010年第1期,第78-95页。 另一种立场则认为民法应当坚守私人自治的基本价值,在法典化过程中努力实现价值中立、以融贯性和普遍性为首要追求的体系建构——“法典是科学性的”。〔2〕 代表性观点参见苏永钦:《现代民法典的体系定位与建构规则》,载《交大法学》(第1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59-93页。 然而,对“法典化”现象的整体反思尚付之阙如。其结果是我们就算能够从宏观上说是现代民族国家形成、启蒙思想发展等历史进程带来了法典化潮流,却无法准确地指出法典化潮流从哪些方面改变了人们看待法律和法学的方式。实际上,19世纪的法典化潮流塑造乃至决定了我们现在对法律的认识。从1793年《法国民法典》第一份草案问世到1931年《中华民国民法典》全部生效之间的岁月,可以说是属于现代法典化的“长19世纪”,也可以说是一个“法典化时代”。就连那些传统上不在讨论范围之列的国家——如美国和英国,也不但出现了法典化的努力,更产生了关于法典的重要讨论。〔3〕 Cf.Wienczyslaw Wagner,Codification of Law in Europe and the Codification Movement in the Middle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n the United States,Saint Louis University Law Journal,no.1(January 1953),at 335-359;Dean Alfange,Jeremy Bentham and the Codification of Law,Cornell Law Review 55,no.1(November 1969),at 58-77. 就连“法典化”这个词也是边沁(Jeremy Bentham)创造的。〔4〕 Cf.Dean Alfange,Jeremy Bentham and the Codification of Law,op cit;Jean-Louis Halpérin,Histoire des droits en Europe de 1750ànos jours,Paris,Flammarion,2006,at60. 人们很难指出哪个国家在19世纪未受法典化波及。甚至说法典化是19世纪法学发展最重要的推动力亦不为过。〔5〕 我国法制近代化也是19世纪法典化浪潮中的一个部分。参见朱明哲:《中国近代法制变革与欧洲中心主义法律观——以宝道为切入点》,《比较法研究》2018年第1期,第155-170页;朱明哲:《从民国时期判例造法之争看法典化时代的法律场》,《政治与法律》2018年第11期,第127-142页。 尽管在经历了“解法典化现象”之后,当代民法典编纂工作的任务肯定不同于19世纪。〔6〕 陆青:《论中国民法中的“解法典化”现象》,《中外法学》2014年第6期,第1483-1499页。 但当前的法典观、乃至法律观仍然是上一个法典化时代的遗产。
本文探讨的是19世纪伴随着法典化出现的现代法律观。法典化时代的法律观包括以下三个主张:①法律创造论——法律来源于人的创造而非发现,从而区别于自然法理念。这一法律的创造论又具体表现为对立法的推崇。②法律进化论——法律应该随着时代进步。③法律工具论——人创造的法律应当作为工具服务于人的目的。整个19世纪,强调法律的创造性、进步性、工具性的观念如此普遍,以至于能得到不同国家中的职业法律人整体的接受,而非局限在某个国家的精英法学家群体。关于法典化时代法律观的研究至少有两种价值。在法理学上,它将帮助我们揭示流行于20世纪的法律实证主义、社会法学、法律现实主义产生的前提,及其与实证法本身发展的联系。在部门法上,它能帮助我们更清醒地在长时段中认识法典的作用、意义及其局限。
法律思想的演变和法律实践的历史应该看作一个发生在更广阔社会背景中相互作用的整体过程。本文必然在回应整体史视角下的19世纪那些更具支配地位的潮流,包括民族国家建构、工业化,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问题。我们把法典化和伴随而来的法观念理解为这些重大变革的产物,经由人们的智力活动,具体表现在法律和法学中。法律创造论肇始于民族国家的建立、法律进化论孕育于工商业和政治的自由化、法律的工具论适应了国家调整社会之需要,以上关系均显而易见,在宏观的法律史叙事中也可以看到。本文只希望揭示法典化在每一种关系之中作为中介的重要性,并同时从微观层面通过文本说明法学家如何从理论上把他们对历史背景的观察转化为法学的知识。
为了说明整个法律职业在与法典相关的实践中逐步认识和接受了创造论、进化论、工具论,本文将分析最初以公开演讲这种特殊的文体形式呈现的文本。对于那些本来就是为了印刷发行而写的文本而言,作者只有一个想象的读者群体,他对作品的传播和解读都无能为力。〔7〕 Cf.Roland Barthes,Lamort de l’auteur,in Le Bruissement de la langue,Paris,Seuil,1984,at61-67. 相比之下,演讲有着完全不同的时间、空间和对象特征。作者知道自己听众的身份和他们的知识构成,也知道自己以言行事的独特场合,还有他自己的目的和听众的预期。听众很可能认识(不仅仅知道)作者,也知道为什么他获邀在这一场合发言。作者发言和听众理解不再是两个在时空上分隔的事件,而是在一个有限的、相对短暂的时间段里,在一个具体的、相对封闭的空间之中发生的共时同地的过程。那么至少从作者的角度而言,要想最大程度地避免误解,他必须最大限度地理解听众所熟悉的语言风格、词汇语法、思维模式。所以,正是演讲最能够揭示那种令“言”得以行“事”的集体心态特征。
从法律的创造论往前再迈一小步,基尔希曼就踩在了法律进化论的台阶上。既然立法者可以创造规则,自然也可以修改规则。既然法学家们可以认识到立法存在的漏洞、歧义和矛盾,那么立法者自然也可以至少借助法学的“评注、释义、专著、解析、思辨、论文以及案例”了解这些缺陷的存在。基尔希曼用词的严谨就在此处体现:他说的是“三个更正词”(drei berichtigende Worte des Gesetzgebers),而非“三个词的改动”。更正意味着立法文本的改变填补了漏洞、消除了歧义、调和了矛盾。大部分引用这句话的作者用它来说明对法学之客观性的挑战。拉伦茨的高明之处在于意识到这句话讨论的是时间性问题,但他因为论题选择的局限性,只提到了“法学在获得能够经受实践考验的认识方面的无能”,并把其原因归结为“实在法的飘忽不定”。〔46〕 同前注 〔39〕,〔德〕卡尔·拉伦茨文,第145页。 这种理解既夸大了这句话所涉及的范围,又低估了基尔希曼思想中的进步因素。基尔希曼说会变成废纸堆的仅仅是法学图书馆中那些围着漏洞、歧义和矛盾打转的部分。〔47〕 同前注 〔38〕,〔德〕冯·耶林文,第152-159页,贝伦茨注5。 在他的嘲讽背后,恰恰隐藏着对未来的乐观主义:创造法律的立法者不但可以改变法律,更可以(不论是否参照法学的成果)改善法律。如果立法不断改善,那么基尔希曼所批判的以立法为立足点的法学其实始终考察着一种更好的对象,本身也可以不断地发展。基尔希曼所描绘的立法和法学似乎并不像大多数引用他名言的人想的那样悲观。
每一篇文本都像一面镜子,照出言说者和听众所处的那个时代的一个侧面。基于对整个法律职业群体的关注和演讲之文体独特性的考虑,本文选取了分别发生于19世纪初期、中期、末期的三次面对不同职业的法律人的演讲。它们分别是1801年波塔利斯(Jean-étienne-Marie Portalis)代表《法国民法典》起草委员会面对资政院(Conseil d’état)就法典草案所作的说明(《法典起草委员会关于民法典草案的演讲》)、1847年基尔希曼(Julius von Kirchmann)在柏林法学会上的演讲(《作为科学的法学的无价值性》)、霍姆斯(Oliver Holmes)法官在1897年于波士顿大学法学院的演讲(《法律的道路》)。这三次发生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演讲有重要的共性。首先,主讲人的身份并非大学教授:波塔利斯是《民法典》的起草者,基尔希曼是柏林的检察官(Staats-Anwalt),霍姆斯则是马萨诸塞州最高法院的法官。其次,听众的身份囊括了不同的法律职业群体。最后,演讲稿最终得以留存于后世,否则也不可能成为研究的对象。我们对这三份文本的内容并不陌生。但是,现在学界很少试图理解它们作为演讲所体现的职业法律人共同意识,更从未把它们放在一起呈现孕育于法典化时代的独特法律观。本文将分别把这三场演讲回置于使其得以发生的历史语境中,从而说明法典化时代中央立法占据了主要法律渊源地位的同时,法律人也普遍认为法律是人类的创造,从而总是有改善的空间,并且可以服务于人的目的。如果一些观念无法在文本之中找到直接的证据,它们终将浮现在置回于语境之中的文本上。
二、《关于民法典草案的演讲》与法律创造论
在对这次演讲的研究中,我国学者几乎没有注意到它和法典化时代之特征的联系。〔76〕 徐爱国教授1997年的论文奠定了我国学界很长时间以内对《法律的道路》的理解,他认为该演讲主要谈到了法律与道德的严格区分、法律内容与发展由历史和利益决定、法理学的重要性。参见徐爱国:《〈法律的道路〉诠释》,《中外法学》1997年第4期,第115-120页。一些学者更多强调霍姆斯对德国历史法学的继受,参见谢鸿飞:《准寻历史的“活法”》,《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第130-140页。随着近年法学方法论的研究渐成法理学主流,也有学者借以讨论广义上属于法学方法的问题,如柯岚:《法律方法中的形式主义与反形式主义》,《法律科学》2007年第2期,第31-39页;秦策、夏锦文:《司法的道德性与法律方法》,《法学研究》2011年第4期,第40-57页;姚远:《以公共政策分析为中心的法律方法论——重访霍姆斯大法官》,《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第70-76页。关于霍姆斯的研究汗牛充栋,挂一漏万,在所难免。 然而,当时美国法学界作为这场演讲之背景的大型争论正是关于法典化的争论。〔77〕 中文文献中最新的研究成果参见明辉:《美国“民法典”的历史命运(1857-1952)》,《清华法学》2018年第1期,第89-113页。 以霍维茨(Morton Horwitz)为代表的美国学者虽然从80年代末开始意识到它是对美国法典化争论的回应(intervention),但只局限在美国一国,没有注意到他参与的讨论的跨国维度。〔78〕 Cf.Grey,Holmes and Legal Pragmatism;Horwitz,The Place of Justice Holmes in American Legal Thought;Lewis A.Grossman,Langdell Upside-Down:James Coolidge Carter and the Anticlassical Jurisprudence of Anticodification,Yale Journal of Law&the Humanities19(2007),at149. 实际上,工具主义法律观在19世纪末于全球范围内出现,深层次的原因乃在于形式平等观无法应对社会不公,在经济领域崇尚自由放任的法政策备受挑战。在此背景下,霍姆斯提出用进步主义的法典引领社会变迁要比普通法传统中回首过去的方法更能适应时代需要。这是一种属于19世纪末的主张,而非属于美国法学的主张。如果说波塔利斯站在法典化的门槛讨论“法典的素材应该从哪里来”,基尔希曼目睹法典规则逐渐变得不合时宜而讨论“法典是否可以发展”,霍姆斯更多带着后见之明指出法典本身无法一劳永逸解决社会问题,法官还是需要利用科学的证据创造法律、改造社会。
《关于民法典草案的演讲》说明法律源于立法者的创造的意识伴随着法典编纂的浪潮出现。虽然波塔利斯本人没有明确这样说,但这种认识是他演讲的前提。文本中给了足够的线索让我们发现这一前提。在演讲中,波塔利斯探讨的更多是立法者应该有的谦抑品格,看上去并没有大张旗鼓地提出法律来源于人的创造。而且他还花大量篇幅强调立法者制定法律的时候应该尊重的其他的法律渊源。换言之,波塔利斯演讲本身从侧面、甚至反面切入立法律的创造论。下文要论证的是这种形式上对多元主义法律渊源观的传承恰恰说明波塔利斯所处的那个时代已经接受了立法至上主义的革命观点。
(一)表面的传承:多元主义的法律渊源观
波塔利斯的核心问题是“法典到底是什么”。他提出的种种洞见中,有两个主张最为明显:①法典化也就是体系化既已存在的规范;②法典无法包括所有规范。〔15〕 同上注,石佳友文,第91-101页。 波塔利斯需要按照草案的顺序先讨论“序章”部分关于法律的定义,然后再讨论留在各编中的习惯法,我们为了论述方便,先讨论法典化时的习惯法问题,再讨论立法之局限性。
波塔利斯明确提出民法典编纂应该保留传统和习惯。“立法为了满足人而创造,人却不是为了满足立法而创造。”所以,“立法必须适应它们所服务的人民的特点、习俗和社会情况。”〔16〕 Jean-Etienne-Marie Portalis,Discours préliminaire prononcépar Portalis,le 24 thermidor an VIII,lors de la présentation du projet arrêtépar la commission du gouvernement,op.cit.,at466. 而让立法适应人民的最佳方式,就是尊重和保全他们的习惯。大革命摧毁了旧制度,却并不意味着一定要改变所有的习惯,因为“习惯当然有些早期野蛮时代的印记,但也有那些前辈智慧的光荣遗产,塑造了民族特性,应当得以保存。”〔17〕 Ibid.,at 481. 言下之意,法典编纂者的工作与其说是在砸烂一个旧社会后也不分青红皂白地砸烂所有旧社会的制度,还不如说是在建立一个新社会之后从旧社会的制度中去芜存菁:“只要没必要摧毁的,留下来都是有用的。只要现存的习惯不是恶习,立法就应该容纳他们。”〔18〕 Ibid. 可见,波塔利斯极力为旧制度下的民事法律规范辩护,认为法典化应该是对过去数世纪成果的整理和汇编,而非重新创造。
中小型民营企业的关键技术和主体技术掌握在一个或几个技术骨干手里,且一般情况下人员流动性远大于传统军工企业,一旦企业某个技术骨干流失,则可能影响公司的专业技术能力,轻则影响后续产品的研发,重则已承担的产品研制生产任务难以完成。
最大限度保留和继承旧制度下优秀民法成果的法典也只能在内容上保证尽可能的完善,却无法做到完美,更无法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可能出现的争议。波塔利斯很严肃地提出了这一点:“认为可以存在一系列提前预知所有可能案件的法律体系,哪怕仅涉及一小部分公民,这种想法也是错误的。”〔19〕 Ibid.,at471. 既然立法无法提前安排好一切,而法官又不能拒绝裁判,那么必然存在并未包含在法典之中的规范,有待法官发现。对波塔利斯而言,这是法典化时代最大的挑战:要么是立法规定得过于细致和琐碎、自命无所不包,以致法官只能在出现无法预料的情况时牵强附会;要么是立法没有给法官足够的指引,以致法官恣意妄为。所幸,这两种情况《法国民法典》都可以避免。他以三个气势磅礴的排比段分别列出了令沐浴在法典化曙光中的法国如此幸运的原因(可惜作者译笔无法尽传原文神韵):
在我们的社会,幸运的是法学成了一种人们可以奉献智慧、满足自尊、激发斗志的科学。……幸运的是有那么多汇编,有通过习俗、公理和规则建立起来的传统,让我们可以在今天如昨日一样裁判。……幸运的是当法官有必要调查、研究、深入了解他所需要裁判的案件时,他必须牢记不能放任自己的恣意和意志。〔20〕 Ibid.,at471-472.为了行文简洁,我们只能引用每一段的第一句。
法学家的学说和对习惯和判例的汇编恰如其分地成了立法的补充和法官裁判的指引。于是,立法只要以一般性的、适用于所有情况的规则指引法官即可,法官在遇到立法未加规定的情况时完全有能力借助判例、习惯和学说裁判。
这两个主张恰好体现了波塔利斯演讲对大革命前法律观念的传承。封建时代的法律秩序中,多种不同的法律秩序同时存在,在各种不同的秩序中不存在当然的等级差异。〔21〕 Cf.Jean-Marie Carbasse,Manuel d’introduction historique au droit,Pari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98 no 67;Jean-Louis Thireau,Introduction historique au droit,3eédition.,Paris,Flammarion,2001,at 134-140;Ernst Kantorowicz,La royautémédiévale sous l’impact d’une conception scientifique du droit,Politix,1995,vol.8,no 32,at5-22;RenéDavid,La doctrine,la raison,l’équité,Revue de recherche juridique,1986,no 1,at 118-127. 这种多元法律秩序的运作很大程度上围绕着习惯与其他法律渊源的互动展开。所以法学家理所当然会重视习惯,同时认为每一种法律渊源都有无法回答的问题,需要其他渊源来补充。
波塔利斯对习惯的强调展现了中央集权、民族国家、多元主义传统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在法国,法典化的先声是法令,17世纪绝对君主制形成后,国王为了增强中央集权而在法学家协助下完成的法令,已经初具法典的形态。颁布于1731年到1741年的几部法令甚至直接侵占了原本属于习惯法的核心领域——遗嘱、赠与、代理。其内容却大部分来源于不同地方的习惯。〔22〕 Cf.Norbert Rouland,Introduction historique au droit,1reéd.,Pari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98,no275. 与此同时,法学家也开始相信存在一个可以适用于整个王国的“法国法”。法学家开始考虑用巴黎(因而是法国北部)的习惯取代其他地方习惯的可能性。现代早期的习惯法学家们仿照罗马法学家的“共同法”理想,从习惯中寻找王国的共同法;在技术层面,他们则模仿《法学阶梯》的结构整合习惯法。于是,王权也从中获益,因为君主的立法把一地的习惯成文化时,也就意味着排除了其他地方习惯在相应领域的适用。〔23〕 Cf.Jean-Louis Thireau,La doctrine civiliste avant le Code civil,in La doctrine juridique,Pari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93,at13-51;Jean-Louis Thireau,Le jurisconsulte,Droits,1994,no 20,at 21-27;Jean-Louis Thireau,Introduction historique au droit,op.cit.,at 247-253. 于是,实务人士用巴列门的判决来证明某种习惯,学者由依据罗马法的方法将其整合并不断创造出适用于全体法国人的共同法,最后经由君主将其成文化。17世纪的多玛(Jean Domat)作为帕斯卡尔(Blaise Pascal)的好友和同道奠定了法国民法的理性主义基础,那么18世纪的波蒂埃(Robert-Joseph Pothier)作为奥尔良地方和法国北部习惯法的集大成者则确定了法国民法(特别是债法)的内容。〔24〕 Cf.Jean Gaudemet,Les naissances du droit:Le temps,le pouvoir et la science au service du droit,4eédition.,Paris,Domat-Montchrestien,1997,at338-340;Jean-Louis Thireau,Introduction historique au droit,op.cit.,at 349;Philippe Malaurie,Anthologie de la pensée juridique,Paris,Cujas,2000,at81 sq.;Pierre-Yves Gautier,Jean Domat?:l’un de cesmessieurs de Port-Royal,Revue trimestrielle de droit civil,1992,no 4,at529-530;Jean-Louis Gazzaniga,Domat et Pothier,Le contratàla fin de l’Ancien Régime,Droits,1990,no12,at37-45. 其结果是在大革命以前,成文法的形式和内容都已经大部分准备好了。在此过程中,包括罗马法、习惯法、教会法和国王敕令在内的多种法律渊源不断互动。虽然习惯法始终占据着最重要的位置,但没有任何一种法律渊源真正具有垄断地位。
站在旧制度的终点和新时代的开端,波塔利斯用重视习惯、承认法律的多元性总结了法典化之前的法律观。这些观念之所以尤为吸引人,是因为它们与现在习以为常的观念不同。然而即便在法典化时代到来前的法律实践中,以习惯法为素材创造适用于全国的成文法的尝试也已屡见不鲜。《关于民法典草案的演讲》是一份承上启下的文本,它除了总结以前的观念以外,还提到了今天所熟知、对于当时的演讲者和听众而言只是模模糊糊意识到的一个新观念:法律创造论。
根据项目示范区产权的划分和石首市项目区实际情况,从水库取水,灌溉方式为自流灌溉的末级渠系供水费用由管理费用、配水人员劳务费用和运行维护费用三部分构成。提水灌溉的区域,由于泵站为小型泵站,且产权归农民用水者协会所有,农民用水者协会负责运行成本和维修,因此,提水灌溉区域末级渠系供水费用由管理费用、配水人员劳务费用、运行维护费用及水泵运行成本四部分构成。
(二)实质的革命:承认法律创造的法典观
我们不能因为波塔利斯对传统法律观念的传承而忽略他在演讲中已经揭示的法律创造论。现代读者不能忘记的是,当时的语境是革命后共和主义观念占主导地位的时代。在19世纪的共和主义意识形态中,立法是规范的唯一来源,只有所有人平等地服从同一种法律,人才能保障自由和平等。〔25〕 Cf.Jacques-Guy Petit,La Justice en France,1789-1939.Uneétatisation modèle?,Crime,Histoire&Sociétés,juillet2002,vol.6,no1,at85-103. 正如1794出版的思想教育课本《无套裤汉的新共和派教义问答》(Nouveau catéchisme républicainàl’usage des sans-culottes)所写的那样,共和主义者依赖的“永远是法律,只有法律,而不是其他任何事物”。早在二十年前,我国学者就认识到《法国民法典》更多是对18世纪自然法思想的传承而非创新,“绝非象自由主义法学家认为的那样充满了个人主义的情调”。〔26〕 傅树静:《〈法国民法典〉改变了什么》,《外国法译评》1996年第1期,第45-54页。 而且1830年前后法典起草辩论逐渐公布出版前,法学家并未从立法者的意图出发解释法律。〔27〕 Cf.Sylvain Bloquet,Quand la science du droit s’est convertie au positivisme,Revue trimestrielle de droit civil,2015,no 1,at 59. 但是,法典的编纂者“是否打算创造全新的规范”“是否真正创造了全新的规范”“是否让法典中的规范如他们所理解的那样为法律的解释者接受”和“法典化是否意味着人能创造规范”终究是不同的问题。对于波塔利斯的听众而言,以立法、且仅仅以立法表达公意的卢梭(Jacques Rousseau)式观念是不言而喻的。故此,只能把波塔利斯所有关于立法尊重习惯和立法局限性的话语理解成对法律创造论的限制而非否定。
在基尔希曼演讲整整50年后,霍姆斯在波士顿法学院新大楼的落成典礼上作了题为“法律的道路”的演讲。〔72〕 OliverWendell Holmes,The Path of the Law,Harvard Law Review 110,no.5(1997):991-1009.霍姆斯演讲的中文本已有不止一个译本,见 〔美〕奥利弗·霍姆斯:《法律的道路》,张千帆、杨春福、黄斌译,《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00年秋季号,第6-19页;〔美〕O.W.霍姆斯:《法律之道》,许章润译,《环球法律评论》2001年第3期,第322-332页;〔美〕霍姆斯:《法律的道路》,陈新宇译,《研究生法学》2001年第4期,第108-116页。本文引用时参照了这三版的译文。 不少美国法学家认为,霍姆斯这份演讲稿是“法学史上最重要的论文”。〔73〕 Steven Burton,Introduction,in The Path of the Law and Its Influence:The Legacy of Oliver Wendell Holmes,Jr,ed.Steven Burt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1-6.本书中文译本参见 〔美〕斯蒂文·伯顿主编:《法律的道路及其影响——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的遗产》,张芝梅、陈绪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不同于那些希望整合霍姆斯之思想体系的研究〔74〕 人们对霍姆斯究竟采取何种一以贯之的哲学立场争论不休。不同的人把霍姆斯描绘成一个现实主义者、不关心道德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一个抽象的法哲学家,或实用主义者。Cf.Thomas C.Grey,Holmes and Legal Pragmatism,Stanford Law Review 41,no.4(1989):787-870.这些解释的共性在于强调霍姆斯思想的融贯性和体系性。 ,本文只具体聚焦于霍姆斯一篇文本中展示出来的一个想法〔75〕 霍维茨(Morton Horwitz)认为霍姆斯正是从《法律的道路》开始放弃寻找统一思想体系的。Morton J.Horwitz,The Place of Justice Holmes in American Legal Thought,in The Legacy of Oliver Wendell Holmes,Jr,ed.RobertWatson Gordon(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31. :以法律为工具改造社会。前文所说的法律创造论和法律进化论是这一想法的前提。如果法律由人创造,社会又不断向前发展,那么人们很容易接受应该不断由人来改造法律、使之与社会相适应的看法。当社会发展高速发展,法律改造的速度也会随之提高,以至于很难再维持法律的稳定。既然人可以改造法律,为何不能在预见到社会发展方向的情况下,通过法律推动社会进步?这样法律便不再对社会发展亦步亦趋,而是成了一种工具,一种服务于社会发展、却也引领社会发展之方向的工具。
正因为当时立法至上的革命观念已经深入人心,波塔利斯才集中精力讨论如果立法者想要制定一部“好”民法典,他们应该在哪些方面加以节制。在演讲另一个流传甚广的段落中,波塔利斯把“好的民事立法”说成是“人们可以给予和获得的至善”“道德的根源”“财产权的圣殿”“公共与个人和平的保证”。〔29〕 Ibid.,at465. 拥有这一切美好事物的前提是“法兰西民族选为其首席法官的伟人”在制定民法典时“始终致力于民族的荣耀和人民的幸福”。〔30〕 Ibid.,at 466. 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牢记“立法并非纯粹权力的行使,它还是智慧、正义、理性的体现。立法者虽然仰仗权威,但更肩负使命。”〔31〕 Ibid. 至于具体的措施,无非上文已经提到过的,允许法官在未来出现的具体事项上决断、尊重和保守习惯与传统。总而言之,好的立法者应当避免过度行使权力:“我们当前的时代过于偏爱变化和改革。在制度和立法方面,此前的若干世纪见证了太多的放任,那些属于哲学和启蒙的时代则见证了太多的过犹不及。”〔32〕 Ibid.,at482.
3)远期目标,智慧出行。在气象和路况信息详细、丰富、准确、及时,导航系统智能化、智慧化的基础上,借助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先进技术和理念,以期实现智慧出行,在出行前、路途中、返程时都能悉知最新的天气和路况信息,并得到系统的最优化建议,使出行更加安全、便捷和智能化。
波塔利斯在演讲中如此强调立法者应当自我限制,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他的听众不认为立法权本身可以受到限制,立法的内容也不受其他规范的内容限制。换言之,只要立法者认为有必要,完全可以用立法取代此前继受自地方习惯、法律学说或国王法令的规范。这也正是所谓法律创造论:人可以有意识地根据政治、哲学、实践等考虑和需要塑造法律,且不必然受限于一个先在的标准。可以说,酝酿了十年的法典编纂在1801年已经让法律创造论深入人心。无论波塔利斯个人是否共和主义者、是否接受立法表达之公意一定正确的想法,也无论《法国民法典》最终的文本到底有多保守,波塔利斯选择在代表起草委员会的第一次公开说明中就承认法律的创造论,本身就意味着他清楚听众并不会为此感到惊讶。
学生对于基因多样性以及生物多样性三个层次的关系认识粗浅,因此是本节的教学重点和难点。教师通过课前组织学习小组进行调查活动,收集并整理资料,课堂上请学生代表上台展示,引导学生从感性到理性建构“生物多样性”这一重要概念〔1〕。
法律创造论的出现和流行象征着法制史上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之间的转换。前文已经提及,法典化之前的旧制度时期,缺乏对于各种渊源在效力和适用上的优先性明确判断标准。主权者所颁布的法律也来源于对习惯法的发现和承认而非创造。现在,具有民主合法性的立法者可以凭空创造法律了。反之,任何规范只要没有经过立法者点石成金,就不能具有法律的地位。立法不但取代了习惯成为最重要的法律渊源,而且一改此前的碎片化状态,成了唯一的法律渊源。所以法典必须大致包括所有可以在诉讼中适用的规范,并形成一个不依赖其他任何法律渊源就可以大体实现自足的独立体系。为了让《法国民法典》确实形成一个独立的体系,起草委员会在“序编”(在法典草案通过前删除)第1条承认了自然法,第2条承认了万民法,又在第4条规定法国的国内法包括了自然法、万民法、立法和习惯。在大革命前的法律多元主义时代,除了立法以外还有其他法律渊源本来就不言而喻。现在,认识到立法之局限性的编纂者认为有必要(而且可以)在法典中明文承认自然法、万民法和习惯。这种做法恰恰说明了立法者获得了在规范创造方面前所未有的垄断地位。一方面,立法者通过立法确定其他法律渊源之有效性;另一方面,立法者通过这种姿态让法典所表达的法不再限于各编之具体规则的文义,从而真正成为能够说出所有“法”的作品。这样做的背后,则是任何规范如无立法认可均属无效的观念。
提出好的问题并设计成问卷,甚至可以与人工智能技术结合,用于中医诊断。百度公司前副总裁梁冬目前转行从事中医诊所事业,但他一直觉得中医不可能规模化、复制化。有一天,他碰到了一位从事人工智能研究的朋友,这位朋友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到中医研究上,改变了梁冬的看法。
(三)小结
就算早在18世纪就有了几部诞生于王权集中背景下的早期法典〔34〕 Jean-Louis Halpérin,Histoire des droits en Europe de 1750ànos jours,op.cit.,at62-64. ,法国大革命让法典编纂具有了现代意义。其现代性不仅体现在尽可能取消了人的身份性,更体现在伴随其编纂过程的共和主义政治哲学中。这种理念主张代表了公意的立法者有权创造法律,而一国之内的人民只应当服从立法。法典既是社会生活唯一的圭臬,又是共和国公民身份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革命后民族国家的建设意义重大。波塔利斯也意识到这种共和主义理念不容挑战,所以他选择了仅仅限制立法至上观念的范围,从而为革命前的旧法学和习惯法争取到了法典化过程中的一席之地。在这一意义上,波塔利斯绝对不是法律创造论的提出者,却以其法哲学沉思让这种新观念得以与既有的法学相容。其结果是《无套裤汉的新共和派教义问答》中较为激进的立法至上主义主张让位于在承认立法者之创造权的同时强调立法之不完备性的理论,并得以屡经共和与复辟之后仍然保留在法国法学正统中。
对开启19世纪法典化浪潮的第一部现代意义民法典的第一次说明并非开启新时代的大地春雷。在过去十年、三个官方草案的基础上,波塔利斯探讨了如何完成一部好的民法典。法典化过程虽然意味着立法取代其他法律渊源成为规范的最终和唯一创造者,但一方面需要保持和新政体不冲突的民事规范,另一方面也要把立法维持在一般规则与原则、“公理”的层面,让法官以此为指引裁决具体的个案。这看似保守、旧制度痕迹明显的判断背后,却是对大革命后中央立法者权力强化的认识或警醒。之所以有必要从理论上说服立法者自我限制,是因为在制度上已经没有什么权力能限制立法权了。此后,在法学上的表现是后人称之为“解经方法”(l’exégèse)的研究范式占据了上风。〔35〕 Cf.Julien Bonnecase,L’école de l’exégèseen droit civil,Paris,de Boccard,1924;Philippe Rémy,éloge de l’exégèse,Revue de la recherche juridique,1982,at254-262. 将近一个世纪里,不管法学家们的观点有多大差别,他们都主张《民法典》条文的字面意思和条文之间的逻辑关系是民法唯一的研究对象,甚至教学和教科书写作都要严格按照法典的条文顺序。〔36〕 1895年的教学改革允许教授们不按照法典顺序授课。到了1898年,不按《民法典》顺序撰写教科书才逐渐成为主流。对新教科书撰写顺序的辩护,Cf.Henri Capitant,Introductionàl’étude du droit civil:notions générales,Paris,A.Pédone,1929,at2. 背后的观念再明白不过了:立法者是法律的真正创造者。一个属于法律创造观的时代开始了。
三、《作为科学的法学的无价值性》与法律进化论
下面要研究的是一个具有高度争议性的文本。时间已经来到了1847年,地点在普鲁士王国的首都柏林,场合是一个柏林法学会(Juristischen Gesellschaft zu Berlin),演讲者是检察官基尔希曼。〔37〕 德国法学史上的一个争议是,1847年基尔希曼演讲的这个学会到底是不是我们所熟悉、现在仍在活动的那个“柏林法学会”。后者1859年才正式成立。在一部关于柏林法学会的博士论文中,作者提出基尔希曼发表演讲的学会是1848革命前夕众多公民讨论场所之一,和现在我们所说的柏林法学会没有渊源上的联系。Vgl.Andreas Fijal,Die Geschichte der Juristischen Gesellschaft zu Berlin in den Jahren 1859 bis1933.Berlin.Walter de Gruyter 1991,at 7.但拉伦茨1966年在柏林法学会发表演讲回应基尔希曼时,说自己有幸在“同一个协会”发言,而且这句话出版时保留下来了,至少说明学会本身乐于放任人们认为基尔希曼1847年发表演讲的组织是自己的前身。柏林法学会成立125周年的纪念大会以及相应文集中,也收录了一篇讨论基尔希曼演讲的讲话,其作者承认,对两个协会之关系的探讨至今没有结论。Vgl.Sendler Horst,Zur Makulaturproduktion des Gesetzgebers,in:DieterWilke,(Hrsg.),Festschrift zum 125 jährigen Bestehen der Juristischen Gesellschaft zu Berlin,Berlin.Walter de Gruyter,1984,at753-773.不过,据说在一个在“三月革命”以前很有影响力的报纸在报道这次演讲时说“现场观众反响并不强烈”。(Rainer Maria Kiesow,L’unitédu droit,Paris,éditions de l’école des hautes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2015,at38.)对比现场听众的平静和基尔希曼讲稿印刷后在德国法学界引起的强烈反响,似乎应该认为现场听众的立场更接近于基尔希曼而非后来猛烈抨击他的那些法学家。在这个意义上,可能当时邀请基尔希曼发表演讲的协会更接近于一个志同道合者组织的小型学者团体,而非一个能代表整个大都会法律行业的正式协会。 这名莱比锡大学的毕业生早年是刑事庭法官,1846年开始在柏林担任检察官,同时还是柏林哲学协会的主席。他的政治生活漫长且丰富。〔38〕 关于基尔希曼的政治生涯,参见Rainer A.Bast,Julius Hermann von Kirchmann:1802-1884.Jurist,Politiker,Philosoph,Berlin.Meiner Verlag 1993,at15 ff。另外,贝伦茨(Okko Behrends)评价他“固执己见、毫无妥协余地……又在思想上极具生产力的人物”,参见 〔德〕冯·耶林:《法学是一门科学吗?》(上),李君韬译,《比较法研究》2008年第1期,第152-159页,注2。 他1848年革命后成为普鲁士议会中代表自由立场的议员。革命失败后他加入了进步党,并在1867年帝国议会(Reichstag)创立时便成为其议员。基尔希曼的演讲在两个重要的方面与波塔利斯的演讲不同。波塔利斯需要资政院支持他,所以必须避免引起普遍的反感;基尔希曼则希望唤醒听众反思当时流行的历史法学,所以需要用更激烈的言辞刺激他们。〔39〕 拉伦茨就认为他采取了“论战形式”和“夸张修辞”,以“唤醒自我反思”。〔德〕卡尔·拉伦茨:《论作为科学的法学的不可或缺性》,《比较法研究》2005年第3期,第144-155页。 《对草案的说明》为波塔利斯赢得了长久的掌声、为起草委员会赢得了支持,而且此后两个世纪各国法学家都满怀谦卑地阅读他的文本;《作为科学的法学的无价值性》则为基尔希曼带来了争议和批评。最直观的不利影响是一次职务上的明升暗降:1850年基尔希曼收到一纸调令,离开当时已经有40万人口普鲁士首都柏林,前往位于下西里西亚偏远地区、刚成为普鲁士领土不久、人口不过数万的拉齐布日(Racibórz)任法院副院长。
即便如此,带着后见之明回望,又不得不承认这次演讲至少在两个意义上相当成功。首先,基尔希曼提出的法律科学性问题从此成了法学上一个重要的议题,经久不衰。〔40〕 他的演讲付梓后,不但马上引起了鲁道夫(Adolf Rudorff)的反驳,而且让耶林(Rudulf von Jhering)在1868年的维也纳大学就职讲座上以“法学是一门科学吗”为题作为回应,甚至1966年当拉伦茨在柏林法学会发表演讲时,也选择了基尔希曼的论题。同前注 〔38〕,〔德〕冯·耶林文,第152-159页;《法学是一门科学吗?》(下),《比较法研究》2008年第2期,第152-159页;同上注,〔德〕卡尔·拉伦茨文,第144-155页。 其次,基尔希曼揭示了不同于历史法学之概念化、体系化努力的一种进路,转而更加关注经验。〔41〕 Hubert Rottleuthner,Rechtswissenschaft als Sozialwissenschaft,in:Eric Hilgendorf/Jan Joerden(Hrsg.):Handbuch Rechtsphilosophie,Stuttgart.J.B.Metzler,2017,at251-254;Eric Hilgendorf,Revolutionskritik,Deutscher Idealismus,Utilitarismus,Marxismus und Positivismus,in:Eric Hilgendorf/Jan Joerden(Hrsg.):Handbuch Rechtsphilosophie,Stuttgart.J.B.Metzler,2017,at152-159. 不管如何评价基尔希曼,他的演讲中都表达了法律进化性观念。这种观念又植根于19世纪中叶欧洲的社会发展。工业化和商业活动范围的扩大一方面要求通过政治整合创造国内的共同市场、并以统一的法典规范社会,另一方面又希望法典中的规定满足不断变化的交易要求。但是禁止法律续造的规定却在法典中屡见不鲜。可以说正是基尔希曼所表达的这种进化论,让法学家在理论上有了突破法典条文、使法律回应社会要求的理由。
(一)法律进化论的出现
《作为科学的法学的无价值性》以法律的创造论为前提,强调立法因为是人的创造物所以可以改变,并由此阐述了一种法律的进化论。
连锁企业的涉及范围之广、领域之大,是我们根本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国外的许多企业,现在纷纷都要在各个国家建立分公司,持续连锁经营的发展理念,向国外输送技术、输送物资,企图建立与原公司相同的发展模式,为公司赢得更大的经济利益。连锁企业有着相同的管理模式,各行各业的人都可以参与进来,无论你是农民、工人,还是小区的超市老板,都可以参与进来,不用担心自己文化浅薄的问题,有专业人员给你们培训,而且物流资源一条龙服务,这是你最优的选择。
2.4 疗效评估 患者应当在拔除尿管之后的4~6周复诊,以评价治疗反应和不良事件。如果患者的症状得以缓解且无不良事件,则没有必要进行进一步评估。在4~6周后随访时建议进行以下检测:IPSS、QOL、尿流率和残余尿测定。
一种有价值的法学必须认识到法律的可变性。他所批判的那种作为科学没有价值的法学是忽略了法律之可变性的法学。法学的研究对象是法律,“就是在一个民族中生存着并且由每个人在各自的范围内实现的法律,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为 ‘自然法’”。〔48〕 同前注 〔42〕,〔德〕尤利乌斯·基尔希曼文,第140页。 然后他又说:“首先进入我们视野的一个特征就是作为法学研究对象的自然法的可变性。”〔49〕 同上注,第141页。 正是对象的可变性让法学区别于其他的科学。如果一门学科研究的对象是在时间流之内不断变化的,那么这一对象在每个时代不但表现的特征不同,也具有不同的本质。所以研究不同时代的法律,根本就是在研究完全不同的事物。既然如此,历史法学试图用过去的法律制度来构建现今的制度的做法就完全是错误的。因为这一作法背后的假设是包括家庭、国家、债、乃至所有权在内的一切法律制度都各自有一个核心的本质,通过研究过去的制度可以了解这一本质,从而推论现在应该存在的制度。于是,他认为“按照过时的条条框框来构建现今的制度”就成了“法学罹患的第一个重症”,其结果是“法学自身成了法律向前发展的绊脚石”。〔50〕 同上注,第142页。 要治愈这一重症,就有必要抛弃对制度之历史连续性的迷梦,转而研究那些在本质上就和此前的制度不同的现实法律。
如果法学应该以法律为研究对象,又不应该囿于过去的法律和当前的立法,那么留给法学的可能性只剩下一个了:研究未来的法律。基尔希曼把法律分成自然法和立法。“对于现实的法律却完全视而不见,很自负地把现实的法律推给那些受到轻视的实务工作者”〔51〕 同上注,第143页。 这句话中“现实的法律”说的绝不仅仅是“现行有效的实证法”,它同时也包括了“现在的自然法”。于是马上浮现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判断自然法?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基尔希曼提出:“法律不单纯是一种认识,它同时还是一种感受,它不仅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而且存在于人们的心目中。”〔52〕 同上注,第143页。 而且法律同时作为一种知识和一种感受的特征正是人们应该予以保留和重视的:“对于法律的这一特征不应视为瑕疵,恰恰相反,它或许正是法律的最高价值所在。”〔53〕 同上注,第144页。 既然法律包括了感受的一面,那么法律的可变性实际上是与这种感受的可变性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他才指出,“任何时代都有深刻触动整个民族的法律问题……这些问题告诉人们在哪些领域就有的概念已经逐渐死亡,法律迫切需要新的创造”。〔54〕 同上注,第154页。 这反过来解释了为何每个时代的法律即便在外观上有着重要的共性,却具有不同的本质:人们的感受发生了改变,理解那些看上去一样的法律概念时便不可能遵循前人的理解。于是,如果法学“从来就不曾对现实有所感悟”〔55〕 同上注,第155页。 ,那么就无法洞察现实中正在发生的关于法律之感受的变化。更重要的是,法感受不仅仅时刻在变化,而且在不断进步:“对于以上的指摘,人们不能反驳说这不是法学的事,而是属于立法的政策和艺术,当其他学科以掌握或者引导新事物作为最重要的任务、作为终极目标时,法学却自外于政策,对新事物无能为力,这是法学的悲哀。”〔56〕 同上注,第154页。 如果法学想要让这种悲哀终结,就有必要把新产生的法感受作为自然法的要求接受下来,然后用立法的工具实现它。如此分析演讲的文本就不难看出,此处的“现实的法律”不仅仅是“如其所是”的现行实在法(lex lata),也包括了由法感受表达的、“如其所应是”的未来之法(lex ferenda)。所以,有科学价值的法学必须研究人民感受中体现的未来之法,而这种法学必然认为法律本身是可以向前发展的。
所以,不妨认为《作为科学的法学的无价值性》表达了法典化时代的法律进化论。
为满足教学目标并保障教学效果,在药理学教学中成功实施案例教学法,需要遵循如下基本原则:理论联系实际原则,以基础理论为导向,同时有机结合实际问题;重要性与典型性并存原则,强调选择具有理论重要性和方法典型性的案例;针对性原则,既要针对专业知识,又要针对临床实际问题。
(二)稳定性与开放性追求之间的法律进化论
上一部分重新解读了基尔希曼的名言。除了对法学的批评以外,“立法者的三个更正词就可以使所有的文献成为废纸”这句话还意味着今天存在的事物,明天可能完全是另外一种样子。于是,立法(自然也包括了法典)必须放在时间的序列中考察。波塔利斯所断言的还只是生活中有立法者无法预料之事,却没说社会在发展变化。基尔希曼则明确主张法典一定会在社会发展中变得落后。法律进化论的出现在19世纪中期并非偶然。一方面,此时法学界出现了“超越法典”的主张;另一方面,包括法学、哲学、自然科学在内整个知识界开始关注变化而非永恒。法律进化论的出现意味着此前过于强调安定性和确定性的德国法学开始迎接另一种可能性。
基尔希曼的演讲中既承认了立法者对法律的创造,又蕴涵了法学家要“通过立法、超越立法”的意思。其言外之意是法律的解释者必须构想比立法文本所表达的规范更高明的“自然法”。超越立法文本的想法虽然表达在了波塔利斯的演讲中,但19世纪的主要法典仍致力于阻止解释者的僭越。文义解释和逻辑解释还是各国立法者用以限制法学家们的解释原则。比如在《巴登大公国民法典》(1809)第6条a款中规定:“本法典各条款对民事法律相关事项或作出明确规定,或通过逻辑解释可以得出,除非其他条款作出了相反的规定”。19世纪中叶的民法典则加入了立法者意图的考虑。比如《撒丁王国民法典》(1848)第14条要求法官“在适用法律的过程中,不允许超出条文本身、不同条文之间的组合以及立法者意图之外赋予其它的意义”。《摩德纳民法典》(1852)也类似:“在法律适用过程中,不应当赋予条文超出其用词本义或立法者明示意图之外的其他意义”。〔57〕 Cf.Sylvain Bloquet,La loiet son interprétationàtravers le Code civil,Issy-les-Moulineaux,Librairie Générale de Droit et de Jurisprudence,2017,at394. 然而19世纪初的法学家——所谓的“解经法学家”们——在试图理解法典“文义”时已经广泛援引罗马法、法学家法和其他渊源了。到了19世纪30年代末,随着社会生活日趋复杂、立法中的缺陷暴露得越来越多,已经有强有力的声音主张在通过判例寻找法律所能实现的“社会目标”,从而让判例参与法律演化。〔58〕 Alexandre Ledru-Rollin,Coup d’œil sur les praticiens,les arrêtistes et la jurisprudence,Journal du Palais,1842,vol.3,at IX. 从他同时代人这种对解释方法和法律渊源的探讨中,基尔希曼又往前迈了一步,提出立法只是法律的一部分,而且立法不过是实现不断发展演进的“人民的自然法”之形式工具。
法律进化论背后是一种特殊的时间观,人们开始承认每个时代与此前的时代都在一些重要的方面有所不同。世界在不断发展,社会也随之发展,而法律亦随着社会而发展。〔59〕 丁晓东:《美国宪法中的时间观》,《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7年第1期,第159-170页。 现代的法律背后的线性时间观认为“时间会从某一点出发,不可逆地向前延伸,没有确定或可知的终点”。〔60〕 熊赖虎:《时间观与法律》,《中外法学》2011年第4期,第681-694页。 法律进化论的时间观就更是一种特殊的线性时间观,认为时间不仅是向前延伸的,而且一个时代总是比过去的时代要好。这种时间观在“现代”形成,并逐渐在与其他时间观的竞争中占据上风。它究竟起源于哪个具体的历史时点现在无从确知,只能说从学术史的角度看,19世纪中叶正是这种时间观流行的时刻。〔61〕 朱明哲:《面对社会问题的自然法》,《清华法学》2017年第6期,第75-99页。 进步主义时间观只有在法典化时代才能进入法学,因为只有在人们普遍认为创造法律的是人的意志而非自然法、神的旨意、来源不可考的习惯时,才有可能接受法律是可以改变的。甚至人可以自己的努力使法律“变得更好”。所以基尔希曼才欣喜地主张,法律的可变性是法学本身的光荣。在这一意义上,法学无法成为一种追求永恒公理的科学反而是优点而非缺点。〔62〕 基尔希曼说的“科学”指的是进化论提出以前的那种关注静态的科学。而且,近年科学哲学和社会学的研究也倾向于认为自然科学所研究的对象也非完全不受研究本身的影响。Cf.Alberto Artosi,Please Don’t Use Science or Mathematics in Arguing for Human Rights or Natural Law,Ratio Juris23,no.3(2010),at311-332. 此外,波塔利斯只希望法官实现法典条文的具体操作,他主张法典不要过于细致的理由也是避免法律经常修改而处于不稳定状态。基尔希曼则视修改法律为稀松平常的事情。相比于让立法成为社会改革的障碍,还不如牺牲立法文本的稳定性。
正是这种对法律进步的信念最为直接地刺激了19世纪历史法学的神经。不要忘记1847年演讲的地点是柏林,此时,柏林大学的教授萨维尼“及其创立的历史法学派统治着整个德国法学”,“柏林大学取代了哥廷根大学、海德堡大学成为德国法律学术的中心”。〔63〕 舒国滢:《德国1814年法典编纂论战与历史法学派的形成》,《清华法学》2016年第1期,第92-111页。 借着对回首历史、整理国故方法之科学性的批判,基尔希曼也否定了19世纪德国历史法学中秩序、确定性、封闭性之梦。〔64〕 Rainer Maria Kiesow,L’unitédu droit,op.cit.,at37. 历史法学所强调的法学中立性和科学性在那个特定的历史语境下实际上就是保守和反对改革的政治立场。〔65〕 〔德〕霍尔斯特·雅科布斯:《十九世纪德国民法科学与立法》,王娜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57-58页。 基尔希曼强调的法学政治性则要求法学认真考虑政治进步、经济自由、民族统一的要求。与其说基尔希曼标新立异地批判了历史法学,不如说19世纪40年代末的革命氛围中对历史法学的普遍不满通过他表达了出来。〔66〕 Vgl.Eric Hilgendorf,Revolutionskritik,Deutscher Idealismus,Utilitarismus,Marxismus und Positivismus. 演讲发表的次年,即1848年,革命的浪潮席卷全欧,德国爆发了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革命——“三月革命”,象征着德意志民族意识觉醒的艺术形象“日耳曼尼亚”广泛流传。在这种革命氛围中,可以说法律的科学性并不是基尔希曼关心的主要方面,他只是以此介入1814年论战以来的法学传统。这名日后的进步党人关心的是民主、是当下、是创造适应时代精神的新法律的可能性、是人民通过政治运动表达出来的对变革的要求。〔67〕 Cf.Rainer Maria Kiesow,L’unitédu droit,op.cit.,at55-56. 也正是在这种革命氛围中,历史法学以科学之客观性拒绝政治运动影响的努力终告失败,标志性的事件便是《历史法学杂志》(Zeitschrift für geschichtliche Rechtswissenschaft)仅仅在三月革命之后两年,就在1850年第15期出版后宣告停刊。当然,期刊停刊并不必然意味历史法学的衰败,更不意味着以科学驯服政治的法学家法传统的终止。继起的学说汇纂学派传承、改造并发展了历史法学的成果与精神,并促成了《德国民法典》的最终问世。〔68〕 舒国滢:《19世纪德国“学说汇纂”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中外法学》2016年第1期,第5-36页。 然而无论是概念法学、利益法学还是自由法学,“三月革命”后的法学思潮或多或少都接受了进化的法律观。它们的区别仅仅在于到底是精英法学家还是大众在推动法律进化。
所以,说法律的进化论是法典化时代的第二个发现并不为过。
当时,竹韵即将从省城一家高等职业技术学校毕业,学校组织全校师生去听了一场龙斌的报告会。竹韵坐在最前排,每次掌声响起来的时候她都热泪横流,把手掌拍得发麻。坐在轮椅上的龙斌在她眼里变成了一座巍巍丰碑。听完报告,她第一个冲上台去,讨到了英雄的签名。回到学校,她醮着热泪,写下了一首情意真挚,后来被百余家报刊争相刊登的人生宣言般的长诗。嫁给英雄的念头就是在那时萌动的,接着她冲破父母和亲人的阻挠,谢绝了同学和朋友的劝告,义无反顾地走进了英雄的生活,轮椅在她手上一推就是八年……
(三)小结
一名实务人士对法学的批判在此后一个半世纪里不断引发法学教授的回应,本身就是一个不寻常的现象。基尔希曼对法学之科学性的质疑同时表达了他那个时代的法律观:既然立法是人创造的,那么可以因为人的意志而改变;既然人有能力通过改变立法而改变法律,那么就应该试着改进它;要想改进立法,必须从社会的运动之中了解民族之自然法的最新表达。于是可以推断,“三月革命”在他眼中恰恰是一场“为法律的斗争”。基尔希曼的立场很大程度上表达了19世纪中期整个西欧法学界的关怀。面对工业发展所带来的经济自由化和政治一体化的要求,法律必须在稳定性和社会开放性两者之间取得平衡。〔69〕 Cf.Jean-Louis Halpérin,Histoire des droits en Europe de 1750ànos jours,op.cit.,at72-74. 如果说波塔利斯要在19世纪初解决的是人类应该如何编纂法典的话,那么基尔希曼在欧洲各个政治体已经出现了多种法典方案(不仅民法典,还有刑法、商法、诉讼法等部门法的法典)的情况下,希望解决的是如何改良法典的问题。在法学中,人们希望超越法典;在知识界,进步主义的时间观开始占据上风;在社会上,通过革命实现政治改革的想法最终落实为行动。所有这些因素都构成了理解基尔希曼演讲不可或缺的背景。
基尔希曼还表达了法律的工具观:立法“还是一件没有意志的、随时可以使用的武器,无论对狂热的暴君还是对于聪明的立法者都是如此”。〔70〕 同前注 〔42〕,〔德〕尤利乌斯·基尔希曼文,第146页。 在他看来,立法是一种把人民的法情感实证化为法律的工具。〔71〕 在1933年纽伦堡德国法学家大会以后,支持纳粹的法学家把1847年演讲中对人民法情感的强调曲解为法律的民族性论题,参见高仰光:《纳粹统治时期德国法律史学的源流、变迁与影响——以价值与方法的“连续性”为视角》,《比较法研究》2017年第2期,第139-160页。但基尔希曼本人没有任何意义上的种族主义、集权主义倾向。 但对于法律工具论的完整阐述,还要留待半个世纪后的一位美国法学家完成。
法律创造论是法典化时代对法哲学的第一个贡献,它成了法律工具论和法律进化论的前提。首先,波塔利斯明确指出立法的局限性在于立法者无法预计社会生活发展中会出现何种需要法官裁判的纠纷,也就意味着他模糊意识到有必要根据世事变迁发展法律。虽然他没进一步说“改变法律”,他所倚重的习惯也更多是面向过去而非未来的规范,然而他至少承认现在的规范有补充和发展的可能。只有在接受了法律创造论的情况下,人们才有可能主动依照时代需求补充、发展、改变法律。否则,只能像旧制度下的法学家那样,主张可以用来裁判新情况的规范已经蕴含在习惯、学说、罗马法等等不同的法律渊源之中了。反过来说,既然法典化时代的开端把立法奉为唯一的法律渊源,原先多元主义的解决方式本身也不再可能了。其次,如果法律来源于人的创造而非一个人格神的意志或遥不可知的传统,那么人们很容易进一步主张应该用法律来实现人的某些目的。波塔利斯确实说立法者是“自然公平的虔敬解释者”〔33〕 Ibid.,at 465. ,但他也强调了好的民法对于繁荣、秩序、公民自由的保证,后者恰恰是大革命后立法者所希望实现的目的。
四、《法律的道路》与法律工具论
《关于民法典草案的演讲》清楚地承认了立法者可以通过民法典创制他们认为合适的规则。在他看来,这种认为可以推翻一切、否定一切、创造一切的想法已经过度,所以才必须提醒现实存在、就坐在他面前的立法者们谨慎地行使权力。不同于逐渐形成于实践中的习惯,立法来源于主权者的意志:“在每个社会,立法是主权者关于共同利益之意志的庄严宣告。”〔28〕 Jean-Etienne-Marie Portalis,Discours préliminaire prononcépar Portalis,le 24 thermidor an VIII,lors de la présentation du projet arrêtépar la commission du gouvernement,op.cit.,at477. 作为主权者的立法者有权对涉及公共利益的事项进行任何规定。面对在革命中经过共和主义观念洗礼的立法者,讨论立法者是否“有权”进行各种过于细致的规定、是否有权抹杀所有习惯和传统,已经不再有意义,反而会让起草委员会的法律实务家们陷入他们并不擅长的政治哲学争论。
首先要研究的演讲是以《民法典》起草委员会名义发表的“法典起草委员会关于民法典草案的演讲”。〔8〕 Jean-Etienne-Marie Portalis,Discours préliminaire prononcépar Portalis,le 24 thermidor an VIII,lors de la présentation du projet arrêtépar la commission du gouvernement,in Recueil complet des travaux préparatoires du Code civil,Paris,Videcoq,1836,vol.I,at 463-524. 时间是1801年1月21日(共和历9年雨月1日),听众是资政院成员〔9〕 在法国执政府(Consulat)时代,根据1799年(共和历9年)宪法,资政院是负责法律起草的机关。现在这一机构(Conseil d’état)成了法国的最高行政司法机关,所以一般译为“最高行政法院”。 ,“第一执政”拿破仑也在座。起草并发表演讲的是法国民法学家波塔利斯。〔10〕 波塔利斯的儿子说他是演讲稿的唯一起草人,但有证据显示波塔利斯的秘书们至少合作起草了演讲的初稿。Jean-étienne-Marie(1746-1807)Auteur du texte Portalis,Discours,rapports et travaux inédits sur le Code civil,Paris,Joubert,1844,at1;Bernard Beignier,Potalis et le droitnaturel dans le code civil,Revue d’histoire des facultés de droitet de la science juridique,1988,no6,at77-101.这名普罗旺斯法学家19岁就在律师协会注册,在为包括各界名流的辩护中获得了极高的知名度。大革命的风暴中,他因为在1793年坚称不应处死国王而遭流放。后在拿破仑邀请下返回法国,成为民法典起草委员会最重要的一员。 后来波塔利斯还多次向资政院说明过草案的其他内容。不过这一次说明因为是以起草委员会名义所为之第一次公开演讲,所以自1827年整理出版以来流传最广,并在传播过程中添附了越来越多的传奇色彩。〔11〕 Cf.Bernard Beignier,Potalis et le droit naturel dans le code civil,op.cit.但他们并非第一个委员会,他们的草案也非第一个草案。此前康巴塞雷斯的委员会已经提交了三个完整的草案。 相比于家庭和财产部分在各价值取向之间的微妙平衡,我们重视的是草案中对“序编”(Livre préliminaire)的说明。〔12〕 关于《法国民法典》各草案中主导意识形态的比较,参见朱明哲:《“民法典时刻”的自然法——从〈法国民法典〉编纂看自然法话语的使用与变迁》,《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2016年第2期,第10-28页。 虽然这一编“法与立法”的大部分内容没有出现在投票表决的草案中〔13〕 虽然法典编纂时期的讨论记录已经汇编出版,但我们仍没有明确的证据说明为何“序编”大部分的条文在草案第二次提交审议的时候就已经删去了。一种猜测是议员们认为其中包括了过多“属于法哲学而非民法典”的内容。Cf.Pierre-Yves Gautier,Pour le rétablissementdu livre préliminaire du code civil,Droits,21 octobre 2005,no41,at37-52. ,但波塔利斯如此精练地概括了支配起草委员会工作、并在此后作为法国模式之蓝本影响了多个国家民法典编纂的哲学,以至于每当人们探讨“真正的”法典化概念,总会追溯到这次演讲。〔14〕 其中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惹尼从中找到了法官解释权扩张的论据。François Gény,Méthode d’interpré tation et sourcesen droit privépositif:essai critique,Paris,Pichon et Durand-Auzias,tome II,1899,at87-90.对于其中关于民法典编纂的全面检讨,参见石佳友:《法典化的智慧——波塔利斯、法哲学与中国民法法典化》,《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5年第6期,第91-101页。 而且,讲稿相当精确地把握了民族国家兴起过程中法学观念的转变。要研究法典化时代开端的法律观,不妨从这次草案说明开始。
(一)从法律进化论到法律工具论
在对于霍姆斯的种种解读之中,工具主义法律观是最为传统的一种。〔79〕 Robert Summers,Instrumentalism and American Legal Theory(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2),at20-34. 本文不需要再多费笔墨证明《法律的道路》中表达了工具主义法律观。有必要完成的工作是通过对文本的研究,揭示构成法典化时代法律观的三个方面联系在一起的方式。
首先要指出的是,在19世纪末,明确说法律是一种政策工具仍是一种大胆的主张。〔80〕 霍维茨意识到这种强调法律工具性的观念出现于19世纪。但他主要关心的是美国普通法上的法官如何使用法律。Cf.Morton J.Horwitz,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Law,1780-1860(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9),1-4.本文的主张是,“实际上把法律作为工具使用”“意识到法律的工具性”和“明确主张法律是一种工具”三种状态之间仍然有很大的差别。此外,霍维茨的研究容易造成一种印象:法律的工具论是一种美国特色。我们不否认19世纪的美国法官确实在创造法律实现社会变迁。但这种观念不仅出现在美国,也出现在欧洲。如果我们把大西洋两岸放在一起考虑的话,会发现各国的讨论从来不是孤立的。下文将会更详细探讨这一点。 霍姆斯演讲的开篇是:
我们所研究的法律不是什么神秘的事物,而是一种众所周知的职业。我们研究的是当我们进行诉讼、或者向他人提供建议助其避免诉讼时,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法律之所以是一种职业,人们之所以付酬让律师为自己争辩或提供建议,是因为我们的社会中公众授权法官行使公权力,并在有必要时举全部国家权力执行其判决与裁定。人们想知道在何种情况下、在多大程度上,他可以冒险违背远较其自身强大的国家权力,那么查明何时对此望而却步就成了一门职业。我们所研究的对象也就成了预测。我们要预测的是公权力会借助法院有所作为的概率(the prediction of the incidence of the public force through the instrumentality of the courts)。
根据霍姆斯自己的记录,演讲当时室内相当拥挤,而且空气不好。在他演讲以前,听众们已经忍受了一个多小时的祈祷词,以及关于波士顿大学法学院财政安排冗长乏味的介绍。但霍姆斯马上把他们从昏昏欲睡中唤醒,并一直让听众仔细倾听一个多小时直至结束。〔81〕 Cf.Horwitz,The Place of Justice Holmes in American Legal Thought,at71. 其成功,至少部分要归功于这第一段中明确反对传统的内容。戈登(Robert Gordon)指出,维多利亚时代法律人热衷于在这种庆典场合对未来的律师就他们的职业发表演说,并有固定的文风。〔82〕 Robert Gordon,Law as a Vocation:Holmes and the Laywer’s Path,in The Path of the Law and Its Influence:The Legacy of OliverWendell Holmes,Jr,ed.Steven Burt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at7-32. 类似演说一般会指责三种不称职的律师:因为科学性不足而无法意识到法律文本和判例背后之更一般性原理的律师;从事律师行业仅仅为了赚钱的律师;缺乏反思、一门心思服务其雇主利益而非司法目的的律师。〔83〕 Gordon,at9. 那么霍姆斯在他的第一段中就逐一背离了这种话语传统:研究法学要服务的不是原理,而是实践;律师行业的核心在于收取顾客的费用并提供辩护或咨询;律师所服务的就是他的雇主,而且他的雇主时刻准备冒违法的风险行事。
就从基尔希曼最让人印象深刻的那句名言开始吧:“立法者的三个更正词就可以使所有的文献成为废纸。”〔42〕 〔德〕尤利乌斯·基尔希曼:《作为科学的法学的无价值性》,赵阳译,《比较法研究》2004年第1期,第146页。 它首先传达了两层意思:①法学把立法当作主要对象,而立法是立法者意志的创造;②立法者可以随时改变作为法律一部分的立法。我国学者近年在民法典编纂的背景下已经逐渐意识到了第一种观念及其与法典化的关联。〔43〕 张力:《民法转型的法源缺陷——形式化、制定法优位及其校正》,《法学研究》2014年第2期,第73-92页。 至于第二种观念,目前还隐藏在关于法学的科学性、具体来说是法学作为一种科学的确定性上。〔44〕 陈辉:《德国法教义学的结构与演变》,《环球法律评论》2017年第1期,第149-167页。 这两种观念相互联系,在法典化时代成型并流传下来成为我们法律观的一部分。如果说波塔利斯在1801年还不愿意直言立法者可以根据其意志创造任何规范、希望说服立法者接受起草委员会专家的指引,那么基尔希曼在1847年已经可以毫无顾忌地说即便是立法者的“无知、粗俗和狂热”也不能妨碍其创造作为立法的实在法。这说明至少在19世纪中叶,德意志法学家已经广泛接受了立法来源于人类创造这种想法。否则基尔希曼也不会批评他们只研究立法,甚至只关心“实在法的漏洞、歧义、矛盾”。〔45〕 同前注 〔42〕,〔德〕尤利乌斯·基尔希曼文,第138-155、146页。此处“实在法”在原文中为“positive Gesetz”,指的实际上就是本文用的“立法”。下文中除非直接引用译文,否则将还是使用“立法”一词。类似的情况是基尔希曼用来表达“自然法”的词汇是“natürliche Recht”而非人们现在更习惯的“Naturrecht”。 当时,德意志各邦国既未完成法国在大革命后的实现的中央集权民族国家建设,也没有正式接受卢梭式共和主义的政体和政治思想,但法典编纂早就已经于1794年《普鲁士普通邦法典》开始编纂时启动了。这恰恰说明法律创造论虽然可能在法国与共和主义相关,却可以脱离共和主义在法典化时代独立存在。在这个意义上,基尔希曼的名言首先延续了波塔利斯早在半个世纪以前表达过的想法,只是更加大胆和直接。
无疑,这一开场白提纲挈领地提出了关于预测论、坏人视角、非道德主义法律观等等一系列在下文中出现的主题。但最后所有对维多利亚时代传统的背离和新观点的出现都落实到了一个分句上:“我们要预测的是公权力会借助法院有所作为的概率”。从这个分句开始,法院成了公权力的工具。这相当于本次演讲文眼的分句只有在和霍姆斯关于法官造法和法律进化性的主张放在一起时,才能完全展现其含义。
《法律的道路》和此前两篇讲稿一样,都承认法律来自于创造,但霍姆斯把重点放在了法官对法律的创造上,否定了来自立法者的顶层设计。必须承认的是,关于霍姆斯接受法律创造论的理解并非毫无争议。不但那些对《普通法》(1881)印象深刻的研究者会认为霍姆斯倾向于法律来自于历史的自发生长,而且《法律的道路》中一些重要的段落也暗示法律并非来源于人的创造。比如他把法律的发展与植物的发展相类比,“每一代都迈出了不可避免的下一步,思想和物质一样,无非在服从自生自发规律(spontaneous rules)罢了”。〔84〕 Holmes,The Path of the Law,at 1000. 他还马上举出了当时最富盛名的法国社会学家塔尔德(Gabriel Tarde)在《模仿律》中提出的观点,说每个人都不过是在重复着我们的父辈所做之事。然而霍姆斯在此谈论的是法律“作为研究主题的现状”,而非其“所趋向的理想状态”。〔85〕 Holmes,at1000. 换言之,对传统的研究最多只能解释法律为何以现在人们所能见到的规则的形式存在。而这恰恰只是霍姆斯带领我们迈向“仔细反思这些规则之价值”的第一步。或者用他的话来说,历史研究只是把生成于传统的法律这条恶龙“放在光天化日之下、数清其爪牙、了解其力量”,接下来要么杀死它,要么驯服它、使它成为有用的动物。〔86〕 Holmes,at1001.
霍姆斯接着说:“懂得法律条文的人面向现在,而经济学和统计学大师展望未来。”〔87〕 Holmes,at1001. 研究法律的具体形式、文义、历史渊源只能帮助人们看清现存的法律,却无法让人理解在工具的意义上,公权力可以通过法律做些什么。他在前面的段落批评法官们“未能适当认识到他们对权衡考虑社会利益的责任”〔88〕 Holmes,at 999. ,正是因为法官们以适用规则之名拒绝承担考虑社会利益的责任。法官们担心规则制定的权力过大,只好把它留在立法者手中。〔89〕 同上注。 霍姆斯则敏锐地指出法官就是规则的制定者,如果要他们为这些规则提供理由,那么法官们就会发现他们在声称仅仅适用规则之处,也实际上在充满争议的问题上选择了立场。〔90〕 Holmes,at998. 在列举了从侵权法、刑法、合同法一系列例子说明过去的法律在司法中造成的困惑后,这名马萨诸塞州的法官马上说:“法律是一项我为之献身的职业。如果我不像我内心所指示的那样去改进它,如果我察觉它未来可以实现的理想却踌躇不前、没有全心全意使之接近这一理想的话,我的所作所为便称不上全心投入。”〔91〕 Holmes,at 1005. 那么,一个投身法律事业的法官应该成为展望未来的人,在理解现在规则的基础上根据这些规则在当今社会中实际效用要么废除它们、要么改变它们。
所以,法律的工具性主要体现在人们创造法律并以此实现一定的社会利益。创造法律的人不再只包括立法者,还包括了法官。如果说法官创造规则是一种现实,那么正视这一现实并用这种权力推动社会发展则成了一种法官应该努力实现的理想。
乳腺癌是目前临床的常见、多发病之一,虽男、女均可患病,但女性相对较多,占99%,男性发病率不足1%[5]。关于乳腺癌的病因机制至今尚不清楚,有研究认为乳腺癌的发生、发展与年龄、遗传等因素息息相关,并认为乳腺癌的发病高峰为50~54岁,而当年龄≥55岁时乳腺癌的发病率呈降低趋势[6]。乳腺X线技术是目前国际公认的一种乳腺癌筛查手段,特别是在检查乳腺钙化方面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传统FFDM依靠二维平面技术成像,易导致组织重叠,尤其是用于致密型乳腺的检查,由于该类型腺体缺乏组织密度,因此极易出现假阴性、假阳性的问题[7-8]。
法官要勇于承担责任、创造法律的最根本原因还是时代的剧烈变迁。霍姆斯在批评对逻辑的过分强调时说,“确定性不过是一种幻想,而和谐亦非人类命定固有的状态”。〔92〕 Holmes,at998. 这句评论意味着霍姆斯与兰德尔(Christopher Langdell)的经典美国法学决裂,从对逻辑确定性的追求转向了随时准备“以法治国”的理念。在逻辑形式之下总存在着未经表达的无意识价值判断。在这些价值判断不受挑战的年代,不妨认为严格的逻辑形式确实可以保证一定的确定性。然而他和耶林一样,认为世界已经进入了一个斗争的年代,人们对这些价值本身不再有统一的认识。〔93〕 耶林的《为法律而斗争》在1897年还没有翻译成英文。但霍姆斯无疑已经直接用德语阅读了这份讲稿。在耶林的影响下,19世纪末在德国、法国、美国都出现了把法律比作“斗争”的想法。霍姆斯也是其中的代表。Cf.William Seagle,Rudolf von Jhering:Or Law as a Means to an End,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13,no.1(1 December 1945):at71-89;Brian Z.Tamanaha,ARealistic Theory of Law(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7),at138. 他随后举侵权法为例,说它“来自旧时代的那些彼此独立的、没有普遍特征的过错、人身攻击和诽谤以及类似的情况,法律判断就可以决定它们都造成了什么损害”,但今天所面临的侵权案件却由铁路、工厂这样的大企业所致。〔94〕 Holmes,The Path of the Law,at999. 言下之意是工业社会的发展已经让人们必须反思传统侵权法的过错主义价值评价基础,转而考虑严格责任的合理性。如果说基尔希曼在革命前夜指出的法律进化性还是一种对未来的预言,那么霍姆斯在20世纪前夕显然已经意识到法律必须应对早已深刻变革的社会了。在这个意义上,他并没有比基尔希曼走得更远。但是基尔希曼仍然受制于19世纪中期的创造论,认为法学家只能从人民的法情感中发现未来之法,没有具体谈到法官应当如何作为。多亏19世纪末的社会科学发展,霍姆斯意识到掌握了统计学和经济学的法官完全可以从不同利益的斗争中自己分析出未来的法律规则,然后再以规则制定者的身份公布这些法律。
于是,霍姆斯这篇在维多利亚时代致辞传统下看来离经叛道的演讲,反而延续了19世纪不断自我表达、争论和辩护的法律观——法律来自人的有意创造、法律要不断进步。只不过他继续把这种法律观向前推进了一小步,主张法律不仅仅被动地适应社会,还要在相互竞争的利益、价值中作出判断,以属于明天的法律把社会推向更美好的前景。也只是在这个意义上,法律是公权力的工具。下面要说明的是,他的法律工具论应该在美国法典编纂的争议之中理解,所以仍是法典化时代的产物。
(二)法典化时代的法律工具论
法律工具论同样是一个产生于法典化时代的观念。这样说不仅仅是因为它在19世纪的出现与法典化在时间上重合,更是因为它回应了法典化现象所引发的一系列讨论。《法律的道路》展现的是一种当时不仅出现在美国、也同样出现在欧洲的观念。法典化时代的时代特殊性对于工具论而言比地域的特殊性更加重要。不仅如此,在回应美国的法典化争议时,霍姆斯站在新世纪的曙光中回望整个19世纪法典化的进程,从而比波塔利斯和基尔希曼更能洞若观火。他意识到各国的立法者并不像历史法学派想象的那样,把民族的共同生活经验变成法律,反而积极地用法律干预社会生活。但这些立法干预终将随着社会自身的变化变成明日黄花。社会必须时刻能通过灵活和高度适应当下局势的法律调整自身。此等任务除了法官以外无人能够负担。在这个意义上,霍姆斯一方面介入美国法典化争议,另一方面针对整个法典化的时代提出了以法官法为社会进步之工具的主张。
现在人们通常不认为美国是一个典型的法典国家,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法律史没有经历过法典化的时代。美国最早的法典化运动可以追溯到19世纪20年代。〔95〕 Cf.Horwitz,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Law,1780-1860,at265. 人们把普通法中的商法规则编纂成了制定法。到了19世纪中叶,纽约的律师菲尔德(David Field)在前往欧洲考察各国法典后开始起草自己的法典,并让纽约州在1848年通过了他起草的《民事诉讼法典》。伊利诺伊州在1867年也加入了这一潮流。虽然菲尔德起草的《民法典》在纽约州没有通过,但这部法典很多内容却保留在了《加利福尼亚州民法典》(1872)之中。与加州同时制定法典的还有北达科他州、南达科他州和蒙大拿州,佐治亚州则比它们晚了9年。菲尔德的《刑法典》也在1881年于纽约州生效。〔96〕 Cf.Horwitz,The Place of Justice Holmes in American Legal Thought,at39-40. 1848年到1881年的法典化比此前的商法编纂更广泛地涉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用立法干预社会、特别是私人领域的企图更加明显,所以也激起了更激烈的反对。其中尤以保守的共和党独立派(Mugwump)卡特(James Carter)的意见最具有代表性。〔97〕 关于卡特反对法典化的代表性研究,Cf.Mathias Reimann,The Historical School against Codification:Savigny,Carter,and the Defeatof the New York Civil Code,The 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 37,no.1(1989):95-119;Horwitz,The Place of Justice Holmes in American Legal Thought,at41-43;Lawrence Friedman,AHistory of American Law(Simon and Schuster,2005),at 302-305;Kunal M.Parker,Common Law,History,and Democracy in America,1790-1900:Legal Thought before Modernis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at238-242. 菲尔德和卡特的论战堪比蒂堡(Anton Thibaut)和萨维尼之间的论战。〔98〕 Cf.Reimann,The Historical School against Codification. 限于篇幅,这里只考虑卡特对私法法典化的反对意见。
出于法律观和价值选择两方面的考虑,卡特和他的同道反对私法领域的法典化。在法律观上,他们认为普通法应该借由习惯自然形成、而非由人创造;在道德观上,他们相信政治权力不应该干预私人领域自发生成的规则。卡特接受了萨维尼关于法律于一个民族的历史中逐渐形成的观念,并称法律为“民族正义标准”(the national standard of justice)的表达。〔99〕 Reimann,at 103. 他又用当时流行的达尔文 斯宾塞式语言,把普通法比作有生命的有机体。特别是私法的规则,起源于遥不可及的古代,在私人的社会交往中不断形成和改变,又通过习惯表现出来,就如不断成长的生命。法官并不创造法律,只是把案件发生时已经存在的习惯适用于个案。一旦用立法干预其自行发展,只会导致私法生命的终结。〔100〕 Cf.Parker,Common Law,History,and Democracy in America,1790-1900,at241-242. 如果接受了这种判断,那么人们自然会得到应该继续让社会中的法律顺其自然地发展的结论。霍维茨对这种思想的总结相当到位:“一方面,人们用习惯来反对后革命时代强调自然权利的个人主义,因为这种思想是对秩序的无政府主义威胁。另一方面,人们用习惯来否认大部分立法和社会强制的合法性与必要性。”〔101〕 Horwitz,The Place of Justice Holmes in American Legal Thought,at45. 菲尔德和卡特关于私法法典化的论战始于1884年,延续至90年代初。这段时间正好是霍姆斯的两部最重要的作品《普通法》(1881)和《法律的道路》(1897)之间的间隙。霍维茨提出,两部作品对法律的理解完全不同:《普通法》主要反映了当时关于法律在生活经验中自我成长的观念,而《法律的道路》反而大力提倡法律作为社会进步的工具。〔102〕 Cf.Horwitz,at48. 因此,不妨说法典化及其争论创造了一种历史语境,让《法律的道路》得以发生。这篇演讲回应了反对私法法典化的声音对法律创造论和以法律干预私人交易的质疑。
霍姆斯也正是在法律的形成和法律的发展方向两个方面回应了卡特对法典编纂的批评。
构建“四驱双核”服务型教工党支部过程中工作载体的选择与创新,事关能否充分调动好教师党员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成为“四驱”的原发力量,从而起到先锋模范带头作用;事关能否逐步打造成服务型教工党支部持续推进“双核”迈向纵深的阵地,从而筑牢党支部的战斗堡垒阵地功能;这就需要实现载体选择与创新的准确把握,将特色教工党支部建设与教师党员业务发展相联系,让教师党员对业务发展的热情、对时政理解与把握转化为服务学生培养上的具体行动,做到思想上同心,目标上同向,工作上同步。
首先,他既没有接受卡特的自发形成论,也没有明确支持法典编纂,而是提出了规则的法官创造论。在这一点上,霍姆斯甚至并没有回到“普通法传统”。《普通法》中的观点更接近卡特的主张——强调规则已经存在、法官只是找出规则并适用规则。〔103〕 不同意见,参见陆宇峰:《“规则怀疑论”究竟怀疑什么?——法律神话揭秘者的秘密》,《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4年第6期,第67-77页。 霍姆斯确实不反对规则在个案出现前已经存在(卡特的观点),他也接受立法者可以创造规则(菲尔德的观点),他所做的是指出法官不仅事实上在创造规则,也应该负担起创造规则的责任。而且法官应该认识到自己可以通过创造规则改变社会(和卡特恰恰相反),坏人视角和预测论解释了背后的原因:人们会因为对法庭作为或不作为的预测而决定自己的行为,所以法官可以通过改变这种预测而改变人们的行为。又因为人们并非因为自己心中的道德观而选择是否遵守法律(非道德性命题),所以就算反对法官之价值立场的人,也会因为趋利避害的本能而选择遵守法官创制的规则。
那么这就引向了霍姆斯对卡特的第二个反对意见:法官要推动社会发展,而且这种发展方向应该是进步主义而非保守主义的。〔104〕 学者普遍认为以反传统、反神权、反个人主义为代表的进步主义出现于1870年以后,但是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不存在一种单一的“进步主义运动”。霍芬坎普(Herbert Hovenkamp)最近提出,应该更精确地称霍姆斯为一个“边际主义者”——即他结合了经济学在1870年提出的边际效用理论和边沁的预防理论。Herbert Hovenkamp,The Mind and Heartof Progressive Legal Thought,Presidential Lecture Series,5 February 1995;EllisWashington,The Progressive Revolution:Liberal Fascism through the Ages,Vol.II:2009Writings(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2013);Herbert Hovenkamp,Progressive Legal Thought,Washington and Lee Law Review 72,no.2(2015),at653-705. 霍姆斯所反对的美国“经典”法律思想在方法上强调法律自成体系,在政治立场上则一方面强调国家对私生活道德领域的(饮酒、性行为)高度规制,另一方面要求国家在交易领域严格尊重契约自由、过错责任、绝对所有权等原则。霍姆斯则不然,他多次为劳工组织、保险、工业事故责任的无过失责任原则甚至社会主义辩护〔105〕 Cf.Holmes,The Path of the Law,999,at1003. ,正显示了他更倾向于国家干预传统上属于私人自治的契约和侵权领域。
霍姆斯关心的社会进步也是19世纪末大西洋两岸的法学家们共同关心的问题。当时的法学家把劳资纠纷、工业事故、贫困人口增加等社会现象统称为“社会问题”。〔106〕 Cf.Maurice Deslandres,Les travaux de Raymond Saleilles sur les questions sociales,in Robert Beudant,Henri Capitant et Edmond Eugene Thaller(dir.),L’œuvre juridique de Raymond Saleilles,Librairie nouvelle de droit et de jurisprudence,Arthur Rousseau,1914,at 241-273;élie Blanc,La question sociale,principes les plus nécessaires et réformes les plus urgentes:conférence aux Facultés catholiques de Lyon;suivie d’une Esquisse d’un programmeélectoral;et de l’Examen de quelques opinionséconomiques,Paris,V.Lecoffre,1891.参见石佳友:《〈法国民法典〉过错责任一般条款的历史演变》,《比较法研究》2014年第6期,第17-30页。 司法和立法上对这些问题的回应催生了“法律社会化”的发展。〔107〕 Cf.Joseph Charmont,La socialisation du droit,Revue demétaphysique et demorale,1903,vol.11,no3,at380-405.参见刘作翔:《权利相对性理论及其争论——以法国若斯兰的“权利滥用”理论为引据》,《清华法学》2013年第6期,第110-121页。 最后,学者对意识到此前法学中对人、国家、团体的假设已经不克应对新的社会状况,由是在反思诞生了强调人之社会属性的“社会法学”,并形成了全球性的现象。〔108〕 同前注 〔61〕,朱明哲文,第75-99页。 尽管新的学术思潮包含了许多不同、甚至彼此冲突的理论主张,但有在两个主张上基本上可以形成共识。第一,19世纪末的法学明确表达了对公理体系和逻辑方法的不满。彼时的法学家批评前辈们为了满足抽象的融贯性,创造了立法无所不包、为所有法律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的假象。〔109〕 Cf.François Gény,Méthode d’interprétation et sources en droit privépositif,op.cit.at63. 真实的情况是成文法处处存在漏洞、错误和留白,19世纪末的司法随时准备着改变法律来适应“社会的需要”。〔110〕 关于19世纪末民法领域的司法造法,参见 Jean-Louis Halpérin,Histoire du droit privéfrançais depuis 1804,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2001,at119. 只不过欧洲(这里主要说的是法国)法学家更关心如何用关于法律渊源的理论革新限制法官的裁判权。〔111〕 1899年底,惹尼的《实证私法的法律渊源与解释方法》和普拉尼奥(Marcel Planiol)的《民法原论》(Traitéélémentaire de droit civil)同时出版,不约而同地首次提出法律渊源问题。这两部巨著确定了法国法学未来一个世纪的法律解释基础:形式渊源(立法与习惯)和参照(判例与学说)的二元体系。François Gény,Méthode d’interprétation et sources en droit privépositif,op.cit.at 138;Marcel Planiol,Traitéélémentaire de droit civil,Librairie Générale de Droit et de Jurisprudence,1899,at9. 相反,霍姆斯则明确承认法官创造法律的权力。第二,19世纪末的法学明确表达了引领社会发展的心愿。除了德国的门格尔(Anton Menger)和法国的莱维(Emmanuel Lévy)以外,大部分的欧洲法学家关心社会问题,但既不准备接受社会主义,也不准备让位于社会科学家。〔112〕 Cf.Frédéric Audren,Le“moment 1900” dans l’histoire de la science juridique française.Essai d’interprétation,in Olivier Jouanjan etélisabeth Zoller(dir.),Le moment 1900 :Critique sociale et critique sociologique du droit en Europe et auxétats-Unis,Paris,Panthéon Assas,2015,at 55-74. 他们更愿意找到一个高于法律的原则,用以引导社会发展,避免使之变得混乱无序,也避免以社会之名干预个人自由。〔113〕 Cf.Julien Bonnecase,La notion de droiten France au XIXe siècle:contributionàl’étude de la philosophie du droit contemporain,Revue générale du droit,de la législation et de la jurisprudence en France etàl’étranger,1915,vol.39,at496-506.并参见朱明哲:《服务于法史学的自然法——论19世纪末法史学在法国的形成》,《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7年第3期,第116-131页。 霍姆斯在这个问题上倒是与他的欧洲同行有相近之处,他所主张的也只是法官应用统计学和经济学,却从来没有想过把法官的职位让给仅仅懂得统计学和经济学而不懂法律规则的人。由是可见,19世纪的美国法学并非一种孤立发展的法学。〔114〕 近年逐渐有更多的学者关注跨大西洋的学术对话。拉班(David Rabban)成功地说明美国19世纪法学脱胎于对德国和英国历史法学的继受。Cf.David M Rabban,American Responses to German Legal Scholarship:From the CivilWar to World War I,Comparative Legal History 1,no.1(May 2013),at 13-43;David M.Rabban,Law’s History:American Legal Thought and the Transatlantic Turn to Histor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4),at215-220.其实19世纪、特别是19世纪末的美国法学不仅在方法上,还在更多实质议题和立场上受法国和德国影响。对美国的了解反过来也促成了欧陆法学的反思。
社会问题在19世纪成为一个重要的法学问题,不仅在时间上和法典化的时代耦合,更与法典化时代所产生的法学关系密切。法律来源于人有意识的创造,而人的能力是有限的,所以再全面的法典文本也无法囊括所有未来可能发生的情势。波塔利斯早在1801年就已经把这一点阐述得很明白了。否则也不会产生19世纪早期的法典如何适应19世纪晚期的社会生活的问题了。面对法典文本与社会进步之间的不和谐,法学家不但要研究现有法典的缺陷,而且要研究未来应该成为现实的法律。如果按照大革命后崇尚立法的共和主义观念,法律的进步仍然必须通过立法来实现。基尔希曼通过把立法相对化,提出了一种让法律保持发展的可能性。进而,19世纪末法学家的贡献在于成功从波塔利斯的演讲中找到了法典化并不意味着共和主义立法至上观念的证据,从而让体现了时代发展的“法律”在普遍的法典并不存在(美国和德国)或没有一部取代旧法典的新法典(法国)的情况下,仍然可以成为解决法律问题的依据。终于,到了“法典化时代”的尾声,霍姆斯提出了法典本身不能阻却法律继续在法官手上发展的观点。最后,这样由法学家创造出来的“法律”不但可以适应发展,还能成为法学家的工具,推动、指引社会发展。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法律的道路》回答的是整个法典化时代的普遍问题,表达的也是法典化时代发展到晚期时各国法学家的共同声音。
(三)小结
法典化的一个潜台词是用一部包括了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法典去预见所有争议的分配结果。霍姆斯指出这种野心必将失败。无论是否有法典,法官都必须在了解规则之缺陷的情况下,创造新的规则,并以此为工具,实现他所选择的社会目标。这一演讲应该放在美国法典化争论和19世纪末整个法学界关于法典与社会发展之关系的背景中理解。霍姆斯回答了由人创造并且必然有缺陷和局限的立法如何适应新社会形势的问题:法官也加入“应然之法”的发现和创造。在这个意义上,他结合了上文研究的波塔利斯和基尔希曼两人的观点。但他更进一步,提出既然人们能够通过法律创造把应然之法实证化,那么何妨用新的法律推动社会发展?霍姆斯固然不是工具论的首倡者,但工具论在他的演讲中得到了清晰和令人信服的说明。19世纪的法律观随着工具论的出现终告完成。19世纪末以来的法典传播与继受、起草与编纂、修改与重述,几乎都是以法律的创造论、进化论和工具论为不言而喻之前提的。只要回顾我国1912年到1930年立法史,回顾当时通过用先进立法改造传统社会的论调,想必不难明白这一点。
五、结 论
英雄史观的法史学极力让我们相信伟大学者总是超越其时代、创造新的思想:“新思想的产生及合理性法律体系的创造是一个非常小的精英群体的成就。我们于斯只考虑学派的领袖。其他人只不过像巴汝奇之羊一样浑浑噩噩地跟随他们而已,君固如此,吾亦难免。”〔115〕 Michel Villey,Leçonsd’histoire de la philosophie du droit,Paris,Dalloz,1957,at19.“巴汝奇之羊”典出拉伯雷的《第四书》第三章,比喻不假思索地从众者。 其实他们可能只是更明确、更完整地表达了所处时代的发展趋势。波塔利斯并未凭一己之力奠定《法国民法典》的哲学,就算他有什么新奇大胆的想法,也必须包裹在听众熟悉的话语之中,否则无法为起草委员会赢得支持。基尔希曼背后是19世纪中叶思想发展对历史法学的质疑。同样,霍姆斯并未“发明”法律工具主义,而是总结了法典化时代行将结束时许多作者已经充分意识到的观点。这些见解产生于对法典的讨论,既因此把对社会的观察融入了关于法典的观念中,又反过来令法典得以回应特定时代的关切。
在整个19世纪,法典一直是法学发展中最重要的议题。虽然本文较少探讨法典化与更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但它无疑采取了一种“外史”的立场,认为法学家同时观察法律与社会,并根据其观察的结果随时调整其关于法律的论述。法学由是可能。关于法典的讨论也是如此,它始终既指向法律实践的问题,又回应社会中的新议题。在19世纪初,各国试图用法典消除此前多种法律渊源并存的现象时,核心问题在于编纂过程中如何处理立法和其他法律渊源的关系。在伴随民族国家出现的新主权观念影响下,法律的创造论深入人心。人们把习惯保留在法典之中、并允许判例具体化法典规定,但同时也确立了立法不可动摇的核心地位。到了19世纪中叶,产业发展和进化的时间观让人们普遍意识到社会的变化性,所以法学也要解决如何让已经制定好的法典适应不断变化发展的社会这一问题。强调需要研究“未来之法”的法律进化论应运而生。到了19世纪末,新产业和新的社会现象挑战各法典和当时的主流法学所体现的价值观,法律的社会化既成了需要重视的现象,又成了需要应对的挑战。改造法律、并以法律为工具改造社会的想法随之产生。
在我国编纂《民法典》的时刻,法律的创造论、进化论和工具论都已经呈现在我们眼前了,当然不必等待法典编纂完成才出现。理论界和实务界需要考虑的是如何在上一个法典化时代的遗产上更进一步,编纂一部适应“解法典化时代”的《民法典》,同时避免法典的编纂成为民法学发展的障碍。在此意义上,真正重要的还不是三种相继出现的法律观的内容,而是法学家对它们的阐释。国家创造法律,但阐明规范内容的不仅仅是国家。国家完全可以通过把私人交易活动中诞生的规范吸收到法律中保持其活力和适应性。〔116〕 Cf.Ralf Michaels and Nils Jansen,Private Law beyond the State? Europeanization,Globalization,Privatization,The 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 54,no.4(2006),at843-890. 同时,就算法典的文本清晰明确,法学和司法仍然会不断创造新的规范。法律的创造、发展和用途,最终是各种不同职业共同作用的结果。
考察法律观形成的过程也对法理学的研究有所启发。首先,一种法律观的形成、发展、普遍化并非理论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对实践问题的回应。换言之,如果我们在研究一种对法律的观念或者概念时有意将其从当时、当地的具体语境与实践中抽离,对它的理解一定是不全面的。其次,法理学研究应当适当关注法律实践中产生的问题以及法学家们在解决这些问题时所提出的法律观。如果说19世纪法律实践的中心是民族国家的法典化,那么21世纪初法律实践的重心之一就是把民族国家置于次要地位的全球化。面对伴随全球化产生的法律域外效力、规范产生分散化和法律的进一步碎片化等现象,法理学有必要反思我们现在对法律的理解。最后,如果本文对法学史提出了一种可信的解释,那么许多看上去大相径庭的法律思想实际上是彼此相连的。法律的创造论是法律的进化论和工具论所以产生的前提,法律工具论又是进化论在特定时代中的自然发展。法律思想的发展很少出现与此前主流观点彻底决裂的创新,更常见的是对此前观念的发展和添附。
* 中国政法大学比较法学研究院副教授,巴黎政治大学法学博士。
本文是作者所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法法律交流档案研究(1877-1958)”(17CFX00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并受中国政法大学第五批青年教师学术创新团队(18CXTD10)资助。
标签:法典化论文; 法律创造论论文; 法律进化论论文; 法律工具论论文; 中国政法大学比较法学研究院论文; 巴黎政治大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