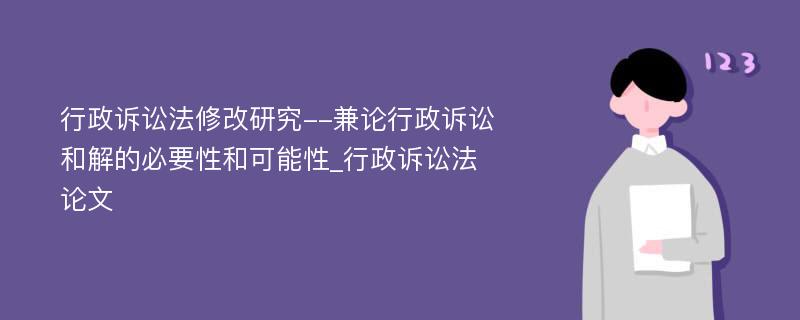
《行政诉讼法》修改问题研究——行政诉讼中和解之必要性与可能性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行政诉讼法论文,行政诉讼论文,必要性论文,可能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行政诉讼法中“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但实践中却存在当事人之间的“和解”。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是否存在讨价还价的余地,在《行政诉讼法》立法之时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体的问题,争论的结果以“不调解”的立法规定而告一段落。事隔十余年,在修改《行政诉讼法》之时这一问题再次浮出水面。笔者结合我国实际对行政诉讼中的和解作一粗浅的分析,以期为立法提供参考。在展开讨论之前,有必要对和解与调解作一比较。通常认为和解是当事人之间的诉讼活动,调解是在人民法院审判人员的主持下进行的诉讼活动,和解与调解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笔者认为,诉讼和解既可能是在法院调解下达成的,在这一过程中当事人处于被动和解的地位,也可能是双方当事人自主达成的,在这一过程中法院处于被动调解的地位。无论是主动和解还是被动和解,结果都是双方当事人的合意,“诉讼上和解是立足于当事人说明以合意解决争讼,而法院调解则是以法院为基点解释以合意解决争讼。这两种制度功能上的统一性,是诉讼上和解可以替代法院调解的基础”[1]。只要当事人的同意或合意对于终结纠纷仍然必不可少,调解者的正当性或多或少地,而且归根结底还因广义上的诉讼和解[2]即包括法院为主进行的和解,本文正是在此意义上使用和解的概念。
一、“事实上的和解”及存在的问题
行政诉讼中,除法定的撤诉原因外,还存在一种隐性的撤诉理由,即被告行政机关一方主动找原告协商希望其撤诉,或者对于一些“敏感案件、有较大社会影响的案件”,为避免行政机关败诉而“影响社会稳定”和“法院与行政机关的关系”,法院主动找行政机关“交换意见”,建议行政机关改变原行政行为,以促成原告申请撤诉。为了规避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的规定,这种做法在法院内部通常称之为“协调处理”,实质则是“没有调解书的调解”[3]。由于行政诉讼中不允许和解,大量的案件通过撤诉的方式结案,撤诉的背后是当事人的和解。这种事实上的和解因缺乏法律的规范,可能出现下述问题:
第一,不应和解的案件却和解。事实上的和解无非两种可能:一是争议案件本身不适宜和解,但被告方为了避免“败诉”,采取各种手段强迫、变相强迫、利诱或动员原告撤诉,原告与被告在私下达成某种交易;二是双方当事人都享有处分权,案件本身适宜和解,而且和解也确实出于双方当事人的自愿,并且不违背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和解在行政诉讼中的适用范围有一定的限制,并非所有的行政争议都可以和解。由于事实上的和解以撤诉的形式出现,而法院对撤诉申请几乎不审查,当事人对诉讼的规避和法院监督的缺位导致大量不应和解的案件却变相的和解,其后果或者以牺牲公共利益为代价,或者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
第二,被告为了达到不“败诉”的目的,无原则牺牲公共利益。行政机关的“败诉率”直接影响其声誉和领导的晋升、工作人员的工资、奖金等方面的待遇,所以行政机关从上到下对当被告甚至可能败诉的结局非常敏感。如果有相对人起诉,有些行政机关如临大敌,一方面找法院疏通关系,另一方面找原告动员其撤诉,只要达到让原告撤诉的目的,什么条件都可以接受。这种做法是以牺牲公共利益为代价的,用公共利益换取自己不败诉的后果。
第三,被告强迫或变相强迫原告接受和解。目前我国行政诉讼案件中原告申请撤诉比重较大,其中相当一部分出于“强制的自愿”。行政机关在实体上处于优势地位,很容易利用其强势地位要求原告接受和解“条件”,而原告为了避免“赢一场官司,输一辈子”的尴尬,只要对被告提出的条件有“50%的满意度”就会接受和解,甚至有些情况下,原告根本没有选择权,只能接受被告提出的“和解条件”。如果原告不同意“和解”,被告方会采取各种手段一方面对原告施加压力,另一方面对法院施加压力,法院只能采取“拖”的办法,“和解”最终变成了原告无可奈何的选择。
第四,法院丧失了独立公正审判的地位和监督行政的功能。行政诉讼中,人民法院既是权利救济机关,又负有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职责,其表现之一就是“人民法院对行政案件宣告判决或者裁定前,原告申请撤诉的,或者被告改变其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原告同意并申请撤诉的,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裁定。”[4]实践中,法院往往片面追求结案率,只要原告撤诉,案卷就可以束之高阁,法院“没必要自找麻烦”。因此“法院对撤诉申请几乎一律‘绿灯放行’,面对几十万起撤诉申请,极少有不准许的。不许调解的规定被悄然规避,名存实亡”[5]。根据中国法律年鉴的数据,从1989年到2001年,撤诉作为一种结案方式,每年行政诉讼撤诉案件占所有已结案件的比率达30%以上,有些年度的撤诉率高达54%[6]。
第五,原告的司法保护被虚置。事实上的和解以撤诉的形式出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六条的规定“人民法院裁定准许原告撤诉后,原告以同一事实和理由重新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事实上的和解游离于现行法的规定之外,当事人达成的和解协议并不具有法律效力,原告撤诉后,行政机关完全可以对协议内容置之不理,此种情况下,相对人既无权对抗行政机关,又不能请求司法救济,司法保护的大门对相对人来说等于虚置。
由于上述诸多问题的存在,因此很多学者提出与其放任事实上的和解,不如承认和解的存在,将其纳入立法的规范和法院的监督之下。
二、行政诉讼中和解的可能性
行政诉讼中能否和解,其实质在于原告和被告是否可以处分自己的权利。“行政机关对诉讼标的的处分权,分为形式与实质两方面。形式上之处分权,指得以缔结契约之方式,以行使其公权力之权限;凡依公法关系之性质或法规规定,不得缔结公法契约者,于该公法关系涉讼时,行政机关于诉讼上即欠缺对相关诉讼标的之形式上之处分权。实质上之处分权,是指行政机关对相关诉讼标的之事物管辖权及地域管辖权。”[7]就形式上的处分权而言,诉讼和解具有公法契约和诉讼行为的双重性质,行政主体缔结公法契约,不需要法律的明确规定,除非“法律、法规禁止签订行政合同或者因拟建立的行政法律关系的性质不适宜订立行政合同。”[8]就实体上的处分权而言,法律往往赋予行政机关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在自由裁量权范围内,行政机关可以选择,包括是否选择作出行政行为以及在法定范围内选择作出何种行为,只要行政主体的选择不存在瑕疵,法院会尊重行政机关的选择和判断。“在裁量余地内行政机关选择一个原告可接受的幅度,这也并非是对国家利益的‘出卖’,否则,自由裁量权的赋予本身就有允许行政机关‘倒卖’国家利益之嫌”[9]。
行政机关在自由裁量权范围内的选择,并非只有惟一正确的答案,即“非黑即白”(all or nothing),不同的裁量选择是可以互相替代的。“传统学说有关不得和解的主张之所以能够成立,是以‘其应履行的义务’明确、合法、合理为前提的。或者说,行政行为的不可处分性的成立前提是羁束性。只要法律、法规赋予行政主体一定幅度或范围的行政裁量权,那么,这里的所谓其应履行的义务就有变动的可能性,就应该是可以‘和解’的。只不过这里的和解要受到更加严格的限制而已。”[10]从相对人方面来看,其在行政法律关系中并非只是义务主体,相对人享有的权利也并非只是程序性权利,大量新型的行政手段已越来越重视相对人的主体地位和权利保护,很多情况下相对人已能与行政主体平等对话。具体来说,双方当事人可以处分自己实体权利的行政争议包括:当事人享有处分权并具有民事争议特点的行政争议,即有关非法律强行性规定的行政合同纠纷和损害赔偿裁决纠纷;行政机关享有裁量权的授益行政行为产生的行政争议;行政机关享有裁量余地的侵益行为争议;事实问题不明确的侵益行为争议。
域外已有行政诉讼和解的立法先例。德国《行政法院法》第106条规定“只要参与人对和解的标的有处分权,为完全或部分终结诉讼,参与人可在法院作出笔录,或在指定或委派的法官面前作出笔录以达成和解。法庭和解也可以通过以法院、主审法官或编制报告法官建议作出的裁定形式,以书面方式在法院达成”。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二百二十七条详细地规定了行政诉讼中的和解。行政诉讼中的和解在日本虽无明文规定,但权威学说认为“实体法上承认行政厅有自由裁量权时,在其范围内可以允许和解”,“不仅对关系人处于相互对等关系的当事人诉讼,而且对从位秩序所支配的撤销诉讼及赋义务诉讼,学说一致承认具有和解的可能性。以和解方式不能潜在地予以解决的诉讼程序是不存在的”[11]。下级法院判决也有承认和解的判例,尤其是在税务争议案件中,趋向于运用和解劝告的方式解决争议。不过在日本由于没有法律的明文规定,“实务上实际实施的和解,其具体内容不是制作正式的和解调查书,而是由法院进入其间,行政厅方面依职权撤销处分,原告撤诉,以终结诉讼。也许应该称之为实务上的智慧”[12]。美国国会于1990年通过了《行政争议解决法》(Administr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Act,ADRA),将ADR引入行政程序。该法的目的是“授权和鼓励联邦行政机关适用调解、协商、仲裁或其他非正式程序,对行政争议进行迅速的处理”。行政过程中的ADR作为纠纷解决的技术,不仅可能适用于行政程序中,也可能适用于对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的司法程序之中。
三、立法的两难选择
实践的混乱、理论上的阐释和域外的经验都告诉我们,修改《行政诉讼法》时规定和解制度是一种可行的选择。问题在于中国行政诉讼制度的建立与西方国家有不同的土壤。行政诉讼和解制度的构建以健全、完善的行政法治背景为依托,并需要相关制度的支持。中国长期以来缺乏法治的环境,如果在行政诉讼中规定和解制度是否能真正达到有效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目的呢?下述问题是修改《行政诉讼法》时不能回避的:
第一,中国行政诉讼是否需要和解的效率功能?
和解是诉讼经济原则的产物,有利于迅速地解决纠纷,减少当事人双方的对抗情绪和案件的实际履行。“‘瘦的和解胜过胖的诉讼’这一西方著名的法谚生动形象地说明了诉讼上的和解对于解决争议所起的作用以及在争议解决体系中的地位。”[13]在德国行政诉讼中,有关减轻法院负担的改革争论,诉讼和解历来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就美国的议论来看,面对审判花钱费时和一刀两断的判决方式未必能真正地解决纠纷的问题,人们期望调解作为对付这两个功能局限的有效手段,充分发挥其简易迅速和根据纠纷的实际情况灵活多样地加以解决的作用。”[14]和解的效率功能是否是中国特色的行政诉讼制度所需要的呢?中国行政诉讼仍处于不饱和的状态,没有大量案件积压的状况,法院不需要减轻负担。实践中确实有很多行政诉讼案件超期审判,久拖不决,但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往往是法外因素。和解制度所具有的效率功能并不能解决中国目前行政审判实践中的低效率问题。
第二,和解是否会导致被告利用其在实体上的优势地位强迫原告接受和解条件?
由于现行立法不允许调解,因此事实上的和解虽然存在,却是“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状态。一旦和解制度登堂人室,是否会变成被告的“救命稻草”。无论什么样的案件,被告一律主张和解,而被告实体上的优势地位对原告造成的潜在威胁,使原告不得不接受和解。“在审判外的交涉中本来就无力实现自己权利的人们,即使到了调解的场合再次提出自己的主张,只要对方有拒绝的权利也就不得不再次碰壁,或者反而被迫接受不明不白的妥协。”[15]中国目前的现状是行政权独大,法院无法与行政机关抗衡。如果我们的担心成为现实的话,和解制度不但不会发挥应有的作用,反而会造成对原告更加不利的局面。如果制度的设计不能达到救济权利与监督行政的目的,还不如维持现状。
上述问题的解决取决于立法者对《行政诉讼法》目的的定位。毋庸置疑,《行政诉讼法》实施十余年在促进依法行政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于“违反法定程序”的行政行为人民法院一律撤销,这一规定催生了大量的行政程序立法,在促进行政程序法治方面功不可没。如果立法者将《行政诉讼法》定位于解决行政纠纷,实施权利救济,那么和解制度是解决纠纷的一种较好的方式;如果立法者同时赋予《行政诉讼法》以监督行政的目的,那么立法是否规定和解制度应慎重考虑。笔者认为,在中国目前的法治大环境下,行政诉讼作为解决行政争议的一种主要手段,还肩负着监督行政的特殊使命,因此行政诉讼和解入法应缓行,待法治环境相对成熟时再规定和解也不迟。
标签:行政诉讼法论文; 法院调解论文; 法律论文; 立法原则论文; 司法调解论文; 行政立法论文; 行政诉讼被告论文; 法制论文; 法院论文; 行政诉讼法执行解释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