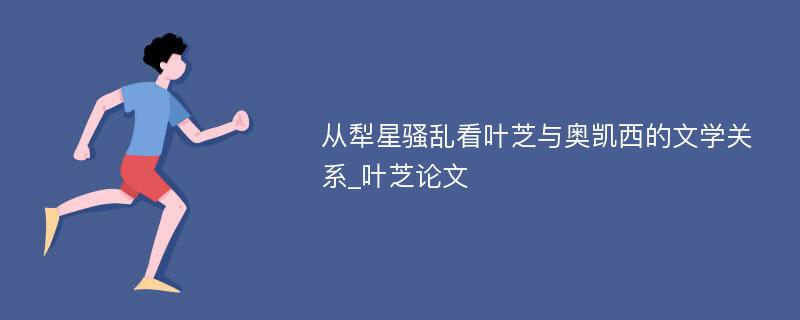
从《犁与星》演出骚乱看叶芝与奥凯西的文学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叶芝论文,骚乱论文,演出论文,凯西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爱尔兰戏剧运动中,W.B.叶芝显然是一个灵魂人物。作为爱尔兰文学戏剧协会的组织者和阿贝剧院的领导者,叶芝的戏剧创作与戏剧活动对于爱尔兰民族来说其实是一种拓荒工作,而不是“复兴”。在学术界,人们用“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一词来称呼与爱尔兰民族独立运动同步进行的文学创作。但是严格地讲,单单就戏剧这一文学类别而言,是不能用“复兴”一词的。爱尔兰文学中并没有源远流长的戏剧传统,正如田汉先生所说:“过去的爱尔兰文学中仅有叙事诗而无剧诗”。①叶芝此前的爱尔兰戏剧家,从17世纪的乔治·法夸尔到18世纪的哥尔德斯密和谢立丹,再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萧伯纳和王尔德,他们的剧作题材基本上不涉及爱尔兰本土,也不带有鲜明的爱尔兰民族风格。他们的出生地为爱尔兰,文学事业的发展却在英国。因此,叶芝担任阿贝剧院经理之后,急需做的一件事就是“拓荒”:建立戏剧协会、组建民族剧院、培植本土戏剧家、探索民族戏剧发展之路等等。一方面,他身体力行,创作了以爱尔兰神话为题材的近30部剧本;另一方面,他用心挖掘和扶持爱尔兰本土作家。西恩·奥凯西就是受过叶芝提携与帮助的剧作家之一。
1926年,奥凯西的剧本《犁与星》在阿贝剧院上演。这是奥凯西都柏林三部曲的第三部,也是奥凯西的剧本第三次在阿贝剧院上演。他的前两部剧作《枪手的影子》和《朱诺与孔雀》分别于1923年和1924年被搬上阿贝剧院的舞台。与前两部剧作的座无虚席和一再顺延演出的盛况相比,《犁与星》十分不走运。戏演到第二幕时发生了骚乱,观众席中一片嘘声、口哨声,不少人唱起了爱国歌曲。第三幕时,骚乱达到顶点,观众一边咒骂,一边朝舞台上扔破鞋、烂菜叶和椅子,并在剧场内点燃瓦斯弹。一些观众甚至冲上舞台与演员打起来,致使演员无法表演下去,只好叫警察前来维持秩序。
这时,身任阿贝剧院总经理的叶芝走上舞台,大声说了以下著名的一段话:
你们再一次丢了自己的脸!爱尔兰出现天才的时候,是不是永远得这样地庆祝?第一次是对沁孤②,这次是对奥凯西。方才你们那几分钟的做法,马上会报道到世界各国。但是,都柏林再一次养育了一位天才。沁孤的声誉就是在这个剧院的这样一个场合下奠定的;同样,奥凯西也要在今晚,在这里名满天下。你们这样做实在是对他的礼赞。③
虽然此时的叶芝已经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爱尔兰文学艺术界的领袖人物,但他的话在当时并没有起多大作用。事后报纸上对奥凯西这部作品依然大肆攻击,奥凯西被称为“从贫民窟里钻出来的二流子”,他的这部剧作被攻击为“阴沟派戏剧”、“为下流而下流的戏剧”、“胡编乱造的廉价杂耍儿”。这就是爱尔兰文学史上有名的《犁与星》骚动事件。
不管怎样,叶芝在公开场合表明了自己对这部剧作的支持态度,并盛赞奥凯西是继辛格之后的天才作家。这使刚刚成名不久的奥凯西备受鼓舞,此后,奥凯西与叶芝、格雷戈里夫人过往密切,积极参加了重振阿贝剧院的许多活动。
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叶芝在上面这段话里传送了这样一个信息,他把奥凯西比作辛格,把此次骚乱事件与当年辛格的《西方世界的花花公子》的观剧骚乱联系起来。在奥凯西刚刚步上文坛时,叶芝确实以为奥凯西在走辛格的未竟之路,但实际上奥凯西完全不同于辛格,也完全背离了叶芝所期望的民族戏剧发展方向。等到叶芝意识到这一点以后,两人的关系随之发生了质的变化。
起初,奥凯西的作品并不被阿贝剧院所接纳。这位工人出身、思想激进的左派作家在《枪手的影子》被采纳之前曾有四部剧作被叶芝为首的阿贝剧院管理班子拒之门外。笔者不知道被拒绝的原因,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奥凯西的创作思路与阿贝剧院的宗旨不太合拍。即便是《枪手的影子》被采纳也不是一锤定音,而是颇费考虑。在《枪手的影子》之前,阿贝剧院上演的基本上是叶芝、格雷戈里夫人和辛格的剧作。叶芝热衷于爱尔兰古老的神话传说,戏剧多发幽古之情。辛格将笔触投向边远的爱尔兰农村,表现爱尔兰民间世俗生活的艰辛、愚昧和荒诞。格雷戈里夫人的独幕剧往往反映淳朴的民风,且具有喜剧风格。虽然叶芝的英雄神话剧借古喻今,辛格笔下边远山村的故事与都柏林当下的政治斗争也不是毫无关联,但是处于斗争年代的人们根本无心去欣赏与现实隔着一层的戏剧。而更重要的是叶芝戏剧中失败的库丘林神话形象与辛格戏剧中丑角般的反英雄人物都让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很不高兴。
因此辛格死后,叶芝孤独地沉醉于对戏剧艺术形式的探索,致使阿贝剧院经营萧条,陷入危机。因此,《枪手的影子》这样一种英雄主义题材剧目的引进,成了挽救剧院的“稻草”。事实证明,奥凯西的剧确实挽救了阿贝剧院,连叶芝本人也承认这一点。他在致奥凯西的一封信中说:“……我始终不会忘记,阿贝剧院近几年所以得以复兴,实在完全有赖于你。如果不是你恰当其时接连给我们送来你的新剧作,我怀疑现在阿贝剧院是否还会存在。”④
从艺术角度讲,两幕剧《枪手的影子》的成功之处在于戏剧人物形象的反差对照。这部作品以1920年爱尔兰游击战为背景,诗人达沃林夸夸其谈,怯弱而无能,却被邻居姑娘米妮误认为是共和军枪手而受到尊敬与崇拜。米妮是一位普通女子,话语不多却充满了英雄气概,因隐藏炸弹而牺牲。首先在容貌描写上,奥凯西就有意强调这一反差,自认为是思想先锋的胆小鬼诗人达沃林“面部表情似乎表明在虚弱与强力之间进行着一场持久的斗争”,“在他的眼睛里人们看到的却是一种不可遏制的向往休息的神情。”相反,姑娘米妮却颇有男子气概:“她已经失掉了恐惧感,不论在任何地方,在任何人——即使是受过较高教育的人们——面前,她都泰然自若,无拘无束。”显然,这样一对反差鲜明的人物出现在舞台上,再加上奥凯西熟悉都柏林贫民窟生活,运用都柏林下层人民的方言作为台词,并熟练地运用情节剧的写作技巧,演出效果甚佳。
但是另一方面,这出戏获得大众好评的更重要的原因是政治。事实上,一种革命的、政治的浪漫主义激情始终弥漫在该剧的字里行间。奥凯西的戏剧本来就是他政治斗争的工具,在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的现实中,米妮这种柔弱女子真英雄的形象是很有鼓动性的。激进的民族主义者欢迎这部作品,昂扬的战斗精神无疑迎合了他们对英雄与英雄主义的需要。下层的劳工欢迎这部作品,粗俗而率真的对话来自于他们熟悉的生活,情节剧中常见的紧张的戏剧冲突又合乎大众的口味。而这两部分人恰恰构成了都柏林观众的大多数。
奥凯西都柏林三部曲的第二部作品《朱诺与孔雀》由于继续了这一女英雄形象,也就继续受到了都柏林观众的欢迎,出现了阿贝剧院成立十年以来少见的“客满”场面。这部剧作以爱尔兰自由邦内战为背景,剧名本身具有象征意义。朱诺是罗马神话中的天后,她用孔雀驾车。在剧中,被称为朱诺的波伊尔太太果敢沉着,在危难面前镇静务实,是一大家子的顶梁柱。这一人物有点像布莱希特笔下的大胆妈妈。相形之下,波伊尔先生却像一只孔雀,只会到处展示自己漂亮的羽毛,整日无所事事,还十分霸道。他说:“我要发出一个宣言,成立一个独立的共和国,我得让朱诺立下忠顺的誓言。”奥凯西甚至故意把他的形象小丑化,“灰色的头发,身体很壮,但很矮。他的脖子很短,脑袋很像我们常常在门柱顶上看到的那种石头圆球。”波伊尔先生,这位以前曾经被称为“船长”的英雄般人物,如今却连养家糊口的能力也没有。就像被伊尔太太说他:“所有的人都叫你‘船长’,可你不过就走过那么一趟水路,从这儿坐着一条破煤船到利物浦去过一趟,可谁要瞅着你那言语行动的神情儿,真会以为你是第二个克里斯多佛·哥伦布呢!”男女人物形象的对照反差继续在这部作品中存在。
需要指出的是,这两部剧作中其实存在一个奥凯西思想的“拐点”,那就是《朱诺与孔雀》中的波伊尔太太与《枪手的影子》中米妮的不同。
两相比较,波伊尔太太更有人情味,在她身上人道主义似乎高于民族主义与英雄主义。米妮是积极投入战斗的战士,具有英雄崇拜的热情。波伊尔太太却是反战的。尽管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她与米妮一样勇敢而镇静,但当她的儿子被自由邦处死之后,她发出悲天悯地的祷告:
上帝的母亲,上帝的母亲,请怜悯怜悯我们这些人吧!圣母玛利亚,当我亲爱的儿子被枪弹打得满身窟窿的时候,你是在哪儿呀,当我亲爱的儿子被枪弹打得满身窟窿的时候,你在哪儿呀?长着神圣的心的耶稣啊,请拿走我们的石头心肠,给我们换上一颗血肉的心吧!请消除掉这种互相残杀的仇恨,让我们也具有你的那种永恒的爱吧!(《朱诺与孔雀》第三幕)
波伊尔太太的这段话只是奥凯西思想转变的“端倪初露”。这种对战争的控诉在奥凯西的下一部作品《犁与星》中得到进一步表现。虽然在《犁与星》中奥凯西继续使用人物对照手法,但男女主人公来了一个彻底的颠倒。以往的女英雄成了温良胆怯的妇人,而以往卑琐的男主角却成了舍生取义的壮士。《犁与星》剧作以1916年起义为背景,犁与星是爱尔兰市民军军旗图案。丈夫杰克要参加市民军战斗,妻子娜拉千方百计加以阻挠。杰克终于因参加了战斗而阵亡,留下娜拉一人以泪洗面,精神错乱。很显然,娜拉完全不同于米妮和波伊尔太太。她喜欢优雅的家居生活,讨厌战争,反对丈夫离家参加战斗:
难道你心上只有康诺礼将军和市民军?难道你的家只是你回来睡觉休息的地方?难道我只是供你夜晚玩弄的消遣?(《犁与星》第一幕)
奥凯西笔下的娜拉反对战争,崇尚美好人性与温馨生活。拒绝暴力与反对战斗的主题昭然若揭。子弹误伤了无辜的群众,士兵们占领了贫民的住宅,这些情节都直接指向战斗的悲剧性。
奥凯西的剧作向来是奥凯西政治观点的传声筒。很显然,正是《犁与星》不同于前两部作品的反战主题导致了观剧骚乱。这个反战主题其实在《朱诺与孔雀》中已有了苗头。值得注意的是,虽说奥凯西的三部曲都是以战斗为背景,但只有《犁与星》完全针对1916年复活节起义。剧本中人民对起义的不理解,起义对无辜群众带来的伤痛,这些情节直接惹恼了爱尔兰民族主义者。他们认为此剧有辱于他们“光荣的流血战斗”。在一个硝烟浓烈和英雄崇拜的年代,这部反战的剧作明显发出了不和谐音。
那么,当时的叶芝为什么会支持这样一部剧作,并认为奥凯西是继辛格之后的又一位戏剧天才呢?当然,叶芝对骚乱的制止首先出于维持剧场秩序和安全的考虑,为此,国内有文章认为:叶芝是精通商道的剧场管理人,是为了阿贝剧院的生存而采用奥凯西的剧本。奥凯西的戏剧并不是叶芝心中的理想戏剧模式,叶芝“懂得市场经济和管理学精髓”,他只是工于用人之道,图的是剧院长远的发展,是“为阿贝剧院树立品牌和赚钱机器”⑤;但笔者认为,叶芝虽生在爱尔兰,具有强烈的爱尔兰民族情感和对故土的热爱之情,但他为人处世的方式却有着伦敦西区老派绅士的温文尔雅。所以不管这种骚乱的原因正确与否,叶芝对观众的粗野行为首先是出于本能的反感,并认为这是对戏剧艺术的亵渎。如果奥凯西的剧作没有得到叶芝的认可,以叶芝的为人,他不会为了“利”而放弃文明社会的一般规则。毕竟叶芝首先是一位作家,其次才是一位剧场经理。从“经营”的角度来解释叶芝的行为显然有些牵强。再说对于“剧场经理”这份工作,叶芝本来就勉为其难,有诗为证:
我诅咒
那些必须以五十种方式排演的戏剧,
诅咒整天与每个无赖和白痴进行的争吵,
剧院的事务,人员的辖管。
我发誓在黎明再次转回之前
我将找到那马厩,把门闩拉掉。
——叶芝《对困难的事情的强烈爱好》
面对这样一位讲求体面文雅、追求艺术至善至美的作家,认为他支持奥凯西是出于政治的考虑也是说不通的。虽然叶芝生活在一个民族战争与政治变革的年代,但他的作品常常流露出他在民族运动与艺术追求上的矛盾。叶芝本是具有浪漫气质的诗人,他对民族政治运动的兴趣一方面来自于他身为爱尔兰人的故园乡情,另一方面来自于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约翰·奥利里对他的影响,当然更重要的或许是来自于他对激进主义者毛德·冈的爱情。也就是说,叶芝的政治兴趣主要是来自于外在的因素,而不是他本人的初衷。关于政治,叶芝在《有人求作战争诗有感》一诗中曾这样明确表态:
我想在这样的时代里最好
让诗人缄默,因为事实上
我们没有天赋以纠正政客。
他在写给毛德·冈的信中说:“我哪个政党也不喜欢,我喜欢自由。”⑥并且在得不到冈的爱情后,“渐渐恨起她的政治活动——我唯一可见的情敌。”⑦1910年5月,他在日记中否定了文学为政治服务的说法:
一切出于有意识的政治目的而造就的文学,久而久之通过造就一种不假思索的服从习惯和对自发冲动的不信任习惯而造就软弱。它借解放之名造就一国的奴隶。⑧
在得知自己获得诺贝尔奖之后,叶芝对记者说,他这一代人在爱尔兰所做的工作是“一种文学的创造,以表现国民性格和感情,但不带有刻意的政治目的。”⑨因此叶芝对奥凯西的支持主要来自于他们在思想与艺术观念上的共识,尽管两人是完全不同类型的作家,但正是有了以下三点共识,才促成了他们在非常时期的友好关系。
共识一,对暴力运动的看法。叶芝和奥凯西都反对激进的、流血的民族主义行为。叶芝在著名诗歌《一九一六年复活节》中,有意细致地描绘烈士们生前的平凡生活来突出生命的可贵,而把战争形容为“一种恐怖的美已经诞生”。在他看来,民族战争固然重要,但人性才是最值得歌颂的。叶芝希望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成功,但拒绝粗野的暴力革命。他的民族主义思想与那些激进的民族主义者所倡导的主张不同。叶芝是温和派,他的理想是配合爱尔兰政治独立运动,建立既不同于英国、又有别于欧洲的爱尔兰民族文学精神。这种文学精神是高雅的、古典的,它拒绝爱尔兰民族个性中的粗俗、愚昧以及暴烈的成分。
奥凯西是马克思主义信徒,一位坚决维护工人阶级利益的共产主义者。他对爱尔兰工人运动的兴趣更甚于对爱尔兰独立斗争的兴趣。他认为工人阶级参加起义是必要的,但是民族独立的成功带来的只是一个资产阶级国家,并不是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在他看来,这场运动是出于一种民族的自大,而不是出于对底层工人阶级的同情,并不能彻底改变工人阶级受压迫受奴役的地位,而且民族独立斗争伤及无辜,反而有损于底层贫民的利益。在《朱诺与孔雀》这部作品中,奥凯西充分传达了这一思想。波伊尔的儿子强尼在战争中失掉了一只胳膊,仍然表示愿意为爱尔兰继续干下去,“因为原则总归是原则”。但母亲波伊尔太太却反驳道:
啊,你丢掉了一只胳膊,我的孩子,那你就是失掉了最好的一条原则;因为对一个工人来说,胳膊才是对他们真正有用的一个原则。(《朱诺与孔雀》第一幕)
在《犁与星》中,奥凯西再次表达了与叶芝一样的看法,即人性高于战争。娜拉反对丈夫克里塞罗出去战斗,她说:
绝对没有一个女人肯把自己的儿子或丈夫交出去送死——倘若有人说愿意,那他们是在撒谎,他们是在欺骗上帝,欺骗自己的心,欺骗自己。(《犁与星》第三幕)
需要注意的是,奥凯西并不是一位彻底的反战作家,在他的《星儿变红了》、《送我红玫瑰》等红色革命题材的后期作品中,他热情讴歌工人阶级的大无畏战斗精神。可见,创作都柏林三部曲时的奥凯西只是从民间关怀的角度和人道主义的角度表达对1920年爱尔兰游击战、爱尔兰自由邦内战、1916年复活节起义这三次事件的看法。正如他在《犁与星》一剧中借传声筒人物小伙子之口指出,“只有为了无产阶级的经济解放的那种战争,才是值得打的。”所以等到后来叶芝与奥凯西的关系发生破裂时,叶芝才恍然大悟地称奥凯西是一位深藏不露的“机会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
当然,叶芝和奥凯西对民族主义运动的看法是不同的。叶芝的民族主义是矛盾的和妥协的,奥凯西的民族主义则听命于社会主义。但在“珍爱普通人的生命”、“反对暴力革命”这一点上两人达成了共识,所以叶芝才会欣赏奥凯西在《犁与星》中对生命的尊重和对人性的关怀,才会欣赏都柏林三部曲中深厚的民间情愫,毕竟人道主义是两位作家共同的立场。
共识二,对爱尔兰民族的看法。叶芝和奥凯西都认为爱尔兰国民与民族是存在劣根性的。叶芝对爱尔兰古老神话与民俗传统、对自己丰饶淳厚的出生地敬爱有加,甚至表现出一种民族自大性。“爱尔兰民族可能已是一个被选的民族。将成为支撑起世界的巨柱之一。”⑩他认为,爱尔兰相形于欧洲其他国家自有一份“灵视的天赋”,他对故土民俗传统的热爱和对民族古老神话传说的兴趣促成了他的民族自大与民族偏见,也促成了他坚信爱尔兰民族文学的独立与美好,并立志倾毕生力量去振兴它。
另外,叶芝的民族主义思想的复杂性还体现在他对宗主国英国的感情。叶芝是一位民族诗人,但在一定程度上又亲近英国文明特别是英国的古典文学传统,而且他的诗歌创作深受英国作家的影响。他说:“我的灵魂属于莎士比亚,属于斯宾塞和布莱克,也许还属于威廉·莫里斯,属于我用来思考、用来说话、用来写作的英语语言,我所爱的一切东西通过英语接近我,我的恨夹杂着爱,我的爱夹杂着恨,为此我深受折磨。”(11)
但是另一方面,还应看到叶芝强烈的民族自卑感。叶芝对爱尔兰大众思想的愚昧与落后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他既热爱祖国的民间神话与民俗传统,坚信那是产生民族文学的厚实土壤,又意识到爱尔兰文化的粗俗杂野的面貌。因此,重塑民族精神就成了这位知识分子最大的政治抱负。他说:“我们要在爱尔兰古老的、传统的铁砧上锻造新的刀剑,为最终恢复古老、自信和欢乐的世界去战斗。”(12)
与叶芝相比,奥凯西一向与底层平民站在一起,他十分熟悉那个阶层,也充分了解爱尔兰的民族特性。但是在对待爱尔兰民族主义问题上,奥凯西和叶芝一样表现出摇摆性与不确定性。奥凯西二十几岁时倡导爱尔兰政治独立和文化自主,为此他曾经将自己很英国味的名字“约翰”改为很有盖尔人特色的“西恩”,可是在1923年,正当他的《枪手的影子》在阿贝剧院上演时,他又将自己的姓氏“奥凯撒塞奇”改为英国味十足的“奥凯西”。这样一来,“西恩·奥凯西”这一名字中名是爱尔兰味的,姓是英国味的,这是很有象征意义的一件事。奥凯西对故土爱尔兰的感情也一直在变化着。他前期的创作立足于爱尔兰本土,有意针砭爱尔兰民众畏缩狭隘的缺点,如都柏林三部曲中的诗人达沃林、波伊尔先生等。到了后期,由于作品不被阿贝剧院采纳,也得不到本土观众的支持,奥凯西成了流亡作家。他先是在伦敦后又在美国追求政治与文学事业的发展。故土对他是一种惨痛的记忆,他甚至产生了仇恨情绪。
而《犁与星》直指爱尔兰人不切实际的盲目英雄主义热情和爱尔兰民众对斗争的不理解。正视爱尔兰人身上的弱点,这构成了与同样在民族立场上摇摆不定的叶芝的第二点共识。
共识三,对宗教的看法。叶芝和奥凯西都是新教徒,与占爱尔兰大多数人口比例的天主教徒格格不入。爱尔兰民族独立运动的实质是一场宗教运动,是爱尔兰古老的天主教与英国基督教新教的一场斗争。因此在这场运动中,身为新教徒的爱尔兰人,这种身份是很尴尬的。早在1833年,爱尔兰作家弗格森爵士在他的《一位爱尔兰新教徒头与心的对话》这篇散文中就形象地描写了这种尴尬:“头说:我是新教徒,必须保持宗教的独立性,不对天主教事业表示同情;心说:我生养在这片土地上,我最爱这片土地,我爱它的人民,不管他们[指占爱尔兰人口大多数的天主教徒]怎么想,我决不感到他们是我的敌人。”(13)
叶芝和当年的弗格森爵士很相似。他出生在新教徒家庭,长大后接触的大多数人是新教徒和英国人,而他所从事的爱尔兰戏剧运动面向的是爱尔兰的天主教大众。他觉得新教徒与天主教徒之间有一条从古至今就难以逾越的鸿沟,但身为爱尔兰人,如何在民族性与国家性上达成统一呢?新教徒不愿认同传统的爱尔兰天主教文化,天主教徒又不愿臣服于英国和爱尔兰少数贵族的新教文明。叶芝提出了一个折衷的解决办法,重塑一种新的爱尔兰文明,而这种文明是与古老的凯尔特文明联系在一起的,是薪火相传的。他说:
我早就注意到,在曾经产生过如此众多的政治殉难者的爱尔兰天主教徒中并没有我所知道的爱尔兰清教的那种品味、礼节和庄重,而爱尔兰清教似乎除了要在世界上取得成功外别的什么也不想。我于是想到,如果我们要有一种使爱尔兰流芳后世的民族文学的话,我们或许该将这两部分整合起来,而我则通过一种尖锐的批评、一种欧洲姿态从狭隘的区域主义中解脱了出来。(14)
叶芝认为,只有在这一新的层面上,两种宗教才能相互宽容。
作为有贵族倾向的新教徒,叶芝对爱尔兰天主教是有偏见的,他认为:“爱尔兰天主教的整个系统贬低有能力与出生高贵者,如果它抬高农民的话,而我相信它确实如此。一种长久的文化持续性,像在库勒的那样,从中世纪起在哪一个天主教家庭里都无法产生,也从未产生过。”(15)“天主教堂仍然是大众的教堂。”(16)在叶芝眼中,爱尔兰天主教是民间的、充满乡野气的下层人的信仰。
奥凯西的作品,尤其是他的后期作品常出现对天主教的攻击和嘲讽。最明显的是他在后期作品《主教的篝火》中将天主教信仰与真实的人性完全对立起来。这部作品不但激怒了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的“英雄正义”感,也触犯了大多数爱尔兰天主教徒的“虔诚”。奥凯西甚至认为爱尔兰的一切苦难都在于天主教对人民思想的统治。剧中人倔老头是作家的传声筒,奥凯西借其口传达出20世纪初现代主义作家普遍具有的姿态——自然高于宗教:
上帝赐给一个人的东西,和上帝赐给所有的人的东西相比起来,又算得什么呢?主教法官上的金色能比得上金雀花的金色吗?他的锦缎上的长靴上的光彩能够比得上野玫瑰花瓣的光彩吗?主教身上的紫色能比得上丝绒一般的蓟花的紫色吗?(《主教的篝火》第一幕)
在对待天主教的看法上,叶芝与奥凯西两人由于同为新教徒而有了共同语言。这是他们的第三点共识。当然,叶芝并不反对宗教,恰恰相反,没有宗教他无法生活,只是因为他的新教徒身份与爱尔兰大众的天主教信仰格格不入,而时代偏偏让他担当起爱尔兰民族文学复兴的重任,这使得他产生了信仰上的两难,再加上20世纪初正是尼采哲学思想与达尔文科学思想风行之时,这种内心渴望信仰而外在现实排斥他的信仰也是他步入神秘主义的原因之一。而奥凯西是政治理想高于宗教信仰,他攻击的不只是天主教,也是所有的宗教。奥凯西是爱尔兰为数极少的“穷新教徒”,他既不能进入受英国文明滋润的爱尔兰新教徒上层,又无法介入贫穷的信仰天主教的普通大众。这种身份使他在宗教信仰上非常尴尬。实际上,创作《犁与星》时的奥凯西在信仰上也和叶芝一样体现出摇摆性,但是到了后期,奥凯西接近于无神论者,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徒了。
不过,叶芝对奥凯西的认识在一开始是存在误解的。早期的奥凯西并没有在叶芝面前充分暴露出自己思想与艺术的真正追求。奥凯西的都柏林三部曲人物形象生动,戏剧冲突激烈,尤其是都柏林工人口语的运用贴切自如,这些都使叶芝以为这位剧坛新秀是当年辛格的再版。当年的辛格就是受了叶芝的指引,创作出关于爱尔兰农村边疆地带的戏剧。既然阿贝剧院创建时的定位是一座民族剧院,叶芝自然非常鼓励作家以爱尔兰本土发生的事情为题材,他自己也是这样身体力行的。奥凯西的三部曲紧贴爱尔兰现实的剧情显然赢得了叶芝的赞许,也符合阿贝剧院入选剧作的原则,再加上奥凯西作品中逼真的都市民间生活情景和鲜活的爱尔兰平民语言使叶芝误以为他是“城市版”的辛格,因此得到了叶芝的支持与认同。
值得深思的是,叶芝与奥凯西在战争、民族以及宗教上的观念共识中其实也暗含着诸多分歧。从战争层面上讲,叶芝是妥协革命者,反对粗野暴力,提倡秩序与精英统治。奥凯西提倡人性,同样反对战争与流血,但并不反对工人阶级的斗争。从民族层面上讲,叶芝崇尚贵族文明,既推崇爱尔兰的民间乡野文化,又抱怨爱尔兰国民性的粗劣愚昧,对祖国爱尔兰又爱又恨。奥凯西同样根植于爱尔兰,也意识到爱尔兰民众的盲目狂热,但并不像叶芝那样倡导民族独立精神与民族文化意识。
正因为两人之间暗含着这些差异,虽然在《犁与星》风波中叶芝“力挺”奥凯西,但两年之后,即1928年,当奥凯西的又一部剧作《银杯》问世时,叶芝已经觉察到他与这位社会主义作家在政治思想与艺术追求上的分歧了。叶芝拒绝在阿贝剧院上演此剧,奥凯西愤而出国,成为继谢立丹、哥尔德斯密、萧伯纳、王尔德之后的又一位“流亡剧作家”,两人从此分道扬镳。
注释:
①田汉:《田汉全集》(14卷),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252页。
②即约翰·辛格(John Millington Synge,1871-1909),20世纪初期爱尔兰剧作家,叶芝领导的爱尔兰戏剧运动的主要参与者。
③大卫·克劳斯:《西恩·奥凯西传》,吴文、张榕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7年,第19页。
④西恩·奥凯西:《奥凯西戏剧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412页。
⑤周江林:《叶芝的商业哲学》载2005年11月26日《财经时报》http://finance.sina.com.cn.
⑥叶芝:《叶芝文集》(三:随时间而来的智慧),王家新编选,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62页。
⑦傅浩:《叶芝评传》,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63页。
⑧傅浩:《叶芝评传》,第112页。
⑨傅浩:《叶芝评传》,第173页。
⑩叶芝:《生命之树:叶芝散文集》,赵春梅,汪世彬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第203页。
(11)Murray Christopher:Twentieth Century Irish Drama:Mirror up to Nation(New York:Syracuse UP,2000)15.
(12)叶芝:《生命之树:叶芝散文集》,第6页。
(13)陈恕:《爱尔兰文学》,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年,第48页。
(14)叶芝:《叶芝文集》(二:镜中自画像),王家新编选,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352页。
(15)叶芝:《叶芝文集》(二),第286页。
(16)叶芝:《生命之树:叶芝散文集》,第20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