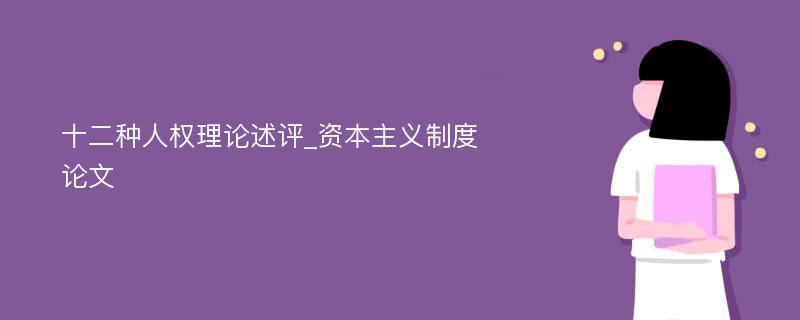
人权十二论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权论文,论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商赋人权论”。这是本人首先提出的。主要内容如下:
⑴确认人权是一种上层建筑,研究人权实质首先要寻找人权的经济基础。
⑵以平等自由为主要内容的人权,乃是商品流通的经济事实在上层建筑领域的一种反映:价值规律吁求平等权利,交换本身则满足了人对各种使用价值的需求从而实现了人的自由(这是人的自由的本义之一)。按照谷超豪先生见解,市场机制是一种“非线性现象”,即它是社会自组织功能的实现机制,因之人权也可被视为这种自组织功能的实现机制之一。
⑶《资本论》等论著关于商品流通产生人权的论述,不是仅仅针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而言的,而是对一切商品经济社会产生人权的一种科学的抽象。
⑷作为科学的抽象,“商赋人权论”乍一看来确实未区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等形态,但是,它按照马克思“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原则,内在地包含着由科学抽象层次向具体层次的回归,在承认人权是商品经济之上层建筑的大前提下,马上区分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及其上的资本主义人权,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及其上的社会主义人权,等等。
⑸资本主义人权以生产领域里剩余价值剥削的不平等不自由为实际内容,而以流通领域里表面上的平等自由为掩饰,因此是一种“反人权”的人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才是以无产阶级自由平等目标的实现和完善为判据,来设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这些设想也构成了社会主义人权的一个来源。
⑹人权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品。因为,社会主义经济也不能不是一种商品经济,公有制与商品经济并不绝对对立,市场机制并无社会制度属性,因此以公有制为主导的社会主义也不能不讲人权。
⑺从人权史来看,由于商品经济的作用,无论是在东方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或者是在古希腊大罗马时期,都产生了不成熟的未成体系的人权吁求或其片断、雏型。中国孔门的仁学和墨子学说之中,就包含着比较丰富的人权思想。
⑻作为价值观的体现,人权又不能不与特定民族的特定文化相纠绞。中国乃至整个东方的人权传统,与欧洲及西方的差异之一,是它从来偏重于群体权利。中国社会主义人权的发展,也有赖于发扬这一传统。
⑼从辩证法来看,人权本身固有“悖论”的性质,它的合理性有限,我们在掌握人权旗帜的同时,要注意它的局限,与社会民主主义者把人权视作“唯一”、“最高”旗帜的行为,划开界限。
⑽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人权是人道主义价值观在法律权利和一般权利方面的体现。对商品经济,二者都有合理性,也都有局限性。就其合理性而言,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也就必然吁求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大潮之前,笼统地断定人道主义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正如笼统断定商品经济是资本主义专利品一样,是很不明智的。
⑾如前所述,人性与人权、人道主义是逻辑上没有必然联系的三个概念,把这些不同概念归纳在一个所谓“人学”或“人的问题”的模式内,用人的本质研究代替对人权经济实质的探寻,在方法论上不对。
从目前情况看,“商赋人权论”在全国理论界引起的反应是十分热烈的。目前见到的公开批评“商赋人权论”的文章,共有三篇。其一是黑龙江团校张成诗先生的文章〔1〕(事实上, 持此见的还有叶立煊先生〔2〕,董云虎先生〔3〕,张兹暑先生〔4〕,等)。 它认为马克思关于商品经济产生人权的论述,是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而言的;“商赋人权论”会导向对人权阶级性的忽视。其实,马克思的有关论述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的体现,它开头不是先论析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及其上层建筑,而是先论述一般商品经济及其上层建筑人权;这种科学抽象又内在包含着具体的资本主义及封建主义等人权的上升,因而说“商赋人权论”会忽视人权阶级性是无根据的。其二是陈世夫和魏晋二先生题为《马克思主义人权观不容否定》的短文〔5〕。 它对“商赋人权论”扣了一些很大的政治帽子,究其未展开述说的理论成份,大体与张成诗先生的指责一样,只不过是一种政治攻击,故不予应答。其三,是郎毅怀先生在《求是》杂志1992年第1期所发文章, 从“综合人权论”或“资格人权论”出发,对“商赋人权论”加以批评。本文后面许多地方已对此作出了反应。
有趣的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1991年6 月召开的人权理论研讨会上,有先生提出,“如果人权是商品经济的产物,那就否定了非商品经济社会存在的人权”〔6〕。这是一种“人权永恒论”的反映。 非商品经济社会无所谓人权不人权,“商赋人权论”对这种不存在人权的社会的人权加以否定,为什么就一定错了呢?另一有趣的现象是,我国有一批资产阶级自由化代表人物,也大讲商品与人权不可分离的关系问题,不过,其所言商品经济实指私有制的个体商品经济,他们是以此为社会主义“侵犯人权”造舆论的。这与“商赋人权”是完全不同的事情,不应混同。
二、“资格人权论”。这是郎毅怀先生提出的。认为,“人权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范畴,是人作为社会存在物所获得的社会承认和界定。这种承认和界定表现为人参与社会交往的资格。有无这种资格,就是有无权利;资格大小,就是权利大小。人们有了权利,也就有了运用自身能力(体力和智力)的社会可能性,有了现实的社会力量,也就可以去获取自己所需要的利益。”〔7〕与此还有张春津先生。 他的提法是:“所谓人权,就是指一切人满足自身需求、享有人身自由、并对自身以外的任何事物发生不同的联系的资格和能力的总和”〔8〕。 郎张二先生提出的“资格人权论”,在理论上是不妥的。
其一,在这种论定中,根本不存在经济基础对于作为上层建筑之一的人权的原生作用,有的只是人本主义地离开特定历史条件思考个体的人及其权利的模型。
其二,任何人,不管社会是否承认,他也都是作为社会存在物而存在的。它不以任何个体和群体的承认和“界定”来获得自己存在的根据。把作为事实的存在看成是需要某个体群体承认和“界定”的结果,岂非颠倒了客观存在与主观承认的关系?
其三,我们暂且违心地假定人权是一种“承认”和“界定”罢,那么,“人作为社会存在物”是与人类社会的产生发展共始终的,难道人权也与人类社会共始终?
其四,一方面把人权说成是一种“承认”,一种“界定”,属于上层建筑中的社会观念意识的范畴,而同时又说“人权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范畴”,既属于经济基础,又属于上层建筑,并明确批判把人权看作一种观念形态。这是自相矛盾的。
其五,把人权界定为“资格”,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来没有这样解说;相反,倒是西方的非马克思主义者早就使用的思路。例如,美国学者约·费因伯格便说,人的“权利”难以“正式定义”,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一切权利似乎可想象为有资格去做,去据有”。他还认为,“资格”这个概念内涵和外延都是“不确定的”,还需要用“要求权”来加以弥补。〔9〕很明显,在西方的这种“资格人权论”中, 根本没有经济基础对作为上层建筑的人权的根源意义的地位。即使如此,“资格”范畴的不确定性,也还使这种理论不能不顾及“资格”之外的人权,并且明确宣布这只是一种“暂用”,不能作为“正式定义”。
其六,“人作为社会存在物”,其主语只能是人的个体,因此,“资格人权论”所说的“人权”,仅仅指个体的人的权利,群体权利,包括阶级权利和民族权利,乃至国家主权,都实际上被“资格人权论”排除于人权之外。
三、“综合人权论”。这也是郎毅怀先生提出来的。认为人权不仅仅是一种上层建筑,而且是一种社会关系(据说,因为我国认为人权包括经济权利),是两者综合形成的一个“特殊的社会范畴”〔10〕。
马克思早就明确说过:“私有财产的真正基础,即占有,是一个事实”,“而不是权利。只是由于社会赋予实际占有以法律的规定,实际占有才具有合法占有的性质”〔11〕。很显然,按照马克思的这种界定,“所有权”之类“经济权”,是经济关系反映在法律等上层建筑(包括法律)方面的用语;而作为所有制之类的经济关系本身,却绝对不能是作为上层建筑的权利。因此,以我国人权包括经济方面的权利为由,把人权界说为经济关系,起码在哲学上混淆了客观存在与这种存在之反映的界限。
四、“人权是资本主义专利论”。《光明日报》1979年10月26日以整版篇幅发表的“本报评论员”文章《略谈人权问题》,是此论在较早年份的一个代表。它明确提出,“从经济基础来说,人权这个具有普遍性形式的口号,只能是资本主义商品货币关系的产物”,因为,“资本是天生的‘平等派’。作为商品所有者,不论是拥有货币的资本家,还是只有自己的劳动力商品可出卖的无产者,在法律上他们是平等的。他们作为商品所有者彼此发生关系,是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平等地进行的。资本主义的商品所有者也必须是在行动上不受限制的自由人”,等等。可以看出,在这一种分析中,我们所面对的一切商品经济,已经被定性为资本主义性质。直到1984年,王锐生先生还写道:“资本主义经济是占统治地位的商品经济。在这里,一切人作为商品所有者都是平等的。因为在商品交换中,根据价值规律,所有人的劳动是平等和同样有效用的。可见,平等之成为人权,深深植根于资本主义经济之中”〔12〕。在王先生的这种论述中,商品交换中的价值规律,仍然是资本主义的专利品,似乎社会主义就不能容忍价值规律存在。邢贲思先生也持同样议论:“启蒙思想家之所以竭力鼓吹‘自由’、‘平等’,正是新兴资产阶级自由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和商品等价交换关系在观念上的反映”,因而,“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完成”它们“也应该退出历史舞台”,因为人道主义中包含着的人权要求,“无非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权利”,自由平等“实际上是一个纯粹的资产阶级的口号”〔13〕,等等。1984年,我党以公报形式公布了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新思想。但是,由于一些论者对商品经济的偏见已经根深蒂固,他们至今也很难跳出商品经济等于资本主义的旧框框。直到1992年初,王锐生先生还写道:“人权的抽象性虽然在商品交换领域有其客观根源,但这种抽象性又总是要被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运行机制所撕掉,随时显现人权的实质。”〔14〕这样,适应于商品流通的人权,似乎仍然是资本主义的一件专有饰品,社会主义人权仍然未能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获得自己应有的确证。王先生在同时发表的另一文中,对这种十分落伍的见解说得很明确:“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是价值规律,而价值规律要求在商品交换过程中、商品持有者之间只存在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关系,而不问他们在其他方面的特点……,所以他们是具有平等权利的。商品交换是‘天赋人权’的乐园——这是马克思的名言。”〔15〕在这一段话里,价值规律作为资本主义专利品的评价,是呼之欲出的。邢贲思先生目前则把对人权问题的研究又一次引向对人的本质问题的探求,对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依然讳莫如深。
由于有王先生和邢先生这样的权威学者坚守旧见,所以,目前在我国理论界,“人权是资本主义的专利论”仍然广泛流播,甚至以“官方”“半官方”的形式出现。《人民日报》于1991年11月2 日发表的社论《维护人权 捍卫人权》,便是此种情况的一种反映。这篇社论根本没有提及人权是商品交换的产物,更没有提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及其上的社会主义人权。这就为论者们仍然把商品经济及适应它的人权定为资本主义专利品开了一个理论先例。
五、“人性人权论”。如前所述,邢贲思先生把对人权的思考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思路移向从人的本质(或人性)探求人权的思路,即为此论的一例。黄楠森先生和陈志尚先生《关于人权的几个理论问题》一文〔16〕,更是此论的一个代表。其不当有:
其一,“人权是人的一个方面”,把人权看成与人共始终的一个问题。
其二,“人权应该从人的本质那里获得自己存在的根据”。这更是不妥之论。人权不是人所固有的东西,只是一种上层建筑,为什么只能从人的本质中获得自己存在的根据?
其三,“人权的根据存在于人的现实的具体的劳动能力之中”,仍然不妥。如果人权的根据在此,那么,人权便成了人固有的某种超经济超阶级的东西了。
其四,“人权产生于人形成、维持和发展自己本质的需要”。按黄陈二先生,人的本质是劳动。人在形成劳动能力的时候,就需要人权?人的劳动的本质,是一个客观的不移的存在,它何必用人权来加以维护?要维护,岂不意味着人的本质有“异化”或丧失之危险。
六、“生赋人权论”。这是叶立煊先生提出的一个论点:“人权是社会一定生产方式或经济关系的产物,是社会一定生产方式或经济制度在制度上、政治上或法律上的表现。也可以说,人权是社会一定生产方式或经济关系赋予的,可简称为‘生赋人权’”〔17〕。此论把人权视为上层建筑,是对的,但它无视人权只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由特定经济基础产生的一种特定的上层建筑,犯了“永恒人权论”的错误。它之所以错误,还在于它根本没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根据。《哥达纲领批判》讲过,“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18〕;法权关系是“与商品经济相适应的”关系〔19〕。只把前者抽出来加以绝对化而不顾及后者,这不是全面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
七、“实践人权论”。这一论点最早是由张春津先生提出的。认为:“人们的社会关系是在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在实践活动中体现的,随着实践活动的发展而改变的;反过来说,实践活动又是现实的人的社会活动,以人们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为必要前提。因此,人权的扩展及其社会作用依赖于实践活动,实践活动是在人类对人权不同认识水平的支配调节下实现的。”〔20〕后来陈锡喜先生又重申了社会实践是人权之源的看法〔21〕。显然,“实践人权论”与黄楠森等先生所说的“人性人权论”,实际上是一脉相通的。“人性人权论”错在哪里,“实践人权论”也就错在哪里。
八、“私赋人权论”。冯卓然先生提出,“人权问题是随着奴隶制社会的出现而产生的,它是私有制的产物”,因为私有制破坏了“原始社会里人与人的平等关系”,“于是便产生了人权问题”;甚至认定,“人权问题的历史命运是同私有制和阶级的历史命运紧密相联的。它随着私有制和阶级、阶级剥削、阶级压迫的产生而产生,因此,它也必然随着这些现象的消失而得到彻底解决。”〔22〕
客观地说,冯先生的看法并不是没有马克思主义文献依据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应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七十余年社会主义实践已经证明,商品(市场)经济与公有制可以并存,说公有制对私有制的取代是人权问题的结束,显然有悖于社会主义人权的实践和理论。其实,把马克思商品交换产生平等规范的命题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实践相结合,马上就可以导出公有制与人权兼容的新结论。
九、“人赋人权论”。毛泽东说过政府工作人员的权力不是天赋的,而是“人赋人权”〔23〕。目前,我国有一批论者便套用这一说法,提出“马克思主义人权观突破了早期狭隘的‘天赋人权观’,更注重‘人赋人权’”〔24〕……。
在这里,争论的理论焦点在于:权力是“人赋”的,而作为平等权利的“人的权利”则不是“人赋”的。人权口号是对人人平等自由的吁求,而权力则显然不是人人都可自由平等地享用的(领导科学以权力为研究的逻辑起点)。
十、变型的“天赋人权论”。张春津先生说,“权利是大自然赋予给人的。人的权利是与生俱来的,而不是后天追加的”;“权利是大自然赋予给人平等地享用的,由此人的这种权利只能按照大自然的规律”行使,“只要权利主体存在,就决不能把权利同其主体——特定的人格分离开”〔25〕。武高寿先生也提出了“社会主义天赋人权论”的口号〔26〕。
“天赋人权论”的变型,主要是由在我国理论界长期占统治地位的“人性人权论”诱发的,或者说它是“人性人权论”的必然逻辑产物。从人的自然属性中寻求人权之根,不管在理论和逻辑上如何花样翻新,却都只能陷入“天赋人权论”的泥沼之中。
十一、“道德人权论”。台湾政治大学教授柴松林先生力主“只有道德才是人权的真正基础”,因为,法律只是人权的外在的界限;而除这一界限而外,尚存内在的潜在的标准,这个存在于人类内心的潜在的标准,就是道德。”〔27〕显然,这种思路,既有康德的启示,又有朱熹理学的因子,虽不无某些合理要素,但整体上,至少与历史的唯物主义挂不上勾。
十二、“法赋人权论”。以西方的边沁、戴西和密尔为代表,认为人的权利并非“天赋”,而是法律所赋予的,因而只有法律所认可的权利才算人权。这种理论只是复述了人权与公民权关系争论中一派的看法——只有法律认可的公民权才算人权。对这种看法,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已有表态:在公民权之外,还存在着别的人权〔28〕。
注释:
〔1〕《理论探讨》1991年第1期。
〔2〕〔17〕叶立煊《人权论》,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59、4页。
〔3〕《世界人权约法总览》,第67页。
〔4〕《新华文摘》1991年第11期。
〔5〕《共产党人》1992年第3期。
〔6〕《学术动态》1991年第49期。
〔7〕〔10〕《求是》1992年第1期。
〔8〕〔20〕〔25〕张春津《人权论》,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2、24、44—46页。
〔9〕转引自汤·比彻姆(美)《哲学的伦理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汉译本,第293—295、318页。
〔11〕〔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82、436—437页。
〔12〕王锐生《论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学说》, 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04页。
〔13〕邢贲思《欧洲哲学史上的人道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9年版,第42、204、46、47页。
〔14〕王锐生《哲学与人权》。
〔15〕《人民日报》1992年2月14日。
〔16〕中央党校《党校科研信息》1991年第14期。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2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02页。
〔21〕《文汇报》1991年12月31日。
〔22〕冯卓然《论平等与人权》。
〔23〕肖延中《晚年毛泽东》,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版, 第289页。
〔24〕《人民日报》1990年8月13日。
〔26〕《山西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
〔27〕台湾《经济建设》1986年第1期。
标签: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自由资本主义论文;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 法律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