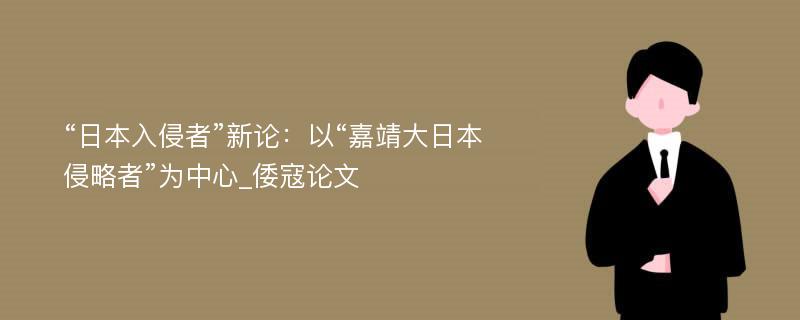
“倭寇”新论——以“嘉靖大倭寇”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倭寇论文,嘉靖论文,新论论文,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K24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89(2000)01—0037—010
一位西方哲人说过,历史是在矛盾的陈述中清理出来的。历史的魅力就在于它的深不可测,一些看来似乎久已成为定论的问题,经过学者们的深入探索,可以发出在前人看来不可思议的新论,令人拍案叫绝。“倭寇”便是一个至今仍引人入胜的课题。笔者1997年曾应邀参加了韩日中三国学者的历史研讨会,会上韩国学者与日本学者就“倭寇”展开了热烈的讨论。韩国的“倭寇”与中国的“倭寇”是不尽相同的。日本学者为了区别起见,把它们划分为“前期倭寇”与“后期倭寇”。例如一位日本学者在论文中说:倭寇通常大别为活跃于十四世纪后半期的“前期倭寇”和活跃于十六世纪中叶的“后期倭寇”,两者的活动范围、目的、构成都是不同的。前者如同“倭寇”二字所显示的那样是由日本人构成的,以朝鲜半岛为主要舞台,从事米和奴隶的掠夺;后者以中国浙江、福建、广东诸省的沿岸地带为主要的活动舞台,进行走私贸易,其构成人员是中国人、日本人的混成部队[1—P279]。可见“倭寇”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难以一概而论。不过这位学者分析到此为止,似乎让人感到意犹未尽。本人试图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略抒已见。
1
长期以来,关于明代的“倭寇”,在理解上存在误区,概念与史实都有所混淆。甚至九十年代出版的《中国历史大辞典》中也仍留下明显的痕迹。该辞典明史卷的“倭寇”条说:倭寇是指“明时骚扰中国沿海一带的日本海盗”[2—P411]。这个结论是很成问题的。也难怪,它其实是以往史学界的一种流行观点。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历史认识已经远远落后于史学自身的发展。
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史学界一些有识之士对此重新检讨,从历史事实辩证出发,提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解释。
林仁川《明代私人海上贸易商人与“倭寇”》一文认为,“倭寇”的首领及基本成员大部分是中国人,即海上走私贸易商人,嘉靖时期的“御倭”战争是一场中国内部的“海禁”与反“海禁”的斗争[3—P194~108]。
戴商煊《倭寇海盗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一书指出:倭患与平定倭患的战争,主要是中国社会内部的阶级斗争,不是外族入寇[4—P16]。
王守稼《嘉靖时期的倭患》一文说得更加彻底:明朝政府把王直集团称为“倭寇”,王直集团也故意给自己披上“倭寇”外衣,他们其实是“假倭”,而“真倭”的大多数却是王直集团雇佣的日本人,处于从属、辅助的地位[5—P277]。
以上新论或许尚有待于完善,但就其主要倾向而言,毫无疑问更加接近于历史真实。
在这方面,海峡彼岸的学者领先了一步。早在1965年陈文石发表了题为《明嘉靖年间浙福沿海寇乱与私贩贸易的关系》的长篇论文,从沿海走私贸易角度去透视“倭寇”。他从五个方面展开论证:一、明代的禁海政策贡舶贸易制度与私贩贸易的关系;二、国人私贩贸易与沿海地理经济条件;三、嘉靖前期的私贩活动;四、私贩转为海盗与朱纨禁海失败原因;五、嘉靖后期的私贩与盗乱。他在文末感慨地指出:嘉靖年间的大祸(即所谓倭患)是明代海禁政策造成的后果,“凡违禁私贩出入海上者,官府皆以海盗视之,严予剿除。彼等既不能存身立足,自新复业,则只有往来行剿,或奔命他邦,开辟生路”[6—P375~418]。他的这一研究思路为林丽月所发挥,写出了《闽南士绅与嘉靖年间的海上走私贸易》,指出:闽南士绅投身海上贸易,无非以追逐个人私利为动机,难免有蔑视朝廷法令与地方官府之讥,但就促进闽南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而言,应不无正面意义[7—P91~111]。
读者不难发现,上述新论与三四十年代以来过多掺杂民族情绪的“倭寇”论相比,是大异其趣的,也是更加客观、更加科学的,是现代史学应当努力追求的境界。
众所周知,“倭寇”问题涉及日本,所以日本学者对此作了大量研究。令人不解的是,以往中国学者在研究这一课题时,却忽略了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只要稍加留意便可发现,日本学者以他们特有的实证风格,揭示出了与上述中国学者大体相近的历史解释。不妨举两个最具影响力的例子以见一斑。
稍早一点的可以明史专家山根幸夫为代表。他在《图说中国历史》第七卷《明帝国和日本》中,谈到“后期倭寇”(日本通常称为“嘉靖大倭寇”)时,强调指出了以下两点:一是后期倭寇的主体是中国的中小商人阶层——由于合法的海外贸易遭到禁止,不得不从事海上走私贸易的中国人;二是倭寇的最高领导者是徽商出身的王直——要求废止“海禁令”、追求贸易自由化的海上走私贸易集团的首领[8—P61~63]。
稍近一点的可以倭寇问题专家田中健夫为代表,他曾写过《倭寇》一书、《倭寇和东亚交通图》一文[9]。1994 年版《日本史大事典》的倭寇条,即出于他的手笔。他对倭寇的释义既客观又精细,大大有助于廓清以往人们心目中混淆不清的倭寇概念。
田中健夫写道,在朝鲜半岛、中国大陆的沿岸与内陆、南洋方面的海域行动的包括日本人在内的海盗集团,中国人和朝鲜人把他们称为“倭寇”,它本来带有“日本侵寇”或“日本盗贼”的意味,但是由于时代和地域不同,它的意味和内容是多样的,把倭寇当作连续的历史事象是不可能的。“倭寇”二字初见于404年的高句丽广开土王碑文, 此后丰臣秀吉的朝鲜出兵以至二十世纪的日中战争等事件中都有倭寇的文字表述。由于时期、地域、构成人员等规准的不同,对倭寇的称呼是各式各样的:如“高丽时代的倭寇”、“嘉靖大倭寇”、“中国大陆沿岸的倭寇”、“浙江的倭寇”、“葡萄牙人的倭寇”、“王直一党的倭寇”等等,在以上这些倭寇中,规模最大、活动范围最广的是14—15世纪的倭寇和16世纪的倭寇。
关于“16世纪的倭寇”,田中健夫作这样的界定:因为依托于勘合船的日明间交通的中途断绝,中国大陆沿岸发生了大倭寇。最激烈的是明嘉靖年间(1522—1566)为中心,持续至隆庆、万历年间约四十年时间,因而称为“嘉靖大倭寇”。这个时期的倭寇,日本人参加数量是很少的,大部分是中国的走私贸易者以及追随他们的各色人等。这时在东亚海域初现身姿的葡萄牙人被当作倭寇的同类对待。自从明太祖以来,称为海禁的一种锁国政策禁止中国人在海上活动,随着经济的发达,维持这种政策是困难的,于是产生了大量的海上走私贸易者。他们和地方富豪阶层(乡绅、官僚)勾结,形成强大势力,推进走私贸易。葡萄牙人因为得不到明政府正式贸易的许可,也不得不加入走私贸易,日本的商船则以国内丰富的银生产为背景与之合流。中国的官宪把这些人一概当作倭寇。浙江省的双屿和沥港作为走私贸易基地,遭到中国官军的攻击而毁灭殆尽,走私贸易者一变而为海盗群。萨摩、肥后、长门、大隅、筑前、筑后、日向、摄津、播磨、纪伊、种子岛、丰前、丰后、和泉等地的日本人投靠了倭寇。作为倭寇的首领,有名的是王直、徐海。王直以日本的平户、五岛地方为根据地,率大船队攻击中国的沿海。明朝方面,胡宗宪、戚继光、俞大猷等负责海防,取得了各种功绩。不久与海禁令解除的同时,日本方面丰臣秀吉国内统一的进行,倭寇次第平息[10—P1312~1313]。
把上述论断与前引《中国历史大辞典》“倭寇”条加以对比,其间的是非曲直是不难辨明的,由此而对所谓定论发生怀疑,进而驳难是容易理解的。
2
嘉靖二年(1523年)发生在宁波的“争贡”事件,被历史学家定位为“后期倭寇的发端”[11—P261];[8—P57]。剖析这个“发端”, 对于认识后期倭寇(或曰嘉靖大倭寇),无疑是很重要的关键。
明朝建立以后,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禁止民间的私人海上贸易活动,只允许保留有限制的官方朝贡贸易。
管理这种海外贸易的机构是市舶司,它的职责是维持明朝与外国的官方朝贡关系。在这种关系之下的外国船舶必须持有明朝颁发的称为“勘合”的凭证,方可前来贸易,因而称为“勘合贸易”。《大明会典》记载:“凡勘合号簿,洪武十六年始给暹罗国,以后渐及诸国。每国勘合二百道号簿四扇”。这里所说的“渐及诸国”,是指:日本、占城、爪哇、满剌加、真腊、苏禄、柯支、渤泥、锡兰山、古里、苏门答剌、古麻剌等[12]。这种勘合贸易,除了由市舶司机构安排在市舶司港口(宁波、泉州、广州)小范围进行之外,主要安排在京师会同馆(接待各国贡使的宾馆)进行。《大明会典》记载:“各处夷人朝贡领赏之后,许于会同馆开市三日或五日,惟朝鲜、琉球不拘期限。俱主客司出给告示,于馆门首张挂,禁戢收买史书及玄黄、紫皂、大花、西番莲段匹,并一应违禁器物。各铺行人等将物入馆,两平交易,染作布绢等项立限交还。如赊买及故意拖延,骗勒夷人久候不得起程,并私相交易者,问罪,仍于馆前枷号一个月。若各夷故违,潜入人家交易者,私货入官,未给赏者量为递减,通行守边官员,不许将曾经违犯夷人起送赴京。凡会同馆内外四邻军民人等代替夷人收买违禁货物者,问罪,枷号一个月,发边卫充军。”[12]
日本与明朝的勘合贸易是在这种受到严格限制的框架内进行的。不过,在冠冕堂皇的“朝贡”与“赏赐”背后,官方默认日本使节的随行人员(僧侣、商人)所挟带的货物同中国商人进行私下交易,这种交易使日本方面获利颇多,因而很有吸引力。
日本的勘合贸易是由浙江市舶司掌管的。日本使节入明,必须持有明朝礼部颁发的勘合,才可以在浙江市舶司所在地宁波上岸,在安远驿内的嘉宾堂歇脚,一面进行岸上交易,一面等候朝廷的入京许可。一旦获得许可,使节一行便携带国书、贡物及挟带货物,在明朝官员护送下前往北京的会同馆。在向朝廷提交国书、贡献方物、领取赏赐后,挟带的货物方可出售,先尽政府有关部门购买,然后才可由商人购买,并买入非违禁货物。据田中健夫《倭寇与勘合贸易》,从建文三年(1401年)到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近一个半世纪内,日本的遣明使节所率领的勘合贸易船队共计十八批[8—P56]。由于嘉靖二年(1523年)发生了宁波争贡事件,使勘合贸易发生危机,因而成为“后期倭寇的发端”。
这时日本的勘合贸易经营权已经脱离足利义持将军之手,落入了细川、大内两家之手。遣明船一向有幕府船、大名船、相国寺船、三十三间堂船等,随着大寺社势力的消退,细川氏、大内氏作为遣明船的主体势力而登场。细川氏是所谓“堺商人”——濑户内海东部沿岸一带的势力,大内氏是所谓“博多商人”——从濑户内海西部到北九州沿岸一带的势力[13—P51]。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这两家发生了争夺主导权的斗争。正德六年(1511年)第十五批遣明船和勘合贸易是由大内氏主宰的,以后幕府也承认了大内氏独占遣明船的运营权,因而引起细川氏的不满。当嘉靖二年(1523年)第十六批遣明船与勘合贸易,由大内氏派遣的正使宗设谦道和尚率领三艘船舶驶向宁波,细川氏为了与之抗衡,凭借已经失效的“弘治勘合”,派鸾冈瑞佐和尚为正使、明朝人宋素卿为副使,率船舶一艘也驶向宁波。先后抵达宁波的大内船、细川船终于发生了正面冲突,不仅互相大打出手,而且烧毁了市舶司的招待所嘉宾堂,袭击了武器库,殃及了沿途民众,正如嘉靖《宁波府志》所说:“两夷仇杀,毒流廛市”[14]。
宁波争贡事件影响极坏,给明朝政府内部主张更加严厉实行海禁政策的一派官僚找到了一个口实。当时任兵科给事中的夏言(后任内阁首辅)上疏强调“祸起市舶”,礼部未加细察,也没有权衡利弊得失,便贸然请罢市舶司。后人纷纷指出,应当罢斥的不是市舶司,而是市舶太监[15]。因为争贡事件除了日本方面的因素,浙江市舶司的市舶太监赖恩处置不当,激化了双方的矛盾,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细川氏的副使宋素卿是宁波人,长期从事贸易中介业(即所谓掮客),为人奸狡,以重金贿赂市舶太监赖恩。于是市舶司破例,在检查贸易品时,把先期到达的大内氏推迟,后到的细川氏反而提前;在招待宴会的座次安排上,也故意把细川氏使节坐于大内氏使节的上座;在双方仇杀时,赖恩有意偏袒宋素卿,暗中资助兵器,致使械斗一发而不可收拾[15]。
浙江市舶司终于在嘉靖八年(1529年)废止,此后除了嘉靖十八年、二十六年有过两次遣明船,不再有日本方面派来的遣明船及其勘合贸易。严厉的海禁为海上走私贸易的兴旺提供了有利的时机。
这一事件被称为“后期倭寇的发端”,就是因为它直接导致勘合贸易的中止,以及随之而来的海上走私贸易的横行。
沿海民众一向有从事海上贸易的传统,作为维持生计的重要手段。明初以降,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严禁沿海民众出海贸易,无异于断绝沿海民众的生计,激化了矛盾,也诱导了违禁的海上走私贸易。浙江、福建、广东三个市舶司垄断的勘合贸易,根本无法适应随着商品经济发展而日益增长的海外贸易需求,因此在正常的市舶司渠道的官方贸易之外,早已存在走私贸易这种民间渠道。正如台湾学者陈文石所说:“在贡舶贸易(即勘合贸易——引者)制度下,虽然持有勘合国家可享有贸易上的种种特殊权益,但究为贡约所限,不能随其所欲自由往还。同时此仅为贡舶国家王室或官方支持下的贸易,一般番商因不能取得勘合,便无法进口。而贡舶输入货物,又为政府所垄断。虽然市舶司或会同馆(会同馆开市仅限三天或五天)开市时,中国商人可承令买卖,但仅为官方所不肯收买的残余物品,货色粗劣,数量亦微,品类价格又都有限制,而且往往供求两不相投,双方俱不能满足所欲,于是贡使、中外商人,遂互相勾结,窝藏接引,进行秘密私贩活动。尤其中国海商,在政府禁海垄断,外舶特权独占的双重刺激下,既不能取得公平合法的贸易,便只有越关冒禁,挑战下海,从事非法贸易了。”[6]相对于广东沿海对南洋的贸易而言,浙闽沿海对日本的贸易,控制更严,这种矛盾更为突出。一旦浙江市舶司停罢以后,海上贸易的供求失衡尖锐地凸显了出来。
对于“罢市舶”所引起的严重后果,当时人深知其害,几乎众口一辞地指出:“罢市舶,则利孔在下,奸商外诱,岛夷内讧,海上无宁日矣。”[15]及至这种严厉的海禁政策扩展至福建,情况更趋严重,曾参与平倭的谭纶说:“闽人滨海而居者不知其几也,大抵非为生于海则不得食。海上之国方千里者不知凡几也,无中国绫绵丝枲之物则不可以为国。禁之愈严则其值愈厚,而趋之者愈众。私通不得则攘夺随之。昔人谓弊源如鼠穴也,须留一个,若要都塞了,好处俱穿破,意正在此。今非惟外夷,即本处鱼虾之利与广东贩米之商、漳州白糖诸货皆一切禁罢,则有无何所于通,衣食何所从出?如之何不相率而勾引为盗也。”[16]深刻地揭示了海禁愈趋严厉的大背景下,沿海民众由海上走私贸易而发展为海盗(即所谓倭寇)的轨迹。
日本的正常勘合贸易断绝之后,他们所需要的大量中国商品只能通过海上走私贸易渠道获得,中国的走私贸易商人鉴于获利丰厚,多愿意与日商勾结进行走私贸易,甚至远航至日本沿海岛屿进行交易。日本商人大多以现银(日本所产白银)支付,中国商人常获利达十倍之多。由平倭总督胡宗宪挂名、出于其幕僚郑若曾之手的《筹海图编》,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书中记载走私往日本的中国商品种类很多,有丝、丝绵、棉布、绵绸、锦绣、红线、水银、针、铁锅、瓷器、古钱、药材等,其中尤以太湖近旁湖州所生产的湖丝最为畅销,价格不菲:“丝,所以为织绢紵之用也,盖彼国自有成式花样,朝会宴享必自织而后用之。中国绢紵但充里衣而已。若番舶不通,则无丝可织,每百斤值银五十两,取去者其价十倍[17]。与徐光启《海防迂说》所提供的资料可以互相印证:湖丝运往日本“取去者其价十倍”[18]。如此一个重大的获利渠道,一旦遭到官方禁堵,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正如茅元仪所说:“贫民倚海为生,捕鱼贩盐乃其业也,然其利甚微,愚弱之人方恃乎此。其奸巧强梁者自上番舶以取外国之利,利重十倍故耳。今既不通番,复并鱼盐之生理而欲绝之,此辈肯坐而待毙乎!”[19]
由此人们不难悟出嘉靖年间东南沿海所谓倭患的根源来了。
当时留心经世韬略及边防的唐枢,在“倭寇王”王直接受招抚后,为身负平倭重任的胡宗宪咨询时,谈到倭患的根源,直言不讳地指出了以下几点:第一,中国与外国的贸易难以禁绝,海禁只能禁止本国百姓。他说:“中国与夷各擅生产,故贸易难绝。利之所在,人必趋之。本朝立法,许其贡而禁其市,夫贡必持货,与市兼行,盖非所以绝之。律欵通番之禁、下海之禁,止以自治吾民,恐其远出以生衅端”;第二,嘉靖年间的倭患,起源于海禁政策。他说:“若其私相商贩,又自来不绝,守臣不敢问,戍哨不能阻。盖因浩荡之区势难力抑,一向蒙蔽作法,相延百数十年。然人情安于睹记之便,内外传袭,以为生理之常。嘉靖六七年后,守臣奉公严禁,商道不通,商人失其生理,于是转而为寇。嘉靖二十年后,海禁愈严,贼伙愈盛。许栋、李光头辈然后声势蔓延,祸与岁积。今日之事,造端命意实系于此。夫商之事顺而易举,寇之事逆而难为,惟顺易之路不容,故逆难之图乃作”;第三,所谓倭寇,其实是中国百姓。他说:“使有力者既已从商而无异心,则琐琐之辈自能各安本业,而无效尤,以为适从。故各年寇情历历可指:壬子之寇,海商之为寇也;癸丑之寇,各业益之而为寇也;甲寅之寇,沙上黠夫、云间之良户复益而为寇也;乙卯之寇,则重有异方之集矣”[20]。
唐枢作为倭寇的同时代人,以目击者的身份所提供的证言,洞若观火、鞭辟入里的分析,今日读来仍禁不住要拍案叫绝!
3
谈到“嘉靖大倭寇”,“倭寇王”王直是必然要提及的重要人物。被明朝官方视作江洋大盗的“倭寇王”王直,其实是一个从事海上走私贸易的徽州商人。
徽商研究的奠基人藤井宏最早注意到这个问题。他在成名作《新安商人的研究》中,注意到徽商(日本学者称为新安商人)在浙闽沿海的进出口贸易。他指出:嘉靖十九年(1540年)许一(松)、许二(楠)、许三(栋)、许四(梓)勾引葡萄牙人络绎于浙海,并在双屿、大茅等地开港互市。《筹海图编》卷五浙江倭变记云:“嘉靖十九年贼首李光头、许栋,引倭聚双屿港为巢……光头者,福(州)人李七;许栋,歙(县)人许二也……其党有王直、徐惟学、叶宗满、谢和、方廷助等。出没诸番,分迹剽掠,而海上始多事矣。”此时王直不过是许氏兄弟的僚属。《日本一鉴》海市条:“……嘉靖二十二年邓獠等寇闽海地方,浙海寇盗并发。海道副使张一厚因许二等通番,致延害地方,统兵捕之。许一、许二等敌杀得志,乃与佛郎机夷竟泊双屿,伙伴王直(名鍟,即五峰)于乙已岁(嘉靖二十四年)往市日本,始诱博多津倭助才门等三人,来市双屿。”嘉靖二十七年浙江巡抚朱纨派遣都指挥卢镗等突袭双屿港,一举覆灭所谓海贼的老巢,生擒李光头、许栋,王直等收集余党,重振势力,把老巢移到金塘山(定海县西八十里海中)的烈港(沥港),直到嘉靖三十六年被胡宗宪擒捕以前,东南海上全是王直的独占舞台。
藤井宏还指出:王直是徽州盐商出身,后来为日本商人当经纪(牙侩),是货物贸易的仲介者,在双屿、烈港开辟走私市场。王直死后,徽商在海上还相当繁盛,后继者有徐惟学、徐海。王直借助闽广海商称雄浙海,遭官军打击后,在日本平户建立根据地,建都称王,部署官属,控制要害,形成了以“徽王”王直为中心的徽浙海外贸易集团,把徽州海商的海外贸易活动推进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鼎盛阶段。自王直以后,日本的平户港一直是明末清初中国民间海商往来日本的一个主要据点[21—P184~189]。
这种基于史料的实证研究,为理解王直与倭寇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令人不解的是,以上研究成果迟至三十年以后才在中国学者中激起反响。
在这方面最有力度的当推徽商研究的后起之秀唐力行,他从徽州海商的角度来考察倭寇,反过来考察日后成为倭寇首领的徽州海商,“为了对抗明王朝的武力镇压和扩大贸易,海商们渐次组合成武装的商业集团……这些船头又在竞争兼并中聚合成几个大的武装海商集团。其中,较为著名的以徽州海商为首领的有许氏兄弟海商集团、汪直海商集团和徐海海商集团”。他的一大贡献是考证了《明史》改王直为汪直很有必要。王直本姓汪,从事海上走私,风险大,为家属安全计,隐瞒真姓(汪)。《明史》中有汪直传,以前均认为有误,其实王直本来姓汪。汪为徽州大姓,“为贾于浙之杭绍间者尤多”[22—P35~46]。横行东南沿海几十年的倭寇首领许氏兄弟、汪直(王直)、徐海等,莫不是徽州海商,这一史实是值得深长思之的。
把王直等海商集团的活动放在国际贸易新形势下来审视,许多问题便可迎刃而解。
欧洲大约于1300年开始了商业革命,两个世纪后,海外探险航行十分有力地刺激了商业革命,西班牙和葡萄牙都想在对东方贸易中占一席之地。这些航海探险和建立殖民地帝国所产生的后果几乎是无法估价的。首先使局限在狭隘范围内的地中海贸易扩展为世界性事业,航海大国的船只在历史上首次航行于“七大洋”(西方的习惯说法),其次是商业额和消费品种类的大量增长。葡萄牙航海家发现了绕非洲好望角的欧亚直接航路之后,导致了1520年葡萄牙使节与中国的第一次正式交往,当他们的贸易要求遭到拒绝之后,便游弋于中国沿海。
英国历史学家博克瑟(C.R.Boxer )在追述这一段历史时说:“对于葡萄牙人来说,与中国的贸易是非常宝贵的,不经过一场斗争就让他们放弃这一新兴的、前途无量的市场是绝对办不到的。故而在随后的三十年内,佛郎机(Frank的音译,十字军东征以后, 近东人概称西欧人为“佛郎机”,此名随阿拉伯商人传到印度、中国。——引者)继续游弋于中国沿海,他们有时在地方官员的默许下进行贸易,有时则完全不把地方官放在眼里。由于最初是在广东相当严厉地执行那道明王朝禁止其贸易的诏令,葡萄牙人便将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向较北面的沿海省份——福建与浙江,他们在那里隐蔽、无名的诸岛屿及港湾内越冬。在那些暂时的居留地中,最繁盛的要数宁波附近的双屿港,以及位于庞大的厦门湾南端的浯屿和月港。……从中国载籍中可以清楚地看到,1521—1551年间频繁出没于中国沿海的那些葡萄牙走私商人得到了急于要与其交易的中国各阶层人士的广泛同情和支持。”[23—P292~294]
博克瑟的说法是可信的。葡萄牙人从1524年起,在中国东南沿海闽浙一带进行走私贸易,他们落脚的宁波甬江口外的双屿岛(今普陀县六横岛)便是一个大规模走私贸易的据点。海上走私集团首领许栋、王直、李光头(即所谓“倭寇”)从葡萄牙人手中贩买从非洲、东南亚、欧洲带来的货物,以及先进的火器(用以对付明朝官军),葡萄牙人则购买中国的生丝、丝绸、瓷器、棉布、粮食,每年交易额达三百万葡元,绝大部分以日本银锭支付。双屿成为当时葡属东方殖民地中最富庶的一个商埠,葡萄牙商人以此为基地展开对中国与日本的贸易。正如田中健夫所说:着眼于中国贸易利益的葡萄牙人,在广东方面进行的走私贸易形式,在北方沿海以出会贸易的形式继续进行,这样,葡萄牙人的走私贸易从广东逐渐向漳州、泉州、宁波方面展开。宁波附近的双屿港和福建漳州的月港,成为走私贸易的中心地。葡萄牙人在中国中部的进出,一度成为中国海商的仲介,和南下的日本商人势力发生接触[24—P183]。
过分敏感的明朝政府把上述现象一概视作“倭患”,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任命朱纨为浙江巡抚兼福建军务提督,查禁倭寇,革渡船,严保甲,搜捕奸民,严禁泛海通番、勾连主藏之徒,并且调动军队把双屿岛基地彻底捣毁。据说在双屿岛上的天妃宫十余间、寮屋二十余间、大小船只二十七艘被毁。朱纨此举引起闽浙一带仰赖海上走私贸易的势家大姓的极大反感,遭到朝廷中闽浙籍官僚的攻击,迫使朱纨罢官回籍,不久就含愤自杀。朱纨为官清正,这样的死法未免有点可惜,其悲剧就在于,他根本不明白在新的国际形势下,海上贸易已是大势所趋,海禁政策是不合时宜的,堵塞不如疏导。与耶稣会士关系密切、热衷于促进东西方交流的徐光启很清醒地指出:朱纨“冤则冤矣,海上实情实事果未得其要领,当时处置果未尽合事宜也”[18]。朱纨的过激措施,反而使东南海上走私贸易走向了另一极端,即谭纶所说的“私通不得则攘夺随之”。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明朝政府首次把王直集团骚扰沿海地区称为“倭人入寇”。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王直吞并了另一海上走私集团,成为东南沿海独步一时的领袖,由于向政府要求通商遭到拒绝,便劫掠浙东沿海。由此也就展开了嘉靖时期的所谓御倭战争,其对手便是横行海上的王直。
在此之前王直曾向政府请求开海禁、允许与日本开展正常贸易。他说:“窃臣直觅利海商,卖货浙福,与人同利,为国捍边,绝无勾引党贼侵扰事情……为皇上仁慈恩宥,赦臣之罪,得效犬马微劳驰驱,浙江定海外长涂等港,仍如广中事例,通关纳税,又使不失贡朝,其主各为禁例,倭奴不得复为跋扈,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者也”[25]。因为政府背信食言,王直才决计报复,僭号称王[6](P404~405)。他先称净海王,后改称徽王。据《筹海图编》与《汪直传》称:“参将俞大猷驱舟师数千围之,直以火箭突围去,怨中国益深,且渺官军易与也。乃更造巨舰联舫,方一百二十步,容二千人,木为城,为楼橹四门,其上可驰马往来。据居萨摩洲之松浦津,僭号曰京,自称徽王,部署官属,咸有名号。控制要害,而三十六岛之夷,皆其指使,时时遣夷汉兵十余万,流劫滨海郡县,延袤数千里,咸遭荼毒”[26]。
很显然,王直集团在日本建立根据地,又从日本出发来骚扰东南沿海,明朝官方便把这支武装力量视为倭寇。王直手下确有一些日本人,但起主导作用的始终是王直。正如王守稼所说:“这批‘真倭’大多数受王直海盗集团雇佣,王直一伙、以财物役属勇悍倭奴自卫……王直一伙在倭寇中的组织和领导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大量史料证明,历史的真实情况似乎与以往流行的说法相反,嘉靖时的‘真倭’,反而倒是受中国海盗指挥,处于从属、辅助的地位。”[5]这一点, 连指挥平倭战争的总督胡宗宪及其幕僚也不得不承认,他们编纂的《筹海图编》字里行间不时流露出事实真相:
——“(王直)倾赀勾引倭奴,门多郎、次郎、四助、四郎等为之部落”;
——“初,直自列表之败,而之日本也,居五岛之松浦,僭号徽王,频岁入寇,皆直之谋,其党承奉方略,辄以倭人藉口,故海上之寇概以倭子目之,而不知其为直遣也”[26—卷八、卷五]。
鉴于这种背景,我们不由得钦佩万历时福建长乐人谢杰在《虔台倭纂》中,对倭寇原由分析的高明。至少以下几点是值得注意的:
第一,成为中国大患的“倭寇”,其实多是中国人——“倭夷之蠢蠢者,自昔鄙之曰奴,其为中国患,皆潮人、漳人、宁绍人主之也。其人众其地不足以供,势不能不食其力于外,漳潮以番舶为利,宁绍及浙沿海以市商灶户为利,初皆不为盗”;
第二,由于政府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粤闽浙沿海民众海上贸易的生路受到遏制,由商转而为寇——“嘉靖初,市舶既罢,流臣日严其禁,商市渐阻,浙江海道副使傅钥申禁于六年、张一厚申禁于十七年,六年之禁而胡都御史琏出,十七年之禁而朱都御史纨出。视抚设而盗愈不已,何也?寇与商同是人,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始之禁禁商,后之禁禁寇,禁愈严而寇愈盛。‘片板不许下海’,艨艟巨舰反蔽江而来;‘寸货不许入番’,子女玉帛恒满载而去。商在此者,负夷债而不肯偿;商在彼者,甘夷居而不敢归。向之互市,今则向导;向之交通,今则勾引。于是海滨人人皆贼,有诛之不可胜诛者”;
第三,政府推行政策的偏颇是导致倭患愈演愈烈的根本原因——“初但许栋、李光头等数人为盗,既则张月湖、蔡未山、萧显、徐海、王直辈出而称巨寇矣!初但宫前、南纪、双屿等数澳有盗,既则烈港、柘林、慈溪、黄岩、崇德相继失事,而称大变矣!初但登岸掳人,责令赴巢取赎,既则盘据内地,随在成居,杀将攻城,几于不可收拾矣”;
第四,归根结蒂,倭患根源在于海禁太严——“推原其故,皆缘当事重臣意见各殊,更张无渐,但知执法,而不能通于法之外;但知导利,而不知察乎利之弊,或以过激启衅,或以偏听生奸……闽广事体大约相同,观丙子(万历四年)、丁丑(万历五年)之间刘军门尧诲、庞军门尚鹏调停贩番,量令纳饷,而漳潮之间旋即晏然,则前事得失亦大略可睹也。已夫,由海商之事观之,若病于海禁之过严”[27]。
※ ※※ ※
末了,对“嘉靖大倭寇”还得再说几句。其一,戚继光、俞大猷在平倭战争中崭露头角,战功显赫,后人对他们表示敬仰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求证于史实,他们从事的并不是一场抵御外患的战争,而是一场平定内乱的战争。其二,真正解决倭患的关键之举并非战争,而是官方政策的转换。面对势不可挡的国际贸易大潮流,战争不能解决问题,或者说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嘉靖大倭寇”的实质是海禁与反海禁的斗争,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政府必须放弃海禁政策。隆庆元年(1567年)明穆宗及其辅政大臣主张实行比较开放灵活的政策,取消海禁,准许人民航海前往东洋、西洋贸易,所谓倭患也就烟消云散了。其三,以此为契机,明末清初东南沿海的私人海上贸易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呈现出一片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大量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刺激了沿海地区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对此,全汉昇、百濑弘等已作出了精深的研究(注:参看全汉昇:《明季中国与菲律宾间的贸易》、《明清间美洲白银的输入中国》、《自明至清中叶西属美洲的中国丝货贸易》,以上三文均载.《中国经济史论丛》.(香港新亚研究院,1972年)第417—474页。全汉昇:《明中叶后中日间的丝银贸易》,《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五十五本第四分册,第635—649页。 全汉昇:《略论新航路发现后的海上丝绸之路》,《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二期,第30—37页。百濑弘:《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研文出版社,1980年,第15—19页,第39—65页。)
〔收稿日期〕 1999-9
标签:倭寇论文; 嘉靖论文; 明朝论文; 市舶司论文; 明朝海禁论文; 明朝历史论文; 中国古代史论文; 日本中国论文; 筹海图编论文; 王直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