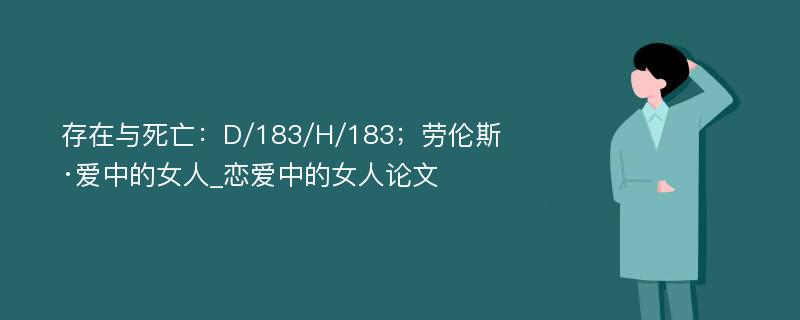
存在与死亡——读D#183;H#183;劳伦斯《恋爱中的女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劳伦斯论文,在与论文,恋爱论文,女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她死了倒好——这样倒能显出她的存在来。死亡使她变得更为实在了。
死没什么了不起的——没有比它更好的事情了。
我宁愿去经历它——我宁愿去经历死亡过程。
有属于死亡的生活,还有不属于死亡的生活。我向往爱情,它如同睡眠,如同再生,又像是刚刚降生的脆弱的婴儿。
这些话出自《恋爱中的女人》(Woman in Love ,1920)的第十四章,它们像小说的题记,揭示了作品的基本思考和情调。
写作《恋爱中的女人》的日子,是劳伦斯癫狂而忧愤的时期。身边的一切失败,已足以让劳伦斯跌入惶惶的绝望,那战争带来的巨大的死亡之网更罩住了劳伦斯不屈的躯体和灵魂。战争,这意味着他个人主观经历中和世界精神历史上的一个时期的终结。
大战的危机使劳伦斯萌发了对人类的莫名失望和憎恶,以致渴望正在衰颓的人类彻底死去。当人类在文明的扼杀下,成了“废弃的文字”,而死亡也成为当代最明确的现实的时候,那么以雄健的死亡去扫掉疲萎的死,“一直走向前去,使解体进入到死亡的黑暗,达到消亡的极点”,〔1〕似乎是言之成理的事情。 这种意绪也是与那个时代普遍滋生的毁灭感相通的。
正是在世界末日的阴影和可怖而狂乱的感觉的驱动下,劳伦斯制造了这部形同世界末日的小说。小说围绕着纯粹的毁灭性,开展了关于哲学、人生、情爱、死亡等领域的研讨,奔涌着一次次的死亡冲动。
这部作品的基调与《虹》全然不同。《虹》是毁灭加完美性的作品,而《恋爱中的女人》的创作主旨则建立在“我们已经在死亡中选定了我们的退化,而不是最后的完满”这样的准则之上,因而它是纯粹的越陷越深的孤独中孕育出来的毁灭性图示。“死亡”、“腐朽”这类字眼鬼魂般缠绕住这部作品,引领着读者感受神秘而必不可少的死亡进程。
小说中,对死亡有着特殊敏感的古德兰相中的男友就是具有毁灭意义的杰拉尔德。作品交代杰拉尔德的图腾是狼,他本人冷冰冰的俊秀外表象征着北欧民族腐败的深度。杰拉尔德线条分明的北方人的躯体和一头金发,像是阳光在一闪之间照亮了的透明的冰层,他的流畅的血液像是带电的,蔚蓝色的眼睛里燃烧着热切冷峻的光。杰拉尔德总是白森森地如同幽灵伴随在古德兰左右,周身发散着一种缺乏生命活力的美。
这是劳伦斯以往小说中所没有的性格。年轻的煤矿主杰拉尔德统治着积满黑尘的冰冷严酷的矿区。这矿区令经过它的古德兰感觉是在“通过一阵破坏性的浪潮,那浪潮是由成千名精力充沛、有几分发呆的下层社会矿工的存在掀起来的;它冲击到大脑和心脏,唤醒了一种致命的欲望,一种致命的无情。”就是这样的地方,却让古德兰体味出“一种污浊的美”,“里面有一种热烘烘的混浊的诱惑力”。这矿区更让具有强力意志的杰拉尔德热情满怀、激动不已。他向往的是在同自然环境的斗争中不折不扣地实现自己的意志。他此时的意志就是要有利可图地从地下采出煤来。他要同物质、同大地和地下蕴藏的煤较量一番。他头脑中唯一的念头是,对地上的无生命物质发动攻击,把它降服在自己的意志力之下,为了这场同物质进行的战斗,人就必须有完美的工具。这是一种机械装置,它在工作中是那样精妙和谐,代表了人类独一无二的意志;通过它不懈的重复运动,就会不可抗拒地、无情地实现一个目的。杰拉尔德想要建成的正是这种在机械结构中的无情的原则,它几乎像宗教热情一样鼓舞了他。他,这个男人,能够干预一种完美、恒定、像神一样介于自己和物质之间的工具,并去制伏物质。有两个对立面——他的意志和地球上与之对抗的物质。在这两极之间,他能建立起表达自己意志的东西,使他的权力具体化,并建成一种完美无缺的了不起的机器,一种制度,一种秩序井然的活动和纯粹的机械重复;这是无限的重复,是永恒的和无止境的。在把完美协调的纯粹的机器原则贯彻于纯粹、复杂、无限重复的运动的过程中,他发现了自己的永恒和无限。
不幸的是,杰拉尔德奉行的这种非人的机械原则,不仅整治了被大机器工业吞没的矿工,也统治了它的信徒的灵魂,使现代机构文明的化身发生了严重的变化。杰拉尔德由此变成了一个精神空虚、感情枯竭的人。一种莫名的恐惧时时会袭上他的心头,使他半夜惊起,顾影自怜,害怕有朝一日他会精神崩溃,变成一堆无用的东西,只会在黑暗中发出含糊不清的声音。他在这种空虚与恐惧中越陷越深,到后来只有三样东西能使他兴奋起来:毒品的麻痹、伯金的安抚和女人的陶醉。在《死与爱》一章中,杰拉尔德正是怀着填补失落、排遣恐惧的需要,黑夜从阴森森的教堂墓地潜入古德兰的闺房。
杰拉尔德与古德兰的第一次做爱,出乎意想地疲弱,那股死气始终追随着他,尽管情欲在炽燃,但是生命已经耗尽,而且他的大脑还因之遭到毁坏,让他的男子汉的头颅垂倒在女人胸间,彷佛在想象中再次进入母腹。
他又几下子脱掉外套,扯松领带,解开了衬衫的前胸饰钮,每一颗饰钮上都镶着一粒珍珠。古德兰倾听着,张望着,希望没人会听到上了浆的亚麻衬衫的刮擦声,它劈啪作响,就像是在开手枪。
杰拉尔德是来剖白心迹的。古德兰听任他用双臂搂住自己,把自己紧紧抱在怀中。杰拉尔德在她身上找到了无限的解脱,又把自己那受到压抑的邪恶和蚀人的死气全部倾注到她的身体中。他又成为完整的人了。这真妙极了,棒极了,简直是奇迹。这是他生命不断再生的奇迹,对此的了解使杰拉尔德迷失在一阵解脱和惊异的狂喜中。古德兰从属于他,接受了他,把他当成一个盛满致命烈药的容器。她在这场危机中已无力抵抗,心中满怀着由肉体摩擦而来的可怕的狂热。在从属于人的狂喜中,在剧烈的痛楚中,她接受了它。
……
而古德兰呢,她就是伟大的生命力的源泉。杰拉尔德崇拜她,她是母亲,是构成一切生命的物质。身为孩子和男人的杰拉尔德接受了她,使自身又完整无缺了,纯粹的肉体的他几乎要死掉了,但古德兰乳胸中流溢出的神奇温柔的东西又弥漫于他全身,浸透了他遭到毁损的干枯的头脑,如同医病的琼浆,又像是慰解人的温柔的生命力之流本身;它竟如此完美,杰拉尔德似乎又一次得以在母腹中沐浴。
杰拉尔德的头脑受到伤害,枯萎了,脑体组织像是全毁了,他还不知道自己受到了怎样的伤害,不知道自己的机体组织——也就是脑组织怎样毁灭于死亡的腐蚀性的洪流中,而此刻,古德兰身上流溢出的治病的浆液通过了他全身,他这才知道自己已经被毁到了什么地步,活像是内部组织因霜冻而涨裂的一株植物。
他把自己坚硬小巧的头颅埋在古德兰的胸怀中,用两手按住她的双乳贴在自己脸上。古德兰颤抖着的双手也抱住了他的脑袋,紧贴在胸前不放。杰拉尔德已进到极端亢奋的状态中,她却依然十分清醒。可爱的创造生命的暖流涌遍杰拉尔德全身,他像是在子宫中做着有关生育的沉沉一梦。
凭借社会地位和漂亮的表面,在外在现实中不可一世的人物,拥有的就是这等虚弱的内核、荒芜死寂的灵魂。连营造生命的辉煌瞬间,都不能赋予他力量,人类存在的悲哀状便可想见。
古德兰与杰拉尔德相辉映,代表着的也是那种在无意识中竭力寻求死亡的现代人类。让古德兰目迷的是尽头像在地球的中心处的峡谷、延伸到永恒封闭的空间的雪原、直入云霄的积雪的石壁。这样的景地让她恍惚出神,感觉总算到了自己的地方,像是水晶遗失在了白雪之中。杰拉尔德引诱古德兰的,也是与这样的景观相匹配的死亡气息。在《水上游园会》那章,杰拉尔德爬进小船时,引得古德兰心中狂喜的就不是有热气升腾的生命景象:“哦,他的大腿有多美、多迷人呀,爬过船帮时,它们似乎还在白幽幽地闪着微光。这使古德兰魂魄出窍,恨不能马上去死。”
杰拉尔德对古德兰来说不只是一个男人,而是一种化身,象征着生活中一个伟大的阶段。当杰拉尔德已经透进了她心灵的所有外层空间,并让她有力量应对之后,杰拉尔德的所谓局限也就暴露了。对古德兰来说,杰拉尔德对死亡的浸入不够彻底,他还在内心中依恋其他人和整个世界,无法摆脱对诸如德行、正义、情欲、理想等人间事物的依附。因而古德兰要去探寻新世界的亚历山大,可是并没有新世界,也没有男人了,有的只是生物,像洛克那样可鄙的最后的生物。这似乎正对古德兰的心思。在她的意识里,世界是完蛋了,剩下的只是个人内在的黑暗,自我的感觉,神秘的恶魔似的分裂摩擦运动,以及生气勃勃的生命机体的瓦解。
古德兰明白,在内心世界的极深处,洛克与万物是隔绝的,对他来说,既没有天堂,也没有尘世和地狱。他不承认有什么忠诚,对一切都无所谓。他是独立超群的,由于同其他所有人分离,他自身就是绝对的。这种更为绝对的与人世相弃绝的态度,把古德兰吸附到了这个带着苍蝇般的恶心劲的纯否定的啮齿类小动物身边,让杰拉尔德成为他的手下败将,并受冥冥之中主宰历史进程的天意的安排,葬身于古德兰所热望的冰雪峡谷之间。
对于古德兰,能够满足消亡的意愿,投入永恒的死亡和冷酷的腐朽,实在还是人生最好的选择。
她太清楚了,肉体不过是表现了灵魂,完整的灵魂的变形也就是肉体的变形。除非我坚定意志,把自己从生活的节奏中解脱出来,平心静气,清静无为,了断尘缘,在自己的意志里得到超脱。可是比起这种单调的一再重复的生命来,最好还是去死。死就是和不可见的万物一道遨游。去死也是一种快乐,是顺从比已知世界更为伟大的事物的快乐,那更为伟大的事物就是纯净的未知世界。这是一种快乐。而麻木不仁地活着,被隔绝在意志活动的小圈子里,如同一个超脱了未知世界的物体那样活着,却是可耻的和不光彩的事情。死是光明正大的。在空洞呆板的生命中有着十足的可鄙。对于灵魂来说,生命的确可以是可耻的和不光彩的,而死亡却绝不是耻辱。死亡本身像无限空间一样,是我们所玷污不了的。
……无聊乏味的生活,没有内在的涵义,没有任何真正的意义。生活有多么肮脏啊,现在活着对灵魂又是怎样一种可怕的羞辱啊!而死去却是何等地清静和崇高!人再也不能忍受这种没有价值的悲惨而乏味的生活带给人的耻辱了。人可以在死亡中得到正果。……在生命中没有值得寻觅的东西——这在所有国家所有民族无一例外。唯一的窗口就是死亡。人可以满怀感情地瞧向死亡那浩大阴暗的天空,就像他在学童时代从教室窗口向外张望,见到外面自由自在的大千世界一样。而人现在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他知道灵魂只是这肮脏庞大的生命大厦中的一个囚徒,除了死亡,别无它计从中逃脱。
……
死是多么美丽、崇高和完美,盼望它又有多好啊。在那里,人可以洗掉在这个世界沾上的所有谎言、耻辱和污秽。这是一次彻底的清洗和令人愉快的身心恢复,是去向未知的、确切无疑的和不会降低人身分的世界。毕竟,只有在完美的死亡的前景里,人才是富有的。这样盼望纯净的死亡是与人性相左的,又是最令人高兴的。
如果说,劳伦斯的《虹》追寻的还只是克尔凯郭尔式的孤独个体的精神个体,一种单独自我的存在状态;那么他的《恋爱中的女人》则已陷入了恐惶、厌烦、忧虑和绝望的人类痛苦的深渊。温暖友好的外界是消失了,生活的色调淡薄了,人与世界之间隔着一层奇特的幕布。人没有可以依附的东西,绝对地孤独,被异己的力量包围着、挤压着,进入了彻底的虚无。要命的是,这种虚无被描绘成“存在”的最真实的表现,原生的实在,人生的最基本的内容!人只能在混混沌沌的虚无中堕入一种“愿做自己的绝望”。而这种绝望产生的原因,就在于“自我”不能靠自己达到永恒和安全。既然作为精神上的表现的绝望,与人的内在的永恒性有关,而人又是一个由上帝创造的,介于有限与无限、自由与必然、暂时与永恒之间的综合体,那么人就永远无法解除他心中的永恒成分,解除他对天国的企盼,就像古德兰小姐大彻大悟地把趋向死亡视为生命完整过程的一个阶段,追求个体完满的最终手段。
劳伦斯,一个那么洞悉生命、纵情生命的作家,竟如此冷静地写下弃绝生命的鸿篇巨制,不管他本人对这类趋向死亡的人物持赞美还是批判态度,对这类人物的倾心探索本身就透露了在那种压抑人的时代、社会氛围下,作家对生存本身的一些本质性的看法。
尽管在《虹》之后的每部小说中,劳伦斯好像都在扮演着一个宣告人类末日到来的预言家,但是,劳伦斯的骨子里不可能是一个绝然冷漠的弃世论者,他依然是个带有浓重的浪漫风情的幻想家和实践者,他渴望创造的欲望与渴望毁灭的欲望同样强烈,劳伦斯的毁灭是一种过渡,否定虚假的生存是为了求得真实的生存,是通过彻底毁灭现有状态,让旧的人类完全死去,从而使新的生命能在纯粹中诞生。
古德兰和杰拉尔德的爱情关系就带有存心经历腐朽的自毁性,情欲的摩擦性活动招致的全然的消耗,引发肉体与心智的销毁。而《恋爱中的女人》刻画的另一对两性关系的代表厄秀拉和伯金,则由完美的性关系而走向再生。
伯金也对世界进行死亡的判决,他把人类称作一棵死亡之树,指望人类从世界上一扫而光,他相信,死亡是对旧事物的否定,死中蕴含着再生,一个新的世界必将在毁灭的废墟上建立,一个新的生命必将在旧我死亡之后诞生。“在你能了解肉欲现实之前,必须先彻底堕落,堕落,隐入无知无识的境界,放弃自己的意志力。在能够生之前,你必须先学会毁灭。”为着人的新生和世界的新生,伯金开始对两性关系的理想模式探索,企望通过高扬人的本性、欲望、感性、直觉,“回归到生命的源头,回归到原始人类的初始状态。”伯金的思想状态和行为方式是劳伦斯型的,劳伦斯本人在进行改革社会的种种构想时,也是当仁不让地把调整两性关系作为最大的前提。不仅如此。“我们可以把伯金的信仰列成表格,并可以一一与劳伦斯自己的理论相对应,无论是他关于世界末日即将到来的理论,关于种族,关于互补的创造与消亡的流通的理论,还是他关于所谓“超越爱情”——“行星般均衡的真正婚后关系,有张力而没有摩擦,有精神而没有知觉的理论,都可以在劳伦斯那里找到影子。”〔2〕当然,在小说中,伯金也时常处于被讥讽、 批判的地位,这表明劳伦斯思想体系的矛盾性。
在《恋爱中的女人》里,伯金不是平白无故地把思绪突然从消亡这个主题转到与厄秀拉建立一个灵魂均衡的婚姻关系的念头上来,他是把这种婚姻当作对消亡的抵制。
伯金认为,世界是由神秘的结合凝聚在一起的,这就是人们之间终极的联合——是一种契约。这种直接的契约就是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契约。伯金憎恶那种把自身幽禁在排外的小圈子里的传统婚姻,觉得它缺乏更广泛的生活,也没有更进一步的结合。伯金希望男女自身都是单一的个体。他相信两性结合,但不愿意性欲比其他欲望高出一头,他把性行为视为人体机能的一种过程,而不是把它看成是圆满的境界。因为在这之上,他还向往进一步的结合,在那种结合中,男人有其独立的存在,女人也有自己独立的存在;那是两个纯洁的生命,每一方都使对方获得了自由,就如同一股力量的两极彼此保持着平衡,又像是两个天使,或者是两个恶魔。伯金说,这是创造的规律。人必须把自身永远同别人结合在一起——这并不是失去自我——而是在神秘的平衡和完善中获得自我——就像一颗星星同其他星星保持平衡一样
劳伦斯是彻底的。这种彻底贯彻在他对一切生命现象的感知,当然也包括最让劳伦斯费心思的情欲。在小说中他借伯金之口批判一位与古德兰同属一条衰颓战线的赫麦恩妮女士:激情和本能——你确实想要它们,但那只是经过头脑在意识中要。一切都发生在头脑里,发生在你颅骨的下面。你并不想当一头野兽,而只是要观察自己的动物本性,从中寻求精神上的刺激。你以为那些本性纯粹是处于从属地位的——比最墨守成规的唯理智论还要颓废。因而你的激情是一种谎言。你根本就没有真实的躯体,没有隐秘的感官的生命躯体。你对情欲不感兴趣,有的只是个人意志。而情欲,它不是别的,那是一种实现——是在实现头脑中所不能有的真正隐秘的知识——那种隐秘的下意识的存在。那是一个人自我的死亡,但同时又产生了另一个人。这种知识在血液里,当精神和已知世界沉浸在黑暗中时,一切都必须离去,必须被淹没在其中。然后你才会发现自己是在一个摸得着的黑暗躯体里,是一个恶魔,只有如此,才能进入到更深的、作为存在的深层中去。
古德兰和杰拉尔德的肉体关系的失败,也在于停留在情欲的表层的恣意放纵。古德兰想得到的,无非是像罗马祭酒女神,获取心理上的享乐,一种主观上的肉体满足。杰拉尔德尽管在女人身上找到了最惬意的解脱,但是仅就女人这个意义上说却又微不足道,他感到在肉体亢奋之前,自己先需要头脑方面的刺激。
被劳伦斯肯定的厄秀拉和伯金这一对,才是毫不犹豫地突进了更深的存在。
与激情中的古德兰捧着杰拉尔德的脑袋全然不同,厄秀拉是去摸索伯金的大腿后面,两侧肋腹的下方,他的脊背,因为她觉得正是在那里,她才真正找到这个男人的神秘而充沛的生命之流。(我们知道,这一位置正是劳伦斯尊奉的脊柱神经的所在地。)
伯金站在炉边地毯上打量着她,瞧着她那一朵花似地向上仰望着的脸。那是鲜嫩明亮的一朵花,熹微的曙光映照着花朵上的露珠,闪烁着迷蒙的金光。他挂上一抹浅淡的笑意,好像除去每人心中默默无语的愉快的花朵,世界上就没有语言了,两人微笑着,为对方的存在、那种纯净的存在而欢欣鼓舞。他们并不费心琢磨这种存在,甚至也不了解它,伯金的眼睛带点儿嘲弄味地眯了起来。
如同在一道符咒的魔力中,厄秀拉被奇异地引向了他。她跪在伯金面前的炉边地毯上,两臂抱住了他的腰,脸贴在他的两条大腿间。财富!财富!对一笔无价之宝的感受把她压倒了。
“咱俩是彼此相爱的。”她快活地说。
“岂止是相爱。”伯金应和道,低下了闪光的脸,神情安闲地望着她。
无意之中,厄秀拉敏感的手指顺着伯金大腿后面摸过去,追循着那里的某种神秘的生命之流。她发现了某种东西,某种妙不可言的东西,它比生命本身还要奇妙。它是伯金生命运动的奇异的神秘所在,就在那里,在大腿的后面,在两侧肋腹的下方。它是伯金的隐秘之处,是存在的本源,就在大腿根向下的地方。在那里,她发现伯金是神之子的一员——和在开天辟地时一样。他不是男人,是不同于男人、高于男人的东西。
这是最终的解脱。厄秀拉有过情人,也见识过情欲,不过这既非爱情,也不是情欲。这是人的女儿又回到了神之子的身边。这些陌生的超人的神之子,他们原本在世界的开端处。
伯金站在厄秀拉面前。厄秀拉把手展开放在他的大腿后面,仰望着他,脸成了闪烁金光的令人眼花撩乱的一团。伯金俯视着她,眼睛上方是明亮饱满的额头,如同一顶王冠。厄秀拉娇美得像是在他膝前开放的一朵鲜嫩妙极的花朵。她是一朵天堂的花,超脱了女人气,是那样一朵光耀夺目的花。然而,伯金的心绷得紧紧的,里面还有什么东西没有放开。他不喜欢这样的蹲伏,不喜欢这样容光焕发——不喜欢所有这一切。
厄秀拉两手抚摸着伯金腰部和大腿的线条,抚摸着他的脊背,浑身烧透了由他激起的活生生的邪恶欲火,这是她从伯金身上解放出来,又引到自己身上的一股邪恶的电流般的情欲洪水。她构成了一种丰富新奇的循环,那是往来于两人之间的一种新奇的情感电流,它是从肉体上最黑暗的电极中释放出来的,形成了完美的回流。这是一股从伯金奔向她的邪恶的电火,把两人淹没在一片宁静和心满意足之中。
“亲爱的。”厄秀拉喊道,抬脸向着伯金,嘴和眼睛在狂喜中大张着。
“亲爱的。”伯金应道,弯下腰去吻她,不停地吻她。
在伯金屈身向她的时候,她将双手合拢在伯金丰满浑圆的腰间;她似乎是在触碰邪恶的神秘所在的最敏感的部位,那才是肉体上的伯金。她在下面眼看要晕倒了,伯金俯在上面也快支撑不住了,对两人说来,这是完美的死去,是同时出现的最难以承受的接近,是妙不可言的直接满足带来的充实;它压倒一切,从生命力最深的源泉中迸涌而出,从人体最阴暗奇特的生命源泉的极深处涌出,从腰的后面和底部涌出。
静默中,奇异丰富的暗流掠过她,泛滥开来,冲走了她的理智,顺着她的脊柱汹涌而下,到了膝盖,过了脚面。这是一股陌生的洪流,荡涤了一切,使她脱胎换骨得以重生。在这之后,她感到挣脱了束缚,在情感舒畅和自我完善中自由自在了。于是她站起身来,冒冒失失地冲伯金傻笑着,伯金就站在她面前,脸上放光,活生生的一个人;厄秀拉的心几乎要停止搏动了。伯金完整陌生的身躯就立在那里,其中有着神奇的源泉,比她过去想像的和已知的要更为神秘有力,也更令人满意;啊,这是最终的神秘的、肉体方面的心满意足。她原以为没有比男人的阳物更深的源泉了。而现在,瞧呀,从男人躯体的迷人的柱石上,从奇异妙极的肋腹和大腿根处,从比阳物更为神奇的更深的处所,竟涌出了无以言喻的隐秘和丰饶的东西。
接着在一个漆黑一团的夜晚,舍伍德森林一片长满小草的圆形空地里,厄秀拉和伯金完成了进入完整生命的实践。
夜色纯净,斑驳的树影活像是别的什么夜行动物。伯金把一块小地毯扔到蕨草上。在涤心荡虑的沉寂中,他们坐了下来。树林中传来微弱的声音,却没有骚乱,没有那可能出现的骚乱。世界处于一条陌生的禁令之下,神秘的新事物随之而来了,两人脱掉衣服甩在一边,伯金把厄秀拉拽向自己怀中。他发现了她,发现了她那永远不会让人瞧见的纯净的肉体,肉体上还闪动着朦胧的微光。已经失去常态的他拚命压抑住自己,用手指触摸着隐藏在夜暗中的她的裸体;这是沉静的手指在抚爱沉静的肉体,是神秘夜色中的一个躯体覆盖在神秘夜色中的另一个躯体之上,夜幕下的男人和女人,他们彼此见不到对方,用理智也无法了解对方,只是靠了手的抚摸才探到了对方活生生的肉体。
厄秀拉也渴望着他,触摸着他,并在触摸中达到了无以言传的交流的极境。那是黑暗,是精妙,是生动的沉默,是一件意味无穷,可以一再给予的礼物,是完美的接受与屈从,是神秘的事物,是永远无法知晓的现实,是意识永远达不到的生机勃勃的肉欲的现实;它留在意识之外,是黑暗中的沉静精致的活生生的肉体。是神秘莫测、实实在在的肉体。她的欲望满足了,他的欲望也满足了。因为双方在对方心目中都一样,是已经无从追忆的极其动人的事物——是摸得出的神秘真实的肉体。
厄秀拉和伯金的性爱场面的描述,很有生殖器崇拜的味道,而这正是不折不扣的劳伦斯原则。劳伦斯曾倡导:生殖器意识是所有真正温柔、真正美的源泉。温柔和美将把我们从恐怖中拯救出来。文明的巨大灾难是对性所怀的变态的仇恨,现代男人和女人深层的心理疾病就是直觉官能的病变和萎缩。劳伦斯说,在我们这个时代,人的生殖器官是僵化的、疲惫不堪的,这个干涸的生殖器官无法使我们重新诞生,生命之树已经枯萎了。我们的生命被抑制、被束缚。现在,有些人转向黑暗之泉,有些人转向光明之泉,人们变得疯狂,完全失去自制,于是大混乱开始了,一切都四分五裂。绝望中的劳伦斯萌生出新的观念,或许首先应该使一切进一步恶化,而后才有可能到达新的时代,或许腐败和破坏是一种前进的方法,在腐败中仍有神灵的内容,在腐败所具有的柔软而闪光的淫奢中,在爬行动物湿软而令人战栗的狂热中,有神性的标志,腐败为我们推翻那些已经死去的形式。通过更深地陷入腐朽,我们或许能冲出这个虚伪的宇宙,让一切重新开始,以至能最终回到生命的本源中去。用不着考虑恋爱关系是“摩擦性”的,与衰朽之流流向相同,会越来越深地导向死亡的领地。劳伦斯的朋友默里对劳伦斯有最深刻的体悟:“劳伦斯先生的最终完美是一种堕落,他的所谓进入另一世界,其实是进入地狱,而他的全胜则是惨败。”如此,以性策略拯救世界的尝试,当然落实在以男性为主导的生殖器的运作。人类该踏踏实实地回归到有生气且真正可爱的生殖器的自我和生殖器的意识中去(这一观点是《查太莱夫人的情人》中令世人关注的性爱场面描写的理论根据),并且这种回归必须依赖能够健全本能的性爱经历。
毫无疑义,劳伦斯理想的完整的男女之爱是双重的,它既是精神的,又是肉体的;既是融为完美的和谐,又是绝对的两性摩擦。肉体之爱确实是毁灭性的,但彻底的毁灭中包孕着全新的再生。在同一分爱中就该同时拥有甜美的心神交融和激烈自豪的肉体满足。如此才能形成完美的生命节奏,形成世上最伟大最完整的感情。
这也是圣灵的法则,是完美无缺的婚姻的法则。每个生者,都在寻找这种结合。每个男人都从自己最深切的愿望开始,希望在他自己和另一女人之间建立完美的婚姻关系,达到一种将使他获得充分满足和表达出存在的完整性的境界。伯金和厄秀拉就实现了这种再生的寓言。他们走出了杰拉尔德似的雪谷,融入了温暖的意大利南方。
伯金和厄秀拉身上印有很深的劳伦斯和弗丽达的印痕。当然按照弗丽达的母亲的说法,劳伦斯笔下的女性都有弗丽达的影子,不过,厄秀拉的情感气质似乎与费丽达更为接近。而伯金愤世嫉俗的情绪,固执玄虚的理论以及对婚姻爱情的偏激态度,就更是劳伦斯哲学理念的形象化了。
从小说《虹》开始,劳伦斯的创作方法有了明显的改变,一种变幻莫测的神秘主义的象征流贯其间,随处可见的象征推进着情节进展,折射出人物之间关系的微妙变幻以及人物潜在心理的意向。也就是说,象征在劳伦斯的许多重要作品中(诸如《虹》、《恋爱中的女人》、《查太莱夫人的情人》)不单纯是手法,而且是结构的因素,性格的因素,作品内容的因素,因而也就是作品的灵魂,是开启劳伦斯小说艺术的钥匙。
在这类用象征意象包装的作品里,一个情感经验的意象就是一个象征,它可以唤醒情感的自身及原动力自身,达到挖掘人物深层心理和小说哲理内涵的目的。
《恋爱中的女人》全书几乎被意象象征包容,由意象象征联缀。取自劳伦斯所錘爱的自然之中的一系列意象——树林、马匹、月亮、黑夜、墓地、雪谷——的跃动,提示着人物情绪的状态,使读者从这些暗示性极强的、赋有不可知神力的意象象征中捕捉特定情境的潜流,感悟由不可逾越的象征物控制下的人物心理上的搏斗厮杀。
劳伦斯显然是善于紧张气氛的心理描写大师,他的具有代表意义的象征描写都是使人物进入不断加强的紧张、对峙、不可逆的危机窘境。尽管劳伦斯重要作品的主要人物和事件常常出自他本人及周围亲友的生活经历,但是他的描述手法却是想象力十足、才气十足的,无与伦比的象征思维为他的作品创造出深邃、神秘、玄奥和难以企及的风范。
在劳伦斯的作品中,还有一个让劳伦斯深入骨髓、标榜完美的情爱关系实现的情境,和考察人生存在的实在性与否的超级象征,那就是“黑暗”。劳伦斯的各色人物,有血性的无血性的,男性的女性的,有力度的苍白疲弱的,都知道仰仗这个“黑暗”。连杰拉尔德那么智性的人都明白“把灯吹掉,那我们就能看得清楚点儿了”。他的人物无论是被劳伦斯寄予希望的,还是限于诅咒的,要想成就那种真正完满的男女之间的事业,都必须融入黑暗,否则即使是对情欲颇有悟性的厄秀拉也会在光的暴露下失败。
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注意,那就是劳伦斯在作品中不仅把月亮的银光视作女性的强大威力,也把它视为异教徒中执掌阉性的茜比利。在伯金奋力与水中月搏斗时,口里诅咒着的就是“该死的叙利亚女神”。他既在反抗女性给他施行的精神压力,又在与阉割分庭抗礼。当然,黑暗崇拜的根源主要来自劳伦斯的一整套关于建立和谐的两性关系、完成男女之间正常情感生活的思考。
劳伦斯认为的视觉总是意识的一种表现形式,视觉提示意识,令意识警醒。黑夜中的月亮、光亮等都是视觉的象征,这些有助视觉的事物,阻碍人类松弛地进入潜在的存在。我们看到,当厄秀拉把自己奉献给那个闪着光的月亮时,她就不能拥有和进入存在的黑暗。视觉意识使她热情冷却,遏制她失却理智。我们也记得,热恋中的厄秀拉与安东在黑夜的沙丘中猛地看到了光辉四射的月亮时的惊恐万状,厄秀拉只见眼前一片白,月亮像一个圆形的炼钢炉门一样,火光闪闪,从里面射出一派强烈的月光,照遍了海洋上的半个世界。那是一种令人眼花撩乱的可怕的白色的光。这光,导致了厄秀拉与安东那次幽会的彻底失败。
这就毫不奇怪地解释了厄秀拉对有关光亮的一系列抱怨了。“这些愚蠢的光亮,”厄秀拉在她那阴暗的傲慢之中,暗暗对自己说,“这愚蠢的、人为的、自我夸大的市镇正散发出它的光亮。”有了一个更强大的、曾经接触到那个黑暗的自我的厄秀拉,心灵完全懂得也根本不在乎那处于人为的光亮之中的世界会发生些什么。由于沉入过黑暗,她便以为整个世界只是在次要的意义上存在着,而她的存在却是绝对的。从此,那存在于黑暗中和黑夜的骄傲之中的离奇的分割力量,便始终没有离开过她。
劳伦斯崇拜象征人世间可知的和不可知的各种意义的黑暗,把它奉为无法逃避的神秘力量,认定真正意义上的男女之爱只能在真实的黑暗和不可知的情感意识中默默地进行。劳伦斯只信奉在全然黑暗中的两性触摸,纯粹的不依赖于意识的直觉探寻,觉得非如此不能把情爱中的男女导向真正幸福的彼岸。他所要求的意境就是《虹》中第十五章描绘的:“他们就这样在那至高无上的黑暗的亲吻中战栗着,这亲吻已经同时战胜了他们两人,使他们屈服,把他们合成了那流动着的黑暗的一个充满生殖力的核心。这是一种无边的幸福,这是一种使那充满生殖力的黑暗具有核心的过程。那容器由震动而趋于粉碎,于是意识之光跟着熄灭以后,便只有黑暗统治着一切,便只有了那无法述说的美满。”
就是在这样的黑暗庇护下,在意识完全退隐的状态,在只存有黑乎乎的潜意识和单纯的肉体面前,《恋爱中的女人》中的厄秀拉和伯金终于获得了一次至高、完美的交合。小说特意写道,那是一个乌云压顶、漆黑一团的夜。
这就是说,劳伦斯的“黑暗”是一种生命的黑暗,黎明前的黑暗,是成就血的支柱和血的深谷黑暗。
与此相反,他的作品中凡是出现白色集聚的地方,必然是在提示一种毁灭和死亡。(当然,劳伦斯作品中也不断出现黑色与死亡相连的情况,印证到劳伦斯本人在《男人要工作,女人也一样》的短文中所说的:“在已经确立的过去阶段的内部,光明已经深入了黑暗,未来已经孕育成熟,黑暗被光明拥抱着,开始与结束混合在一起。”在这里,黑暗与光明、生命与死亡的描绘的结伴出现,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想想杰拉尔德一身雪白的躯体、周围永不消散的闪闪白光和最终接纳他的白色冰峰,再联系到《儿子与情人》中的米丽安如何以全副身心扑向那朵朵白花——她的花,而米丽安恰恰又是一个缺乏生命力和性感的人物,我们就能比较容易地意会劳伦斯作品极爱出现的黑、白两色的涵义了。
《恋爱中的女人》是标志着劳伦斯创作高峰和最高文学成就的作品,其中蕴含的丰富的哲学思考和情感韵致,以及全新的象征思维和心理分析的叙述方法,都是劳伦斯后期作品和当代许多大红大紫的作家们所无法企及的。
注释:
〔1〕《二十世纪艺术精神》第181页。
〔2〕弗兰克·克默德:《劳伦斯》第102页,三联书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