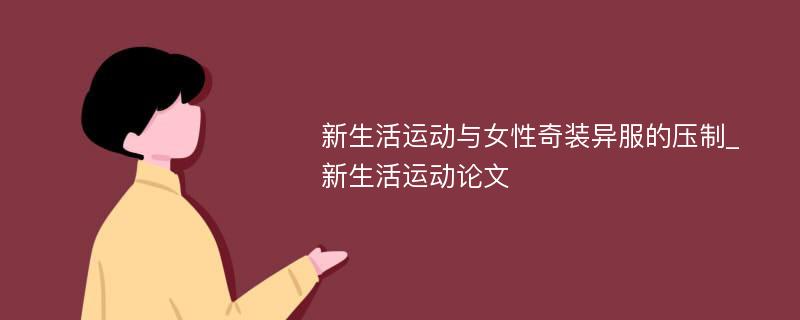
新生活运动与取缔妇女奇装异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奇装异服论文,新生活论文,妇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新生活运动史的研究逐渐引起海内外学人越来越多的关注,其着眼点主要偏重于政治、文化层面,较少关注新生活运动对女性的规定和要求、女性地位的变化以及女性对新运的感受等问题。全面抗战爆发前,在新生活运动的推行过程中,依照蒋介石的授意,国民政府内政部及一些省市政府曾以强制方式取缔妇女奇装异服,触及到女性生活最基本的层面。当时社会舆论沸沸扬扬,反响不一。对新生活运动中这一颇具象征意义的事件,学术界迄今只有片段的论述(注:涉及取缔妇女奇装异服的论著,主要有陈贻琛《国民党新生活运动拾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江西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总第12辑),1983年;东山尹《韩复榘与山东的“新生活运动”》,《文史精华》1999年第4期;肖自力《陈济棠》,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由于此事不仅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人们对于新生活运动的评价,而且折射出国民政府在社会文化生活方面的基本立场和态度,很有探讨价值。本文就几个问题略作申论,以就教于同好。
一、禁令的出台
服饰变化,往往是社会风气俭奢的晴雨表。19世纪中期以来,由于海禁开放和通商口岸的相继设立,近代西方的物质文明步步渗入,各种洋货源源而来,冲击和占领着广大的中国市场。在号称“东方巴黎”的上海,各大百货公司供应着世界上几乎所有最新最时髦的商品。而且,美国好莱坞和欧洲电影大量传入上海,使西方的摩登生活、流行风尚广为传播。随着欧风东渐,尤其是1920年前后的新文化运动鼓吹人格独立与个性自由,国人的思想观念与价值取向发生了显著变化。在所谓“畸形”发展的大都市中,一些男女崇尚摩登,男士西装革履,女子则珠光宝气,争奇斗艳,衣服的式样,一年数变,花样翻新。
受西方风尚的影响,妇女服装日趋大胆开放。以旗袍为例,20年代末,旗袍开始在上海等城市流行,其特点是宽大、平直,下长盖脚;1928年,受欧美短裙风的影响,旗袍的长度缩短至膝盖处;1930年,西方短裙之风继续影响旗袍,旗袍摆线又上升至膝盖以上;1933年左右,旗袍的叉越开越高,几近臀下。[1]这些大胆变化引起老派的责难,指为有伤风化。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的对华侵略不断升级。加上1929年以来的世界经济大危机,列强疯狂地向中国倾销过剩产品,以转嫁危机,日本货更加排山倒海般地输入中国市场,导致国货销路萎缩,民族工商业纷纷倒闭,失业问题严重,同时又进一步刺激着都市中弥漫的享乐风气。这在社会上引起了各种反弹。
1932年12月,自称“中国布衣会”发起人的程淯向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递交请愿书,请“颁定女子制服式,通行全国”。他说:今日我国“中上等社会女子,在马路所见,竟无一人用完全国货造衣”,而且“女子之服装,奇邪已极矣。夏不能蔽体,冬不能御寒”,请规定一种制服,“长短尺寸,毋许违反”。[2]
1933年8月,广东省财政厅长因该厅女职员“力尚时髦,容饰则曲发染甲,抹粉涂脂,衣饰则着绿穿红,争奇炫异”,认为“有失庄严”,故于10日发出一道诰诫式的通告,“饬女职员自重”,“力戒浮靡,洗净铅华,并须穿用土布衣服”。广州市社会局长也宣布“禁止裸足短裳”,“对于一切奇异服装,均一律禁止”。[3]
1933年12月,上海市商会为实现“国货救国”的目的,联合其他团体公定1934年为“妇女国货年”[4],据说理由是“服用国货,固无分男女,可是服用大权,却完全在妇女手里”,因为“女子的消费力,要比男子们高上几倍,不论在化妆品或服饰品方面”。[5]
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1934年2月,新生活运动发端,提倡节约和服用国货,得到各地方政府的积极响应,山东、江苏、湖南等省政府纷纷厉行布衣运动。浙江省政府决定“自4月1日起,全体职员一律改用国货制服”,并且出台“取缔女子妖冶服装”办法。[6]然而,时人观察到:“以俭朴为宗旨的新生活运动虽风涌全国,但是一点也没有影响到太太小姐们爱漂亮的心,奇装异服之依然甚炽,便为显明的实例”[7]。
上述反差明显的现象,引起新生活运动最高指导者蒋介石的关注。据1934年6月7日的南昌快讯:先是,蒋委员长以“南昌妇女妆式、头发服装之大小长短尺寸等,应由警察速定一个标准令行,如不遵行者,应由警察负责取缔”,手令江西省政府遵办。江西当局奉令后,即迎合蒋介石的意见,认为“近来本市妇女服装,炫奇斗巧,不但妨害卫生,而且有伤风化,际此厉行新生活运动之时,自应及时纠正”,迅礼速于1934年6月6日拟定了《取缔妇女奇装异服办法》,其主要内容为:
1.总则:为取缔妇女有伤风化及不合卫生之奇装异服起见,特订定本办法。2.衣着方面:旗袍最长须离脚背一寸;衣领最高须离颚骨一寸半;袖长最短须齐肘关节;左右开叉旗袍,不得过膝盖以上三寸,短衣须不见裤腰;凡着短衣者,均须着裙,不着裙者,衣服须过臀部三寸;腰身不得绷紧贴体,须稍宽松;裤长最短须过膝四寸,不得露腿赤足,但从事劳动工作时,不在此限;裙子最短须过膝四寸。3.装束方面:头发须向脑后贴垂,发长不得垂过衣领口以下,长发梳髻者听;禁止缠足束乳;禁着毛线类织成无扣之短衣;禁止着睡衣及衬衣,或拖鞋赤足,行走街市。4.推行办法:本办法之推行,先自南昌市起。女公务员、女教员、女学生及男公务员之家属限半个月后实行;其他各界妇女,一个月后实行;本办法由省会公安局抄录,并制就传单挨户分送;妇女衣着装束不遵守本办法者,由岗警加以干涉,如有违抗者得拘局惩处。[8]
江西当局将拟订的《取缔妇女奇装异服办法》呈请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南昌行营核示。可能考虑到条款过于苛刻,难以实施,南昌行营将原定标准放宽,删除了服装具体尺寸的规定;对于违规妇女的惩罚办法改为“由岗警随时善为劝导”;并加上“暂行”二字,确定自7月16日起实行。7月10日,南昌行营令江西省政府按修改办法切实执行。[9]
南昌实行《取缔妇女奇装异服暂行办法》后,上海市商会闻风而动,要求国民政府行政院“规定女衣式样,取缔奇装异服。对于男女衣料,以采用国货为原则,俾资改变风尚,日趋简朴”。对此,了解南昌方面动态的行政院作出了正面回应:“值此实行新生活运动,奢靡之风,亟宜取缔,奇装艳服尤应禁止”。1934年7月3日,行政院令交内政、实业两部,分别拟具办法,呈复核办。[10]
依照行政院的命令,内政部“九月六日令各省民厅首都警厅等机关,取缔奇装异服,对于服料,尽量采用国货”[11]。11月15日,内政部正式制定了《取缔奇装异服办法》(注:要点如下:长袍不得拖靠脚背,领高不得靠颊骨,袖长最短齐肘,衣叉须近膝盖,短衣须着裙,胸腰臀不得绷紧,裤裙长须过膝,短发不得垂过衣领,女公务员禁止烫发,染指甲,禁着睡衣拖鞋上街。妇女衣着不遵守办法者,由岗警干涉,如有反抗,拘局罚办。见《内政部规定取缔奇装异服》,1934年11月16日《益世报》。),作为全国妇女的服饰标准。该办法参照了南昌《取缔妇女奇装异服暂行办法》的主要条款,并添加“女公务员禁止烫发,染指甲”的规定,而惩处办法则恢复原样。
总括来说,导致禁令出台的直接原因大体有三:一是都市中摩登女性的服饰趋向欧化,大胆暴露,被认为有伤风化,不合乎礼义廉耻;二是摩登女性崇尚奢华,以用外国货为荣,导致金钱大量外溢,既影响国民经济,又违背了新生活运动崇尚简朴、提倡国货的原则;三是民间人士、社会团体以及地方政府对妇女服饰的不满乃至干涉。不过,从蒋介石的手令到江西省政府、国民政府内政部制定的取缔条款来看,着眼点显然更侧重于维持社会风化,反映了当局社会文化生活政策的态度和立场。
江西省会南昌远不如上海等大都市繁华,却成为取缔妇女奇装异服之嚆矢,当与其为“剿共”大本营和新生活运动策源地密切相关,由此可见当局此举还有更深层的用意。
1930年代初,南京国民政府面临内外交困的统治危机。日本自侵占东北后,又向关内咄咄进逼;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苏区不断壮大;国民党内派系林立,争权夺利;地方军阀割据称雄,混战不已。此外,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思想文化领域呈现出多元化趋势,起源于西方的各派新思潮,几乎都传入到中国,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日益广泛,新旧冲突激烈。而社会上出现了一些借名自由实行放纵的极端现象,大都市中的一些女子“误解自由,纵情享乐,专爱时髦,兢尚摩登”[12]。
蒋介石反复权衡利弊,决定“攘外必先安内”,以“安内”为“攘外”的必要前提和准备。为了排除异己,巩固政权,达到“安内”的目的,蒋介石一面亲自指挥对革命根据地的“围剿”,一面采纳幕僚杨永泰提出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谋略,进行“政治剿共”。1934年2月19日,蒋介石本着“攘外必先安内,革命必先革心”[13]之旨,在“剿共”前线的江西省会南昌发起了一场以复兴固有道德文化,提倡礼义廉耻为核心的新生活运动,以便在实行军事统一的同时,进一步实行政治文化统一,以儒学控制民心,清除共产主义等思想学说的传播。(注:参见关志钢、赵哲《试论新生活运动之缘起》,《深圳大学学报》第11卷第2期,1994年5月。)
蒋介石对新生活运动寄予很大期望,视为“复兴民族”的基础。按照他的计划,新生活运动要在大处着眼,小处下手,先从改革国民衣食住行的日常生活习惯做起。蒋介石认为,一般中国人的生活,是“污秽、浪漫、懒惰、颓唐的野蛮生活”,是不合理的“鬼生活”[14]。因此,“我们现在先从南昌起,开始一种新生活运动,我们要使南昌所有的国民,个个人都过整清简朴,一切能合乎礼义廉耻的新生活,可以做全国人民的模范”。[15]1934年3月,在《新生活的意义和目的》的讲演中,他进一步强调:“现在我们提倡新生活,就是要使人人能够实践礼义廉耻,就是先使他们从衣食住行日常简单容易的生活中开始做起。先使一个地方的国民日常生活,做到整齐划一的程度,然后推而至于一省,最后使全体国民一切精神行动,都能整齐划一。”蒋介石发动新生活运动的终极目的,就是要通过“军事化”的“整齐划一”,“使全国国民个个人能够共同一致,保种强国”,确实达到“全国总动员的程度”,[16]为由他领导的抗日作精神准备。
善于揣摩蒋介石意旨的杨永泰对“为什么要做新生活运动”也有一个总说明,他指出:中国的病根不在政治制度本身而在人心风俗的颓败,所以“革命必先革心,变政必先变俗”;而革心变俗最迅速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由外形训练促起内心变化”,外部的生活方式改变了,内在的精神自然会随之改变。[17]杨永泰之言,表明新生活运动就是要“革心变俗”,把礼义廉耻表现于衣食住行,通过“外形之训练,促进内心之建设”[18],最后统一国民思想,为集权统治奠定基础。
改变妇女的奇装异服,正是由外形训练实现内心变化的最佳入手,因此便成为当局推行妇女界新生活运动的重要举措。
二、推行过程与效果
自南昌取缔妇女奇装异服及国民政府内政部发布禁令后,南京、福州、济南、汉口、蚌埠、北平、广州等沿海沿江和内地的大中城市,先后颁布了相关办法。
首都南京响应较早。禁令内容与江西大同小异,而在妇女的发饰问题上,则有所“创意”。妇女的发型一度成为关注的焦点,也是源于蒋介石的一项指令。蒋介石手谕石瑛市长以及首都新生活运动促进会设法取缔妇女烫发,“最好定一办法,如已剪发之女子,发长不得过几寸,过几寸者,必须梳髻或戴帽”[19]。消息发表后,女人的头发成了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许多人对这项禁令提出质疑。由于妇女发式问题闹得沸沸扬扬,反响颇大,蒋夫人宋美龄特地出面转圜,她专就这一问题发表谈话:
新生活运动应从大处着眼,彻底改革我国人民生活之旧习惯与恶习惯,而为复兴民族之基础。关于禁止剪发烫发之事,外间颇多误解蒋委员长之真意者。蒋委员长前以妇女在国家社会家庭中所居之地位,极为重要,所负之责任,亦极重大,而近年以来,我国妇女颇多趋尚时髦为荣,以致生活行动多浪漫不羁者,影响国家民族复兴之前途,极为巨大,深觉有彻底改革之必要,务使我国妇女,能崇尚朴素,保持固有之美德。所谓提倡改革蓬发烫发者,其真意不外乎此,然而并非干涉与禁止也。是以今后对于推进妇女界之新生活运动,亦应深切体会蒋委员长之真意,务使大处着眼,矫正浪漫不羁之恶习,而代以淳厚朴素之美德。[20]
宋美龄的这段谈话是为了消除人们对蒋介石反对妇女烫发散发的反感,所以强调蒋的用意并非强迫干涉与禁止。自1927年12月与蒋介石结婚后,宋美龄即成为后者的得力助手,她不仅为蒋发动、宣传新生活运动出谋划策,而且身体力行,全力推动。(注:宋美龄是妇女界新生活运动的领导者。1936年2月,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根据运动发展需要,扩大组织,在总会内增设妇女指导委员会,指导全国各地妇女生活的改进,由宋美龄任指导长。)宋美龄曾在美国留学10余年,受西方文化的熏陶,喜欢洋装。但婚后因身为中国第一夫人,必须以身作则,所以改着旗袍,梳发髻,与蒋介石长袍马褂的形象相配合,可以说是标准的夫唱妇随。
与宋美龄的解释相对应,由蒋介石任会长的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也发出指示:妇女烫发,“费时耗财,影响风化,殊违新生活之旨趣”,但如果厉行禁止,严格取缔,恐怕事实上难免发生障碍,因此应“取劝告态度,启发一般妇女之自觉心”。如此办理,收效虽迟,但可持久,“一时毋庸严令制止也”。[21]不过,南京市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仍然以“妇女烫发,既不经济又碍卫生”,通令“理发业厉行新生活”,“禁止烫发”,从1935年2月1日起开始实行。[22]
烫发禁令颁行一年后,1936年2月5日的《中央日报》报道:首都新运会对于妇女电烫头发,违反新生活规律,屡次严令禁止,并订定取缔办法,通饬本市各理发店切实遵守。只因“日久玩生”,近时“妇女电烫之风复炽”。该会以新运总会现已迁来南京办公,“督饬厉行新运工作,更为加紧”,为了“彻底铲除恶习”,“对妇女烫发,尤为注重取缔”,即“再严查禁止,以符功令”。[23]接着,在2月13日,新运总会出面召集首都新运会、宪兵司令部和首都警察厅代表,会商“妇女推行新运”问题,决定“应从远大处着眼,以提倡妇女天然美德,造成简朴勤劳风气为鹄的,如烫发蓬发等项,既不经济,又不美观,凡有识之妇女应自动起而改良,以免耗费无谓之时间与金钱,沾染奢靡之恶习”[24]。新运总会及南京新运会三令五申禁止烫发,反映其推行效果极不理想,禁者自禁,烫者自烫。
取缔奇装异服在南方的广州更加办得“有声有色”。“南天王”陈济棠的文化取向相当保守,对于取缔妇女奇装异服不遗余力。他认为“人心不古,世风日下”,为“改良社会风化,挽救世道人心”起见,特向广东政治研究会提议制定服装标准。经该会修正通过,函请省政府执行,省政府准函,饬省会公安局同广州市社会局负责办理。两局奉命,即发出布告及传单,劝导妇女界一律遵守,并组织女子宣传队,到各公共场所演讲。“讵行之已十数日,而市上穿着奇装异服,招摇过市者,仍触目皆是”。公安局长认为非强制执行,不能收实效,故令所属各分局,在各大马路满悬标语,大书“公安局取缔奇装异服,九月一日起强制执行”字样。[25]
1935年9月1日,省会公安局派大批休班武警,分赴市内各裁缝店调查,只要发现有奇装异服,一律没收焚毁。当天,女性衣着过于奇异者,“已尽行绝迹”,但“御蝉翼轻纱衬薄内衣者”仍属不少;违反得最多的标准则为“短袖”。广州市公安局为统一执行标准,让各界进一步明了具体要求,特联合市社会局及提倡国货会共同筹办所谓“日常服装样式展览会”及举行“服装标准巡行”。鉴于“仍有顽固女郎视公令为儿戏”[26],有碍当局执行,特拟就强制执行办法多项,分饬各公安分局长遵照执行。
然而,这次行动不久便不了了之。因为此项禁令的反对者“多具潜势力之人。令虽下,亦无切实执行,禁者自禁,穿者自穿”[27]。
1936年初夏,广东当局又一次开始采取强制措施。当局预先颁布了关于妇女衣着的标准,主要包括衫腰之阔窄、衫裙之长短以及衣袖是否过肘等几个方面。5月5日,省会公安局组织了30多个所谓“维持风纪队”,分途出发执行取缔,情形如临大敌。遇有衣着违反标准的妇女,即拘之上车运返公安局,在其衣袖上盖以“违反标准服装”字样的印记,并声明再犯时,则拘留惩戒。一时间,广州街头囚车载道,外出的妇女个个惴惴不安,“违禁”者受尽难堪的侮辱,反而败坏社会风气。旁观者每遇警察向妇女干涉时,“语多揶揄,且有资以为乐。即非穿违反标准服装之妇女经过,亦多言三语四,乘机轻薄”[28]。广州的一位漫画家老纪创作了一幅漫画《卓别林游广州后得到的笑料》[29],让美国喜剧明星卓别林变身为官方的检查人员,将衣着摩登的女子用车游街示众,引起众人围观起哄,以讽刺当局行事的荒唐。
较早取缔奇装异服的福州和汉口,效果同样不佳。1936年7月新运总会主办的《新运月刊》报道,福州近日时届夏令,“一般摩登妇女,每袒胸裸腿,穿着奇装异服,招摇过市,或徘徊公园,引人注目”。该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认为有损风纪,特由该会职员及各学校女教员、各机关女职员所组织妇女劳动服务团于每天傍晚出发,分为3组,对奇装妇女和颜婉劝,每晚被纠正妇女,均达数百人。[30]而汉口方面,湖北省新运会推行新生活运动,各项工作成绩斐然,“惟对妇女界同胞,所有改变服装规定者,尚未达到要求之鹄的,长此以往,殊影响工作之完成。刻特拟定取缔妇女奇装异服办法”,分函武汉两女青年会、妇女协会和省会妇女劳动服务团,请努力宣传,设法劝导实施。[31]
从上述各城市的推行情形来看,禁令均未达成预期的效果。禁令难以推行,大概与下列一些因素有关系:
首先,各级政府以行政命令对女性的生活方式强加干涉,完全超出了政府的职权范围。政府无法也无需为百姓制定衣着服饰的具体标准,高压政策只能收效于一时,而不可能长期维持。
爱美是人类天性,而美因时因地因人而异,没有固定的标准,服饰随之千变万化,如何选择,应属个人自由。虽然蒋介石声明推行新生活运动“重感化而不事强制,先指导而后纠察,纵有必须施行纠察者,亦应以公务人员及在校学子为限,而不及于民间”[32],但是没过多久,他就亲自下令对妇女的衣着装扮加以约束,开展了一场由官方主导、以行政手段强制干预妇女服饰的运动。对此,主张自由主义的胡适评论道:“我们不能滥用权力,武断的提出标准来说:妇女解放,只许到放脚剪发为止,更不得烫发,不得短袖,不得穿丝袜,不得跳舞,不得涂脂抹粉。政府当然可以用税则禁止外国奢侈品和化装品的大量输入,但政府无论如何圣明,终是不配做文化的裁判官的。”[33]对政府干预妇女服饰的举措不满之外,更借此表达对国民党加强思想文化控制的抗争。
政府强行规定女子的服饰标准,是对女性个人生活及装饰自由的粗暴干涉。特别是一些地方政府的取缔方式令人反感和气愤。如山西太原市公安局规定妓女一律佩带桃花章、烫发、穿高跟鞋,以与良家妇女有所区别[34];而广州、长沙违令的妇女,被警察以永不脱色药水或洗刷不掉的黑漆涂在手臂和腿上。这些举措很容易激起民众的公愤。
署名“养愚”者撰写了《为长沙妇女请命》一文,对妇女的遭遇深表同情。作者认为:新生活运动的真意究竟怎样,浅识的我们,是莫测其高深的;不过根据现行约法,“人民的衣食居住,得享受自由的权利”。“妇女服装本是一个很小很普通的问题,欲求改革,尽可由妇女自动研究办法;妇女以外的人,只有从旁善意劝导的份儿,决没有实行恶意干涉的权利”[35]。
广州市妇女协会对于当局制定的妇女服装标准提出强烈抗议,认为严重侵犯妇女人权,侮辱妇女人格。广东省女权同盟会还一再致函政府,要求“停止检查妇女服装”。虽然收效不大,但“足以表现妇女们不甘示弱的气慨”[36]。
其次,各级官员常常只是单方面强制老百姓遵守规定,而自己的家属以及有地位身份的女性却不受约束。不一视同仁,民众自然不会信服,推行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所谓奇装异服,主要是都市里少数有钱又有闲的摩登妇女的装束。这些妇女多为官僚、买办、富商的太太小姐,生活无聊,又无所用心,专在个人的装饰上用功夫,以争妍斗宠。
有人指出:奇装异服者大半都是有钱有闲的,同时她们也是有相当地位的人。例如广州警察干涉奇装异服女子,恰巧碰到个阔人太太,奇装异服未得取缔,而警察自己反受到处分。所以取缔奇装异服,简直行不通的![37]《新运月刊》上也有文坦率批评:“现在各地都在取缔奇装异服,尤其是广州和济南,还悬为施政禁令之一。然而在事实上,禁者自禁,而穿者自穿。寻其症结,虽然有不少社会的习尚力,然而提倡的人,也许便占了大半的原因。——尤其是闺阁中人,简直在取缔的标准以上呢。”[38]由此可见,对于真正奇装异服的摩登妇女,禁令不起作用。所谓“取缔”不过是一种“拿老百姓开玩笑的官样文章”[39]。
再次,奇装异服现象,有其发生和存在的社会根源。基础不变,女性的时髦和奢侈就不会终止,这不是人为的禁令可以奏效的。
女子奇装异服,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背景,“不是女子天赋人格的低贱,而是物质的环境驱使她这样做的”[40]。一方面,由于经济萎缩,都市萧条,失业人数增加,大批中下层的妇女,无法找到正常工作以维持生计,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去当娼妓或舞女、招待、交际花之类,“用浓厚的脂粉,妖艳的服装,尽量美化自身,以博得顾客们垂青”[41]。她们宁可节省饮食,而衣服不得不求华丽。另一方面,家庭妇女感觉到自己地位的危险,为要争回丈夫的恩爱,不得不用心力揣摩男子的喜好,装饰自己。鲁迅早在1933年4月就尖锐地指出:“民国初年我就听说,上海的时髦是从长三幺二传到姨太太之流,从姨太太之流再传到太太奶奶小姐”,这些家庭妇女“多数是不自觉地在和娼妓竞争,——自然,她们就要竭力修饰自己的身体,修饰到拉得住男子的心的一切”。[42]
妇女生活的两极化,都是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里女性地位可怜的表征。虽然经过20多年的女权运动,女子名义上获得了政治、法律、经济等方面的平等权,其实大多数女子并未得到经济上的独立与平等。而在经济问题没有真正解决以前,女子“还是做着奴隶,当着商品;因其是奴隶,所以不得不听主子的使唤,以图承欢,因其是商品,不得不装煌点缀,以求销售”[43]。因此,妇女的奇装艳服,“不是妇女们自己的罪恶,而是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所造成的必然的化物”[44]。而要消除这种现象,首先得根本改造产生奇装异服的社会根源,使妇女有做独立自尊的“人”的机会;若仅仅取缔妇女的服装,是舍本逐末,没有效果的。
上述情形没有改变,南京国民政府推行“取缔妇女奇装异服”的禁令难以奏效,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三、女界的反响
各级政府对妇女服饰的干涉,因触及女性生活最基本的层面,立即引起了一些知识女性的关注。她们在政治趋向上或许有异,但反应倒显得基本一致,为了维护女性的尊严,纷纷撰文发表意见和主张。
南昌取缔妇女奇装异服的新闻传开后,一位女性表示“叹服蒋委员长的一番盛意”:“当此国难关头,而注意到我们妇女界的服装与头发,且规定了式样及大小长短的尺寸,这种‘明察秋毫’的精神,确实难得!”她进而指出,“目前的当务之急,并不是妇女的服装与头发的问题,而是整个的民族解放的问题。”[45]这些言辞不仅反映了作者对当局的强烈反感,而且提请人们思考维持风化与民族解放孰轻孰重的重大问题。
随着取缔妇女奇装异服的推行,社会上各种歧视妇女、压迫妇女的守旧势力乘机抬头,复古空气弥漫全国。有位女性观察到:在广东当局禁止男女同泳后,更有人起而禁止同行、同食;南昌出现利用新生活运动的招牌,鼓励少女望门守节的奇谈怪论;赣、粤、闽、沪乃至首都等处,普遍禁止妇女奇装艳服;教育部还发布了中等女生着重贤妻良母训练的通令。她认为,这些现象足以表示“压迫妇女势力抬头”的倾向,并且质问“为了几个摩登妇女就值得这样开倒车吗”?[46]将取缔妇女奇装异服视为思想文化的倒退。
服装禁令的不合理,必然激起妇女界对新生活运动的反感。1936年7月,上海《妇女生活》杂志主编沈兹九在《妇女的新生活》一文中指出:“中国大多数妇女过的生活,一向都是地狱的生活,囚徒的生活,奴隶的生活。……现在妇女新生活运动,雷厉风行于全国,我们十二分地期望着:中国妇女真能从此得享受真正的新生活。然而根据新闻杂志的记载,以及口头的传言,则是某地因厉行长袖,忙煞了裁缝,某地因警察检验妇女内裤,至起纠纷。”沈兹九本来对妇女新生活运动寄予厚望,但事实却令她大失所望。她不禁质问“凡此种种,对于真正陷于水深火热中的姊妹,究竟给与了多少恩怨,多少害益”?[47]显然,她认为妇女新生活运动反映出来的结果,只是给妇女带来了伤害。
由于新生活运动中所谓妇女的新生活,不过是注意“袖子如何长,裤子脚如何短”的琐碎事情,“徒顾皮毛,吹毛求疵,给予人民不少恶劣的印象”,[48]使得妇女界对新生活运动的反应不积极,即使推行妇女新生活运动的工作者也有抵触情绪。女界对于取缔奇装异服的不满,使得一些地方的女性新生活运动团体在相关问题上夹在广大女性和新运总会之间,难以开展工作。
1936年6月,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为考核各地妇女新运推行的成绩,特派总干事管梅瑢赴南昌、汉口、长沙等地视察。管梅瑢在长沙视察工作时发现:“长沙妇女新运现仅有妇女新生活劳动服务团之组织,工作计划虽已订立,但未见诸实行。盖因当地妇女对于新生活不了解,且当地人士之心目中认妇女新生活运动只在于取缔奇装异服等事,致引起当地妇女对新生活之反感。”[49]为了推进妇女新运,管梅瑢与长沙市妇女界领袖谈话后,于7月14日约请当地女界领袖36人成立湖南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妇女工作委员会。其后,新运总会对粤汉线新运工作进行视察,在报告中谈到湖南省新运妇委会的情况:“实际工作甚少,且闻曾因取缔烫发及奇装异服事,与新运会意见相左,工作之无实际进展,此亦或为原因之一。”[50]这一方面固然表明湖南省新运妇委会有名无实,另一方面,也显示该会在取缔奇装异服问题上与新运总会存在分歧。
大多数知识女性在反对政府干涉个人生活的同时,也认为真正解放的女子应该有独立的能力与自尊的人格,不要盲目地追求时髦。
1935年7月,北平《独立评论》刊登了陈衡哲撰写的《复古与独裁势力下妇女的立场》,认为女子的私人生活,如衣服鞋袜,身体发肤之类,要“坚决的拒绝任何外来权力的干涉”。正因为如此,女子对于自身所负的责任也就格外地严重了,“对于自身的服饰与行为也就应该使它们更能与我们的人格符合,以引起外界的尊敬与同情了”。[51]既要抵拒当局干涉女子的私人生活,又强调女子的自重自爱。
1935年12月4日,《中央日报》刊登了一篇署名“静元”的《女子装饰平议》。作者针对当时社会上一些人对于女子的装饰打扮“痛心疾首,抨击笑骂,无所不用其极”的状况,表示“愿意就一个女子的立场上,心平气和地来说几句话”,提出三点:一是女子“不应将打扮修饰视为人生第一义”;二是美要“和谐”。女子的打扮装饰,必须与她本人的年龄、性情、身份等等相合;三是个人装饰要顾及社会情绪,应当“不扰乱社会的情绪”。而奇装异服的盛行,则扰乱了社会的情绪。因为这是一种病态的、畸形的追求,它藉赖一种不正当的力量去刺激人家、刺激社会的情绪。同时,因为中国的国民经济衰落,每一个人都应该使自己的生活简单朴素,不应再事奢靡浪费。[52]作者的议论比较客观,指出了女子应有的人生观、审美观及社会责任感。
1936年6月,在新运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召开的“谈谈奇装异服”的座谈会上,当谈到关于“衣服的标准”时,有人认为:“我们衣服的标准当以卫生,舒服,简单,整齐等为标准,不该专以奇形怪状的装饰引入注意。”还有人说:“本来我不反对人家穿奇装异服,以发展各自的审美观念。不过在目前的中国,有多少人没有饭吃,有多少人连衣服都没有穿,而只是少数有钱有闲的女子穿奇装异服,我是反对的。尤其是当这国难严重的时候,我们该埋头苦干,挽救国难,对于生活必需之衣食住行,当竭力简单,那有闲功夫来从事于个人外表的装饰!”[53]
由此看来,知识女性只是反对政府强制实行取缔奇装异服的手法及其背后的动机与负面效应,至于反对过分打扮修饰,提倡简朴的生活方式,则有一定程度的共识。
四、结语
1930年代以来的中国,内忧外患,经济衰落。新生活运动倡导传统的简朴美德,不无合理之处。不过,国民政府的种种长远目标,都以实现统一政令、统一思想的集权式统治,加强文化垄断和精神控制为前提,势必与五四以来的个性自由思想解放风气相抵触相冲撞。服装禁令虽有提倡妇女使用国货、挽救民族经济之意,新运总会以及各级政府更注重的是维持社会风化,显示了当局的文化保守取向。特别是社会旧势力随声附和并且进一步扩张其保守的一面,更遭到女性的抵制和舆论的批评,从而转化为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领域的进步与反动之争。在推行的过程中,各级政府不能恰当地区分公私,遵循法制,采取各种强制手段迫使妇女接受其硬性规定的服饰标准,施政范围超出清洁、秩序、卫生等属于公众生活的方面,行政执法直接干预简单、朴素、节俭这一类属于个人私生活的领域,使人民感觉压迫,令女性受到歧视,更加弱化了女性的社会地位。结果适得其反,不仅引起广大妇女的反感,影响整个新生活运动的推行,而且动辄将女性的穿着打扮上升为国家大事,视为影响“党国”兴衰的要素,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未免因小失大,避重就轻,甚至有故意转移视听之嫌,很难为公众舆论所接受。
服饰改革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既与一定的社会经济背景相联系,又与社会大众生活水准、审美观念的变化密切相关。在当时的中国,从某种意义上讲,奇装异服不仅是所谓“畸形”发达的都市女性趋慕新奇时尚的表现,而且与大多数妇女经济没有获得独立有很大关系。这方面的改革若想取得成效,既需要在生活观、价值观方面予以耐心的教育和引导,更重要的,是有待于民族的解放、国家的强盛、社会的进步,使妇女在政治上、经济上、人格上得到独立与平等,能够自由地决定那些本来属于她们自己权力范围内的事务,而不必由旁人或者政府来越俎代庖,说三道四。想仅仅依靠禁令来实现这一目标,当然是不合理,也是办不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