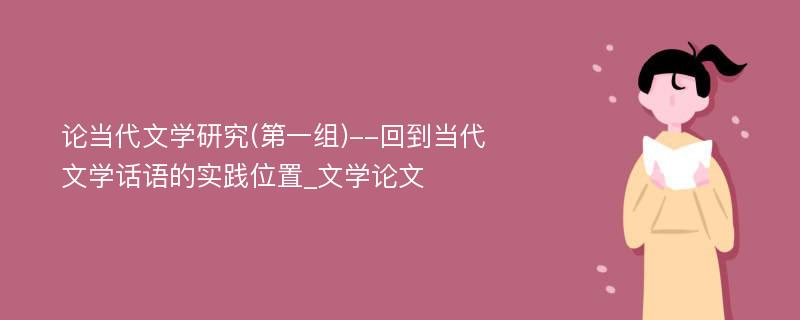
当代文学研究笔谈(一组)——重返当代文学话语实践的场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当代文学论文,笔谈论文,话语论文,场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403(2004)01-0074-09
“当代文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存在,我以为是一个无须讨论的问题。李扬曾经从知识谱系学的角度详细论述了“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学科互动的历史,我很赞同他的相关观点。我觉得,“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一直存在着互相“改写”的问题。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当代文学”改写了“现代文学”,而在80年代以后,则是“现代文学”在改写着“当代文学”。正是基于这样一个不断互相改写的历史,我认为现当代文学的学科建设在很长时期内是处于非学术状态的,并没有建立独立完整的知识体系和理论准备。对于“当代文学”而言,如何推进学科话语的成熟这一问题应该在争议中“浮出水面”。
五四新文化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始终是学科历史改写中两个显现的或者隐含的价值层面。在70年代的文学史和文艺思潮史著作中,已经建立起了以“1942年”为起点的当代文学史叙述框架,这样的思路其实与1949年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对“国统区”和“解放区”文艺的阐释是联系在一起的。在六七十年代,主流文艺思想的观点是,五四以来的现代文艺是“两种根本不同的文艺路线和文艺思想”斗争的历史,现代文艺运动的本质特征就是这种斗争,对斗争的描述与分析代替了对现代文艺自身演进历史的研究。新时期文学“回到五四”的种种想法,既是“拨乱反正”,又是回应西方现代性话语的最初方案。这样一种价值判断和选择,很长时期成为当代文学史研究中的主导思想。无疑,“五四”作为“现代中国”的思想原点是无法绕开的,但是,在用一个不断被现实重新解释、重新改造的五四来叙述“现代文学”的历史和确定“当代文学”的合法性,本身就是个问题。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并不会由于谈论了五四就获得一种历史感,也不会由于谈论了五四就获得了一种思想的高度,或者就具有了一把衡量当代文学的尺度。
五四新文化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文化之间的联系及差异其实是需要辨析的,而不能仅仅从“继承”了什么的申明来看由五四新文化到当代社会主义文化这一历史过程。在这样一个历史过程中,现当代文学史并没有一个不变的“现代性”,如果有,那也只是表面的。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过程中,“现代性”问题已经以另外一副面孔出现在当代中国社会和当代中国文学的话语实践中。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文化不仅是当代文学发生的语境,也是现代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建立、改造和重建的背景。所以,如果我们离开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文化来叙述当代文学史,就不可能获得“当代文学”的“当代性”。我并不赞同“文化决定论”,但我始终觉得,当代文学史写作和研究中的种种简单化的现象,与我们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实践意义和复杂性认识不够有关。可以这样说,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文化是与当代文学相关的最大“空间性”因素。在这样一个大的空间中,文学话语与政治话语及其他话语之间的纠缠与冲突变得特别复杂,当代文学的生产方式或者说当代文学的话语实践有了鲜明的“当代性”。和“现代文学”相比,“当代文学”与意识形态话语的关系,文学期刊与出版,作家与现实、体制的关系,作家与读者、批评家的关系,文学教育制度与经典的选择,中国文学等等都有了几乎是根本的不同。如果离开这一实际状况,只是用抽象的“五四”和空洞的“西方”来读“当代文学”,可能会离“当代文学史”越来越远。
事实上,在一些当代文学史著作的叙述中,一直存在“压缩”、“断裂”与“简化”的现象。譬如说,“十七年文学”在现在的文学史叙述中所占的篇幅与这段时期文学的实际价值明显不符,越来越多的文本和作家被逐出。而“文革文学”则长期被搁置。在通常的叙述中,新时期文学的发展有这样一个序列: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等。这样的叙述正反映了“现代性”思想的特征。但是,以“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为例,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些思潮之间并不构成时间的定义,并不构成一个单一的线性的文学史秩序;相反,思潮与流派常常是多元共生、冲突交融、必然又偶然。因此在强调时间性的同时,不能忽略文学史的空间性,需要在由时空构成的场所中,尽可能叙述和记录文学话语实践活动的全部复杂性。在不同主体的叙述中,在对同一对象的相同叙述和不同叙述中,我们会发现这种复杂性,会发现同一性之外的差异性,会发现文学话语和其他话语(如哲学话语、政治话语等)的互动。因此,在当代文学史研究中重返当代文学话语实践的场所,已经成为必要。(福柯《知识考古学》的中译本在解释思想史时用了“场所”这样的措辞,该书由三联出版社1996年出版)
针对当代文学史叙述中的压缩和断裂问题,我曾经提出要在文学史哲学的层面上纠正“非历史的观点”,在中断的缝隙中发现“历史联系”。这一想法所持的理论依据是恩格斯对“十八世纪的唯物主义”局限的论述:它不能把世界理解为一种过程,理解为一种处在不断的历史发展中的物质。这种非历史的观点也表现在历史领域中。在这里,反对中世纪残余的斗争限制了人们的视野。中世纪被看作是由于千年来普遍野蛮状态所引起的历史的简单中断;中世纪的巨大的技术进步,这一切都没有被人看到。这样一来对伟大历史联系的合理看法就不可能产生,而至多不过是一部供哲学家例证和插图的汇集罢了。恩格斯的这一思想为我们解释当代文学史的内在联系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论支点。而在另外一方面,我意识到只强调“文革文学”与“十七年文学”的联系,或者只强调“文革文学”、“十七年文学”与“现代文学”的联系还是不够的,在发现种种联系的同时,我们不能不正视文学史本身的断裂(不是文学史叙述中的断裂),这样的断裂特别是深层次的断裂,显示了文学史不同阶段的差异性,有时常常是因为有了这种差异性,这一阶段的文学才有了研究价值。所以,在研究“文革文学”的发生时,疏忽“历史联系”是一种偏差;如果正视了“文革文学”与历史的断裂,而不能发现“文革文学”本身的独特性同样是一种偏差。大而言之,我们在考察当代文学史时,需要看到“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文化”与“五四新文化”之间的联系与断裂。
在重返当代文学话语实践的场所时,面临着当代文学的历史文学问题。以“文革文学”研究为例,历史文献的整理与叙述是十分薄弱的。关于“文革文学”的历史文献大约有两类文本:第一种是“文革”时期的文本,有公开的,也有地下的,有官方的,也有民间的,我觉得民间这一块重视得还不够。今天我们看到的民间的这部分是很多以“大字报”、“上书”的形式发表的,有些是在当时的报纸上发表的,像遇罗克的文章;公开的就是像中央的文献、报纸上的社论、公开的出版物。第二种是关于“文革”的回忆。我觉得这些东西很有价值,这个价值不在于提供了多少史料,而在于它告诉了我们,一些“文革”的亲历者,在“文革”之后是如何重新解读“文革”的,真实反映了在今天当下的立场上,大家对“文革”的不同记忆。许多当事人在今天的语境下,对当时的记忆、解释已经作了许多的修正。因此,在作研究的时候,要把这两种文本参照起来。除了文献以外,我们对口传记忆材料时,涉及文献与记忆的真伪问题,包括一些文本产生的时间问题。在这一点上,我觉得福柯的话是有启发的:“历史的首要任务已不是解释文献、确定它的真伪及其表面的价值,而是研究文献的内涵和制定文献:历史对文献进行组织、分割、分配、安排、划分层次、建立序列、从不合理的因素中提炼出合理的因素、测定各种成分、确定各种单位、描述各种关系。”(福柯《知识考古学》,第一章,第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