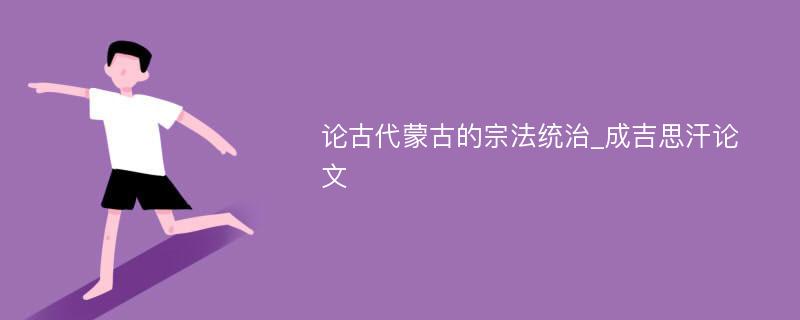
蒙古古代宗法统治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蒙古论文,宗法论文,古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8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281(2003)05-0010-05
一、“阿寅勒”个体游牧方式的出现与贫富分化的加剧
唐代蒙兀室韦为蒙古部先民。据《旧唐书》卷199《北狄传·室韦》记载,这一时期,包括蒙兀室韦在内的室韦诸部尚无君称,亦无汗号,但其部落首领皆“世管摄之”。公元840年,回鹘汗国灭亡,回鹘人大量西迁,蒙古草原地区政治势力衰微,室韦—达怛人便开始了入迁蒙古草原的过程。室韦—达怛西迁之前主要从事渔猎,亦有少量农耕;西迁之后因受突厥、回鹘人的影响而逐渐离开森林,进入草原,并向游牧经济转化。但仍有部分室韦—达怛人在山林中居住和靠狩猎、采集而生。因此,唐末五代之际的室韦—达怛各部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并不平衡。依其居地和经济文化类型,大体上可以分为“森林狩猎民”(即“林木中的百姓”)和“草原游牧民”(即“有毡帐的百姓”)两大类[1](P1-3)[2](P18-20)[3](P318-319)。但是,蒙古诸部统一前的半猎半牧经济生活仍在蒙古人中占有重要地位。他们“自春徂冬,旦旦逐猎,乃其生涯”[4]。不仅森林百姓“以射猎为生”[5](乙集卷19),而且草原游牧民亦过着“牧且猎”[6]的生活。不过,由于受到草原游牧民的影响,生活在森林中的蒙古人逐步转向游牧经济,“从事围猎的古代布里亚特狩猎民,也知道使用马”[7](P36)。公元11~12世纪时,“森林部落……有马供狩猎使用。”[7](P19)这种经济生活方式的变化,为蒙古人游牧宗法奴隶制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蒙古诸部统一前,蒙古社会处于大变革时期,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首先表现在阶级社会中的“阿寅勒”个体游牧方式逐步取代氏族社会时期集体游牧、共同驻屯的“古列延”游牧方式上。
“古列延”(gureyen)的含义较多,其产生的具体时间也不清楚,但研究者们一般认为它是氏族社会时期形成的,而且在阶级社会仍然存在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原始氏族制时期的人们往往以血缘关系结成较为持久、牢固的生产组织。“古列延”就是这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建立起来的社会生产组织。每个“古列延”的成员出于同一血缘。另一方面,由驯养野生动物的萌芽阶段过渡到游牧经济后,随着牲畜的不断增加,必然会产生出相应的生产组织,这是“古列延”产生的经济前提和必然性[1](P40)。“家畜的驯养和畜群的繁殖,开发出前所未有的财富的来源,并创造了全新的社会关系。”[8](P53)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剩余产品的增加,为私有制的产生提供了物质基础。蒙古族社会中的私有制产生于何时,史无明载。“然而,对畜群的私有制,一定是很早就已经发展起来了。”[8](P53)“在成文史的最初期,我们就已经到处都可以看到畜群乃是家庭首领的特殊财产,完全同野蛮时代的工艺品一样,同金属器具、奢侈品以及人畜—奴隶一样。”[8](P54)从《元朝秘史》、《史集》等史籍来看,其记述的内容多从以私有制为基础的个体家庭开始,介绍了自成吉思汗二十二世祖孛儿帖赤那起20多代个体家庭的具体情况,也反映了一些家庭的私有继承关系,表明蒙古社会至少在孛儿帖赤那时代已存在着个体家庭私有制了[9](卷1,卷2,卷3,卷5)[10]第一卷第一分册,P249-255;第一卷第二分册,P6-9)。
伴随着私有制财产的产生和发展,与私有制相联的财产继承、遗嘱制度、财产转让及掠夺抢劫等各种社会现象在蒙古社会中亦普遍存在[1](P50-54)。私有制的存在,加剧了为掠夺财产而进行的战争及因贫富分化而导致的阶级对抗和对立。在这种情况下,原有的“古列延”集体游牧方式逐渐丧失其经济意义,并开始向私有的“阿寅勒”个体游牧经济转化。与此同时,邻近汉族地区的汪古部、弘吉剌部等蒙古部民在农业民族的影响下开始转向定居[11](卷153)。蒙古人游牧方式由“古列延”向“阿寅勒”的转化及定居生活的出现,是其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同时也是其氏族制社会瓦解的重要标志。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蒙古族的氏族社会虽然可能在公元9世纪时已经瓦解了,但其氏族血缘组织却不同程度地存留了下来,直到成吉思汗时代乃至元朝时期仍有所表现。“阿寅勒”个体游牧方式的出现,是以私有制和阶级分化为基础的,并与个体婚制的家庭社会结构相适应。随着家庭作用的增强,以家庭为基础的“阿寅勒”个体游牧生活在蒙古社会中渐居主导地位。
根据《元朝秘史》(卷1)的记载,成吉思汗二十二世祖孛儿帖赤那夫妇“同渡过腾吉思名字的水,来到于斡难名字的河源头,不儿罕名字的山前住着”,还说成吉思汗的十二世祖“脱罗豁勒真伯颜……妻名孛罗黑臣豁阿,他有一个家奴后生……又有两个好骟马……脱罗豁勒真生二子”。这些记载,大致反映了当时蒙古人的个体家庭情况。9世纪后半叶,蒙古社会产生了“伯颜”(bayan,即“富翁”、“财主”之意)和“牙当吉古温”(yadanggi gu'un,“穷人”之意)等反映贫富差别的蒙语名称。当时的蒙古社会贫富差别和分化极为明显,洪钧《元史译文证补》卷1谓富者“牲畜遍野”;《元朝秘史》卷2说中等牧民“家财……尽够”维生;而该书卷1则说贫者因“穷乏”卖子易肉,即可窥见。这种贫富分化现象反映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中,便是产生为这些现象辩解的剥削阶级的宿命论,亦即“贫贱富贵,命也”[12]。这种“财产的差别,通过世袭显贵和王权的最初萌芽的形成,对社会制度发生反作用”[8](P111)。蒙古社会私有制的存在及“阿寅勒”个体游牧方式下的贫富分化加剧,导致了其氏族制的最终瓦解和游牧宗法奴隶制的形成。
二、国家政权的形成及其宗法奴隶制
公元12~13世纪间,“阿寅勒”个体游牧方式下的蒙古社会已分裂为以那颜(意为官人)贵族为统治阶级和以哈剌出(意为庶人、平民)及孛斡勒为被统治阶级的两大阶级。“随着分配上的差别的出现,也出现了阶级差别。社会分为享特权的和被损害的、剥削的和被剥削的、统治的和被统治的阶级。”[13](P145-146)阶级的出现及其矛盾不可调和的结果,便是早期国家的产生。
一般认为,蒙古早期国家始建于公元12世纪初期,其创始人为成吉思汗的三世祖合不勒汗(1101-1148)。合不勒汗为孛端察儿八世孙,其父亲、祖父均为蒙古诸部首领,曾祖父海都被“八剌忽怯谷诸民,共立为君”[12]。合不勒汗“在蒙古诸部中,他的[名声]昭著,很受尊敬。[合不勒汗]是自己部落和属民(atbá')的君主和首领”[10]第一卷第二分册,P42),辖蒙古全部,并在“忽里勒台”(即族众会议)上被推举为汗,蒙古至此始用“汗”号。1147年,鄂伦贝勒(即合不勒)自称祖元皇帝,改元天兴[14]。合不勒汗建立的初期国家政权被宋朝称之为“蒙古”,金朝则称之为“朦骨国”。合不勒汗死后,俺巴孩及忽图剌先后继承汗位。但忽图剌汗去世前没有提出汗位继承人,后来其侄儿也速该把阿秃儿(铁木真之父)统治了全蒙古。也速该于1171年被塔塔儿人所害,此后泰亦赤兀惕贵族集团内部发生了争夺汗位的斗争,导致了朦骨国的分裂。1189年铁木真重建朦骨国后,其内部的汗位之争已演变成汗国之间争夺蒙古草原统治权的斗争,因为蒙古部建立初期国家政权的同时,克烈亦惕、乃蛮、汪古等部也建立了自己的国家[2](P23-24)。不过,这些国家的政治体制基本上是氏族血缘组织与初期国家行政、军事“三位一体”紧密结合的宗法统治。
在蒙古初期国家政权结构中,那颜贵族及其权位高于那颜贵族的“汗”构成了蒙古社会统治者。他们不仅在政治上享有种种特权,“管着”“众达达百姓”[9](卷1),随意对百姓施发“号令”[9](卷2),而且往往世袭权位。《元史》有云:“海都殁,子拜姓忽儿嗣。拜姓忽儿殁,子敦必乃嗣。敦必乃殁,子葛不律寒嗣。“[12]虽然合不勒汗之后的汗位继承存在不同的说法,但基本上是在一个宗族之内传承,他们都是海都的后裔,“汗位只是从一个家系转到另一个家系”[1](P130)。与此同时,克烈部、乃蛮部及汪古部的汗位亦为世袭。这时的汗已成为凌驾于众人之上的最高统治者,但其始汗多由氏族部落首领演变而来。毋庸讳言,这种在家族、宗族范围进行的父系血缘的权位传递,带有明显的宗法文化特征。
正是由于汗成为凌驾于众人之上的统治者和汗位的世袭,才会出现那颜贵族为争夺汗位而进行的分裂、敌对和攻杀。“也速该辖尼伦各族,咸畏服之,然同族有隐忌者……族人如蝎。”[15](卷1上)泰亦赤兀惕部之塔儿忽台乞邻勒秃黑常与自己的同族人为敌[10](第一卷第一分册,P295-296),“诸部多苦其非法”[16](卷1)。其它各部同样存在这种现象:照烈惕部之塔海鲁被“族人忽敦忽儿章……杀之”[17](P14);“亦乞列(思)部人孛徒者,为火鲁剌(思)部所逼,败之……”[17](P60);而“弘里兀惕……与弘吉剌人和亦乞列思人同出于一根……彼此为长幼宗亲,但他们经常为敌,互相作战”[10](第一卷第一分册,P269);塔塔儿部彼此之间亦“发生过许多战争和冲突,他们经常互相屠杀,蹂躏和抢劫”[10](第一卷第一分册,P168)。不仅如此,这种争权夺位的残杀还发生在近亲之间。成吉思汗与撒察别乞、泰出均为合不勒后代,同属祖父裔孙,但后来成吉思汗率兵灭之[12]。乃蛮部太阳罕与不亦鲁黑罕“昆弟交恶,分国而治”[15]。忙忽惕部“者台那颜之父由于追随成吉思汗,被他的叔伯们所杀;他们还想谋杀当时还是个乳婴的者台”[10](第一卷第一分册,P199)。这种同门相煎的权利之争,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血缘亲属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氏族血缘组织在蒙古早期国家统治中不复存在。事实上,游牧民族的氏族血缘组织仍然存留在蒙古初期国家政权之中。
蒙古族氏族血缘组织不仅在其初期国家建立之后与行政组织紧密结合,而且还与其军事组织相结合。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诸部以前,蒙古地区虽无统一军队,但各部各有自己的军队。至合不勒汗时代,蒙古地区渐呈统一之势。忽图剌汗时,蒙古部的军旅由成吉思汗之父也速该统领。与此同时,蒙古地区几个较为强大的部落也有自己的军事实力,如乃蛮部“有一支庞大而精良的军队”[10](第一卷第一分册,P224),泰亦赤兀惕部也“拥有无数的军队”[10](第一卷第二分册,P23)。这种“保聚尤甚,众至数十万”[18]的军事力量发展的结果,必然会要求建立起相应的军事组织形式。
与其他游牧民族一样,蒙古初期国家的军事组织带有明显的游牧特征。他们自幼养成“勇悍善战”[5](乙集卷19)和“善骑射”[19](卷74)的社会传统,故有所谓“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12](卷98)之史载。“古列延”曾是蒙古氏族制时代的集体游牧方式,它后来虽为“阿寅勒”个体游牧方式所取代,但由于它仍具有集合各个个体家庭的协调和防护功能,因此便逐渐从游牧的经济组织发展演变成为一种军事组织形式。“所谓古列延是圈子的意思”,“在古时候,当某部落屯驻在某地时,就围成一个圈子,部落首领处于像中心点那样的圈子的中央,这就称做古列延。在现代(指成吉思汗‘十三翼之战’之时—引者注),当敌军临近时,他们[蒙古人]也按这种形成布阵,使敌人与异己无法冲进来”[10](第一卷第二分册,P112)。这在当时是一种十分重要的防御和进攻的军事组织形式。“其出兵,常在秋季,盖在当时马力较健。结圆营于敌人附近,统将居中。人各携一小帐、一革囊盛乳、一锅,随身行李皆备于是矣。用兵时随带一部分家畜,供给其食粮。”[20](P32)辽代时,札剌亦儿部亦曾以这种军事组织形式与契丹作战[15]。毋庸置疑,这种由集体游牧、经济组织演变而来的军事组织,不可能不带有氏族血缘组织的宗法特征。
事实上,这种已演变为军事组织的“古列延”形式不仅存在于蒙古诸部统一以前,而且在成吉思汗乃至他的继承人时代仍然存在。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诸部的过程中,“古列延”这种军事组织管理形式渐趋完善。在成吉思汗与札木合进行的“十三翼之战”中,成吉思汗“按照万、千、百人点数”[10](第一卷第二分册,P112),“大集诸部兵,分十有三翼以俟。已而札木合至,帝与大战,破走之”[12](卷1)。后来,其军事组织分工更细。《元史》卷99《兵志》有云:“元制,宿卫诸军在内,而镇戍诸军在外,内外相维,以制轻重之势,亦一代之良法哉。”行军作战时既分中、左、右军,又别前锋、后援、前哨、后哨[9](卷3、卷4、卷5、卷6、卷7、卷8、卷10)。此外,还“严整军马”,严明号令。“自将帅以至士卒,虽无敌时亦当筹备,一闻号令,立即起行”[15]。“未战之先,号令诸军:……若军马退……不翻回者斩。”[9](卷5)
在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诸部的过程中,汗及那颜贵族的“那可儿”(即伴当)成为军队的骨干力量,以致后来成吉思汗的护卫散班均有那可儿作随从,但那可儿的数量有着严格的等级限制。“若是千户的子……带伴当十人,百户的子……伴当五人,牌子并白身人子……伴当三人。”[9](卷9)那可儿早日充当主人的“从者”[15]“出入侍从”[11](卷2),并为主人牧管牲畜[9](卷4),战时则“多敌行……做前哨”[9](卷3)。此外,结交安答也成为一种联合盟友和扩充军事势力的重要组织形式。安答结交一般建立在彼此利益一致的基础之上,如王罕与也速该是由于王罕被其叔菊儿罕败而“奔于烈祖。烈祖亲将兵逐菊儿[罕]走西夏,复夺部众归[王]罕。汪罕德之,遂相与盟,称为按答”[12](卷1)。如果彼此之间产生矛盾和利益冲突,安答关系则难以为继。成吉思汗与札木合之间的安答关系的破裂,即为明证。这种依靠安答关系建立起来的军事组织协作虽不稳定,但它“使没有血缘亲属关系的各部扩大了联系,加速了各部成员彼此混杂的过程,进一步打破了氏族部落界限”[1](P77),另一方面却又促进了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的结合。
三、宗法奴隶制向宗法封建制的过渡
成吉思汗征乃蛮部之前,曾将其部属编组为千户,任千户长进行管理;又从千户长等各级官员子弟和平民中挑选80人组成宿卫军,另选70人组成散班,封了6个扯儿必官统领,并建立了分四番轮流宿卫的军事制度。
1206年,铁木真在斡难河源头召开忽里勒台,诸王群臣共上尊号称他为“成吉思皇帝”[12](卷1),此后,成吉思汗开始建立封建统治秩序。他将千百户制度普遍推行于蒙古各部,以千户、百户、十户的形式把全体蒙古人组织起来,并封那些有功的那可儿们为千、百、十户长,进行统管,且其职位世袭,史称“莎余儿合勒”(即恩赐、分封之意)。这样,千户便成为蒙古社会最基本的行政军事单位。成吉思汗还把蒙古国的臣民百姓视为自己的家产,除自己直接管领一部分外,其余部民均分封给自己的母亲和兄弟子侄,他们每人得到若干千户,称为“忽必”(即份子)。
与此同时,成吉思汗还扩建了原有的怯薛(即护卫军),形成了一支由其直接掌管的万人常备军,其中包括千名宿卫士、千名箭筒士及八千名散班。这些官兵均由各级那颜及平民的子弟担任,他们自备马匹、武器和给养,而且还可以随身带有自己的“伴当”。因此,这些“怯薛歹”的身份往往高于在外的千户长。
此外,成吉思汗通过创制蒙古文字、设立也可扎鲁忽赤(蒙语“扎鲁忽赤”汉译为“断事官”)及编定大札撒等措施,建立起了大蒙古国的封建统治制度。至此,蒙古族的游牧宗法奴隶制开始向宗法封建制度转化和过渡。
公元1036年(宋开禧二年),成吉思汗被推为“汗”后开始了其内外征讨的步伐。当年,他即派兵征服了吉利吉斯及斡亦剌、八剌忽等森林部落。1211年,高昌畏兀儿和哈剌鲁贵族分别杀死西辽少监并遣使降附。1218年灭西辽,1227年灭西夏,1234年灭金,1247年招降吐蕃,1254年灭大理,1279年灭掉南宋。
在完成统一中国的同时,蒙古国亦曾多次西征中亚与东欧地区。1223年,灭亡花剌子模。1236年,成吉思汗长子术赤之次子拔都率军征服位于现今伏尔加河上游一带的不里阿耳部落和伏尔加河下游的钦察部。1240年,蒙古军征服斡罗斯(即俄罗斯),次年攻入波列儿(今波兰)、马扎儿(今匈牙利)境内后班师回返。1252年至1258年间,宪宗蒙哥派其弟旭烈兀率军西征,先后征服了木剌夷国(位于现今伊朗马赞德兰省)和在报答(今巴格达)的黑衣大食等两个伊斯兰教派的政权。成吉思汗及其后继者们经过70多年的征讨,建立起了横跨欧、亚两洲的大蒙古帝国。
蒙古大帝国的建立过程,同时也是宗法封建制逐步形成的过程。成吉思汗直接掌管位于漠北中心地区(即土拉河、克鲁伦河、鄂嫩河三河之源一带)的领地,其东面从鄂嫩河、克鲁伦河中游迤东是成吉思汗四个弟弟的封地,这四人即史称“东道诸王”的哈撒儿、合赤温、别里古台和铁木哥斡赤斤。成吉思汗的三个儿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史称“西道诸王”)被分封在阿尔泰山及其迄西地区,幼子拖雷则继承直属于他的牧地和民众。
这种东、西道诸王与匈奴族左、右贤王的设置极为类似。“西道诸王”的封地在西征的过程中不断扩大,后来形成了三大汗国(即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和窝阔台汗国)。拖雷第三子旭烈兀征服木剌夷和报达之后,又建立了一个大汗国——伊利汗国。这四大汗国名义上直属于蒙古大帝国管辖,号称蒙古大帝国之宗藩,但由于四大汗国的内部又实行亲属诸王的分封分治,因此它们实际上是一个将氏族血缘组织与地缘性的军事行政组织结合并逐渐向地缘性的行政组织转化的政治联合体。在这个联合体中,成吉思汗推行了颇似于西周时期的宗法分封制,他以直系子孙为宗藩来统治各大汗国,并借宗法上的尊卑、亲等和隶属制度来巩固对被征服地区的统治,从而使其宗法统治与行政、军事统治趋于合一。
1260年3月,忽必烈即位,此后采用汉制建立政权。1271年建号“大元”,以中原正统王朝自居,但“大蒙古”之号终未废除,故他名义上仍为整个蒙古国的大汗。1279年灭亡南宋,建立起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之后,蒙古社会已正式完全转变为宗法封建制社会。
总之,古代蒙古的宗法统治经历了一个较为明显的转变过程。蒙古族的祖先室韦一达怛西迁至蒙古草原地区并由“古列延”集体游牧方式转变为“阿寅勒”个体游牧方式后,其社会逐渐从氏族制社会过渡到阶级社会;合不勒汗建立起蒙古部的初期国家政权后,蒙古社会进入了游牧民族的宗法奴隶制阶段;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后,蒙古社会由游牧宗法奴隶制过渡到宗法封建制,这个过程直到元朝建立后方才完成,亦即元朝建立后蒙古社会已完全正式步入宗法封建制。
[收稿日期]2003-04-10
标签:成吉思汗论文; 蒙古军队论文; 蒙古文化论文; 中国古代史论文; 氏族社会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历史论文; 元朝秘史论文; 突厥论文; 旧石器时代论文; 新石器时代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