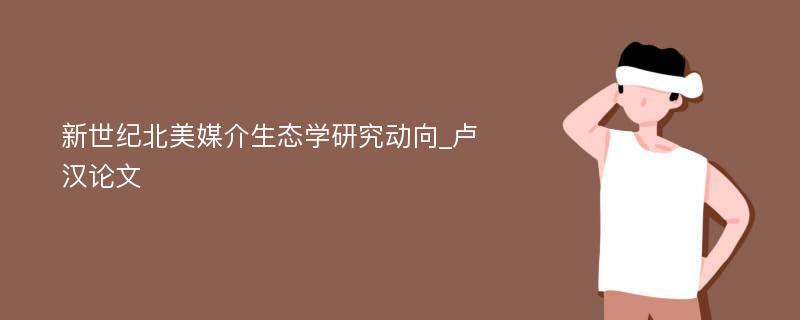
新世纪北美媒介生态学研究动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美论文,新世纪论文,生态学论文,媒介论文,动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媒介生态(Media Ecology)这一概念由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在1970年最早提出,次年他在纽约大学又创建了媒介生态学科。三十多年来,该学科吸引了大批的研究者,也培养出大量的研究人才。
这是一个涵盖广泛的研究领域,研究成果颇多。本文以美国媒介生态研究会(The Media Ecology Association,简称MEA,成立于1999年)本世纪以来的研究为主要线索,发现近年来北美媒介生态学研究具有如下特征:
第一,重视媒介生态学理论建构,追溯媒介生态学理论源起、探讨媒介生态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
第二,注重研究媒介与社会的关系,尤其是新技术、新媒体给社会文化以及宗教、艺术等领域带来的影响。
第三,该学科还是一个处于发展中的领域,从理论建构与研究视野来看都是如此。
一、媒介生态思想研究
本世纪以来,媒介生态研究者们非常注重媒介生态学学科理论建设,许多学者在媒介生态思想研究和媒介生态的理论资源、理论视野上投入了相当多的精力。关注最近几年MEA年会的文章可以发现,在媒介生态思想研究方面主要有两大学派比较值得关注:一是多伦多学派的理论,一是芝加哥学派的理论。
(一)对多伦多学派的追溯
出于对技术的关注,媒介生态研究者大多把刘易斯·芒福德、哈罗德·伊尼斯或麦克卢汉作为他们的鼻祖,今天媒介生态研究的纽约学派基本上继承了多伦多学派的衣钵,因而追溯媒介生态起源的路子基本上在多伦多学派这条线上滑行。
在MEA第三届年会(2002年)上,学者Lance Strate在题为《作为学术活动的媒介生态学》的报告中追溯了媒介生态学的起源:他认为1968年尼尔·波兹曼就提出了“什么是媒介生态学”的问题,至今人们仍然在探索这个问题。波兹曼将媒介生态学定义为“把媒介作为环境的研究”,而MEA的学者们则认为,媒介生态学是对符号、媒体与文化之间及内部复杂关系的研究。
Paul Levinson在《麦克卢汉与媒介生态》一文中认为,麦克卢汉对于媒介生态学的贡献就像氧气对于水的形成的贡献一样。如果没有麦克卢汉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著作,就很难理解以传播为媒介的人类社会的多样性与广泛性如何得以形成。他认为,媒介之于社会,就如同麦克卢汉之于媒介生态学;波兹曼也受到了麦克卢汉的影响,因此,整个媒介生态研究领域的学者都可以称之为麦克卢汉的学生,整个媒介生态学领域的研究都可以看作其思想的延续。在他看来,多伦多学派的研究本身就是媒介生态研究的一部分。
作为媒介生态学的研究者之一,Donald A Fishman在《重新思考麦克卢汉:对一个媒介理论家的思考》一文中也认为,麦克卢汉对媒介生态运动的影响是巨大的,他对传播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他向世人宣布了媒介的多种影响,提出了媒介变革如何导致社会性质变化的问题,他认为传播方式从口语到印刷媒体到电子媒体的变化是具有挑战性的,他关注技术更新(如电报,电灯,打字机等)的意愿使得许多学者重新关注那些被认为已经过时的话题。麦克卢汉的思想最近重新流行是因为他把研究重点放在了传播技术对社会变革的作用上,尤其是在这样一个大众媒介技术迅速变革的年代,麦克卢汉的思想显得更加有预见性。
在MEA首届年会上(2000年),尼尔·波兹曼做了题为《媒介生态学的人本主义》的发言。他肯定了杰奎斯·阿罗尔、麦克卢汉、阿瑞克·哈伍罗克、苏珊·朗格等人对媒介生态学的理论贡献,但他不认同麦克卢汉对于媒介技术中立的不加评判的态度:麦克卢汉认为把过多的时间与精力放在研究媒介带来的好处与坏处上,就会偏离对媒介本身的理解。而波兹曼认为,媒介生态学这一研究领域的开创本身就是出于道德的因素:开创这一研究领域的目的就是为了研究媒介生态是否以及如何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好处或坏处。他认为,除非放在道德的语境中,否则媒介研究毫无意义。在这一点上,他赞同刘易斯·芒福德和杰奎斯·阿罗的观点。他关心的问题是,在什么程度上媒体影响了人类理性思维的运用与发展?媒体在多大程度上对人类的民主进程起到了推进作用?在什么程度上新媒体给我们提供了接触更多有意义信息的通道?在什么程度上新媒体提高或降低了我们的道德感和我们的良知?通过阐述对媒介生态学的观点,他试图让人们把目光投向“人类何以生存”以及在人生之旅上人们如何做得更有道德等问题上。
(二)对芝加哥学派的重视
在媒介生态理论研究中,芝加哥学派的“符号互动论”显得相对比较边缘,没有形成主流,但在部分媒介生态研究者的眼中,这一视角已经开始出现。
Susan Barnes在《媒介生态与符号互动》一文中探索了乔治·赫伯特·米德在媒介生态研究中的作用,并从个人交往的角度研究了米德与媒介生态学的关系,包括米德的“自我”概念、符号互动理论以及符号互动论与媒介生态的关系。他认为,媒介生态学者与符号互动论者都对传播过程中的符号系统感兴趣,但由于媒介生态学者对技术感兴趣,人类交往中的信息交换很少被他们研究。随着因特网的普及,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都发生在媒介化环境中,面对面的交流与媒介化的交流都涉及符号互动。从媒介生态学的角度来看,符号与符号互动的环境都将影响人们对信息的理解。符号互动论者显然把人们的意图和行为作为他们考察的中心,当把研究的重点由技术转移到人,米德的理论就可以被用来更好地理解人们如何通过网络向他人展示自己。当把符号互动理论运用于媒介生态研究,媒介生态研究者就应当考虑媒介环境、技术约束和传播者阐释信息的方式。由于真实身份与网络身份的隔离,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展示自己,这是网络时代的重要特征,这一特征影响了传播者传播和交换信息的方式。作者认为,研究这种现象,媒介生态学者可以以米德的符号互动论为基础。
Janet Sternberg在《媒介生态研究的阴与阳》中用中国道教中的“阴”和“阳”来暗喻媒介生态研究中的两种对立的传统:“阳”是指把媒介作为环境进行研究,关注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阴”是指把环境作为媒介来进行研究,关注自我传播。近年来,由于缺少两种研究传统的整合,媒介生态研究中不平衡的趋势在抬头:媒介作为环境的研究掩盖了环境作为媒介的研究,这对该研究领域的整体性是一种损害。通过展示两种研究的不平衡及其带来的后果,作者认为,为了实现该研究领域更好的平衡,应当寻找长期以来被忽略的“阴”的一方的学术源头——这一源头实际上指米德的符号互动论——给这一分支更多的探索和关注,整合这两方面的研究。
Steve Bailey的《我与媒介:新米德观对理解媒介化社会环境的贡献》探索了长期以来被忽视的米德的追随者们对当代媒介,尤其是个人与媒介化环境之间关系的研究。他认为,新米德传统强化了米德提出的一些核心概念,这对更好地理解媒介生态和当代社会环境有着重大的意义。文章对该学派对媒介研究和媒介生态研究的广泛贡献进行了研究。
(三)其他研究视野
除了对这两大学派理论的运用外,媒介生态研究者还在试图开拓更广泛的研究视野、借鉴更多的研究方法,如批判学派的理论,行为科学的方法等。
有学者认为,媒介生态学研究媒介环境和技术的影响,而行为科学研究群体动力、组织变化、社会变化的理论与实践,把这两个领域联系在一起,有助于在我们日益技术化的社会中提高引导企业与社会变化的意识和行为,这种结合有利于使人们从概念与经验层面更好地理解广泛的媒介和技术进步以及个人、组织与社会的变化。
Paul Grosswiler在《于根·哈贝马斯:一个媒介生态学家》一文中认为,影响媒介生态学发展的技术与文化学者为媒介生态研究的广泛性与多样性提供了证明。提供这一视角的学者不仅包括伊尼斯、麦克卢汉、瓦尔特·温、波兹曼、詹姆斯·凯瑞、乔希瓦·麦克瓦茨等人,还包括一些跨学科的学者,比如杰克·古蒂、阿瑞克·哈瓦洛克、刘易斯·芒福德、杰奎斯·阿罗尔、伊丽莎白·艾森斯坦等。总之,媒介生态学综合了很多学者的研究思想,这些学者都对媒介与人类社会的关系给予关注,包括科学、哲学、社会学等学科。这篇文章将法兰克福学派晚期的学者——传播学者哈贝马斯也纳入了媒介生态学者的范畴。文章探讨了媒介生态、媒介环境与哈贝马斯的著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提出的“公共领域”的概念之间的关系,认为二者有一些共同元素;将媒介生态学的概念与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的概念进行对比后,作者认为媒介生态学对技术、文化、历史的研究可以参考哈贝马斯的观点。
二、媒介与文化研究
媒介与社会的关系也是近年来媒介生态学研究的重点之一。媒体与文化、宗教、道德、艺术、历史等的关系都成为媒介生态学者研究的重点。与此同时,对于国内学者关注的新旧媒体及各种类型的媒体之间的关系,他们也给予了一定的关注,在此不做赘述。
Stephen Biggs在《地球村与城市乌合之众:文化,自我构建与网络》一文中认为,现代传播技术如因特网已经打破了地域疆界,模糊了文化之间的差异,引发了人们从心理上进行自我构建的问题。文章以全球化的网络为文化背景,阐述了网络作为一种传播和交流手段的文化意义、个人意义和心理意义。网络是否促进了人们的个人主义倾向和相互依赖性?这是文章研究的一个主要问题。文章采取心理学的文化研究视角,即把人类的自我经验和感知与文化联系起来。作者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想要把网络文化与其对网民的影响联系起来,就必须采取这样的视角。最后,作者认为,新技术给社会和文化带来的影响是复杂的,需要进行大量深入的研究,思考如何使新的传播技术成为一种文化的媒介,而不是一种个人媒介,这一点非常重要。
Janet Sternberg在《实质上的不当行为:网络环境中行为规则的破坏》一文中认为,人们在虚拟空间中交往时,有的人能遵守或强化既有的文化规范,有的人则打破文化规则,产生不当行为。文章阐述了网络上不当行为的类型,被打破的规则的种类以及网络上人们对这种不当行为采取的行为与态度。作者认为,为了准确了解网络交流和交往的实质,就必须对网络不当行为有清晰的了解;通过研究人们在网络环境中制定、打破并强化规则的行为,能提高我们对符号环境与当下现实环境、线上的网络社区和线下的传统交往的理解,这就是文章的意义之所在。
Jean-Paul Fourmentraux在《网络艺术,艺术家和电脑程序师:分享创意》一文中认为网络艺术品不再是一个作为成品的物体,而是一个有机的过程,一个集体的、开放的、互动的过程。由于技术复杂性的提高,艺术设计需要更混杂的技术。为了创作受欢迎的作品而和电脑程序师进行必要合作给艺术创作的现状和艺术创作者本身都带来了很大的变化。文章对一个艺术家和一个电脑程序师之间合作的案例进行了文化分析,目的在于理解共同设计的过程,创作者之间的协商以及艺术品本身的普适性。通过分析媒体技术、媒体间工具和交流的作用,作者把重点放在了当创作过程被改变的时候,创作人员任务的分配和功能的定位。作者认为,在合作的边界及艺术创作者的功能与作用的不断变化中,艺术品的形式与意义得以形成。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艺术家和电脑程序师之间的沟通、协调与最后达成一致对作品的重建作用。
另一学者在《关于日本的媒介话语:历史教科书在朝鲜的争议》一文中认为大众传媒的一个功能就是记录、解释民族历史上重要的事件,帮助人们形成所谓的“集体记忆”。大众传媒为记忆提供了内容和形式,也为与记忆相伴而行的历史话语提供了场所。文章通过对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朝日两国媒体报道的话语分析,讨论两种不同的媒体话语如何形成了日本在当前的社会语境中的“他者”形象。
Kevin G.Barnhurst, John Nerone在《报纸的形式:对报纸作为环境的思考》中将人类经验分为从微观到宏观四个层次的理论(从直接经验到通过组织、团体与他人交往到广泛的意识形态领域)探讨了在美国历史上报纸作为环境对各个层次的影响,认为媒介不仅是一种信息传递的系统,更是一种环境:我们不仅记得事件,而且记得事件在媒体中是如何呈现的;当记忆随着时间流逝变得模糊,留在脑海里的就是事件所呈现出来的模式——即报纸所创造的环境,在那个环境中我们经历了哪些事件。
综上所述,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学科,媒介生态学一方面在学科建构上继续开拓,另一方面也运用从媒介生态学的角度对媒介技术与文化的关系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在新的媒介技术不断涌现的媒介环境与社会语境下,这一学科显示出巨大的活力。总体来说,虽然研究对象广泛,但其研究视野还相对狭窄,有待进一步探索和开拓。
